《译林》杂志四十年通俗小说的启蒙之路
2019-07-22毛翊君
毛翊君
如今,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回忆起来,还记得自己当年在《译林》杂志上看到《尼罗河上的惨案》时,有多么痴迷,甚至把印有小说的那些页码撕下来带回家保存。
那是1979年的《译林》杂志创刊号。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正是当时热门电影原著的译本,讲的是一位同新婚丈夫蜜月旅行的女人在尼罗河上的游艇中被枪杀,价值5万英镑的项链同时失踪,接着又有两人在船上接连死亡,一位侦探随后找出了令人意外的真凶。杂志因此获得60万的销量,也招来上级领导认为选题“堕落”的批评。
这份杂志最初是季刊,《吕蓓卡》《音乐之声》《教父》《沉默的羔羊》等多部国外流行小说让读者如获珍宝。它历经了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的拓荒,它不只看重那些国外的纯文学作品,也因大胆引进流行文学和侦探、悬疑小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
四十年后,李景端在南京的家中,见到准备上任的译林出版社第五任社长。这位85岁的《译林》杂志创始人提醒,“要有融媒体意识,不然将来要被AI淘汰了。”
外国通俗小说拓荒
1979年,江苏省出版局接到江苏省委要求,要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时任出版局局长高斯把任务交给了编辑李景端。
接下任务后,李景端考虑到,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难免涉及政治问题,不好把握。如果在杂志上介绍外国文学,则有不小空间。
1949年之后,中国对国外作品的翻译和引进,主要集中在苏联文学方面,其余西方文学作品几乎是空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以此走出思想禁锢。此时,全国的外国文学杂志——北京有隶属社科院的《世界文学》,上海有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其他地方则是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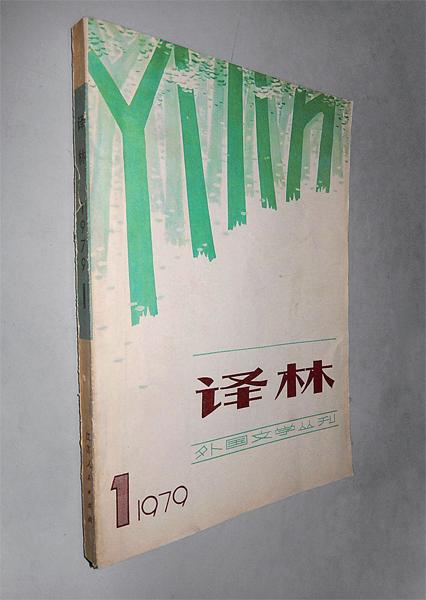
《译林》创刊号。
李景端觉得《世界文学》的内容过于严肃,《外国文艺》则过于新奇。他不是学外国文学出身,反而没有束缚,从读者角度想,觉得吸引人的才有生命力。杂志的定位慢慢浮现,要有助于大众了解国外当今的文学创作情况,选择能够展现外国现实生活的通俗文学,介绍流行的作家和作品。“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最后定下的宗旨。
一天,李景端和古籍编辑孙猛聊天,对方无意中冒出“译林”这个词,李景端一下想到枝繁叶茂的景象,觉得用作刊名很好。就这样,《译林》编辑部成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下设部门。
最初,杂志只有李景端和新来的编辑金丽文两人。李景端负责向北京组稿,金丽文负责南京和上海。当时,英国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正火热上映,编辑部得知上海外语学院有位英语教师正在翻译电影的原著,金丽文便上门约稿,最终小说刊载在创刊号上。“很偶然,当时没有考虑这是侦探小说,也没想到会惹来麻烦。”四十年后,李景端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当时的创刊号16开、240页,定价1元2角,交给新华书店零售。20万册几天便脱销,立马又加印了20万册,很快再次卖完。新华书店要求再加印40万册,但因当年纸张供应紧张,最终只再加了20万册。
新华书店不能办理长期订阅,很多读者只好汇款到编辑部邮购。头两期,邮局送到编辑部的汇款单装在大邮袋里,一次好几袋,邮局员工为此加了几天夜班。而李景端后来得知,当年黑市上的《译林》每本卖到了2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
这引来时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志的批评。1980年4月,冯志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对《译林》杂志刊登的《尼罗河上的惨案》《钱商》《医生》《珍妮的肖像》,和浙江出版的《飘》发出责难,认为“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希望出版界不要趋‘时媚‘世。”之后,胡乔木将这封信加上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要求“研究处理”。
最后,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表态,介绍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学没有错,有责任由出版局党组承担。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艺实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责任最终没有再被追究。
包括钱钟书在内的编委会
李景端此前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杂志的选材和翻译都是隔行的事儿,只能去请教专家。

1997年5月,李景端(左)在北京医院探视冰心。图/受访者提供
他曾在报纸上看见,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马上写了封信,希望对方给予家乡创办的新刊物一点指导和帮助。没想到,得到了回信肯定,戈宝权寄了自己翻译的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诗,提供给《译林》创刊号。
李景端因此想打造一个高水平的编委会。1978年,李景端参加广州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多位英语界专家现身小组讨论会。他就想借机邀请诸位名家。
李景端做了功课,读过北京大学杨周翰编的《欧洲文学史》,之后去北大拜访,他表示赞同杨周翰在广州会议上所说——国内曾经编写的外国文学史大多受到苏联“左”的思想影响,对西方许多作家和流派持批判否定太多,现在有必要重新認识。“不过,苏联文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存在已久,编文学史恐怕也不宜将其简单删去,可否把有过的不正确观点照写,但要加上新的认识和批判。”杨周翰一听,觉得有共识。第二天就向李景端详细了解了《译林》选材标准、当代与古典作品的比重、对性和暴力描写如何处理、译文质量如何把关等,最后同意担任《译林》的编委。
对于英国文学翻译家周煦良,李景端三次上门拜访。第二次见面,周煦良问到杂志如何在多种多样的西方通俗小说中做选择,李景端告知,主要放在社会小说、经济小说和法律小说上。再见面时,周煦良夸赞了杂志刊登的《吕蓓卡》。这是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在193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开篇就死去的神秘女性吕蓓卡为全文制造了悬念,这是一个嫁入山庄的女人,却因为和表哥偷情被丈夫枪杀,她的死亡在丈夫的第二任妻子进入山庄之后被揭开。周煦良在英国时就很喜欢这部作品,通过阅读两期《译林》的文章,他决定加入编委会。
当李景端得知文学翻译家戈宝权和钱钟书夫妇是江苏老乡时,他请求戈宝权出面邀请他们。钱钟书本已多年谢绝虚职的聘请,但被戈宝权游说成了。
然而,因为长期在文学上的禁锢,翻译界也有部分译者对《译林》选择外国通俗文学无法接受。《世界文学》原主编陈冰夷曾在跟戈宝权一同出差的途中,对坐在火车上看《译林》的戈宝权说,“你看,《译林》又在登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指的便是《吕蓓卡》。俄语翻译家孙绳武也曾对中国译协副秘书长林煌天说,译协要同《译林》“保持距离”。
当时,出版社没有翻译资源,作品都是靠译者自己去找。李景端只好从突破知名翻译家转向高校中青年教师。他去了趟上海,把目光放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寻求建立合作关系。他给出承诺,在校内成立杂志的联络组,先拨付1000元,供打印、邮寄等开支使用,给译者每人赠送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还能提供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专著以及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的机会。
曾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的张柏然、许钧,原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谭晶华,日后成为知名翻译家的杨武能、黄源深、张以群等,都是从当时的《译林》走出来的。
畅销书与版权
在杂志的选材上,李景端一直要求编辑,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来做判断。一些名气大的现代作品,怪诞难懂,都被李景端排除掉。惊险、悬疑、推理、爱情和商战是主要的选题方向。“大众喜欢现实胜过唯美,爱悬疑超过虚幻。”李景端这么觉得。
在《吕蓓卡》之后,《译林》又刊登了《天使的愤怒》《爱情故事》《音乐之声》《教父》。因为杂志比书便宜得多,通过杂志阅读一部长篇小说更实惠,《译林》因此保持了稳定的订阅量。
一次,李景端忽然收到上海寄来的日本小说译稿,一看内容,发现是之前在国内热映的日本电影《人证》的原著译稿。原著作者是日本有名的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作品之前在日本角川书店出版。其实,在电影于国内公映前,小说的译稿已经出来了。译者先前投给上海的出版社,但是被退了稿。最终才转投到《译林》。因为书稿太长,不适合杂志发行,李景端决定发行单行本,书名改做《人性的证明》,销量上百万册。
但1983年,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兴起。时任《译林》编辑部日语编辑竺祖慈记得,当时杂志刊登的日本短篇小说《我的茉莉子》,因为描述了日本的妓女生活,受到杂志非议。最终,编辑部自我检查之后说明,这篇作品是反映妓女一类下层人的悲惨生活,而没有色情描写。江苏当地主管部门也把《译林》杂志的文章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短暂的风波再次过去。
多位编辑回忆,编辑部的把关一直非常严格。包括石川达三的《破碎的山河》,刊登时也删去了露骨的描写。而选择这部作品,编辑部也有自己的考量,“家庭生活中两面派的伪君子面目,以及种种矛盾的心理,刻画细腻深刻。而这些能让读者对日本社会有认识。”李景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种认识体现在了刊登的多部作品里。在小说《白色巨塔》中,讲到了日本医院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后来,有医学学术组织一次买下了几十本。还曾有位农户从杂志的小说中得知,法国人喜欢吃蜗牛,写信到编辑部,要做进一步了解,想学会养殖蜗牛的方法。而常州有位办企业的人,看见《译林》一篇小说中讲到,西方的房子中有“蜂鸣器”这种东西,客人来訪时,可以先按动它发出声响。对方也写信到编辑部询问细节,因为想到可以制作此类东西,做出口生意。
1988年,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成立译林出版社,《译林》正式从江苏人民出版社独立出去,变成译林出版社的一部分。
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在此之前,《译林》刊载的那些译作都是没有版权的,而现在,李景端意识到必须要大胆买进版权。“今后出版实力之争,就是拥有版权之争。”
买版权的钱是个问题,李景端向江苏省出版总社申请设立“外国版权基金”。当时,出版界还没有这种习惯。1992年,著名悬疑小说《沉默的羔羊》系列版税率3%,系列中每本预付金不到1000美元。因为市场刚打开,“版权比较好谈,而且多数都在几百美元,不贵。”《译林》杂志原编辑施梓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杂志进入稳定期。曾有人提出要收购并改版为时尚杂志,也有人在纸质杂志市场和互联网的冲击下,想到要做综合文学类刊物,《译林》的多数领导还是坚持了最初的外国通俗文学方向,因为毕竟它是全国唯一以此为特色的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