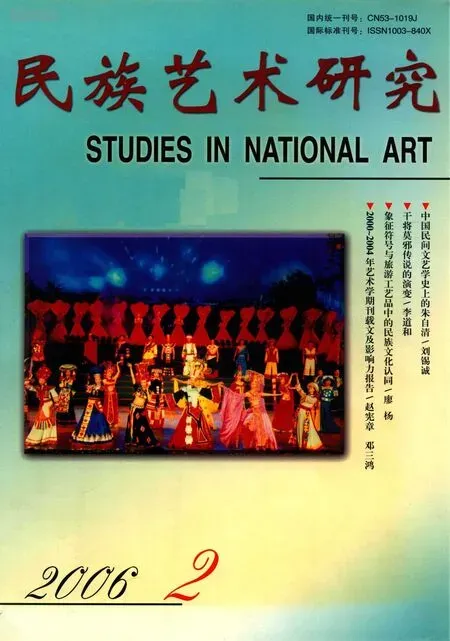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讨论的焦点与热点
2019-07-17方李莉
方李莉
一、学科的自觉与反思
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从成立至今也已走过了12年的风风雨雨,每年的学术年会都会出版分量很重的论文集和大量的译著与专著。这些论文和专著所形成的资料足以让我们去总结和反省学科所走过的发展之路。另外,201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年,而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发展也是由此开始。在2018年,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进行学科反思,开始有了学科自觉,并在追问我们中国艺术人类学应该做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在未来我们还需要做什么?这些追问意味着中国艺术人类学正在由快速发展逐步走向成熟。
这一年,方李莉在《思想战线》2018年第1期发表了论文《中国艺术人类学之路》,主要是对中国艺术人类学40年的发展之路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让我们看到:任何新的理论都是来自于新的社会实践,中国40年来的巨大变化,为中国学术理论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资源,尤其是艺术人类学,因为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艺术,在社会实践方面往往具有先锋性,其所具有的创造性精神往往是冲破旧藩篱的一种力量。为此,艺术人类学学者们所收集的丰富的田野材料和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实践,正在促使其本土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并汇集为一股推动中国学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同时在2018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上方李莉宣读了论文《建构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设想与实践”》,这篇文章首先从中国艺术人类学自身发展所经历的历史背景和国家社会实践,来确认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初心,进而来探讨是否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再进一步讨论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其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在论述中,方李莉认为,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一开始的切入点就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从认识“他者”的艺术,认识异邦的艺术开始的,而中国艺术人类学则是从认识自身的艺术开始的,是从反思和发掘自身的文化资源和艺术资源开始的。因此,其研究之路是在通过保护、发掘、认识自己的艺术和文化资源及脉络,去重构中国新的当代文化和艺术,既富有传承性又富有建设性。因此,其所论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实践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个中国学派,加入到世界学术的共同体中。
洛秦在《音乐研究》2018年第2期发表的《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一文则提出了艺术人类学的“中国经验”这样的论述。这一论述很重要,因为没有艺术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也就不会有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学派,笔者认为这是相辅相成的。他在论文中提出的“音乐上海学”里面不仅体现有“中国经验”,还有上海这样大都市所形成的自身经验,可以形成一个上海音乐学派。笔者相信,以后像这样有地方特色,有自身独立见解的研究会越来越多,并将汇集成一个中国学派的洪流。
孟凡行的《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一文,是从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角度做了一个深刻的反省与讨论。他提出艺术人类学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因此,学科属性很模糊,但在高校中,每一个学科都要找到一个明确的属性,才便于学科建设。于是,艺术人类学到底是人类学下面的门类学科,还是艺术学下面的或者成为艺术学下面的学科,这样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他认为,有关这个问题就研究的层面来谈,归属于哪个学科都是可以的,但是按照学科分类,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来讲,就必须要有一个站队。他个人认为,艺术人类学就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只是属于一个分支,但就艺术学的角度来看,其实属于一个层面,分支砍掉问题不大,但层面却是离不开的,因此,应该归属于艺术学,这样的看法别开生面。就学科来看,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主要是偏重人类学,但目前关心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并在实践中运用艺术人类学来讨论问题的,大多是来自艺术院校的学者,而且这一研究方法和角度纠正了传统艺术学的许多观念,的确成为艺术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孟凡行的观点的确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董波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第4期发表了一篇《今天需要什么样的艺术人类学——新时代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新的生长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她在论文中梳理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历年开会的主题,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始终是跟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来选择研究主题的,每一次国家提出的重大战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都是在积极参与,如非遗保护、传统文化复兴、振兴传统手工艺、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因此,这样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可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安丽哲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艺术与设计)》2018年第4期发表的《2006-2016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式与特征——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数据与文献为例》,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的各种数据以及历年论文为例,分析了近10年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5种主要研究范式,并用数据证明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者是以艺术类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为主要主体的,这决定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当前阶段的向度与特征,即多数研究以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艺术方面的问题,而非从艺术角度去探索人类学关注的问题。这样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非常重要,让艺术人类学的学者们对自己学科的发展路径、知识结构和研究目标有了一个清晰认识,从而可以更进一步地完成学科自觉性。
二、由关注“物”到关注“人”
通过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收到的论文,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开始由“物”向“人”的转化,而且,从开始研究人的外表到研究人的内心世界。如张士闪的《生计、信仰、艺术与民俗政治——胶东院夼村谷雨节祭海仪式考察》,通过对胶东院夼村人每年所举行的“谷雨节祭海仪式”的田野考察,提出了“基于生计、信仰、艺术等统合而成的民俗政治,是解读这一仪式传统的关键”的观点;同时认为,研究者需要在深度田野研究中体察民众主体意识,并结合国家历史进程与地方社会发展的时移势易态势予以分析,才有望获得真正的理解与阐释。通过他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民俗仪式的空间是可以改变的,仪式的程序也是可以改变的,仪式的主体参与者同样可以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内心深处的东西,也就是信仰,包括信仰的主体“神”,这是不可变的,若变了就不能成为仪式。还有它里面的那些仪式符号也是不可变的,仪式符号既是象征物,同时又可以给予人们单调的生活带来喜悦的艺术形式,而这样的东西也是不可变的。他的这一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表面的形式只是外在的可变因素,而只有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才是相对恒久不变的因素。
纳日碧力戈的《艺术与实效》一文指出:人本身是物的存在,随时为自我和他者生产着“物感”;艺术离不开“感官技术”,也离不开观众互动,更离不开文化解释和艺术思想。作品、观众、解释的结合产生实效,实效决定了艺术品的价值,这都是因为人是指导。如果人是指导,艺术是指导,那么人就是艺术,做人是一个制作和创造的过程,学习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身体力行的过程,根据实效自我评价、自我调整、自我实现的过程。这篇论文将对艺术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哲学的层面,并认为人和艺术是可以互换的,从某种程度来讲,人不仅创造了艺术,人自身也未尝不是一件艺术品。这一观点值得深思。
来自日本的杨小平博士的论文《艺术与和平——和平象征物的创造与社会意义》,用“和平鸽”和“千纸鹤”的象征意义,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国民的特性,也看到了艺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在民族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发言的主题是日本人怎么通过一系列的象征符号来平复战争的痛苦。也许是因为广岛的原子弹给日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战争就成为许多日本学者反复研究的主题。杨小平指出,在日本艺术中的“和平鸽”实际上是抚平战争痛苦的一个象征,而日本人喜欢叠的“千纸鹤”,也是因为千纸鹤代表健康,人们通过千纸鹤抚平对死亡的恐惧感,他的这一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象征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
罗易扉的论文《从物的工具回到人的本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通常我们很容易只是把人类学作为一种研究事物的工具,而她认为人类学研究回到人的意义本身非常重要。她提出的“启蒙现代性”和“温和现代性”让笔者比较感兴趣,“启蒙现代性”是一种知识精英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是作为人类学家,他和大众在一起形成的是相互学习和商讨的关系,是以一种平等的眼光和角度来实现的“温和现代性”,这样的讨论也是很有意思的。
在近期的论文中,有关以人为中心的讨论还有不少,如关祎在《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8年第6期发表的《作为社会存在的造物者——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手工艺者》,她将手工艺以及手工艺者放在文化整体之中进行考察,检视手工艺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手工艺及其从业者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社会功能以及经济功能等。
三、从历史文献、器物、图像的角度诠释
艺术历史的艺术资源是中国艺术人类学所要发掘的重要宝库,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历史一直没有中断的农业文明古国,并且远在2000多年以前的秦朝就有了统一的文字。连绵的历史文明不仅遗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图像资料,还遗留下大量的手工艺制品,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重要资源。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去重组和研究这些资源,毫无疑问会形成中国学派最有特色的一方面。在2018年艺术人类学的论文中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重要论文。如李立新的《鹿车考述》,其通过搜集来的中国古代器具史的资料,写成的一篇有关中国独轮车考,是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章。
像这一类的论文还有李金来的《神与物游:民俗文化对宋瓷艺术性生发的价值探析》,讨论了宋代民俗文化中火神与窑神崇拜、五行及道教思想、神仙信仰、饮食习俗及乡野俚俗传播四个方面对于宋瓷艺术性的影响,这是以前很少有的角度,非常新颖。还有孟蕾的《唐代陶瓷执壶形态演变研究》是将唐代陶瓷执壶形态的变化与唐代生活方式、执壶使用的操作行为以及饮食环境等建立联系,通过研究提供了当时重构生活场景、大众生活认知的科学依据,这都是以往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较少关注的角度。在孔含鑫的《云南师宗黑尔村新发现石寨山型古代铜鼓研究》一文中,以2005年在云南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发现的两面石寨山型古代铜鼓,论述了黑尔壮族先民以铜鼓祭祀农神、祈求丰年的神圣宗教仪式等,同时认为,铜鼓在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之间发挥重要的调适作用,也是铜鼓及其宗教信仰在南方边疆社会治理中的体现。
除了以上对古代器物研究的论文,还有对古代图像研究的论文,如何雅闻、罗晓欢的《“永恒”的演出——论四川地区清代墓葬建筑的戏曲雕刻》以大量田野考察为基础,从石头的纪念碑性、匠师雕刻技艺、墓主的主观意愿等角度进行了探讨,特别是传统工匠如何将即时性的舞台表演转向固化的雕刻图像,并实现作为墓主祈求“永固”的载体。这些墓葬建筑上的戏曲雕刻图像,不仅深刻地反映出墓主生前的喜好和其时戏曲演出的繁盛,更彰显墓主对吉祥寓意、自身德行和子孙教化的复杂语境。还有李浥的《安岳宋代菩萨造像:文化表征与历史记忆》, 李强的《宝鸡西山新民村圣母庙壁画与信仰的再调查》,李东风的《想象与事实——四川藏民居的艺术与宗教》,牛犁、崔荣荣的《族群认同与服饰选择——以屯堡与屯堡服饰为例》等都是通过古代庙宇、建筑、服饰上的图像研究,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古代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观念、乡土习俗的传统,如何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景象。
四、有关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研究
艺术人类学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在于其研究始终是跟随中国的社会实践,也始终是为中国的发展而做的研究。近期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是艺术人类学界所关注的一股潮流,从2016年开始由方李莉倡导和主持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论坛,每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承办。2017年出版了《艺术介入社会: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对话乡村建设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的论文集。与此同时,《民族艺术》2018年第1期发表了方李莉的《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论文的主要观点为:社会的转型常常会引发启迪人类心灵的文艺复兴,艺术介入社会建构,介入美丽乡村建设,是一场“中国式的文化复兴”的表现形式之一,而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意义在于通过艺术复兴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式样”,修复乡村价值,将“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推动“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的发展之路。
而后,在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年会上,多个学者宣读了相关的论文,如季中扬、康泽楠的《主体重塑: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重要路径——以福建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为例》一文,通过对山西许村和福建龙潭村两个以艺术介入的乡村建设所进行的对比研究,论述了艺术应该如何介入乡村建设的重要路径,其论述的观点和方法很有启发。其通过在许村的考察发现,许村模式的“艺术乡建”对乡村经济的长期性带动有限,是由于其“艺术乡建”的出发点并不完全是为了乡村,为了乡民,因此忽视了乡民的主体性。而龙潭村乡村建设观念的首要之务就是要让当地村民发现自身的价值。让他们通过艺术创作“专注自己,并认可自己的价值,由此逐渐表达自己生命的精彩。”这样的“艺术乡建”的宗旨既不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也不是为了艺术本身,更不是为了来自城市的游客,而是为了乡村,为了乡民。其认为,“艺术乡建”的关键就在于以现代艺术精神重塑乡民的主体性,促进乡民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精神汇通。
李祥林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艺术》一文,讨论了从现代社会的“去语境化”到后现代的“再语境化”过程中,乡村艺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与价值。在文章中其批评了随着城镇化快步推进,以“统一模式改造乡村”不断进行,构成“千村一面的现象”,为此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让农业更发展、农村更美丽和农民更幸福。既然如此,要做好“三农”工作,让乡村实实在在振兴起来,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美好生活,无论从物质还是从精神上讲,都不可不关注各个地方拥有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系统,不可不重视“在地性”乡民与乡村的乡土文化(物质的和精神的)及乡土艺术(传统的和现代的)。并指出许多传统的乡村艺术包括“傩”艺术遗产作为乡土资源被空前激活,正在构成新的乡土文化和乡村振兴的一股新的力量,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罗瑛的《民族艺术的认同空间:文化景观与地方表述》,论述了民族艺术是文化景观构建与地方性表述再生产的重要元素,其认为在这样的再生产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公开和不断扩展的法则,对世界文化多样性进行不断的新阐释。其认为,在视觉表象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现代性社会中,文化差异越大,地方性表述和族群性表述的需求就越重要,文化作为象征性生产机制的实践当中,文化景观、族群意识、地方标记与符号象征体系等的塑造,是区分人我的手段,也是民族艺术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它唤起了地方意象并表述族群身份认同,同时从中自证身份并获得本学科的认同空间。民族艺术在族群文化特性构建与诠释方面,形成一套直观而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它包括仪式、节庆、图像、形象、音乐、工艺、自然物等等,为洞见不同社会基本规律与族群欲求提供了丰富的途径。这样的观点使我们意识到,乡村振兴也包括了乡村景观形象和地方性表述的再生产,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艺术与乡土艺术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将也是属于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一部分。
还有王璇的《艺术人类学视角下“安居乐业”的乡村空间形态探析》也是从生活和人本层面考察了传统与当代乡村空间在追求“安居乐业”目标时两种存在形态的特点与比较,讨论了如何通过正确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使乡村空间形态更加符合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更加宜居。从而为乡村振兴出了有益的思考。东南大学的王廷信在《民族艺术》2018年第6期发表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体系建构》,文章中提到乡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基础性的关键作用,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乡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观点。其认为,在一些艺术形式处于凋零状态的情形下,如何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建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体系是一个关涉乡村生态的综合性问题。并指出,只有在梳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在乡村的生存现状、保护乡村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培育艺术创作队伍,结合相应的策略、机制、体制研究,才能保障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五、有关手工艺复兴方面的研究
手工艺复兴也是2018年艺术人类学所关注的重要研究,取得的相关成果也很丰硕,有荣树云的杨家埠年画研究,安丽哲的潍坊风筝研究,杨柳的云南新华村金属工艺研究,王永健的景德镇陶溪川研究,孟凡行的陕西凤翔泥塑研究,郭金良的景德镇老鸭滩瓷板画研究,李宏复的江苏镇湖刺绣研究,吴南的北京雕漆研究,韩澄的北京金属工艺研究,朱立叶的宜兴紫砂陶研究,洪梓萱的福建莆田仙游镇红木家具研究,邹龙洁福建莆田仙游镇木雕工艺研究等,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2018年陆续得到了发表。艺术人类学对手工艺的田野考察成果引起了《中华文化画报》的关注,于2018年辟出了一期题目为《中国传统手工复兴》的增刊,里面发表了以上这些学者们的田野考察的研究文章共14篇。这些研究都属于国家重点课题社会转型中的工艺美术发展里的子课题成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手工艺复兴的田野调查。这一课题于2015年立项,将于2019年结题,现在研究已接近尾声。
在这一研究中作为课题主持人的方李莉发表论文《生活革命与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新观察》,其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手艺中国”的概念,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其认为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国家,还是一个农工国家,也就是农业和工业并存的国家,当然这里讲的工业不是机械工业,而是手工工业。因此,中国不仅是一个乡土中国,也是一个手艺中国,这是中国的文化基因。基因的重要性就在于其始终会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在工业文明时由于机器代替手工,中国的手工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中国落后了。当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并向超工业文明时代转型时,在中国大地产生的一场手工艺复兴的潮流,就有可能让中国无论是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都获得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是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观的转变,这一时期人们的审美更加趋于个性化和情感化;其次,全球化带来的本土性反弹,使人们更加趋于从母体文化中吸取养分,并将其投射到自己的生活审美中。另外,由于中国的经济得到腾飞而产生了一个白领阶层和富裕阶层,这个阶层需要有一个新的文化符号来定义自己,于是充满着文化附加值,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情感的手工艺品,开始进入这一阶层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生活革命正在中国悄然兴起,方李莉将这场生活革命称之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其认为,如果说,缘起于14、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是从人理性的认识人自身开始的,那么这一场源自于中国的文艺复兴却是从重新认识和肯定自身的文化,复兴传统生活样态开始的。
传统工艺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在艺术人类学者关注这一研究的同时,民俗学界也开始与艺术人类学的学者们联手介入这一研究。2018年12月9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市场与能力:传统工艺当代传承关键问题”学术论坛在上海举办。会议邀请了来自全国12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余名专家学者和上海多所高校的研究生参与讨论。其讨论的主题是:随着我国新中产的崛起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影响,传统工艺有望成为新的生活时尚而走向复兴。面对新时代下由城市中产阶级主导的消费市场,传统工艺逐渐实现转型。传承人基于文化自觉及市场能力积极进行生产实践的更新,尤其是传承人联合企业、创意工作室、创意开发团队等新型生产模式,结合当代市场需求开辟创新路径的传承和发展模式。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做出哪些反应?在这次会议上,方李莉做了“传统手工艺复兴与中式时尚的审美转向”的主题发言。其指出,中国的审美转向面临两个特点:1.从崇洋转向崇敬传统文化;2.富裕阶层和白领阶层所拥有的文化符号不再是洋派的、西式的,而是中式的:古代的文物、本土艺术家的艺术品、中式的实木家具、中式的建筑、中式的服饰、中式的生活方式。时尚开始于一个新的和“自然的”生活,所有这些样式的存在不是人为意志决定的,它是一股时代潮流,也是值得人类学家关注的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六、前沿理论的探讨
这里的前沿理论探讨,指的是以往艺术人类学较少关注的新研究,这一研究有的还与国际的潮流有关系。第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艺术人类学对当代艺术的研究,这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开始。
2018年国际在这方面的研究,继出版于2017年的有(挪威)阿雷德·斯奈德主编的《全球性相遇中另类的艺术和人类学》(AlternativeArtandAnthropology:GlobalEncounters)[注]Arnd Schneider:Alternative Art and Anthropology: Global Encounters,Bloomsbury Academic,2017.后,2018年又出版了由维也纳人类学家托玛斯·菲利兹(Thomas Fillitz)和保罗·范·德·格利普(Paul van der Grijp)主编的《当代艺术人类学:实践、市场和藏家》(AnAnthropologyofContemporaryArt:Practices,Markets,andCollectors),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是其不仅关注到当代艺术的人类学转向,还把眼光拓展到欧洲以外的艺术领域。在阿雷德·斯奈德主编的《全球性相遇中另类的艺术和人类学》关注到了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不丹、尼日利亚、菲律宾等地的当代艺术,玛斯·菲利兹(Thomas Fillitz)和保罗·范·德·格利普(Paul van der Grijp)主编的《当代艺术人类学:实践、市场和藏家》一书,不仅关注欧洲艺术,更将眼光投向了巴西、土耳其以及亚太地区的艺术。
2018年刘翔宇将阿恩特·施耐德主编的《全球性相遇中另类的艺术和人类学》的前言抉择:世界本体论和当代艺术与人类学的对话翻译出来,被收集在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的论文集中。在这篇文章中最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是:一方面,许多艺术家(西方)已直接接触到西方之外的他异性和各种知识,这种知识的接触将会改变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学的理论要重新构建,并对艺术品的构思和制作产生影响,当然这些影响不是表现在田野调查的现场周围(或是在民族志表演活动)中,而是在艺术家工作室(也就变成了实验室)并最终在展览空间和艺术界中物化的艺术形式中。[注]Douglas R. Holmes and George Marcus, “Para-Ethnography,”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ed. Lisa M. Given (Thousand Oaks: Sage, 2008), pp.596-7.这样的结果将导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进入田野,成为准人类学家,同时人类学家也可以介入到艺术创作中成为准艺术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考。另一方面,他提出了有关艺术“当代性”的概念问题,从他者的视角看,西方艺术又如何是当代的(与他者同时发生)?或者其他地区生产的艺术又如何“是当代的”?是不是“当代艺术”只是一种有着历史偶然性、属于特定时代(或特定历史时期)的西方艺术形式呢?为了讨论这一问题,在他的这本论文集中,收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类学家共同完成的有关当代艺术方面的论文,包括方李莉的有关798艺术区的论文也被收入其中。
美国华人作者王爱华(Aihwa Ong)在她的《马可波罗忘了:当代中国艺术重建全球》一文中提出了“全球的非欧洲式重构”的观点,并指出:“未来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未来不再由唯一的历史观来预想。”[注]Aihwa Ong, “What Marco Polo Forgot: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Reconsfigures the Global,” Current Anthropology, 53(4)(2012): 471-94 (including comment section), ppl 483, 472.特里·史密斯也在其《当代艺术:超越全球化的世界潮流》的文章中认为“全球化的霸权作为一种世界现象”已经被打破,全球化不能替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注]Terry Smith, “Contemporary Art: World Currents in Transion Beyond Globalization,” in Hans Belting, Andrea Buddensieg, and Peter Weibei (eds), The Global Contemporary and the Rise of New Art Worlds (Cambridge, MA:MIT Press, 2013), p.186.在这里史密斯看到的不是只有一股全球化力量在影响当代艺术,而是各种不同当代艺术的同时并存,每种当代艺术都有其自身的审美标准。[注]Terry Smith, “Contemporary Art: World Currents in Transion Beyond Globalization,” in Hans Belting, Andrea Buddensieg, and Peter Weibei (eds), The Global Contemporary and the Rise of New Art Worlds (Cambridge, MA:MIT Press, 2013), p.188, my italics.因此,即便是当代艺术也不只有一种标准,其和传统艺术一样,存在着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阿恩特·施耐德提出,“我们必须要认可差异、尊重彼此。”“必须承认差异的同时代性。”他的这些观点告诉我们,“当代艺术家与土著艺术家的合作超越了传统的边缘与中心、西方与非西方、民族国家与土著团体或其他二元模式。”[注]Mark Watson, “Centring the Indigenous’: Postcommodity’s Transindigenous Relational Art,” Third Text, 29, (3)(2015): 141, 142, 144.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全球化当代艺术场景。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在中国这样的案例也很多,如杨丽萍的《云南映象》、谭维维的“华阴老调一声喊”、谭盾的《女书》等都是当代艺术家与民间艺术家的合作,在2017年的中国策展人邱志杰以“生生不息”作为主题,通过中国古代神话,采用传统的民间技艺,推出了具有中国哲学思想的当代艺术。在他组织的创作队伍中不仅有当代艺术家,同样还有传统的民间艺人。
李牧在其论文《“人类学转向”下的当代艺术的文化逻辑与民族志实践》也关注到了这一相关理论,他在文章中引用了西方人类学家的观点,指出人类学家研究的“他者”及其文化,正在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不断涌入西方世界,成为自身或者当地艺术家可资利用的创作材料和灵感来源。它们通过被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挪用(appropriation)和杂糅(hybridism),作为具有能动性(agency)和文化附加价值(value)的“物”,参与了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作品的生成和生产过程。[注]参见Schneider, Arnd. 1996. “Uneasy Relationships: Contemporary Artists and Anthropology .”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1, no. 2: 183-210; Schneider, Arnd and Christopher Wright. 2006. Contemporary art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Schneider, Arnd and Christopher Wright. 2010. Between Art and Anthropology: Contemporary Ethnographic Practice.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Schneider, A., and C. Wright, eds. 2013. Anthropology and Art Practice. Oxford: Berg; Strohm, Kiven . 2012. “When Anthropology Meets Contemporary Art. Notes for a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ve Anthropologies 5: 98-124.也就是说,艺术人类学家早期所关注的、脱离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而独立存在的纯粹“他者”,已不复存在。[注]Foster, Hal. 1995. “The Artist as Ethnographer?” In The Traffic in Culture: Refiguring Art and Anthropology, edited by George E. Marcus and Fred R. Myers, 302-30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因此,艺术人类学研究正在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这一转型涉及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艺术人类学的艺术民族志的实践中,将进一步思考如何从学理上将传统艺术研究者所极为倚重的独立的审美观照和审美经验,放置于历史、文化变迁、文化交换和全球化过程等更为宏大的话语情境中进行理解;另一个方面是人类学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这一影响使当代艺术界出现了一个“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 turn)或者“民族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注]参见Desai, Dipti. 2002. “The Ethnographic Move in Contemporary Art: What does it Mean for Art Education?”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A Journal of Issues and Research 43, no. 4:307-323; Coles, Alex, ed. 2000. Site-Specificity: The Ethnographic Turn. London: Black Dog Publishing; Rutten, Kris, An Van Dienderen and Ronald Soetaert. 2013. “Revisiting the Ethnographic Turn in Contemporary Art.” Critical Arts 27, no. 5: 459-473; Siegenthaler, Fiona. 2013. “ Towards an Ethnographic turn in Contemporary Art Scholarship.” Critical Arts 27, no. 6: 737-752. 当然,与艺术界的“人类学转向”几乎同时进行的,是人类学界在民族志研究中出现的“感官转向”(sensory turn)。所谓“感官转向”,是指人类学者开始更多地运用艺术手段(如拍摄民族志电影)去呈现和书写其田野经验和进行民族志思考。关于人类学的“感官转向”,可参见Pink, Sarah. 2009. 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 London: Sage;Schneider, Arnd and Christopher Wright. 2006. Contemporary art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以及张晖《视觉人类学的“感官转向”与当代艺术的民族志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8期)中的相关论述。的现象,这一现象是指“艺术家透过人类学视角(anthropological gaze)”,[注]所谓人类学视角,即对异文化和他者文化传统和生活世界的关注。有时甚至直接采用田野调查等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完成其艺术作品或者进行相关的艺术实践;最后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在“人类学转向”的影响之下,西方学者与艺术家观看“他者”艺术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而造就了新时代全球艺术的崭新格局与样貌,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将这一变化称为从“世界艺术”(world art)向“全球艺术”(global art)的转变。[注]Belting, Hans. 2013. “From World Art to Global Art: View on a New Panorama.” In The Global Contemporary and the Rise of New Art Worlds, edited by Hans Belting, Andrea Buddensieg, Peter Weibel, 178-18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本文原文为德文,由伊丽莎白·沃克(Elizabeth Volk)译为英文,后由陈娴、华代娟从英文译为中文,发表于《美术文献》2014年第2期。本文写作参考的是沃克所译的英文版。以下关于汉斯·贝尔廷的讨论均出自此文。关于贝尔廷所谓“世界艺术”和“全球艺术”概念的定义和主要特征,笔者根据其分散于文章各处的论述进行了概括和综合,为避免累赘和过度繁琐,本文将不一一列出原文对应之处。李牧的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转向,而中国的当代艺术界虽然也出现了如此的现象,但中国的艺术人类学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这方面的艺术民族志就更少。在2018年的论文中,有一篇傅祎与廖澄合作的民族志论文《当艺术家遇见民艺大师》记录和讨论了这一问题。
2018年值得探讨的前沿研究还有关于虚拟民族志的问题。王可在其论文《非线与深浸——虚拟民族志的双重性刍议》中别开生面地将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也就是在虚拟空间中研究数字化艺术。其定义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是指:针对虚拟空间里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和虚拟社会/社区展开的民族志研究。它以计算机和数字网络为媒介,以虚拟田野的行为体验为基础,具有多路径、非线性叙事的超文本特征,属交互的、沉浸型民族志。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即:“虚拟艺术人类学”,他认为虚拟艺术人类学是从人类学的视角阐释虚拟艺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虚拟艺术,研究虚拟艺术世界中人(艺术家与受众)、物(艺术作品)、事(艺术行为与艺术事件),并从中揭示内在关系和整体关联。他的这一研究让我们看到,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开始从实体空间进入到虚拟的空间,人类也开始从“实体的生存”转向“数字化的生存”。未来,我们在实体空间里面有一个具体的人,在虚拟空间里面还有个“替身”,所以我们为自己建构了一个“彼岸”,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可以进入的“彼岸”,那就是一个“数字化的彼岸”。在论文中,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术语,比如说“互动”、“选择”、“反馈”、“交替”、“流变性”、“冲浪”(surfing)、“导航”(navigation)和“潜水”(diving)拼贴、超文本、非线性叙事等。同时他还就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将我们所讲的“深描”,加上了“深绘”“深浸”等关键词。深浸这个词很有意思,是要将人浸透到虚拟世界中去。还有看世界不光是用目光来看,还可以通过镜像来看,通过镜头来看等等。这些新的概念,新的词语都扩展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
王永健的论文《后工业社会城市艺术区的景观生产与景观消费——以景德镇陶溪川为个案的调查与研究》也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性。他认为,在工业废弃地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城市艺术区是后工业社会背景下的一种景观生产,是对工业遗产资源的再利用。这些城市艺术区往往现代气息浓郁,成为当代艺术与时尚的展示场,是城市最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将艺术景观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艺术景观作为一个消费对象来研究和考察,拓宽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
七、艺术民族志的记录与研究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主体就是做田野、撰写艺术民族志,这样的工作在2018年仍然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主流工作,学会同年出版了第一部专门讨论艺术民族志的文集《写艺术——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由方李莉主编,内容有六个方面:艺术民族志写作方法探讨,城市艺术民族志写作,舞蹈民族志写作,音乐民族志写作,美术民族志写作,非遗、民俗及其他,选入了30余位具有代表性作者的论文,对于年轻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队伍来说,这部文集的出版具有一定的典范性和引导性。
另外,从2018年发表的论文,包括在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上收到的论文,最多的还是反映不同地域和民族的艺术现象的民族志。在这些论文中,学者们对不同地域的不同艺术现象、艺术仪式进行了描述,记录和呈现了中国多元的地方艺术和民族艺术的发展现状,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描述不同少数民族艺术的文章,如申波的《“地方化”语境中的“象脚鼓”乐器家族释义》,牛乐、刘阳的《洮河流域“拉扎节”田野考察》,刘雨的《医巫闾山满族剪纸的艺术特征与创新发展——张侯氏剪纸艺术研究》,刘鑫林的《关东满族刺绣枕头顶图案研究》,王晓珍的《文化交流中的新疆库车建筑彩画》,袁晓莉的《刻木为契:黎族物化的原始记事符号研究》,张红梅的《海南黎族传统手工艺中的原始宗教信仰研究》,向芳的《艺术的神话背景— —以壮族铜鼓、服饰为例》等,这些都是一些极其珍贵,非常值得去记录和研究的民间艺术现象。
还有一些艺术民族志研究自觉地将非遗保护与传承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因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这些民间艺术事项基本上都是当地的非遗项目,因此,如果我们是动态的研究和记录这些艺术事项的话,就不得不讨论这方面的内容。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很多,如黄丹的《沪剧保护与传承的艺术人类学思考》一文就提出,以往非遗保护关注的往往是非遗项目本身,但对其所存在的社会语境和整体环境关注不够,任何艺术都是社会的产物,都不能孤立的存在,因此我们对沪剧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土壤;黄龙光、杨晖的《非遗视野下彝族花鼓舞保护的多主体协作》,以非遗项目“彝族花鼓舞保护工作”的考察为案例,提出彝族花鼓舞传统内源性传承式主体保护模式已消失,加上长期以来彝族花鼓舞仪式、套路与动作等本体出现不同程度变迁,新形势下亟须建立能沟通地方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三方资源的多主体协作的保护机制。吴衍发的《皖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生成性分析》,其试图通过对皖北非遗分布概况进行梳理研究及概括分析,从而揭示出非遗特征及其生成原因,有助于皖北非遗的传承保护,并彰显皖北的地方文化自信。
这些民间的传统艺术资源不仅面临需要讨论的非遗传承与保护问题,还面临着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新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商品化所带来的冲击。如杨丹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视角下的龙州壮族天琴女性禁忌破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考察对象“龙州壮族天琴”产生之初是作为民间信仰法事操持者——魓,在求花、招魂、安龙、受戒与供玉皇、侬垌节、寿诞等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活动中使用的法器,但为了挖掘和打造民族文化品牌,2003年龙州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挖掘和打造龙州壮族文化品牌领导小组,并成立了一支由纯女子组成的龙州天琴女子弹唱演出队伍,一方面打破了当地“传男不传女”的禁制,另一方面又改变了传统天琴表演的本来意义。学者提出,面临这样的情况,非遗保护的原则将如何去规范这种传统的伦理问题,以此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还有杨飞飞的《非遗传承与特色小镇的融合新范式——以浙江非遗主题小镇为例》,通过对浙江非遗主题小镇的田野考察,提出了在小城镇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发掘非遗文化资源创新动能,充分释放文化自身的活力并促使非遗文化在吸纳、扬弃、调整、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演进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文化复兴与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张晨的《商业场域视角下民众在文化重构中的推动作用——以土家族撒尔嗬为例》,从艺术场和商业场域两种层面去分析撒尔嗬的重构过程,让我们看到其是如何从丧葬礼仪中走出来成为民俗文化的象征符号,然后又如何成为艺术商品,并提出了普通民众是撒尔嗬商品化的最早驱动力,是观众的偏好决定了商业场域中的惯例标准,民众作为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撒尔嗬演绎的具体内容以及表演形式。郝春燕的《艺术教育视阈中网络“非遗”人类学价值研究》,提出了有关如何通过网络艺术教育的“异托邦”空间有效地再造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托邦”存在,创造非遗重生性转化的空间,同时又如何通过网络教育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再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网络艺术教育中重新回归人类生活并诞生相关的艺术伦理、教育伦理的问题。以上的这些论文不仅记录了传统的民间艺术如何成为保护的非遗对象,以及转化为具有商品价值的现代人的消费对象的动态过程,同时还提出了许多令人深省的思考。
最后,笔者关注到的还有吴昶的《近现代鄂西南土瓷窑的兴衰及其山地社会特征——以映马池、磁洞沟、堰塘坪三个调查点为例》,这是一篇关于湖北山区土窑陶瓷研究的民族志,写得很朴素,但却反映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可以破除以往一些理论局限性的社会事实。如:按照我们现有的研究,我们认为,民国时有很多手工艺陶瓷因为机器的使用受到了冲击,很快就受到了历史的淘汰。但是他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即使到2000年以后,在山区还有许多手工生产的土窑存在,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在山区里面很不方便,由于没有公路,运输全靠人力来挑、牲口来驮,土窑就为这些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提供他们的日用陶瓷器。这让我们改变了一个观念,传统手工艺不仅是因为机器的冲击才衰败的,还与交通有关系,便捷的交通让工业化的产品得以普及,反之,没有交通的便捷,工业化和现代化就难以普及。
结 语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理论的总结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扎实的民族志的记录与研究,我们就很难及时关注到中国在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文化与社会的变迁甚至是重构,也很难关注到在这些变迁与重构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之间又会产生哪些变化?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作为社会象征符号和体系的艺术作品,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其意味着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转型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此,只有走进田野,在田野中感受中国社会不断实践的脉搏,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资源,认识中国的文化基因,沿着从实求知的人类学研究之路走下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最终才能够建立一个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学派,为世界人类学理论大厦的建构贡献一分力量,也包括为推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贡献一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