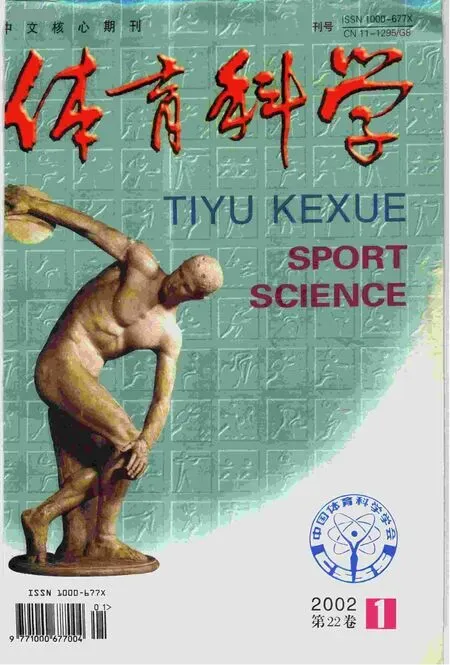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的法治化路径
2019-07-13袁钢
袁 钢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的法治化路径
袁 钢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启动,确立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管理竞技体育的同构模式,该模式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在公共事务社会化管理和“放管服”改革大背景下,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选择法治化改革路径。这就要求必须明确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权利是来自法律授权和会员权利;作为独立民事主体,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必须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脱钩,与体育行政部门建立契约型合作关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自主制定章程来明确其权利义务;通过完善委员(理事)会建设,加强会员建设,建立监督机构和健全治理规则来提升其自治能力。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善治;法治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外,体育社团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均发挥重要作用,是体育事业发展的主体要素。1993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加快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步伐,建立有中国特色协会制”,开始设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以下简称“项目管理中心”),到1998年底完成所有运动项目的中心管理制改革。自1998年开始,作为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重要环节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以下简称“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与项目管理中心“脱钩”探索以多种形式铺开。2015年,中国足球协会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标志着新一轮单项协会管理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单项协会改革”)正式开启。2017年,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以及新一届中国篮球协会通过修订其章程,真正从制度上实现政社分开,权责分明。当前单项协会改革的“足协模式”、“脱钩模式”和“功能优化模式”3种模式(刘东锋 等,2018)未实质解决体育行政部门、运动项目管理管理中心与单项协会的关系以及单项协会自治能力、会员基础薄弱等问题。笔者认为,在制定单项协会改革方案时,特别是顶层设计时,应当首先厘清改革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必须牢牢把握法治化基本方向,方能有序推进单项协会改革。
1 为什么要坚持单项协会改革的法治化路径
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关系到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更事关我国体育事业总体目标的实现。自20世纪50年代,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引入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至今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引进与消化、改革与发展的过程。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举国体制”的管理体制和思维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科学、有序发展我国竞技体育的需要。
1.1 “同构”模式的历史意义
为便于参与国际体育赛事,20世纪50年代开始体育行政部门陆续设立了单项协会,形成了“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单项协会”的管理模式。由于职能不明、缺乏人员、经费和编制,单项协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与体育行政部门合为一体”(张耀红,2016)。在1993年开始的协会化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在1998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体育行政部门剥离运动项目管理职能,成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并与各单项协会形成“两块牌子,一个机构”的结构,构建“项目管理中心+单项协会”的管理体制,即“同构”模式(史康成,2013)。随着同构模式形成,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形成了由国家体育总局(作为竞技体育决策主体)、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作为竞技体育管理主体)、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作为竞技体育执行主体)、各业余与专业、商业和职业体育俱乐部等(作为竞技体育运作主体)构成的垂直化的管理层次。
同构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先锋举措,在打破原有政府“管得多、统得死”的体制束缚,增强竞技体育国际交流,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沟通方面有着积极、重要作用。但在2008年后,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步伐“开始停滞不前,并未有实质性举措”(张毅恒 等,2013)。
同构模式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同构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推动形成,单项协会并非在社会历史条件下,由功能性群体自然演化或者社会群体的正式化所形成,而是由社会动员造就(蔡建飞,2012)。同构模式本质上是原有体制内权力与职能的优化与调整,存在政府主导决策、组织产权不清、缺少监督机制、“挂靠”的组织模式、非自愿入会等方面的问题。而从改革过程来看,体育行政部门分流人员组成受托行使行政权力的项目管理中心,实际承担了单项协会的职能,控制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延缓或者阻滞了行政权力向社会分权的过程。而从改革效果来看,单项协会改革试点凸显出社会化和产业化之间的矛盾。
1.2 单项协会改革的法治化路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要求“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这些决定为单项协会进一步深化改革确立了新的目标和任务,也要求必须对现行竞技体育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这必然直接涉及体育行政部门及项目管理中心等人员的切身利益,能否实现这种改革,需要下力气、真改革。
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明确的,即最终形成“以协会管理为主体、多种管理主体并存、业余与职业相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高雪峰,2007)。但是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思路上,却存在改良和重组两种意见。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以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体育协会改革试点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明确了统筹考虑、试点先行、分类推进、分步实施的改革原则,但仍然坚持“非一步到位式”的改良思路,这也是目前单项协会改革的基本方向。正在实施中的单项协会综合改革试点、单项协会承接项目管理中心全部职能、单项协会管办分离、协会功能优化等均属改良型单项协会改革方案。
为实现单项协会完全、真正的脱钩,不仅需要在清晰顶层设计下进行务实地资源配置,而且更需要所有单项协会改革坚持法治化路径,这是实现“依法治体”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证改革方案“不走弯路”的基本保证。首先,各国都把体育社团纳入了制度化、法治化轨道,这为体育社团正常活动提供保障和制度供给,因此,坚持单项协会改革法治化路径是各国体育社团管理的必然选择。其次,在科学、民主制定的有关体育立法基础之上的单项协会改革法治化路径,具有确保单项协会管理有章、权利得以保障的程序性价值,以及保障单项协会自由、公平、有效和有序发展的实体性价值,即借助“法治”最终实现从“人治”到“自治”的转变。最后,坚持单项协会改革法治化路径是重点解决目前我国体育社团法治问题的必然选择,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体育社团法规不完善、体育社团自治与政府规制结合不规范(殷泽锋,2011)、体育社团管理缺乏监督(汪全胜 等,2010)等。
坚持单项协会改革法治化路径需要提高单项协会的自身能力建设,需要真正实现单项协会的法人治理。正如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所说,任何本文都是双重的本文,总有两个本文同在一起:两个本文,两只手,两种眼光同在一起又同时是分开的(杜小真,2000)。用解构主义观点来审视单项协会改革,既往的传统行政主导下改革试点是第一种本文,即在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思维下,政府应当将“公共职能”逐步卸下,将执行性、操作性、事务性职能授权、委托给民间团体。政府对于竞技体育的管理,也从直接、微观管理转向间接、宏观管理,重点是对体育社团进行规划、引导、监督和服务。行政主导下的改革,单项协会是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被动接收者。而法治化视野下的改革路径就是“与第一种不同的、但又是同一个”(杜小真,2000)的第二种本文。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体育社团不同于政府,是具有合法性、自愿性、民间性、非营利性的组织。准确界定单项协会法律定位是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相关规定以及社团设立的宗旨和性质,单项协会属于社团法人,系非营利组织,这是单项协会的基本法律定位。从这一基本法律定位出发的单项协会改革法治化路径,从法律权利角度,需要明确单项协会为何享有权利,享有何种权利,如何行使权利这三个基本的法治建设问题;从法律性质角度,这三个问题对应的是单项协会的法律主体地位、权利与义务和法人治理结构。笔者认为,只有真正解决好这三个基本问题,才能实现单项协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管理。
2 为何享有权利:单项协会的法律主体地位
回答单项协会为何享有权利问题,首先,应当明确单项协会权利来源和主体性质,以确定其法律主体地位;其次,应当解决单项协会权利边界存在“行政性权力关系”和“契约性权力关系”双重权利关系模糊的问题(王旭光等,2007),需要从权利角度来界定单项协会与项目管理中心、体育行政部门的关系。
2.1 明确权利来源:法律授权与契约让渡
根据《民法总则》第57条,作为社团法人,单项协会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独立权利是法人的法律身份,是法人权利能力抽象体的体现,是通过法人具体权利的享有和义务主体具体义务的履行来实现。单项协会权利应该来自于法律授权和契约让渡。
实际上,《中国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在法律层面上对于单项协会的授权是非常明确的。《体育法》第31条第3款原则性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第29条和第39条又规定“单项协会享有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以及管理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权利”。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竞技体育的职责被确定为“统筹规划竞技体育发展,设置体育运动项目,指导协调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指导运动队伍建设,协调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国务院办公厅,2009)。两相对比,单项协会负责直接管理运动项目,而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对于运动项目的管理限定于“设置”体育运动项目、“指导”训练、竞赛和运动员以及“协调”社会保障,没有具体管理体育运动项目的职权。
“公民体育权利是现代社会与现代法治发展的必然产物”(于旭善,1998),更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体育运动是人人享有的权利,并不属于行政管理,更不是行政许可的范畴。各竞技体育参与、经营主体,如俱乐部、运动员应当成为单项协会的团体会员或个人会员,并为实现共同利益共同让渡出其享有的部分法定权利,通过契约方式(主要是以章程形式)将权利交由单项协会行使。单项协会通过组织、管理这类契约性权利以实现全体会员利益最大化。对应的是,会员应当遵守单项协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行业规则,否则要接受相应处罚。
2.2 明确主体性质:民事主体
在主体性质上,依据《民法总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单项协会为私法性质社团法人,属于民事主体范畴。但实际上,单项协会行使权利的内容大部分系公共事务管理,易被误为“公法人”。严格根据公法人的概念(葛云松,2007)和理论(崔拴林,2011),单项协会不具有公法人的法律人格,也不应具有公法属性。
关于单项协会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朱利等(2006)建议,为了保证会员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能寻求到司法的保护,需要赋予单项协会行政主体资格。彭昕等(2011)认为,单项协会管理行为的法律性质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应对单项协会管理行为进行细致分析后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以此平衡法律职权与法律职责。根据行政法基本理论,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被授权组织以及受委托组织3种类型。以单项协会对会员的处理为例,单项协会作为民事主体,可以依据章程、内部规定对于会员进行处分,会员对于处分不服,可以通过专门体育仲裁或者民事诉讼来解决;单项协会只有依据授权或委托所为时,才可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单项协会受托行使行政权力(公权)与其自身享有自治权利(私权)的性质不同,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主体资格。但是单项协会依授权或者受委托行使行政权力,特别是行使处罚权的时候(赵许明 等,2005),也必须遵循行政程序和承担行政责任。单项协会作为民事主体,需要接受内部监督机制民主监督和制约,也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和制约。
2.3 明确法律关系:与体育行政部门的法律关系
准确界定单项协会与项目管理中心、体育行政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单项协会改革法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3.1 “同构”模式下项目管理中心与单项协会的关系
项目管理中心在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中,扮演着国家体育总局直属事业单位和单项协会的常设机构的双重社会角色。同构模式设计初衷是体育行政部门在运动项目管理上依靠项目管理中心实现运动项目的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杨丽芳,2013)。可以说,在前期改革中,项目管理中心成为助推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的“孵化器”,孵化成熟后,应将单项协会从体制内释放出来,成为真正具有实体功能的机构(冯欣欣,2017)。
根据现行有效的《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规范化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政字〔2001〕46号)和1993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运动项目管理实施协会制的若干意见》,除了承担“管理和指导国家单项运动训练基地工作”和其他任务外,项目管理中心与单项协会的职责几乎没有区别。1993年5月24日,《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将项目管理中心定性为“过渡性机构”。项目管理中心成为前期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而真正实施项目管理的是中心所属的业务部门或处室。项目管理中心事实上行使着政府职能,导致单项协会对政府有着过分的依赖,实际上使项目管理中心成为单项协会的管理机构。中国的社团具有“官民二重性”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所决定的(孙炳耀,1994),“社会”自身具有相当的“国家”属性,新设社团多数走的是“体制内生成路径”。这也是体育行政部门为适应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所做的制度选择,项目管理中心政社同体性及单项协会同构依附性表明了改革的不彻底性和过渡性,这也导致单项协会至今没有真正发挥体育社团的作用。
同构模式的长期存在,形成了单项协会与项目管理中心同构的利益关系,必然对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形成严重阻碍(王凯珍 等,2010)。而目前项目管理中心的机构性质、管理方式等,客观上对单项协会实体化进程产生极大影响。有学者提出分类分步改革路径,建议将现有的项目管理中心撤并成5个综合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改良方案(杨丽芳,2015)。从单项协会改革的法治化路径上来看,体育行政部门应摆脱传统以行政主导进行改革的路径依赖,以更大的制度变革力度,打破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资源的垄断,推动单项协会与项目管理中心全面脱钩,最终实现协会管理体制。笔者赞同多数学者意见,在以“改良思路”为主的单项协会改革方案中,项目管理中心仍然存续并发挥作用,这实际上是与法治精神相悖的。因为任何过渡性或临时性立法、行政、司法机构都必须有明确期限限制,即便没有明确期限也应在合理期限范围内发挥作用,项目管理中心作为过渡性机构至今20余年,其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实现。
2.3.2 “合作”模式下体育行政部门与单项协会的法律关系
1. 社会转型期体育行政部门与单项协会的关系:中国社团发育中出现了“形同质异”(沈原,2007)现象,体育社团发展亦是如此。西方国家先有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后有利益主体的自主化,而我国社团的形成与发展更多是依靠政府制度供给。我国社团通常以“挂靠”的形式,同时依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资源,并“政府”和“社会”的双重需求。社团基本职能是服务功能,在社会转型期分担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是政府管理社会权力的延伸,但单项协会“在政治上缺乏权威性,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体育政府部门对体育社团能否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尚有疑虑”(宋剑英,2011)。此外,竞技体育最重要的人、财、物、时间和信息要素还掌握在改革后所组建的项目管理中心手中(周玉波 等,2016),而管理体育运动需要科学处理、有效利用、合理配置这5种资源。
2. 体育行政部门对单项协会的“放权”:在不少国家,政府与体育社团采取合作方式,由体育社团承担体育事业的管理职能,实行自主管理,如美国地区性的公园与休闲委员会、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意大利国家奥委会等,体育协会在英国竞技体育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黎涌明,2017)。现代社会管理已从政府一元化管理走向政府、组织(包括营利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合作模式,体育行政部门不能再统一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在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客观上要求体育行政部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创新加强监管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的行政权(李克强,2015)。体育行政部门应将竞技体育执行层面的全部工作直接交由单项协会负责。
体育行政部门的“放权”也不是“一放到底”或者“一刀切”式放权。体育行政部门应在总结“脱钩”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有序推进单项协会改革,尊重、保障单项协会的社团法人资格及对体育资源的掌控,发挥单项协会在管理微观体育事务中的主体作用。这需要打破国家与社会分离与对抗,构建体育行政部门与单项协会协议化的合作关系,建立合作模式(马志和,2003),因为合作有助于弥补双方各自的弊端,有助于平衡双方各自的利益。体育行政部门还应当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建立与单项协会的合作互动机制。因此,二者之间是协议关系,而不是直接管理的关系。
3. 体育行政部门对单项协会“监管”:作为社团的单项协会的运作与完善,必然使得竞技体育整合趋向组织网络化,有利于将分散个体依其意愿加以组织,这有利于政府提高效能、协助政府实现善治。社团在政治、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能造成负面效应。社团活动可能会产生某些集团收入增加,但是社会总收入却减少的“分利”倾向(奥尔森,1993),会阻碍公共利益的实现,也可能出现提供公共产品不足的“失灵”现象,需要政府担负起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应当说,任何国家的社团都存在“失灵”问题(王绍光,1999)。
解决单项协会“失灵”问题,要求在改革中,不是完全取消体育行政部门对竞技体育的管理,但体育行政部门对单项协会的监管必须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并且法律强力高于行政权利会促进体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体育行政部门对单项协会的监管方式要发生转变,从对竞技体育的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调控,即通过法律法规“立改废”,制定体育发展目标,拟定体育运作政策来加强对竞技体育的管理。此外,体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和健全体育社团工作考核评估体系,由其委托第三方对单项协会的组织建设、日常工作、竞赛活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考核和评估。
3 享有何种权利:单项协会的权利义务
从韦伯和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论述出发,康晓光(2007)提出社团的“官方合法性”(依法登记注册和行政管理)和“社会合法性”(社会的承认和信任)问题。而获得社会支持与认同是社团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也是社团有别于其他组织的基本特征。社团合法性根源于社会,只有不断强化自主能力,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不明晰的政府与社团的关系、社团与社会的关系、社团的权利和义务导致社团合法性的欠缺。目前单项协会的自身权益、业务活动、权责范围、组织管理、经费收支等都缺乏保障机制,这也对单项协会发挥其应有的民主法治功能构成了一定的制约。
3.1 完善法律法规界定权利范围
建立完全社团化的单项协会管理体制,是建立我国现代体育事业改革的历史必然要求,具有可行性,是单项协会改革的理想模式。作为专业性行业组织,单项协会具有代表会员利益,以及作为行业代表表达整体诉求和维护行业发展的共同利益的功能,特别是当行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要代表行业与国家进行协调,达成利益平衡。
依据《体育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反兴奋剂条例》等法律法规,单项协会具有章程制定权、日常管理权、制定协会发展规划与政策、各级竞赛与兴奋剂处罚事务、纠纷处理事务等权利(彭昕 等,2012)。目前,在同构模式下,项目管理中心与单项协会运作中公权和私权较为模糊,规避规则约束,会出现分别以项目管理中心或单项协会来行使公权、私权的现象。宛丽等(2001)认为,体育社团的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是法律合法性的前提,并且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体育社团如仅依托单一合法性,其法律合法性是难以诉求的。就单项协会而言,这种难以诉求的法律合法性表现在现行体育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方面,只对单项协会的权利义务做了原则性授权,未对单项协会享有的权利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因此,相关体育法律法规需要对于单项协会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独立性(自治性)、组织架构、职能等进行建构。现行《体育法》在竞技体育和体育社会团体的两章中对于单项协会权利进行概括性规定,较为符合《体育法》作为体育行业基本法的定位,并且,《体育法》难以增加更多具体条款。较为适宜的做法是在国家体育总局2001年制定并实施的《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基础上,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部门规章层面的《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管理办法》。第一,从立法依据来看,作为《暂行办法》立法依据的《体育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目前都处于修订之中,《暂行办法》会陷入立法依据不足的困境。第二,从法条冲突来看,现行《暂行办法》中部分规定已经与现行法律法规、党内法规存在冲突,如《暂行办法》第39条关于总局领导兼任社团领导职务的职数规定等。第三,从法律效力上来看,《暂行办法》已经实施近20年,不能再继续暂行下去。第四,从法律效果来看,《暂行办法》仍让单项协会与体育行政部门保持挂钩关系,有关规定已经侵害了单项协会的法人治理。第五,从规定内容上看,《暂行办法》实质是全国性体育社团登记管理办法,更关注的是全国性体育社团的登记,而不是对于单项协会进行有效管理。
国家体育总局直接管理竞技体育的职责只有“设置体育运动项目”(国务院办公厅,2009),且《体育法》已经明确应由单项协会负责管理单项运动,因此,真正实现单项协会实体化转型的问题症结不在于《体育法》修订,而在于《体育法》的实施。笔者建议,《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管理办法》应以专章形式,逐一规定单项协会权利与义务的范围,明确单项协会享有的权利与体育行政部门对于运动项目指导和协调权力的界限,特别是废止《暂行办法》中国家体育总局各职能部门的归口管理,按照“放管服”要求实行一个职能部门对口管理;取消单项协会的各种报批规定,只保留在重大事项上的事后备案要求,以避免国家体育总局指导和协调的宏观权力微观化,以保障单项协会的自治地位。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议将《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管理办法》上升到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3.2 自主制定章程,明确权利义务
独立意志是单项协会的主体意识,是其自主活动意识。单项协会应当通过正当程序自主决定其组织章程,自主作出组织决定,其中,依法制定章程是单项协会独立的基础。《民法总则》第58条原则性规定,单项协会应当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暂行办法》具体规定单项协会成立的条件和程序。根据《民法总则》第90条,单项协会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社团法人资格。虽然绝大多数单项协会都已制定章程(崔丽丽 等,2002),但是章程往往是仅被发起人视为设立社团必需报送的一个文件,章程整体未能发挥其应有功能。
《体育法》第36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体育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组织和开展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由于单项协会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因此,单项协会在章程制定中应当突出其享有行业管理的主要权利,包括运动员、教练员、俱乐部等资格认定;运动员的注册;研究制定并组织本运动项目全国竞赛制度、计划、规程和裁判法,负责本项目全国性竞赛的管理,审定全国比赛规则和运动成绩;指导和管理本项目优秀运动队伍的建设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制定和执行联赛规则、裁判规则、仲裁规则;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不同运动项目协会行业管理权利既具有相似性,又具有专属性,因此,在制定、修订章程时还需根据运动项目特点、国际交流需要等,特色化确定协会权利,切忌“照搬照抄”。此外,章程应对单项协会内部管理做出具体规定,如发起人的资格、组成人员资格、会员的资格、会员代表大会权利等。
《民法总则》第60条和62条,单项协会应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承担民事责任。此外,单项协会还应承担为会员提供如信息服务、组织培训、交流、专业合作、项目研究和成果出版等服务的义务。
4 如何行使权利:单项协会的法人治理
民间社会组织的兴起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当代的社会结构、秩序性状和法治模式,展现着全球化时代的法治理念变革和法治秩序走向(马长山,2008)。
4.1 加强委员(理事)会建设
单项协会应当具备法人治理结构,通常是指委托者、决策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之间通过分工合作和各司其职而形成的权责明确、制约有效、规范代理、保障使命,并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角色关系模式(王凯珍 等,2016)。根据《民法总则》第91条,设立单项协会应当依法制定章程,应当设立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等权力机构,应当设立委员(理事)会等执行机构。
目前,单项协会仅具有社团或独立法人的外观,其实际运作与社团独立法人要求严重背离。作为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设机构的委员(理事)会或委员(理事)一般不参与单项协会的长期战略制定,也不参与管理,决策权基本上在体育行政部门,这也是单项协会所发布的制度、规则实际上具有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文件的性质的主要原因。并且,单项协会委员(理事)会的职责不甚明确,委员(理事)的代表性不足。
单项协会治理结构出现问题主要源自《暂行办法》自身存在矛盾,既规定社团自律(第17条),又安排内部人事(第31~47条)。单项协会领导人的产生,应当是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但是目前单项协会存在明显的行政化人事管理倾向,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政社分开的原则。作为《暂行办法》上位法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并未对任职情况作出明确规定,《暂行办法》第五章“任职管理”的依据不足,并存在与现有规定的冲突。
4.2 加强会员建设
单项协会的社团属性决定了其应当重视发展会员,因为壮大会员队伍是单项协会发展的基础,同时完善的会员制度是单项协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目前,我国单项协会会员普遍来源不够充分,部分单项协会只有团体会员,个人会员有限。如德国足球协会下辖俱乐部数量、会员人数众多,相比而言,我国足球协会的会员制度不完善,会员人数少(王瑞 等,2018)。因此,法治化改革路径要求单项协会应将本项目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运动员、教练员、研究者等都吸收成为会员,设置合理的会员条件,进而发挥会员代表大会的实质作用。此外,目前我国体育协会管理制度普遍采取国家、地区“分级管理”原则,部分单项协会采取间接承认地区协会会员的机制,这导致单项协会作为全国性体育社团与其会员的直接联系薄弱。因此,单项协会必须打破分级管理的束缚,借鉴国内外社团建设经验,不作“迭床架屋”式要求,不把成为地区协会会员作为全国性协会会员的前置条件,进一步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真正把作为单项协会基础建设的会员工作抓好,才能单项协会真正具有“社会合法性”。
4.3 设立监督机构
单项协会的监督和制约目前主要通过体育行政部门来实现,会员难以对单项协会进行监督。有些单项协会“透明度”低,内部管理不公开,财务制度不完善。由于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并未对单项协会的监事制度作出任何规定,因此,单项协会普遍没有设立监事或者监事会。监事制度的缺位使得单项协会缺乏相应的内部监督机制。因为单项协会具有自主制定章程的权利,即便没有上位法的强制规定,也是可以根据现代治理理论与实践,借鉴其他社团经验建立单项协会监事制度,如可以参考“国际体育组织善治计划”提出的体育行业组织的内部治理体系(罗思婧,2017)。尽快推动监事或者监事会的设立和制度建设,并尽快发挥其应有作用,是保障单项协会具有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王扬 等,2018)。
4.4 健全治理规则
单项协会内部治理需要一系列制度加以保障,主要包括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日常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诚信自律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会员权益保障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制度、激励制度和监督制度。多数单项协会选举、会议、决策、运行等日常管理制度不太完善,即使有相关规定,实际运行中往往流于形式。此外,还应当重视建立健全单项协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单项协会可以通过制定章程或者修订单行规则的方式来完善相关制度,并且相关制度的完善还需要考虑单项协会的社会文化影响、体育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等制约因素。相关制度的实施更需要配套的健全机制、合格人员、充足经费,这样才能保证规则不会停留在“纸面上”。
5 结论
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启动的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张伟,2017),必须充分肯定渐进式改革所取得的有益成果,必须吸收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的经验教训,更也必须认识到,单项协会改革已步入深入区,抵达攻坚期。其中,作为体育社团的单项协会“合法性”(legitimacy)或者更应翻译为“正当性”问题,是单项协会改革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王旭光 等,2007)。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应该是单项协会改革的基本方向。单项协会“正当性”源自其能够真实地扎根于社会、能够真正地服务于社会,坚持单项协会改革法治化或者称之为“法律合法性”是保证单项协会能够“正当性”最基本的保障,也是包括单项协会在内中国体育社团改革最基本的模式。
保证单项协会改革坚持法治化路径,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达成共识并有所作为:应当坚持单项协会非营利性质,不能让单项协会成为营利工具或者营利主体;应当真正明确单项协会社团法人的法律定位,方能从法律上保证其独立性;应当明确单项协会的权利是来自法律授权和会员权利,方能从公共职能上保证其运作的有效性;应当明确单项协会是独立民事主体,必须与体育行政部门、项目管理中心完全脱钩,并与体育行政部门以签订契约方式建立合作关系;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自主制定章程,方能解决单项协会改革中的掣肘问题;必须完善委员(理事)会建设、加强会员建设、建立监督机构和健全治理规则,才能提高单项协会的自治能力。只有坚持法治化改革路径,单项协会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力;只有坚持单项协会基本法律定位、性质和地位,单项协会才能走上多元发展道路。
奥尔森,1993.国家兴衰探源[M].吕应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47-48.
崔丽丽,叶加宝,苏连勇,2002.全国性体育社团现状分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7(4):1-5.
崔拴林.,2011.论我国私法人分类理念的缺陷与修正——以公法人理论为主要视角[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9(4):83-93.
杜小真,2000.德里达的解构主义[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34(3):95-103.
冯欣欣,2017.单项运动协会制度变迁的“锁定效应”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36(3):29-33.
高雪峰,2007.中国竞技体育管理变革之路[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66.
葛云松,2007.法人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再探讨——以公法人概念为重点[J].中国法学,(3):77-99.
国家体委,1996.中国体育年鉴1994-1995[M].北京:中国体育年鉴出版社:558.
国务院办公厅,200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体育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EB/OL]. [2018-06-26].http://www.sport.gov.cn/n16/n33193/n33208/n33478/n33973/n1078181.files/n1078277.doc.
胡孝安,2002.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19(3):20-21.
康晓光,2007.创造希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M].桂林:漓江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637.
李克强,2015.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5-15(5).
李艳翎,2002.论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渐进式改革[J].体育科学,22(1):27-30.
黎涌明,2017.英国竞技体育复兴的体系特征及对我国奥运战略的启示[J].体育科学,37(5):3-10.
刘东锋,姚芹,杨蕾,等,2018.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模式、问题与对策[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2(4):50-55.
罗思婧,2017.我国体育行业自治及其法律规制重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0(3):16-21,32.
马长山,2003.全球社团革命与当代法治秩序变革[J].法学研究,(4):132-148.
马志和,2003.我国单项运动协会的角色定位与制度变迁[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6(2):265-267.
彭昕,周小敏,罗雅莉,2011.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的行政法律地位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3(2):115-123.
彭昕,周小敏,2012.全国单项体育协会自治困境与对策研究[J].山东体育科技,34(4):9-13.
秦笃训,1995.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单项协会体制[J].体育文史,(2):15-16.
宋剑英,2010.体育行政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10-211.
沈原,2007.市场、阶级与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01-324.
史康成,2013.全国性体育社团从“同构”到“脱钩”改革的路径选择[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36:(12):1-5.
孙炳耀,1994.中国社会团体官民二重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6):17-23.
宛丽,罗林,2001.体育社团的合法性分类及发展对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4(2):155-157.
王凯珍,汪流,戴俭慧,2016.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17.
汪全胜,陈光,张洪振,2010.论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33(5):17-24.
王瑞,张扬,2018.政社脱钩背景下我国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相关问题的研究——以足协为例[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32(4):42-45.
王绍光,1999.多元与统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9.
王旭光,惠继红,2007.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社会合法性挑战和发展途径[J].体育科学,27(7):7-13.
王艳,孙汉超,1998.我国单项运动协会依托项目管理中心发挥实体作用的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15(2):5-8.
王扬,陶玉流,2018.体育社团法人治理之困境及破解对策[J].体育科研,(2):47-53.
杨丽芳,2013.我国单项运动协会体制改革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学位论文:49.
杨丽芳,2015.我国单项运动协会体制改革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9(6):42-47.
殷泽锋,2011.中国体育社会团体自治权的法理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34(12):14-20.
于旭善,1998.论公民体育权利的时代内涵[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1(4):10-13.
张伟.2017.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智力结构分析[J].体育学刊,24(4):22-30.
张耀红,2016.新时期改革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思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32(4):44-48.
张毅恒,彭道海,柳鸣毅,2013.我国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J].体育与科学,34(5):27-30.
赵许明,张鹏,2005.体育社团处罚纠纷处理机制的比较及选择[J].体育科学,25(4):81-84.
周玉波,张秀华,2016.有关全国单项性体育协会现状与问题的综述研究[J].体育大视野,6(31):192-193.
朱利,陈家鸣,2006.试论单项体育协会的行政主体资格[J].辽宁体育科技,28(6):15-16.
The Path of Rule of Law of 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 Reform in China
YUAN Gang
Since the reform of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management system started in the 1980s, the isomorphic model of national sports governing body and 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hav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ized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reform of delegating more powers, 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optimizing services, the reform of 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 system chooses the path of rule of law inevitably. This requires that the rights of the 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 must be clearly from the legal authorization and the transfer of the rights of members. As an independent civil subject, the sports association must decouple from the national sports governing body, and establish contractual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To clarify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 by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ndependently formulating articles of sports association. To strengthen the autonomy of the 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 by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ittee member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embers, establishing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and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rules.
1000-677X(2019)01-0020-07
10.16469/j.css.201901004
2018-07-12;
2019-01-06
中国政法大学交叉学科培育与建设计划(体育法学)资助项目
袁钢(1979-),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法学、司法制度、人权法学,E-mail:yuangang @ china.com。
G80-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