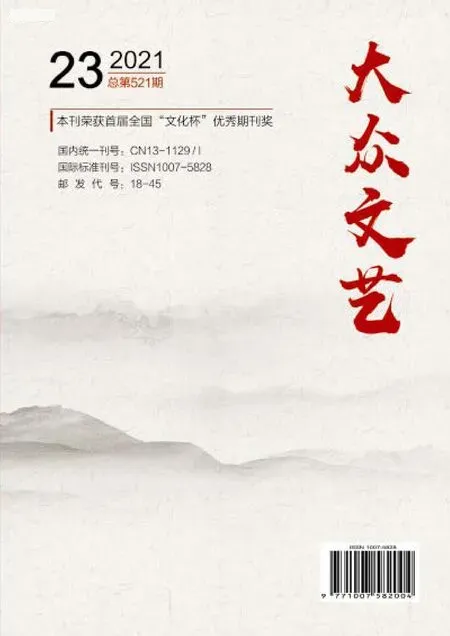格非《望春风》
——荒诞桃花源的精神高地
2019-07-13贵州大学人文学院550000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 550000)
对格非的乌托邦(桃花源)书写已有许多研究者做出阐释,乌托邦与桃源都是具有理想色彩的代名词,结合乌托邦的阐释更侧重于制度建设实践的探索,而桃花源则更多回归到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桃源情结。在格非的最新作品《望春风》中,桃源的书写颇具荒诞意味,也许是桃源的构造者意识到,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古老的乡村生态消逝不可避免,文本中的“我”既身处荒诞桃源之中,也是荒诞桃花源的书写者身份,“我”坦然的态度与现实物质的窘迫形成对比,儒里赵村的乡村桃花源生态中也纠缠着种种冲突。“桃花源”不再是理想美好的代名词,美好往往是一种可控制的蒙蔽,这种书写正是让我们警惕这种蒙蔽性的美好衍生为自欺欺人。格非书写的桃源还原了和谐与冲突并存的荒诞的状态,废弃的便通庵成为“我”和春琴安家生活的荒诞桃花源,同性恋唐文宽、赵更生被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接受乡村伦理的审判,通过礼平、同彬、“我”三个人所展示人的欲望的刻度,格非选择在“我”的欲望灰烬之上构筑理想的精神高地,荒诞桃花源的书写也许正是一种寄寓,在肮脏阴暗的欲望的死灰之中,会复燃起桃花源般的欲望。
一、荒诞桃花源的尴尬美满
在叙事风格上,格非总体承杜甫沉郁顿挫之文脉,抒情着墨不多,主人公即便是处在最低谷的惨淡时刻,也只费几笔平实的情绪描写掠过,几乎不会沉溺在情绪中极尽渲染而不可自拔,但是对于特定情结书写的钟爱,可见于格非的作品及其研究者的阐释。退隐和避世只是桃花源的在古典文学中人云亦云的表层意象,格非所书写的桃花源既是诗学的辩证也是乌托邦的辩证,是审美的,也是政治的,这种意识形态在本质上都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范畴。
在格非最新作品《望春风》中,“我”与春琴最后安家在水电不通的便通庵,这是一个具有荒诞意味的桃花源。从荒诞的审美心理来看,荒诞的根本是分离,一是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悖论的不可知性;二是人在这种非理性矛盾冲突中所产生的心理上的陌生感和异己感1。从现实世界秩序的角度审视“我”和春琴最后居住在施工装修后的便通庵,过着不通水电的生活,二人情感关系和精神世界却又是和谐美满的,格非所着意书写的是个“尴尬”的桃源,这不是如实书写,而是基于客观现实的可能性构造。“我”和春琴坐在同彬和莉莉的越野车的真皮座椅上,车绕过未竣工的体育馆,驶入了八车道的南徐大街,途径雄伟而又轻佻的财政局大楼、法院大楼、城投集团公司大楼……在宜侯墓遗址公园附近,踅入了一条幽僻的林间小道,最后抵达“我”和春琴的桃源——水电不通的便通庵。尽管在这里叙述者“我”的口吻上是极为超脱的,这种物质上巨大反差的对比似乎没有给“我”的坚守造成一丝的撼动和伤害,因为“我”也没有任何情绪上的表露。但是我们的思考不能止于此,作者真的想传递的是“安贫乐道”吗?格非为何要设置这样的颇具荒诞色彩的情节,“我”这一生的波折与动荡没有给我的心理留下过重的创伤或烙印,最终“我”只想靠着积蓄和春琴一起平淡地生活,我没有强烈的谋生意识,更没有反抗“我”的命运达到自我实现的想法。也许是“我”设法隐藏了自己的感受,但是儒里赵村这些人的命运遭际都早已在我的心里牢牢地留下了烙印,最终将逐一从我笔下流泻而出。“我”并不是没有反抗,也许这经过我选择提炼的书写才是一种反抗,而我书写的反抗,从后记中看来,又只得在一定程度上屈服于春琴的喜好,春琴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是不允许被书写的。
剥离开格非独具风格的超脱淡雅的语言外壳,这背后的层层交织的矛盾都渗透着荒诞色彩。这边是车水马龙的高楼文明,那边却屹立着一座水电不通的便通庵,便通庵就像是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一座人性神庙,格非没有虚伪地讴歌这样的“安贫乐道”,而是让我们从两个身世飘零的苦命人相依为命的生活中看到了爱情的力量。
二、唐文宽—悬置回时空的审判
格非所书写的儒里赵村也是一个桃花源生态,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小冲突,但在古朴的乡村伦理和大家长秩序调和之下,人们的生活都还是呈现着和谐美满的状态。如果说赵孟舒、唐文宽乃至赵锡光的遗老作风是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逆的冲突性闹剧,那么这个隐藏自我的外来人唐文宽注定是这片土地上永恒的悲剧。
格非在叙事上布下了埋伏,在第一章父亲中,交代了唐文宽是个喜欢愚弄小孩的“故事大王”,直至第三章“余闻”中单列出一节唐文宽直接到写东窗事发。格非将唐文宽完全置于村民的角度来审视,将事件还原到了当时的时空之中,唐文宽是一个在和谐的乡村伦理中不合理的存在。
透过文本用书写者的眼光来看,唐文宽是个复杂扭曲的形象,“如果说唐文宽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的行为,已足以让三个人面面相觑,心惊肉跳,他接下来所供述的那桩丑行,更是让人目瞪口呆,神魂出窍”——唐文宽不仅是个同性恋,还是一个恋童癖。接下来的赵德正的处理方式其实也看似符合了一个人情乡村社会的现实逻辑——赵德正抽光了烟盒里的烟又向定邦讨了一支,叼在嘴上,这才道:“这种丑事,要报上去,文宽的命就保不住了。常言道,人命关天。他一个外乡人,少了一条胳膊,投奔道我们村里来,虽说做出了这等伤天害理的事,但也没到挨枪子的地步。……得把这件事整个兜住。要是以后鼓了包,漏了水,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与你们两兄弟不相干”。格非给这个人物命名为“德正”,也许是对于此种乡村伦理道义的表态。在“我”的叙述中,唐文宽始终是一桩“奇闻丑事”般的存在,文本中对唐文宽的描述也是见闻式的,他整日整夜睡不着觉,反复梦见公安干警在学校操场上逮捕他,或是在刑场上被枪决时突然想撒尿,唐文宽常去赵德正办公室前晃荡,只有看见赵德正稳稳当当朝他点头微笑时,心中那种濒临崩溃的悸动不安才会暂时平复,如此往复恶性循环。赵德正一面“兜”住了这件事,另一面内心也担着深重的隐忧。这样双向的困境,也许正是在说明,这种解决方法的荒诞性,将事情遮掩,表面的相安平和与各自内心的风起云涌构成一副颇具荒诞色彩的精神存在状态,在这种道德伦理之下的办事方法,实则分别将当事人推入了一个另一个深渊。
在格非对唐文宽的书写中,其荒诞性并不在于呈现人物本身的痛苦和隐忍,而是在于书写这个村子里的人,或者中国民间对同性恋(病态心理)的态度。从好奇、惊异地传播——忙着挣钱而变得冷漠——与艾滋划上等号的恐惧,文本中叙述者“我”以记录一桩奇闻异事般的旁观者身份而存在。唐文宽并未像赵德正所忧虑的那样会连累了小满,事实是,在唐文宽离开村子子后,一直躲在暗处的更生,终于被人推到了前台,在村人审判式的目光下,成了肮脏、变态和猥琐的象征,受尽了村人的冷遇和家人的白眼,死后遗体火化家里众多亲戚也无一人到场。在这里的隐含作者的叙事态度未必与“我”是一致的。荒谬其实就是指出理性种种局限的清醒的理性2。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格非所企图呈现的是“指出”的态度,或者说格非所选择呈现这一事件的立场选择。我们意识到了唐文宽的病态存在,然而一双双眼睛、一张张嘴巴对病态故事的咀嚼是基于娱乐至死的猎奇心理?还是基于对人的关怀和尊重意识的人文理性?唐文宽形象因其病态本身就具有荒诞色彩,格非对其的书写是有节制、有明显的立场和态度,是保持距离的一种观看。这种病态人物本身就是一种召唤式的存在:独特的心灵需要被书写、被记录。从荒诞的审美心理价值来看,审丑是对现实否定性的呈现,具有负面的生存意义,是人的主体精神失落的产物。荒诞的审美心理结构,所带来的不是讨好的愉悦,而是摆脱理性道德之后的放纵和走向否定的彻底的解放3。审丑的价值不是美学意义上的,而是具有社会价值的:倘若我们要去治愈病态,就必须直面和了解病态。无论是对于唐文宽、更生的内心世界,还是整个儒里赵村人对他们的态度,冲突中产生的荒诞感,其实就是对个体生命的蔑视,故事背后呈现的是一种“你和我们不同,我们便不让你有生存空间”的伦理逻辑,是集体对个体的残酷碾压,但从情欲部分的书写来看,这是一个病态的性取向者与人类异性之间发情般的动物秩序的荒诞的较量,异性之间大规模地偷情在乡村伦理中被默许了。
纵观历史,上个时代的日常往往在接受这个时代的审判会被贴上善或恶的标签。无论是荒诞的现实化,还是现实的荒诞化,这都是书写形式的审判。因为荒诞在本质上是客观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的一种突出的独特的表现形态4。个体对不合理现象荒诞感的丧失即是个体陷入集体无意识的象征。
三、三重欲望刻度的人物设置
格非设置的三个人物“我”、同彬、礼平,代表着人的欲望的三重刻度。在关于社会的物质或地位的自我实现上,同彬的欲望书写是隐现的,而更多侧重书写“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抉择,在两个莉莉之间的二选一,虽然最终选择哪一个女人做媳妇的决定权始终还是在同彬妈妈心思的操纵之下,但是格非在这里对于同彬态度立场的书写是暧昧悬隔的,也许这也是一种基于人性深渊的诚实书写。对女人的渴求,也是欲望的一种,但更值得深思的是,“我”是便通庵这座荒诞桃花源的守护者角色,而同彬所扮演的是便通庵这座荒诞桃花源的维护者角色,正是他和莉莉出钱修缮这座庵,并帮助“我”和春琴安顿了下来,如果没有同彬和莉莉,便通庵终归只是一座破庙,不可能成为“我”与春琴安贫乐道的精神高地。“我”和春琴在水电不同的便通庵住了下来,靠着“我”的积蓄度日,如果没有呈现夫妻二人和谐美满的精神世界,这对夫妇的现实生活颇像一对反抗拆迁的钉子户形象,但正是这欲望灰烬之上自足美满的精神高地,反衬出礼平欲望的膨胀扭曲的丑陋。赵礼平是现实社会的成功者,“我”是现实社会中的“落魄者”;赵礼平在世俗社会张牙舞爪、为所欲为,“我”退缩在精神世界里哀叹,在将死与未死之间挣扎;赵礼平对女人的渴望几近变态,女人在他眼里就像玩具一样,看中了就要“弄到手”;“我”始终本分安稳,接受命运的“抛掷”,最后和春琴“凑合”在一起,一心一意过日子。
格非对人物作出这样的设置有何寓意?赵礼平因蓬勃的欲望而“爬”到钱权在握的高地,“我”经历了数重磨难在这奄奄一息的欲望灰烬之上与春琴共同建筑了一片美满和谐的精神高地,这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一种渗透着荒诞意味的对现实可能性的书写。
在格非的书写中,“我”用桃花源里琐碎美好的日常通往终极的精神高地,“我”听闻赵礼平因欲望的膨胀而驱使通往对底层群众的倾轧和剥削,性欲的膨胀则表现得更为夸张,这是通过书写对可能性的现实进行意识形态的审判。这审判的结果令人反思:为什么“我”的精神高地必须是抱守在这座荒诞桃花源里?而属于赵礼平自我欲望的成就之路又是如此阴暗?纯洁的精神高地和阴暗的欲望构成一对荒诞性的存在。
人们往往设法掩盖住自己的丑陋一面,以光鲜示人。所以也存在这样认知逻辑:外面光,里面脏。格非所书写的不仅是外表的冲突,也是内在精神和欲望的冲突,这二重冲突的实现或者变异,里面充斥着种种荒诞性。荒诞不在于希望与等待,荒诞生发于自我,是内化的,等待是一种期盼性的,是有对象的,是外化的。当一个人清晰地知道自己生存的终极目的并坚信其合理性时,他就不可能不感到充斥周围的荒诞性。同理,当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以及秉承这种教育思想下诞生的理想与现实生活中积累的实际经验之间的巨大落差,如果理想尚存,冲突永远在发生着,荒诞便无处不在。而格非选择在欲望的灰烬之上构筑理想的精神高地,也许是一种美好的寄寓,肮脏阴暗的欲望的死灰之中,会复燃其桃花源般的欲望。
注释:
1.荒诞的审美心理价值新探,楚亚萍,魏家文,美学论坛。
2.【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3.荒诞的审美心理价值新探,楚亚萍,魏家文,美学论坛。
4.荒诞的现实化与现实的荒诞化—中国当代喜剧电影两种创作思路初探,王璐,杨璐,学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