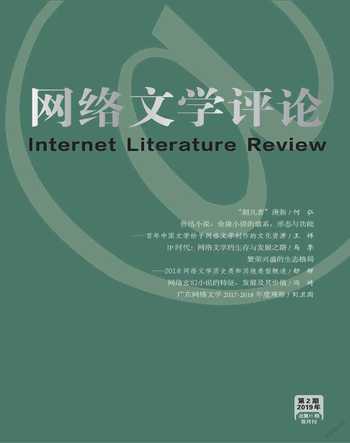远古迷雾、恶魔性因素与迟来的正义
2019-07-13陈红旗
摘要:《鬼吹灯之云南虫谷》讲述了胡八一、王凯旋和Shirley杨去云南虫谷探险、盗掘献王墓寻找并成功带回雮尘珠的故事。在一定层面上,“我们仨”去云南盗掘献王墓不是一种普通的盗墓行为,而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活人与死人的殊死搏斗,这段盗墓生活的开始也是一种新的道德观构建和文化政治的开端。通过小说的线性叙事,作者揭露了利用邪恶痋术守陵和害人的献王这类统治者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这种恶魔性穿行在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丑陋而狰狞地展现了人性的阴影和深层中的恶意。小说还重构了古滇国的墓葬文化政治,展现了作者重塑“民间正义”的潜在动机,也隐喻了迟来的正义及其限度等问题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天下霸唱 《鬼吹灯之云南虫谷》 探险 恶魔性 迟来的正义
天下霸唱的《鬼吹灯》是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它在起点中文网连载之后创造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纪录,以至于2006年被玄幻界称为“《鬼吹灯》年”①。2015年,依据《鬼吹灯》的相关情节改编而成的电影《寻龙诀》和《九层妖塔》上映后,《鬼吹灯》更是在中国成为最火爆的盗墓小说,将其视为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恐怕都不能算说得过分。《鬼吹灯》成功的原因在于将盗墓、探险、拯救、秘术、情义、生死、爱情等诸多吸引力很强的文学主题精妙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能够吸引各个层面读者的关注,尤其是获得网民的钟爱。《鬼吹灯》一共包含八部长篇小说,而《鬼吹灯之云南虫谷》(以下简称《云南虫谷》)是该系列小说中的重要一环,其叙事主线非常明晰和一致,几乎没有什么情节枝蔓现象,小说主人公是胡八一、王凯旋和Shirley杨,其中除了Shirley杨以外,胡八一和王凯旋均是由于生活所迫加之没有其他工作技能才沉迷于盗墓的。作为一伙摸金校尉,他们的思想未必阴暗和反动,恰恰相反,他们对历史的讲述完全是对特定时期主流叙述或曰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照搬,这种照搬有时并不恰当,甚至给读者以“搞笑”的感觉。尽管这些盗墓者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放浪不羁,却有着果敢决绝的意志力,他们不但完成了一段常人无法想象的云南历险,还借此解开了一段“远古时代的迷雾”。小说通过诸多惊险离奇情节的推进和叙述,不但满足了网民对充满新式的“灵异和科幻色彩”与“藏宝图式的传统探险元素”②的故事叠加的阅读期待,还消解和批判了古滇国献王这类统治者的成仙心理,从而彰显了迟来的正义及其限度的社会意义。
一、虫谷历险与远古迷雾
《云南虫谷》顺延了《鬼吹灯之龙岭迷窟》的情节,讲述了“我们仨”——“我”(胡八一)、“胖子”(王凯旋)和Shirley杨,为了拯救自己和扎格拉玛部族后裔被鬼洞诅咒的命运——四十岁以后会死于极为痛苦的“铁缺乏症”,将探险视域从西部地区转向西南地区——去云南虫谷盗掘献王墓,寻找能够解除鬼洞诅咒的上古三大神珠之一的雮尘珠(即地母所化的凤凰),并最终将已经与献王头颅融为一体的雮尘珠成功带回北京的故事。献王是古滇国的一代国君,该国由秦始皇下设的三个郡组成,秦末楚汉相争时,这三个郡的首领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封闭了与北方的交通往来,自成一国,到了古滇国的末期,汉武帝向献王索要雮尘珠,但献王将一枚冒充的影珠送给了汉武帝,将真的雮尘珠藏匿起来,并妄图借助这件神器脱胎换骨、得道成仙。古滇国虽是一个南疆小国,国力并不雄厚,但献王竭全国之力来修建其陵墓,修陵人数始终维持在十万左右,总共花了二十七年的时间,终于在“水龙晕”中建成了一个“殊难为外人所破”③的墓穴。透过“我们仨”的探险、探秘和探究,读者不但可以知悉献王墓的梦幻奇特之处,更可以洞悉信奉邪神的献王为了一己私欲所展现出来的人性中的恶魔性。为了“尸解成仙”和防止盗墓,献王利用痋术害死了几万滇国百姓,其中包括两万多名少数民族女性。就这样,作者借助掩存于云南蟲谷中的墓葬符码,揭开了古滇国墓葬文化的神秘面纱,也凸显了献王这类统治者令人咂舌的歹毒心理和无情虐杀滇国百姓的残酷手段。换言之,《云南虫谷》表面上是在书写“我们仨”在虫谷的所见所闻所感尤其是惊心动魄的历险过程,但实际上更像是一段“我们”在虫谷的“漂泊”纪录。“漂泊”之旅既是一次冒险、盗墓之旅,也是一次解密和发现之旅。
小说一开始,写“我们仨”从北京乘火车南下昆明,再转道奔赴遮龙山(当地人称为“哀腾”,即“无尾龙”),所乘汽车在半路上压破了一个里面生满蛆虫的人形石俑。这样的石俑被本地人视为“不吉的征兆”,但在遮龙山附近有很多,它们都埋在山里,有时赶上山体滑坡就会显露出来。人形石俑的出现预示着“疾病和死亡”,也预示着“我们仨”此行的凶险和诡异;同时,它还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表明作者根本无意于讲述一个普通的盗墓故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依据从陈瞎子手里得来的人皮地图,进入虫谷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遮龙山上的风口翻越,一条是沿着蛇河绕过遮龙山。“我们仨”选择了第二条路线,驾着竹排顺着地下河驶进了遮龙山的腹地。在遮龙山深处的洞穴里,“我们”看到了难以想象的奇景,到处是嶙峋怪异的钟乳石,有的像观音菩萨,有的像酣睡的孩童,有的像悠闲的仙鹤,有的像牛头马面、面目狰狞凶猛的野兽,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数魔幻般的场景和美得“触目惊心”的奇景令“我们”觉得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迷宫”。随后,“我们”看到地下河流进了一个巨大的似虎似狮的兽头口中,它好像正在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咆哮,露出满口的锋利獠牙,想要吞咬一根倒悬在河道正中的朱红色天然石柱,而时间就凝固在了这一瞬间,它的姿势被定格,由于河道刚好从它的大口中通过,因此“我们”面对的就像是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更可怕的是兽门后的洞穴顶上用铜链悬吊着无数倒背双手且呈被捆绑姿态的石人俑。这些人俑都是用活人做的,所使用的正是滇南古老邪恶、臭名昭著的痋术。痋术以死者的亡灵为媒介,冤魂的数量越多,痋术的威力就越大。这些死者很有可能是修造王陵的奴隶和工匠,为了保守献王墓的秘密,他们在工程完毕或者献王尸体入殓后,被捆绑结实和强迫吞服一种痋引(含有痋虫的药丸),并被封死七窍后吊在洞中活活憋死,三五天后痋卵大量产出,人体的血肉内脏全成了虫卵的养分,由于在短时间内快速失去水分,人皮会迅速干枯,硬如树皮石壳,而当虫卵吸尽人体的汁液和骨髓后,人体就会形成一个真空环境,虫卵不见空气就不会变成幼虫,始终保持着冬眠状态。在阴凉的环境中,人皮外壳可以维持千年以上,所以直到“我们仨”前来盗墓,这种痋术依然在起作用。此后,“我们仨”将遭遇诸多因痋术所带来的可怕凶险,小说也逐渐展现出一种劫运难逃的恐怖氛围。当然,沿着“我们仨”的故事,小说不但显现了作为摸金校尉的“我们”对自己盗墓使命的选择,更写出了献王作为守墓者利用痋术守陵和害人的事实。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启蒙文学,如何启蒙民众实现现代化这一近现代中国最大的道统,一直是新文学家们自觉承担的重要使命,为此,“如何在包括民族国家认同在内抽象的现代性知识与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之间进行‘跨语际实践,将‘个体讲述到一个故事中去,讲述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内中,一直是新文学家终极的目标。④”但这一目标或曰“路标”在21世纪中国文学中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娱乐至死”的心态令读者尤其是网民们不再仅仅聚焦于关涉民族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他们开始日益关注个体的奇遇、冒险、秘闻和僭越行为,反映在文艺领域,同样是追求文艺大众化,新世纪文学尤其是盗墓文学利用网络这一媒介,不仅实现了文艺大众化,更实现了大众的文艺化,即通过网民参与或曰集体智慧来完善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细节知识,甚至让参与者生出“没有人是作家,也没有人不是作家”的成就感。反观《云南虫谷》,它成功地将盗墓叙事与大众诉求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三个摸金校尉的虫谷历险,反映了一个旧时代历史主体——封建帝王——成仙梦的荒诞与破灭。当“我们仨”摆脱各种怪物的攻击终于打开人形棺椁看到献王尸首时,他的五官都已经变得模糊扭曲,只留下些许痕迹,口、鼻、双眼几乎难以分辨,好像是融化在了脸上,他的肉身虽然保存得极为完好,但根本就没有“尸解成仙”。由于“我”猜到献王口中含了雮尘珠,所以毫不客气地用工兵铲和伞兵刀割去了他的人头,至于其剩余的尸体则随尸洞一起变成了一堆腐臭的烂泥。这意味着在“未来世界”或曰现代的时空维度中,献王的尸体最终完成了“尸解成泥”,并与他的帝王时代和以人为奴的陈腐观念一起被现代人所批判和扬弃。
小说结尾部分,作者通过“我”的回忆,引出了“我”在西藏大凤凰寺的遭遇,“我”和连长等战友闯入格萨尔王封印魔国的一处密宗禁地,与狼群搏斗,在一块从坟里掘出的古碑上看到了一幅展现藏地上古传说中的场面的鬼母击钵图,亲眼看到大凤凰寺附近水塘中的怪物伸出一只大如车轮的青色巨手抓住战友大个子,使他的半个膀子全部干枯萎缩如脱水干尸,又通过军医格玛知悉了魔国国君所掌握的“达普”(妖魔之虫)焚烧煎熬炊事员老孙的惨况,还在一座古坟里亲眼看见了达普鬼虫烧死卢卫国以及白狼杀死敌特徐干事的情景。此后,“我”跟随部队进昆仑山深处施工。如今,“我”发现藏地古尸穿戴的特殊服饰和表情与献王墓所建铜人狱墓中的壁画非常相像。种种迹象表明,献王所信奉的邪神和使用的邪术来自藏地。如此,作者将故事的悬念再次构建和保留起来,为下一部《鬼吹灯之昆仑神宫》的情节演绎做好了铺垫。在小说中,作者对“我们仨”的盗墓行为进行了“道德化”处理,这一修辞手法的运用,以献王头颅的被砍象征着旧道德的被“斩首”,无疑既形象又深刻。或者说,作者表面上是在写盗墓故事,内里实则在进行道德审判,这也是他一定要在结尾插入“我”和战友们在藏区鬼母坟和鬼子坟遭遇“达普鬼虫”等恐怖经历的原因。因此,在一定层面上,“我们仨”去云南盗掘献王墓不是一种普通的盗墓行为,而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活人与死人的殊死搏斗,这段盗墓生活的开始,也是一种新的道德观构建和文化政治的开端。
二、邪恶痋术与恶魔性因素
在《云南虫谷》等系列《鬼吹灯》小说中,“欲望”是天下霸唱创作中的一个隐形结构,它既指向统治者妄图死后富贵或得道成仙的贪欲,也指向摸金校尉的盗墓渴望和探秘诉求。而作者对古代帝王、达官贵人丧葬文化心理的质疑和批判,对财富应归还于民的民间观念的认同,对社会人士异能奇术的钦羡以及对民间原始道义的强化,都令他倾向于挖掘和揭露献王这类统治者的邪恶心理或曰恶魔性因素。“恶魔性是指人性中有一种阴暗的因素,以创造性与毁灭性同时俱在的狂暴形态出现,常常被正常道德观念理解为‘邪恶,但在社会发展中又是不能忽视的人性因素。⑤”这种恶魔性会使得统治者做出令人惊骇的可怕行为和罄竹难书的滔天罪恶,反映在《云南虫谷》中就是所有令人感到恐怖、愤慨的物与事均源于献王施展巫邪痋术所造就的怪物和惨景。献王利用痋术把怨魂转嫁到其他生物身上,使无毒无害的生物变成致人死命的武器或毒药,死者临死前的痛苦和怨恨越重,痋术的威胁和威力就越大,对其他生物造成的危害就越高。
在小说中,“我们仨”遇到的痋术之一是“痋蟒人体”的攻击。献王主墓的陪陵中安葬了一位陪护其亡灵的主祭司,后者在献王入殓后,利用痋术将一条以人俑为食的凶暴巨蟒活剥后同自己的尸身一起殓在一口用西藏密天玉制成的棺材中,并以两株夫妻老榕树为坟,其位置处于献王墓的“烂骨穴”。所谓“烂骨穴”:“即是陰不交阳,阳不及阴,界合不明,形式模糊,气脉散漫不聚。阴、阳二气分别是说,行于穴位地下的气息为阴,溢于其表的气脉为阳。丛林中潮气湿热极大,地上与地下差别并不明显,是谓之‘阴阳不明。地脉气息无止无聚,又无生水拦截,安葬在这里,难以荫福子孙后代,仅仅能够尸解骨烂,故此才称作‘烂骨葬或‘腐尸埋。⑥”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地方本来不适合葬人,但以树为坟的方式改变了这里的风水格局。主祭司的尸体下葬后,老榕树被痋蟒中人俑的怨魂所寄生,变成了一种助纣为虐的自然生物,痋蟒则在棺中生出无数红色肉丝并穿过“莨木”棺底连接到老榕树的内部,人尸、痋蟒和玉棺全部连接在一起后再也无法分开,且这些红色肉丝可以攫取活物,吸食它们的血髓,从而维持了祭司尸体的不腐不烂。出于解开老榕树身上发出的幽灵般的摩尔斯求救信号之谜,“我们仨”上树求索,结果被这些蚯蚓状的红色肉线所缠,它们仿佛会自动生成和复制,斩断一个又出来三个,好像带血的蛔虫一样不停地扭曲蠕动着逼近,恶心得令人想要呕吐,如果不是“我”急中生智,将红色肉线得以滋生的本源——盛满动物鲜血的玉棺用冲锋枪打碎,“我们仨”也将与其他遭难的飞禽走兽和那名来华助战的美国飞行员一样被它们吸尽血髓,沦为滋养祭司尸体的血液给养体。同时,在老树下还埋着一个负有献王墓陵谱的椒图,用以镇压王陵附近的邪气。显然,上述描写已经把献王及其手下的魔鬼性情初步凸显出来,献王还没有“出场”,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善用邪术和诡计的大祭司。小说随后的故事发展更加“荒诞不经”,叙事视角沿着洞穴的纵深不断延展,却把献王生前阴毒凶残、迷恋权势和妄想成仙的病态心理充分揭示出来。
“我们仨”遇到的痋术之二是痋女怨念的折磨。“镇陵谱的浮雕中,最高处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月城、角楼、内城、瘗碑、阙台、神墙、碑亭、献殿、灵台等建筑一应俱全。后边的山川都是远景,宫殿下没有山丘基石,而是数道霞光虹影,凌空步烟,四周有飞龙缠护,显出一派超凡脱俗的神仙楼阁风采。⑦”这是献王墓地上明楼的造型,这座空中楼阁威严森然,宛如人间仙境。“琼瑶仙境”既是献王欲望的终点,也是献王墓“神话”的发端。当然,真正的仙境在人间并不存在,结果“尸解成仙”成了献王内心世界恶魔性得以投射和膨胀的引子,他害死数万人修建王陵,不过是为了彰明自己死后的地位和满足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欲望。为此,他使出各种邪术尤其是痋术来制作毒雾避免外部势力入侵以便保护王陵。他牺牲两万多名夷女的性命制作出一条邪恶的“痋毒生产流水线”。这是一场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大规模“牺牲”,他用“痋引”使妇女感孕生产虫卵,在她们十月怀胎生产虫卵之时,将她们折断四肢并反抱住刚产下来还没有完全脱离母体的“痋卵”,然后立刻用一种类似于烧化的热松脂或是滚沸的树胶的东西,活活浇在痋女身上,连同她们背后的“痋卵”一起,做成透明的“活人琥珀”,等冷却后,在表壳上刻满“辵魂符”,这就等于把她们死亡时的恐惧、哀伤、憎恨、诅咒都一起封在了“琥珀”里,并通过身体传进她们死时产下的虫卵中,如此,这些虫卵才有毒性。而那些刚被痋女产出的“痋卵”生命力很强,不会被轻易烫死,它们通过细孔吸食水中浮游生物,在无尽的怨念中生存。这些怨念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气场,令人产生莫名的忧伤、失落、孤独、压抑、沮丧和梦魇般的恐慌感。如果外来者求生意志不够强大,就会被这种怨念所缠,直至失魂落魄。
“我们仨”遇到的痋术之三是痋虫毒雾的侵袭。献王占有“虫谷”附近领地后,觉得这是处风水绝佳、天下无双的仙妙灵慧之地,又在“葫芦洞”里发现了被当地夷民供奉的“山神”,即一只巨大的远超人类想象的远古神秘生物“蜮蜋长虫”(又称“霍氏不死虫”),这只半石化的巨虫身体的某一部分就在山谷里。献王禁止当地人再向这只巨虫供奉有毒的大蟾蜍,待巨虫散尽毒气、无力反抗时,把它装进一套厚重的“龙鳞青铜甲”中,戴上一个有着某种宗教色彩的“黄金六兽面具”,加上某些不为人知的神秘手段,把这条仅存于世的虫子折磨得半死不活。然后利用它吞吃水中“痋女”背上“痋卵”的排泄物——一种仿佛鱼卵的肉菌类生物,这些排泄物附着在痋女的外壳上,在长成透明蛆虫样子后,会被巨虫体内散发的鲜红雾气吸引,然后随同女尸一起靠近巨虫并被它吞掉,那些肉菌会被巨蟲消化,而死者怨念所形成的“痋毒”会通过巨虫的躯体转化为虫谷中常年不散的含有剧毒的白色“山瘴”,令近者即死,从而保护献王墓不被外来者所入侵。为了防止巨虫将女尸排泄掉,献王命人将土人视为守护大山的神明——三只山魈杀死,加上夷人的宝物神器——玉胎放在一具四四方方的铜质棺椁中,一起填进巨虫肚内,用这种变态手段来破坏当地人的信仰,也使其成为阻止巨虫消化浮尸与虫卵的“胃瘤”。当巨虫无法消化又不能直接将裹有硬膜的女尸排泄出去时,它只好将她们原样呕吐回水潭里。然后,那些在痋女身上的痋卵又会按照原样吸食浮游生物,排除肉菌,浮出水面被巨虫吃掉吐出,不断地轮回往复。由于巨虫吞噬毒物和排放毒雾,“我们仨”难免会受其毒害,好在事先准备了防毒面具,才没有被巨虫的毒气毒死。
“我们仨”遇到的痋术之四是痋婴的围攻。痋婴是一种看起来半人半虫的怪物,前肢上长有吸盘,身体具备了人和昆虫的多种特征,它们发出的是比夜猫子叫声都难听的嘶哑哭声。由于巨虫被“我们仨”打残,不再释放能够让痋婴保持睡眠状态的红色雾气,所以它们突然从痋女母体中脱离,并对“我们仨”发起了疯狂攻击。它们的嘴部会朝四个对角方向同时裂成四瓣,每一片的内部都生满了反锯齿形倒刺,如同昆虫的口器,被这种怪口咬住是难以挣脱的,还会被其满嘴的黑汁毒液毒杀,且这种痋婴的生命力极其顽强,除非它们的头被打得稀烂才会彻底死去。更糟糕的是,这种痋婴非常多,加之处在洞穴中,不利于逃亡,所以“我们仨”面临的处境可谓险象环生。这种痋婴还善于游泳和攀援,且分裂和生长的速度很快,只一会的工夫,它们的身体就比先前长大了一些,脱离了婴儿的形状,显现出了更加明显的昆虫特征。幸亏防止虫子越界的“毒道”和不同于山洞气候的自然环境暂时阻隔了这种痋婴的集体攻击,否则“我们仨”难免要沦为它们的食物。
“我们仨”遇到的痋术之五是人俑体内产生的水彘蜂和尸蛾的攻击。“我们仨”的竹筏在遮龙山内部的地下河中漂流不久,挂在岩顶的人俑便接二连三地掉进河里。从人俑身体的裂缝里冒出了很多干枯的虫卵,它们见水即活,迅速膨胀后变成手指肚大小的水彘蜂(蚂蟥),这是一种在云南令人谈之色变的浅水生虫类,游动的速度极快,咬人吸血很是厉害,幸好不能飞出水面,加之它们被蟒蛇和刀齿蝰鱼啃吃精光,“我们仨”才免于被它们吸血。在某种层面上,这体现了自然界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的道理。而在献王墓中,“我们仨”碰到了更为可怕的尸蛾。当镶嵌在墙上的献王王妃尸首倒下来后,尸体膨胀得极快,皮肉在顷刻间被撑成半透明状,尸身砰然破裂后喷散出了无数飞蛾,它们体内都是尸粉,沾到活人皮肤上就会起尸斑并令人中毒,这些尸蛾身体有几分酷似人形,不但令人毛骨悚然且极为悍恶,它们即使被丙烷喷射器喷出的火焰烧着也仍然会向前猛冲攻击活人,直到翅膀烧尽后落在地上还不停地扑腾。“我们仨”拼命逃进墓室,用梯形铜棺和黑驴蹄子堵住那个王妃原来所在的人形缺口后才逐渐解除了它们的威胁。献王将自己的尸骸安葬在一个巨型肉芝太岁的尸壳里,而这肉芝太岁的外壳是拿人尸制造的,人尸一遇到活物就会伸手将之拉进万年老肉芝的尸壳里,使之化为尸洞的一部分。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献王居然用痋术将自己的王妃制成可以喷出尸蛾的痋尸,然后在封住阴宫时将她的尸首塞住肉芝太岁的太岁眼,将自己的尸骸葬在另一个太岁眼——人形肉椁之中。对自己的王妃尚且如此狠毒,可见献王的魔鬼性之强。
透过《云南虫谷》可知,献王把“尸解成仙”的自我欲望置于首位,从而遮蔽了其人性中最基本的善念,这本身就是封建时代人性异化的重要标志。献王本想通过建立空前绝后的陵墓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高贵和霸权,但最后留下的不过是令人极为心悸、厌恶和恶心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来讨论献王这类统治者与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的关系,那样不过是重复了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做过的工作。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通过“我们仨”的历险过程展现了献王是如何被成仙欲望激发出魔鬼性的,又是如何以痋术这种反人类的罪恶方式推进其“成仙工程”的。应该说,《云南虫谷》中所涉及的痋术大多是作者创造和虚构的,但帝王们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恶魔性穿行在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丑陋而狰狞地展现了人性的阴影和深层中的恶意。
三、迟来的审判与正义的限度
《云南虫谷》反映了古代帝制在古代中国引发的官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不可調和的阶级矛盾。对于古代以巩固帝制和自身统治为终极目标的帝王来说,他们必然要面临这种冲突和矛盾。因此,他们无论是对于自己生前还是死后的地位、利益和“享受”都要设法加以保障。这就催生了厚葬习俗和防盗体系,但暴君终归要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在小说中,献王的尸体化成了尸洞中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狂追“我们”,但随着他所葬其中的乌头肉棺冲到虫谷谷口被“青龙顿笔,屏风走马”的风水形势挡住,附着在其上的混沌凶煞顿时烟消云散,尸洞流出了无数污水,最后只剩下一个房屋大小的肉芝尸体,而被尸洞腐蚀掉的全部事物(包括献王的尸体)都在腐烂后归于尘土。如此,作者通过对恶毒献王尸骨无存结局的设定和道德意义上的终极审判,折射了正义的力量。与此同时,如果说“我们”的宿命是通过拯救自己来拯救族人,那么“我们”与历史迷窟以及统治者恶魔性的斗争和缠绕,就构成了《云南虫谷》故事情节和话语实践得以延展的内在逻辑和核心命题,这些情节具有强烈的“重力感和命运感”⑧,可以引发读者对人的存在意义和正义的限度等问题的哲学思考。
《云南虫谷》写出了发生在古滇国的墓葬文化政治。为了追求权力和仙道,献王已经变得极其疯狂和变态。首先,献王陵区的风水形势都是半天然、半人工的,可以说这些所谓的宝穴都是改格局改出来的,完全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逆天而行”。其次,献王穷奢极欲,将自己的陵墓建成一座壮丽神秘、令人目瞪口呆的“天空之城”:“无数条彩虹托着半空中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宫阙中阙台、神墙、碑亭、角楼、献殿、灵台一应俱全,琼楼玉阁,完全是大秦时的气象,巍峨雄浑的秦砖汉瓦,矗立在虹光水汽中,如同一座幻化出的天上宫阙。⑨”这也是一座整体的大型歇山式建筑,如同世界闻名的悬空寺一样,以难以想象的工程技术修建在悬崖绝壁的垂直面上,四周山壁植物掩映,加之山间七彩虹霞异彩纷呈,使人猝然产生一种目睹海市蜃楼的梦幻之感。这么大的王墓安全超乎后人的预想,其背后所隐含的却是无数工匠的尸骨累累和血泪控诉。再次,献王不仅生前作威作福,死后还要让自己的陵墓永世长存。他将自己的陵墓明殿建在水龙晕的风水格局中,在清浊不分明的环境中,让宫殿建筑保持了上千年依然如新,成了真正的“凌云天宫,会仙宝殿”。在作者看来:“宫殿这种特殊的建筑,凝结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与技术的全部精髓,是帝王政治与伦理观念的直接折射。⑩”因此,献王古墓建筑群中的“凌云宫”“会仙殿”等名称,无疑体现了献王追求长生不老的妄念,所以他借助“我”之口嘲骂道:“献王大概想做神仙想疯了,以为在悬崖峭壁上盖座宫殿,便能请神仙前来相会,陪他下棋弹琴,再传他些长生不死的仙术。?”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种成仙心理确实可笑,不过是一场“如光似影的梦”,但帝王们为了生前死后都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往往逆天行事、不顾百姓死活。对于这种淫欲无度的帝王,老百姓们寻求正义的方式只能是造反,一旦成功就盗掘帝王的坟墓,抢劫一空后还要将帝王尸体挫骨扬灰方解心头之恨。献王虽然没有死于百姓之手,但百姓对他的仇恨心理无疑是非常真实和厚重的。
《云南虫谷》展现了作者重塑“民间正义”的潜在动机。民间正义追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式的公平公正。为了实现这种正义追求,民间所持有的手段是非常野蛮和原始的,这自然有其不足之处,也往往缺乏法律依据和官方支持,但这有其合理性,也更具真实性和有效性。为此,作者将摸金校尉盗取献王墓的行为称为“尽人事,安天命”,他消解了帝王们愚弄百姓的造神论,“到了现代,神明只不过作为一种文化元素,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可以看作是一个精神层面上的寄托”,因为人们业已知道,尽管伟人会被捧上神坛,但不管他多么伟大和杰出,都难逃生老病死,所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不会有神,人毕竟还是人”。由于统治阶级的财富均来自对老百姓的剥削,因此摸金校尉对于帝王墓葬中的财宝自然不会客气,正如“胖子”所说:“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献王死都死了两千年了,估计成仙不死是没戏了,没烂成泥土就不错了。他地宫里的陪葬品,也陪着死人放了这么久,是时候拿出来晒晒太阳、过过风了。?”献王墓中的陪葬品几乎把整个滇国都埋进了墓坑里,这里有财宝,更有臣民和奴隶,对于这些财宝的处理方式只能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至于献王的尸体则被心窝里插进桃木钉,头颅被砍掉带走。这等于验证了民间关于正义来临的说法:“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必定来报。”死后尸体被辱乃至死无全尸,这是献王生前最害怕的事情,可最后还是怕什么来什么。在民间看来,这是一种报应,也是一种命运的象征。献王的残暴酷虐、倒行逆施和骄奢淫逸,注定了他未来尸骨无存的下场,这就形成了对其追求仙道心理的辛辣讽刺。换言之,重塑“民间正义”一直是《云南虫谷》等盗墓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民间正义的衰落固然在网络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但迟来的审判终究是要来的,正义的效力也终究是要显现的。
《云南虫谷》形象地思考了生与死、黑与白、正与反的问题,体现了天下霸唱求索正义的有限性等问题的社会意义。在帝王们看来,他们在亡灵世界里依然应该洪福齐天、尽享荣华,但问题在于,墓穴里的时间是停止的,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已经终结,也意味着他们所赖以寄托成仙得道的理想信念的词语“不朽”“永生”“万代”等都将失去存在根基和“原有的意义”?。这也算是“原始正义”彰显作用的一种表现。当然,正义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所有的邪恶和罪过都能受到及时审判和应有惩罚。对于那些屈死的冤魂来说,献王尸体受辱及其陵墓被毁固然体现了正义的力量,但这正义来得实在迟了些。西方谚语强调“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也就是说,对于渴望正义的当事人或受害者而言,迟来的正义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非正义的东西。所以阿图尔·考夫曼说:“正义的许多原则——各得其所,黄金规则,绝对命令,公平原则,宽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认为超越了一切历史经验,实际上为一空洞的公式,它们也不存在什么优先规则。这些原则只是在形成中,即它们如何在各自时代背景下展现内容,才具有含义和顺序。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把握和完成我们今天的使命。?”这里,他强调了正义的时效性和“时人”追求正义的责任与使命。但从民间的视角来看,正义迟来总比不来要好,迟来的审判和正义的限度对“后人”依然具有道德告诫的隐喻意味,这同样是一种社会正义和道德意义得以发生作用的标志。至此,民间视角的介入体现了作者朴素的正义思想和感性的个人体验的独异性,体现了他赋之以文学性表达的严肃性和审美性,也体现了其思维方式中民间性和现代性的绞缠互动。
注释:
①舒威铃.“惊悚悬疑”背后的现代心理追求——探析网络小说《鬼吹灯》的内在意蕴.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4):59.
②天下霸唱.鬼吹灯·后记.鬼吹灯8巫峡棺山.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444.
③天下霸唱.鬼吹灯2龙岭迷窟.青岛:青岛出版社,201:248.
④李杨.“人在历史中成长”——《青春之歌》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2009(3):97.
⑤陈思和.欲望:时代与人性的另一面——试论张炜小说中的恶魔性因素.文学评论,2002(6):62.
⑥天下霸唱.鬼吹灯3云南虫谷.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83.
⑦天下霸唱.鬼吹灯3云南虫谷.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93.
⑧天下霸唱.鬼吹灯·后记.鬼吹灯8巫峡棺山.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445.
⑨天下霸唱.鬼吹灯3云南虫谷.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197.
⑩天下霸唱.鬼吹灯3云南虫谷.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212.
天下霸唱.鬼吹灯3云南虫谷.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213.
天下霸唱.鬼吹灯3云南虫谷.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259.
刘纳.《说鈤》·新物理学·终极——从一个角度谈鲁迅精神遗产的独异性和当代意义.中山大学学报, 2006年(6):46.
[德]阿图尔·考夫曼等.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53.
本文为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立项建设项目“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程优秀教学团队”(编号:粤教高函〔2014〕97号)、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编号:粤教高函〔2015〕72号)基金项目。
陈红旗,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副院长,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