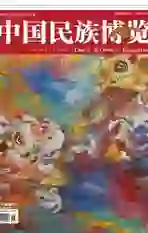论唐代狐怪故事的叙事技巧
2019-07-09闫翥骐
【摘要】狐怪小说是唐代众多小说类型中的一种,多记载狐怪的变形、法术等。狐怪故事在唐代文化的土壤中自成一体且记载颇多。本文以《太平广记》中“狐”类所收录的狐怪故事入手,分析唐代狐怪故事的叙事技巧,以及唐代的叙事艺术如何超越魏晋六朝、将故事结构变得更加丰富深曲的。
【关键词】唐代;狐怪小说;叙事技巧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狐的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魏晋时期的志怪笔记中已有不少关于狐怪形象的描述和对于狐怪故事的记载。《玄中记》有:“狐十五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①《异苑·胡道洽》云:“胡道洽(狐怪)……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弟子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②魏晋南北朝笔记中虽然留下了不少关于狐怪的记载,但是其故事性并不是很强,多数记叙还处在“志怪”的层面,没有像后来唐代记载的故事中运用叙事技巧来展现一个更为曲折的故事情节。唐代记载的狐怪故事与魏晋六朝的记载最大的不同便是由分散的、志怪性的记载转向了具有丰富情节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情节曲折且叙事技巧丰富的唐代狐怪故事甚至可以被视为现代意义上优秀的短篇小说。
在唐代,狐与人们的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就为唐代狐怪小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朝野佥载》云:“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③这种民间信仰的普遍反映出狐文化在唐初以来的流行,狐怪文化普遍地深入人们的信仰体系之中。狐文化的盛行丰富了唐代狐怪小说的叙事,比如《纪闻》中《张长史》与《田氏子》都是关于生活中误会的故事。前一则讲张长史去找被女婿欺负的女儿,而误入全节县。当赵县令看到张长史的异常行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他被狐魅附身,进而真地将他当成了狐魅鞭打;后一则记载了山路中老仆人与妇人相遇,互相都将对方误以为是狐怪的滑稽之事。像这类产生误会的故事,因其情节往往非常曲折,所以在叙事上也必然会曲折而丰富。
在两则故事的叙事中,都着重描写了一方因为狐疑而对另一方态度的改变,于是在叙事层面上产生了一种转折的效果。事实上,误会类的故事本身就包含了误会及误会的解决两个部分,连接这两个部分的正是叙事中必要的转折。作者在叙事中先不交代事情的真相,而是故意留下一个“悬念”来制造戏剧性的效果,在双方误会发生以及解决误会之后,最终真相也自然明了。于是,误会类的狐怪故事因叙述中存在的事实的延宕而在叙事上变得曲折而富于变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一类叙事与狐变身成为人有关,此类故事往往讲述的是狐怪变身成为人之后与人类发生的种种故事。从《太平广记》所引用的材料来看,“狐”类故事多数都有狐怪变身为人类的情节。《广异记》中的《李参军》《李元恭》《谢混之》《薛迥》《李黁》,《纪闻》中的《王贾》《沈东美》,《宣室志》中的《尹瑗》《计真》《韦氏子》,《灵怪集》中的《王生》,《大唐奇事记》中的《昝规》,《三水小牍》中的《张直方》等都有对狐精变形为人类之后的细致刻画和描写。
在众多故事里,狐怪的人类形象是多样的,有富豪甲族之类,有谈吐風流的公子之类,还有各种妇人,也有白发银须的老翁老道等,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三水小牍》中的《张直方》。
《张直方》主要讲述了范阳节度使张直方幕僚王知古雪天打猎,误入狐怪巢穴,狐怪变身为众妇人,宴飨王知古,并意欲招其为婿,后因得知王氏为张直方幕僚而作罢的故事。如果我们对情节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故事的主要叙述部分在王知古如何误入狐穴以及群狐飨宴王知古的部分。
小说情节曲折,其中狐怪宴飨王知古的情节描写尤为精彩。
无何,小驷顿辔,阍者觉之,隔壁(按,尚在外)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惟闺闱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问于内(按,将入内也)。”……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按,入矣)。……
保母亦时来相勉。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宦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家室为望,惟泥涂是忧。……睠以佳耦,则生平所志,毕在斯乎!”
保母喜,谑浪而入白(按,入答小君也,入)。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忻慰孔多,倾瞩而已。”……知古复拜(按,拜一),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貌如月华,室若云邃,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谁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按,拜二)。④
小说为了引出狐精之女,设置了重重“门槛”。首先是看门人与王知古的对话,由此引出保姆,再由保姆与王氏的对话引出狐女,然而此时并未见狐女本人。在狐女出场之前,以两个人物渐相引出主要人物,通过人物的对话一层层、如抽丝剥茧一般展开故事。这样的叙事手法使故事情节变得非常丰富,就如园林之中障景的手法一般,将一个情节并不丰富的故事通过叙事技巧变得曲折有趣。
这种对于情节的延宕在唐代狐怪小说具体的篇章中又各不相同。如《宣室志》的一篇故事中: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四年秋,自邑中游焉。
日暮,见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与纸笔书其事,妾得以执诣邑长,冀雪其耻。”韦诺之。
妇人卽揖韦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巵,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巵(按,横云断山),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卽东走数十步,化为一少狐。韦大恐,视手中巵(按,接续前,文理细密),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⑤
情节并不复杂,讲野狐精欲害韦氏子而被识破,露出原形逃跑的故事。在这个段落的描写中,当韦氏刚要举起酒杯喝酒的时候,作者突然横插一笔,突来的一队人打断了故事的进程。这种手法可以视为一种“横云断山”法的延宕。在情节之中突然生出事来,当妇人化为狐狸之后再接续韦氏手中的酒杯,造成剧情上的跌宕。虽然故事短小,但在情节的处理上很注重叙事手法的使用。
在狐怪与人斗法类的故事中也会使用一些手法使叙事跌宕起伏,增加情节的悬念感。《广异记》中《汧阳令》有狐怪与罗公远斗法的情景:
……寻至所居,于令宅外十余步设坛。成策杖至坛所,骂老道士云:“汝何为往来,靡所忌惮?”公远法成,求与交战。
成坐令门,公远坐坛,乃以物击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击公远,公远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数十,公远忽谓弟子云:“彼击余殪,尔宜大临,吾当以神法缚之。”及其击也,公远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为之备。公远遂使神往击之,成大战恐,自言力竭,变成老狐。公远旣起,以坐具扑狐,重之以大袋,乘驿还都。⑥
作者为了增加斗法情节的曲折跌宕,故意设置了罗公远使用诈术骗狐怪的情节,于一来一往的斗法之间横生变数。类似的情节在《广异记》的《长孙无忌》中变成了颇有道行的崔参军开始请十二辰之神禁制天狐不得,又转请五岳山神才将天狐束缚。小说往往设置一个阻碍,人与狐的斗法并不是顺行而下的,而是经历起伏跌宕,有时候看似狐怪占据上风,但是最终被人类所擒。这种手法又照应了前文所说的障景之法,增加了小说的魅力。
唐代狐怪故事中《崔昌》《刘众爱》《祁县民》等都是专门讲述狐怪无意暴露出动物身份的故事。《崔昌》中记载一老人醉酒,而“吐人之爪发等”,这是狐怪在喝醉酒之后失去控制力,呕吐出了吃下的人的爪发。《刘众爱》记载了刘众爱夜间遇到一个妇人,而妇人直接抓起老鼠生吃的事情,也是从狐的觅食习性来刻画狐怪形象。《祁县民》讲述了某村民路遇妇人,而妇人无意中露出狐狸尾巴的故事,这是从狐狸的尾巴是其明显的身份标识来刻画的。另外,大量的狐怪小说都会有狐怪遇到猎犬现出原形的描写,这是从狐天性怕犬类的特征方面着手构思的。沈既济著名的《任氏传》就写到了任氏因见到猎犬而现出原形。
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来刻画狐怪的形象,这些唐代小说都顾及到了狐怪形象的人格特征和动物特征的双重性。一方面是人的形象,另一方面带有鲜明的能代表此类动物特征的行为,将两种特性汇集在一个形象身上,给小说带来了很大的新鲜感,将精怪拟人化来写,但实际上脱离不出动物的本性。
中国古典小说的这种艺术手法被广泛运用在谐隐精怪小说、神魔小说等不同的小说类型之中。比如写孙悟空,虽然是人格化的猴子,但终究保留着作为猴子的机敏、急躁、爱吃桃子等习性;猪八戒则保留了好吃懒做的习性。在唐代小说的叙事中,这样的技巧起到的作用是提示读者精怪的原形,并塑造精怪的特性。这种叙事手法的运用原理也类似于前文所述的设置转折的手法。当读者读到狐怪动物性一面的描写时,就是实现情节转折的时候(因为读者已经知晓了其原形是狐)。
唐代狐怪小说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小说的艺术上说,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狐怪小说的叙事要素和情节模式,很多狐怪小说都可以从唐代小说中找到影子。就其叙事手法而言,不论是采取情节中设置的转折还是情节的延宕,还是在情节中突生波澜,这些手法都是为了使情节更为跌宕起伏,使故事更富有传奇色彩。从这个角度看,唐代狐怪小说中采用的多种手法出色地完成了其叙事艺术的功能。
注释:
①《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七引《玄中记·说狐》条,3652.
②《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七引《异苑·胡道洽》条,3656.
③张鷟,《朝野佥载》,167.
④《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五引《三水小牍》,3714-3715.
⑤《广记》四百五十四引《宣室志》,3712.
⑥《广记》四百四十九引《广异记》,3671.
参考文献:
[1]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牛僧孺.玄怪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李復言.续玄怪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张读.宣室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太平广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作者简介:闫翥骐(1990-),男,山西太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