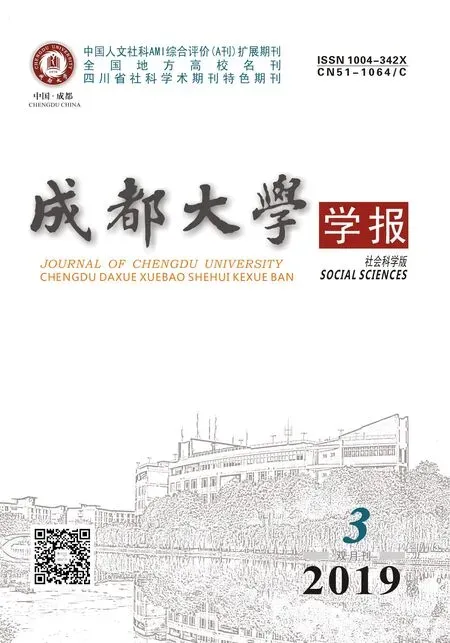《华阳国志》所见西南地区祠庙探赜
2019-07-08舒显彩
舒显彩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志书,“《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我国方志编撰体例的先河,其中保存的大量丰富、翔实的西南地区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民俗和人物等方面的史料更是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4]近年来,时贤们从史料价值、士族文化、民族关系等角度出发,对《华阳国志》展开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就书中所涉及的诸多祠庙,论者颇甚少,以至学界在梳理上古祠庙时,常忽略广袤的西南地区。鉴于此,笔者不揣庸陋,旨在以《华阳国志》所见西南地区的祠庙为切入点,拟对书中的祠祀对象进行系统归纳,而后就祠庙的分布特点作一探索,希望能对进一步认识秦汉魏晋时期巴蜀等地的祭祀文化略尽绵力。
一、《华阳国志》所见祠祀对象
地方祠祀不仅体现着民风民俗,更是“国家礼制与民间信仰的重要结合点之一,它们既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下限,又是地域文化与信仰传统的反映。”[5]220《华阳国志》记载的祠庙达30余座,所涉对象如下:
(一)帝王
“自古帝王统绪相传,易代以后飨祀庙廷。”[6]5886对先代帝王的祭祀,不但关乎存亡继绝,更涉及权力的正当性和统治的合法性。《华阳国志》所载帝王祠庙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以上古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为主,如蜀郡涧山有鱼凫祠,《蜀志》载:“鱼凫王田于涧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涧。”[7]118南中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祠,《南中志》云:“竹王生于大竹之中,遂以竹为姓。”[7]230《文献通考》亦云:“邛州,秦汉并属蜀郡……大邑, 有竹王祠、嘉鱼穴。”[8]8775-8776
又如巴蜀地区的杜宇祠,杜宇即后世所称的“望帝”,其统治期间蜀国国力蒸蒸日上,“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直至魏晋时期,“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7]118

(二)神仙
历史时期,“俗好巫鬼禁忌”的西南地区充斥着大量有关神仙鬼怪的传说,传世文献中亦有不少关于仙人、仙桥、仙药的记载。《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广郡“俗妖巫,惑禁忌,多神祠”[7]279。同书言蜀郡有“升仙桥”,刘琳注引《成都记》曰:“城北有升仙山,升仙水出焉。相传,三月三日张伯字道成得上帝诏,驾赤文芋兔,于此上升也。”[12]231常璩言南安县有仙药,“汉武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药,不能得。”[7]175有学者指出:“《后汉书》所列方术之士共32人,其中巴蜀地区便有8人之多,占总数的四分之一。”[13]受这种神秘主义文化的熏染,神仙自然被纳入西南地区的祠祀之中,江神即为一例。《水经注·江水》引《风俗通》曰:“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冰以其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9]734同书又云:“蜀有回复会,江神尝溺杀人,文翁为守,祠之,劝酒不尽,拔剑击之,遂不为害。”[9]735此外,《华阳国志·蜀志》载犍为武阳县有王乔、彭祖祠,《后汉书·郡国志》“武阳有彭亡聚”条注引《益州记》曰:“县有王乔仙处。王乔祠今在县,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14]3510巴郡江州县有张府君祠,《华阳国志·蜀志》谓:“汉初,犍为张君为太守,忽得仙道,从此升度。”[7]30王乔、彭祖、张府君等得道成仙者受到瞻仰祭祀,与巴蜀地区的神话传说密切相关,反映了人们对永生的向往,“此前只有神明才能拥有的不朽和瑰丽时空,如今被嫁接在人生的延长线上,成为人类也可以期待的生命属性。”[15]33
(三)清官循吏

(四)当地名士

(五)自然生灵

二、《华阳国志》所见祠庙的分布情况
《华阳国志》所载地理空间包括巴、蜀、汉中、南中四大区域辖下的100余县。为明晰各地祠庙的分布情况,兹据书中提供的信息,制成表1。

表1 《华阳国志》祠庙分布表
在此需说明的是,《华阳国志》所载西南地区的祠庙是不完整的。常璩虽谙熟当地的风土人情,但囿于客观条件,他最多也只记录了东晋初期尚为人知晓的祠庙,至于前代业已毁弃或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那部分祠庙,则不可能也无法载入史籍。辅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不难发现,《华阳国志》对“去古未远”的汉魏时期的祠庙记载仍不完全,前文所言李冰、文翁、张翕、韦义、杨厚等清官循吏之祠可资证明。又如《史记·封禅书》概括秦末山川祭祀格局道:“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四大名川之一即为“江水,祠蜀”[20]1372,《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江渎祠在益州成都县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20]1372-1373然考求《华阳国志》,却未言有江水祠,此为一大疏漏。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否认它的史料价值,该书不啻为了解东晋以前西南地区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最权威、最重要的文献,其对西南地区祠庙分布情况的记载较其他史籍更为详尽。


三、《华阳国志》祠庙所反映的巴蜀等地祭祀文化的特点
由《华阳国志》所载祠庙可以看出,西南地区的信仰体系是多元且复杂的,无论是身居庙堂的帝王将相,还是山间水际的花石草木,都可能成为当地民众祭祀的对象。仔细揣摩,这种表象背后所反映的巴蜀等地的祭祀文化又有诸多共同特征,以下分述之。

巴蜀民众更倾向于为明君贤臣和神通广大之人立祠,并不代表该地区就完全忽视对先祖的祭祀。《华阳国志·巴志》云当地有祭祀诗:“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诗歌描绘了民众于孟春时节以黍和牺牲祭祀先祖的虔诚场景。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南门柱北侧所刻画的“迎谒图”亦为当地的祭祖习俗提供了佐证。该图左侧有一右向而立的老妪,她头戴高冠,右手柱杖,左手前伸,似有所指。右边数人作拱手跪迎状,应为妇人之子孙。信立祥先生言:“画面描绘的是子孙家人迎接墓主来享堂接受祭祀的场面。”[26]274图1为1972年出土于四川郫县的东汉画像石棺侧面,有学者将它解读为“宴客乐舞杂技画像”,认为画像中部为楼观式建筑是“当时封建官僚地主寄生生活的宴飨情况”的写照[27];也有学者从画像石所描绘的情景乃整个墓葬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出发,指出“画面表现的是墓主乘车马从地下世界到墓地祠堂接受子孙家人祭祀,并在祠庙中欣赏献祭乐舞杂技演出的场面,图中的二层楼阁就是墓地中的祠庙。”[26]279画中高大建筑究竟是世家大族宴饮娱乐之所,还是生人仿照尘世楼阁为祖先建造的祠庙,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毋庸置疑,即使秦汉魏晋的巴蜀地区存在宗族祠庙,其数量和规模也不可与同时期的关中、关东等地同日而语。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尚未报道此地有早期祠堂类建筑遗址。这表明,巴蜀地区虽存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祭祖行为,但该时期内宗族祠庙的普及程度和对祖先祭祀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中原一带。究其缘由,大概是因为尊祖敬宗乃儒家所提倡的价值观,而巴蜀地区尚道,道法自然,故对祖先神的推崇程度较其他地区为弱。①

图1四川郫县新胜一号墓石侧面图
(采自李复华、郭子游《郫县出土东汉画像石棺图像略说》)
第二,原始的民间信仰和后起的政府力量共同影响着祭祀的发展。多神、泛神崇拜起源久远,本身便具有浓厚的原始色彩。[28]3综观《华阳国志》中的祠庙,有相当一部分是民众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自发建立的,如褒中县的唐公房祠,《水经注·沔水》云:“百姓为之立庙于其处,刊石立碑,表述灵异也。”[9]621又如孝子姜诗为母求得鲤鱼,“所居乡皆为之立祠”[7]565。称江祠、青石祠、方山兰祠等也应是当地百姓出于自然崇拜而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主动整合民间信仰并建立新的祠庙以推动祭祀朝着官方或半官方化发展,秦汉之际,这一现象十分普遍。如蜀郡江阳县有“贵儿祠”,相传为光武帝刘秀敕造,“世祖微时,过江阳,有一子。望气者曰:‘江阳有贵儿气。’王莽求之,县人杀之。后世祖为子立祠。”[7]180严君平祠和李仲元祠也是官府修建,东汉末期,王商任蜀郡太守,“为严、李立祠,正诸祀典。”[7]564政府主导地方祠庙的兴建,表明官方意识形态已作用于地方文化。故有学者将战国秦汉之际视为巴蜀文化的转型期,其理由是“巴蜀文化由一种作为独立王国形态和民族特质的文化,向作为秦汉统一帝国内的一种地域形态和以秦汉文化为符号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的转化。”[29]
第三,巴蜀一带的祭祀文化有着浓厚的地域色彩。有学者道:“巴蜀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两个层次的整合,一个层次是它同秦汉文化的整合,即外部整合;另一个层次是它自身原先的文化在秦汉之后经过重组达到的再整合,即内部整合。”[23]494-495秦汉以降,巴蜀文化的这两次整合并未抹杀其原貌,作为宗教信仰和祭祀文化的载体,《华阳国志》所载祠庙反映着该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和风俗民情。无论是古巴蜀国国王鱼凫、杜宇、蜀侯恽等人的祠庙,还是源于自然生灵的天马祠、黑水神祠、铁祖庙祠,亦或是对清官循吏、当地名士的祭祀,无不体现着巴蜀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这些祠庙的享祭者就是巴蜀文化的缩影,他们或是当地人物,或对巴蜀地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巴蜀民众为大禹设立祠庙,除了他是华夏族的杰出首领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地人坚信大禹生于蜀的传说,《史记·夏本纪》引扬雄《蜀王本纪》言:“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于今涂山有禹庙。”[20]49据考证,今汶川县飞沙关、理县通化乡、北川县禹里乡、什邡县九联坪乃至都江堰市龙池等地皆有石纽山及禹庙的存在,而关于禹的传说故事更广泛流行于川西北地区。[30]再者,巴蜀人所祭祀的王乔、彭祖等神仙,也或多或少掺杂着地域情结。《华阳国志·蜀志》谓武阳有王乔庙,《史记·封禅书》“正伯侨”条引裴秀《冀州记》言:“昔有王乔,犍为武阳人,为柏人令,于此得仙。”[20]1369关于彭祖的记载,见《列仙传》:“彭祖者,殷大夫……历夏至殷末,年号七百,常食桂枝,善导行气……后升仙而去。”[31]38巴蜀人多认为“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7]727故常璩云:“蜀之为邦……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婚,则黄帝婚其女。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起冈。”[7]216-217巴蜀地区大量存在的本土神祠表明,上古时期业已积淀成形的巴蜀文化在融入秦汉大一统的潮流之后,依旧保留着自身的底蕴。
综论之,探研《华阳国志》中的祠庙不仅对进一步认识西南地区的民间信仰、人文景观大有裨益,更有助于加深对巴蜀文化以及其与中原文化关系的理解。一方面,巴蜀文化受中原文化渐染颇深。从战国到汉魏时期,巴蜀地区的祠庙经历了自萌芽至蓬勃发展的历程,这是政治大一统推进过程中中原文化逐步向巴蜀渗透并影响该地祭祀习俗的结果。为顺应这一趋势,巴蜀等地还积极整合民间信仰,将象征中央政权的皇帝和官吏一并列为祠祀对象。另一方面,以巴蜀为代表的西南地区的祭祀文化仍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该地区的祠庙内所祭祀的大多是本土神,且基本不包括宗族成员。这是秦汉魏晋时期巴蜀等地的祭祀文化同中原相比的一大显著差异,说明巴蜀民众建立祠庙的基本目的乃追念前贤和感恩报德,而较少涉及祖先崇拜。总之,通过对《华阳国志》所载西南地区祠庙的梳理可看出,秦汉魏晋时期的巴蜀文化在整合自身并融入大一统潮流之中的同时,依旧保留着自身的底蕴和魅力。
注释:
①此点承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指点,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