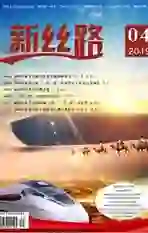抗战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内迁及其影响
2019-06-11李佳
李佳
摘 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史语所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历程。先是迁至长沙,后辗转昆明,最后立足于四川李庄。在战时艰苦的条件下,学术研究受到极大限制,但学者们仍然努力开展科研活动,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而使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并未因战争而中断,反而得以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迁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批准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该院以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学术研究为任务。依据不同学科,院内又分设若干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对于史语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之前和迁台之后,而对于抗战时期的史语所研究较少,故此,笔者欲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着重对抗战时期史语所的内迁历程及其影响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史语所隶属于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10月22日成立于广州。下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等8个组。1929年迁入北平,将原设8个组归并为历史、语言、考古3个组。1934年5月又增设人类学组。这四个分支机构即奠定了后来史语所的学术规模。
史语所生逢民族多难之际(1928~1948),尤其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史语所辗转迁徙。“九一八”事变后,史语所由北平迁至上海。1934年又由上海迁至南京。
一、抗战爆发后史语所的内迁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史语所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历程,曾带着一千多箱图书、档案、仪器、标本辗转迁徙大半个中国。先是迁至长沙,后辗转昆明,最后落脚于四川李庄。
1.史语所的内迁历程
(1)南京——长沙
1937年11月,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担负中央研究院西迁之重责。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研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大学一起迁至湖南长沙。其实早在淞沪会战之前,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局演变,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往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1]迁到长沙后,史语所寄驻在长沙城东边的圣经学校和韭菜园子,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筹组了“长沙临时大学”,也借用圣经学校上课。
(2)长沙——昆明
1937年12月,日本开始向武汉进攻。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多公里,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必遭攻击。面对危局,临时大学的常委们决定迁往云南昆明。当时,傅斯年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因此,史语所参与了临时大学撤退昆明的共同行动。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同时,中研院总办事处电令史语所向昆明转移。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2]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
初到昆明,史语所分住在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三号两处。9月日本飞机又开始轰炸昆明,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史语所为保存发掘出土的文物及书籍免受损毁,决定立即搬家,搬到一个既安静又不用跑警报的地方,于是人们又开始在昆明城外找寻迁徙地。秋天,史语所迁往昆明郊外的龙泉镇,暂栖棕皮营的响应寺、龙头书坞及宝台山弥陀殿。
(3)昆明——李庄
史语所就这样在龙泉镇暂栖了两年,直到1940年秋天,昆明的形势开始恶化,日军对重庆、昆明等西南各省主要城市进行持续轰炸,同济的一名學生在一次空袭中被日本人炸死。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立刻停止,打算往四川迁移。在昆明龙泉镇的史语所、社会所等学术单位也都酝酿再次迁徙。最终他们选择了四川南溪县李庄,选址在距离李庄还有七八公里地的板栗坳。其原因是:李庄的地理位置远离城市,又有很多庙宇适宜安置图书资料和人员的居所。当时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而李庄就具有这个特点。
史语所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搬迁以后,于1940年至1941年间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学术研究工作逐渐转入正常。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物价上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使得学术研究工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史语所的学者们仍然根据既定的研究宗旨,努力创造条件,做了一些语言、民族学调查,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二、史语所内迁的历史影响
史语所的内迁,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它在战火中,为国家完整地保存了这一学术研究机构,及其重要的资料、仪器、设备,这对于推进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1.保证了近代中国学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1)保存文物档案
抗战爆发后,为避免珍贵的文物、图书档案等沦入敌手,史语所决定将最珍贵的中西文图书、善本及殷墟出土的器物等打包装箱,转移到大后方。因此内迁过程中最难搬运的就是那些宝贵的文物和图书资料。每次转移,史语所都有严格的计划,从哪里发车,共有多少车,车上的货物都有清单,由哪些人负责押运,哪些人负责接货,到哪个地方换乘火车、轮船都做了细致的安排。这样就极大地避免了文物、图书在转移过程中的丢失、损毁。据可查得的资料统计,中央研究院各所在战后迁返时,史语所拥有的图书资料最丰富, 有中外文书籍14万册。其他各所仅为:社会所4.6万册,天文所1万余册(含杂志),化学所8000余册, 地质所5000余册,心理所4000余册(含杂志),工学所1300余册,植物所1000余册,数学所1000余册[3]。当然这里面也有史语所原藏书比较丰富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史语所内迁的确保存了从南京带出来的千余箱图书仪器档案及本所开办以来收集到的数百箱第一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原始资料,为中国近代文脉的保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