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争与解决的尝试:论法国当代戏剧中的争辩
2019-06-11赵英晖
赵英晖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马克斯·韦伯关于“世界的祛魅”和“诸神之争”的说法勾画出了现代社会深陷其中的价值相对主义困境。“祛魅”之后的世界由于普遍元叙事的瓦解,人对世界的解释日趋多元。法国当代戏剧中广泛存在的争辩现象就是对这个现代性事实的反映和反省,是戏剧试图对当今人类文明的问题做出概括和回答。本文拟探讨在扎根于现代性经验的当代戏剧中,当争辩成为戏剧的主要表现内容时,情节结构——这一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基础,在法国古典戏剧中得到强化,在黑格尔《美学》关于戏剧诗的论述中得到延伸,经过贝克特、皮蓝德娄等的解构之后依然不曾摧折的关键戏剧成分——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争辩的戏剧地位
海德格尔指出理解奠基于“前见”“前有”“前把握”之上,伽达默尔将这三者统称为“前理解”或“视域”,并指出理解的差异源于每个个性化存在的特定视域间的差异,因为每个个性化存在的特定视域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则理解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因而,争辩作为理解差异的具体体现之一,在人际交流中总是存在的。以展现人际互动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戏剧中历来有对这个问题的反映:莫里哀《女学究》(Les Femmes savantes,1672)里两姐妹关于女性教育和社会角色激辩(第一幕第一场),马里沃(Marivaux)《爱情·偶遇·游戏》(Le Jeu de l’amouretduhasard,1730)里主仆关于婚姻意义的争论(第一幕第一场)等。
现代文明由于缺乏一个超越的绝对者或人们可以向之回溯的普遍命题,人对世界的诠释越来越主观化、特殊化,当代戏剧中的争辩现象变得更为常见:夏洛特(Nathalie Sarraute)、科尔代斯(Bernard-Marie Koltès)、维纳维尔(Michel Vinaver)、拉葛尔斯(Jean-Luc Lagarce)等的作品中均存在篇幅不等的争辩场景;争辩甚至成为一出戏的全部内容,例如近年在我国上演的《孤寂在棉田》(Dans la solitude des champs de coton)、《爱的落幕》(Clôture de l’amour)等。
而且,在许多当代戏剧中,争辩成为戏剧冲突的重要或唯一表现形式。诸多戏剧实例告诉我们:戏剧冲突不一定以争辩的形式表现出来,争辩也不一定与戏剧冲突有关。如莫里哀的《贵人迷》(LeBour-geois gentilhomme,1670)中,儒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的几位艺术老师间的争辩持续了3场之久,每人都坚信自己从事和教习的艺术最高贵,但这场以拳脚收场的争辩纯属噱头,对主要情节(贪慕权贵的儒尔丹作茧自缚)的发展不起推动作用。冲突作为戏剧的核心部分或戏剧的代名词,在遭到贝克特作品的全面破坏之后,在今天的戏剧中呈复兴之势,或者说如萨拉扎克(Jean-PerreSarrazac)指出的那样从未被真正瓦解,而是以“回顾”“碎片化”“预期”等形式在更长的情节时间跨度内和一系列的小问题(而不是古典戏剧人物面临的大灾难)中持续存在。当冲突以对白为表现载体时,争辩便不是游离于戏剧进程之外的插曲,对争辩的处理也就是对戏剧冲突的处理,能够影响戏剧的情节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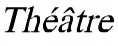
目前国内外对“争辩”的研究以语言学研究居多,从语用学角度,结合言语行为理论,探讨争辩与会话原则的关系。这类研究因其对“争辩”的定义不同而导致研究对象不一致,它们对“争辩”的定义可分两类:一类认为争辩是由谈话双方(或多方)意见分歧引发的冲突性话语,即一方的话语中包含对另一方话语的否定性、对抗性、反驳性言辞;另一类除强调冲突性外,还特别指出言辞的激烈程度和包含的敌意通常以挑衅、辱骂等方式表现出来,认为“人身攻击和侮辱是争辩的突出特色”。本文使用“争辩”的第一类定义,即不认为人物激烈的情绪和侮辱性词汇的使用是争辩与否的首要区别,而是强调双方言辞中存在的对抗性,因为这种对抗性是人物意志冲突在语言中的反映,于戏剧而言,决定情节结构的是意志冲突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如何构建。
此外,我们尤希望将“争辩”概念与利奥塔的“歧争”(le différend)概念联系起来,以找到争辩成为当代戏剧重要内容的现代性根源。由此,如何处理争辩,既是戏剧情节结构的问题,也体现了戏剧对现代文明危机的思索。利奥塔的“歧争”概念不是对争辩、诉讼、战争等各种冲突形式的描述,而是揭示滋养这些冲突的意见分歧:“歧争是两方(或多方)的冲突,由于不存在对双方论证都适用的评判标准,这一冲突无法得到公正的解决。”此定义特征有二:1.强调争执双方具有广泛“离散”的本质,利奥塔认为这种异质性源自争执双方各自遵从的规则不同,他把这种遵循不同规则的异质性称作不同的“语言游戏”,歧争是不同世界、不同游戏规则相遇的契机。2.他还指出对待“歧争”的方式,认为不存在对所有异质性因素都普遍有效的、统一的元规定,因为凌驾于争执双方之上的判断标准排斥个体的意义创造,他希望实现不必整体化的规则多样性,维护一种作为“新的可能性”和“正义”保障的“开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实现“非约束性的、并且不必整体化的规则多样性”。当代戏剧对争辩的处理,确有不接受关于元规定的预设,不提供“解”作为异质性力量间冲突发展的唯一方向,极力展现差异的做法,虽然不可通约的多元价值在这样的戏剧中得到平等对待,但共同体间际氛围的建立也变得困难。但也有作品不满足于分裂的结局,仍然试图寻找解决争执的方法。不论悬置歧争还是力图解决矛盾,新的戏剧结构都在对现代性经验的审视和对统一可能性的探求中发生了。
二、无“解”之“结”
一部分以争辩为主要内容的戏剧,最突出的特色在于人物争辩愈演愈烈,争辩进程具有与古典戏剧情节的线性推进(开端-发展-高潮)相似的结构,但是人物冲突在落幕时分依然存在,戏剧有“结”而无“解”。
夏洛特(NathalieSarraute)的《没什么》(Pourun oui ou pour un non,1990)呈现的是友人H1和H2就词句理解发生的争执,那些在通常看来“没什么”的细微语调变化(拖腔、顿挫等)却在这里造成了朋友间不可弥合的裂隙。利克纳(Arnaud Rykner)称这部剧作为“言戏”(logodrame),突出该剧涉及的语言学问题。但我们在此希望赋予“言戏”更加宽泛的意义,即“戏在言中”,不仅指这部戏剧几乎全由两个人物的对白组成,更重要的是指人物之间矛盾的产生、发展、激化(即所谓“戏”)的过程都由语言推动,“当语言带来情境变化时,或者当语言引发由一种立场向另一种立场或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时,语言就是行动(被称为‘语言-行动’)。”这样一来,“言戏”就具有了描述该剧情节结构的意义。
整部戏无场次之分,但我们依然可在流畅衔接的对白中区分出若干“回合”并发现“回合”间逐步推进的发展逻辑:
1.从开始到“你明白吗”。H1来看望他的朋友H2,问H2为何疏远他,H2起初辩解自己并非疏远,而后道出实情——被H1一句话的语调触怒。(矛盾1)
2.“现在我想起来了”到“我觉得这显而易见”。两位友人追溯当时的具体语境及 H1的轻蔑因何而来。由此道出两人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诸多分歧。(矛盾2)
3.“你想让我告诉你吗”到“我去叫他们”。H1给引发H2疏远的语调起了名字——“傲慢”,但他拒绝为自己的“傲慢”向H1道歉。又由H1一句话的措辞引发两人新的不快。(矛盾3)
4.“喏,这位是”到“您请便吧,我来处理”。H2请邻居评判,但邻居不理解两人的争辩。(他者调解无效)
5.“那么你相信”到“我最好还是走吧”。双方总结以上诸多矛盾,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观点并指责对方。H2认为H1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炫耀个人幸福,H1在H2的反应中看到的是嫉妒,他被深深地伤害了。(矛盾4)
6.“对不起”到“你或者我”。H2表示歉意,开始数说自己的不到之处,化用了魏尔伦的诗句。H1就此又对H2发起攻击,指出H2也在弹老调,而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真的能够做到在俗世价值之外。(缓和-矛盾5)
7.“这你就过分了”到“对,我看出来了”。两人都回忆起对方使用过的谩骂词汇,互相的指责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矛盾6)
8.“翻脸有什么用”至结束。H1提出到法庭上诉,H2劝阻,两人对争执的无法调和有自知之明。H1一如既往遵从主流秩序,H2依然反对一致主义。(法庭调解无效)
H1与H2的交谈中不断出现新矛盾,而任何一个矛盾都得不到解决,对白处处都是“雷区”,一只只地雷不断被引爆,交谈是满目疮痍的战场。
科尔代斯的《在棉田的孤独里》(Danslasolitude des champs de coton,1985)展现了卖者(Le Dealer)和买者(Le Client)的“言语殴斗”,也具有“言戏”的结构方式:双方都在试图说服对方,让对方坦陈自己,但最终所有企图都未实现。卖者的每个提议都被买者拒绝,卖者对买者意图的每个揣测也都被买者否认,同样形成了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矛盾不断滋生的话语(戏剧)进程。如果说在《没什么》中我们依然可以从言辞中分析出人物的身份特征,那么在《棉田》中买卖双方两个人物的话语风格以及用话语进攻和防御的手段并无太大差别,我们无法从性格、社会阶层、文化归属等方面对两人进行区分,甚至无法确定其性别。《棉田》设定了两个人物间不需要任何具体表征的绝对差异性和矛盾。
“说到底,我们也许只需赞叹话语种类的繁多就够了,就像赞叹动植物种类的繁多一样。”在《棉田》和《没什么》中,每个异质性因素都得到了表达,并充分展现了它们的不可通约性和平等关系。这样的戏剧中形成了两条线索,它们在数次徒劳地试图交叉之后各奔东西,渐行渐远,无法形成亚里士多德戏剧美学中要求的“单一性”。
三、解决的尝试
利科(Paul Ricoeur)在《时间与叙事》中指出了长期统治西方人思想的“结局意识”,“结局”不仅是时间上的结束,还是逻辑上的归一。利奥塔本人在《后现代状态》中也指出,尽管他不断提醒我们每种语言游戏都遵循不同的规则,不存在可以支配所有语言游戏的元规则,但事实上这样的元规则在每个时代都不曾缺席。弗兰克(Manfred Frank)借用康德的理论指出,寻找统一性是人类理性的必然运作方向,“理性试图在推论中将悟性认识之极大杂多还原至最小数目的原则(即一般条件)上面,并以此引申出这些原则的最高统一性”。因而,即便在元规则、统一性、普遍真理的合法地位遭到质疑的现代文明中,戏剧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型态,也没有停止过将歧争进行划一的尝试,一些剧作家力图在《棉田》《没什么》等剧作展现的现代性困境中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表明了他们对现代社会面临的主体无限扩张、价值相对主义及由此导致的虚无主义困境的把握和诊断。大致可归纳出三种解决争执的尝试:
1.古典式
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贺拉斯的《诗艺》,再到布瓦洛(Nicolas Boileau)的《诗艺》(Art poétique),一整套关于戏剧创作的规范建立起来,包括对主题、情节结构、话语形式(对白、独白、旁白)、人物性格等方面的规定。按照这套规范创作出来的戏剧通常由一个人物或一个团体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或一个需要达成的目标引发,在解决问题或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支持和反对这个人物或团体的势力一一出现并发生对抗,直到最终问题得到解决,目标得以实现,主人公的命运因而由逆转顺或由顺转逆。同时必须满足的要求是,戏剧行动必须完整自足,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且必须集中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发生。今天的法国戏剧中仍有很多作品依循这种传统而作。在这样的戏剧中,争辩代表的对抗性最终会被消除,同一性将取代差异性。
施米特(éric-Emmanuel Schmitt)的《访客》(Le Visiteur,1993)即是如此。施米特在这部戏中将弗洛伊德和“访客”置于一场关于信仰的意见分歧中,他让“上帝躺进弗洛伊德的躺椅”,也让“弗洛伊德躺进上帝的躺椅”,他们互为精神分析师和患者。这部17场的独幕剧,“结”和“解”都十分清晰:“结”是阻止弗洛伊德承认信仰和促成弗洛伊德承认信仰这两股力量间的纠缠。阻止他承认信仰的是当前黑暗的欧洲大陆上恶的横行、善的隐匿。促成他发现并承认深存心底的信仰本能的是“访客”。弗洛伊德和“访客”关于信仰的争论正是这个“结”由最初的令人一筹莫展,经过几次“起伏”“曲折”,最终被“解”开的过程。这场争论总是被前来捣乱的纳粹军官和后来平安归家的安娜打断,断续出现在第 4、6、8、10、12、14、16 场中:弗洛伊德的观点是:自己不信上帝,因为把一切托付给上帝是件太容易的事,在走投无路时依赖这样一种幻觉是人类懦弱的表现,而且,目前纳粹的作为本当令人神共愤,但却没有神力显现以阻止他们的疯狂,那么即便有上帝,那也不过是个只承诺却从不践行的骗子。“访客”认为一切灾难都因人类的自负而起,人类从前只想挑战上帝,而现在却自以为替代了上帝。在整个过程中,弗洛伊德的心理状态因与“访客”的辩论而发生明显改变,由开始的完全怀疑,到最后对访客的依赖以及向之询问未来,中间虽经历两次曲折,但弗洛伊德对“访客”的信任在逐步加深,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身上不会消失的、属于潜意识的信仰本能。而随着这场争辩引发的思想变化,弗洛伊德在该剧开始时面临的问题也逐一解决:不必再为安娜担心、签署了承诺书并决定尽己所能带更多的人脱离纳粹魔爪。这个古典式的争辩处理手法,完成了一种黑格尔式的逻辑体:一个主体的行动和思想不断地和另一个主体的行动和思想相互关联,在与异质性因素相遇之后,自我最初的、僵硬的规定性被消解,吸收异质性因素,最后形成更加丰富的自我。
2.叙事与戏剧结合式
一些剧作中出现了跳出戏剧解决争辩的办法,例如科尔代斯的《返回沙漠》(Le Retour au désert,1988):阿德里安和玛蒂尔德兄妹二人的争辩在戏剧的范围内仍然没有结局,而是在剧本之后所附的《赛普努兹家族百年史》(Cent ans d’histoire de la familleSerpenoise)中得到了解决。在这部剧作中,玛蒂尔德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故乡,与其说是归家,不如说是找以兄长阿德里安为代表的当年迫害过她的人寻仇,而阿德里安常年受保守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熏陶,视这个当年辱没门庭的妹妹如瘟神。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兄妹间争端四起,任何一个小举动和小措辞都能引发对方辛辣的讽刺、辱骂和挑衅。
剧本后的《赛普努兹家族百年史》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对剧中每个人物的身世、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了介绍,对人物在对白中简要提及的事件进行了扩展。其中讲到玛蒂尔德兄妹一起离开小镇,在美国一座小城定居下来,阿德里安当选了市长,姐弟二人相处融洽。科尔代斯并未说明兄妹和解的原因,但他把戏剧嵌入叙事中、使戏剧中的争执在叙事中得到解决的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戏剧构建了一个元层面。通过戏剧与叙事的结合,科尔代斯将戏剧中的故事延伸到戏剧外,以叙事确立一个在戏剧的当下性之外的时空,剧中人物和事件并非自足,每个戏剧动作的前身和后果不一定在戏剧之内,而是与叙事构建的那个戏剧外的世界相关。叙事与戏剧的关系在戏剧理论家的艺术分类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相互排斥,黑格尔将戏剧诗视作史诗和抒情诗的超越,布莱希特则将叙事提升到戏剧理论高度并凭借它实现“间离”效果。科尔代斯的叙事剧与布莱希特的叙事剧不同处在于,布莱希特通过这元层面阻止观众沉溺在戏剧制造的幻觉中,请观众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展示给他们的故事,但在科尔代斯这里,叙事强化了戏剧营造的虚构世界的逼真性,而且,叙事是作为戏剧中一切情节、人物性格、对白的合法化基础存在的,因而它也可以提供一个超越对峙双方的判断依据,尽管科尔代斯没有明言这个依据是什么。
3.反思式
所谓“反思”,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是对某种言语行为的“形式语用学前提和条件加以重构”,因为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和符号使用者间的关系,所以这里的“形式语用学前提和条件”指的是与人的言语相关联的人的生活世界。斯丛狄认为反思的意思是“人自身的社会存在对人来说成为对象性的东西”,是人与自己的行为或社会存在之间发生疏离。戏剧中从不曾缺乏反思成分,阿贝尔(Lionel Abel)等学者将那些具有自我意识、检视自身的剧作称为“元戏剧”。例如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中世纪道德剧中的寓言式人物的说教都常常出现对整部戏剧中发生的事件的回顾和评价。上文提及的布莱希特要实现的观众与戏剧、演员与角色之间的“间离”,也是反思的具体表现之一。
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反思成为了解决人物间争辩的手段。表现形式之一是人物的自我反思,通常以人物独白的形式出现,对已发生的事件回顾、分析和评价。雷扎(Yasmina Reza)的《“艺术”》(“Art” ,1994)中就充满了这样的反思,并以此解决争辩。这部作品讲的是塞尔日(Serge)花高价购买了一幅纯白的油画,引起朋友马克(Marc)的不解和恼怒,两人因此激烈争执。他们共同的朋友“和事佬”伊万(Yvan)前来调解无效,却成了二人的指责对象,因而也卷入争辩。全剧无幕、场之分,以星号分隔为18节,其中第2、3、13节展现塞尔日和马克两人的正面冲突。这18节可以分成3个阶段:1-6节展现两人对这幅画态度的根本对立;7-12节讲好友伊万前来调解,塞尔日和马克的争执仍十分激烈,而且两人对伊万发起挑衅;13-18节讲马克接受了塞尔日的看法,在这幅白色的油画上看到了一个在白茫茫雪地上滑雪的白色小人,塞尔日则递给马克一支笔让他在这幅昂贵的白底白画上随意涂鸦,向他证明友谊比美学观念和经济价值重要。
之所以在第三阶段出现和解,是因为这部以展现意见分歧为主的戏剧中,不断出现人物对自己言行、对事态局面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主要以独白的方式呈现,全剧18节里有12节独白。回顾和内省一直是戏剧独白的重要功能,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在独白里剧中人物在动作情节的特殊情况之下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对自己表白出来。所以独白特别在下属情况中获得真正的戏剧地位:人物在内心里回顾前此已发生的那些事情,返躬内省,衡量自己和其他人物的差异和冲突或是自己的内心斗争,或是深思熟虑地决策,或是立即做出决定,采取下一个步骤。”《“艺术”》中每一场面对面的争执之后,都是人物对争执的反思。人物在独白反思中回顾双方的争辩,找出彼此的不一致处及其原因,探究对方的行动理由,质疑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单纯以个人的视角来判断,同时寻找重新开始交流的基点,进而在下一次与对方谈话时调整自己的交谈策略。
表现形式之二是戏剧对自身的反思。同样出自雷扎笔下的《生活的三个版本》(Trois versions de la vie,2000)以三种方式讲述同一天晚上发生在同样五个人物间的事:物理学家亨利(Henri)正筹备一篇学术文章,需要上级于贝尔(Hubert)支持。于贝尔携妻到亨利家赴宴,却弄错了日期,两对夫妻在亨利家客厅里尴尬地吃着零食,他们的谈话不时被亨利六岁的儿子搅扰。三个版本呈现的都是这五个人物间的交流,但人物言辞和由此造成的人物关系却明显不同。在第一和第二个版本中,四个朋友在酒精作用下,也由于多个原因(儿子的搅扰、亨利论文发表受挫)导致情绪失控,人物间从开始的虽各怀鬼胎但表面友善,发展到后来的失态和争辩。而第三个版本没有争辩,一切都是“愉快”(enjouement)的。
三个版本包含一些相同元素(人物、时间、地点、事件、语词等),作者在探索把相同元素进行不同构造产生的结果:“我想最大程度实践剧作家的权力:这部戏把同一个场景演了三次,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情形。唯一改变的是,由我按严格规则来操纵人物。”雷扎所说的作家对人物的“操纵”,就是指在元戏剧层面每一个版本都构成对前一个版本的反思和改写。所谓“按严格的规则”,结合雷扎本人关于戏剧的其他论述可发现:1.指三个版本中若干元素的相互呼应,以及一些相当“古典”的、使戏剧情节符合“逼真”“有度”等原则的手法;2.指语意与语境的关系,“一句台词的位置变化对整体的意思影响很大。同样的词,以不同方式说出来,会改变一切,若二人互相憎恶或倾慕,尽管他们说的话一样,但情形会完全不同。”雷扎意识到语境对意义巨大的改变作用,因而尽力创造不同语境,也即创造哈贝马斯所说的“形式语用学前提和条件”,使人物话语意指的形式、过程和结果均产生“差别”,从而根本改变对话的结果、交往的结构,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到第三个版本中,被改变了的语境包括:1.人物对人际交往原则的一贯遵守:情绪平和、肯定对方、协商的口吻及委婉语气;人物真诚地试图理解对方并检讨自己;2.人物的个体特性:孩子独立、乖巧,亨利不计较功利。语言与语境的互动关系造成的微妙差别可以改变交往的面貌。在第三个版本中建立起了一种满足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有效性要求的、在协商基础上建立的沟通。无论是《“艺术”》中人物跳出事件进程对自己和他人行为方式的质疑,还是《生活的三个版本》中雷扎作为“操纵”者对事件的语用学前提的重构,争辩的人物都在反思中走出了不可交流性、相对主义和自我封闭造成的人际关系暴力,找到了共同生活的方式,一种新形式的元戏剧也由此建立起来。
总 结
当争辩这个现代性问题成为戏剧的重要表现内容,戏剧的情节结构在传统的“结”与“解”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趋向分裂,人物间的沟通和一致越来越不可能,众声喧哗造成戏剧间际氛围的瓦解,始终平行的线索造成有“结”无“解”的戏剧;另一个方向在绝对价值缺失的前提下重新寻找统一的可能性,或效法古典式,主体将异质性因素吸纳入自身从而诞生新的主体,或以叙事方式在戏剧之外构建规则元系统作为矛盾的仲裁,或在人物对自我和戏剧对自身的反思中达成交往理性,达到主体与世界的一致,被瓦解的间际氛围得以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