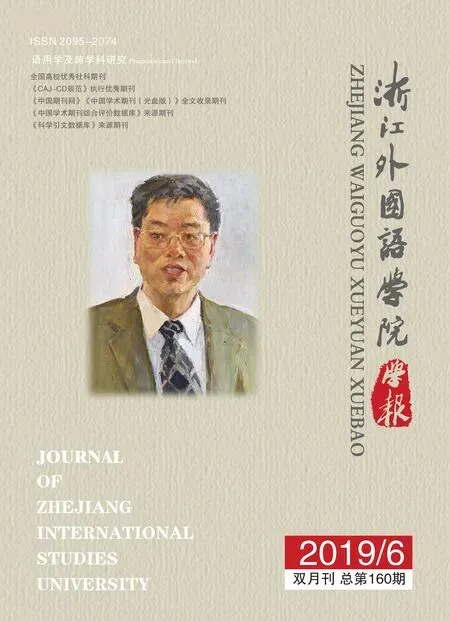“动宾+动宾”类成语活用的认知语法探微
——以“望×兴叹”为例
2019-06-10田良斌
田良斌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一、引言
汉语成语作为中华民族语言的精华,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可以极大地增强汉语语言的表达力,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汉语成语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研究颇为丰富(如邢福义 1996;徐耀民 1997;刘振前、邢梅萍 2003;徐盛桓 2004,2009;陈满华 010;王寅、王天翼 2010;魏在江 2015,2019;胡雪婵、吴长安 2016;王文斌、高静 2019)。刘芳(2007)统计了2004 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发现其中常见的成语有二百五十多条,而“V1O1+V2O2”(动宾+动宾)类成语多达四十六条,占比近五分之一,由此可见该类成语在汉语言教学以及常规使用中出现频率之高。从诸多研究(如马琴珍 1985;谢鸣雄 1987;胡兴华 1993;马荣立 1995;黎剑光 000;翟赟 2009;李少虹 2013;李运富 2013;赵付美 2013;常婧 2014;张懂、史小平 2016;李雪、田良斌 2017)也可看出对该类成语进行研究的重要性。而在该类成语的研究中,“望洋兴叹”的相关研究较有代表性。马琴珍(1985)、马荣立(1995)及黎剑光(2000)等学者主要从语言规范化或修辞的角度对“望洋兴叹”及其活用现象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望洋兴叹”中的“望洋”是连绵词,本义表示仰视的样子,而新生的“望×兴叹”结构,诸如“望车兴叹”“望书兴叹”等都是对“望洋兴叹”的误读。但谢鸣雄(1987)却指出,将“望洋”理解为动宾词组并不是一种误读,“望洋”本就不是连绵词,而是注解者受到误用词语“旋其面目”中“旋”的影响,对“望洋”作了误注。胡兴华(1993)和李运富(2013)则认为,新生的“望×兴叹”结构是人们根据需要仿拟的新词,不能把“是否符合原义原用法”当成唯一判断标准,应该用发展演变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新生构词。赵付美(2013)从模因论的角度对“望×兴叹”结构作了探讨,她认为,“望×兴叹”是强势模因,其使用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笔者认同“望洋兴叹”中的“望洋”本义表示仰视的样子的看法,而随着语用频率的增加,“望洋兴叹”逐渐呈现为“V1O1+V2O2”式结构,则是一种典型的“习是成非”现象。然而,尽管以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望洋兴叹”及其新生结构的理解,但就“望×兴叹”的生成条件及其背后的认知动因而言,大多没有进一步挖掘,缺乏深入的探讨(李雪、田良斌 2017)。
尽管翟赟(2009)、常婧(2014)、张懂和史小平(2016)从认知角度探讨了汉语成语的仿用,但对于“V1O1+V2O2”式结构“望×兴叹”却只是关涉性或例证性提及。李雪和田良斌(2017)对“望×兴叹”作了专门探讨,较为细致地论述了该构式的生成机制以及能产性问题,但对于新生词项和“望×兴叹”的关系、新生词项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允准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对于“望×兴叹”的能产性问题还缺乏相关限制条件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认知语法视角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以期为“望×兴叹”及其相关实例提供更为完善的诠释。
二、认知语法中的识解、类型和例示
(一)识解
Langacker(2008:43)把识解定义为人们以不同方式构想和描绘同一情景的多维能力。他(Langacker 1991: 5-12,2000: 5)提 出,对 于 识 解 的 描 写,可 以 从 详 略 度(specificity)、辖 域(scope)、背 景(background)、视角(perspective)和突显(prominence)五个方面来展开。鉴于研究偏好和本文所涉及研究对象的需要,此处重点关注详略度和背景在“望×兴叹”及其相关实例识解中所起的作用。
详略度主要指人们可以从不同的精确度或详细度层面来对同一个实体进行构想和描述, 而人们对事物识解的差异和对外界观察的详略度密切相关(王寅 2011: 23-24)。详略度的识解可以发生在词汇层面,如例(1):
(1)a. Chianti >wine >beverage >liquid >substance
b. sprint >run >move >act >do
Langacker(2013: 55)指出,图式化程度(schematicity)是和详略度相对立的术语。因此,在例(1a)和(1b)中,从左到右词汇的图式化程度逐渐升高,而从右到左词汇的精细度逐渐升高。对于同一情景的识解也可以有多种表达方法,呈现出详略度各异或精细度不同的句子表达,如例(2):
(2)a. Someone did something.
b. Someone broke something.
c. Someone broke the toothbrush.
d. Someone completely shattered the toothbrush.
e. Tom completely shattered the toothbrush in the bathroom.
f. Tom completely shattered the toothbrush in the bathroom by hitting it solidly with a brand new wooden-handled claw hammer. (转引自王寅 2011: 25)
识解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范畴化的过程,而范畴有不同的层次,主体可以选择非常高的层次,也可以选择非常低的层次(任舒俊等2014)。从例(2a)到(2f),句子所描述的情景越来越详细,构成了一个描写同一情景但精细度逐步变化的语言连续体(王寅 2011: 25)。
背景主要指在理解或识解某一个结构时,总是需要其他结构来作为理解的基础,而这些作为理解基础的“其他结构”就是背景成分。例如,若要理解动词概念“买”,不仅需要知道“买方”和“商品”这两个直接概念,还需要对“卖方”和“货币”等所提供的背景信息有所了解。另外,在话语理解中,先前的话语或语境是后续话语理解的背景,能为话语理解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信息(Langacker 2000: 5)。
(二)类型和例示
Langacker(1991: 56-57)指出,例示域(domain of instantiation)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类型(type)和例示(instance)的区别。例示域表示实体在其中所占据的位置足以将其确定为某范畴的一个例示,而该例示与其他可能的例示具有显著差别(任舒俊等2014)。简而言之,例示就是例示域中某种类型的一个实例,其在例示域中拥有特定的位置。需要注意的是,类型是判断或明确不同实体可以作为同一种类的基准,其并不属于这一种类中的任何一个实体,从范畴化关系来说,类型和例示应该是上下位范畴的关系。另外,由于人们会将他们对于物体的经验区分为不同层级,因此一些不同的类型也会有不同层级的抽象度。例如,“我的猫”不仅是类型“猫”的例示,同时也属于“哺乳动物”“动物”甚至“事物”的例示,其所呈现出的类型层级为事物>动物>哺乳动物>猫。在这个类型层级中,前一个类型均比后一个类型更加具有图式性或抽象性,从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出次类型(subtype)。类型(x)和次类型(y)之间是细化关系,而(次)类型和例示(z)之间是例示关系。三者的关系如图1 所示:

图1 type >subtype >instance 层级图(Langacker 1991: 62)
Langacker(2000: 270-271)认为类型和例示的区别与简单名词和名词短语的语法区别相关联。换句话说,简单名词和名词短语的区别就是类型和例示的区别(任舒俊等2014)。例如,在英语中,简单名词“spoon”表达的是类型,而名词短语“the spoon”则表达的是例示。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名词短语“the spoon”并非强调其属于世界万物中的某个实体,抑或是某种类型实体的集合,而是被识解为简单名词“spoon”所侧显的次结构的概念化。换言之,名词短语“the spoon”是简单名词“spoon”的一个实例或例示, 二者之间存在例示关系。 从类型转变为例示的操作被称为例示化(instantiation),Langacker(2000: 271-274)用入场(grounding)来表示这种操作。某种类型通常有多个例示,如类型“猫”就可以有诸如“一只猫”“那些可爱的猫”“我家的猫”等多个例示。
三、“望×兴叹”的例示关系和语义理解
(一)“望×兴叹”的例示关系
“望×兴叹”结构在认知语法框架下能获得较为深入的解读。具体来说,“V1O1+V2O2”是汉语成语的类型之一,而“望×兴叹”则是类型“V1O1+V2O2”的一个次类型。与类型和例示的关系相似,一个类型也可以有多个次类型,如“闻O1起舞”“打O1骂O2”“见O1生O2”等。笔者同意赵付美(2013)、李雪和田良斌(2017)等学者的观点,即“望×兴叹”的形成主要源于“望洋兴叹”,这和“望洋兴叹”在日常表达中的高频使用密切相关。例如:
(3)a.损失10 亿欧元! 洪水一周三袭,威尼斯“望洋兴叹”(中新网标题2019-11-18)b.洪水一周三袭威尼斯 民众“望洋兴叹”(中新网标题2019-11-19)c.助中国企业家不再望洋兴叹 君智咨询获“2019 君士坦丁奖”(搜狐网标题2019-11-07)d.面对奢侈品消费外流,不能只是“望洋兴叹”(上观新闻标题2017-01-24)
由于日常使用频率高,“望洋兴叹”在结构上逐渐图式化,人们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经常将“望洋兴叹”中的“洋”替换掉,构成如“望楼兴叹”“望医兴叹”“望书兴叹”等仿用成语。根据构式语法,“望洋兴叹”应该归于图式性成语构式,因为其在原有成语构式框架基础上提供空位,主要体现为“望×兴叹”(李雪、田良斌2017),这是语言使用影响语言结构的结果。根据李雪和田良斌(2017)的研究,“望洋兴叹”本义指河伯抬头对着海神感叹海神的伟大、自己的渺小,而后来在使用中逐渐引申出抽象构式义,即对某事力不胜任,或因没有某种条件而感到无可奈何。另外,从“望洋兴叹”的活用中也可以概括出其表层基本义,即看到什么东西发出感慨。这种抽象构式义和表层基本义是“望×兴叹”在识解中呈现为类型的基础,所有新生的“望×兴叹”实例都以该抽象构式义和表层基本义为原型,并通过添加相应语境中的“×”成分而获得具化。例如:
(4)a.词汇是基础,应该摆在六级准备的前头。没有词汇做基础,对于词汇题只能望题兴叹。(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简称CCL)
b.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医疗卫生事业也有所改善,但眼下医药费用高涨,使得部分只能解决了温饱的农民“望医兴叹”。(CCL)
c.尽管图书涨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作为读者,我还是真诚地希望书价悠着点涨,免得让读书人只有望书兴叹的份儿。(CCL)
d.由于房价的节节上涨,老百姓更买不起房,只好“望房兴叹”。(CCL)
例(4a)中的“望题兴叹”表示,在准备英语六级考试的过程中,英语词汇是重中之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词汇量,那么在考试中只能是看着题不会做,徒生感叹。例(4b)中的“望医兴叹”则表示,由于承担不起医药费,而无法接受治疗。同理,例(4c)中的“望书兴叹”和例(4d)中的“望房兴叹”也都表示,没有条件解决困境或难处的无奈。如前文所言,“望洋兴叹”已经逐渐图式化,其中的“洋”逐渐淡化,甚至经常可以被替换掉,从而呈现出类型结构“望×兴叹”。这些语料库中的实例为该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进一步来说,这些实例都可以看作是“望×兴叹”的例示,它们在意义上都具有该构式的抽象构式义和表层基本义,但在表述上却更为具体可及。换句话说,“望×兴叹”与其实例之间存在例示关系。较为明显的证据是,例(4)中所有“望×兴叹”的表达都可以用较为图式化的“望洋兴叹”来替换,而意义在语境支撑下基本保持不变。张辉(2003)指出,图式化的成语构式在常规化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在更一般和广泛的相关语境下使用,获得较为普遍的概括意义,而新生实例是拥有较为具体构式义的构式,相较于类型来说,例示在结构上和语义上都获得细化,这也是新生实例不断产生和存在的理据。
由表1中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桩59-X30井生产指标中的累积产油量和采收率都随着注水压力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注采比[2]的增加,地层平均压力不断增加,采出程度升高,但是含水率也不断升高。当注采比为0.92时,地层平均压力保持水平过低,模拟期内油藏脱气,采出程度相对较低;随着注采比的增加,虽然累积产油量和采出程度增加,但是增加幅度不高,而注入水量增加很大,所以不能单纯考虑采出程度。由图1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油井见水时间随注水压力的增加而减少。综合各项指标,认为注采比为0.965方案为佳。此时对应的注水井井底压力为40MPa左右。
(二)“望×兴叹”的语义理解
Langacker(1987:81-82)指出,语法结构就是语义结构和音位结构的配对,是形义配对体的完形,因而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简而言之,对于语法结构来说,如果识解方式不同,所表达的语言结构会有差异,而语言结构的差异又直接导致语义上的差异。因此,尽管较为抽象的“望洋兴叹”可以替换较为具体的实例,如“望题兴叹”“望书兴叹”及“望医兴叹”等,但“望洋兴叹”并不等同于这些实例。较为明显的区别是,新生实例更加具体可及,而“望洋兴叹”显然在精准度上还比较欠缺,需要进一步具化。从较为抽象的“望洋兴叹”到具化的实例,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识解中对类型“望×兴叹”例示域中的某个例示的聚焦,从而在句子层面达成一种突显,即新生实例实际上是“望×兴叹”的某个概念的侧显,其在表达的详细度上更加精准,区别于其他例示域中的实例。从这一分析来看,对于“望×兴叹”相关例示的语义解读离不开对其类型的概念理解。换句话说,对于新生实例的理解是以“望×兴叹”的表层基本义和抽象构式义为背景的,甚至可以说,对类型“望×兴叹”的掌握和理解是相关新生实例得以获得解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为了更详细地阐释语义理解的过程,请见例(5):
(5)广大居民想房、盼房,有了房子却无力购房,只好望“房”兴叹了。(CCL)
例(5)中,广大居民日思夜想、翘首以待的房子终于建好了,但由于房产开发商一味追求奢华装修,导致房价居高不下,远远超出了广大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消费支付能力,因此广大居民只能对着建好的房子徒生感叹。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新生实例“望房兴叹”,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望洋兴叹”作为背景知识,即我们在理解“望房兴叹”时是以“望洋兴叹”为基础的。因此,在语义识解中,尽管我们对于“望房兴叹”是不熟悉的,但“望洋兴叹”已经固化成为一种完形结构,其任何细节都会激活它的其他成分乃至整体。Harris 提出,人们将一个成语中的每个词概念化为一个整体的体现形式的每一部分,只要有一个或两个词出现,就可以激活整个成语(转引自白红爱、郑成虎2001: 26)。“望房兴叹”中的“望×兴叹”激活了我们熟悉的“望洋兴叹”,而“望洋兴叹”的表层基本义和抽象构式义又使我们从语义上理解了“望房兴叹”。简而言之,从类型“望×兴叹”到其例示,如“望医兴叹”“望楼兴叹”“望书兴叹”等,只是在详略度上存在差异。在对例示的语义理解上,需要以对类型的理解为基础,获取相应背景信息,这也是正确理解实例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四、“望×兴叹”的允准机制和语用动因
基于用法的理论认为,一个表达式或多或少都受到更一般类型或图式的允准(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49),而认知语法恰恰就是一种基于使用的理论模型(Langacker 1987: 46)。因此,笔者认为,“望×兴叹”的相关例示,即新生实例,也受到相应类型的允准。从认知途径来看,整个过程应该经历了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的允准过程。根据Evans & Green(2006: 114)的论述,语言用例通常有对应的图式,而图式则是从常规用例中归纳出的用例模型(田良斌 2020),用例模型可以作为模板为新生语言用例提供允准和语法规范。
“望×兴叹”相关例示的允准大体上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尽管“望洋兴叹”类成语是图式性成语构式,但在语法上却属于核心语法构式,体现为常规“动宾+动宾”结构,且符合人们认知中的顺序象似性原则(李雪、田良斌 2017)。这种常规表达在日常生活中极为常用,例如,人们看到熟悉场景突发感慨称为“睹物生情”,有些人达到目的后将帮助之人一脚踢开称为“卸磨杀驴”或“过河拆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望洋兴叹”类成语和现代汉语中的动宾联合结构颇为相似,其中“望洋”部分在句法上就是常规的“动宾”结构,这也是人们经常将“望洋兴叹”看作图式性成语构式,在日常使用中根据语用目的替换掉其中的“洋”的原因,毕竟“动宾”结构是人类最为常见的一种语言表征结构,和人类认知世界、改造世界具有象似关系。例如,“晒被子” “吃饭” “饮水” “呼吸空气”“种树”等都是人们在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非常熟悉的(有些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日常行为,而从这些“行为-事体”的概念结构中,人们可以概括出较为抽象的认知表征[X动词Y名词]。在该图式中,“Y”通常为受事,和“X”组成典型的动宾结构(田良斌 2020)。虽然“望”属于感官动词,但其后面经常需要宾语来进行补充说明,因而“望×”可以看作“动宾”结构的一种,受到动宾图式[X动词Y名词]的允准。
李雪和田良斌(2017)发现,除了较为典型的“动词+名词”的动宾结构外,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也出现了一些较为特殊的语言用例。例如:
(6)a.比较后进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克服望先进而兴叹的无所作为的情绪,急起直追,迎头赶上。(CCL)
c.于是引得不少领风骚一度的作家望凋零而兴叹,为文学的潦倒不平不安。(CCL)例(6)中,“望先进而兴叹”“望贫兴叹”及“望凋零而兴叹”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处于宾语位置的成分本应为名词,但在用例中所显示的都是形容词。李雪和田良斌(2017)指出,这些语言用例和较为典型的“望山兴叹”“望江兴叹”“望楼兴叹”等相比,在形式结构上有较大偏离,因而属于非典型构式或边缘构式。而之所以用例能够出现并合法,主要在于转喻机制的作用,其可以用比较突显的语义内容帮助人们识解新生实例(田良斌 2019)。例如,在“望贫兴叹”中,形容词“贫”在此处发生非范畴化,用以转指“贫困的现状”,其本质上是一种语法转喻,这种认知机制的作用使得人们可以准确理解“望贫兴叹”。从允准机制来说,“望贫”只能是动宾图式[X动词Y名词]的扩展,受到该图式的部分允准。Croft(2000:100-103)认为这种语法现象(扩展或部分允准)产生的原因在于没有某一个词或短语可以用来表达人们想要交际的每一种体验。换句话说,如果想要表达所有的人类经验,语言使用就必定是部分非惯例性的。同时,它又必须是部分惯例性的,因为语言的创新用法必须依赖现存语言的某些方面(Evans &Green 2006: 123-124)。Langacker(1987: 69)明确指出,语言用例的使用并不需要和既定惯例完全适配,合法不合法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能否使用的关键在于其使用频率和语境支持。
李雪和田良斌(2017)认为,构式的生成受到固化成语格式(成语本身格式)、核心构式(动宾结构)、次序象似性的压制。而实际上,构式压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允准。Langacker(1988:130)指出,图式化表征也可以作为模板为其他新生语言用例提供允准和语法规范,其中的语法规范就是一种压制。
另外,从外在动因来看,“望×兴叹”相关例示的形成还受到语言经济原则的影响。前文提到,相较于类型的概念意义(“望洋兴叹”的表层基本义和抽象构式义),相关例示在语义和结构上都更为精准。尽管相关例示受到成语本身格式的压制,在结构上并没有体现出经济性,但却蕴含了更具体的概念意义,其不仅包含类型“望×兴叹”的表层基本义和抽象构式义,同时在概念域中还获得了聚焦,进一步具化了类型的意义。这样一来,尽管使用的是几乎相同的结构,却可以编码和理解更为丰富的例示意义。
五、“望×兴叹”的能产性问题
李雪和田良斌(2017)所探讨的构式压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望×兴叹”能产性的限定条件,但他们讨论的主要是语言构式本身的限定,对较为特殊的“望×兴叹”的新生实例还需要从外部语用条件进行分析,才能获得全面解释。
笔者认为,Goldberg(2019)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为“望×兴叹”的能产性问题提供较好的语用解释。Goldberg(2019)的研究设想主要来源于对“explain-me-this”谜题①Goldberg(2019)发现,在英语中既可以说“tell me something”,也可以说“tell something to me”,而对于“* explain me something”和“explain something to me”,英语母语者通常认为只有“explain something to me”是符合语感的。的思考,对此她提出了覆盖范围(coverage)和竞争(competition)②关于覆盖范围(coverage)和竞争(competition)更详细的介绍以及相关论证过程,可以参看Goldberg(2019)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两个概念来对“explain-me-this”谜题进行阐释。其中,覆盖范围主要为语言的能产性情况提供解释,即语言用例存在的合法性,但对于有的语言用例不能成立的原因,还需要结合竞争这一概念来诠释。在日常交际中,当我们理解话语的时候,我们会预测言者接下来说什么。根据言者实际所表达的话语,我们可以借助错误驱动学习的方式来提高未来预测话语的能力。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反复使用或遇到某一表达式会加强该语法构式和语境中所表达意图之间的联系,导致“在特定语境中使用先前可支配的表达式来描述语境信息”成为惯常行为,而其中的惯常表达式通常会“竞争过”潜在的创新表达式(Goldberg 2019: 40)。然而,如果没有这种语境和表达式之间惯常的联系,那么言者就需要在语境中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以此来表达其意图。简而言之,构式表达之间的竞争主要通过统计优先(statistical preemption)机制来限制构式能产性(Goldberg 2019: 142)。因此,根据Goldberg(2019)的看法,“* explain me something”不合法的原因就在于“explain something to me”这一惯常表达式具有高使用频率并逐渐固化,而“* explain me something”这一创新表达式没能竞争过“explain something to me”。
显然,本文中所探讨的“望×兴叹”的能产性问题也同样可以用竞争这一概念进行合理解释。结合对“望×兴叹”及其相关例示的观察,笔者发现,相关新生实例之所以能够被使用,主要是因为在具体语境中新生实例是最为经济的语言表达,并且在语境和表达式之间还未形成惯常表达式,这时新生实例可以被创造性地应用于语境中以表达交际意图。而之所以还有很多名词或其他相关词性(大多应该为形容词)还不能进入这一构式(如“*望头兴叹”“*望妈兴叹”“*望高兴兴叹”等),主要在于这些新创表达在语境中还没有达到一定使用频率,因而无法对统计优先的表达式产生动摇作用,这就导致人们在交际中仍然倾向于使用常规表达。换句话说,“给定背景下预期信息的表达式是易于获得的,它通常会战胜潜在的创新表达式”(谭晓闯 2019)。潜在的创新表达式如果使用频率逐渐升高,则会在语境使用中逐渐获得惯常性联系,从而成为合法语言用例,而如果潜在的创新表达式使用频率不高,那么给定背景下预期信息的表达式仍然会被优先使用。
六、结语
基于以往研究未对“动宾+动宾”类成语进行较为深入的认知考察,本文从认知语法视角对“望×兴叹”及其相关实例进行了讨论。笔者认为,“望×兴叹”和其相关实例存在例示关系,新生实例是类型“望×兴叹”的具体表达,从识解角度来说,相较于类型“望×兴叹”,例示在结构和语义上更为详细和精准,在例示域中占有不同于其他例示的特别位置。简而言之,新生实例是图式性成语构式的例示,其存在具有合法性和理据性。另外,“望×兴叹”的允准机制和构式压制现象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主要在于抽象出来的图式性结构不仅具有允准的功能,还具有提供语法规范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动宾结构在产生构式压制的同时,也为新生实例提供模板并给予允准,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经济原则也是重要的外在动因。借用Goldberg(2019)最新研究成果,笔者从语用角度对“望×兴叹”的能产性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覆盖范围和竞争是扩展和限制“望×兴叹”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