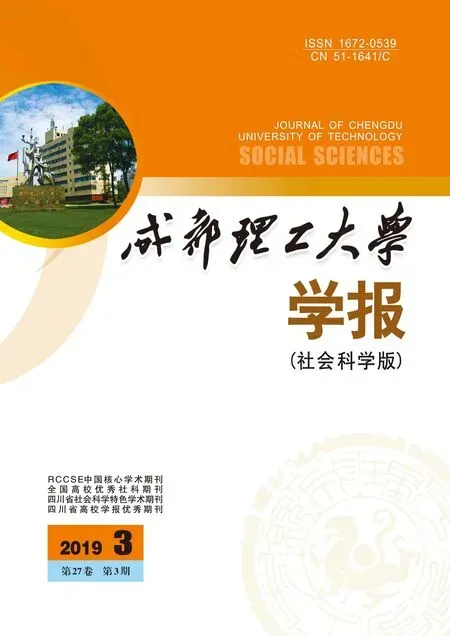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性质与效力:实证考察和路径选择
2019-05-30詹泽淳
詹泽淳
(中国人民银行 广州分行, 广州 510120)
一、引言
为更好发展房地产行业以推动经济增长,减轻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借鉴英国等的法制引进了房屋预售制度,即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特定条件下,可以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预购人,由预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全部或部分给开发商。基于防止开发商悔约将已经出售的住房再次出售或者进行抵押而损害商品房预购人的权益[1]107[2]31,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借鉴德国法,引入预告登记制度,并将之规定于第二十条。这一适用于“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的预告登记制度创设的初衷是实现预购人以变动不动产物权为归宿的债权请求权。由于在商品房预售中,预购人在无法一次性支付全部购房款,需先支付首付款后向银行借贷,而此时会应银行的要求将预购的房屋作为担保物设定抵押以保障银行房贷债权的实现,谓之为预购商品房抵押。
与商品房交易这一关乎社会生活中普通人之切身利益经济活动的重要性相比,我国法律对预购商品房抵押之规定仍过于笼统,特别是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具体法律效果如何付之阙如。学界对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研究大多是从立法论和解释论的角度去展开,鲜有从法院相关判决展开实证研究。有鉴于此,为保证研究的针对性和实践性,避免理论研究成为无本之木,本文收集相关案例,并进行系统归纳,考察法院裁判现状,在充分了解我国目前预购商品房抵押纠纷司法现状的基础上,从中归纳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二、司法实践的实证考察
本文在北大法宝案例数据库以“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为关键词检索案例(1)。鉴于在该案例库中,检索到的相关案例数据较为庞大,为了便于分析,本文随机选取180篇判决书,剔除与预购商品抵押登记无关的案例、重复案例、同一法院审理的相似案例,另外有一审和二审乃至再审裁判文书的案例,统计时只列为一个案例,最后获得的样本案例共计114个。样本案例地域分布范围广泛,囊括了26个省级行政区,基本上覆盖全国,而且经典案例和法宝推荐案例占绝大部分,确保样本案例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一)宏观数据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相关纠纷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先对选定的样本案例阅读分析,进而作简略的数据统计(见表1)。

表1 案件的审理法院和审级
表1给出的是样本案件的审理法院级别及审理程序:最高院判例(含最高院公报案例)1个,高院判例10个,中院判例83个,基层法院案例20个。27个一审程序审结的案件,87个二审及再审程序审结的案件。

表2 预购商品房抵押案例的复审的改判率
表2展示了样本案例的上诉率和改判率。从表2可以看出,复审案件数量明显多于初审。114个样本案例中,有84个案例经过了上诉(包括2个既经历上诉,又经历再审程序的案件),上诉率达73.6%。另外,在87个复审案例中,改判的案例有39个,占比44.8%。可见,在司法实践中预购商品房抵押案例的终审改判率也不低。
在阅览复审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改判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对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法律性质为何,原审和复审的观点不一。比如在一个案件中,一审法院认为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性质是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二审法院的裁判观点是,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属于抵押权预告登记,其法律性质不同于抵押权设立登记,进而在登记所产生的法律效力问题上,与一审法院观点存在较大差异(2)。
(2)基于对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所产生效力的认识不同,原审法院和复审法院对登记权利人享有何种权利作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39个改判的案例中,有37个案例就登记权利人对登记房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持对立观点。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终227号案例:一审认为,“办理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证明,抵押已生效”,就已办理抵押登记的预购商品房,登记权利人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二审法院则以在未办理房屋抵押权登记之前,抵押权未设立为由,变更一审关于登记权利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决(3)。又例如在另一案件中,二审法院认为,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的对外公示性使其产生优先受偿的效力,变更一审判决,判决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登记权利人就抵押预告登记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4)。
(二)微观数据分析
以上是从总体性数据的角度大致了解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相关纠纷的裁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再分析所检索到的样本案例,发现法院审判思路大同小异,基本上首先是判断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性质,其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接着判断登记权利人享有何种权利,最后决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如何救济登记权利人。由此形成了表3所示的四种审判路径。
(1)法院的主导性审判思路是明确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性质为抵押权的预告登记,不是抵押权的设立登记,抵押权并未因而设立。在未办理抵押正式登记之前,登记权利人对登记项下的房产并未享有抵押权(5)。换言之,采纳该审判路径的法院认为,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所登记的对象是将来设立抵押权的请求权,并非现实的抵押权;登记权利人享有的是,在抵押条件成就或双方约定的期限届满的情况下,请求对方办理房屋抵押权正式登记的权利。对如果预购商品房建成后的产权未登记于债务人名下以致无法办理抵押权本登记,或者虽登记于债务人名下,但不予配合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则债权人不能对该预购商品房行使抵押权。

表3 法院的审判路径
(2)即使法院认定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性质为预告登记,对于登记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并非都认为是债权请求权。即在登记权利人对抵押权的预告登记未能转为正式登记无过错的条件下,其对预购商品房享有优先受偿权(6)。何谓无过错?在预购商品房具备物权登记条件下,抵押权未能办理正式登记的事由不能归责于预告登记权利人(7)。在实务中,不能归责于登记权利人的事由是指非因预告登记权利人自身原因阻碍抵押预告登记转为抵押权正式登记(8)。其一般包括开发商延期交房或者预购人无故不及时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不予配合办理抵押权正式登记甚至下落不明。在此情况下,不少法院认为债权人对未能办理预购商品房的抵押权本登记无过错,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即使已超过三个月的登记期限仍然有效(9)。而且有法院主张:此时商品房已经具备办理抵押登记条件,预购人怠于办理登记的行为,本质上属于预购人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应参照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视为条件已成就,即债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条件因义务人恶意阻却而依法视为已成就(10),从而支持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若实现抵押权过程中登记部门需要以办理产权证为前提的,则债权人可先行垫付相关费用办理产权证,此后再从拍卖、变卖该房产所得价款之中扣除(11)。即在预购人未申请办理商品房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手续,房屋的所有权仍登记于开发商名下时,债权人可依判决书请求开发商协助办理预购商品房所有权转移登记,并向登记部门单方申请办理抵押权本登记。
为了减少对物权法定原则和物权公示原则的冲击,有些法院还会判决先由购房人和房地产开发商协助配合登记权利人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在办理抵押权正式登记后或购房人拒不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依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确认债权人对抵押房屋的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12)。
(3)少数法院将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定性为预告登记,但其产生的法律效力与抵押权本登记的效力无异,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进而认定预告登记权利人享有抵押权以及对预购商品房处置后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权(13)。因为预告登记的效力在于赋予其所产生的请求权以物权效力,体现在抵押权预告登记上就是登记权利人对预告登记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14)。
(4)最后一种审判路径认为,预购商品房作为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其抵押登记的性质是在建工程抵押登记,并以此作为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依据(15)。采纳该审判思路的法院认为,《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一百八十七条确定了正在建造中的房屋可以进行抵押,而且并未限定抵押登记的形式;无论是抵押预告登记还是正式的抵押登记,只要当事人在登记机构明确作出了申请办理抵押登记的意思表示,抵押权就自登记时设立;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16)。甚至有法院直接在判决理由中言明:预售房屋作为正在建造中的房屋,可以成为抵押物,只要办理了抵押权的预告登记,该抵押即为有效抵押,抵押权人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任意第三人不能取得预购抵押房屋的所有权(17)。另有法院虽然没有明确将预购商品房抵押认定为在建建筑物抵押,但以《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18),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七条为判决依据(19),实际上也是采纳这一审判路径。
综上可见,法院为了解决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都要确定它的性质,在遵循这一思路时却有不同的路径,未形成统一且稳定的见解,亟待澄清和统一。因此,如何正确认识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性质和法律效力,仍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将以此作为切入点来对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制度进行反思和完善。
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登记的性质
预购商品房抵押制度首次出现是在《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但因该部门规章制定时尚未有预告登记制度,所以对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未作定性,只要求登记机关对抵押合同作记载。如此,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性质是预告登记抑或本登记不无疑问。
有论者以《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权囊括预购商品房抵押权[3]460[4]16,并依据《房屋登记办法》将预购商品房抵押与同属于“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在建工程抵押”相区分,认为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是本登记,预购商品房抵押办理的是预购商品抵押预告登记[5]464。
上述观点殊值赞同,但其解释仍有待商榷。《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五)项将“正在建造的建筑物”纳入抵押财产范围,其后在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成立”。细言之,在建建筑物抵押登记后债权人即取得抵押权,这暗示“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登记是正式的抵押权设立登记,是本登记。而预购商品房抵押的客体是预购人从房地产开发商处预购的商品房,可能是正在建造的建造物中已经建造完成的部分,也可能是尚未建造的部分,其与“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客体仅限于已经建造完毕的建筑物部分,不包括尚未建造的部分有很大区别。从理论上讲,当在建建筑物非商品房的情况下,与商品房预售和预购商品房抵押毫无瓜葛,只有在建建筑物是商品房的情况下,商品房竣工验收前,部分商品房已经建造完毕成为在建建筑物一部分时,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和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的标的物有可能会重叠。然而,实务中预售该商品房即需要取得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出具解除抵押权的书面同意,消除在建建筑物抵押权,或者出具同意预售的书面证明,抵押人的同意则往往产生放弃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的效果,否则无法进行预售(20)。若预售都不可能完成,更遑论预购商品房的抵押,何来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可见,在建房屋抵押与预购商品房抵押在时间轴上是不可能重合的,只要办理了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则该预购商品房不属于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的标的物,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也无法被在建建筑物抵押登记所包含。
另外,在建建筑物抵押登记是开发商为解决在建工程的融资问题而办理的,然而在建建筑物是否完工存在不确定性,以其作为抵押物难以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所以,在建建筑物抵押的真正价值主要体现在土地方面,不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也不会规定在申请办理在建建筑物抵押时要一并提交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这与预购商品房抵押主要体现在房屋价值存在区别,更何况预告登记主要解决的是购房人与银行之间的贷款风险问题。
是故,预购商品房抵押权包含于“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权,并与在建工程抵押权并列区分实为不妥(21)。正因为预购商品房是期房,商品房或尚未建成,其上不能成立所有权,或尚未办理所有权的首次登记,也就无法办理抵押权的正式登记[6]79。作为借贷人的银行为确保将来债务人(即预购人)能够偿还贷款,保障自己的债权能够实现,有在以预购商品房为担保设定抵押的强烈需求,该需求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安排,由此,《房屋登记办法》将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规定为预告登记(第六十七条第(二)项、第七十一条)。《细则》继受这一规定,并于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中规定,在预购商品房经房屋所有权登记取得产权证书后,当事人应当将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转化为现房抵押权的首次登记,再次强调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非本登记,而是预告登记。
四、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法律效力问题
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作为预告登记之一种类别,对维护诚信,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该登记最重要的功能是保障登记权利人实现债权,而能否发挥担保功能取决于抵押权预告登记所具有的法律效力。
(一)保全效力和顺位效力
预告登记是为保全将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请求权而进行的不动产登记[7]168。具体而言,其具有保全债权请求权发生所指定效果的效力,排斥后来的其他物权变动[8]384。在办理了预告登记之后,预告登记义务人即不动产登记名义人违反义务对不动产进行处分,损害预告登记权利人即债权人利益,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依《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的处分不发生物权效力,该条款被下位法具体化为登记禁止,即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登记机构不得办理处分该不动产的登记(《土地登记办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房屋登记办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可见,我国的预告登记立法模式不同于德国“相对无效”立法例[9]431-432[10]36-38[11]109-110,采取的是限制不动产权利人的处分,即“登记障碍”,也称为“登记簿冻结”。
在办理预购商品房抵押情形下,即预购人在与银行共同办理预购商品房抵押的预告登记后,将预购商品房再行转让或者再次进行抵押的预告登记,对前一预告登记权利人(借贷人)将产生何种法律效果?
对于物权变动,我国采取了区分原则。《物权法》第九条强调不动产登记对物权变动发挥实质性作用,第十五条则明确了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债权合同(原因行为)的生效依据债的生效要件[12]48。即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物权变动的原因和物权变动的结果,这两个法律事实的成立生效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不同[13]。就预购商品房再次转让合同以及约定二次抵押预告登记的合同效力问题,虽依《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否定物权效力,但是在第十五条区分了物权变动合同的效力与物权登记效力的前提下,未办理物权登记并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另外,我国《城市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六条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予以规范,但国务院至今未对该问题作出规定。在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私法无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下,依据私法无禁止即自由,应当认定预购人和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合同有效。由此可知,《物权法》第二十条“不发生物权效力”并非指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不发生效力,而是指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法院不支持以出卖人缔结合同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由提出的合同无效诉求。在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中,虽然因为商品房尚未建造或者尚未建造完毕(22),所有权尚未存在,预购人谈何享有所有权,只能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但这是一种效力强大的债权请求权(23),能够在未来就预购商品房所有权办理本登记的请求权。举重以明轻,在完全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而签订的买卖合同尚为有效,则能够在条件成就时请求开发商转移房屋所有权办理产权登记,从而享有商品房所有权的预购人(抵押权的预告登记义务人)未经抵押权的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转让预购商品房之合同是为有效。在登记程序上,《细则》第八十五条第二款对此进行细化:在未取得预告登记的权利人书面同意,处分该不动产权利并申请登记的,不予登记。加之,在预购商品房不具流通性且有网上签约机制和与不动产登记簿准确对接的楼盘表等预售交易机制共同规制的情况下[14]130,第三人与登记名义人签订合同后很难办理登记,只能追究登记名义人的违约责任。于此,仅就《物权法》第二十条和《细则》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而言,其并没有区分转让已办理抵押预告登记的不动产与再行抵押已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的不动产这两类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则明确,就已经办理预告登记的不动产,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无论是转让还是设立他物权均为不发生物权效力。实质上,预购商品房办理了抵押权预告登记,能否限制预告登记义务人的处分行为特别是再次抵押的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预告登记保全效力的具体内容,也涉及抵押权预告登记是否具有顺位效力的问题(24)。
对此,有学者认为,《物权法》第二十条没有明确规定权利顺位的效力,第十四条却明定物权变动以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即以本登记为准,申言之,预告登记不具有顺位效力[15]61。另有观点认为,预告登记的权利顺位效力须进一步审慎讨论,理由是我国的抵押登记是以登记时间的先后确定顺序先后,并没有采取顺位固定主义[16]361。学界中亦有预告登记保全的债权因履行而转化为物权时,该物权的顺位依据预告登记时间予以确定,而不依其产生时在登记簿中记载的时间为准的观点[17]432。
笔者认为,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的最大利益是将预告登记推进为本登记,那么只要中间处分所产生的权利不抵触本登记权利,则其应该有效。中间处分与本登记是否抵触,应视中间处分登记的权利内容与嗣后所要办理的本登记权利内容是否相容而定。众所周知,不动产抵押权实际上是以不动产的交换价值担保,并具有优先受偿的特性,自然可以就标的物的剩余交换价值,再设定抵押权,而依据抵押权登记的先后顺序,决定其受偿的先后次序。而预购商品房在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之后,再次抵押并办理预告登记,如果嗣后都能够办理本登记,则两者为相容物权。所以,先后办理多次抵押权预告登记,予以并存记载是具有可行性的,并依其成立先后,决定其效力的优先劣后。
预告登记毕竟属于预备登记,其有两种最终路径,一者在条件成就时转化为本登记,另者在其所依附的债权请求权消灭时而自动失效。为了能够实现预告登记所保全的债权请求权指定的效果,从而保障将来实现债权,在预告登记转为本登记时,其所具有的权利内容和顺位必然同时复制于本登记之上,且申请本登记的效力溯及预告登记之日,否则在预查封、查封和强制执行中抵押预告登记的担保功能无法实现,成为有名无实之制度[18]110-111[19][20]95。可见,预告登记的顺位效力是与担保效力相辅相成的,即使不认同文义解释的结论,也应肯定预告登记具有保全顺位的效力,方不背离预告登记的立法目的。在预告登记具有顺位效力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对预告登记名义人再行抵押预购商品房予以限制(25)。在不动产登记立法中规定“按照预告登记事项办理相应的登记”,即按照预告登记的类型和权利内容办理相应类型和相应内容的本登记,而按照预告登记的顺位来确定本登记的顺位,也属应有之义(《房屋登记办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细则》第八十五条第三款)[21]317。
综上,按照现行立法例,未经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债权人即银行)书面同意,登记名义人转让预购商品房,只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物权变动效力并不发生,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为其办理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即便办理了登记,也不发生不动产物权转移的效力;而再次抵押预购商品房的,无论是在预购商品房仍处于在建时申请再抵押的预告登记,还是在预购商品房建造完毕成为现房申请现房抵押本登记或预告登记均不应予以禁止。
(二)完全效力
按照德国法系预告登记的制度经验,预告登记保全的权利在预告登记的义务人破产或被强制执行时,仍能从义务人负担的其他债务中脱离出来并得到完全实现,是为预告登记之完全效力。
一般而言,预购人通常是自然人,但是现行法并没有禁止企业成为预购人,所以作为登记义务人的企业被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对权利人请求权有何影响,还是有探讨的必要。即在破产宣告之前已经办理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预购人于破产宣告之后,预告登记权利人能否对破产管理人请求本登记?对该问题,基本上有三个立场:一则认为破产宣告前,抵押物权因尚未完成登记而没有设立,则不能对抗第三人,故不能请求办理本登记;二则认为在破产宣告后,只要具备实体法上要件,可以请求办理本登记;三则认为在破产宣告前,具备实体法上要件,在当时则已具备转化为物权的本质,此时得请求破产管理人协助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管理人不得拒绝,应协助预告登记权利人将抵押权的预告登记转为抵押权的本登记。第一个观点,似乎有忽视预告登记本身所生效力的问题,仅认为只有办理本登记才能对第三人主张权利。而第三个观点认为,只有在破产宣告前具备实体法上要件,才具有物权效果,似乎对抵押权预告登记的保全效力未予重视。而第二个观点极力倡导预告登记不因日后登记义务人被裁定宣告破产而受影响,权利人得对破产管理人请求本登记,认为预告登记所记载的权利属于广义的保全权利的一种。预告登记所登记的权利之所以有类似于物权的性质,是因为其被登记部门记载而公诸于众,能够为相关交易者查阅知悉,具有公示性。换言之,单纯债权请求权因被预告登记而带有类似于物权的性质,若以未办理本登记而不能对抗第三人,此与单纯债权请求权并无区别,则抵押权预告登记对于第三人的物权性格,又具有何种特殊内涵呢?因此,以抵押权预告登记有类似物权的性质,在破产情形下,应作取回权或者别除权处理。
对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是否亦具有对抗强制执行程序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因征收、法院判决或强制执行而办理的新登记,系国家权力保证执行的结果,预告登记的请求权人不得主张新登记乃其私权利之妨害而无效[22]250,即预告登记不能对抗征收、法院判决或强制执行而产生的新登记。所谓征收,是国家为公共需要或公共用途的目的,基于公权力依照法定程序强制取得私有财产所有权,并给予合理补偿的公法行为。依据私法权利原则上受公共利益的限制,预告登记对因征收所为的新登记无排除效力,符合法律趣旨,应无疑义。而就法院判决或民事强制执行而言,依私法自治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权利未能得到满足时,以国家权力强制促其实现。换言之,私法上权利是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促其实现而已,与征收的公共利益目的有区别(26)。民事强制执行作为仅为实现当事人私人利益的国家行为,其执行后之新登记与预告登记并无公私之分,故预告登记对其具有对抗效力[23]31。何况,预告登记作为物权性之担保方式,具有对抗强制执行之效力是必然要求,不若则难称其为特殊担保[24]593-594。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对办理了受让物权预告登记的不动产,受让人享有提出停止处分异议或排除执行异议的权利,而根据《物权法》第二十条,不动产物权受让人既可以是房屋的买受人,也可以是其他不动产物权协议的权利人,则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样享有此权利。由此看来,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似乎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
不过,一旦办理了预告登记,则不动产无法强制执行,未免对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人过度保护。毕竟强制执行是为了迅速、经济地将标的物查封并变换为较高的价金,以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到满足,欲实现该目的须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不能有偏颇。执行程序分为保全措施和变价措施这两个阶段,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是否具有完全效力应分别就两个阶段进行讨论。在保全措施阶段,如果是预查封,预购商品房尚未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预告登记权利人享有预期财产性利益,只有当预告登记转化为本登记,预查封方才转为正式查封;如是查封,则表明预购商品房已办理权属登记,或是开发商办理商品房权属初始登记,抑或预购人办理商品房的产权证书。基于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的顺位效力,预查封登记时间(无预查封则以查封登记时间为准)或者查封登记时间与抵押预告登记时间孰先孰后决定其顺位的先后,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不会因预查封或者查封而减损。
在变价阶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我国对拍卖不动产上权利负担的处理是根据不动产上权利负担性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立法政策,就以取得不动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权利采取涂销主义,以取得不动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权利采取承受主义,但无论何种情况都配之以剩余主义。而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所保全的是请求预购人办理房屋抵押的权利,在抵押权的预告登记符合转为本登记的条件时,预告登记权利人可以确定地取得商品房抵押权,则拍卖、变卖该不动产之后,按其抵押顺位受偿,无须在保全阶段赋予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提出强制执行异议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银行可能因商品房被拍卖、变卖而丧失预期利益,故而在清偿时有必要对其所担保的债权利益、期限利益予以适当考虑。
(三)优先受偿之效力
当作为债务人的预告登记义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符合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条件时,作为债权人的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是否有权处分抵押物并以其变价款优先受偿,对混合共同担保中债权人实现担保物权的先后顺序、作为保证人的房地产公司是否免除阶段性保证责任等问题的解决都起到决定性作用[25]449-451,更重要的是这决定了预告登记能否从债权转化为物权,保障物权的实现。
通过实证考察可知,否定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享有优先受偿权是实务界的主流观点,许多学者也持这一观点。其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我国《物权法》明确采取了物权法定原则,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所登记的并非现实的抵押权,而是将来设立抵押权的请求权,该请求权虽具有排他效力,但预告登记本身并未使预告登记权利人获得现实的抵押权,其不享有优先受偿效力。
其二,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与抵押权设立登记二者的法律性质不同,法律效力也存在差别。预告登记是特殊的公示方式,所登记的客体并非物权。在预购商品房抵押中,办理预告登记并未使债权人现实地取得抵押权,只是担保预告登记权利人在登记条件具备、或者所附条件成就及所附期限到来时能够取得预告登记不动产的抵押权。因此,其法律效力是使抵押合同上的债权(请求抵押人办理抵押登记的权利)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并不能取代抵押登记。单凭抵押权预告登记并不能使登记权利人获得抵押权,缘由在于未办理抵押登记之前,债权人不可能获得抵押权[26]。
第三,现行法并未规定抵押权的预告登记权利人就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等特殊权利。预告登记权利人相较于其他债权人,并无特别的利益付出,自然无须特别对待。另外,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房屋是否能够竣工尚不确定,房屋初始所有权能否存在仍有变数,则变卖、拍卖无从谈起,更遑论就处置房屋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所以,若不假思索肯定抵押权的预告登记权利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只会出现空有权利之名,而无权利之实的情形。
第四,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利益完全可以通过现行法律框架提供保障,无须通过赋予其优先受偿权的路径予以保护。具体而言,对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权利采取区分保护的路径,区分标准是预告登记是否具备转化为本登记的条件。在具备转化条件时即预购人已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可应预告登记权利人的诉请判令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义务人协助办理房屋抵押权登记,并可予以强制执行;在不具备转化条件情况下,若是因规划、资金等原因造成预购商品房无法建成导致银行的债权无法实现,这是商业风险所在无法避免,如何解决有赖于立法论,如果是开发商有能力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而故意不办理,则一般由开发商对预告登记义务人即预购人的贷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若是预购人的原因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可判决开发商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并进一步办理抵押权登记实现抵押权。因此,不赋予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优先受偿权并不会对其债权的实现有重大影响[27]19-20。
正如否定说所强调的抵押权预告登记不同于抵押权设立登记,不同法律性质决定了法律效力的不同,故而,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将使两者混淆。然而,因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身原因而未办理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时,或者当预购人资金链断裂,难以偿还贷款,为了逃避债务,以各种借口不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时,将导致作为登记权利人的贷款银行无法将抵押权的预告登记转为抵押权设立登记,加剧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影响了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安全。面对这一状况,应例外地承认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在具备实现抵押权的条件时,享有优先受偿权。理由如下:
首先,预告登记旨在保障债权人“将来实现物权”,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强化债权人的请求权,将其从一个单纯的特定人之间的请求权转为具有排他效力的请求权,从而具有物权的性质。所谓“将来实现物权”,并非仅指在登记条件具备时通过将预告登记转为本登记进而取得相应的不动产物权,也包括在登记条件已经具备虽未转为本登记但危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出现时,使债权人能够处于类似于物权人的地位,使其债权获得特定的物权效力以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将抵押权预告登记的功能仅仅理解为使债权人取得了将来发生抵押权变动的请求权,即当抵押登记条件具备时或约定期限届满时对涉案的不动产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请求权,显然不符合《物权法》的立法本意。
其次,否定预购商品房是优先受偿权标的物的依据之一是建设部、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然而这一规范性文件第七部分(27)限制的是当事人之间转让预购商品房,并未将预购商品房作为禁止流通物[25]455。而且,该《意见》侧重的是未竣工的预购商品房,并不包括竣工的预购商品房。因此,在出现预购商品房已经竣工,但因开发商故意拖延等原因未办理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或者开发商已办理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但预购人不予配合办理商品房所有权转移登记等非预告登记权利人过错或所能控制的情况下,现行法律并没有否定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的优先受偿效力,何况“在特定条件下承认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的优先受偿效力,并不等于一律赋予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以优先受偿权”[28]427。
再次,否定说一方面认为,抵押权预告登记使债权人取得了将来要求债务人配合申请设立抵押权的请求权,该请求权经预告登记后具有了排除物权变动的效力;一方面又认为,抵押权预告登记不等于抵押权登记,故此预告登记权利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抵押权人并不占有抵押财产,因此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的排他支配并不体现为对抵押财产实体的排他控制,而是体现在对该财产交换价值的排他控制即享有优先受偿。显然,所谓债权人在抵押权预告登记后的排他效力只可能体现在预告登记权利人于抵押权实现条件具备时,就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该项请求权的排他效力。
另外,承认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的优先受偿权也符合我国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从楼盘的建设到开发商办理所有权首次登记,再到预购人购房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每一环节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存在时间间隔。在此时间段内,预购人不按期偿还贷款或者不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证进而阻碍抵押权本登记的办理等情形时有发生,银行就极需要通过优先受偿权来确保自己的利益。
虽然有论者以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由,主张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债权实现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固有保护途径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另一保护途径的合理性,何况开发商的阶段性保证担保并不能充分保障银行债权的实现。若先前存在在建建筑物抵押权,则预购商品房抵押贷款一部分用于偿还在建建筑物抵押所贷款项用以除去在建建筑物抵押权,剩余一部分则被开发商一般作为企业周转资金,用于楼盘的继续开发或者其他业务。债务人逾期不偿还贷款的情况下,由于商品房预售资金是专款专户、专款专存、专款专用(28),因此自有资金极其有限的开发商很难对银行承担保证责任,特别是存在房地产开发公司破产的情况。因此,欲通过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阶段性保证来防范银行实现主债权所存在的现实风险的目的难免落空。是故,银行债权的实现唯有通过确认其对预购商品房享有优先受偿权来予以保障。
最后,承认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的优先受偿权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预告登记本身作为沟通物权法和债权法的桥梁,融合了物权和债权的双重特性,是债权内容和物权效力的结合体[10]34。既然《物权法》第二十条已经明确规定了预告登记制度并且通过该制度赋予了债权人的请求权以物权特征,肯定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的优先受偿权也完全不违背物权法定原则。
五、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保护的路径选择
(一)救火扬沸式的解释路径
与修改法律相比,法律解释的成本和难度较低,因此在明确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效力之后,寻找遁入现行法律制度的路径成为首要任务,而这涉及法律解释的问题。
针对预购人不配合房地产企业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或者在取得房地产权证之后,不配合申请将抵押权预告登记转为房屋抵押权登记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可将预购商品房抵押等同于在建工程抵押,从而支持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但这存在不妥之处。首先,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性质并非抵押权本登记,而是预告登记;其次,预购商品房抵押与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差异在上文已有阐述,此二者不能混淆。故将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视为抵押登记,或者认定为在建建筑物抵押登记,从而认为登记权利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观点有待商榷。有观点主张依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以司法判决确认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的优先受偿权。但《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指形成性裁判文书,并不包括给付性裁判文书和确认性裁判文书,这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七条得到明确。所以,无论是确认预告登记权利人享有优先受偿权,抑或判决登记义务人协助办理本登记的法律文书,均无法以《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作为裁判依据。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作为预购人的债权人,自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行使债权人代位权。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将代位权的客体限缩为“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但是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趣旨在于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并不局限于金钱债权,其他债权、物权及物上请求权、形成权等权利自然应当包括在内。因此,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应扩张解释为包括登记请求权在内的能够构成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权利。那么在预购人不予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导致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无法转为房屋抵押权登记时,预告登记权利人可通过行使债权人代位权,要求房地产企业在办理完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之后,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转移至房屋预购人名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亦规定了在预购人未履行贷款合同义务,也未办理商品房抵押登记手续时,债权人可以取得预购人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全部权益,亦即有权要求开发商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在取得房地产权证之后,预购人若不配合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办理抵押权登记。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可诉请预购人履行合同义务,协助办理本登记,法院可以判决预购人履行申请义务。逾期不配合申请的,预告登记权利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预告登记权利人持确定判决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抵押权登记。然而这一解释存在些许瑕疵。其一,申请登记的行为是向登记机构提出请求登记的意思表示,该申请义务是否可以强制执行不无疑问。其二,即使将登记申请定性为程序性行为,不涉及当事人合意,可予以强制执行,并由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拟制登记义务人的申请,其实质是登记权利人单方申请。然而,依据《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抵押权登记是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而且依据该条第二款的兜底性规定,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能规定单方申请登记的情形。虽然《细则》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持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单可以单方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但是作为部门规章的《细则》规定单方申请的情形不是很妥当。
面对房地产企业因故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导致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未能转为房屋抵押权登记的情况,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如何赋予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享有对抵押财产的优先受偿权,存在解释上的困难。
《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处分不动产权利的行为无效,表明了我国对预告登记的保全效力采取了绝对无效的路径。然而,这是针对不动产权利人处分不动产之后,第三人所取得的不动产权利与预告登记权利人的请求权所要实现的物权内容发生冲突的情况,对已经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的预购商品房再次办理抵押权的预告登记,明显不在此列。因此,在可对“不发生物权变动”作限缩解释,后一抵押权预告登记不应无效。
(二)绝薪止火的应然路径
商品房预售制度在可预见之将来仍将存续,其以未来物作为买卖标的物,使整个交易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为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降低风险,增强信用安全,预购商品房抵押不可或缺,其登记之效力与预告登记大同小异。虽然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从现行法中无法确定地推导出其具有优先受偿之效力,但是存在的并非均是合理的。唯有恰当适度地扩充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法律效力的内涵,才能保护银行权益,相应地也维护了交易稳定,为当事人之经济活动扩展空间。基于此,我国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制度的应然路径如下:
(1)未经抵押权的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同意,抵押权预告登记义务人对该不动产再次抵押,所办理的抵押权预告登记有效。
(2)预告登记保全的债权请求权实现时,由此产生的不动产物权依据预告登记的时间确定其顺位。
(3)抵押权预告登记不得对抗法院的执行措施,但是在强制拍卖阶段,预告登记并不因强制拍卖而消灭,而且应考虑预告登记所担保的请求权价值,即所担保的债权数额,并将其从拍卖价款中予以扣除,为预告登记权利人提存,以待预告登记转为本登记之时,满足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若抵押权的预告登记未能转为抵押权登记,则应当将提存价款交付执行债权人,用以清偿其债权。
(4)抵押权的预告登记义务人破产的,该不动产不属于债务人财产,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5)在符合实现抵押权的条件或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对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注释:
(1)参见北大法宝数据库,http://www.pkulaw.cn,检索案例的时间截至2018年4月1日。
(2)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甘民终107号,兰州中海宏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等金融借款纠纷案。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终277号,伊犁豫兴混凝土有限公司诉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4)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终2108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沧海支行等与赵楚等金融价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5)典型案例是,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诉上海东鹤房地产有限公司、陈思绮保证合同纠纷案,详细案情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9期,第36-40页。此类案件还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再终字第14号,攀枝花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许某榕、攀枝花市鼎盛鑫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豪思佳居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天韵金沙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二终字第00891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百大支行与王武甲、王文甲、杨健康、李葳、铜陵银基置业有限公司、铜陵市宝业商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沈01民终11228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南湖支行与陈立娜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终313号,颜山诉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郊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再3号,罗秋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赤岗支行与张医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2民终651号,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武口支行与沈建军、李学兰、石嘴山市瑞祥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民初3451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诉黄国良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6)参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980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支行与袁相宏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金商终字第37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胶州支行与周凯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二初字第00689号,长沙市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诉段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7)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404号,刘军达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等撤销之诉上诉案;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1民终2439号,太原宝佳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平阳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8)参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哈民三商初字第137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与高秀英、刘殿君、黑龙江东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衢商终字第374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等诉黄建春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9)参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金商终字第189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诉金香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0)参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榕民终字第5965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北支行与周文娟等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11)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126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与柳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12)参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终2359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王栋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6民终1687号,辽宁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终3379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与韦秀芳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7民终1567号,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胡进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13)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3民终1676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与吴湘婷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再141号,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蒋村支行诉黄虹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鄂0528民初413号,湖北长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虎、向红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等。
(14)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镇商终字第183号,镇江市远达电器公司诉建设银行扬中支行预告登记抵押权确权纠纷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终3022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与张芳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15)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终字第691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市支行与詹庆须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062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与乐永明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等。
(16)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民二终字第00780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南城支行与刘忠发等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17)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922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与陈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18)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民终2182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四支行与高卉、鲁商置业青岛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商终字第1040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六(商)初字第2354号,黄益弟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温州市苍南县人民法院(2015)温苍商初字第2489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行诉潘孝战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浦民六(商)初字第674号,甲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分行诉瞿乙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等。
(19)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8)浦民二(商)初字第4679号判决书。
(20)实务做法参见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四十九条,《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国土籍[2007]751号)第5条,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房屋登记工作规范》(京建法[2014]10号)第5.3.1.1条第(七)项、第5.3.1.2条第(六)项。
(21)实际上,在建工程抵押、“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和在建建筑物抵押只是法律和部门规章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
(22)在预购商品房已经建造完毕的情况中,开发商因合法建造该事实行为取得所有权,但因未登记未取得大产权证,在出售给购房人依据《物权法》第三十一条不发生物权效力,预购人不享有商品房的所有权。
(2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无论是预购商品房还是现售商品房的交易,购房人的债权既优先于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又优先于抵押权。
(24)担保物权是以获取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内容的权利,是对标的物价值的支配权,并不转移标的物占有,因此在同一财产上可以并存数项担保物权。只要承认抵押权预告登记的顺位效力,自然毋须再限制预告登记权利人再次抵押的行为。
(25)尹田教授、冉克平教授和程啸教授以立法例不禁止“重复抵押”,即同一财产上可以同时存在多个抵押权,以及只要承认预告登记的顺位效力,即使预告登记名义人再次抵押不动产(包括抵押权本登记和抵押权预告登记),也不会损害先前预告登记担保的请求权为由,认为没有必要禁止其再次办理抵押登记;参见尹田:《物权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冉克平:《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06页;程啸、尹飞、常鹏翱:《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68-469页,该部分由程啸教授撰写。另外常鹏翱教授反对预告登记有登记禁止法律效果,认为应当参照德国立法例承认预告登记的相对无效效力,否则有悖私法自治,且不利于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参见常鹏翱:《物权程序的建构与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26)法院的确定判决一般可以成为强制执行的执行名义,所以没有必要将二者分开讨论。
(27)《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第七部分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禁止商品房预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
(28)实务做法参见地方政府部门规章,如《天津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合肥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南宁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