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的世界视野
2019-05-23吴晓东
☉吴晓东
1926年2月15日出版的《良友》画报创刊号登载了一篇充满春的气息的《卷头语》:
春来了。万物都从寒梦中苏醒起来。人们微弱的心灵。也因之而欢跃有了喜意。
听啊。
溪水流着。鸟儿唱着。
看啊。
春风吹拂野花。野花招呼蝴蝶。
大自然正换了一副颜面的当儿。我们这薄薄几页的《良友》。也就交着了这个好运。应时产生出来了。《良友》得与世人相见。在我们没有什么奢望。也不敢说有什么极大的贡献和值得的欣赏。但只愿。像这个散花的春神。把那一片片的花儿。播散到人们的心坎里去。
紧接着这篇短短的卷头语的是一幅西洋雕塑的照片,一个带翅膀的天使左手环抱着一个花篮,右手舒展开去,撒着花瓣,雕塑的名字叫《春之神》,因此也就有了卷头语“把那一片片的花儿。播散到人们的心坎里去”云云。而这期创刊号的封面则是刚刚出道的19岁的影星胡蝶手捧鲜花的特写照片,取名《胡蝶恋花图》,仿佛花之神播撒的花种已经在胡蝶的怀里朵朵绽放,花团锦簇了。
中国画报史上鼎鼎有名的《良友》就这样诞生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份对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影响深远的画报,恰如阿英所说:“在现存的画报之中,刊行时间最长,而又最富有历史价值的,无过于《良友》”。从创刊到终刊,《良友》登载的照片达三万两千余幅,堪称民国社会画报版的百科全书。
《良友》在现代中国的新闻出版史上之所以独领风骚,究其原因,自然与它以图像为主打内容这一固有的优势密切相关。正像林语堂在《谈画报》一文中说的那样:
其实画报之未列入“文学”,倒是画报之幸。一登彼辈所谓“大雅之堂”,便要失了生趣,要脱离与吾人最切身关系的种种细小人生问题。在我看来,今日画报比文字刊物接近人生的切身问题,而比文字刊物前进。
将来中国教育果普及,工人农人都能看报,文字刊物也非走上这条路不可。
林语堂洞见到“画报比文字刊物接近人生的切身问题,而比文字刊物前进”,这种“前进”的特征与现代科技的进步息息相关。《良友》作为画报,直接得益于20世纪日渐成熟和发达的印刷技术以及摄影技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技术革新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认知手段,而认知手段的革新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许多关于传播媒介技术——如印刷术、摄影术以及新兴的网络媒介的讨论,最终想要解答的都是这一问题。在晚清以降的一系列技术革新中,传入于19世纪末风行于20世纪初的摄影术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人们表达和认知世界的方式。”《良友》的历史地位也需要从它直接影响甚至改换了现代中国人“表达和认知世界的方式”这一高度上着眼。对普通民众来说,摄影图像带给他们的是比文字更加切近的“真实感”与“直观性”,使民众直接目击大千世界万花筒般的影像,对自己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更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从而带给普通读者的正是鲁迅所谓“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世界感受,这种世界感受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民众“表达和认知世界的方式”的现代性转型。
《良友》创刊号“卷头语”这种浅易明快的风格,也无意中显示了《良友》给自己的定位,它此后一以贯之的平民化的风格也为《良友》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如果说“五四”诞生的新文学要求的读者主要是知识阶层和文艺青年,而《良友》却可以摆放在普通的都会市民的床头,或者抵达粗通文字的平民的餐桌,“成为增广见闻、深入浅出、宣传文化美育、启发心智、丰富常识,开拓生活视野的刊物。做到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当时就有人说《良友》画报一卷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不嫌其高深”。

《良友》创刊号封面《胡蝶恋花图》
创刊号的“卷头语”表现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杂志的低调姿态。编者最初可能也没有料到《良友》甫一发行,就引起轰动。创刊号初印三千册,两三天内即售罄,再印两千册也很快销售一空,最后又加印了两千册,“第二第三期时,已达一万”,六年之后已经稳定在五万份的销量。《良友》1932年第72期上题为《今年的良友报又大改新》的启事称:“良友图画月刊每期有五万的销数,每期有五十万读者。”即使保守点估计,赵家璧所说的每期销量4万份的说法也是可信的。即便如此,《良友》依然保持低调的姿态,这种低调进而成为《良友》的办刊风格。与那些高蹈派和先锋派的杂志相比,这种低姿态更有助于彰显平民化的立场,从而赢得更大的市民读者群。如研究者所论述的那样:
与其他怀有“教导”、“启蒙”意图的刊物不同,《良友》的大特点是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良友》编者曾把刊物比做一个“蒙昧的青年”……。
除了市场营销的战略考虑之外,《良友》也注重形成自己的精神性底蕴,其办刊目标堪称所谋者大。《良友》创办一年之后明确提出:“《良友》的目标是‘在普遍性的园地,培植美的,艺术的,知识的花朵’。”“我们想这杂志不是供少数人的需求,却要做各界民众的良友。”李欧梵曾经得出这样的观察:“《良友》的良好声誉不是通过知识刺激或学术深度达到的,而是借着一种朋友般的亲切姿态做到的。”而与读者之间这种平等亲切的朋友式关系,也决定了《良友》画报的“言说方式”。《良友》画报第30期上,有胡汉民为《良友》所作“以平等待我者为良友”的题字,编者由此题字发表了一通感言:
我们很感谢胡先生爱护本报的雅意,我们在他的题词中,可以知得他为我们《良友》取义的深切了。确是,我们《良友》的责任和主旨,是要号召普天下人,尽成良友。当天下人尽成良友之时,平等,自由,自然实现了。我们弱小的中国人,不是天天呼喊着要“自由”与“平等”吗?若是,请实行我们良友之道吧,因为良友的道义,就是要实现“平等”与“自由”。
“良友的道义”,由此被提升到实现“平等”与“自由”的历史性高度。而“号召普天下人,尽成良友”的宏愿,也表现了《良友》兼济天下的世界观和大局观。
从新的世界感受出发,《良友》所刊载的图片的世界视野也得以扩展。《良友》主编马国亮回顾说:“《良友》畅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对时事的重视,每月发生的重大新闻,几乎都可以从画报中找到如实报道的图片。”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战争题材成为《良友》的一大主题,相继刊发有《北伐画史》《甲午中日战争摄影集》《日本侵占东北真相画刊》《黑龙江战事画刊》《锦州战事画刊》《九·ー八国难纪念》《榆关战事画刊》《上海战事画刊》等专刊与号外。《良友》也同时把镜头对准底层。如第103期的《上海街头文化》《北平民间生活剪影》和第119期的《世上无如吃饭难》《上海穷人的新乐园》,都是关于民间生活的速写和剪影。此外如《十字街头》《到民间去》《平民生活素描》等栏目都是持续设立的专题。《良友》涉猎题材的广泛,为读者建构的是现代世界的全景性视野,丰富了读者对于大千世界的想象和认知。
《良友》杂志根植于现代都市文化,注定是海派市民文化的产物。如文学史家吴福辉从《良友》与海派的联姻角度解释《良友》的成功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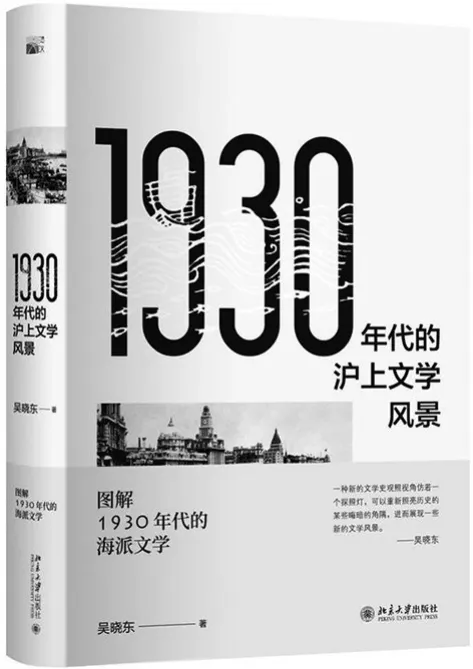
《良友》从来不呈一种单纯的图片加说明的模样,它的文学性历来充沛,特别是海派特性的充沛。比如对于反映上海现代文明形成的驳杂历史过程,它不遗余力。不论是一组摄影作品或连环漫画,从题目到前后安排,都很精心。22期表现日常平民生活,有点心铺、馄饨担、代人写信摊子、剃头挑子、小菜场等多幅写真照片,题目是“上海十字街头”。58期在总题为“现代文明的象征”之下,所载照片有烟囱林立、无线电台天线高耸入云、都市建筑曲线与直线合奏、钢架和铁桥远望、铸造钢铁刹那间的热与力、爵士音乐流行的狂歌醉舞、大教堂管风琴的参差美。其他如31期“新奇之事物”栏有英国机器人、德国飞艇、美国带客厅浴室的长途汽车等介绍,立意和效果都相当艺术化,也体现出海派关注的兴奋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读者如何经由《良友》了解变动中的上海和世界,如何借此大大扩展了眼界。
在《良友》力图展现的世界视野中,核心的视野依然是海派文化和都市生活图景。而图片中内涵的意识形态倾向则集中反映在吴福辉所谓充沛的“文学性”上。陈子善在《〈良友〉画报和马国亮先生》一文中说:“《良友》并非纯文学刊物,但30年代中国文坛的代表作家鲁迅、胡适、茅盾、郁达夫、田汉、丰子恺、老舍、施蛰存、穆时英……几乎无一不乐于在《良友》亮相,或以作品,或以照片,或以手迹,其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良友》由此也携带了文化品位和审美趣味上的双重性。它游走于通俗与高雅,启蒙和媚俗,精英与大众之间,一方面有着启蒙主义式的精神性导向,另一方面也难免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而迎合市民阶层的趣味,只不过无论是精神导向还是市民趣味都潜移默化地融入图像世界以及“文学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