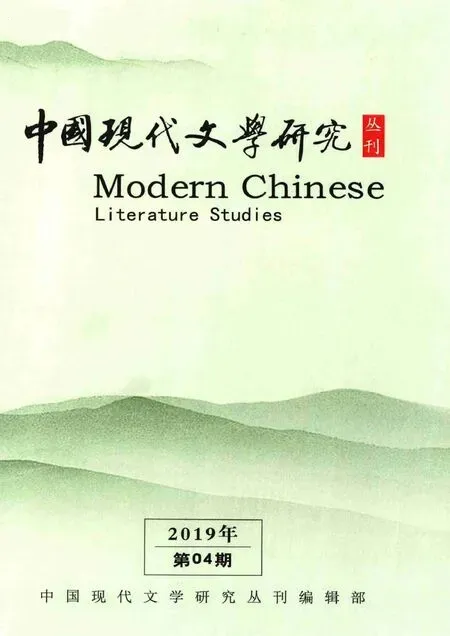张爱玲书信与《小团圆》身体书写
——档案学视角的解读
2019-05-22林幸谦
林幸谦
內容提要:本文将从张爱玲书信的档案学视角及其写作《小团圆》的心路历程,探讨张爱玲如何在自传体小说中展开作家个人自我、身体与情欲的叙事建构。从这本1970年代中期已成书定稿的《小团圆》,可发现张爱玲的女性身体书写已超越那个年代的文化价值观,也构成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叙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小团圆》一书是张爱玲在深具争议性的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建构中,针对爱情毁灭后还能剩下“什么东西”的思考,进行了生命哲学的反思;其所建构的情与欲的身体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女性叙事作品,亦是文学乃至文化的一种叙事建构,为中国现当代女性身体书写提供了新的叙事模式。
一 档案学视角下的《小团圆》与女性自传体叙事
在《小团圆》的写作上,张爱玲留下的信件中有大量的档案数据,构成张爱玲书信档案学的重要基础,从中可找到不同层面、视角的文本解读之依据。事实上,从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件可看出张爱玲本身很清楚这些涉及小说写作过程中的想法与感受及其有关个人生活情欲内容隐私的争议性质。这些书信成为可供研究张爱玲文本的档案学材料,从中可依据张爱玲本人的观点,从不同视角更深一层地探讨《小团圆》一书的价值与意义。
从档案学视角研究张爱玲书信,或将为张爱玲研究带来新的学术视野。从她书信中所提及有关《小团圆》的资料,可进一步考察张爱玲晚年时期传记小说化创作的成果:一方面以其自身的经历重新演绎女性成长过程的自我与主体形构,另一方面这些书信隐含了张爱玲在创作上的个体记忆,是作家写作心路历程与文本建构中不可替代的要素。事实上,作为一种“物质的文献”和固化的信息,书信档案是传递个人经历与社会记忆的媒介。①从档案学视角来说,在社会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方面的考察,亦可直接或间接地推导出书信档案也是社会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
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具有本源性与回溯性的统一、多样态和多媒介的统一、连续性和累积性的统一、层级性和互构性的统一、静态性与动态性的统一、历史重构与历史定格的统一等特点。②
可见书信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乃至基因记忆的构建与重构上具有重要的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知识的内存;不只是知识咨询和转换的媒介,也是保存作家记忆和心理的媒介和桥梁。③
因此这里首先从张爱玲书信档案中有关写作《小团圆》的真实数据加以梳理与探讨,以提供更全面的论述依据。至今,张爱玲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其中不少亦已经出版④,这些书信档案真实地记录了张爱玲的心理、思想和写作历程等第一手数据;其中很多内容对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档案学视角而言,张爱玲书信数量可观,内容丰富,可靠而真实。由这些书信档案可进一步证实《小团圆》最终出版与否的决定性因素⑤。2009年年初,张爱玲遗嘱执行人宋以朗决定出版《小团圆》,表示要还给读者多一个选择的空间,这无疑是还原了张爱玲当年想要出版此书的意愿。正如他在最新出版的、张爱玲两本中译版新书中所言,张爱玲乃是通过这些著作亲自完成了她在叙事文体中的自我形象建构。通过《小团圆》,张爱玲进一步将散布于各部作品间——包括小说和散文背后的张爱玲形象拼凑起来,成为更加有血有肉的真实而多重面貌的张爱玲。
正如张爱玲书信中所言,当年她写作《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因为朱西宁去信对她说他要动手写她的传记。这是张爱玲于1975年10月16日致宋淇夫妇信中所提到的话:由于朱西宁要根据胡兰成的记忆动手写她的传记,因此她要赶在别人之前写出自身的传记,才有了日后这一本自传体小说⑥。虽然张爱玲已回信告知朱西宁希望他不要写这传记,然而她并不相信这话会被朱西宁所接受,并担心朱西宁的传记文章写成后将会“有一半以上也都不相干”的内容出现⑦。显然,张爱玲很担心也不愿意朱西宁或胡兰成等人来撰写她的生平往事。因此她想赶在这些不真实的传记之前完成她自己的传记,不难看出作家想要通过自传的方式自我发声,形构自我,并在自我形象中重新书写身体乃至主体建构的意图。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除了完成自我形象的全图画像外,也为自我形构及其相关的男女爱情、母女两代关系以及有关精神与身体生活作了令人惊异的诠释与脚注。其中针对男女关系的情欲铭刻内容,显示出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思想:作为女性作家,早在1970年代她已经敢于处理较大胆的男女关系及其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通过自我的情与欲的写作,张爱玲把男女两性的情欲融合为自我与性灵的建构。⑧
朱西宁书信中亦包含许多档案的传记资料,除了胡兰成口述的亲身经历外,也包括当年张胡相恋时互通的情书内容。如《小团圆》中有所点明的,这些当年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书信,可惜张爱玲都已索回;而在她日后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我的信是我全拿了回来,不然早出土了。”⑨这些索回的信,当年张爱玲赴港时没有带走,想是留在她姑姑处。如果这些早年的张爱玲书信保留下来,将成为张爱玲生平传记最重要的档案数据。又或者朱西宁根据胡兰成的资料果真写出一部张爱玲传记,也许亦可从另一个视角为张爱玲早年的事迹增添更丰富的参考数据。然而日后朱西宁似乎没有动手写出有关传记文章,而这些当年张爱玲离开上海赴港时留下的书信似乎也踪迹全无——张爱玲在《小团圆》中显然不想进一步透露她如何处理这些信件的。
从张爱玲书信中有关《小团圆》一书的各种相关资料,不难看到张爱玲创作此部自传体小说的身体与自我形象建构的重要依据,其中有许多令人动容的焦点,甚至有让宋淇夫妇感到所谓的“震动”之处。针对她重写早年的初恋与婚姻经验等自传内容,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中明白道出:
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1976年4月4日信)⑩
从这书信档案中可见,经过前两本英文小说《雷锋塔》和《易经》的写作后⑪,张爱玲对本书的自传体内容可说驾轻就熟,对于其中有关个人自我形象的重新建构以及女性主体的体认与想象,自然也更加深思熟虑。这一点张爱玲本身也十分清楚,因此她给宋淇夫妇的信提到了此中暧昧之情,担心他们会“窘笑”她,但张爱玲表示预备在港台同时连载本书(1975年9月18日信)。可见张爱玲完成《小团圆》后,虽自觉地认识到这方面的争议问题,却仍然有清晰而坚定的自觉意识,主张尽快出版。
事实上,除了张爱玲的初恋故事外,这些书信亦透露出《小团圆》这本书一个最具争议性的主题,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关于张爱玲/盛九莉与胡兰成/邵之雍之间的两性关系刻画及其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内容。在这本自传体小说的写作中,张爱玲更进一步指出她写作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完全站在自身有利的视角去肯定自己而忽视他人,她自言并没有厚此薄彼:
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忙着写长篇小说《小团圆》,从前的稿子完全不能用。现在写了一半。这篇没有碍语……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1975年7月18日信)⑫
张爱玲在此自传体小说中采取相当客观的态度,并没有刻意为自己辩护,这是她尊重事实的可贵表现。同一封信中,张爱玲也指出这篇小说没有碍语等,一再表明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有很高的可信度,没有偏重自身的利益而写。这说明即使有因情节需要而重组虚构的内容,亦可视为是来自她个人情感的投射。这种书写应该像司马迁写《史记》,主要事件/历史内容没有失真或涂改,然而事件与情节的详略、变常、曲畅和措辞等则可能有所增删与重组。
从爱情到情欲,两者往住只是一线之隔,对于一个知名女作家来说,以自传体小说表述自己的情与欲、身体铭刻与个人隐私生活内容,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这事发生于相对保守的、1970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化界。
上海时期的张胡恋情,不但是构成张爱玲个人生平最重要的中心事件之一,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史最受人谈论的争议性恋爱事件:很多读者都好奇张爱玲晚年时将会如何重写自己的初恋经历。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不久即开始了她的作家生涯,作品于第二年即1943年起开始大量发表。在她开始写小说的初期,她自知本身是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年轻写手,书写爱情小说让她感到很“心虚”。她在《小团圆》中,记述她开始以写作赚取稿费的初期,有一个晚上走在回家路上,明月当头,心中想起这一心事而感到一阵阵空虚:
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⑬
这里的心虚,不只是因为没有恋爱经验写爱情小说一事而言,更是直指她内心深处的寂寞与孤芳自赏。此一孤独与寂寞心理,类似于张爱玲在港大遭受日军炮弹轰击时,在死里逃生中突感到没有人可以倾诉的悲哀。因此当一个写了一篇评论她的文章的男人⑭,从编辑文姬(苏青)处拿到她的住址找上家门时,她情不自禁地爱上这一位说着一口湖南腔国语的男人。此后才有了今日《小团圆》中复杂叙事体的传记。
此一爱情故事,正是《小团圆》一书除了张爱玲的成长主题,以及她与家人、亲友等人关系的故事以外,另一个最受人关注的重心。她通过初恋的重写,铭刻了她年轻时期复杂迂回的内心情感生活。自然,最令大家惊异的是,她通过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重新诠释1940年代女性的情欲生活内容——这原本是女作家处于他者的文化角色与位置中的主题。她的这项努力,显然转变了前一世代女作家在情与欲问题上被长久定位于被动、消极、他者的位置,为当代中国文学建构女性情与欲主体的可能空间。
我们不难在1975年9月18日的信中不难发现,其实张爱玲已经预见到宋淇夫妇俩可能对此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的反应,指出他们将对书中的某些描写产生不安:“这篇小说有些地方会使你与Mae替我窘笑。”果真,张爱玲对宋淇夫妇的预测相当准确:
你早已预到(小团圆)有些地方会使我们觉得震动——不过没关系,连我都不像以前那么保守和闭塞。我相信没有别一个读者会像我那样彻底了解你为什么写这本书。(宋邝文美致张爱玲信1976.3.25)⑮
幸好有这些书信档案,才可见在写作初期张爱玲其实已意识到女性身体书写与女性情欲叙事的自传体小说将会引人不安,她不但已有自知之明而且预测宋淇夫妇会因此感到不自在或窘笑。而宋淇夫妇所用的词语是“震动”,可说在张爱玲的预感之内,却又略为强烈些。
《小团圆》一书中,张爱玲从自我形构到初恋情爱的追忆,再转入情欲书写,可说走过了同时代(女)作家所不敢也不愿走的道路,不能不说具有较为超前的、先锋性的女性意识⑯。从这些信件内容来看,《小团圆》当初没有出版的主要原因正是宋淇夫妇所担心的、书中那些令读者“震动”和“窘笑”的情欲与身体内容。因此正可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作家自我形构与情欲问题所涉及的整体时代、文化大环境。此种大胆的女性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所构成的自传体小说,不但令宋淇夫妇感到“震动”,最终也在宋淇夫妇的劝诫下被搁置了下来,开始了漫长的、三十三年“等待”出版的历程。
回顾张爱玲针对《小团圆》的写作历程的自述,不难发现张爱玲对于这本书最初的定位是“爱情故事”,这在她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
《小团圆》情节复杂,很有戏剧性,full of shocks(充满惊奇、震动之意),是个爱情故事。(1976年1月25日信)⑰
而后在3月14日的信中,她也略为提到这本书是另一本“奇长的”英文作品《易经》中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再次强调“加上了爱情故事”。但是,八天以后待她写作完成时,她却把这部小说重新以“热情”的故事加以定义:
这是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1976年4月22日信)⑱
显然她的写作已从充满惊奇震动的爱情故事转向爱情幻灭后的“热情故事”。而从《小团圆》一书所涉及的身体叙事文笔来看,显然“热情”一词并非只是一般的用法,而是含有男女感情热烈乃至涉及情欲的内涵。
从男/女、女作家/男汉奸的“爱情”故事转向“热情”的书写,这或可解读为张爱玲把一篇原本只想写成短篇小说的写作构思发展为长篇小说的同时,已决心在主题和内容上也要有所突破——而这显然特别针对男女情欲的身体书写——这可从后文将提及的新增稿内容看出一二。这在张爱玲身体书写中具有突破意义。在上海时期她不曾大胆书写的男女情欲的身体刻画,显然人到中年时有了新的体悟与想法,并决心跨入争议性较大的男女情欲主题——这可从她在书中多处一再表现情与欲的文字见出。在深具争议性的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中,张爱玲针对爱情毁灭后还能剩下“什么东西”进行生命哲学的反思。
从爱情故事到热情故事的转向中,《小团圆》另一个更重要的争议自然涉及了作者与胡兰成/盛九莉和邵之雍的故事。这种转变或可解释为何张爱玲在写作过程中深感“矛盾得厉害”。这在她的书信档案中有明确的自剖:
《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虽然是我一直要写的,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更得了意,实在不犯着,所以矛盾得厉害,一面补写,别的事上还是心神不属。(张爱玲信 1975年11月6日)⑲
如信中所言:“心神不属”与“矛盾得厉害”等语指的都是她和胡兰成的上海恋情。这显示张爱玲为了忠实刻画她这段恋情的真实面貌而引发了矛盾情绪。这种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在她书写本书过程中显然富有自觉意识。无奈此种女性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在当时的文化社会大环境中不利于作家,特别是对张爱玲这样的知名作家而言。
二 情欲性身体叙事的建构:个人隐私与道德批判
这里有必要先讨论张爱玲的爱情观,再进而探讨其中所涉及的情欲现象。基本上,抛开胡兰成的汉奸因素,张爱玲对于这段初恋是怀抱肯定的态度。在张爱玲五十六岁的晚年重写三十余年前发生的初恋经验,尽管这期间张胡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然而张爱玲却忠于她自身的爱情信念。邵之雍所反映出的胡兰成影子是较为美好的形象——其中虽然也有负面的某些细节描写,但毕竟仍保留很多恋情时期的浪漫华丽。
今日回顾张爱玲年轻时所表达过的爱情信念与观念,有许多可在《小团圆》中找到相互印证之语。2010年夏,由宋以朗主编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中,发表了当年邝文美所记下的三百零一则张爱玲语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数据。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爱情观值得探讨。首先,张爱玲对于恋爱中人美化所爱之人的言论值得留意:
所爱之人每显得比实际有深度,看对方如水面添阳光闪闪,增加了深度——也许别人真有深度。⑳
这种爱情观在《小团圆》中可找到印证,例如张爱玲描写盛九莉和燕山在一起时,无意间会想起她前夫的影像,像手中流逝的水月般突然感到恋人的眼睛有无限的深邃;进而指出,当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总会感觉她所爱的人更神秘、更有深度㉑。这一前一后两者观点相当一致。
综观《小团圆》中张爱玲对于恋爱中人的大部分描写,都符合这神秘而有深度的恋人形象。此种恋人视角,其实也是与张爱玲当年对邝文美所说的另一观念相吻合,即作家“对世界所有事物皆以爱人观点出之”的体现㉒。因此张爱玲以一个恋人的视角出发,将现实中的胡兰成原型铭刻成邵之雍的深情形象,一再表现了此位恋人及其恋情的美好质量。这是张爱玲另一个情爱的信念语录:恋爱使恋人体现崇高的人性质量,一个恋爱中的人最能表现天性中崇高的质量㉓。而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也早已提到类似的观点。
此外,《张爱玲私语录》一书中表示,面对爱情,即使破裂、即使曾经感到很痛苦,可是不觉懊悔:
我一点不懊悔……只要我喜欢一个人,我永远觉得他是好。㉔
这句话不但印证《小团圆》中她对于胡兰成/邵之雍以及张胡/盛邵恋情的美好刻画,同时更进一步从另一个视角印证1950年代初她所说过的爱情永恒的观点:
恋爱上的永不与永远同样的短促吗?但我的永不是永不,我的永远是永远,我的爱是自然死亡,但自然死亡也可以很磨人和漫长。㉕
以上这几点爱情观,经过二十余年后辗转植入她的叙事文体之中。这些有关情爱的信念,一再印证了张爱玲在1970年代创作此篇作品时的思考主题,即思考爱情的万转千回,在完全幻灭以后还有什么东西存在。
据此,张爱玲早年的爱情观对于本书的创作可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印证的功能。张爱玲重新书写她早年的恋情事迹,通过书写让他人分担她的人生与记忆,而让世人记住的同时,更意味着她自身可以因此而忘却㉖。有了以上种种张爱玲关于情爱的信念,不难理解《小团圆》中有关胡兰成及其恋情的美好刻画。此中近于美化的文笔似乎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汉奸形象的理解。
张爱玲写作《小团圆》过程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写作背景。原来书中一段最为争议的情欲身体书写,是张爱玲在《小团圆》完稿后的另外重要修改时的填补。大概没人会料到本书最引发争议、最强的情欲书写内容,竟是在她寄出全书定稿以后另外再补加上去的:
昨天刚寄出《小团圆》,当晚就想起来两处需要添改,没办法,只好又在这里附寄来两页——每页两份——请代抽换原有的这两页。以后万一再有要改的,我直接寄给皇冠,言明来不及就算了。那份正本如果太皱,就请把副本给世界日报,正本给皇冠。这次复印的墨迹够浓。世界日报的一份不知道Stephan会不会直接寄到美国,所以空邮费没数,附上的$70支票千万不要cash,有多下就请先搁在这里。这篇小说时间上跳来跳去,你们看了一定头昏,我预备在单行本自序里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于梨华又来了封信,说看了“私语张〇〇”,知道我们这么些年来的深交,引咎自责,叫我用不着回她的信,以后再有稿子,她一定match别处的稿费。又,我忘了提两次收到明报月刊那两篇短文的稿费。赶紧去寄出这封信。你们俩都好?(张爱玲信1976.3.18)
从这信件中张爱玲仔细交代有关修改文稿事务,可见她对此段爱欲描写的重视。这显示张爱玲的某种矛盾:可能她原先已经写下了,定稿时感觉不适而删去,然后三思之下又重新想列入而寄给宋淇夫妇。或者,也可能是定稿寄出后全新增添的文字内容。无论如何,她补寄这两页新添的情节内容,可以看出她的用心与慎重。
张爱玲信中所附带的这两页小说修订稿,讲述1944这一年间,在张爱玲的生日阳历十月五日这一晚,一个文本中的少女度过了新婚期间性爱的疼痛体验,而对性爱有了新的想象与感受。这里准备引用稍长的相关文字,以说明新增文字的震动性:
他(之雍)微红的微笑的脸俯向她,是苦海里长着的一朵赤金莲花。
“怎么今天不痛了?因为是你的生日?”他说。
他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像鱼摆尾一样在她(九莉)里面荡漾了一下,望着她一笑。
他忽然退出,爬到脚头去。
“嗳,你在做什么?”她恐惧的笑着问。他的头发拂在她大腿上,毛毵毵的不知道什么野兽的头。㉗
此段叙事,是张爱玲最有女性主体情欲意识的书写:她(九莉)是岩洞口倒挂着的蝙蝠,一只兽(之雍) 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泊泊的用舌头卷起来,像是一只动物/兽在小口小口地啜着她的核心。
然而若追踪此中档案的梳理,发现此段全新的叙事文字和原来的旧稿完全不同。现附上有关未更改的原稿版本以供参阅:
他微红的微笑的脸俯向她,是苦海里长着的一朵赤金莲花。
“怎么今天不痛了?因为是你的生日?”他说。
他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像鱼摆尾一样在她里面荡漾了一下,望着她笑了。
快睡着了的时候,虽然有蚊帐,秋后的蚊子咬得很厉害。
“怎么会有蚊子?”他用手蘸了点唾沫搽在她叮的包上,使她想起了比比用手指蘸了唾沫,看土布掉不掉色。
早上醒了,等不及的在枕上翻看埃及童话。他说有个故事里有个没心肝的小女孩像比比。她知道他是说关于轰炸的事。
他是不好说她没有心肝。
可见原稿的文字十分简略,完全没有情欲刻画,也没有动人的文采和令人意外的意象。从“像鱼摆尾一样在她里面荡漾了一下,望着她一笑”句之后,完全省略,直接跳到“快睡着了的时候”。行文苍白无力,完全不能显现男女新婚性爱的激情与缠绵。而从她完稿后新追加补写的文字与行为不难见出,张爱玲对于此中情欲性身体书写的自觉性与主体性。
当宋淇夫妇收到张爱玲的这两页新稿后,邝文美立刻回信给张爱玲道出两人对本书情欲性身体书写的忧心:
今天收到你十八日的信,有两页需要抽换,很容易办。问题是Stephen(即指宋淇) 说另外有许多小地方他觉得应该提出来和你商量一下。(宋邝文美致张爱玲信1976.3.25)㉘
接着又指出他们的担忧:
这本小说将在万众瞩目的情形下隆重登场(我意思登上文坛),我们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处处为你着想,这片诚意你一定明白,不会嫌我们多事。(宋邝文美致张爱玲信1976.3.25)㉙
张爱玲在四月四日回信后,宋淇于同月十五日给张爱玲的信中道出了前封信中邝文美所提到的诸多忧虑,即许多应该提出来和张爱玲商量的问题(小地方);特别强调了胡兰成的影响:担心他 “至少可以把你拖垮”㉚。
张爱玲信中所附上的这两页《小团圆》新修订稿的内容,相信最令宋邝夫妇感到惊讶与震动。因为几天后,即同月二十八日,宋淇夫妇再次迅速回复讨论有关课题。他们规劝张爱玲不要出版此书的主要原因不只是胡兰成的因素,其中亦涉及情欲课题㉛。
事实上,这不只是全书中较引人争议的文字,也是1980年代以前中国(女性)文学重要的铭刻。从这段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看来,即使在当今文学界中也有人深感费解与不安,更何况是1970年代道德与政治禁忌中的保守文化环境,恐怕更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认同与肯定,甚至遭遇严厉的道德批判。而这情况,正是当年宋淇夫妇所担心的问题。
对一个像张爱玲这样的知名女作家而言,以她的地位与声望,她如果不写这种情欲内容,她将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而若写出人性中最隐密幽微的情欲世界,则将面对很大的不确定和名誉危机。因为1970年代的两岸乃至全球华文文坛仍然是十分保守。宋淇即指出,尤其当读者是中国人时,绝不理会小说是虚构这一套学说,而喜欢将小说和真实混为一谈(宋淇,1976年4月28日信)。这正是宋淇所担忧的,因此宋淇认为这种险不值得去冒。用邝文美的话说:她看完《小团圆》后心里的感觉“很复杂”,不难看出夫妇俩的担忧与不安。因此宋邝文美在信中写道:相信没有别一个读者会像她那样彻底了解张爱玲为什么写这本书,并表示夫妇俩虽然没有“那么保守和闭塞”,但显然仍深感担忧。
从这些第一手书信档案资料的追溯,可进一步发现让宋淇夫妇更为担忧的,是小说中所涉及的主角人物:那个有着汉奸之名的无赖人/胡兰成——而被宋淇称为“定时炸弹”。若再加上女作家与大汉奸之间的情欲书写内容,这还得了,他们担心这会触动人们的是非之心,白白让人家看热闹,当笑话看。因此宋淇在4月28日的信中明白指出,对多年没有消息/作品的张爱玲而言,很多人早已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
拿了显微镜在等你的新作面世,以便在鸡蛋里找骨头,恨不得你出了什么大纰漏,可以打得你抬不起头来。(宋淇,1976年4月28日信)㉜
宋淇对于当时文坛可能针对张爱玲的攻击表现出极大的忧虑:
从好的一方面说,你现在是偶像,不得不给读者群好的一方面看;从坏的一方面说,你是个目标,说得不好听点,简直成了众矢之的。……所以要特别珍重。以上就是我们处理你这本新着的primary concern(主要忧虑)。(宋淇,1976年4月28日)㉝
宋淇在信中进一步针对3月25日邝文美所表露过的“震动”感受,以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他们的忧心,提醒张爱玲不要忘记她自身已建立起来的良好声誉与形象。不宜自毁长城,否则将成为受人攻击的道德批判目标。我们可以设想,倘若张爱玲写她初恋的爱情故事中没有涉及较为露骨的情欲内容或风月笔墨,宋淇夫妇可能还不至于如此大力反对此书的出版——因爱情主题仍在道德范围之内。但是,性和情色内容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这无疑正是宋淇夫妇对此书最大的关注点,自然也就是他所说的“主要忧虑”(primary concern)。
关于宋淇此一“主要忧虑”,我们可以对照另一封他劝说张爱玲不要发表《同学少年都不贱》的信中看出来。在这封写于1978年7月19日的信中,宋淇明确告诉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不要发表”,以免被人捉到把柄后大作文章。他举了当年余光中的诗遭人攻击的例子。余光中的诗作曾被人专门挑出一些和色情描写有关的句子串联起来批评。最后结集出版,以《这样的诗人余光中》为题出书,以情欲主题大加侮辱诗人及其诗作。宋淇从这件事来说明这些人将如何“无所不用其极,极尽各种方法打击”知名作家的可怕之处㉞。有关信件档案列于下文供参阅:
《同学少年都不贱》一篇请不要发表。现在台湾心中向往大陆的知识分子很多,虽不敢明目张胆公开表态,但对反共作家的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各种方法打击。你是自由中国第一位反共作家,自然成为对象,好在你有其他出色的作品,为你撑腰的有夏志清等学院派和很多作家,其中最出力的是朱西宁。最近有人把余光中二十年的诗作中,挑选出有色情色彩的句子(其实是out of context〔断章取义〕)串连起来,写出一篇“这样一位诗人”,侮辱余为pornographic(色情)作家。你这篇其实很innocent(天真无邪),可是如果给人以同样手法一写,对你极不利。同时,它又并不比前两篇好多少。发表之后,使你的撑腰人都很为难。最近一本杂志公开说McCarthy、Iowa的作家训练班的学生如余光中、白先勇、王文兴等都是特务。所以你千万不必提起McCarthy和赤地那段往事。
从中可见除了胡兰成的因素以外,《小团圆》延宕出版的原因可能相当复杂,既有显性的因素,亦有隐性的隐忧。前者以胡兰成所将引发的各种问题为主要考虑,而后者则与自传体中所涉及的一些较不能为当时社会、文化所接受的情欲内容有关。
宋淇夫妇的判断显然是正确的,宋淇身在影艺界,自然深知有关性课题与情欲事件对于一个女作家的伤害有多可怕。因此,《小团圆》一书当初受宋淇夫妇忠告未能出版的真正原因应该就是书中所涉及的这些情欲内容和作家情感生活的隐私问题,然后才有1990年代初张爱玲一度提出想要毁掉此书的念头——因果不宜本末倒置。
依据上述众多第一手的书信档案可知,1970年代中期既已定稿成书的《小团圆》构成她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女性叙事,亦是作家在自我形构历程中一段最为刻骨铭心的自传性身体叙事。
通过此一女性叙事与内容刻画了人性与心灵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构成盛九莉、包括邵之雍等男女的圆满形象,深具七情六欲,也更有血有肉反映真实人性,同时体现锐利的女性主义意识与现代主义思想。这种大胆无碍的女性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构成了这本自传体小说的中心价值之一。实际上,这本自传体小说中和自我与主体相关的课题有更复杂的多元性质,其情欲主题的女性叙事和张爱玲的自我与主体建构仍有待更进一步加以全面探讨。
更深一层言,此自传作品与自我内在的情欲脉络含有拉康镜像理论的内在关系;张爱玲以此心理机制在自传体的创作上对自我及主体进行了深层精神分析对话,深入挖掘她内心深处的女性他者欲望。从拉康凝视理论中,自传体书写中的张爱玲或可被视为一个对着镜子的婴儿/作家被看成的一种“能指”,一种作家所渴望的主体;而婴儿/作家镜中的镜像正是“所指”,镜中的镜像正是作家自身的意义所在㉟。质言之,张爱玲通过生平与历史记忆的重写,张爱玲/女主角盛九莉的自我与主体被不同层次的剪裁、悬搁、分割、重组、扩张,并在模拟、直写、伏笔、暗示等多重可能的组合叙述中形构出作者、叙事者和被叙事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小团圆》到中英版《雷锋塔》和《易经》二书的出版,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完成,标志她自传体圣杯式的文本建构㊱。
本文试图在上述的研究基础及第一手书信档案的探讨中,更深广地从张爱玲写作的真实背景及其心理现实中展开不同层面的透视图,补充现今有关《小团圆》的研究。因此,这些留存下来的作家书信档案资料,成为研究《小团圆》乃至自传三部曲的最重要的作家观点依据。《小团圆》全书除了充满爆炸性的隐私内容,以及以上所讨论的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课题外,其实亦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要点,例如关于张爱玲和母亲以及她和上海时期各主要人物的关系等,张爱玲所写出的内容不少充满冲击性。其中有关盛九莉堕胎一事的描写同样令人震动:“抽水马桶里十寸大小的男胎,血水的肌肉、鲜血构成的胎孩轮廓”,等等。恐怕这也是一般人所不愿揭露的隐私生活实情,而可能有害于作家原有的自我形象㊲。这些种种要点应该都包含在宋淇夫妇的顾虑之中。而这些背景,也应是当年宋淇夫妇为张爱玲把关免她出书后受人非议的理据。
我们不能说当年的宋淇夫妇是思想保守的人,他们完全顾虑到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在人性复杂面的理解上,在文学创作中有关男女情爱和性爱方面,张爱玲可能要比宋淇夫妇来得潇洒超俗,特别在爱情的浪漫认知上,张爱玲似乎较他们夫妇俩更加透彻与超越——正因为有这种差异造成某种文学观与价值观的落差,因而才有《小团圆》三十三年“等待”的命运。
张爱玲说过她不写所谓“时代的纪念碑”的作品,而《小团圆》无疑则是张爱玲式的“感情纪念碑”作品。一幕幕历史往事在她的女性叙事中再次以文学的形式演绎,许多事件和人物都有迹可循,无处不在。在此独特的女性叙事中,这些传记语境都和作家的生命与情感系统紧密相系,缺一不可。
注释:
①③徐拥军:《档案记忆观:社会学与档案学的双向审视》,《求索》2017年第4期。
②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106页。
④现今主要有四种已出版的张爱玲书信资料文集:2007年苏伟贞《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2008年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2013年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以及2010年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等。
⑤详见宋以朗在《小团圆》的前言,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3~17页。
⑥自《小团圆》出版以来,探讨的论文颇多,本人于2009年发表了《小团圆》最早的长篇研究成果,详参拙文《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年第4期。其后本人亦发表了两篇相关的研究报告。近十年前,本人提及《小团圆》一书的书写源头契机之一,即是张爱玲对自身传记的发言权之自保。这些年来,经过本人对《小团圆》的各视角和方向的探讨,本文将在有关基础上进一步从作者写作的动机和当年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进一步重读《小团圆》一书所可能隐藏的次文本及其有关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意义。
⑦⑨⑩⑫⑬⑮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㉘㉙㉚㉜㉝张爱玲:《小团圆》,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5、10、8、4、162、7、6、10、5~6、66、313、66、120、120、121、121、7、7、9、10、10页。
⑧其中一些相关的论点,可详参本人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小团圆〉的“圣杯”意象与符号意义》(《南开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小团圆〉的隐私文本:自我意识与自传体书写心理》(《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5期),《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⑪张爱玲这两本以英文写作的自传体小说《雷锋塔》和《易经》,约成书于1963年。
⑭当时胡兰成的稿还没发表,是苏青寄了给张爱玲看而知道了这一个人。
⑯详参拙文《宋以朗与张爱玲私人书稿特藏馆》,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2009年4月,第146~160页。
㉗“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泊泊的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的啜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难忍的愿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详见张爱玲《小团圆》,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240页。
㉛此新改的内容,幸好宋淇夫妇按张爱玲的要求替换在书稿中。如果当年宋淇夫妇为了替张爱玲“着想”,将此新修订稿遗失了,没有取代原来的旧稿,那么我们今日就难以全面认识70年代女性文学中这一段男女情欲的女性身体叙事。
㉞此外,宋淇还提醒张爱玲当年的政治环境很乱,要她当心不要常提起和她交情要好的迪克,即麦卡锡(Dick McCarthy)。麦卡锡是张爱玲在香港工作时的美国新闻处处长,后在台北接待张爱玲访台之人,因为已有人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他和一些爱荷华文艺工作营的作家,除了余光中外,还包括白先勇和王文兴等人也都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成员。
㉟本人曾撰文对此指出,通过拉康镜像理论的剖析可发现张爱玲通过他者的凝视与重写中发现自我与主体,作家也在自传里渴望看到自己内在的自我,即是镜像中的自我影像;其实在自传叙述中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自我或主体身份,但却能为我们从另一个视角解说张爱玲书写《小团圆》的某些深层精神分析内容。因此这部自传体作家演绎的是永远难以穷尽的生命形态。详见拙文《〈小团圆〉的隐私文本:自我意识与自传体书写心理》,《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4期。
㊱有关张爱玲自传体写作的新叙事模式的研究,除了当年《小团圆》出版时本人最早的一篇研究探讨过以外(详见《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2009年7月,也曾在其他两篇论文中从不同的视角讨论过有关课题。在叙事模式上,本人曾从“同体叙述”(homodiegetic)及“自体叙述”(autodiegetic)的交叉使用发挥,张爱玲处于本身的叙述之中到本身不在场的叙述之内,以主角身份呈现于同体叙事建构自我与主体,各有不同意义的体现。详见《〈小团圆〉的“圣杯”意象与符号意义》,《南开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㊲有关本书中相关课题的讨探,详见拙文《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