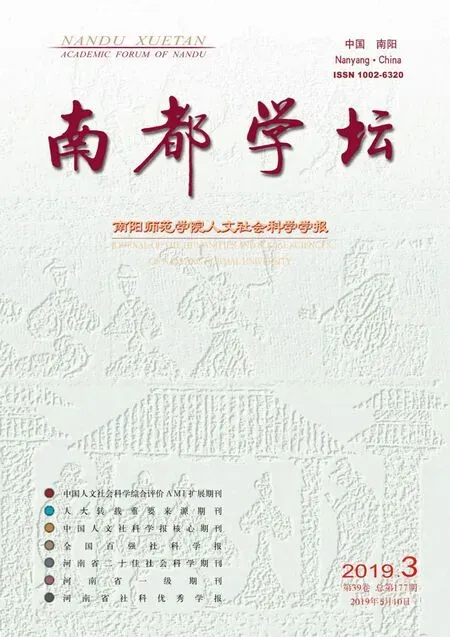杜甫歌行体诗的艺术境界
2019-05-22吴淑玲韩成武
吴淑玲, 韩成武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本文以“七言长歌,不用乐题,直自作七言,亦谓之歌行”[1]所点示之因素为歌行标识,遵从《文苑英华》和宋敏求、严羽、姜夔、冯班等人的歌行概念审视杜诗,大体对杜甫的歌行体诗有如下认知:杜甫的歌行体诗不是他的诗歌体式里写得最好的一类,但在唐代诗人里,他的歌行也是仅次于李白而已,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且有《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白丝行》《饮中八仙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传唱佳品。杜甫的歌行体诗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境界:一是“以气概盛”的情感力量;二是开合自由的结体方式;三是全面周到的关注视角;四是潇洒俊逸的审美特质。其歌行长篇,亦诗亦史,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歌行体诗歌的艺术高度。
一、“以气概盛”的情感力量
李之仪在《姑溪居士文集》卷十六《谢人寄诗并问诗中格目小纸》一文中谈及歌行体诗时说:“方其意有所可,浩然发之于句之长短、声之高下,则为歌;欲有所达而意未能见,必遵而引之以致其所欲达,则为行。”[2]321李之仪是北宋时期的诗人,他对歌行的解释给我们很多启示。笔者认为,从李之仪的论诗格话语里,歌行应该有浩然之气,有其他诗体表意所达不到的力量,这就是歌行体诗歌“以气概盛”的情感力量。歌行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与它不受声律和语体影响有关,惠洪《天厨禁脔》曰:
律诗拘于声律,古诗拘于句语,以是词不能达。夫谓之行者,达其词而已,如古文而有韵者耳。自唐陈子昂一变江左之体,而歌行暴于世,作者皆能守其法,不失为文之旨,唯杜子美、李长吉,今专指二人之词以为证。夫谓之歌者,哀而不怨之词,有丰功盛德则歌之,诡异稀奇之事则歌之,其词与古诗无以异,但无铺叙之语,奔腾之气。其遣语也,舒徐而不迫,峻持而愈工,吟讽之而味有余,追绎之而情不尽。叙端发词,许为雄夸跌荡之语;及其终也,许置讽刺伤悼之意,此大凡如此尔。[2]321
联系惠洪之语,比对杜甫歌行体诗,大体相合。杜甫的歌行体诗歌,其内容多是“丰功盛德则歌之,诡异稀奇之事则歌之”,虽然在写法上不追求铺叙排比,但也是尽情描写,有较多“雄夸跌荡之语”,因而在诗中容易形成“以气概盛”的情感力量。比如《瘦马行》,先是交代瘦马被三军遗弃的情况,再写“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的可怜情状,回过头来交代瘦马以往为国家征战的经历以及因病被弃的原因,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吞吐其间。我们先不论此诗是否诗人为房琯所作,也不论其是否诗人为自己哀伤,仅以瘦马本身而论,此诗亦如刘辰翁所言:“辗转沉著,忠厚恻怛,感动千古。”[3]吴瞻泰亦云:“‘雁为伴’,无知己也;‘乌啄疮’,伤凌辱也。英雄失路,楚楚可怜。”[4]109又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
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
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
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
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将军画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
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
此诗为一代鞍马画家曹霸晚年的清贫境遇鸣不平,激昂愤慨之气跃动于字里行间。使用对比手法,将曹霸在开元年间的荣宠与安史之乱后的漂泊生涯构成强烈反差。诗以大量篇幅歌颂曹霸的艺术造诣:首先言其祖上文采风流之泽被,接着叙述其潜心于画艺,及开元年间完成两件惊世作品,用“一洗万古凡马空”概括其巅峰造诣。这就为慨叹其晚年的遭遇备下了充分的缘由,增强了批判社会世俗的力度。结尾处由曹霸身世推及古来盛名才士皆遭坎坷,更使批判的波澜汪洋浑厚。刘辰翁曰“起语激昂慷慨,少有及此”,“首尾悲壮动荡”[5]3205,翁方纲称“如此气势充盛之大篇,古今七言诗第一压卷之作”[6],可见此篇的情感力量。再如《狂歌行,赠四兄》:
与兄行年校一岁,贤者是兄愚者弟。
兄将富贵等浮云,弟切功名好权势。
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
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
吾兄睡稳方舒膝,不袜不巾蹋晓日。
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须缯腹中实。
今年思我来嘉州,嘉州酒重花绕楼。
楼头吃酒楼下卧,长歌短咏还相酬。
四时八节还拘礼,女拜弟妻男拜弟。
幅巾鞶带不挂身,头脂足垢何曾洗。
吾兄吾兄巢许伦,一生喜怒长任真。
日斜枕肘寝已熟,啾啾唧唧为何人。
此诗写诗人和四兄沦落嘉州的不幸命运,放言长歌,感慨淋漓,先谈自己和四兄对功名富贵的态度,再谈京城遭遇,又谈嘉州沦落,既展现了自己潇洒不羁的困顿,又抒发了内心的牢骚和不满。全诗内容拉拉杂杂,读起来莽莽苍苍,情绪连绵不断,真率之情充溢全篇。王嗣奭曰:“此诗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其状四兄,真有王民皞皞、不识不知景象,奔走风尘者对之汗颜。虽脂垢不洗,自然清静。”[7]邵长蘅曰:“真率,别是一格。”[8]薛天纬曰:“此篇略无拘束的散漫叙事,正体现了歌行自由抒写的艺术特性。”[9]又如《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
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
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
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
内府殷红玛瑙盘,婕妤传诏才人索。
盘赐将军拜舞归,轻纨细绮相追飞。
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
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
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
此皆骑战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
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
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
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
借问苦心爱者谁,后有韦讽前支遁。
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
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
自从献宝朝河宗,无复射蛟江水中。
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
此诗正面描写曹霸鞍马画艺之高超。起笔便从大处落墨,站在绘画史的高度评价曹霸,说唐朝开国以来,江都王李绪之后,最有名的鞍马画家就是曹霸。他曾为太宗的骏马“照夜白”画像,导致龙池雷震十日。他所画《九马图》,骏马雄健的跃势使人觉得洁白的画绢上卷起漠漠的风沙,有如远处寒空飘动的烟雪,它们个个顾视清高、神气沉雄!此诗绘形生动,笔墨雄健,行文大气包举,气势磅礴,将曹霸的鞍马绘画艺术推向极致。
杜甫的歌行大都有这样壮盛的气势。再举一例。对于《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原文见下一部分)开头的九句和全文内容风格的关系,王嗣奭评议道:“此篇起来八句(实际九句),如雷轰电闪,风雨骤至,长短错杂,似无条理,而所着意在‘骨鲠绝代无’‘足以宁君躯’,而衬语形容其清冷。”[10]杜甫的歌行体诗,皆为个人抒情之作,无论所写为他为己,都具有很强的个体性特点,具有“浩然发之于句之长短、声之高下”的特征,或拉拉杂杂,或感慨万千,或任意挥洒,充分将叙事、议论、抒情的功能融汇到一起,达到尽情抒写的艺术境地。
二、开合自由的结体方式
“结体”一词,出现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周振甫注曰:“结体:组织结构。散文:敷文,运用文辞。”[11]我们这里使用“结体”一词,指的是诗歌的组织结构,各种诗体都有自己的结构方式。
歌行体诗歌的结体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以自由流畅、变化无拘为特点的,宋人谓之“体如行书”,可能就是指其这一特点,而钟秀对歌行体诗特点的概括也是“大约皆浑浩条畅,牢笼万象”。唐代的歌行,初唐的律化歌行在结体方式上比较讲究,盛唐以后就向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李白、杜甫的歌行,钟秀谓之:“纵横变化,较之汉魏,虽去古稍远,然究不失汉魏遗意。”[2]324
杜甫作为唐代歌行体诗的大家,在歌行体诗的结体方式上与李白各有特点:李白在天上,天马行空,恣肆纵横,任意往还,云里雾里,神而又奇;杜甫在人间,自由抒写,开合任情,牢笼诸象,开合跌荡,潇洒自然。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度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此诗可分为四个意段,仇兆鳌分析此诗的结体:起首五句“记风狂而屋破也”,接着的五句“叹恶少陵(凌)侮之状”,接着的八句“伤夜雨侵迫之苦,在第三句换韵”,最后五句“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此亦两韵转换”[12]831-832。汉语诗歌以偶数句为一个意段和押韵单元,这首歌行却打破了这个常规,五句—五句—八句—五句,而且出现了在意段内换韵的现象。作者以表意为主,不再追求句数的骈偶,不再束缚于换韵的常规,我们可以感受到诗歌结体的自由和诗人洒脱的心态。又如《天育骠骑歌》:
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今之画图无乃是。
是何意态雄且杰,骏尾萧梢朔风起。
毛为绿缥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
矫矫龙性合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
伊昔太仆张景顺,监牧攻驹阅清峻。
遂令大奴守天育,别养骥子怜神俊。
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材尽下。
故独写真传世人,见之座右久更新。
年多物化空形影,呜呼健步无由骋。
如今岂无騕褭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
天育是马厩名称,是国家养马的地方。当年,太仆卿张景顺派遣得力人手驯养出几匹骏马,请画家把它们画出来以传世人。杜甫看到了这幅画,写了这首诗。诗的开端以惊叹的口吻称赞骏马为天子的千里马,属于大笔开端,有如雷贯耳之势。然后穷极笔力铺写它们伟岸的身姿和雄杰的意态,甚至连马尾卷起朔风的感觉都产生了。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诗的结尾就停留在赞美骏马上面,那就难免跌入俗套。作者没有这样做,而是由张景顺以画马见之座右的做法引发议论:难道今天就再也没有神奇骏马了吗?不!只是没有王良伯乐那样的御马人、相马师,所以神骏埋没于草野,毫无意义地结束了生命。这种结尾大大超越了题目本身,犹如一缕新奇的钟声发人深省:马是如此,人亦如此啊!此诗开得恢宏,结得奇异,开合随意,结体自由。再如,《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更是结体自由的代表:
窦侍御,骥之子,凤之雏。
年未三十忠义俱,骨鲠绝代无。
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寒露之玉壶。
蔗浆归厨金碗冻,洗涤烦热足以宁君躯。
政用疏通合典则,戚联豪贵耽文儒。
兵革未息人未苏,天子亦念西南隅。
吐蕃凭陵气颇粗,窦氏检察应时须。
运粮绳桥壮士喜,斩木火井穷猿呼。
八州刺史思一战,三城守边却可图。
此行入奏计未小,密奉圣旨恩宜殊。
绣衣春当霄汉立,彩服日向庭闱趋。
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还成都。
江花未落还成都,肯访浣花老翁无。
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
仅从诗歌的形态上看就非常自由,前九句,三个三言句,接一个七言句一个五言句,又接两个九言句,再接一个七言句加一个九言句,极其散漫,而接下来的二十句,则一顺的七言句,也就是说,在语言节奏的使用上,诗人完全任性而为,想自由时自由,想整齐时整齐,完全是李白式的语言使用方式,以至于申涵光说:“是集中变体。长短纵横,太白所长,正尔不必效之,失其故步。”[13]2467但陈訏却认为此诗“若求之字句长短,诚以变体,试细寻其脉络针线,起伏照应,仍是公诗本色,未见失其故步也”[13]2468。
语言错落者开合自由,语言整齐者依然开合自由、自成条理。如《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是一首整齐的七言歌行,从其韵律的安排看,前二十句都用一个韵部,上声十九皓,后面却是一组押十灰韵的七言诗句,这七句里,最后三句为一组,结尾两句连用押韵句。双数、单数,押韵句数的多和少,完全不顾忌,这即是自由结体的特点。仇兆鳌《杜诗详注》:“杜诗格局整严,脉络流贯,不特律体为然,即歌行布置,各有条理。如此篇首提端复,是主,再提薛华,是宾,又拈少年诸生,则兼及一时座客。其云悲笑忧乐,腰尾又互相照应,熟此可悟作法矣。”[12]295此诗“格局整严”说不上,但确实“脉络流贯”,题目即云“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则诗中自然不能不提及诗题中的几位,故诗人完全是顺势而为,谈不上讲究,却各有条理,有其顾及诗题的存在价值。
又如《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以四句一换韵的方式出现,使用“一先”“五未”(“四置”通押)“九泰”“十三职”四个韵部,平仄互相转换,每次换韵均首句入韵。而在内容的安排上,则是前四句写楠树倚江为卜居之由,接四句写楠树被风雨连根拔起,但却不接写楠树被拔之后的境况,而突然插回去叙述楠树在时树映江波佳景堪玩的可爱,之后再突转回来写楠树被拔之后的旅况凄凉,这是通过叙述方式呈现的结体自由。再如上文所提到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也是一首整齐的七言,且每八句一转韵。仇兆鳌将全诗分为五个段落,开首八句“叙曹霸家世及书画能事”,“开元”八句“记其善于写真”,“先帝”八句“记其画马神骏”,“玉花”八句“申言画马贵重,名手无能及者”,最后八句“又言随地写真,慨将军之不遇”[12]1146-1151。从文字多寡而言,似乎比较拘束,但从内容上分析,则显得开合自由,开首即把笔触拉向遥远的三国时代,交代曹霸的身世,显其贵重,还把他的学书学画与卫夫人、王右军相连,见其艺术功底之非同凡响,是为其不当被冷落张目,这就拉得很开。接着拉拉杂杂的,全是曹霸的绘画本领,中间还拉出了曹霸弟子画马水平不及曹霸都被重用,而在最后交代曹霸在干戈扰攘的时代漂泊僻壤、形同常人的悲剧结局,也是高开低走、大起大落的文势。
三、全面周到的关注视角
这里所说的关注视角,是指对一个人、一件事从不同角度去审视。
杜甫的歌行体诗歌,或长或短,任性而为。短歌,因其短,故一般只有一个视角,无所谓周到与否。我们所指主要是杜甫十句以上的长篇歌行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审视。杜甫的歌行体诗写作的方向与乐府体诗歌大不相同。他的乐府诗是关注社会现实的,是深刻的史诗性的存在,关注层面较多是必然的。而他的歌行体诗,大体是风物描写、题画、宴饮赠答和个人生活,总体倾向于私人方向,不容易拓展写作视角,但杜甫的歌行体诗仍然具有全面周到的关注视角,对于所描写的人或事,总是尽可能从更多的角度去关注。如《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沈沈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这是一首流传千古同时也让郑虔永留形象的歌行体诗。全诗以描写广文馆主人郑虔的落拓人生为主旨,替郑虔的遭遇鸣不平。诗中的郑虔,被时人称为诗书画三绝,唐玄宗专门为郑虔设置广文馆,说是令天下人都知道广文馆专为郑虔而设,给予其极高的荣耀,但也只是个名头而已,并没有实权,也没有给予丰厚的俸禄,所以郑虔仍然属于人生失意的落拓之人。诗歌关注了广文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官衙,描写了号称广文先生的郑虔饭都吃不饱的生活情况,写了郑虔超过屈原、宋玉的杰出才华,写到了诗人自己和郑虔忘形尔汝地饮酒,又描写了两人高歌时诗思泉涌似有鬼神相助而结果却不知会不会填沟壑而死的担忧,最后以劝郑虔早赋归去来和落拓衔杯作结。诗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关注了郑虔所受的与名声极不相符的待遇,抒发了对才子不遇的满腔郁愤和不平。再如《石犀行》: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
终藉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
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参人谋。
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
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
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
这首诗记述议论治水事。石犀牛,是秦人立下的镇水之宝。诗人不信厌胜之法,而以自然为宗,却也交代了蜀人矜夸的江水千年不溢的情况。接着描写了今年灌口给百姓带来的伤害,一句“此事或恐为神羞”交代了灌口损伤人口的惨状;又写众人用木石阻挡洪水以证石犀牛厌胜无效;又议论先王之法,直接点出石犀牛“不经济”;最后的结语还是希望壮士“平水土”。无论是否定厌胜之法,还是写灌口之灾,还是论先王之道,都意在表达杜甫在治水问题上对人力的肯定。吴瞻泰曰:“抑扬反覆,一唱三叹,悠然有余,而不见议论之迹,驳邪归正,可以羽翼六经。”[4]121-122
又如《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见前引文)写著名画家曹霸所画之《九马图》。诗人从曹霸画马得名写起,林林总总地例数了30年来曹霸给皇上、内府、婕妤、才人、将军、贵戚、权门等所画之各类名马图,铺垫之全面,罕有所见。然后才转到在韦讽录事宅所见的这一幅图画。描写这幅《九马图》,也是按照画面层次,有主有次,先两马,再七马,分别写其气质神态。然后以“忆昔”展开联想,遂露今昔之感。此诗的写法,尤其开篇之法,用牢笼万物之手段,吴农祥“竭力写鞍马乎”的问话,意在牵出他所认为的此诗的主题“写英雄将相耳”,若抛开后一句仅留前一句,“竭力”二字正是点出了此诗的周到之处,恐怕这也就是张溍所说的“风格之老,神韵之豪,针线之密”[5]3212了。
再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名为公孙大娘弟子而作,实为公孙大娘而作,诗写公孙大娘之剑舞,连写八句,分别从影响力、观者反应、雄矫舞姿、起收动作、唇妆衣饰、成名弟子等角度写公孙大娘剑舞的魅力,交代可谓详尽,而这一切均为后文抒发感慨作铺垫。吴瞻泰曰:“叙事以详略为参差,亦以详略为宾主,主宜详而宾宜略,一定之法也。然又有宾详而主反略者,如此诗公孙大娘,宾也;弟子,主也。乃叙公孙舞则八句,而天地日龙,雷霆江海,凡舞之高低起止,无所不具,是何其详!叙弟子则四句,而言舞则‘神扬扬’三字,抑何其略!究之诗意,非为弟子也,为公孙大娘也。则公孙大娘固为主,而弟子又为宾,仍是主详宾略云耳。”[4]138这就指出了此诗以公孙大娘为主角且多角度写其舞姿的写作手法的价值。我们再进一步说,这样写公孙大娘的当年盛况,正是突显开元年间歌舞盛世的升平景象,则其弟子的流落山川草野,正可引发诗人今昔对比、今不如昔的时代悲慨。
从所举相对较长的这些诗例可以看出,杜甫在歌行体诗的写作上,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赋的写法,将笔墨向相对更全面、更周到的方向关注,使得他的大部分歌行体诗作都拥有关注周到、牢笼众象的气度。
四、潇洒俊逸的审美特质
胡应麟、胡震亨等人是大歌行观的主张者,故他们所言及的古诗包含歌行体诗。在谈及古诗时,胡震亨认为古诗的审美有如下特点:“七言古诗要铺叙,要有开合,有风度。迢递险怪,雄峻铿锵,忌庸俗软腐。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记极。备此法者,唯李、杜也。开合灿然,音韵铿然,法度森然,神思悠然,学问充然。”[14]这里含有对杜甫歌行体诗歌的认识。笔者认为杜甫的歌行体出入变化,开合灿然,“迢递险怪,雄峻铿锵”,其审美特质可概括为潇洒俊逸四字。
杜甫是一个典型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者,他的情感表达方式很少有李白式的狂呼呐喊,而往往相对柔和。歌行体诗歌的结体自由、抒情任性,本身就决定了歌行体诗歌具有潇洒自由的美质,而歌行体诗歌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展示的描述或抒情方式,就容易形成雍容俊逸的审美特质,尤其是长篇歌行体,更是如此。尽管杜甫的歌行体诗作也有急管繁弦的抒情作品(如《贫交行》《逼仄行,赠毕曜》),也有悲切淋漓的作品(如《同谷七歌》),但歌行体作为唐世之新歌,其文体表征主要以七言为标记,而七言在表意上繁复转折、易多修饰,再加上杜甫不甚外露的个性特征,也就形成了目前杜甫歌行体诗歌潇洒俊逸的审美特质。如《醉歌行》:
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
总角草书又神速,世上儿子徒纷纷。
骅骝作驹已汗血,鸷鸟举翮连青云。
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
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
旧穿杨叶真自知,暂蹶霜蹄未为失。
偶然擢秀非难取,会是排风有毛质。
汝身已见唾成珠,汝伯何由发如漆。
春光澹沱秦东亭,渚蒲牙白水荇青。
风吹客衣日杲杲,树搅离思花冥冥。
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
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泪零。
这首诗是诗人送别从侄杜勤落第时所作。诗人以陆机为比喻起笔,连写八句赞从侄本领,可谓赞语不惜美词。接着八句用心抚慰从侄落第受伤的心。最后八句写别亭周边风景,衬托离别之情。“凡三转韵,层次分明。首赞其才,中慰其意,后惜其别。以半老人送少年,以落魄人送下第,情绪自尔缠绵。”[15]其自由俊逸的风神还体现在“写送别光景,使前半叙述处皆灵,忽句句用韵,忽夹句用韵,亦以音节动人”[16]。又如《观打鱼歌》:
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鱍鱍色胜银。
渔人漾舟沈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
众鱼常才尽却弃,赤鲤腾出如有神。
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飒飒吹沙尘。
饔子左右挥双刀,脍飞金盘白雪高。
徐州秃尾不足忆,汉阴槎头远遁逃。
鲂鱼肥美知第一,既饱欢娱亦萧瑟。
君不见朝来割素鬐,咫尺波涛永相失。
这首诗规谏暴殄天物者,并没有太多的讽喻之意。诗写鱼之色、鱼之怒、鱼之脍,“将鱼之生死、强弱、力量、精神一一写出,令读者之意中又惊又喜,又惨淡又畏惧”[17]。下笔时均依据诗人观察和思考想象的次第,并不刻意调动曲折回环转换等手段,一任情之所至,议论亦随性而发,用黄生在《又观打鱼歌》中的评论概括即“体物既精,命意复远”[18],是一种俊逸风神。再如《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江心蟠石生桃竹,苍波喷浸尺度足。
斩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
梓潼使君开一束,满堂宾客皆叹息。
怜我老病赠两茎,出入爪甲铿有声。
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
路幽必为鬼神夺,拔剑或与蛟龙争。
重为告曰: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
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

这首诗所写,不过是梓州留后章彝赠给诗人的桃竹杖而已,但诗人却动用如许笔墨描绘其形象,使其颜色鲜明、形状诡奇、作用非凡。其语言节奏的恣肆变化、语气中的不吝赞美,给全诗带来了潇洒不羁的神韵。钟惺在《唐诗归》中称其“调奇、法奇、语奇,而无泼撒之病,由其气,故奥也”[19]。吴瞻泰《杜诗提要》曰:“一杖耳,忽而磐石苍波,忽而江妃水仙,忽而宾客叹息,忽而鬼神欲夺、蛟龙欲争,忽而踊跃化龙,忽而风尘柴虎,写得神奇变化,不可端倪。”[4]125
杜甫歌行的这种特质,几乎得到历来评论家的一致认可,人们评价杜甫的歌行体诗,所用语言,往往能概括出洒脱俊逸之意,如梁运昌评《魏将军歌》曰:“此诗直起直落,不装头尾,谷苍而格老,其雄奇卓荦处,太白何以过之……前缓后急,叠句叠韵,与《醉时歌》相反而正相似,铜丸挝鼓,音节豪壮而紧捷,那不动人!”[20]王得臣在评《义鹘行》时评杜甫诗:“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含今,无有端涯。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21]乔亿评《李潮八分小篆歌》曰:“洞悉八法源流,信手落笔,不事张皇,而清古之气左萦右拂,空行不窒,亦歌行之上格也。”[22]李因笃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曰:“绝妙好辞!虚以错落妙,诗以整妙。错落中有悠扬之致,整中有跌宕之风。”[23]
杜甫歌行的这种洒脱俊逸的特质使得他的歌行体诗虽没有乐府诗那么深刻的诗史价值、没有律诗那么广泛的内容和精美的形式、没有古体诗那么的沉郁顿挫,却也有一种独特的洒脱俊逸的风神,使杜甫成为与李白并称的唐代歌行体诗歌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