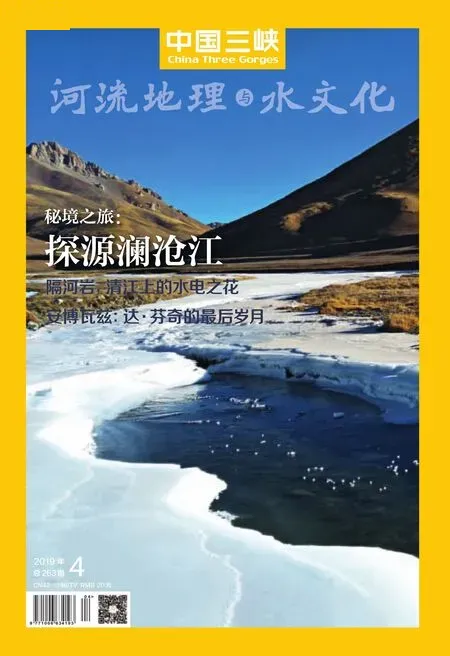士心即侠义
2019-05-13杜鹏
文|杜鹏

武侠片的末日 汪洋 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版
《武侠片的末日》是上海大学副教授、纪录片导演、话剧导演兼影评人汪洋的第二本书,这是一本他的专栏作品集。他的第一本书作于三十年前。当时的汪洋只有十岁。
三十年前的汪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为男子争气——十岁汪洋的诗》,并在北京受到了文学大师冰心的接见,并为其题写书名。他作为洛阳市的少年代表,经常代表洛阳市到处做报告,是整个河南省有名的“神童”。但是,过早成名使得当时的汪洋痛苦不堪。在《武侠片的末日》的后记中,汪洋写道:“作为一个成绩其实一直还不错的人,我就喜欢和所谓的差生们交往,从这些江湖朋友们那里反而可以得到一种被称为‘平等’的‘自由’。然后,所有慕名而来的‘崇拜者’都是我厌倦和鄙视的。”对“江湖”的向往,对侠义、隐逸的追求,以及对“小人物”的关怀,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在汪洋的心中产生影响,以致汪洋后来的专栏文字,都有着铮铮铁骨以及对世俗生活的不屑一顾。
由于这是本杂文集,而非论文集,所以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和广义上的“武侠”关系不大。但是单论汪洋的语言,却是辛辣无比,刀刀见血,颇像一个以文字当武器的武林高手。虽然汪洋的语言功力,完全可以化“辛辣”为“尖酸”,从而博得不少眼球,混成一个所谓的“公知”。但是汪洋在保持尖锐的同时,依然没忘了那些最基本的人文关怀。作家许石林曾用“闪烁着士心的温柔”形容过汪洋的文字,这是一个极为精准的评价。能做到“批判性”与“人文关怀”兼备的评论家已是少之又少,而汪洋就是其中的一员。
汪洋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是一个极佳的提问者,而非挖苦者。 汪洋的提问往往涉及人文关怀,而非技术层面的吹毛求疵。以《 我的诗篇 ,谁的诗篇?》这篇文章为例。《我的诗篇》作为一部制作精美的纪录片自上映来就赚足了观众,尤其是文艺青年的眼泪。然而作为一名旁观者的汪洋却对这部影片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在影片的表现形式上,汪洋用“缺乏烟火气,更多香水味儿”来形容这部努力在“表演诗”而非“纪录诗”的“诗电影”。过于精致的画面,以及过于刻意的摆拍在汪洋看来,这些都违背了“纪录片”的初衷。关于纪录片,汪洋有自己的原则,就是“没有回到真实的生活现场,也就没有真实的心灵现场”。而生活现场本身的粗砺感恰好是纪录片最能震撼人心的地方。
除了对于影片表现形式的批评,汪洋更是在文章的最后质疑这部影片的拍摄初衷,就是由于导演自身的立场和价值的不坚定。在汪洋看来,《我的诗篇》是一部为了感人而故意营造感动的、带有极强消费主义色彩的“伪纪录片”。而汪洋的这种批判,并非出自个人审美的偏好,而是源于其对于边缘人士的关怀以及对于“消费主义”的不满。
汪洋相信有一个武侠江湖的存在,而且相信这个江湖并未随着高度现代化的时代而消失,在《被放逐的江湖》一文中,汪洋也提到了这一观点。《武侠片的末日》一书作为一部文化评论集,里面的每篇文章都透着汪洋的人文关怀。并不会武功的汪洋,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于“侠义”的追求。
LINKS

逝去的武林李仲轩 口述 徐皓峰 记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版
口述者李仲轩曾是三位形意拳大师唐维碌、尚云祥和薛颠门下弟子,后隐于市井几十年,曾在西单商场当过多年门卫。晚年机缘巧合地将武学大师们的言行娓娓道来,勾勒出一幅原汁原味的江湖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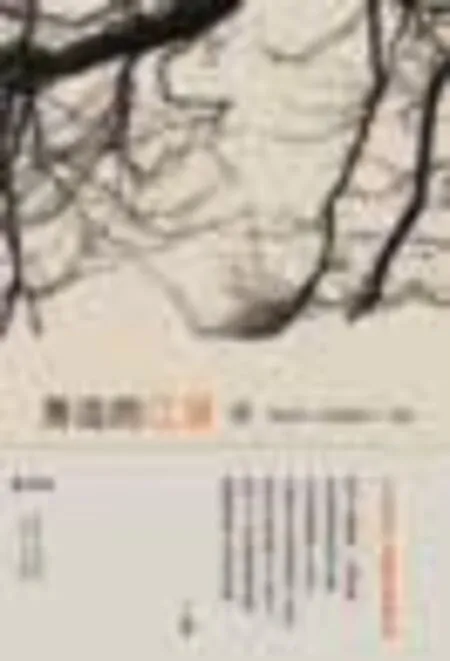
身边的江湖 野夫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版
《身边的江湖》是作家、诗人野夫的一部随笔集。野夫在这部书中用老练的笔法写尽江湖中的小人物,展示社会变革中那些并不为人所知的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