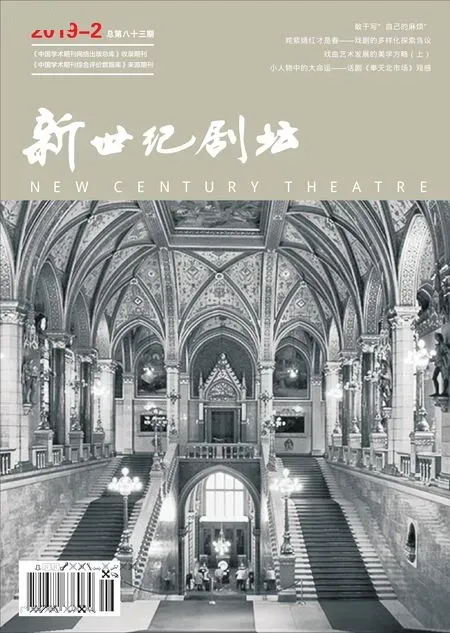小说的戏曲改编
——从两部《金锁记》谈起
2019-05-11王兴昀
王兴昀

河北梆子《金锁记》 河北梆子剧院演出
小说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创作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一些优秀小说作品,其内容较为成熟,并且在观众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将其搬上戏曲舞台,较之原作易于被观众接受。《金锁记》作为张爱玲的知名作品,受到许多改编者的青睐。本文试图对比台湾国光剧团魏海敏主演的京剧《金锁记》(以下称魏版《金锁记》)和天津河北梆子剧院赵靖主演的河北梆子《金锁记》(以下称赵版《金锁记》)在改编上的异同,以期对小说的戏曲改编有所助益。
两版《金锁记》的共同特点在于均以时间为序,依据主人公曹七巧人生轨迹来安排剧情。小说与戏曲在叙事表达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小说不仅能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描写,更能在时空的交织中展现曲折的情节,描述纷繁复杂的事件和人物。戏曲的表现手法受到舞台的限制,所表现时间和空间难以像小说般自如,于是多采用以时间为序的线性叙事。虽然近年来随着舞台装置技术的进步以及一些西方戏剧表现手法的引入,许多戏曲作品也能较为流畅的采取多时空叙事,但是同观众长期以来养成的观剧习惯之间还是稍有隔膜,所以选择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有利于观众接受。而在对原著的取舍和改编手法上,两版《金锁记》发生了分野。
一、聚焦一人与人物纷呈
曹七巧是小说《金锁记》的主人公,戏曲舞台上的两版《金锁记》都围绕曹七巧来设置剧情,却又有显著的不同。魏版《金锁记》的情节安排较为齐整,大体分为哥嫂来访、麻将风波、季泽成婚、怒斥丈夫、分家寡居、呵退侄儿、季泽来访、婆媳不睦、替女辞婚几个部分,试图对原著中的重点章节进行具体再现。七巧的哥哥、嫂子、侄子,姜家长房伯泽和玳珍夫妻、三房季泽和兰芝夫妻、小姑云泽等等各路人马先后登场,而且都有不轻的戏份,还特意增加了合族打麻将以及三房季泽成婚等情节。当然全景式的对原著人物进行再现也无可厚非,可是在两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众多人物如同走马灯似的穿梭登台,难免使观众目不暇接,对剧情产生某种程度的混淆感,也就难以将目光完全聚焦到曹七巧身上。
赵版《金锁记》明确以曹七巧为绝对核心,来精简原著的情节和人物。先是删去了原著中如曹七巧哥哥、嫂子和侄子曹春熹来访,儿女因故辍学、女儿长安相亲等内容,哥嫂、侄子、三房女儿长馨等人物也随之剪去。以姜季泽、姜长安、姜长白为主要配角,配合推动全剧剧情演进。姜老太太、童世舫、袁芝寿等人物为次要配角,丫鬟小双、凤箫以及长房媳妇玳珍、三房媳妇兰芝作为串场人物,辅助烘托全剧氛围递进。依据时间顺序串联起嫁入豪门、合族生活、析产分家、季泽来访、婆媳不睦、替女辞婚等几个重要情节。
该作以原著中所没有的曹七巧出嫁作为开场,此时的曹七巧“山野花此一番艳过牡丹”,憧憬着嫁入高门大户的美好生活。然而沉浸在喜悦中的曹七巧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的送亲队伍。伴着凄厉的音乐,身着黑衣送亲的人们表情木讷,好似泥塑木雕,如同是一支送葬的队伍,将曹七巧送入坟墓。本应是欢天喜地的婚礼反成了曹七巧命运的葬礼,映衬出曹七巧即将开始的多舛的一生,这也为后来她性格的变化埋下了伏笔。对比强烈,寓意鲜明的表现手法,使得观众在开场之际便被激起了观看的欲望。
两版《金锁记》另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人物和表现手法的虚实处理上。魏版《金锁记》侧重写实,赵版《金锁记》则以写意为长。例如曹七巧的丈夫:魏版《金锁记》中由演员扮演,虽然让观众直观看到了姜家二爷的病残,可是舞台上匍匐挣扎的病体似乎又欠缺了几许美感;赵版《金锁记》中却是用道具进行表现,姜家二爷只是椅子上的一袭白衣。夫妻间的一举一动,通过曹七巧手捧这一袭白衣展示出来,在舞台上不断被挥动的这一袭白衣,衬托出了曹七巧丈夫病体难支,命似风中絮。这样一来不仅对应了原著中的描写,而且彰显出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
二、深化主题与独饮一瓢
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金锁记》的女主人公曹七巧被认为是“人性恶”的集大成者。只是曹七巧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堪?原著中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似乎曹七巧之所以是恶人,因为她本就是恶人。不论是戏曲,还是话剧的《金锁记》,改编者都试图在剧中给出自己的答案。
魏版《金锁记》将曹七巧的“恶”归结为爱情的失落。该剧是在一片纷乱的人声中开场,似乎想体现出大家族的人事纠葛。曹七巧在幽暗的灯光下,身着嫁衣起舞,唱着“正月里梅花粉又白,大姑娘房里绣鸳鸯。二月里迎春花儿头上戴,花香勾引了探花郎。三月里桃红映粉腮,情哥哥他夸我比那鲜花香。四月里蔷薇倚墙开,夜半明月照上床。五月里石榴……”的小调。随着灯光的亮起,曹七巧已是一双成年儿女的母亲,丈夫是青梅竹马的药铺伙计小刘,一家人其乐融融。突然仆人龙旺的一声“二奶奶”,惊醒了曹七巧,原来是南柯一梦。美好的婚姻对于曹七巧来说只能寄托于梦境,醒来的她不得不重新面对现实中子幼夫病的困境和娘家哥嫂上门讨钱的窘境。
全剧收尾处曹七巧掐灭了女儿长安和童世舫的爱情。童世舫慨叹离去后,灯光暗下,曹七巧再次陷入梦中。往日的心上人药铺小刘,突然再次浮现,吹灭了曹七巧的烟灯。从年轻时与药铺伙计小刘的情愫,到为钱出嫁的一幕幕场景都涌现到曹七巧眼前。小刘的声音再次在曹七巧耳边响起,“你若是跟了我何至于此,这两个孩子又何至于此。”曹七巧喃喃自语到“哥哥嫂嫂恨我吗?二爷恨我吗?季泽恨我吗?芝寿、娟儿、安姐儿、我的白哥儿,他们都恨我吗?” 在得到“恨”的答复后,曹七巧问小刘,“你恨我吗?”小刘回答,“打从你一双脚一步一步的踏上了姜家花轿,我与你今生今世再无瓜葛啦。” 全剧在开场那首“正月里梅花粉又白”小曲吟唱中,伴着睡梦里的曹七巧落下了帷幕。

河北梆子《金锁记》 河北梆子剧院演出
在对小说进行戏曲改编时,限于演出时长,确实需要对原著主旨到内容进行恰当的取舍,从而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舞台呈现。这种取舍如果选择不当,会较大地削弱原著精神。许多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在进行戏曲改编时,往往以情感纠葛为叙事主线。这类改编剧目确实多有成功之作,越剧的《红楼梦》即为例证。在淡化了原著的宏大背景后,宝黛二人的凄美爱情,让观者落泪,闻者伤心。可若是对于原著的梳理欠妥,忽视了人物在原著中所处的具体情景,单纯以爱情或情感为线,有可能使改编留下缺憾。魏版《金锁记》将曹七巧幸福的期许建立在一段似乎是喜欢对方,并且止于提亲从未开始的婚姻之上。似乎曹七巧的不幸人生源于她选错了人,只要她选了对门中药铺的小刘,就能收获幸福生活。观众看不到曹七巧同药铺伙计之间是否真的有爱,只有曹七巧梦中的幻影,或许这不过是她的一厢情愿。即便选择了小刘,曹七巧可能仅仅是从一种不幸,走向了另一种不幸。在难以激起观众共鸣的同时,将原著的深层次价值肤浅化。
赵版《金锁记》则试图将观众的思索引向更深的层次。曹七巧嫁到姜家时,一道巨大的门楼出现在面前。门楼下的曹七巧显得那么微小,她心中婚后生活的愿景被这扇高门大户所碾压。丈夫病废在床,无夫妻之爱;姜家上下对她冷眼相看,冷语相加,无家族之亲。曹七巧的人性被冷酷的现实一点点打磨掉,使她自以为被人轻视皆因为出身贫寒,也就将金钱同社会地位画上了等号。分家另过后,姜季泽登门骗钱,打碎了曹七巧人性中最后一丝期许,让她深感“情有何用钱重于山,真又如何钱是祖先。”最终使得曹七巧萌生出对于婚姻、爱情乃至世人的不信任,认为“人心哪有善,人只知欺骗。人心不如狗,人恶满世间”。而这种观念也戕害了姜长白、姜长安一双儿女的幸福。剧中写出了曹七巧随着人生的幻灭而被摧毁的人性,观众能感到曹七巧性格走向异变源于外界环境的压迫挤压。曹七巧一切的“恶”,或许是出自一种为抵御外界“恶”的极端的“自保”手段。
结尾处曹七巧已从十七八岁的青春少女,变为行将就木的临终老妪。在“今夜月又残魂飘云里仙,梦随烟飘散浮生醉其间”的伴唱中,满头白发的曹七巧雪天独坐,慨叹这一生累了,“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睡了”。风雪中她为自己缝制寿衣。“寻一方洁净地深埋睡莲,将此生烦仇怨留存世间。年幼时自有娘缝补衣暖,人将死装裹衣需自裁连。剪儿划纸儿破苍白粉面,也笑纸正如人福薄命单。最是它能由着性儿来剪,剪出个人模样覆盖枯颜。我多想剪出个当年模样,却怎么总剪得不像从前。”人生的确是一条单行路,一步走错,能就难以回头。人性和灵魂一旦被外界环境异化,就再难以恢复本来面目,最后只落得“清冷夜我自己自身祭奠,把自己爱怜。”由此引发观众自身现实处境和日常行为的警醒。
结 语
小说对于人物、事件能够充分展开篇幅,娓娓道来。即便稍显平铺直叙,却能以文字表达独特的魅力抓住读者。而戏曲的创作“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压榨出最浓烈、最深厚的人的思想精神情感,把‘戴着镣铐’的舞蹈跳到极限。” 所以在将小说进行戏曲改编时,需要在把握原著主旨内涵的基础上适当增删,建构起完整的剧情。要本着“聚焦核心人物,深化主题意涵”的理念,巧妙改编,尽显匠心。更要注意遵循戏曲创作的特点,避免跟随原著的节奏,使剧情和人物成为流水账,不但弱化了舞台上的情节冲突,也难勾起观众的兴趣。小说的戏曲改编是一个在戏曲发展史上不断演进的课题,在历史上有着为数众多的成功案例,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进而有效地指导当代的戏曲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