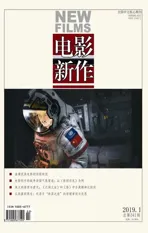把纪录片搬上银幕
——与萧寒导演对谈
2019-05-09聂倩葳
萧 寒 聂倩葳
受 访 者:萧寒,导演,代表作《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等,曾获中国首届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传播力奖”。
访问/整理:聂倩葳,《电影新作》《东方电影》《电影故事》编辑。
对谈时间:2018年11月27日
对谈地点:杭州潜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聂倩葳:萧寒导演您好。您已经有了几部很受欢迎的纪录片作品,并且您都将它们搬上了院线,这在现在的电影市场里是一件很有情怀的事情,现在您的新作《一百年很长吗》也登上了银幕,首先向您表示祝贺。2018年是纪录片集体爆发的一年,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目前纪录片在电影市场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您对于纪录片电影进院线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期许呢?
萧寒:我们还算是有成功作品的团队,但是面对市场依然感到无能为力。《一百年很长吗》做宣传的时候,有很多人帮忙,黄渤还义务帮我们唱歌。制作出来放到网上口碑很好,微博也有几百万的播放量,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就是很难转化成票房,很难转化成驱动大家进入影院的动力。
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已经形成太深太久了,看纪录片要去影院看的这种习惯在国内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们会想当然地产生疑问:我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看一部纪录片?平时我都是在电视上看纪录片的,如果我想看我在电视上也可以看。但是我偏偏认为,纪录片就应该去电影院看。因为看纪录片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在电影院这个沉浸感更强的环境里,会更容易进入到纪录片的语境当中,也更容易进入到主人公的生活当中去。我觉得纪录片更需要一种沉浸式的观看体验,需要电影院这样的场合。
这种观影习惯很难建立起来,也没有办法很快地去建立这样一个习惯。其实在纪录片这个领域我们努力了三年多了,已经出了三部作品了,虽然也有好评,但是面对这个市场我依然觉得非常累,我们总是尽力吆喝,这种效果也有限。有时候我也会思考人生,觉得自己没必要非要较这个劲。我觉得纪录片比好莱坞大片更需要慢慢去品,但审美习惯也要慢慢去培养。我们的片子并不像《都灵之马》节奏那样慢,它里面生活中的戏剧冲突感还是很强烈的,片子的节奏还有其他各方面,其实完全可以和一个剧情片相提并论了。
人想要接受一个新事物是不容易的,这需要一个量的积累,需要更多的导演有这个信念,也去做这样的事情,才能渐渐产生质变,如果大家都是拍完一部之后受挫,然后铩羽而归,谁都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事情就很难实现。
聂倩葳:您之前说您特别喜欢一部纪录片叫《永远》,这部纪录片对您有什么启蒙意义吗?
萧寒:《永远》的确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纪录片。我第一次看《永远》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拍摄自己的纪录片了。那时候我正在拍我的第一部片子,也就是《丽江·拉夫斯基》,拍摄之前我看了大量的纪录片,国外也看了很多,还专门跑到阿姆斯特丹看纪录片的影展,但是《永远》的气息和它所讨论的问题很打动我。这部片子在讨论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永远》里面出现的那个拉雪兹神父公墓很震撼,那里埋着很多艺术家,像肖邦啊,王尔德啊,还有很多我很喜欢的画家,他们都在那里。很多人来看这些艺术家,甚至有人特意接一瓶水,给坟墓边上缝隙里生长出来的小花浇水。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妙的,非常打动我。
聂倩葳:这是对生活和艺术的信仰,其实和《一百年很长吗》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如出一辙的。标题里的“一百年”其实就是人的一生,在这一生之中,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或者说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更喜欢活着,就像影片里的黄忠坚,对于他来说这个东西可能是舞狮,而对于阿合提老爷子来说,也许就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所带来的文化归属感。
萧寒:没错,就是这样的。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参得不透,我还有很多执念,比如我一定要让纪录片上院线之类的(笑)。这都是执念,但是我觉得人的心里要有这个东西。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有一次我去巴黎,特意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待了一天。我不懂法语,还请了一个当地的朋友陪我。他说他在法国待了五年了都没去过那片墓地,还很奇怪我居然专门要去那里。我让我朋友帮我找那些大艺术家的墓,我看到了肖邦、王尔德他们的墓,我突然特别能体会《永远》里的那种心境。我在那里完全没有萧瑟的感觉,反而很释然,在这种状态下,墓地也变得像一个公园,我也理解了《永远》里的人们为他们喜欢的墓主人浇水的行为。
聂倩葳:他们为墓主人浇水,站在那里和故去的艺术家对话,其实那些话是说给他们自己听的。他们是在通过跟自己的内心交流,达成对心灵的安抚。
萧寒:是的。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别人问他是干啥的,他说:“我是出租车司机,但是这不是我生活的意义,不是我活着的目的。”他很羞涩,说话也很慢。然后别人又问他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说:“歌唱。”那一刻我感动得浑身颤抖了一下。人的生活里都得有这么一个东西,即使你为了谋生每天做着很枯燥的事,一天中绝大多数的时间你都是为了活着而去努力,但是如果没有“歌唱”,那么在做那些谋生之事的时候,你将变得非常痛苦。而因为有了“歌唱”,就像那个出租车司机那样,连那些乏味的东西都不会那么痛苦了。
这可能就是生活和生存的区别。《一百年很长吗》里的黄忠坚,如果没有舞狮和蔡李佛拳,那他的生活就没有太大滋味了。他在那么小的出租房里,承担着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只要让他拿着脸盆出去舞一会儿狮子,他就会很开心,那一刻的释放能帮助他去面对生活,也能帮助他去排解一些不好的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很需要这个东西。其实《一百年很长吗》就是讲的我们是怎么度过这“一百年”的,到底是什么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度过去的。
聂倩葳:有人说电影的名字和内容没关系,其实有关系。影片的主旨是隐在后面的,需要观众自己去提炼,提炼出来的东西是很有力量的。
萧寒:对,是有着很紧密的关系的。比如那个出租车司机,他每天可能十个小时都在开车,只有一个小时能去看看他喜欢的诗歌,去唱唱歌,这个比例是十比一。而黄忠坚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是十,摆弄那些他喜欢的手艺是一。但我不想就只拍那几分之一的东西,恰恰是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才能彰显它的力量。
聂倩葳:现在的观众观看过那么多电影和电视节目,对于纪录片的真实程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看到《一百年很长吗》里面演员状态的真实度很高,你们是怎么让被摄者将自己有些困窘,甚至前途未知的生活完全展现给你们的呢?人物在片中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你们会去帮他们排解吗?
萧寒:我不需要安慰黄忠坚他们,他们的自我调整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强得多。比如黄忠坚,他未出世的孩子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这让他突然暴躁,当着女朋友的面怒踢婴儿车,我们就在旁边待着不说话,已经是完全画外的状态了,像透明人一样,他们也会渐渐习惯摄影机的存在。而且越往后他会越信任你,因为黄忠坚其实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已经跟他一起同甘共苦过了。一开始他发现女朋友怀孕了,他就去见岳父母了,我们当时是陪着他给他壮胆的,结果见岳父母不成,还被赶出来好多次。他的岳父母也不让我们拍摄,我们就在门外把声音记录了下来。这一切我们是和黄忠坚一起经历的。经历过这些之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见证了他和雪菲两个人遇到困难、解决困难的全过程。最后突然发现雪菲肚子里的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一切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时间大家都不知所措。但这时候黄忠坚已经拿我们当朋友了,拍摄也就继续了下去。
聂倩葳:新疆阿合提老爷子的名字,在官方资料上显示的是“阿合特”。
萧寒:没错,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阿合提”是他们方言的叫法。老爷子的名字念起来是“阿合提”,但写出来其实应该写“阿合特”,后者是身份证上的名字,但是新疆那边的发音是阿合提,我们也就入乡随俗了,影片里也是这个叫法。
聂倩葳:听说您拍摄之前寻访了很多人,找到了很多的故事,最后只呈现了黄忠坚和阿合提,其他人的故事后续会以其他形式和观众见面吗?
萧寒:我们全中国都寻访了一遍,连台湾、香港都去了,希望能多碰一碰缘分。在所有的故事里黄忠坚的最吸引我,不是因为他最苦,苦难并不吸引我,吸引我的是他面对苦难,与之作斗争的精神。他所经历的事情,以及他身上丰富的生命质感,这个东西很难具体去表述。我看到黄忠坚的时候,觉得他很像周星驰《喜剧之王》里的主人公。那一刻感觉突然就来了,所以说并不是因为他某个具体的表情,或者坚毅的性格什么的,那是一种很完整又很复杂的东西,怎么描述都可能会有失偏颇,那就用影像呈现出来的故事本身来打动观众吧。再一个就像你说的,《一百年很长吗》如果三个主人公可能会更好,“三”这个数字有众生的含义,但是看了所有的素材后,我发现其他故事的节奏和质感与既有的这两个故事不契合,所以两个就两个吧,纪录片也是遗憾的艺术,这样剪出来会很舒服,其他的故事以后也会和观众见面的。
聂倩葳:阿合提的故事是很有少数民族风情的,但是和黄忠坚的故事放在一起一点也不违和,很多在情节上比较相近的剪辑点被推到了一起,好像在不同的土地上,他们两个产生了一个命运的交汇和对话。
萧寒:这就是电影的魅力。《一百年很长吗》本身就是一部电影,所有的剪辑都是按照一个电影的规格创作的,而不是做一个电视节目。我做的三部电影,《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百年很长吗》没有一部有旁白,这对于纪录片来说是很难的,因为主人公不能演戏,而只有故事和影像支撑不了才会用旁白去凑。我觉得我这样做会更高级一些,至少在我心里是这样认为的。

图2.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
聂倩葳:您在拍摄的过程中看到了那么多的故事,也见证了很多的奇迹,有没有某一刻会产生一个换位的念头,当您置身于主人公的境地时,您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萧寒:我会感同身受,尤其是和被拍摄者共同经历了他们的一段人生,我会去感知他们的生活、命运和内心,但是不一定会类比具体的事情。我其实是在寻找我们情感当中相同的一种东西。至于为什么会拍这个人,为什么会把它做成电影给别人看,其实还是源于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打动我到了我的内心。我们自己看素材剪辑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落泪,也会发自内心地笑,我很希望的是把我的这种感受传达给观众,所以不能冰冷麻木地看人物和素材,这个事情是没法用理性的思维去计算的。
聂倩葳: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您曾经谈到过的“热眼旁观”,这个观念蛮有趣的。当您看到被拍摄者遭受困难时,既要保持中立,又要过自己心里这一关。
萧寒:对的,这个真的很难。其实一直以来,我们从创作上都不希望去干涉拍摄对象的生活,有人说我们拍纪录片是冷眼旁观,我说我们既不是主动介入,也不是冷眼旁观,我们是热眼旁观。我们的心会跟着主人公一起起伏,跟着他们紧张,跟着他们开心,跟着他们难受。但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像一个朋友一样去陪伴他们,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去做这个事情,谁也没有资格像上帝一样去改变另一个人的人生。但是很多时候我都很煎熬。
比方说像阿合提借钱,他们家人急需换肾,急得老爷子想借高利贷。高利贷这个东西他可能不了解,但即便我们努力劝他,他可能也不太能接受我们的观点,还是会去借,因为他有他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在他们生活的那个语境里,也许这就是对他而言最直接、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手工马鞍是阿合提的祖传手艺,但在市场上却在渐渐凋零,在一年一度的市场上他终于接到了几个订单,面对来之不易的订单我们在一边也特别高兴。但这对于他们家治病救人可能还是不够,我自己悄悄托人买了两个,放在我工作室了,我不希望让老爷子知道这事,我能做的可能就是悄悄地买两个马鞍吧。
聂倩葳:《一百年很长吗》是您的第三部纪录电影,和拍摄前两部的时候相比,心境有没有一些变化?以后有没有考虑过尝试其他类型的影片?
萧寒:在心境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拍摄中我还是会非常享受,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拍摄的时候没有什么心理变化,但是技术上和经验上肯定是越来越完善的。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创作的方式和整个拍摄的理念其实都没变过,都一直在坚持,但是面对市场空间的无奈,我还是会有一些悲伤和难受。所有的东西都有兴衰更替的过程,只是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置身于这个潮流之中,但是既然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那么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吧,起码短时间内我是不会放弃的。
之前我在美院读了十年书,从美院附中、美院研究生都是在美院读的,就是因为喜欢。但是我毕业之后就没怎么画画,因为我那时候又喜欢传媒了,后来就开始做传媒了,画画依然我生命里的一个爱好,多年学习美术的经历,以及对审美的培养,都对我拍纪录片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我这个人还是很追随自己爱好的,所以也没觉得拍纪录片苦。以后有可能会拍其他类型的影片,这个就不会刻意了,随缘吧,但纪录片我会坚持拍下去的,我很享受拍摄纪录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