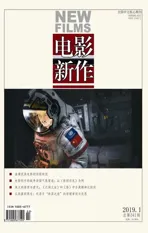胡金铨武侠电影的世界性影响力探因
2019-05-09杨世真
杨世真
2017年是著名武侠电影导演胡金铨先生逝世20周年。斯人已逝,但他留给世人的是武侠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我想,对胡金铨导演最好的纪念乃是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并学习、吸收他的武侠电影艺术精华,为中国电影国际化传播、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明鉴。围绕胡金铨武侠电影的艺术成就,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令人欣喜。然而,相关的研究中尚存不少误解乃至偏差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深究。其中关于胡金铨武侠电影究竟缘何产生如此之大的世界性影响力,或许是存疑最多并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归纳起来,大致有“民族文化说”“中国电影美学说”“电影技巧至上说”等几种说法。下面尝试着一一加以辨析,以便与各位同仁交流、商榷,更好地理解、继承与发扬胡金铨武侠电影的优秀传统。
一、民族文化说
众所周知,胡金铨的武侠电影讲的大都是中国明朝的事,其中充满着中国传统的绘画、音乐、戏曲(特别是京剧)、武术、书法、服饰、建筑等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元素。“胡金铨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导演”1,胡金铨导演本人也坦承:“我学习、涵泳于中国艺术的无限传统之中,自知戏剧世界中许多高度的象征技巧多有其悠久深厚的民族根底。”2正因为如此,说胡金铨武侠电影具有突出的民族性,似乎无人能驳。另一方面,他的武侠电影又输出五大洲(尤其是东南亚)诸国,获得较高的票房业绩。胡金铨本人更是首位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奖的华人导演,也是首位获评英国《国际电影年鉴》“世界五大导演”之一的华人导演。胡金铨武侠电影也获得西方电影理论界的关注,汤尼·雷恩、大卫·波德维尔等都做过深入研究与高度评价。胡金铨武侠电影的世界性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作为对一种结果的描述,人们当然自豪地可以说,胡金铨武侠电影不但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其中的民族文化元素因此得到广泛而有效的传播。但是,如果认为“他借武侠电影这个酒杯浇自己的文化块垒,他的武侠之美,美就美在对侠的关注背后,体现出他对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的沉迷、思考和反省”3,或认为胡金铨武侠电影从世界电影的层面而言,“是纯正的中国古典文化通过电影打动了世界的例子”4,就很值得商榷了。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对异域的观众来说,几乎所有中国影片都天然地具有本民族的特性,但真正得到世界性好评的中国导演和影片却屈指可数,这又如何解释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影片中堆砌各种民族文化符号,的确满足了一些国际评委的好奇心,让某些导演获得国际大奖。这令急于走出去的中国电影人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胡金铨导演获得的是戛纳电影节的最高综合技术奖,显然不同于那些在表面上堆砌民族文化元素的导演。当被问到他是否觉得西方对其电影的评论较为着重形式方面,而东方则比较着重主题和内容方面时,胡金铨导演的回答是肯定的。5所以,其世界性影响力当然不应忽视从艺术形式方面去考量。

图1.电影《功夫熊猫》
在电影文本中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元素的吸引力,一直是电影创作中的一大难题。从根本上说,就是“拍什么”与“怎么拍”的问题。“拍什么”是素材问题,而“怎么拍”则是形式问题。对于作品的创作来说,选材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很显然是运用艺术形式去对素材进行加工处理。否则,人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根据同一个事件、同一部小说或同一部戏剧改编的不同影片,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在影片中机械展示民族文化符号,试图借此博得域外观众的眼球,不但暴露了艺术创作观念上的偏差,而且也是对民族性内涵的误解。俄国作家果戈理曾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描写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是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6张艺谋导演的《长城》之所以遭到国内外一致的差评,与创作者把民族性简单等同于长城、饕餮、火药、孔明灯、秦腔等外在符号有关。在影片中堆砌民族文化元素比较容易操作,但要表现出抽象的民族精神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正因为如此,功夫是中国的,熊猫也是中国的,但《功夫熊猫》这部影片却是好莱坞的。
电影是一种具象的、写实的视听艺术,要展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绘画、音乐、戏曲、武术、建筑及各种典型的生产生活器具,只要发挥摄影机的复制功能即可。但要在电影中表现抽象的民族精神,就离不开电影形式的创造功能。将胡金铨武侠电影的世界性影响力归因于民族文化元素展示,是一种陈旧的内容决定论思维,是对胡金铨武侠电影艺术与美学成就的忽视。更何况,观众在其影片中看到的、对观众产生效果的各种民族文化元素已经不是电影创作的原始素材,而是已经与人物关系、情节走向、人物命运以及表演、摄影、服装、录音、灯光、制作等创作要素结合在一起—即与胡金铨具体而独特的电影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所谓“内容”。正如黑格尔所说:“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7把电影的素材混同于电影的内容,把胡金铨武侠电影中的民族文化元素或符号抽取出来单独加以评判,是误将胡金铨武侠电影的世界性影响力归因于民族文化元素的主要原因。这种把电影的内容与形式割裂开,并进而认为电影的内容决定电影的形式的思维模式,是很难对胡金铨武侠电影的真正魅力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的。
当下,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文化艺术观念深入人心。但在实际的理解与做法上,往往是夸大了前者,误解了后者。主张胡金铨武侠电影凭借传统文化元素扬名海外的看法,正是夸大了素材的作用,忽视了艺术本体的力量。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步伐越来越快,上述观念在电影界也越来越有市场。它给善意的人们增加了盲目的自信,轻易占据了道德高地,获得了天然的学术合法性。但其中包含着非理性的文化艺术观念,令我们至今未能正确地认识、总结与吸收胡金铨武侠电影产生世界性影响力的宝贵经验,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
简而言之,胡金铨武侠电影中的民族文化元素受到世界性的关注与喜爱,只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如果把那句话换成“越是优秀的,越是世界的”,可能更为合理,“就像吃东西,我们该注意的不是谁喜欢吃辣或者谁喜欢吃甜,而是必须做得好,不管是辣是甜,都要做得好吃。”8另外,不能简单地把拍摄与罗列民族文化素材,当作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捷径。也用不着惦记外国电影节奖项的光环,用不着迎合外国评委与想象中的外国观众。胡金铨明确表示:“我的戏当然是拍给中国人看的。”9可见,只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拍摄接地气的、为本土观众喜爱的电影,自然有可能真正获得世界性的影响力。
二、中国电影美学说
除了上述“民族文化元素说”外,还有不少中外电影学者认为,胡金铨以其一系列的武侠电影构建的“中国电影美学”体系,使得中国电影获得世界的首肯,并对世界电影美学作出了贡献。例如,有人认为,胡金铨电影“汇聚了各种艺术类型和哲学传统,形成一种综合的‘中国性’形象,凸现胡金铨以鲜明的‘中国美学’立场抗衡西方文化”10。也有学者认为:“西方学者由胡金铨而开始推武侠电影,首肯武侠电影所彰明的‘中国电影美学’。总体而言,胡金铨武侠电影的超越性在于:开创新武侠世纪的历史新纪元,建构严密完整的武侠电影美学体系,确立‘文史武侠’的经典叙述范式,从而奠定武侠电影类型的国际地位。”11还有人认为,胡金铨武侠电影“对世界电影的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那么,被不少人推崇的胡金铨武侠电影所体现的所谓“中国电影美学”体系(如果存在的话)究竟是什么呢?它在世界电影美学体系中又具有何等价值地位呢?所谓的“中国电影美学”在中外学者眼中似乎并不一致。外国学者也语焉不详。如大卫·波德维尔认为:“胡金铨历久不衰的声誉,主要建基于动作场面的精彩处理”13,将其风格概括为“一瞥美学”,“其感染力之精确计算,相信爱森斯坦和黑泽明都会对这场戏佩服得五体投地”15。但这种赞誉明明谈世界电影通行的蒙太奇与剪辑问题,无涉中国电影美学。国内有学者则明确认为:“胡金铨是中国唯一本土电影理论‘影戏’美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对其电影美学之阐释,即对于中国本土电影理论的有效推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15
如果将胡金铨的电影美学归结到“影戏说”是出于善意的褒扬,那么实际上只能说是一种谬赞。胡金铨导演如若知晓,未必领情。说“影戏说”是中国唯一本土电影理论,大致没问题。然而其本身却是一种不成熟的电影理论,它只是对早期中国电影依赖“戏剧的拐杖”的不发达历史阶段的准确概括。或者说,“影戏说”其实是一种否定性的电影美学——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电影违背电影本性的某种特征,虽然一度成就了中国电影的辉煌,但也长期束缚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就连当初提出“影戏说”的主要学者之一陈犀禾先生早已于提出“影戏说”的当年,即在1986年11月29日的《中国电影时报》刊文,肯定了从影戏到影像的转变是新时期电影美学重要转向。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者却大多误以为提出者即赞同者。
具体来说,胡金铨武侠电影的确吸收了很多京剧的元素,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一切都是经过了真正的电影化改造而成了电影的内在组成元素。陈墨先生指出:“胡金铨的电影虽然受到中国传统戏曲的明显影响,但他的电影作品在‘电影化’方面却又十分突出,甚至独树一帜。所谓的‘电影化’,当然是相对于传统中国电影的‘影戏化’而言,即常常是把电影只当成记录戏剧表演的手段和形式,而没有真正学会用影像/画面叙事的电影化方式。”16胡金铨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借鉴吸收,似乎也应该这么看。
我国电影界在改革开放之初发生了“扔掉戏剧的拐杖”“戏剧与电影离婚”等论争。虽然这次论争直接启发与引导第五代导演进行中国电影语言的革新与探索,但不得不承认,这终究是一次迟到的论争。因为在电影史上,人们早已纠结过这个问题。格里菲斯原来是位戏剧导演,刚开始并不懂得如何拍电影。但是他有一个秘诀,那就是尽量不按照戏剧的手法去拍电影。结果,格里菲斯因为发明了电影的一系列基本表现手法而被称为“世界电影之父”,自此电影被普遍确认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在论上,关于电影与戏剧的关系问题,也早已发生过广泛的论争并已有被普遍接受的结论。其中电影理论家拉尔夫·布洛克于1927年在《日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是戏剧,不是文学,不是绘画》的文章可为代表。他在文章中指出,“换言之,电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生活的。”17
如果因为胡金铨武侠电影中吸收了京剧等一些元素,就将之归结到“影戏说”这种本身并不完善的电影美学体系中,在某种意义上是低估乃至贬抑了胡金铨武侠电影的艺术成就,有削足适履之感。胡金铨导演1968年赴美参加美国亚洲学会会议时曾发表谈话,谈话主旨就是“电影是独立艺术,并非任何其他艺术的副产品”。18就拿胡金铨武侠电影中最为人称道的动作场面来看,其中固然吸收了很多京剧的元素,但胡金铨导演表示,他本人其实对武术一无所知,银幕上的武打动作都是通过电影手段创造出来的。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我信(库里肖夫效应——引者注)。为什么呢?因为,不论什么戏剧也好,都是在继续性、连续性中表达的。而电影则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是可以通过剪辑,即蒙太奇的方法去表达的。”19
由此不难看出,将胡金铨武侠电影归结为中国电影美学(影戏说)的代表,实在是对胡金铨电影美学的误解。更进一步说,如果胡金铨武侠电影真的是影戏说的代表,那么是不可能对世界电影美学做出真正的贡献的。从早期电影发展史来看,戏剧的确曾经助力过电影的发展,但那也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电影之所以成为独立的艺术样式,正是从与戏剧的区别中开始的。正如巴拉兹·贝拉所言,电影是一种新形式和新语言,“如果一位艺术家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而不是个劣等工匠的话,那么他在改编小说为舞台剧或改编舞台剧为电影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是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20
“影戏说”体现了中国电影长期以来的一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它在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与发展的,在历代电影研究者心中具有崇高地位,早已被奉为中国电影美学的最高典范。然而,特点并不一定等同于优点。世界各国、各个时期、各个导演的电影美学风格千变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电影是以“动态影像”为媒介材料、以蒙太奇为基本手段去表现外部世界的,只要视力正常的人都应该能看得见、看得懂。在这种意义上讲,电影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即使人物的对白用了各种语言,但语言终究隶属于观众眼中所见的空间,只要辅以字幕,并不妨碍电影的交流与互相欣赏。“电影市场的规律只容忍那些全世界人民—从公主到女工、从旧金山到伊斯密尔—都能了解的通用语言。”21
有趣的是,因为电影声音技术发展与影像技术的偶然性错位,西方电影发展经历了一个30多年的默片时期。而正是在默片时期,以蒙太奇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电影语言趋于完善,促使电影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从而与绘画、戏剧、文学等传统艺术区别开来。中国电影虽然仅仅比西方电影诞生晚了10年,却错过了一个完整的默片时代,缺少一个独立发展影像的阶段,可能也因此导致了电影语言自觉意识的缺乏,致使中国电影美学(语言)长期依附于戏剧(曲)美学。有学者提出:“‘影戏’的阶段应当是属于电影艺术发展的一般过程,而不是中国电影的独特性之所在。《影戏剧本作法》整个建立在西方戏剧理论和戏剧美学的基础之上,这是显而易见的。以这样一部深受西方戏剧理论和戏剧美学影响的电影剧作理论来论证‘影戏’是中国电影美学的核心概念,认为‘影戏’观是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体系,岂非咄咄怪事……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植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超稳定的电影美学理论体系。”22
有理由相信,胡金铨武侠电影之所以获得世界性的关注,不太可能是因为其代表了一种阶段性的、不成熟的戏剧化电影美学—“影戏说”,而恰恰是因为他的电影抛弃了传统戏剧(曲)手法的桎梏,掌握了世界电影语言的核心特征。在这一基本问题上如果发生误判,将会极大地阻碍中国电影国际化步伐,用电影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愿望也很难实现。
当然,我们认为,电影虽然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但戏剧对电影也并非毫无价值。实际上,在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中,二者的关联度依然很高,古老的戏剧艺术并未从银幕上消失,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电影从戏剧(曲)中汲取题材及表现手段,二是戏剧(曲)电影依然存在,三是主流电影虽然独立于戏剧(曲),但离不开“戏剧性”—冲突。胡金铨武侠电影毫无疑问从中国传统戏曲中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但前提是要经过电影化手段的过滤。胡金铨曾表示自己的电影是“京剧的电影化改编……主角们的对打是经过我的导演和剪辑而制造出来的”23,所指重心应该在“电影化的改编”,而非“京剧”本身。
三、电影技巧至上说
主因既不是民族文化元素,亦非中国电影美学,那么胡金铨武侠电影具有世界性影响这一客观现象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只要我们暂时放下研究者心中固有的尺子,而用各种尺子去衡量胡金铨的作品,首先应该不带预设与成见去聆听导演本人的心声,可能会给我们不少启发。20世纪90年代在接受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的学术采访,回顾他对创作经历时,胡金铨谈道:“去到内地,常有人问我:‘你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其实我的电影主题一向就是电影。我也反论过,难道电影是不可以没有主题的吗?但他们说艺术是必须要有主题的。我于是反问,那么,柴可夫斯基和莫扎特的乐曲有没有主题?莫扎特在十岁时就作曲了,他没有可能想过主题。此外,讨论塞尚的画是什么主题也没有意思。”24乍看起来,“我的电影主题一向就是电影”颇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意味,这种观念在内地是曾长期遭到批判的。但胡金铨却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与接受。照这么一来,民族文化传统在胡金铨武侠电影里的位置又摆在哪里呢?其实,早在1968年在香港接受王敬义采访时,胡金铨就明确表示:“我觉得对电影而言,主题不要紧,故事也不要紧,故事的好坏与主题都不足以影响一部电影,电影最重要的仍是表现的技巧”。王敬义则当场表示反对意见,认为故事和人物造型对观众更重要,并给胡金铨扣上了“电影技巧至上”的帽子。胡金铨坚持认为故事等要素“绝不会比电影技巧更重要。此外,我只是说不注意故事,不是不要故事”。25
那么,胡金铨的“电影技巧至上”到底所指为何?
从胡金铨电影技巧的来源及其影片文本自身的形式来看,胡金铨自称的“电影技巧”显然不是所谓的“中国电影语言”,而是世界叙事电影历经多年积淀而成的、以分镜与蒙太奇为核心技巧的电影语言体系。巴赞在其著名的论文《电影语言的演进》一文中指出:“1930-1940年间,在电影语言中仿佛形成了一种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表现手法,这种表现手法主要起始于美国。好莱坞因五六种类型影片的成功而保持着自己的霸权,这些类型片包括美国式的喜剧片、滑稽笑料片、音乐歌舞片、警探片和强盗片、心理与风俗片、神怪或恐怖片、西部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有声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已经明显达到均衡和成熟的水平。再谈影片形式:摄影与剪辑风格清晰明快,符合主题要求,声音与影像配合完美……总之,我们看到一种‘经典的’艺术臻于完美的一切特征。”26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用的是“电影叙事”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古典叙述:好莱坞范本”和“正典叙述”:“剧情片中,有一类叙述模式独占鳌头。电影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古典主义,也就是1917-1960年的好莱坞片厂电影。”27此后世界电影发展的实践业已表明,上述世界电影语言体系已经不为好莱坞专属,而成为一般叙事电影的通用手法,对世界电影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说顺之者兴逆之者衰亦不为过。
胡金铨武侠电影获得的世界性影响力足以表明,胡金铨已经全面理解与掌握了世界电影语言的一般规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实际创作中还有所突破与创新。这又可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是胡金铨导演深谙运动性题材对电影的重要性。希区柯克曾表示“追赶是电影手段的最高表现”。弗拉哈迪认为西部片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在原野上策马奔驰的景象是叫人百看不厌的”。克拉考尔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多种多样的运动是最上乘的电影题材,是真正“电影的”,因为“只有电影摄影机才能记录它们”。28纵观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人物要么是在不断地前进的行者,要么就是处在生死之间的战斗者。而对运动事物的高度敏感是人和一切动物的视觉本能。研究者石琪和吴昊都注意到了胡金铨武侠电影中人物多行走与奔跑的特征,但对此现象的阐释更侧重其“移民”“过客”“流散”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视角,而鲜有从关联电影本体的视角来探究。
第二个层次是胡金铨全面掌握了以蒙太奇为核心的电影语言。上述电影镜头中运动着的对象固然比静态的事物更吸引观众,但毕竟还是低层次的运动,因为在这里电影更多地还只是在发挥其复制现实的功能;靠电影化手段创造出来的第二重运动(感)——如摄影机的运动(感)、剪辑创造的运动(感)——对观众具有更强烈的视觉刺激。“正在看电影的人的眼,并不是在看放映出来的现实的动作”,这真正体现了电影语言的本质属性。正因为如此,不会一点武术的胡金铨却拍出了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系列动作场面,从中可以看得出是“蒙太奇理论的最佳实践”29。虽然胡金铨不懂武术,但是他懂电影,会剪辑,从而创造了新的运动形式。比如,拍摄角色螺旋式飞跃上高高的竹梢,在现实中不可能,在京剧中也不可能,但是胡金铨改变方向拍几次跳起的镜头,然后用剪辑的技巧就创造了这样的神奇效果。
鉴于中国电影语言在整体上却与世界一般电影语言发展客观上存在代差,胡金铨导演纯熟地掌握与驾驭世界一般电影语言手段,就显得尤为可贵。直到1979年,张暖忻、李陀发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内地电影界才逐渐认识到我们的电影“落后于形势,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太陈旧了”。30及至1986年,邵牧君重提“中国电影创新之路”,但仍然强调“电影创新的合理局限性,指的是电影同其他艺术相比起来,在创造上有某些不可跨越的合理界线”31,又说“电影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因此,中国电影注定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模仿时期”32。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中国电影一直在吁求“创新”,倒不如说是以“创新”的名义在“补差”“补缺”“补课”。如今,发展类型电影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对电影的基本特性和现代电影语言没有很好的掌握,那么拍娱乐片就是瞎胡闹”。33近年来,不少跨界导演的作品遭遇的差评就是一个明证。
第三个层次是胡金铨对世界电影语言体系的突破及创新。胡金铨并没有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电影语言,而是不停地在寻求创新与破格。比如徐枫扮演的侠女杨慧贞跃上竹子顶端的镜头,就舍弃了常用的“慢镜头或倒拍这类易拍的方法,而用纯粹的蒙太奇的手法,拍出了自然的迫力”34。最出色的就是在《侠女》竹林大战那一场戏中,胡金铨打破了世界电影剪辑中一个镜头不少于八格的金科玉律,大胆用四格胶片作为一个镜头,创造出了令人窒息的极端动作场面。电影学者卓伯棠先生在其重要论文《电影语言的开创者——论胡金铨的剪辑风格》中对此有专门讨论。胡金铨导演自己觉得,这个剪辑技巧才是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高等电影技术委员会大奖的原因。35也正因为类似的原因,胡金铨导演被视为“‘电影艺术之父’D.W.格里菲斯的正统继承者,并要把他跟伯格曼、费里尼、戈达尔等伟大的‘电影作者’并列。”36
由上可以看出,胡金铨的“电影技巧至上”说并非简单的某个电影拍摄手法或剪辑手法,而是代表了胡金铨的电影语言在整体上与世界电影语言同步,甚至在局部超越了后者。从这个角度来探究胡金铨武侠电影的世界性影响力,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需要指出的是,说胡金铨电影语言达到了与世界电影语言同步的水平,丝毫没有低估胡金铨武侠电影的制作水平。从电影专业创作角度来看,与其说他涵泳在民族文化传统或中国电影语言的世界里,还不如说涵泳在世界电影语言的传统中更恰当。换句话说,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民族文化元素是借助于胡金铨出色的电影语言把控能力才得以为域内、域外观众欣赏。
当然,胡金铨导演虽然“不太喜欢去表现那些具有社会性或时代性的所谓主题”,但也“并不是完全不想表现任何主题,只不过是并不特别重视这方面的问题罢了”37。他强调“一个电影编导要注意三件事:好的内容、有创意,好的技巧,描述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的认真态度”38。可见,他非常重视电影形式,但实际上并非一个形式主义者。

图2.电影《长城》
四、如何学习胡金铨
经过十多年的产业化发展,中国电影内地总票房在2018年12月末已达到创纪录的491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银幕总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一大批跨界导演、新导演跻身主流导演行列,中国电影进入“黄金十年”的预言似乎正在得到印证。然而,繁荣中隐含危机,盛世中不乏危言。除了少数作品外,许多跨界导演的作品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市场与口碑的巨大反差,创作中暴露的一些普遍问题或硬伤也备受专家学者们的关注。这些问题或硬伤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势必成为他们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断崖式的负增长引发了“拐点说”“寒冬说”,更加剧了人们对跨界导演后续乏力的担忧。
对外而言,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近年来遭遇瓶颈,出现了“三少”现象(票房少、增长少、影片少)。接下来,中美双方将就电影进口片配额进行新一轮谈判,预计中国电影市场配额将进一步放开。有业内人士坦言:历史留给中国电影的时间不多了。
在这样的情势下,对于担当市场竞争与文化传播双重使命的中国电影来说,胡金铨武侠电影的成功经验可以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尤其可资当下新生代导演及跨界导演学习借鉴。这里主要谈两点。第一,要讲好中国故事,导演必先掌握电影语言基本功。
不论是参与市场竞争,还是对外文化传播,都要以掌握电影语言基本功为前提,充分重视艺术形式的重要作用。失去了电影语言的支撑,再正能量的素材也难以为观众所接受,只能产生概念化、脸谱化、抽象化的作品,电影的市场功能与文化功能很难实现。胡金铨武侠电影的成功首先是艺术表达上的成功,“我不是很相信一般所谓的主题,就是那些载道、言志之类,当然我并不反对这个。一般对创作的说法,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内容,一个是表现方法。内容可能是旧的,如传统故事,但表现方法可以是新的。”39巴拉兹·贝拉也谈道:“任何一部影片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欢迎,先决条件之一是要有为全世界人民所能理解的面部表情和手势。独特的民族特征只能作为异国情调的珍奇现象偶或出现。而某种统一规格的‘手势学’将是不可缺少的。”40我们需要努力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但必先掌握与精通世界电影语言。
第二,要掌握电影语言基本功,导演必先经历一个长期的、全方位的磨炼。
导演的培养不外两个途径。一是学院派,就是进入电影学校或电影专业进行系统的电影知识与电影技能学习,然后进入片场工作。另一种就是实践派,采用传统的师带徒模式,边干边学。胡金铨的导演之路属于第二种。
从1952至1965成为独立导演之前的13年间,胡金铨参与过多部电影的制作,担当过美工、表演、编剧、剪辑、副导演等各环节的职位,“要和导演、厂长、摄影师、录音师、灯光师、道具、服装、木工、漆工、电工,各式各样的实际工作者接触、请教,所以学了不少东西”41。除了传统的师父带徒弟式的学习,胡金铨还有意识地自学电影理论与电影技巧,特别是关于蒙太奇的理论与技巧。另外,大量地观摩约翰·福特、乔治·斯蒂文斯、弗雷德·齐纳曼、罗伯特·怀斯等的影片。还有意识地从导演角度观摩黑泽明的影片。胡金铨的导演成长过程走的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之路,可以用“转益多师是汝师”来形容。
的确,在资本充裕、技术扩散、平台多元及教育普及的当下,电影门槛越来越低,从其他行业半路出家、跨界做导演也越来越容易,甚至不乏“只要找到一个投资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做导演”42的现象。但是,有一道门槛却是电影导演始终绕不过去的,这就是电影语言基本功。导演是电影创作的核心,而电影语言基本功是导演创作的前提,是衡量导演形式创造能力的关键。胡金铨的导演成长之路给跨界导演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这也是我们纪念胡金铨导演的重要意义所在。
【注释】
1 梁秉钧.胡金铨电影:中国文化资源与六十年代港台的文化场域[J].现代中文文学学报,2007(胡金铨电影专号):8.
2 胡金铨.胡金铨谈电影[M].胡维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86.
3 张建德.胡金铨与《侠女》[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22.
4 贾磊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辉映下的胡金铨电影[J].当代电影,2011(08):91.
5 胡金铨.胡金铨谈电影[M].胡维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2.
6 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转引自文艺理论学习资料[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594.
7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78-279.
8 胡金铨.胡金铨谈电影[M].胡维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
9 胡金铨.胡金铨谈电影[M].胡维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2.
10HectorRodriguez,QuestionsofChineseAesthetic s:FilmFormandNarrativeSpaceinCinemaofKingHu[J].CinemaJournal,no.38,1998(73).
11吴迎君.论胡金铨武侠电影的超越性[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6.
12宋子文.台湾电影三十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2.
13罗卡、卓伯棠、吴昊.超前与跨越:胡金铨与张爱玲[M],1998:25.
14大卫·波德维尔.香港电影的秘密[M].何慧玲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12.
15吴迎君.论胡金铨电影的“中国美学”体系[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8(3):73.
16陈墨.中国武侠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54-155.
17RalphBlock.NotTheatre,NotLiterature,NotPainting[J].TheDi al,VolumeLxxxII,JanuarytoJune,1927.
18胡金铨.胡金铨谈电影[M].胡维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4.
19胡金铨.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37.
20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279.
21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33.
22颜纯钧.与电影共舞[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123、127-128.
23胡金铨.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58.
24胡金铨.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90.
25胡金铨.胡金铨谈电影[M].胡维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6-109.
26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4-65.
27大卫·波德维尔.电影叙事:剧情片中的叙述活动[M].李显立等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335.
28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52-53.
29胡金铨.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17.
30 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J].电影艺术,1979(3):40.
31邵牧君.中国电影创新之路[J].电影艺术,1986(9):4.
32邵牧君.中国电影创新之路[J].电影艺术,1986(9):6.
33李陀、陈犀禾、郝大铮、孔都、姚晓濛.对话:娱乐片[J].当代电影,1987(1):57.
34胡金铨.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17.
35胡金铨.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19.
36胡金铨.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346.
37胡金铨.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03.
38胡金铨.胡金铨谈电影[M].胡维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85.
39胡金铨.胡金铨谈电影[M].胡维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22.
40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33.
41胡金铨.胡金铨谈电影[M].胡维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83.
42胡金铨.胡金铨谈电影[M].胡维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