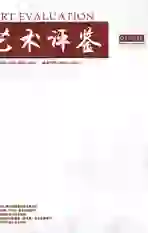理论与实践的碰撞
2019-04-26徐铭睿
徐铭睿
摘要:带着对“田野工作”相关问题的思考,笔者在对“田野工作”中的“局内人-局外人”“主位-客位”两个问题进行拓展研读之基础上,通过对其作以一定的归纳与总结,同时就相关问题提出笔者个人对其的体认与思考,以期将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相关观念及方法更好地运用于笔者个人当下及未来的田野工作中。
关键词:“局内人-局外人” “主位-客位”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5-0175-02
作为一名中国传统音乐(Traditional Music In China)亦或是针对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进行长期性学习的人员,对于“田野工作”(Fieldwork)这样一个词组显然不会觉得陌生。本文缘起于笔者在平日学习生活中的实际感受,当笔者看过、听过一些民族音乐学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后,便不禁陷入对“田野工作中一些常见的观念及方法,怎样结合自身学习对其作进一步的认知”这一问题的思考。那么,我们如何将“田野工作”中常见的“局内人-局外人”和“主位-客位”两对概念,通过与自身研究对象相结合,从而有效地将其运用到个人的“田野”当中?故此,笔者欲对“田野工作”中的“局内人-局外人”“主位-客位”两个问题,从阅读到思考,谈谈自己的体认与观点。
一、“局内人-局外人”(insiders-outsiders):文化身份
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人类学家派克(Pike)提出“局内人”(局内人主要指的是:对于某一种文化内部特征的持有者,也被称之为“族内人”)和“局外人”(局外人指的是:针对这一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外部研究者、考察者等,也被称之为“外来者”)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概念。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后期在人类学当中被许多研究者广泛的运用,在这当中主要是针对研究者以及被研究者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以及所不同的特征进行强调。正如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所认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则是民族音乐学家将自己与所研究对象相互区别的代名词。
对于“局内人-局外人”的具体含义,社会学学者马岚则认为“局内人”主要指的是:对于某一种文化内部特征的持有者,也被称之为“族内人”,这些人大多都是属于同一个文化群体当中的人,这些人都享有着相同的或者是相类似的一些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或者是生活方式、生活经历等,对于一些事物大多都会有着相一致的一些看法。局外人指的是:针对这一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外部研究者、考察者等,也被称之为“外来者”,这部分人大多数都是整个文化群体以外的一些人,这些人与这一群体之间并没有一定的从属关系,并且这部分人与“局内人”之间往往都会有着各不相同的一些生活体验,仅仅只能够依靠外部的一些特点进行观察或者倾听来对“局内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以及想法进行了解。在张伯瑜《局内人与局外人、主位观与客位观的三层定位》一文中提出“局内人与局外人这二者之间不仅仅在身份表现上有所区分,而且他们对于文化上也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看法。”对此观点,欧阳邵清在其文章中发表有相似的言论,“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局内人和‘局外人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对其中的角色进行有效的划分,其所表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对文化进行的理解和沟通方式”。在本文所阐述的内容当中,本文的作者逐渐研究并指出“创作者通过将不同的音乐融入到习俗当中,对其进行整体的考察和探究,也就是使之进入到对音乐进行重新制作,并在音乐的制作和表演过程当中运用音乐思维对音乐文化予以解释,这一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依据‘局内人视角进行探究的过程,是艺术研究者很难能够达到的一种高潮的境界。”
对上述学者的言论,笔者个人以为,身为一名中国传统音乐或是民族音乐学的学习者,在进入“田野”时,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最为现实与最迫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怎样去针对所研究的对象在研究过程当中所处的环境以及文化等特点,在其最大的成就之上去针对“文化隔膜”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消除和规避,进而促使我们通过一个探索者或者说是局外人这样的一个视角将自身文化习惯以及被观察者(局内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习惯表现上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二、“主位-客位”(emic-etic):观察视角
派克(Pike)在其“局內人-局外人”的理论中,还借用了与这对概念相对应的语言学术语“phonemics”(音位学)和“phonetics”(语音学),从而创造了“主位-客位”(emic-etic)的观察视角。
杨民康认为此二者最大的区别,“即针对于前者所注重的往往是语言表现的生理发音以及物理音响现象,所表现出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建立在客观性、偏向绝对性、普遍性等基础之上的。而对于后者而言,其所关注的主要则是能够与语义内容进行有效联系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语音现象,在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划分依据就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特殊时期以及相对性这两种不同标准之上。”著名的人类学家海利斯(Harris)则将emic-etic这对观念视角“看作是建立在‘精神的和‘行为的差别之上。他曾这样说道:‘emic之所以被人类认为是专指参与者大脑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事项;而‘etic则主要指的是:行为流中的那些具体行为,也就是人类身体动作或者是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的因素,比如一个旁观者所觉察到的一样。学者何璇在其《浅论“主位-客位”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文中,将“主位-客位”研究法的要求概括如下:“一个研究者能够真正的‘融入他所研究的音乐环境中去,像一个‘局内人那样去行动与思考,并且又能‘跳出所处的音乐环境,像一个‘局外人那样去分析与研究。”同时,该作者在其文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举反例,“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中,接受专业音乐教育的人,一进入农村就体会到一种现实的差距感,在听了当地村民演奏的民间鼓吹乐之后,不自觉地使用所学的音乐知识与听觉习惯去评判当地音乐的优劣。这样的主观习惯就会使笔者很难‘融入当地音乐文化体系之中,从而不能达到考察的目的。”笔者个人认为,学者何璇在其自身“田野”中的这段“弯路”经历,可使我们对“主位-客位”研究法作以更为形象具体的感知。
综上,笔者个人的观点是,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对观察者观察事物的角度十分重视,而“主位-客位”这对概念视角,从实质上即体现出我们自身观察音乐的角度问题。导师曾以我们都很熟悉的皮影戏为例,为我们讲解这对概念:当我们作为观众在台下所观看到的皮影戏仅是其表面的样态,倘若我们去幕后观看其表演者的实际表演过程,显然会和台下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笔者个人对此的理解是:皮影戏的“台前幕后”从某种程度上(看戏的不同视角)即是“主位-客位”观的一种体现。因而,没有绝对的“主位”与“客位”,关键在于我们自身如何去界定它。倘若以“我”为研究的主体,此时的“我”便居于“主位”,而研究对象居于“客位”;反之,当研究对象为研究主体时,“我”即转变为“客位”,研究对象则是“主位”。
三、结语
简言之,“田野工作”是中国传统音乐亦或是民族音乐学论文完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关键组成部分,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学习阶段。它虽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挑战过程,但却使人乐在其中。已有的几次“田野”经历常给笔者一种“悲喜交加”的感受:你永远不知道调查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当然你也不知道会得到哪些意外的收获!
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在“田野”中,亦或是结束“田野”在对收集到的各种研究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时,都会涉及对文化身份(“局内人-局外人”)、观察视角(“主位-客位”)的认识与思考。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进入田野”之前,对“田野工作”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一定的了解与学习,使我们在整个“田野”过程中始终带有这方面的相关意识,为深入了解研究对象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导师常教导我们,在进行“田野”的过程中,不可将眼光仅仅局限于研究对象本身,一些外围的资料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資料。总之,笔者个人觉得“田野工作”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进入“田野”也绝非是为了“看热闹”,而是透过“热闹”的表象深入挖掘当地人音乐活动中所隐含的地方文化内涵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岚.“局内人”与“局外人”[J].青海民族研究,2009,20(02):35-38.
[2]张伯瑜.局内人与局外人、主位观与客位观的三层定位[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02):44-49.
[3]欧阳邵清.局内局外观民俗·主位客位写文化——对杨沐《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60年》的品题[J].人民音乐,2017,(08):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