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田墨痕新,远去是何人
——追忆中国话剧史论专家田本相先生
2019-04-20宋宝珍
宋宝珍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田本相先生(1932.5.5-2019.3.5)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老所长、话剧史论专家,也是我读硕士、博士时的导师,是我的如父恩师和学术引路人。作为一个学生,我眼里的先生一直都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他步履生风,精神矍铄,似乎在下一分钟就能冲到我的面前,给我布置新的研究任务。但是这一次,风云骤变,2019年3月5日晚上8点23分,田先生突然撒手人寰。宁隔千山,不隔一板,田先生真的云崖远遁——除非在幻想中,在现实里永不相见——痛感永诀,刺骨锥心。
一
1932年5月5日,田本相先生出生在天津葛沽镇。这里离渤海很近,水系发达,盛产小站稻米和鱼虾,是北方的富庶之地。在田先生的自传《砚田笔耕记》里,他谈到家世:其曾祖父田炳周家境贫寒,因欠债无力偿还,便只身逃往东北,后来成为东北军队里的工兵旅旅长。日俄战争爆发,田炳周离开军营,携全家来到葛沽,就此安家。他购置了百十亩薄田,分给农民租种,也不收租钱,只收些粮产,因此,葛沽一带的百姓,送给他家一个匾额“福善之家”。
田先生的祖父田鹤年当年报考了北洋大学俄语系,后来又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大约是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浙江督军卢永祥部下任教官、参谋长等职。后来赋闲在家,家境殷实,无所事事,便抽上了鸦片。田先生的父亲田澍雨,青少年时期曾在浙江读书,擅长国画,精于二胡,喜文弄墨,颇有才华。他曾在葛沽开办书局,成立国剧社。1933年,又在天津创办了《治新日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人占领天津。1938年8月,田澍雨因出版抗日号外,被日军通缉,报馆被查封并没收,工人被逮捕。为了营救这些人,他只好变卖家产。屋漏偏遭连阴雨,土匪又趁乱入室抢劫,致使田澍雨一病不起,于当年11月离世。父亲逝世后,温和善良的母亲带着5个孩子,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
活着不易,这是田先生自小就有的经历。三四岁时,他在自家养荷花的大水缸前戏水玩耍,一不小心栽了进去,要不是家里人发现了朝天蹬踹的小脚丫,把他拽出来,他可能就一命呜呼了。生命无常,父亲去世,他被从小学课堂里叫回家中——家里的顶梁柱坍塌了。他的童年记忆中既有家乡的美好、社戏的红火、河汊的欢游,也有眼里的痛苦、心灵的伤痛。
他热爱自己的小学校,觉得读书很开心,可是上学的路却叫他郁闷——每天他必须经过日军的岗哨,横着刺刀的鬼子逼着中国百姓向其脱帽鞠躬,小小年纪的他绝不屈从,愤恨极了,宁可走很远的路绕过去,也不肯向鬼子低头。他还记得没有月亮的夜晚,母亲会把他从睡梦里叫醒,手里捧着一碗热腾腾的米饭,让他赶紧吃。那是母亲用藏起来的米偷偷煮的,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以私藏军粮为名拉出去枪毙。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稻米,吃不到自己嘴里,却要全部交给鬼子做军粮,换回些粗粮和杂合面充饥。
在失去父亲后,一家人的生计基本上靠地租维持,田先生在五兄妹中排行老三,母亲很倚重他,家里没有口粮了,母亲就让他到七八里外的佃户家去背粮,农民也说没有粮,他无法跟他们理论,只能落寞地、无奈地空手回家。
现实生活的艰难,让田先生向往着没有忧患的世界。少年时期,他喜欢上了听评书,他还记得有个叫马正明的说书人,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出摊。只要交上一毛钱,就可以一直听到散场。他入迷地听此人说《三侠剑》《雍正剑侠图》《说岳全传》。后来,听书不能满足他的兴趣了,他就趁着祖父外出时,找来他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来读。田先生说:“那时还珠楼主的小说是最时髦的,什么《蜀山剑侠传》,有四五十卷,还有《青城十九侠》,也有二十卷,我都看过。再有就是家里收藏的《施公案》《彭公案》等,都是看过的。家里一本《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画得极为精美。”(田本相:《砚田笔耕记》)后来,他到南开大学读中文系,喜欢上文学,大概同这些阅读有关。
1947年,田先生考入河北省立师范学校,从此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他爱读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他还热衷于练习单杠、跑步,练就一副好身体,准备毕业后报考南开大学。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学生们都到校门外看光景,只见解放军整齐地睡在大街上,没有一人闯进百姓家里。两个女战士走来,要求见学校领导,希望校方腾出一间房子,救护伤员。她们十分和气,很有礼貌,不是命令,而是商量。这让田先生对解放军的第一印象太深刻了,与平时见到的国民党官兵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17岁的田先生没有和家人商量,果断退学,加入解放军的南下工作团,随着解放战争的洪流前进。
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田先生随第一批志愿军赴朝作战,在中央机要处任机要秘书。这是他再一次面临生死考验。从北京到沈阳再到丹东,他坐着一辆大卡车跨过鸭绿江,沿途是被战火撕裂的土地和炸毁的树木的碎片。当汽车开上一座大桥时,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紧接着传来敌机扫射的轰鸣声。战士们跳下汽车四处躲避,趴在了泥泞的稻田里。敌机飞走了,他们才发现大桥附近挤满了汽车,他们乘坐的那辆车,竟然一个车轮悬空在桥面上,而轮下是怒涛滚滚,如果再进一步,一车人就都会葬身鱼腹。司机也惊得手足无措,只好求助别的车辆拉拽,但是这样做也很危险,方法不当,可能会导致两辆车同时坠落。终于,有位勇敢的司机站出来,将他们的车子拉回正途。大家一再询问这位司机的姓名、单位,但是那人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战火无情,生死一线。田先生的战友刘参谋,要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汇报工作,汽车经过敌人封锁线,遭到扫射,加足马力闯了过去。停车时人们发现,坐在后排的刘参谋已经中弹牺牲了。田先生自己也曾遭遇生命危险:一个小战士擦枪走火,枪响了,他觉得自己心口一震,人们循声找子弹,却没能找到。中午吃饭时,有战士发现田先生的军装露出棉花,他自己伸手往里一探,在靠近心脏的棉衣夹层里,居然是那颗走火的子弹。
在朝鲜战场,田先生负责电码翻译,工作环境异常艰苦。夏天热得如在蒸笼里坐,冬天冷得牙关错。如雪片般飞来的各种密码电报,需要尽快翻译,为了防备敌方破解,密码本需不断变异,往往是刚刚熟悉的一套规则,转眼就变化出新的样式,这要求机要员快速适应。这种军事训练养成了他对数字的敏感,直到晚年,他扫一眼通讯录就可以记住一些人的手机号码。但是也不无遗憾地说,能快速记忆,也会快速忘记。
田先生在朝鲜的工作相当出色,他发明的一套密码快译法,得以在志愿军中推广,他也因此荣立三等功,并获得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变得成熟、干练、勇敢、坚强,他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遇到了美丽善良、真诚贤德的志愿军女战士刘懿君女士,二人一见钟情,结为一生恩爱、相依相伴66年的模范伉俪。
即使在战场上,田先生也没有放弃他的文学梦想,他把发到单位的《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八一》,以及兵团自己办的《前线》杂志,都细心地保存,有空就看。朝鲜战争停战后,他站在山岗上眺望远方,看到炊烟激动不已,以致诗兴大发,在笔记本中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清晨,
我站在山峦的峰巅;
松树的香气飘来,
松鼠也似乎格外的欢快。
山谷,
是出奇的宁静,
似乎可以听到
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啊,炊烟,
多年不见的炊烟
袅袅地在山谷里升起
是多么美妙的梦幻?!
啊,炊烟,
为了你永远地升起
我愿荷枪
守候这美丽的山峦
(田本相:《砚田笔耕记》)
田先生是热爱和平的,但是他绝不惧怕战争,也特别珍惜志愿军的荣誉。当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田先生愤怒了,他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假设,那些事后的诸葛亮,还是不要当为好。你要研究朝鲜战争,你就要真正地掌握全面历史资料,还原真正的历史情境,还要综合考察其历史使命和历史作用,而不是一叶障目,道听途说,肆意发挥,胡说八道。中华儿女血写的历史,换来国家数十年和平崛起的大好时机,岂是某些人口沫飞溅就抹杀得了的?!”(田本相:《砚田笔耕记》)他性格耿直,作风犀利,眼里不揉沙子,他所拥护和他所反对的,在他心里是非黑即白、没有过渡地带的。
三
1956年秋天,作为一名调干生,田先生离开军营来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报到,走在大中路上,看着清新美好的校园,他的文学梦再度升腾。然而在第二天的开学典礼上,中文系系主任就告诫学生们,这里是培养教授、理论家、学问家的地方,如果有人幻想当小说家、诗人,就请丢掉幻想吧。在他的创作之笔还没有画出痕迹时,迎头而来的是各种课业。《训诂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艺学概论》《中国古典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批令他景仰的老师如李何林、马汉麟、许政扬、华粹深、王达津、孙昌武,等等。

田本相、吴戈、宋宝珍著《田汉评传》
然而校园毕竟不是象牙塔,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除四害”等,都让校园风起云涌。在别的学生忙着给老师贴大字报、大炼钢铁的时候,田先生却忙着读他所能找到的各种文学书。因为有人批判《约翰·克里斯多夫》,他就找出这本书认真读,翻完最后一页,不仅觉得没有什么可批判的,反而被小说的浪漫激情所打动,以致又找来《包法利夫人》《红与黑》《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仿佛是饥渴的旅人找到了沙漠中的清泉,埋头畅饮起来。
1961年,南开大学毕业的田先生被系主任李何林先生留下做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那时他已经33岁,妻子怀孕待产,他想工作,不想读书了。可是李何林先生还是让他坚持读下来。在研究生阶段,他努力做两件事:一是读,二是写,他的一系列评论文章相继在《天津日报》副刊、《河北日报》副刊、《新港》、《前哨》等刊物上发表。当编辑向他约稿时,当稿费到手时,他有一点小得意。有一次,李何林先生找他谈话:“听说你写了不少随笔,以后不要把时间耗费在这里。要把眼界放大些,目标放远些。”(田本相:《砚田笔耕记》)他听从老师的训诫,放下随笔不写,开始继续大量读书。
这一时期,他也开始接触鲁迅先生的著作,他说:“在转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习时,我采取了一种笨办法,我按照文学发展的时序来读选集以及长篇的代表作。就是这样,我读了一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就这样挑着读,也是读不完的。按照时代顺序读的好处,是有时代的关照,是有前后比邻的比较,是有发展脉络的理清,更有总体的把握,从而对一些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有所思考。譬如,我在这样比较阅读中产生一种感想,鲁迅在现代作家之林中,他的著作是耸入云端的高峰。” (田本相:《砚田笔耕记》)他在读完了《鲁迅全集》之后,又阅读了鲁迅同时代人的小说,用一种比较的方法考察鲁迅小说,并从鲁迅小说的风格研究入手,从三个层面来论证其独特价值:沉郁浓重的悲剧气氛、强烈而严肃的讽刺色彩、深厚的抒情音调。最后,揭示这个风格形成的原因。唐弢、王士菁等先生出席了他的硕士毕业答辩会,对论文给予很高评价。
1964年7月,获得硕士学位的田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工作。这所新成立的大学没什么名气,连李何林先生都以为它是通过广播授课的大学。当时这所学校位于复兴门外,田先生到新闻系文学教研室报到后,领了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任务。为了备课,他把一本《别林斯基论文学》翻烂了,并且大量阅读朱光潜、李希凡、蔡仪、李泽厚的文章,这时候姚文元正处于上升势头,可是田先生却不喜欢读他的文章,不喜欢那种文风和习气。田先生的教学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校方评选他为北京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6年3月,他还参加了在西苑饭店召开的隆重的表彰大会。
“文革”当中,田先生的教学与研究被迫中断,由河北望都的小村落到河南淮阳的黄泛区,他不得不去干校参加劳动,他甚至在那里还学会了编筐之类的手艺。赤日炎炎,他曾累晕在大田里,秋收时节扛粮食,他一米六几的身体要扛起一百多斤,以致落下后遗症——腰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
“文革”后期,田先生曾有一次出差,被派到南开大学查档案,调查一个人的历史问题。在故纸堆里,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份右派分子的检举信,此人列出一大串名字,说这些人都有国民党特务嫌疑。田先生自己哥哥的名字赫然在列。他终于明白学业优异的哥哥为什么不能考取钱学森的研究生,原来告密者一个随意的小动作,就这么毁了他人的一生。
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田先生才得以重拾文学研究的旧梦。他依然坚持其鲁迅研究,发表了《鲁迅小说风格初探》《论〈呐喊〉〈彷徨〉与五四小说之比较研究》,等等。1979年,他开始写作《曹禺剧作论》。他说:“大多是在夜间写作,星期天则是最好的突击写作日。而假期,就成为写作的节日了。记得暑假期间,我就躲到办公室里。尽管汗流浃背之时,独自一人,我就脱掉上衣,埋头写作。有时,写不下去,就大声朗读剧本,让自己化身角色,进入戏剧的情境之中。揣摩人物的心理,体验矛盾冲突的力度,品味语言的魅力。每有所得,就独自开心,在办公室里手舞足蹈。”(田本相:《砚田笔耕记》)后来,戏剧出版社社长杨景辉在写作《论郭沫若史剧》中,突患疾病,田先生接过了未写完的章节继续写。那时,他的教学工作也很忙,完全靠开夜车。在“文革”中白白失去的10年岁月,他要夺回来,因此就拼命地写作,常常写到深夜。
在十分紧张的教学和日夜写作的情况下,田先生的身体透支厉害,十分虚弱。1982年到庐山休假时,他突然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急救。西医检查的结果是“植物神经紊乱”,中医诊断说他的体质就像一件到处是窟窿的破衣裳,需要好好修补。
在工作了整整20年之后,1985年2月27日,田先生离开广播学院,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这是谭霈生先生的热诚引荐、徐晓钟先生的慧眼识才的结果。1985年到1987年,田先生在东棉花胡同过着平静、自由的教学生活。这一时期,他开始构想比较戏剧研究的结构框架,开始全面涉猎中国话剧史的宏观视野。
四
1987年,应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院长是文化部部长王蒙)李希凡先生的诚挚邀请,田先生到话剧研究所担任所长,直到2000年离休。他在所长任上,依然是忘我地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话剧进入低谷,演出数量稀少,研究经费不足,研究人员的工资很低。当时流传着一个黑色幽默: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研究院的。可是田先生的词典里就没有消极、等待这类的词汇,他的生命里也没有怠惰、颓唐这些细胞,他确实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人物,就一心一意做他的话剧研究。他从院团研究开始,河北承德话剧团、沈阳话剧团、北京人艺、总政话剧团,他组织召开研讨会,出版论文集,想尽办法把话剧的文脉延续下去。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来话剧研究所工作,在经济大潮席卷下,话剧跌入低谷,偌大个京城,就找不出几个像样的话剧演出。1993年,田先生以坚守阵地、绝不退缩的心态,联合中国剧协、中国话剧协会,举办了“93小剧场戏剧展演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没有资金,他就到处化缘,还争取到商业资本的赞助,此间的重重困难、各种烦难,他都设法解决了。这次活动,可以说为当时暮气沉沉的中国话剧界,输送了一缕清新舒畅的气息。
1996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田先生以他的战略思维和文化胸襟,又是自筹资金举办了大陆与港澳台戏剧同仁共同参加的第一届华文戏剧节,不仅有四地剧团的演出,还有四地学者参加的广泛的学术研讨。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大陆戏剧家、学者与港澳台的戏剧家和学者,增进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增加了学术互信和交流。自1949年两岸隔绝以后,台湾戏剧第一次登上了共和国的舞台,台湾的戏剧人也第一次看到了解放军的话剧演出,闭幕时他们激动地跳到舞台上,对解放军演员说,你们的官兵关系如此亲近如此关爱,我们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撤退台湾了。
田先生对中外戏剧交流所做出的贡献,令人感慨。他厌恶世俗功利的人情交往,主张以坦诚之心以文会友,认为心灵的互动、精神的互通、灵魂的包容才是交友之道。田先生逝世后的几天,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国内外的学人,深情款款地表达他们对老师的感激,还有一些我素未谋面的人,他们说他们是被老师提携、关爱、帮助、指导过的学生和晚辈。在这一刻我才知道,在我这个入门弟子的周围,他有着怎样广大的私淑弟子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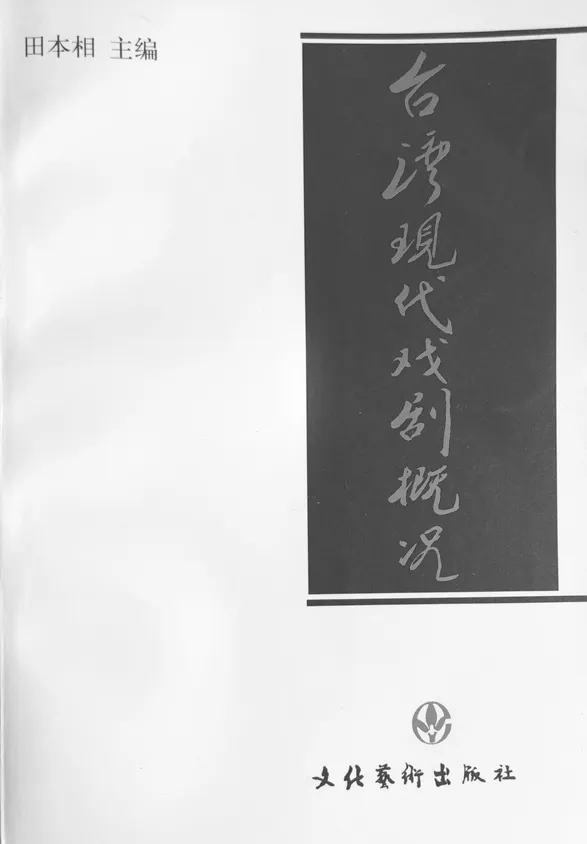
田本相主编《台湾现代戏剧概况》
田先生一直说他是话剧界的友人,我的理解是,一个研究者应当与他的研究对象保持理性客观的距离,实际上他对很多的话剧艺术家,充满了感情上的亲近和理念上的景仰。他跟很多人交往不多,但视为精神上的知己。
澳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朱寿桐说:“田先生一生耕耘戏剧学术,营构戏剧交流平台,堪称中国戏剧乃至汉语戏剧界的一株参天梧桐。他的著述涵盖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的每一个方面,从戏剧文学,到戏剧艺术,乃至戏剧舞台、戏剧团体,成为当代戏剧学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还遍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他还勤勉地进行散文和戏剧剧本的写作,其学术和文学业绩像高大的梧桐树那样盘根错节。田先生倾20多年的心血缔造并领导了连接台港澳及内地戏剧节的华文戏剧平台,每两年笙箫轮番,精彩纷呈,凡十届硕果累累,弦歌连绵。”(朱寿桐:《又见梧桐》,《羊城晚报》2019年3月19日)他是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热爱话剧的人们心中永远的“田老爷”。
田先生一生的功绩很多。1981年《曹禺剧作论》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曹禺剧作的学术专著,很快就脱销并再版印刷,累计印数上万册。1984年此书获得“1984年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是新时期戏剧理论著作的第一次全国性评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田先生与曹禺先生的交往日益密切,读了田先生的评价,曹禺引用《诗经》中《巧言篇》里的两句诗来表达他的心情:“他人之心,予忖度之。”这是一个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最好的默契、最佳的状态。
田先生事业心强,不为杂事分心,不为时潮所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他总是骆驼坦步,稳扎稳打。研究曹禺,就从剧本精读、史料收集、作家访谈、细节阐释认真做起,形成一整套研究成果,出版《曹禺剧作论》《曹禺年谱》《曹禺传》《曹禺评传》《曹禺词典》《中外学者论曹禺》《曹禺研究论集》《曹禺代表作》《曹禺全集》《曹禺研究资料》等一大批史料翔实、构思恢宏、视角新锐、文采飞扬的学术著作。
田先生曾经说,他与曹禺先生成为精神上的知己,并且开始研究曹禺戏剧,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家庭居然是如此的相似:天津是他们共同的家乡,他们的祖上都是行伍出身,发迹以后都是置地修屋,闲居在家,长辈都是威严、专制的,他们也都早年失怙,家道中衰。田先生回忆说,曹禺先生“谈得那么口无遮拦,谈他的家庭,谈他自己的经历,谈他的剧作,我深深感到,他真的是把他的心交给我似的。我看过他以前的访谈记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率真畅快,这样深挚动情,这样交心”。甚至夏天天热,有的时候谈得开心,曹禺就脱去了外衣,真是不拘小节,肝胆相照。可是每当谈话结束,曹禺先生一定要蹒跚着把田先生送到门外电梯口。

田本相著《曹禺剧作论》
他们之间的谈话断断续续延宕了20年,以致后来有人在采访曹禺先生的时候,曹禺先生会说:“你去找田本相吧,我的事情他都了解。”田先生后来出版了《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曹禺的女儿万黛、万昭在田先生去世后,在唁函中说:“我们虽然生活在爸爸身边,但是他很少向我们谈他的剧作生活,特别是他的内心世界,田老师的曹禺研究引发了爸爸谈话的极大热情,赢得了爸爸的心,记录田老师与爸爸交谈的曹禺访谈录,大概是爸爸留在世上不可再生的心灵轨迹,它是无价的,因为还有谁能够在爸爸活着的时候,让他如此‘掏心窝子’,谈得这么多、这么系统、这么深入、这么坦白呢?我们衷心感谢田本相老师,会永远铭记他的伟绩!”
田先生做郭沫若史剧研究、田汉研究、新时期戏剧研究,都不是一般性地完成一部著作,而是具有宏大的学术抱负和高远的学术追求。他在话剧史学方面的建构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如《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新时期戏剧述论》《中国戏剧论辩》《中国百年话剧史述》,等等。9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以280万字的篇幅,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史料最为完备、论述最为系统的话剧史著。此后田先生为推动话剧研究的深入,继续整理出版了《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书系》38卷、《民国时期话剧杂志汇编》100卷,又开始着手进行中国话剧导演史、表演史的研究。生命不息,耕耘不止,田先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话剧的思索与研究,直到2018年10月,他还在《艺术评论》上发表了他最后一篇学术论文。
在学术方面他提出过很多重要的观念,比如,现当代文学一体化、诗化现实主义、文学史的哲学思考、二度西潮、比较戏剧观念、当代话剧思想的贫乏等,这些观点,对于把中国话剧研究引向深入,必将产生重要的思想启示意义。
五
田先生是一个真正有学术理念的人,他把话剧研究进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春节前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谈,我从一个会议上赶到医院,他拖着只有七八十斤的身体,气喘吁吁地跟我谈,话剧史当中的很多问题,还没有深入下去。他惦记着他所主编的话剧艺术学丛书何时出版,甚至于想把学生们奉献给他的养命钱,拿出来做出版费。田先生到最后时刻,大概也没有想到生命会结束,他的求生欲望很强,因为在话剧研究方面,他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他特别配合地做化疗、放疗,满怀信心地告诉我肿块在缩小,人人都觉得难以下咽的医院的餐食,他也告诉我说粥是好喝的。他寄希望于在病床上躺上一段时间,然后就能起床,疾走在人世间,坐到他的电脑前继续工作。
从2017年3月发现了肺部病症之后,他不是放弃工作好好休息,而是以时不我待的心情“变本加厉”地拼命做事情,《中国话剧艺术通史》9卷本出版后,他又有了新的规划、新的方案,要研究中国话剧的导演史、表演史,我曾经劝说老师放下执念,岂不知是我没有他那样坚定的信念?他的微信一直都很活跃,抒发自己的学术之见,转发别人的戏剧观点,直到2月10日,他还发了最后的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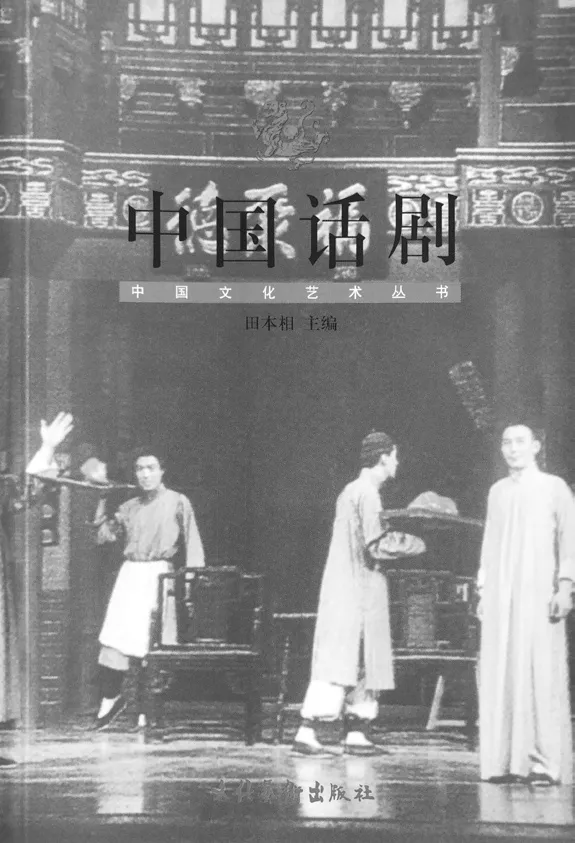
田本相主编《中国话剧》
田先生当过兵,有军旅作风,他厌恶拖泥带水,喜欢雷厉风行。他曾经说,如果他写自传,题目就叫《从士兵到教授》,我以一个晚辈的顽劣戏谑和恶作剧心理,开玩笑说,干脆就叫《武夫学者》,他也不生气。他确实是把学术上的攻坚克难,当成是军事上的争城掠地,瞄准目标一个一个地攻克,找准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进。
田先生意志如钢,从不示弱,在医院里,他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气喘吁吁地说话,说不了几句,大概就累了,他让我叫护工,一个壮实的男护工来了,伸手要抱他上床。他摇摇手制止,跟我说:“你先出去一下。”他依然自尊、要强,不想让我看到他的羸弱,他是像个孩子一样被人“抱”上床去的。
大年二十九,我去看望师母,说起田先生会不会回家过年,师母说还没法确定。除夕之夜,我给田先生发短信,祝他新春大吉,问他回不回家过年,他用短信回复:“在家里,你来吃饭。”我还蛮高兴,以为他还能撑很久的时间。可是等我赶到他家的时候,那里没有他的身影,医生不允许他出院。
田先生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张先教授在剧场里碰到我,他说:“当初《中国话剧艺术通史》结项时,打印稿交到了我的手里,我认真读过了,这部话剧史因为体量大,没人认真读,它的学术价值被大大低估了。以前没有、以后也很难有可以与其比肩的话剧史著作了。”中央戏剧学院的郭富民教授干脆在微信里发声:“中国话剧研究进入了没有田本相的时代。”我是跟在田先生身边最久的学生,由师生成为了同事。有一位话剧院院长曾经问我:“宝珍呀,咱们这个博士啥时候能毕业呀?”我说:“毕不了业了,学习成绩不够好,老师判我终生留级呢。”田先生的集体项目,我多半都是参与者,我不敢夸耀那些学术成果如何了得,夸老师吗?他一直教训我为人要低调;夸自己吗?不敢,想一想都觉得可笑。我还能说什么呢?其实我错过了好好与老师对话并且“掏出他心灵的宝贝”的机会,也错过了在他生前认真研究他的学术的机会。
台湾文化大学王士仪教授曾经给田先生写下了两句诗:“砚田无晚岁,戏论唱高言。”然而我想说,砚田墨痕新,远去是何人?您的永远也写不完的半卷书,您就这么放下了吗?那飘向天国的身影,真的就是您吗?
长歌当哭,无以为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