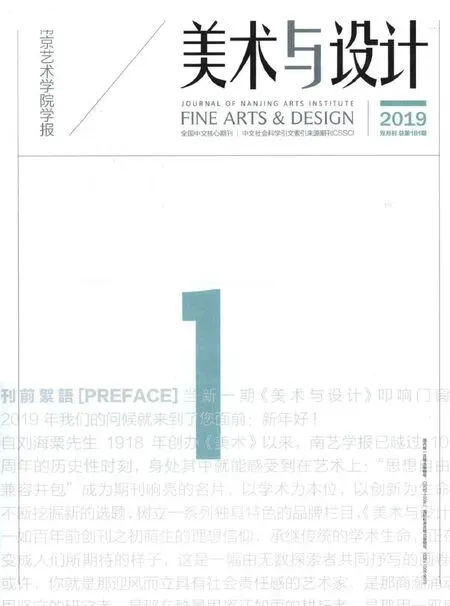城市、建筑、造像:缅甸室利差呾罗古城遗迹初探
2019-04-02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虹口200083
张 翔(上海外国语大学 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 虹口 200083)
在东南亚中南半岛大地上,曾长居于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西方学者称之为“下缅甸”地区)的缅甸先民,据悉与古代中国云南的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他们既骁勇善战又善于发展农耕,在缅甸中部与南部地区形成了稳定的经济与持久的政权。他们是缅甸历史上著名的“骠国”人。骠国都城在今缅甸卑谬附近的室利差呾罗,那坚实的城墙、逐水的城址、宏伟的建筑、残损却依旧不失优雅的千年造像,都是承载缅甸古都室利差呾罗历史的见证。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早期缅甸及室利差呾罗古城
关于缅甸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为“西夷”之说[2]。“西夷”是汉代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余定邦先生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提及的“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中的“西夷”特指的是缅甸与印度一带。与印度相连的缅甸地区,西北部的掸邦高原一带可能性较大,毕竟这里在汉代曾有“西南丝绸之路”贯通中印交通线。《汉书》中的“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指的都是今缅甸及其周边一带,尚有争议。[3]城池林立、多国并立发展是东南亚早期国家发展的“共性”。
郦道元《水经注》引竺芝《扶南记》:“林阳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举国事佛。有一道人命过烧葬,烧之数千束樵,故坐火中。”[4]可见当时缅甸全国佛教的盛行。“道人”在此处有两种解释,一为僧侣,一为婆罗门。而在考古发掘中,确实在缅甸室利差呾罗一带发现了大量石瓮,均做丧葬用途。[5]
关于“骠国”,《后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拒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来往通聘伽罗婆提等二十国,役属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罗君潜等二百九十部落。”[6]描述可知,此期的骠国地域广阔,与其交往国家、部落众多,纵横一时。关于缅甸更早的记载,只能散见于汉晋时期的一些史料中。
贺圣达先生认为,公元6世纪以后,缅甸骠国逐渐强大起来,并定都于室利差呾罗,有“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见者三十二”,“属国十八”。[7]
熊昭明先生认为,公元9世纪以前缅甸境内建有骠国。城址有毗湿奴(Vishnu-city,也写作Peikthano,Beikthano,Peikthano-myo(myo是缅甸语城市之意)或Panthwa[8]、汉林、室利差呾罗、迈莫、达格拉等地。年代从广元1世纪晚至9世纪。毗湿奴城代表了骠人的早期文化,室利差呾罗古城代表了骠人的后期文化。[9]
韦健锋认为,上世纪20年代在骠国古城室利差呾罗钦跋拱(Khin Ba Mound)发现了20张金贝叶,贝叶上抄有用骠文写的巴利文三藏经。他认为这些字体源于印度的婆罗米文字,并出现婆罗米文与表文混写的经文,而越到后期表文日趋成熟,婆罗米文字式微。自婆罗门教、佛教传入缅甸后,梵文和巴利文又作为新的文字流行。[10]

图1 室利差呾罗古城位置

图2 室利差呾罗灌溉发展的四个阶段
关于地名室利差呾罗与达耶其达亚,达耶其达亚古城是骠国曾经古都卑谬古称,即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称之为室利差呾罗。[11]这也跟笔者所整理的出土文物地点吻合。陈序经先生在《骠国考》中援引冯承钧译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文段也证实了这一点。[12]“从此东北大海滨山谷中有室利差呾罗国。次东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国。次东有堕罗钵底国。次东有伊赏那补罗国。次东有摩诃瞻波国,即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阎摩那洲国,凡此六国,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风俗壤界,声闻可知。”季羡林先生认为,室利差呾罗,梵文Śrī Ksetra音译,《南海寄归内法传》译为室利察呾罗,即缅甸故都Thare Khettara①即前文提到的达耶其达亚(Thayekhittaya)古城的另一种写法。,在今下缅甸伊洛瓦底江畔骠蔑(Prome)(也写作卑谬),室利差呾罗是“繁盛之地”的意思[7]。
以上,我们对缅甸早期历史或可形成大致“碎片化”印象:第一,缅甸早期的地域版图多国并立,并有各自政权;第二,与中国魏晋时期同期的缅甸林阳国“举国事佛”,佛教大兴;第三,中印缅三国早期有交通,即有贸易、文化的传播通道;第四,室利差呾罗是达耶其达亚的另称。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于“繁盛之地”室利差呾罗古城的记载十分匮乏。
二、室利差呾罗古城的布局
“对于‘起源’的执着,是治史者的基本姿态”。[13]探寻室利差旦罗古城的“样貌”成为了解缅甸早期历史的重要途径。古城位于伊洛瓦底江流域(图1),古城河网密布,一方面成为室利差呾罗发展的重要交通条件,一方面也是古城重要的灌溉系统。Janice Stargardt先生认为,室利差呾罗古城的灌溉系统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公元6世纪到公元8世纪、公元9世纪[14](图2)。古城的城市格局以王宫遗址和制铁遗址为中心随时间而使城市逐步扩展,具体包括:运河开槽、城郭修筑、塔寺修建等方面内容。时代变迁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古城中央王宫西北侧的铸铁遗址,稳定的生产工具铸造地或为古城文明形成提供着持续的生产动力。

图3 室利差呾罗古城图

图4 室利差呾罗古城
从两张平面图来看(图3、图4),古城位于河网密布的伊洛瓦底江流域,古城城郭呈“C”形布局,除东部城郭由砖砌城郭外,其他三面由多层城郭组成。东郭之外有一周长约6千米的人工湖,Thein Lwin,Win Kyaing,and Jaince Stargardt几位研究者在文中称之为“大东湖”。与之相对的“北湖”与“南湖”分别置于城内的北部与南部。南部靠城墙处零星散布几个小型人工湖。这些湖泊均被纵横交错的人工运河相连接并一直绵延至城外。城郭与运河的交汇处即设出入城的关卡——城门,一共是十二道城门。十二道城门的数字被缅甸后世王朝所沿用[15],或有特定含义。人工运河与东郭交汇处不设城门,在东部砖砌城郭南北两端与多重城郭的南北端交汇处分别设一城门。城内外人工运河河道虽纵横密布,分区不明显,纪念性建筑散落于城内、城外。城郭、运河共同构筑的防御性属性值得深入探讨
在图3中笔者分别用黄色、绿色、蓝色、红色四种颜色分别标注了王宫、居民区、寺庙、窣堵坡四种功能建筑的分区。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王宫位于室利差呾罗古城中心偏西南位置,王宫东面是居民区的主要分布地,也是河流交汇之处。古城北面和西面也散落有居民区,总量不及王宫东面。王宫与其东面居民区中间由南向北纵向分布了四座印度教神庙,古城城墙外南部分布了三座印度教神庙。佛教窣堵坡分别在古城东南西北各面坐落有一座,城内无佛教窣堵坡。

图5 室利差呾罗古城居民区分布示意
从室利差呾罗古城整体上看(图4),有宗教建筑遗迹、墓地、护城河、城墙、人工运河、农田、王宫、铁矿遗址、人工湖等。密布的人工运河为室利差呾罗古城内外的农业灌溉提供了充足水源,也有利于交通便捷。护城河及城墙重叠围合古城区域,坚实的防御工事是古城重要性、文明性的侧证。王宫西北角有一片东南——西北走向的椭圆形区域的铁矿炉遗址,这是室利差呾罗古城生产力的重要象征。古城的王宫西边以及古城外南部、北部、西北部均有墓地或与丧葬有关的区域,南部最多。有意思的是,凡是有墓地的地方就有寺庙和窣堵坡在其周围营建,二者之间有很明显的关联。结合图3、图4我们发现居民区的布局大致分布在水源集中的河流、湖附近(图5)。
以上我们大致可以总结:第一,古城布局带有“随意性”但又有城市布局的规划、“章法”。古城的城墙与壕沟多重层叠、没有统一的曲度,城址整体面貌与同时期的中国晋唐城址相比“随意”很多,但居住区、墓地区域、农田区等地方都又有明显的区块化处理,又有其“章法”。第二,佛教已然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精髓”。现存的寺庙与窣堵坡遗址还有十余处,佛教成为室利差呾罗古城十分重要的文化“精髓”,也反映了当时居民“举国佛事”的精神生活面貌。第三,发达的铁器为古城居民提供着赖以生存的生产工具,支撑其经济与产业发展。古城中的铁矿遗址是古城发达的生产力的表现,或正因为此才成就了“室利差呾罗”梵语本意——“繁盛之地”的美名。第四,密布的河网,是古城人居生态环境、交通系统、给水排水系统的共同载体。古城位于伊洛瓦底江畔,密布的河网方便城内居民的生活起居用水需求,同时也给予了发达的交通系统。河网、城中的“南湖”与“北湖”以及城东外的“大东湖”也为旱涝时期给水排水提供保障。
三、室利差呾罗现存的建筑遗迹
室利差呾罗古城中的建筑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塔、二是寺庙。
塔,印度人称之为窣堵坡(Stupa),是安放佛祖释迦牟尼佛骨舍利之处。印度著名的窣堵坡有桑奇大塔、阿玛拉瓦提大塔、巴尔胡特大塔等。古城城墙外西北、东北、东南、以及正南的城墙外分别是三座窣堵坡建筑遗迹——帕亚基塔(Payagyi Stupa)、帕亚玛塔(Payama Stupa)、迈锡格亚拱塔(Mathigyagon Stupa)、包包枝塔(Bawbawgyi Stupa)。四座塔(窣堵坡)造型相似,底座低矮的方形台基,上方是呈圆柱向上耸立收分的覆钵形构造。与印度窣堵坡最大的区别在于,外形朴素,向上高耸的造型与印度低矮的造型差异不小。而这种高耸、向上收分的窣堵坡形式却成为缅甸后期佛塔造型定式的一种,特征十分突出。

图6 包包枝塔

图7 答枚克佛塔

图8 迈锡格亚拱塔遗址
四座塔(窣堵坡)至今受人崇拜,保存最好的要属包包枝塔(Bawbawgyi Stupa)(图6),通高约50米[16]。其塔身高耸,呈圆柱形,表面残存釉彩,两侧收分极其细微。台基由五层低矮的圆坛相叠而成,逐层向上缩小,部分已埋藏于低下,最上一层有通往塔内的入口。[17]包包枝塔一般认为其为公元5至7世纪时期建造,恰好是室利差呾罗古城发展到鼎盛的时期。这种塔身耸立、略带收分的类似形制的窣堵坡与印度北方邦的答枚克佛塔(Dhamekh Stupa)(图7)形制类似。答枚克佛塔(Dhamekh Stupa)是建于公元500年左右的佛塔,也是印度至今保存下来的少量的阿育王时期建筑之一。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对答枚克佛塔(Dhamekh Stupa)有详细记载:“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无忧王建也,基虽倾陷,尚余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余尺。石含玉润,鉴照映彻。殷勤祈请,影见众像,善恶之相,时有见者,是如来成正觉已初转法轮像处也。”文段中所述“石窣堵波”就是讲的鹿野苑的答枚克佛塔(Dhamekh Stupa),高约“百尺”,与现存高度39米相仿。“石柱”指的是阿育柱。[18]二者之间的详细关联、传播途径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古城东南部、正北方以及西北方的迈锡格亚拱塔(Mathigyagon Stupa)、帕亚玛塔(Payama Stupa)、帕亚基塔(Payagyi Stupa)同样是现存的塔址所在(受损程度不一)。迈锡格亚拱塔(Mathigyagon Stupa)是这三座塔中受损较为严重的一座,具体建造年代不详,目前只剩下约三米高、十五六米见方的台基(图8)。台基四面均有供人上下的台阶。台基上有砖砌圆环状建筑体,似覆钵状塔底。方形台基、圆形塔身的组合类似于印度教神庙建筑与佛教窣堵坡形式的组合。正北的帕亚玛塔(Payama Stupa)建筑形制与包包枝塔类似(图9)。古城西北面的帕亚基塔(Payagyi Stupa)形制与前文所述的包包枝塔、帕亚玛塔(Payama Stupa)形制类似,年代约公元5-9世纪。这几座塔的形制大致类似,由基座与塔身两部分组成(迈锡格亚拱塔(Mathigyagon Stupa)由于残损无法了解其原状)。高耸的塔身,成为这一时期塔这种建筑的主要建筑形态,即高耸的、逐渐向上收分的、似圆锥状形态;印度教建筑对于塔的影响也成为其特征的一个写照,如迈锡格亚拱塔(Mathigyagon Stupa)的基座样式。

图9 帕亚玛塔
佛教寺庙方面,印度教神庙建筑对其影响更为直接。如前文所述,室利差呾罗古城中现存的寺庙建筑有七座,分别是古城王宫东面的帕亚堂寺(Payataung temple)、施温扬宾拱寺(Shwenyaungbingon temple)、东谪古寺(East Zegu temple)、西谪古寺(West Zegu temple),以及古城外南部的亚汗达古寺(Yahandagu temple)、贝贝寺(Bebe temple)、拉姆耶斯那寺(Lemyethna temple)①中文寺名由笔者直译。。这些寺庙均为佛教寺庙,但从造型上看均采用印度教神庙的造型样式。比如方形基座演化成为四壁墙壁,建筑顶部收分或成类似窣堵坡形式的覆钵形顶。建筑整体形制类似中国佛教建筑中的四门塔形制。室利差呾罗古城的这些寺庙形制虽跟印度教神庙有一定关联,但与印度教寺庙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具有真实的实用性,即有一定的建筑内部空间供进行纪念性活动,从建筑空间营建方面看,室利差呾罗的寺庙建筑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建筑内部有独立空间并供人进入进行纪念性活动。如拉姆耶斯那寺(Lemyethna temple)四壁分别有门洞可进入建筑内部,内部中心有柱,柱上有弥勒佛的雕刻,总体形制类似敦煌石窟中的中心柱窟(图10、图11)。这些佛教寺庙建筑与城内外的塔一样,一般以砖砌方式构筑,因此建筑外立面通常为砖面材料,而印度教神庙建筑一般在建筑外部饰有繁缛的雕刻,通常不做内部空间。第二类,建筑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完全隔绝,人不能进入建筑内部。如贝贝寺(Bebe temple),建筑四面围合,只做门型建筑装饰(图12)。第三类,建筑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隔绝,但有建筑有做半封闭空间。如帕亚堂寺(Payataung temple),人虽不能进入建筑内部,但有向内部延伸的半封闭空间(图13)。这些寺庙建筑年代相较于塔(窣堵坡)建筑年代稍晚,约为7至13世纪左右。

图10 拉姆耶斯那寺

图11 拉姆耶斯那寺中心柱弥勒佛

图12 贝贝寺

图13 帕亚堂寺
相较于塔(窣堵坡)而言,室利差呾罗的寺庙建筑形制更加“规则”,建筑形制确定,吸收印度教建筑形制基础上创造出符合纪念性建筑功能要求的寺院建筑形制。另外,从建筑构件来看,向上收分的建筑顶部、顶部与建筑立面的叠涩、连接建筑内外的门洞拱券、窣堵坡覆钵形建筑构件的借用等都是室利差呾罗佛教寺院建筑成熟的标志。建筑技术的进步与成熟也为建筑风格走向独立(脱离印度佛教与印度教建筑风格)提供了技术前提。

图14 坐佛像

图15 坐佛像
四、室利差呾罗古城出土的造像
室利差呾罗古城出土的造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佛教主题的造像,另一类则是印度教主题的造像。从目前出土的文物看,年代均在公元4世纪以后。佛教类主题造像出现得最多的品类是坐佛像、佛三尊像、有佛陀形象的舍利容器以、菩萨像以及饰有窣堵坡形象的工艺品造像;印度教类主题造像多为毗湿奴造像、毗湿奴与吉祥天女双神像、印度教三神像(毗湿奴、湿婆、梵天)。除此之外,还出土了不少带有巴利文铭文的石碑。
在佛教主题的造像中,坐佛像是这一时期出土得最多的品类(图14)。室利差呾罗的这一批坐佛像都有着类似的造型,即躯体纤瘦,通体衣着紧贴身体、腰部饰腰线,结跏趺坐于台基之上,部分台基处有骠文所撰写的铭文,佛像头部基本上遗失。这种佛像的造型样式不免想到印度笈多王朝后期的造像,如阿旃陀石窟中的坐佛形象。而这种通体贴体、躯干纤瘦的佛像造型也是10世纪以后的泰国佛像造型的主要特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坐姿形态类似,造像手法与上述相左的一种,即身材粗壮、造像风格相比前一种要“粗野”很多,多施触地印(图15)。关于两种坐佛风格明显差异的成因,值得深入探讨。
发现于包包枝塔附近的这件造像碑是这一时期佛三尊造像的典型(图16)。佛陀坐于莲花座上,双手持钵,佛陀左侧人物形象已迭,右侧人物形象左手举起,似施无畏印。佛陀座椅顶部的摩羯鱼形象清晰可见[19]。该件造像虽为三尊像,但佛陀形象较为纤瘦,与前文所提及的坐佛像第一种类型相似(图14)。此外,佛教三尊造像中,佛陀与供养人的组合也是这一时期较为多见的一种样式(图17)。

图16 佛三尊像

图17 佛三尊像
装饰有佛陀形象的舍利容器也是室利差呾罗佛教出土文物中比较常见的一类。发掘于室利差呾罗古城的舍利容器盖板(图18)浮雕上的窣堵坡形象与包包枝塔外观形制极为相近。这件盖板现藏于摩萨(Hmawza)博物馆,通高 162.6 厘米,宽 139.7 厘米[20]。窣堵坡自下而上分别为须弥倒座、窣堵坡塔身、顶层华盖三部分形象组成。须弥倒座与窣堵坡塔身之间为五个并排排列的佛龛,佛龛中拱贤劫四佛与弥勒菩萨形象[20]。所谓贤劫,即包括释迦牟尼在内一起出现的现在劫,与过去庄严劫、未来星宿劫对应。贤劫,即现在的大劫,在贤劫中,有一千尊佛出世,故称贤劫,又称善劫。[21]均施禅定印坐于佛龛之中。顶部华盖形象有残损,盖板右侧余留的华盖形象推测为双层华盖。窣堵坡两侧分别有一条自塔顶垂下的幢幡。贤劫四佛,是上部座佛教中常表现的一种样式;弥勒,确实大乘佛教中常表现的一种造像,这种造像一直持续到公元9世纪的室利差呾罗晚期。可见,大乘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图18 舍利容器盖板浮雕

图19 银鎏金舍利容器
与舍利容器盖板相类似的银鎏金舍利容器(图19)具有同样的“功用”。该舍利具通高58.1厘米,直径40.5厘米。据舍利盒底部的巴利文铭文显示,器表的四尊佛分别为佛陀释迦牟尼、拘留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22]这四尊佛均为过去佛,拘留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均为贤劫时出世的佛,均举行过一次集会说法。其中,迦叶佛是释迦牟尼的前世之师,曾预言释迦牟尼将来必定成佛。释迦牟尼佛、拘留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与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共同称之为过去七佛,也将前四者称之为过去四佛[23]。关于过去四佛,霍旭初先生认为,从七佛到四佛是印度佛教信仰的一种逐渐转变,这种转变在4至7世纪时期的印度较为明显。从地域上看,除了印度,四佛信仰在中国、在古代的龟兹地区均存在[24]。缅甸达耶其达亚古城发现的这件四佛形象的银鎏金舍利容器从地域上拓展了四佛信仰的影响范畴。舍利器具四面分别为四佛坐姿形象,佛与佛之间是立姿的迦叶、阿难等弟子形象。四佛座椅分别是摩羯鱼形象,摩羯鱼是印度教艺术中的形象,与佛的形象共生出现显示了中南半岛上的宗教艺术文化的包容。顶盖上方残损的树干据说为菩提树的树干[25]293。

图20 金写经经板
公元4至5世纪左右的这件金写经经板(图20)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具有明确佛教“艺术身份”的作品。写经,即书写佛经的意思。该写经经办每片高3.8厘米,通体黄金。板面上雕刻有巴利文佛经。经板左右分别有一圆形小孔,以穿线成册便于携带[25]206。该金质写经经板的出现,展现了缅甸早期对佛教极高的尊崇。而其“便携”的特点,也展现出该类“器物”当时使用的频繁程度,也可看出使用者身份的高贵。

图21 四臂观音形象
在包包枝塔附近出土了一尊四臂观音形象(图21),总体造像的原样得以保留但部分有残缺。其繁缛的服饰装饰、扭曲的身姿、四臂形象是这一尊造像的最主要特点。从造像的特点来看与印度波罗样式接近。四臂形象,也令笔者关联到印度教神像毗湿奴,从四臂毗湿奴到四臂观世音是否存在义理上的融通进而使得造像的融通,值得深入探讨。
印度教造像同样是室利差呾罗古城造像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城出土了大量关于印度教主题的造像,既反映了缅甸早期佛教文化传入、形成的过程中印度教的角色与贡献,也反映了室利差呾罗信众对古城多元的宗教、艺术形态的包容“心态”。

图22 双面造像碑

图23 印度教三神像

图24 毗湿奴与吉祥天女

图25 金翅鸟
出土于古城摩萨地区的双面造像碑(图22)就有着明显的印度教艺术特征,年代为公元4至6世纪[26],造像碑中三个人物形象并排作行走状。中间的人物形象略大,位于前;两侧略小,位于后。中间人物形象所持的神剑(也有说神棍)形象,两侧人分别所持的善见神轮形象、金翅鸟鸟头形象,与印度教神像的毗湿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善见神轮、神剑这是毗湿奴四臂所持的重要法器之一。金翅鸟是毗湿奴的坐骑。当然,这尊造像碑中间的主尊形象是否是毗湿奴还值得探讨,毕竟毗湿奴的最典型的四臂形象并没有在造像碑上出现。此外,类似的三尊造像还有印度教三神像造像。印度教三神像指维护神毗湿奴、创造神梵天、毁灭神湿婆。该印度教三神像为6-9世纪时期的作品(图23),出土于室利差呾罗古城的卡拉堪村(Kalakan Village),体量大小为38×36×10厘米。三尊造像均坐于莲花台之上,中间造像为毗湿奴,左侧为湿婆,右侧能看见三张脸(实际上四张脸,后面的脸被挡住)的梵天。该尊造像的独特之处在于,三尊造像均为四臂形象,且均坐于莲花台之上,这是印度教三神像造像中少见的(印度不多见,印度教艺术最兴盛的东南亚柬埔寨也不多见)。
印度教神像造像中,男女神也是一类常见的造像母题。室利差呾罗古城中出土了一件公元6至7世纪的毗湿奴与妻子吉祥天女(也叫拉克希米)的造像碑(图24)。该尊造像上部造像已残损,毗湿奴与其妻子吉祥天女的头部已佚。造像残高101.6厘米,宽63.5厘米,石质材料,体量适中。塑像右侧的为毗湿奴形象,四臂中残损的三臂分别持法螺、法轮、神剑等法器形象,站立于坐骑金翅鸟之上。左侧的吉祥天女手持莲花立于莲花座之上。造像整体上类似于浮雕,体积感不如印度艺术中的立体(如桑奇大塔门坊上的女神像)。毗湿奴与吉祥天女腰间所系的服饰是东南亚古国常见的服装样式。该造像的意义在于其较大的体量,证明这件造像使用场景很可能为“公共性”艺术品性质。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印度教整体的接受程度。类似的印度教男女神像,除了毗湿奴与吉祥天女形象,暂未发现有其他形象的组合。除此之外,金翅鸟的单尊造像在这一时期出现(图25),年代为5-7世纪。该造像整体残损严重,扭曲的身躯是印度教造像的典型特征之一。
不论是佛教造像还是印度教造像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室利差呾罗古城对待不同文化的包容。金写经经板、双面造像碑、毗湿奴与吉祥天女造像碑、四臂观音这些物质遗存,事实上同建筑一样,反映的是室利差呾罗早期佛教艺术与印度教艺术的长期并存发展,并在骠国时期的室利差呾罗地区完成造型样式的“本土”转化。毗湿奴与吉祥天女造像碑腰间所系的服饰就是例证。从信仰层面来说,宗教艺术的“杂糅”侧面反映的是当时骠国社会大众及王室对印度文化的接纳程度与包容程度。西方学者对东南亚文化的中心观点是“印度化”[27]。在笔者看来“印度化”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东南亚先民对印度文化的包容性接纳,而非单一性。从目前研究来看,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究竟哪种艺术更早地进入并影响了伊洛瓦底江这片流域,但可以肯定的是佛教艺术、印度教艺术两种艺术形态的“杂糅”对于东南亚早期宗教艺术的形成及后世发展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五、结论
总而言之,不论是城市、建筑,还是宗教造像以及工艺品,都给观者以震撼。这种震撼一方面来自于文化遗产的震撼,一方面来自于强大的人类文明的震撼。笔者从城市、建筑、造像及工艺品三方面总结室利差呾罗古城物质文化遗迹的意义:
第一,从室利差呾罗古城城市布局看,其蜿蜒的城墙,纵横的运河,看似不规整的居民区分布给人更多的“随意性”“无序感”。跟中国同时期(唐宋之间)里坊制下的古城布局差别较大。而事实上城址依山而建,利用伊洛瓦底江水域方便古城城民农业灌溉及生活取水、防御,王宫布局于古城中央显示其重要的地位,各类型建筑分区布局(寺庙建筑与塔有明显的分布“界限”),却又实实在在反映了室利差呾罗古城布局的规划性、艺术性。这是古城的特点。
第二,从室利差呾罗古城的建筑方面看(主要建筑遗存是佛教寺庙与塔),一方面受到印度文化(佛教与印度教)的影响,却又保持独立发展的建筑形制;另一方面对空间的利用灵活多变,形成类别化的建筑空间营建方式(寺院建筑)。不论是佛教建筑塔(窣堵坡)还是带有印度教风格的寺庙建筑,印度文化始终是影响缅甸室利差呾罗古城的最直接因素,但从建筑风格上看却又保持独立。比如室利差呾罗的佛塔建筑,虽然与印度答枚克佛塔(Dhamekh Stupa)高耸的形制有一定外形关联,但细节部分还有诸多不同。室利差呾罗的佛塔外观更加简洁、塔身与塔基有明显的视觉上的结构“界限”。佛教寺院建筑方面受印度教建筑影响却又形成自己的建筑风格,比如印度教建筑大面积外观装饰在室利差呾罗的寺庙建筑上却很难看到。此外,如前文所述,室利差呾罗的寺院建筑形成了封闭型空间、半开放半封闭型、开放型空间三种空间营建的样式,使“观者”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建筑内部空间实现宗教活动,这跟印度教建筑几乎为全封闭空间的建筑形制也是有明显差异的。特别是开放型建筑与半开放半封闭型建筑对于佛教活动举行提供了室内场所。再者,室利差呾罗古城的佛塔建筑、佛教寺庙建筑几乎都是用砖砌方式营建,侧面也反映了室利差呾罗古城工匠利用砖砌方式建造高台建筑(比如包包枝塔通高近50米)技术的成熟。包括砌筑技术在内的叠涩技术、拱券技术等建筑技术是实现室利差呾罗建筑艺术的前提。
第三,从室利差呾罗古城的造像及工艺品方面看,可分为佛教主题的造像以及印度教主题的造像两种类型。佛教主题方面,坐佛像是这一时期造像的主流。坐佛像分为“纤瘦型”与“粗野型”两种风格样式。佛三尊像、佛教纪念碑版等方面同样也以坐佛居多。印度教造像方面,以印度教三神像以及毗湿奴系统神像居多。三神像为毗湿奴、湿婆、梵天共同组成的造像形式。毗湿奴神造像系统包括毗湿奴单尊形象、毗湿奴与吉祥天女男女神像、毗湿奴坐骑金翅鸟形象等形式出现。大体量的印度教造像(图24)说明了其公共性属性,也反映了室利差呾罗古城城民不仅对佛教有虔诚信仰,对印度教也持包容态度。当然也反映了宗教服务的国家机器对不同宗教的接纳“心态”。
第四,室利差呾罗物质文化遗迹是对史料的重要补足。事实上,记载室利差呾罗古城的古籍文献资料十分稀少,仅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只言片语,并只讲述了古城的具体方位。因此,探寻室利差呾罗古城的物质文化遗存对于了解缅甸以及东南亚早期城市、建筑、造像三重艺术形态意义深远,是“鲜活”的古文献资料。
不论是城市、建筑如此的“大空间”物质文化遗存,还是造像、工艺品之类的“小空间”艺术、设计形态,共同反映出古城室利差呾罗曾经的辉煌——文化、宗教、艺术既是佛教的、又是印度教的,这一定是“繁盛之地”的城民才有的包容心、接受心,也才能让其千年后重回我们的视野并有幸了解那段“迷失王国”的前世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