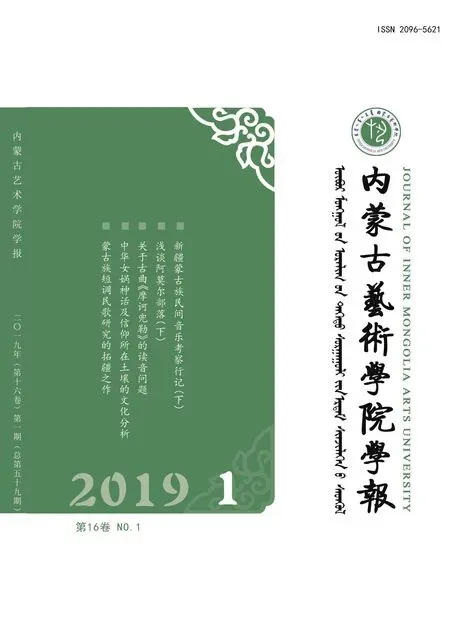中华女娲神话及信仰所在土壤的文化分析
2019-03-28李祥林
李祥林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女娲神话的产生和女娲信仰的流播,离不开中国文化的特有语境。从性别研究视角观之,源远流长又积淀深厚的华夏本土文化具有未必不浓郁的雌柔化气质,其中奥妙值得从深层次考察。本文拟结合此,从“阴阳”词语的知识考古、先秦诸子的学说透视、农耕文明的原始发生三方面入手,就女娲神话及信仰在中国社会所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进行分析(随文配图除了“道”、“儒”二字外,均是本人田野考察中所拍摄)。
一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太极者,阴阳和合也。阴阳观念在华夏文化史上由来甚古,从文献记载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传·系辞上》),“阴阳者,二仪也”(王夫之《周易外传·说卦传》),古老的《易》作为中华先民智慧的文化结晶,以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神奇卦象讲述着东方国度的阴阳理论(见图1)。

图1:太极八卦是伏羲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易》分经、传,经为母本,传乃释义。《易》之卦象发生,古往今来释者多多,立足文化人类学追溯之,此可谓是远古先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符号化产物。“《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就经说《易》,这阴阳是通过卦符“-”(乾)、“--”(坤)直观地表现出来的,所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易传·系辞下》)、“乾刚阴柔”(《易传·杂卦》)。从“近取诸身”的人类学角度看,其当是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反观自身再推及天地万物的结果。1923年5月,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指出:“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的记号。”[1](77)1927年9月,周予同撰文也肯定:“《易》的-、--是最显明的生殖器崇拜时代的符号。-表示男性的性器官”而“--表示女性的性器官”。[2](86)1928年,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进而发挥:“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又说:“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三为最神秘(三光、三才、三纲、三宝、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身、三世、三位一体、三种神器等等)。由一阴一阳的一划错综重叠而成三,刚好可以得出八种不同的方式。这和《洛书》的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配合而成魔术方乘一样……八卦就这样得着二重的秘密性:一重是生殖器的秘密,二重是数学的秘密。”[3](23-24)既然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传·系辞上》),可见《易》之古经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是以两性关系来推论的,不妨说是一种基于原始生殖崇拜的性的宇宙观。
古典戏曲《琵琶记·春科》中有考官(外扮)与举子(净扮)对话:“[外]夏商之时,易有何名?[净]夏易首艮,是曰《连山》;商易首坤,是曰《龟藏》。”而“三易”之说,见于《周礼·春官·簭人》:“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归藏》之书久已亡佚,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逸文若干。因此,“三易”当中,真正流传后世畅行天下者仅有《周易》,对今人来说最熟悉的也莫过于《周易》。岁月流转,世事沧桑,从两性权力移位角度看,这会不会是“周礼”颁定后日益强大的父权制社会有意抑扬的结果呢?现存《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前者当成书于殷周之际,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发挥,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和《杂卦》,又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作,也杂入了战国秦汉间儒士之说。着眼性别文化研究,经过儒们人士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观念大加阐释张扬的《周易》,有浓厚的阳尊阴卑、男主女从意识而透露出男性中心即西方人所谓“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sm)色彩,其作为父权制上扬时代的产物当无疑。从《易传·说卦》中,可以看到以阳性的“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和以阴性的“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的种种借喻,而且乾先坤后、阳尊阴卑、男主女从的等级观念贯穿《周易》全书,古代中国父权制社会奉行数千年不变的人伦准则便由此奠定(见图2)。古往今来,准此思维模式,汉语词汇组合也就循守着阳性词在前而阴性词居后的排列习惯,譬如“男女”、“公母”、“考妣”、“父母”、“儿女”、“龙凤”、“乾坤”、“天地”、“日月”、“昼夜”、“强弱”、“刚柔”等等,其中体现出不无倾向的性别文化意识。然而,《三字经》云:“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证诸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易》作为华夏上古文明的结晶,其丰富的性别文化内涵并非《周易》能全部囊括,《归藏》就向我们昭示着有别于前者阴阳观的另一系统。

图2:天水伏羲庙先天殿的河图洛书石盘
“三易各有所本”而“不相袭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易教》),彼此非惟字数和卜筮方法有区别,连卦序排列也各不相同。《连山》以“艮”开头,艮为山,或以为这表明夏及以前人们“崇拜山野”。[4](21)从性别文化角度看,《周易》以“乾”开头(乾、坤、震、艮、离、坎、兑、巽),比之更早的《归藏》,据罗泌《路史·发挥》“论三易”介绍,则是以“坤”居首(坤、乾、离、坎、兑、艮、震、巽),朱彝尊《经义存亡考》所引卦序相同,并云出自东晋干宝。因此,被指认为商易的《归藏》又称《坤乾》,体现出截然不同而更为古朴原始的阴阳观念。关于这部先坤后乾的《归藏》,儒门鼻祖孔子也曾提及。孔子的家系,可追溯到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其作为殷王后代受封于宋国的贵族,后因避难来到鲁国,下距孔子不过五世,所以孔子自称“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由于这种身世,孔门在家传上无疑受到殷文化遗存的影响,据《论语·八佾》,孔子谈到夏、殷之礼时即称“吾能言之”。他本人对古老的商易系统也熟悉,其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礼记·礼运》)杞为夏之后而宋乃殷之后,所以孔子到二国去寻访夏、殷旧典以求治世之道。
关于孔子此行,郑玄注“得《坤乾》”句云:“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陈澔注:“《坤乾》,谓《归藏》,商易首坤次乾也。”(《礼记集说》)《坤乾》与《归藏》在名义上亦有关联,如研究者指出:“春秋时孔子所得《坤乾》卦书是否就是《周礼》所称的《归藏》呢?史无明文言之。但按:的卦占法历史悠久,当为宋人的祖宗殷人发明;(二)二者先后都流传于中原地区,看来春秋时宋国流行的《坤乾》与战国时《周礼》所称的《归藏》当有渊源关系,按照传统音韵学来分析,‘归藏’很明显是‘坤乾’的音转,所以前者很可能是后者的祖本。”[5]
来自地下的考古发掘,也提供了相关佐证。1993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发掘出一批竹简,内容包括《归藏》《效律》《政事之常》《日书》《灾异占》,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这批竹简,用秦隶、秦篆以及接近于楚简的文字书写,表明抄于不同时期。
其中,《归藏》编号164支,未编号残简230支,共有4000余字,有卦画、卦名、卦辞三部分。①以此来看,桓谭《新论》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称“《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隋书·经籍志》载云“《归藏》十三卷”,又说“《归藏》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惟载卜筮”;《旧唐书·艺文志》有《归藏》十三卷,注云“殷易,司马膺注”,皆当非无稽之谈。
诚然,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未必就是《归藏》最古老的原始文本,其中不少问题也在学界的继续探讨中,但是,前有孔子关于殷道《坤乾》之言,后有秦墓竹简《归藏》的出土,再加上历朝历代文献中有关其内容引述的蛛丝马迹,可知《归藏》在汉代以前就已存在并流传,历史上“三易”之说自有来历,要全然否认之恐怕不容易。另外,在卦象排列上,相传为后周卫元嵩所作的“唐易”《元包》以“坤”开头(坤、乾、兑、艮、离、坎、巽、震),清潘咸认为其出自《归藏》,[6](171)看来也是于古有据的。
此外,顺带说说,在多民族中国,阴阳观念亦见于西南地区纳西族,东巴经里代表“阳”、“阴”的有象形文字“卢”、“色”,二者按照东巴经传统书写格式,通常以“卢”在前而“色”在后,读音为“卢色”,可见古代纳西族表述阴阳观念时,排列顺序为“阳阴”。究其原因,当跟其社会形态从女性为主向男性中心转移的历史有关。不过,现存东巴经古语中有一特殊现象引人注意,即凡称“夫妻”、“男女”时,均以“妻”或“女”在前而“夫”或“男”在后,这跟东巴经记述“卢色”(阳阴)、“铺咩”(公母)时先“卢”后“色”(先阳后阴)、先“铺”后“咩”(先公后母)形成对比。“这种用语上的双轨制,反映出两性权力交接时期的社会现实。”[7]
《周易》以“乾坤”开篇,崇阳尊“乾”;《归藏》以“坤乾”开篇,贵阴重“坤”。
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后者折射出远更古老原始的母性崇拜信息。有论者指出,王家台秦简《归藏》和传世本《归藏》应是《归藏》易的《郑母经》,“郑母”即“奠母”,即“尊母”、“帝母”,体现出《归藏》以母为尊、以母为主思想。[8]“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考察人类生殖崇拜史,女性曾是人类自我崇拜的最早对象,这是由女性掌握着创造生命的伟大秘密所决定的。
华夏神话中,除了独自“抟黄土造人”的母亲神女娲,也有无夫而生九个子女的“女歧”。
再看中国少数民族,南方瑶族“布努”系人崇拜始祖神密洛陀,“据传,密洛陀为创世神,同时也造了人类,用蜂蜡捏人形,孕生12男12女,成为女神孙辈,他们又衍生出汉、壮、苗、瑶族”;北方达斡尔族祖神信仰中,“祖神几乎都是女神”;至于蒙古族,则称大地为“母天”,即“额赫腾格里”。[9](138/152/18)凡此种种,折射出初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世风。
如诺伊曼所言,“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是父系社会出现之前人类崇拜的最大神灵,其产生比文明时代熟知的天父神要早两万年左右。“大母神”崇拜从文化心理上奠定了先民尚母重坤的原始基础,开启了中华阴阳哲学的先河。古人描述宇宙创生图式有“天地未分,谓之太易”之说(皇甫谧《帝王世纪》),按照《易纬》,这“太易”是太极之上“未见气”的更原始的“无形”阶段,郑玄注:“太易,无也;太极,有也。”据考证,“易、阴古字通用”,作为宇宙诞生起点的“太易”其实就是“太阴”,而玄之又玄的“太阴就是无形无色的大混沌”。[10](194)前述地母生天父神话跟《归藏》先坤后乾意识相映照,异途同归地指说着太古社会的崇母信仰。所以,吕思勉谈到殷《易》首坤时指出:“凡女系社会,多行兄终弟及之制,殷制实然,然尤未脱女系社会之习。《坤乾易》及《老子》书,皆其时女权昌盛之征也。”[11](13)坤为土为大地,象征母性。古人云“坤为地,为母”、“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易传·说卦》),“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引郑玄释《归藏》名义),无非是说“万物归藏于母”,天地万物皆由神圣的母性所生所养。不仅如此,《归(一)孔子由《坤乾》以观殷之道,可知该书所传承藏》所重之“坤”亦有其人类学的发生根基,据《说文》,“坤,地也”,地字“从土,也声”,而“也”乃女阴之象形摹写,故而段注释“地”云:“坤道成女,玄牝之门,为天地根,故地字从也。”这种重坤崇阴尚母观念,跟女娲神话及信仰是息息相通的。(见图3)

图3:走访西华女娲城,也看见手捧太极图的女娲
二
从哲学角度看,“儒、道互补”构成了数千年中国精神文化的主干,在两千多年历史上发挥着决定性导航作用。华夏传统历来讲“据于儒,依于老”、“儒治世,道治身”。
吕思勉《先秦史》言及老子学说时指出:“古书率以黄、老并称。今《老子》书皆三四言韵语(间有散句,系后加入);书中有雌雄牝牡字,而无男女字;又全书之义,女权率优于男权;足征其时之古。此书决非东周时之老聃所为,盖自古相传,至老聃乃著之竹帛者也。今《列子》书《天瑞》篇,有《黄帝书》两条,其一文同《老子》。又有《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有《黄帝书》一条。《列子》虽伪物,亦多有古书为据,谓《老子》为黄帝时书,盖不诬矣。”[12](472-474)《老子》是否为黄帝时代之书,暂不讨论,但简、帛《老子》的出土,可证其成书甚早。有“女性哲学”之称的老子学说,其躯体中流淌着古老的母系文化血液,对原始母道的崇尚构成了它的根本价值取向。作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创者,老子主要探讨宇宙生成论、世界观以及人生观这些哲学基本问题,似乎并未正面谈论过男女地位及相关话题,但是,通读五千言《老子》,你会发现,书中从头至尾被作者借以说道论德的喻体和象征体,都跟女性和女性文化息息相关。“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其作为宇宙之原始、万物之根本,曾再三被他喻称为“天下母”、“天地母”。《老子》中,“道”字的出现达70多次,这恍兮惚兮玄之又玄的“道”,无疑具备宇宙最高存在的形而上意义,但它偏偏又有着形而下的人类学根基,被老子形象地称为“玄牝”,所谓“谷神不死,天地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第六章)。“玄牝”者,大阴也,有学者称之为“一个永恒的子宫”,[13](50)其作为道的原始意象,甚至可以从字源角度推究“道”的构成(见图4),为其觅得发生学证据。

图4:“道”的字形演变
检索古代文献及考古资料,“道”在迄今出土的甲骨文中未见,其最早出现在西周“貉子卣”铭文中,字形为“”。将金文中这个古老字符拆开来看,“”是甲骨文有载的“行”字,据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 ,像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至于“ ”,则为“首”字,甲骨文写作“”,是人或动物头部之状写。因此,《说文》释“道”为“从辵,从首”。从人类学看,先民将二者巧妙组合,一个拟象兼会意、具有生殖崇拜内涵的“道”字由此诞生,该字形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妇女生育时婴儿头部先出的顺产状态。有研究者指出,“《老子》谓‘道’:‘道者,万物之奥。’《庄子·渔父》谓‘道’:‘道者万物之由始。’《鬼谷子·阴符》谓‘道’:‘道者,天地之始。’《贾子·道德说》谓‘道’:‘道之导始之谓道。’以研求天地万物之所由始的‘形而上’的‘道’,其对应物,恐怕就是能生儿生女的‘形而下’之‘器’——产道”。[14]也就是说,“常识告诉我们:女人和雌兽的生殖道即阴道是胎儿娩出所必经的唯一通道;而胎儿的正常出生一定是一个以其头部为先导的、有一定方向的运行过程……不难看出,‘道’字初文所展示的不是人行走的道路,而是一幅颇为生动逼真的胎儿娩出图。由此进一步推测‘,道’字的原初意义有两项:(一)女人的和雌兽的生殖道,即阴道。此为名词;(二)导引。此为动词”。②(102-103)如此说来,生养万物之“道”即养育生命之女阴,后者是女性生殖崇拜的具象化和符号化,而老子“母道”哲学的全部人类学奥秘就在此。破译了这关键点,再去读那玄思妙想的《老子》一书,许多问题也就容易理解。
着眼性别批评,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男权至上的国度,而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社会道德中人们又无不体现出对女性道德的倾慕,其中似乎也体现出女性人格的潜移默化的力量”。[15](332)这种文化性格上的二重性,甚至在与道家相对的儒家身上也体现出来。诚然,取法乎周的儒家文化代表着上扬时期的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战国秦汉间儒生大力张扬的“天尊地卑”、“三纲五常”也流露出强烈的男尊女卑意识,但归根结底,其毕竟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华夏语境中生长出来的,要全然避免被打上那由来古老的雌柔文化烙印也难。就拿儒家的“儒”字来说吧(见图5),其语义便跟“柔”(脜)有关。

图5:“儒”的字形演变
有研究者指出,“《说文·脜部》:‘脜,面和也。从脜从肉,读若柔。’此字经传皆以柔为之……《尔雅·释训》‘戚施面柔也’释文引李曰:‘和颜悦色以诱人,是谓面柔也。’凡此皆以柔为脜而训面和者也。‘柔(脜)’本面和,引申之,则泛谓和矣……‘儒’源出于‘柔(脜)’,‘柔’为‘和柔’,而‘和柔’正是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16]的确,古人正是以“柔”释“儒”的,《说文·人部》曰:“儒者,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对于这饶有意味的原始定义,也有人不同意,认为此非其本义而是由别处窜入的,“因为在汉字中,恰有一字之形义与‘儒’极为相近,此字即‘偄’(今通写作‘软’)。《说文·人部》:‘偄,弱也。从人从耎。’‘偄’字只有一个义,即柔弱;而其篆形与‘儒’极其相似。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所谓‘儒’的义训‘柔弱’,是否由于古人将‘儒’与‘偄’形近致混、并且互相讹用的结果呢?”[17](480)“儒”、“偄”是否发生混淆,我们暂不讨论。不过,“儒”在构字上同“需”相关是明显的,章太炎《原儒》即称“儒之名盖出于需”。古代汉语中,“需”同“软”(《周礼·考工记·弓人》:“厚其辀则木坚,薄其帤则需。”),又通“懦”(《墨子·号令》:“当术需敌,离地,斩。”)。故《通雅》卷七云:“柔需,即柔耎……盖需、耎皆软字。”除了“儒”,跟“需”有瓜葛的汉字迄今仍多与柔性相关,如妇孺之“孺”、糯米之“糯”、濡染之“濡”、蠕动之“蠕”、怯懦之“懦”等等,这绝非偶然。而与“儒”之定义相印证的,便是《论语》中比比皆是的“和为贵”、“文质彬彬”、“非礼勿动”、“泰而不骄”、“矜而不争”、“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以德报怨”,以及“内省”、“中庸”、“忠恕”、“孝悌”、“温和”、“恭俭”、“谦让”等等,莫不在人格诉求上流露出内倾性、阴柔化的价值向度。至于来自儒门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人生修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哲学,“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旨归,“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道义精神,凡此种种,也显然难把人引向刚劲、怒张、雄武、猛烈的性格打造之路。
就审美趣味和艺术风尚言,这种对柔美的崇尚和张扬,不仅仅聚焦在先秦诸子时代;自汉至清两千多年中国艺术和美学发展史,也在总体上从阳刚到阴柔、自浓艳向素淡、由繁复而简朴的嬗变或者说回归上,再次于更广泛外延上放大和张目了柔美为贵的文化意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迄今为我们津津乐道的此语代表着富于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辩证法。“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国人的交友之道;“大羹必有淡味”,此乃食客的经验之谈。这种渗透在华夏民族性格中的不主浓重、强烈、外向、怒张而主平和、含蓄、婉雅、素静的审美趣味,无疑是富于雌柔气质的,自当划归“阴柔之美”而非“阳刚之美”范畴。中国古典美学以儒、道两家为主体,一般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注重人事,讲究文采藻饰之美,在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上偏“浓”;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注重自然,崇尚素朴之美,在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上偏“淡”。从诗画艺术发展和审美意识嬗变的纵向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前半期美学基本尚“浓”,这从两汉辞赋的“采滥忽真”(刘勰语)和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陈子昂语)可得证;后半期美学主要崇“淡”,这从文人画在画界崛起和“神韵说”在诗坛风行可看出。
诗歌创作方面,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其田园诗用白描手法绘景写情,去浓艳色,无雕琢痕,意趣真淳高古,风格淡雅自然,被诗坛誉为“开千古平淡之宗”;人称“冲淡派”大师的唐人王维诗、画兼擅,而作诗求淡与之同调的孟浩然、韦苏州、柳子厚、贾长江等人正组成了唐诗百花园中“清淡”一派。诗歌美学方面,晚唐司空图论诗讲“浓尽必枯,淡者屡深”,宋人苏东坡提出“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明人袁宏道喊出“淡”是“文之真性灵”的口号,及至清代王渔洋,就更是在以“古淡闲远”为审美标尺读诗、解诗、选诗的实践中力倡“神韵”之说。中国绘画史上,“随类赋彩,自古有能”,而“水墨晕章,兴我唐代”(荆浩《山水记》)。发达于唐代的青绿、金碧山水,标志着中国画在色彩追求上走向鼎盛。继之,便是“写意”思潮在画坛觉醒,人们开始从五色之外的水墨中发现一个更美妙的淡雅飘逸境界,文人雅士的兴趣中心也就由传统的重“色”移向新兴的重“墨”。宋元以降,随着崇尚萧疏、清淡、简朴、自然的审美意识在中国美学史上主角地位的确认,绘画领域这种取水墨淡雅而弃五彩浓丽的创作倾向更其俨然,“丹青隐墨墨隐水,其妙贵淡不贵浓”(沈周《题子昂重江叠嶂卷》),明代徐渭的水墨写意,近世齐白石的墨笔画虾(见图6),皆道出个中消息。以淡为贵的审美观,其直接哲学基石恰恰是充满雌柔文化气息的道家学说。也就是说,“滥觞于老庄的这种尚淡思想,后来在陶潜、王维等人的创作中和司空图、苏轼等人的理论中得以发挥完善,从而在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上铸就了特色独具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范畴——‘淡’。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意识,它积淀在我国世世代代人民的饮食、交友和娱乐等日常生活活动中,以巨大的张力制约着人们的审美和准审美乃至非审美的价值取向”。[18]

图6:徐渭、齐白石皆擅长水墨写意,这是笔者所著二书
贵淡主静尚柔,这种民族性格和传统观念,是我们结合中国传统深入考察与女娲神话及信仰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场域所不可忽视的。
三
关于《归藏》或《坤乾》由来,据《路史·黄帝纪》:“黄帝有熊氏,河龙图发,洛龟书成。于是正‘乾’、‘坤’,分‘离’、‘坎’,依象衍数以成一代之宜。谓土为祥,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也……”所谓“谓土为祥”,正表达着农业社会对土地不无敬仰的普遍认识。“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说文》),“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土地是养育万物之母,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产资料来自大地。华夏号称“以农立国”,我们祖先自新石器时代便选择了农业作为生存繁衍的主要依托,特定地理条件为中国农耕经济早熟和发达提供了适宜土壤。从根本上讲,“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19](29)2014年我去甘肃秦安大地湾博物馆,看见展厅中设有“中国最早”的若干提示,“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作物标本”是其一(见图7),该史前遗址一期灰坑中出土的炭化谷物种子距今约7800年。立足中华文化语境,考察女娲神话的发生基础和存活场域,不能忽视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
史前人类的原始生产方式包括采集和狩猎,由于生理原则的天然分工,前者多以女性为主而后者多以男性为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中,由于初民所赖以生活的自然条件有别,生产的进展可以有两种方向,或侧重女性方面(从采集到农耕),或侧重男性方面(从狩猎到畜牧),从而也就影响着农耕民族和畜牧民族在个性气质上的刚柔差异,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所言。从生态环境看,中国地处温带,基本属于大陆性气候,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时有节,加上黄河、长江流域的平畴沃野,特别适宜农业自然经济发育。中华文化的雌柔气质与此“以农立国”的国情密切相关。夏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王朝,禹所代表的夏族即是纯粹的农耕族群。所谓“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正指说着因农而兴的上古事实。
考古成果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中心之一,绝大部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农耕文化的性质”。[20](704)在距离陇城“女娲故里”不远的大地湾博物馆(图2—8),有从史前遗址中发掘的碳化黍,并且可以读到关于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的介绍:“即前仰韶文化,距今7800—7300年,是迄今为止渭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这时此地的先民是最早的西北拓荒者,他们创造发明了我国最早的彩陶,同时种植生产了我国第一批粮食品种——黍。”③(图2—9)远古时期我国粮食作物以粟、稻为主(大地湾遗址二期亦有炭化粟出土),由于黄河与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些农作物栽培在中华大地有广泛分布。

图7:在距秦安陇城“女娲故里”不远的大地湾博物馆可看见多项“中国之最”提示
据考古发现,在陕西西安、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甘肃永靖大何庄以及长城内外2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墓葬中,均出土有炭化粟粒或粟壳;年代尤早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的粟粒,经C14测定,距今7300年。这说明距今6000年前后华北和西北地区已普遍种粟,直到今天,俗称“小米”的粟仍是黄河流域重要农作物之一。在长江流域,距今7000多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在10多个探方达400多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曾发现稻谷、稻壳、稻秆、稻叶及其它禾本科植物的混合堆积,其平均厚度达四五十厘米,经鉴定为栽培稻中的晚籼稻,比曾被视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泰国奴奴克塔遗址出土的稻谷要早数百年。
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南部道县发掘出一万年前的炭化稻谷;在这之前,广西南宁地区已发现上万年前的稻谷加工工具。此外,还有不少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的稻粒和稻壳遗存相继出土,如1954年在江苏无锡仙蠡墩遗址出土成堆的稻壳、1956年在云南剑川县海门口发现炭化稻粒、1961年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现稻谷及稻叶、1972年在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许多炭化稻粒、1973—1976年在广东曲江石峡及泥岭遗址掘出稻谷和炭化稻米,此外在台湾省台中县营浦遗址也发现了史前稻谷遗存,等等。这些稻谷遗存据考证最晚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此可知,那时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几乎整个南中国都已栽培水稻。
不仅如此,在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和山东半岛的栖霞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有稻谷痕迹被相继发现。④如此早熟并沿袭不变的农耕文明,在少险峻也少波涛的大陆平原型华夏土地上得到超稳态发展,为造就中国人的亲和自然意识、母性崇拜情结、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平和淡然的民族性格以及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提供了适宜土壤和温馨摇篮。
在人类历史上,农业的发生跟初民采集野生植物作为食物的生活直接相关。人们为维持生存需要而从事采集,他们在长期劳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经过无数次试验而摸索出栽培作物以生产粮食的方法,由此拉开了农业文明的帷幕。远古时期,担任食物采集的主要是妇女,她们是原始农业的发明者,受到崇敬,甚至被推举上神的宝座。如神话学家指出,“在农耕社会,神话特有的形式是庆祝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仪典。其中女性象征居于突出地位,因为谷物的繁衍同妇女的生殖类似。学者认为:农耕首先是妇女开拓的,即使在比较先进的狩猎和采集社会,农事仍然由妇女承担。因此,农业共同体中呈现出许多母神、地神和谷神的现象”。[21](87)初民信仰中,“大女神在任何地方都是产生于大地的食物的统治者”。[22](270)
迄今汉语“生产”和英文“fertility”仍为“收割庄稼”和“妇女分娩”二义兼指,不是偶然的。文化人类学提醒我们,史前考古遗址中发现具有生殖崇拜意味的远古女性雕像是一跨地域和跨文化现象。有研究者指出:“新石器时代女性人体雕塑的出现是世界性的现象。我国在80年代以来,在东北、河北、内蒙等地都发现了一些女性的裸体雕像,其中尤以辽宁喀左东山嘴出土的雕像最为完整。她明显和生产巫术有关……”这巫术如何呢?“农业巫术的基本原则是认为土地的生产能力和土地的生殖能力可以优育模仿妇女的生育功能而得到强化,农耕巫术之所以要以妇女为主体,就因为它存在于妇女的生殖能力和土地的生殖能力的联系中。”
总之,“女性雕像在新石器时代的世界性发现绝非偶然,因为在所谓‘地母’、‘母神’雕像的后面是一个漫长的、历时几千年的农耕领导者的传统。”[23](197)
女娲在中国神话里是创造大神,把她的创造活动跟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鲜见于古书记载,但求诸民间传说,倒是有若干蛛丝马迹。如在四川,有采自古蔺县丹桂乡不识字农民口头的神话《神农制谷子》,说神农制出谷子后不知装什么在里面,是女娲娘娘挤出奶水装入后,谷子才成了,所以米是白色的。在当地民间,每当有人生病,也熬米汤喝,“因为米汤是圣母的奶汁,最补人”。[24](13)这是直接把谷物传说与女娲挂钩,强调正因为有了女娲的奶水灌注,人类才有了大米吃。河北涉县民间有“女娲造六畜”的故事,讲女娲为人世间造了鸡、犬、羊、猪等后,“让儿女们采集野果野菜时,注意它们的生长规律,把它们的果核和种籽弄回来栽种。每当后世人们庆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时,你可知道当初女娲造畜辨谷的辛苦?”⑤(142-143)这又把女娲跟种植谷物等联系起来。河南西华流传的民间故事《女娲芪的来历》,则从女娲为所造人儿觅得可吃之草(芪)透露出跟农业发生有关的原始“采集”活动信息。20世纪80年代从浙江湖州年老乡民口中采录的《人皇女娲创世》,也讲女娲在造人之后又寻找谷种来栽种,从此后“有了人,有了稻谷,世界又热闹起来啦”。[25](40)从诸如此类口头文学或民间叙事中,大致透露出女娲也具备母神与农神重合的神格。
农业诞生跟原始采集有关。从源头看,发达的农业文明在中国从更古老的采集文化发展而来。“考古事实表明,中国人的祖先看来没有像世界大多数民族那样经历漫长的游牧、游耕或半游牧、半游耕时期以后才进入定居农业生活。这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大特点。”[26]比较可知,由于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差异,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有发达的定居农业在中华大地出现,本土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是明证;在欧洲,作为西方文明发祥地的希腊半岛,濒临海洋、岭嶂峦盘,石多土少,土质瘠薄,年降雨量偏少(有雨也三分之二集中在冬季),明显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因而迟至公元前9世纪或8世纪中叶才告别漫长的游牧游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其转入定居农耕生活要比前者晚三四千年。原始农业在华夏大地从初民社会以女性为主的采集生活过渡而来,自然就更多保留着慈柔温馨的母性色彩,不像史前欧洲长期狩猎为主的生活那样充满男性的勇武刚强(这在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明母系制让位于父系制何以在我中华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这种源头分野铸就了东西方文化史上的“童年记忆”,为民族性格上中国人的“内倾情感型”和欧洲人的“外倾情感型”的划分奠定了心理原型基础。
因此,从恩格斯说的“两种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角度看,原始采集活动决定了妇女的主角身份而原始生殖崇拜确立了母亲的崇高地位,这来自初民社会的双重事实是我们从源头上考察中华文化的雌柔特质时不可忽视的。
从采集植物到播种植物,对谋求食物以维持生命需要的华夏先民是顺理成章的过渡,其间不存在什么文化断裂。有学者说个性极强的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梁漱溟语),此乃证明之一。
在原始农业时期,“靠天吃饭”的初民要完全依靠耕种来解决一年四季温饱恐怕成问题,采集活动在他们生活中依然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河姆渡遗址中,在出土稻谷以及镰、耜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的同时,亦发现了不少橡子、酸枣、菱角、芡实等富含淀粉可供食用的籽实;半坡遗址中,也发现有很多罐藏的榛子、松子、栗子、朴树子等可供食用的野生籽实,可见采集野生植物仍是当时人们解决食物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古老的采集文化在《诗经》中亦留下回声,“诗三百”中有相当数量的“采集诗”,即以采摘某种植物为描写对象的诗歌,这绝非偶然。在女性勤劳的手中,从采集植物到栽培植物是自然而然地过渡,因此原始农业文化总是同原始母性崇拜连在一起,“我们很可以在一切以农耕为生存主业的原始社会中,找到有母权形式或有母权遗迹的家族”。[27](30)在民间信仰中,受原始思维支配,大地生长谷物和母亲生育子女是异质同构的,由于祈求谷物丰产和祈求人丁兴旺的心理重合,农业崇拜和生育崇拜往往关联密切并通过女神崇拜体现出来。
中华大地上,众多考古发现在展示远古农业灿烂图卷的同时,也再三把史前女性崇拜的辉煌遗迹呈现在我们面前。1983年,在河北滦平县金沟屯镇后台子遗址中,清理出石雕裸体女像6具,经鉴定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赵宝沟文化遗物。6具女像均为圆雕,较完整者高32厘米左右,有5件都是裸体孕妇形象,共同造型特征为:双乳外凸,腰腹粗肥,两手曲肘抚着隆起的肚子,取蹲坐姿势,有的还用凹坑将女阴表现出来。
这批史前“维纳斯”,造型上刻意突出丰乳、肥臀、鼓腹之孕妇特征,折射出以原始生殖崇拜为底蕴的女性崇拜事实。与此印证,有1989年在内蒙古林西县东南西拉木伦河北岸的白音长汗遗址的石雕女像,该像头顶盘发,也是隆腹鼓乳、双手抚肚、屈腿蹲坐的孕妇造型。白音长汗是距今7000年的聚落遗址,这尊35.5厘米的女性雕像发现于一座半地穴式房子的火塘附近,可能是家族保护神,兼有生育神与火神的双重神格。
还有1991年在仰韶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中发现的残高6.8厘米的陶塑裸体女像,头部和四肢已残缺,但凸乳、鼓腹的“大母神”特征明显。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致跟中原仰韶文化同步。红山文化被今人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距今5000多年女神庙和祭坛遗址的发现。
1979—1982年,辽西喀左县东山嘴发掘出大型石砌祭坛遗址,祭坛为圆形设于山嘴空地,祭坛周围发现两件无头裸体女性陶塑立像(残高分别为5厘米和5.8厘米),均臀部肥大,腹部隆起,阴部有象征女性生殖器的三角符号,也是怀孕妇女形象。随后,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村发现了女神庙遗址。
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平台形地,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组成,所供神像已被坍塌的屋顶砸得七零八落,断头残肢以人像为主,亦有猪、鸟等动物塑像。人物塑像包括头、肩、臂、手、乳房等残块,大致分属五六个个体,形体或大或小,年龄有老少之别,肩臂线条均细腻圆润,呈现女性特征,乳房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但都可确认是女性的,其中还有一女性头像,跟真人大小相当,蒙古人种特征明显。这些雕像中未见有明显男性特征人体,可以确定这是一群倍受先民膜拜的女神,她们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的祖先神,也可能是专司繁殖的生育女神,或者是同时掌管农业和生育的地母神。⑥从原型层面看,她们在神性和神格上跟大神女娲有相沟通处。
在人称“女娲故里”的秦安县陇城镇,民间传说女娲就出生在这里的风谷,那里至今尚存幽深的“女娲洞”(图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距此不远的大地湾史前遗址一期文化根据考古学界所定为“前仰韶时期”,这里既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作物(黍)”也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彩陶”。神话传说中女娲娘娘以土造人,有论者从农业文化角度指出:“女娲抟土造人用黄土,是与中国大片的黄土地及土地崇拜密切相关。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从世界范围内看,以土造人的发生地,许多都是农业文明发生较早的国家……‘黄土造人’是农耕方式的产物,它将‘人’与‘土地’紧紧地维系在一起。”[28](6)的确,原始社会研究表明,“热带许多部落传说人类从池塘里或泥土里产生出来,反映了他们当时已经过着农业经济生活了”。[29](433)大地湾出土的陶器有葫芦瓶,彩陶纹饰中的动植物纹样有鱼纹、蛙纹等(见图8),还有一件器口呈女性特征的人头形彩陶瓶,十分引人注目。若“在地性”地联系方方面面考察之,我们不难从中悟出些什么。
总而言之,考察中华文化的雌柔气质,⑦不可忽视华夏本土起源古老又长久发达的农耕文明,后者也给中华女娲神话及信仰的存在与流播提供了适宜的温馨土壤。

图8:史前陶器的鱼纹、蛙纹以及葫芦形都被认为跟女性生殖崇拜有关
注 释:
①相关报告及文章: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2000年北京大学等主办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等等。
②文达三:《老子新探》,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43页。根据对“道”的这种考释,有论者进而解读了《山海经》中有关女娲神话的文字段落。《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郭璞注:“或作女娲之腹。”又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有研究者认为,“女娲之肠”应为“女娲之肠神”,其中“肠”指妇女的子宫;“栗广之野”疑是“粟广之野”,指人的腹部,取人以粟食为主之意;“横道而处”指十神轮番当产门而居,行逐月保胎之职;“道(導)”之本文为产道,“首”在“辶”上而其下加之“寸”(指手),则“道(導)”的本义是指接生;“有神十人”则疑为同篇下文的“灵山十巫”。合而言之,《山海经》中这段文字或“映射一种意在保胎的原始宗教行为:妇女怀孕之后,每当一个妊娠月,都要到皋禖女神的女娲祠庙祈祷,女娲便会逐月‘派遣’一巫(其实是巫师自己的行为)降神,以之为此孕妇保胎。由于巫有一定的医药知识(‘操不死之药’),故可托为神意,使孕妇一定程度上得到心理和肌体的治疗,从而达到保胎的目的,使婴儿健康发育而不死”(范三畏:《旷古逸史——陇右神话与古史传说》,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103页)。
③2014年9月28日抄自甘肃秦安大地湾博物馆。
④具体情况请参阅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文物》、《考古通讯》、《考古学报》等杂志上相关发掘报告及文章,因篇幅之限,恕不一一注明。
⑤《神话传说·女娲系列·造六畜》,张海旺、史安昌搜集整理,见史安昌主编《涉县名胜》,涉县女娲文化节丛书编委会编印,1999年8月第1版,2003年9月第2版,第142—143页。
⑥具体情况请参阅:《试论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文物》1994年第3期;《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等等。
⑦对中国文化雌柔气质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拙文《中国文化与审美的雌柔特质》(载《新余高专学报》2000年第4期)、《对中国文化雌柔气质的发生学考察》(载《东方丛刊》2003年第3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