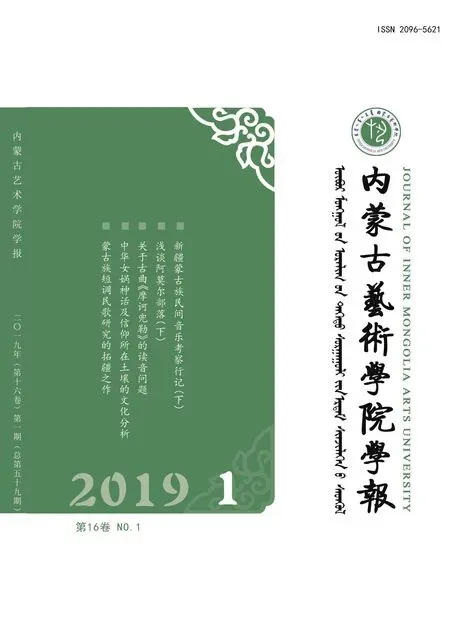5世纪晚期到6世纪早期中国艺术中的植物主题和卷草纹(上)
2019-03-28苏珊布什祁晓庆武志鹏
(美)苏珊·布什 著,祁晓庆 译,武志鹏 校
(1.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美国 波士顿 021382;2.敦煌研究院 甘肃省 敦煌市 736200;3.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公司 北京 100020)
最近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发现的有关5世纪末到6世纪初的墓葬,使得艺术史家们可以在原本空白的艺术区域上标出明确的图表。中国原本南北截然不同的区域性艺术风格现在可以更加精准地找到其对应的位置了,因为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在墓葬或世俗装饰中均有表现。去收集一个时期内具有平衡性的观点也是可行的,迄今为止,对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的认知主要通过北方石窟寺里保存的佛教造像。或许有乐观主义者会认为各种形式艺术的影响力都可以以中国期刊发表的考古报告作为参照来加以描述。然而,如果我们能关注一些细节性的主题,那么可资利用的证据就 会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例如弯曲的植物、风轮、放射状、环绕的莲花、卷曲葡萄藤状的棕榈叶和半棕榈叶等。这么做的话,有人应该会将这种植物装饰与超自然的创造物和飞翔的天神联系在一起进行评论,这些植物纹饰装点了贵族的车马、宫殿、寺院和墓葬。
一、中国南方
南京和丹阳附近的南朝帝王陵墓的纪念碑上用来保卫“灵魂之路”的兽纹长期保存着最原始的艺术题材类型,这些艺术题材是从南朝首都发起的。1960年,在南京西善桥墓室中发现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题材的模塑砖。接着,1965~1968年,在丹阳县发现胡桥墓和建山三个大型的石砖墓,这个区域埋葬有南齐宗族墓和梁天子墓。这批墓葬中最著名的是1965年发掘的胡桥墓,在保存最完好的墓室墙壁上有一幅“仙人戏虎图”,非常引人注目。
南朝时期(420~589)在临近南京和丹阳的帝王陵墓中长期保存着护卫“灵魂之路”的不朽石兽,这是由南朝首都发起的艺术类型原始的证据。到1960年,在南京西善桥墓墙边发现的一块刻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模砖。[1]时代更近一点,到了1965和1968年,在丹阳胡桥挖掘出三块大的墓室砖,这个地方是由南齐(479~501)宗族统治的区域,也是梁朝皇帝(502~557)的墓葬区域[2]。这个墓最著名的是1965年考古过程中在墓室西壁发现的一幅“仙人戏虎图”。

图1①
据《文物》1974年第2期刊载,这个墓葬习惯上被认为是齐成帝修安陵或者萧道生陵墓。公元479年,在他死之后不久他弟弟也去世了。萧道生的儿子,萧鸾(459~498),也就是齐明帝,在11位王子为争夺王位相继离世后的494年即位。495年,他将他父母的墓移至帝后陵,并将他们的墓命名为修安陵。自从发现此墓葬为夫妻合葬墓,并且与惠安有关的文献记载也与这个区域相符后,考古发掘报告的作者暂且接受了这一传统观点,并且根据墓室结构将墓葬的年代定为478年。[3]然而,与南方其他类型的墓葬相比,这个墓葬群规模较大,可能表明萧道成在494年之后以帝陵的规格重新安葬其父母。无论如何,这种在墓道入口处放置石兽的方式被认为是南齐风格(图1),就目前所看到的,在破损的出土物的配置或表面装饰方面都与498年护卫萧鸾的惠安陵不太相似。[4]

图2,3
如果有人对比这些墓室当中的神兽和老虎,会看到它们颈部明显的S曲线、具有动势的毛发或小而卷曲的翅膀,这些都说明塑造者试图在石头上对已有的图像设计的线条传统进行再创造。然而,在胡桥墓壁画中,老虎的这种瘦的、身体扭转、翅膀像火焰一样,并且向后倾斜的鬃毛和胡须都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刻画。在这件作品中,白虎作为西面方位的动物,被其他神灵护送,它们代表了南方区域内一种折中的趣味和信仰。在老虎不远处是道教仙人或卷发“羽人”,羽毛装饰表明了他的超自然属性。这件作品让我们想到了汉代晚期或者汉代以前的模型。例如雕刻在沂南画像砖上的3世纪时期的神仙与鹿的形象。[5]但是“羽人”现在已经穿上了束腰外衣与短裤,规则的头部造型与他高而倾斜的前额和瘦肖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图2,3)。

图4
翱翔于老虎背上方的是两身名侍从,其形象截然不同,向上飘扬的绶带强化描绘了它们瘦而弯曲的身体和右侧腿部。正如天神或神仙,是一种中国的佛教飞天或飞仙,相似的形象还将出现在6世纪20年代的北朝石窟寺甬道、壁龛或天顶部位,方形头部和瘦长型的身体与垂饰都是这个时期比较流行的特点。第二身手持浅盘的侍从似乎正在向空中散花或者珠宝(图4),在他之后明显有第三个形象正在演奏乐器,但是却缺失了。[6]
这种扭转的漩涡形植物让我们想到佛教典籍中曾经提到的吉祥花雨,正如风吹云气的纹样表示蒸汽一样,或者与汉代艺术中超自然王国有联系。这些松散的草图和点状结构的云气给人以书法的效果。这里的引导者是一名鸟人,他类似孔雀一样的尾巴从衣服中伸出来,关于这种拥有西方天使翅膀一样的鸟的最不平常的解释,是认为它可能是紧那罗,即佛教净土世界中的音乐神。[7]
虽然这件作品中的图案被认为很可能具有西方来源,但是他们穿着具有中国风格的长袍,正如南方佛教最终融合到新道教思想中一样。[8]也因为这件作品仍然具有汉代动物的保护和吉祥意义,所以仅有的极其微弱的有关佛教的元素只有他的飞翔姿态和后面的莲花造型。在这里我们首次遇到用凌乱的植物造型填充壁面的做法,这最有可能说明它属于南方风格。另外,位于墙壁更低一层的侍者形象的设计,只有“仪仗队”展示了骑在马背上的演奏者头顶上有卷草纹样,或许表明音乐的精神力量,也可能只是简单地在人物形象上方起到填充空间的作用。通过与1968年发掘的南京丹阳墓室相比较,可以推测这种相似的地面装饰毫无疑问也出现在已经残缺的天神与狮子的设计中,或者名为特殊主题的画像砖题记中。[9]

图5
在“仙人戏虎图”的底部发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植物图案。最流行的应该是可以称之为“卷草”的纹样,从莲花的侧面看,可以看到在不同阶段随着空气流动的线条和随风摆动的植物。仙人左侧大约与腰部等高的位置下方是另一种由八瓣花叶环绕而成的图案,树叶和花朵从外环的八个边伸出来(图2)。如果这些叶片数量增加或者从一个方向转动,它们将变成一种完全全新的“植物风车”样式。这些图案在当时被当做一种简单的时尚以便很容易理解它们的组成部分。在之后出现的派生图案中,它们逐渐变得复杂和松散。例如,1968年发现的两个丹阳县墓葬中的其中一座,虽然其护卫石狮拓片还没有公开出版(图5),但是可以看到这种卷草纹样获取了更多的植物拖尾,并且随意地用气体漩涡构思,甚至变成了打开的卷。[10]

图6
这种复杂的版本接近装饰了著名的邓县墓主题的卷草概念,在这里额外的植物纹样已经被改造成了似乎可以快速旋转的水波纹。而邓县墓的身形矫健的白虎与来自胡桥墓壁画中的畏兽十分相似,这种植物填充物启迪人们描绘出更复杂和更加简化的样式(图6)。任何部分在品质上的不同都自然可以被地解释为胡桥多室砖结构墓葬和宽度仅有15英寸的邓县单室墓葬在规模上的巨大差异。同时,邓县墓(图7)的这几种不同类型的植物风车造型证明了一种对繁茂和具有独创性的植物形式的兴趣。[11]然而任何有关邓县墓图案与丹阳图案设计之间关系的最终结论都必须延迟至对南方墓葬的其他类型装饰题材的综合考察之后。

图7,8
胡桥墓中满布的装饰逐渐内收并趋向几何形,最后提供了一系列更早时期的装饰形式。装饰的砖画,占满了没有被使用的墙壁空间以及不太规则的边界部分,最普通的装饰是连续环绕的圆形莲花。一对六瓣变体植物纹样可以用来装饰垂直砖块的末端,或者将两块砖首尾相连形成一个规则的模型,在更高浮雕上面用来保持更大规模的八瓣莲花形设计。[12]更早一点的最初版本的设计也出现在这里,是一对连接在一起的叠压的长方形五铢钱。三排水平铺砌的画像砖与垂直放置的砖层交替出现。(这种典型的系统结构也证明在大型绘画作品中,可能已经被设计者采用特定的规格尺寸。)这些水平方向砖块指向一种叠加成钻石形状的恰当的十字形剖面,但是这种瘦长的框架被连续环绕的花形或者硬币形分成更小的单元放置在每一个末端。中间一排被随意地用一种构思更加自由的植物藤蔓装饰,这种藤蔓装饰更接近于在克孜尔看到的内部为植物的连续的椭圆形设计,[13]但是其中有一支花蕾指向一边(图8)。
除了上一种形式之外,这个墓葬的装饰图案显示了典型的南京地区的本土特征。在首都附近的非帝国西晋墓已经生产出了与301和308年一致的模印砖。这种砖装饰有几何菱形和吉祥硬币,以及最小画幅的龙、虎、鹿和鸟等绘画。[14]

图9
画面中更有趣的是东晋墓葬(万寿村1号墓)中已经模印出了写有公元348年纪年的铭文,正如拓片上看到的一样;砖末端的龙可以由上述模制砖上的图案加以印证。三块垂直放置的砖末端被连接起来形成了四身坐着的非常写实的弯腰驼背的老虎形象,每个角落各一只,传达出“虎遨游在山上”的寓意[15]。在一个小规模墓葬中这些设计引领了南朝多室砖画,在这种多室墓葬内的图像被绘制成突起的浮雕线条和主题,如七贤,并标注了名字加以识别。348年墓葬中的其他类型的装饰包括了面具、一种传统形式的十字形对角线(图9:1,4,5,6),以及报告中提到了但是没有详细阐释的一种粗糙的不成熟的莲瓣设计。后者是对植物图案没多大兴趣这个区域中的部分线索之一,这种植物图案变成了南朝装饰纹样的主要内容。与之并列的南京新宁1号工厂墓模制砖拓片阐释了6世纪早期流行什么纹样的问题(图9:2,3,7,8)。一对头向下嘴里衔着植物的龙和植物风车边饰让我们想到了邓县砖的设计。“从怪兽面具到植物装饰”似乎显示了南方风格的一种明显的转变。然而,这样的推论很可能会误导读者,因为我们可以从3世纪沂南画像砖墓的边缘和脸部看到这种原本是怪兽面具,而如今转变为莲花图案的例子,山东墓葬可以为这两种几何装饰样式和2个世纪之后的胡桥砖墓八瓣莲花样式提供一种便利的资源。[16]
可以肯定在4世纪晚期,植物图案在南京地区站稳脚跟,这一点从刻有384年纪年的墓葬外部中山门上呆板的八瓣莲花侧面的两根轴线可以判断出来。[17]另外,几何形在串联的银币图案的变异中处于优势地位,这种串联的银币图案出现在象山墓王氏家族392年夏金虎墓中。[18]报告描述了一种环绕的八瓣设计,叠加在对角平分线上,作为一种花瓣样式,但它不是南齐成熟的环绕莲花的形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来自东晋墓葬,这个墓葬是1972年在湛江发现的,模印砖上面有398年铭文纪年,后来知道是金口,“首都口岸”,坐落于南京北部丹阳的扬子江畔。而更小的画像砖是用较为平常的代表幸运的钱币、动物或者菱形图案设计的,更大的方形图案被延伸至墓室墙壁之外,就如鄧城一样。[19]与居住于Shan-baicbing的奇形怪状的动物相比,这种主题在特征上显得比较保守:仅描绘了汉代的四个方位动物,吉祥鸟神,怪兽等。[20]然而,用超自然神灵的方式进行构思是南朝风格的前兆,它特别强调从头部到胸部之间瘦长的S形颈部所表现的奔跑姿势。

图10
值得注意的是那种植物装饰在这里仍然是极少数,仅仅出现在固定的主题中:如同羽毛一样的卷草图案作为具有吉祥含义的鸟神的边饰和松散弯卷的朱雀装饰。对于这四个方位神兽,朱雀仍然以伸展的翅膀、抬起的腿,下垂的尾部为标志,但是白虎和与它配对的绿色的龙一样,被设计雕刻成C形,使得它们伸长的身体看起来是作为整体处在一个方形或者矩形的格套中(图10-1,2,3,4)。6世纪对龙图像的使用呈下降趋势,他们具有相似的身体特征:腿部瘦而且弯曲呈斜面展开,尾部交叉。而下方的这两种鸟神作为一种奇怪的配对方式出现在520年北魏碑刻和朝鲜墓葬壁画中。一般而言这些图像没有任何与佛教徒有关的元素,在这些墓葬装饰中也没有任何西方影响的踪迹。
现存的第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具有外来卷草样式的画像砖来自南京地区,图案中似乎应该有半棕叶形的波状葡萄纹,和有着清晰明确的节点装饰的西善桥墓中著名“七贤”作品。[21]这种类型的画像砖首尾相连形成一幅连续的卷轴画(图11)。(两行这种形式的砖与下方颠倒样式形成一个双层的半棕叶形的卷轴画。)这个设计明显受到来自西方物品的影响,[22]并且预示了这种花饰的统治地位。在一系列由帝王家族成员构成的南朝墓葬中,西善桥墓成为首选的研究对象。因为它的建筑和绘画设计呼应了丹阳附近的南齐胡桥墓,它令人信服地构建了一个刘宋(420~479)统治下半个世纪或更早时期的装饰风格,新出土的随葬品无论如何都不会比五世纪中期晚。[23]著名的“七贤”画像砖图像代表了肖像画作中的高峰时期,但这并不等于它们能被后来的帝王墓装饰所采纳。然而,这种植物装饰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并不是佛教的花雨降落在新式道教的圣贤身上,除半棕榈叶卷形外,传统的银币和菱形样式继续装饰其他的砖画。然而,目前,南齐胡桥墓“仙人戏虎”壁画首次说明这种发展了的植物主题在这个首都区域备受喜爱。
从1961到1962年在南京西善桥发掘的大墓判断,后来南齐帝王墓的装饰其实十分保守。因为它所在的位置和墓葬的规模,被认为很可能是陈献帝。若果真如此,之后的近一个世纪,这种墓葬的内部装饰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缺乏创新可能是时代萎缩的一个反映。
在入口处留存下来的仅有的这副狮子图像也部分被破坏,它的后半部分与1968年发掘的大型丹阳墓葬里的狮子拓片非常相似,[24]但是空间设计明显缩小了,因为卷曲的植物装饰砖代替了它,并且空白区域填充了环绕莲花主题。墙壁表面这些重复的六到八瓣的花儿整齐划一的影响持续地被位于水平线砖层上的几何交叉线的偏好所强调。
1971年到1972年在韩国光州宋山里发掘的公元525年的百济武宁王和他妻子的合葬墓提供了这种联系,说明这种形式的砖在6世纪时继续被使用。这位韩国国王501年至523年在位,曾经于512年至521年之间送使者到健康并被梁武帝授予百济大将军的头衔。墓葬墙壁上没有出现画像作品,墓葬的建筑也仅仅与南朝中国的墓葬模式近似。[25]但是画像砖是以南齐的形式装饰的,除了六瓣花朵外,似乎已经完全替代了五铢钱和植物样式,而代之以八瓣花上的对角线设计(图12)。然而这些改变一定既反映了梁代(502~556)的内部装饰,也反映了韩国地方的偏好,但是如果将之与此时期中国南方其他地区繁复的植物主题进行比较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图11,12,13
有更早的证据表明,湖南和云南地区从汉代一直到北朝,在莲花形式方面仍然保持强烈的兴趣。例如,长沙出土东汉墓画像砖已经用一种可识别的四瓣花瓣围绕的纵横交错的植物样式进行装饰。[26]位于云南省的东晋昭通后海子石墓非常有趣,时间大约是公元386年到394年之间,壁画上绘有汉代六瓣和十二瓣花叶组成的呆板的莲花,以及类似罗盘设计形式的卷云纹中的四个方位神(图13)。这种原创性的艺术特征非常显著,黑色龟背包裹的像一个手榴弹,旁边还有像蛇一样的莲花,但是这种壁画可能是目前在四川成都发现的一种形象化的区域性版本,在这里死去的霍彪首次被埋葬。[27]换句话说,有趣的是昭通附近发现的东汉墓幸运钱树展示了几种侧面的莲花轮廓。[28]但是这些例子也不能解释植物装饰图案突然出现在5世纪末的原因。
长沙的刘氏家族墓的时代与499年的南朝2号墓葬一致,壁面水平砖层缺乏几何形状,并且与在丹阳发现的环绕莲花主题一样绘制得非常呆板。它们称之为“花鬘”的卷曲的藤蔓装饰纹样从底部到天顶覆盖了起来,非常具有装饰特征。

图14,15,16
画像砖拓片[29]能够使我们再一次看清卷曲的半棕榈叶形状,在棕榈叶中间部分,每一片叶子都被延伸,尖端弯曲,与早期西善桥墓中的同种类型相比较而言,形式似乎变得更加细长。在右边,以一种迂回蔓延卷曲的形式,十二片花瓣以来自古典远东地区的忍冬纹相间隔,其中的棕榈叶饰侧面为两片半棕榈叶形,但却并不是采用环绕藤蔓而弯曲的形式(图14)。仔细观察这些壁画图片[30],会发现当这种卷曲样式水平延展时,在画像砖的尾端会出现一种垂直型的不同的设计样式:在这里,植物,包括棕榈叶在内,两侧被两片半棕榈叶形上下辐射形成一个中间十二瓣的花形(图15)。与此相似但是更小一些的设计类型出现在长沙北部偏东边的湖北省武昌市郊区的一个南朝墓葬画像砖的末端[31]。虽然这座武昌墓葬年代不明,但是奢华的花饰品味被武昌发掘出的485年编号为193的镶嵌有多层莲花瓣的陶器和两簇半棕榈叶卷曲形的墓碑复制了下来[32]。在年代未知的画像砖拓片上,还可以看到一种不寻常的六瓣花饰,和包含有六瓣花饰变体的不同类型的卷曲装饰(图16)。这两种新形式在520年的梁墓碑刻中也有发现[33],其中一个是棕榈叶形藤蔓,另一个应该是一种沿着垂直方向重复的棕榈叶形式附以藤蔓卷须从半棕榈叶背面向下弯曲(图17)。
后来对这种卷曲藤蔓的界定,母题更加自由并且倾向于不再具有连贯性。这一观察符合来自南京附近的新宁工厂1号墓和邓县墓的设计(图9:2,3,8)。在这种奢华的花饰成熟期,风车设计中从中间莲花辐射出弯曲的植物的设计方式变得非常流行,并且花叶植物经常出现在边缘。尤其是在邓县墓画像砖上的奢华植物装饰非常令人震惊[34]。但是可能它代表了从长沙南部到武昌这一地区的奢华装饰倾向的高潮。例如,邓县墓的忍冬藤蔓(图18:中心)、棕榈叶和半棕榈叶在稠密的垂直方向的叶形装饰中显得不再那么易于识别了。

图17,18,19

图20-1,2 图21
位于墓室背面每一侧用多重拼砖构成的镇墓武士,大多数被有机构成的花叶形式交织的旋涡主题所围绕,具有强烈的暗示性意味。这种设计(borrorvacui)预示着唐代旋涡形装饰无处不在,但是它仍然是由独特的单个元素,如植物、花瓶等组成,旋转花叶不再正式融入到520年以后的波卷纹中(图19)。在其他邓县墓拼砖结构中,某些植物样式或者花叶边沿有一个相对简单的自然主义的特征,比如位于两身歌唱永生的鸟神之间的植物以及位于一位仙人两边的植物(图20-1,2)。然而,这些形式很显然不是来源于自然,而是来自更早期的艺术形式,这可以从雕刻在江苏蕲州汉墓和来自中国道教题材的带翼麒麟或独角兽和跪姿仙人的花纹轮廓中判断出来(图21)[35]。邓县墓拼砖既没有这种植物也没有弯曲的花纹边沿,而是有夸张变形的早期曾被描绘过的像是被风吹弯的植物样式。这种更加静态的装饰主题似乎成为520年梁朝“火红花束”风格的前驱。
对这种程序的有限的讨论还在持续开展着。这种特殊装饰主题的分析自然不足以接近邓县墓拼砖的时代,因为历史环境、墓葬结构和陶俑也必须作为和其他所有形式主题一样来进行研究。这种综合性方法已经被刘涵和安耐特·朱莉诺(Annette Juliano)的研究所采用:但是精确研究邓县墓的建造过程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位于湖南边界地区的南方政权控制之下,498年在北魏政权手中[36],甚至很难去给它安置一个时代标签,因为它很显然是南方风格,被认为属于5世纪晚期南齐时代,那么与它同时代的丹阳相关材料的关系也必须进行解释。正如已经被争论的,刻有“仙人戏虎”图像的胡桥墓的年代似乎更可能是495年左右,而且它的背景图案显示出“最早期”的花朵意向形式,这种样式也同样出现在邓县墓。因为较晚期的丹阳材料(图5)更接近邓县墓主题风格,有研究认为这种装饰纹样进一步延续到了6世纪早期。另外,胡桥墓拼砖中的弯曲植物和植物风车的区别可能是接近这些主题本源的结果,南方首都的绘画设计和帝王墓葬设计中的保守倾向,正如582年的镇江墓一样,可能甚至在诸如胡桥墓等更高级别的帝王墓装饰设计中都已经成了固化的形式。当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将诸如此类的考虑都放在脑海里仔细斟酌。如果邓县墓拼砖上这种类型的花饰比南齐丹阳墓“仙人戏虎”图(图2~4)和499年的长沙墓的例子(图14)更发达一些,那么它的时代仍然不可能晚于6世纪早期,(这一点)从南京附近的梁墓遗迹之一的萧弘(死于526年)墓石碑雕刻设计就可以判断出来[37]。这种复杂结构的拓片中可以看到,一对飞身向下的龙面对石碑背面的洞,而上部位于莲花基座上的蚩尤怪兽支撑着一个拱形顶,在它两侧两身胁侍兽昂首阔步似乎要表达什么。这种摆动的姿势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520年和似乎是6世纪早期汉代类型的出土物中非常流行[38]。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没有出现在邓县墓的主题中。此外,这种主题可在地面看到,例如植物随着叶片的纹路卷曲,似乎更加优美,比邓县墓中相互缠绕的设计或者丹阳墓类似的卷曲形式更加弱化。两侧面的植物伸向下方,到达三身饰有珠宝饰品的佛像两旁,比邓县墓相对简单的花叶植物更加复杂且细长。

图22
在佛教文本中,叠加的莲花植物作为普陀山石碑佛陀背光部分的装饰[39]。但是萧弘石碑的设计是基于单一的刻在不规则火焰纹末端的棕榈叶和半棕榈叶植物形式。与他们同时期的纯粹的装饰形式而存的金色放射性花纹可以与百济武宁王帽子上的装饰联系起来(图22)。这里,莲花和棕榈叶形式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非常漂亮而又时尚的风格,在韩国装饰中,散落的黄金坠饰可能是模仿水滴的造型而形成的。这种创造反映了520年左右梁代朝廷的最新样式,这个纪年雕刻在这座墓出土的一个银手镯上面[40]。无论如何,在萧弘墓碑上这种放射纹是由规则和不规则线形作为丰富的植物主题。类似的不同类型的中国装饰都毫无疑问位于不久后就被劫掠的南朝帝王墓中。不幸的是,武宁王的财富只是保留下来的其中一部分,它可以焕发南方装饰艺术的异彩。在这一方面,最近在中国北部的的考古发现更进一步展现了出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