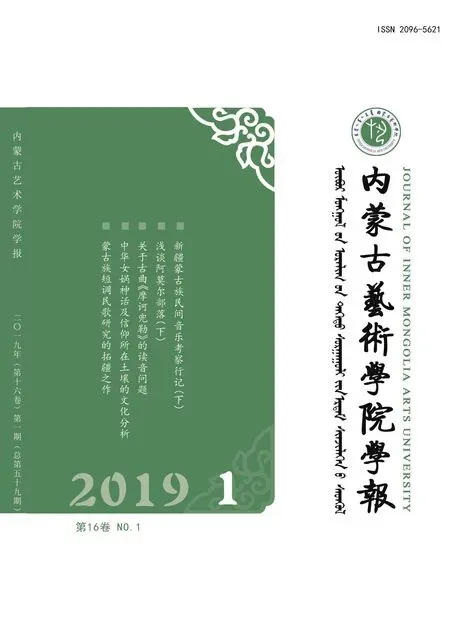民族音乐学美国学派的“源”与“流”
2019-03-28张竞方苗金海
张竞方苗金海
(1,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2,浙江传媒学院音乐学院 浙江 桐乡 314500)
引 言
“Ethnomusicology”源于“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但正式的发端是在1885年,英国学者J·埃利斯首次提出。同年,奥地利音乐家阿德勒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标》一文中,将比较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纳入音乐学中。当时的欧洲,由于受到进化论与文化传播论的影响,比较音乐学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以施图普夫为代表,包括埃利斯、萨克斯、赫尔索格等人,主要从事音乐史、音乐形态、乐器学研究的柏林学派,这也为美国学派的诞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民族音乐学“美国学派”的起源
博厄斯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他的“整体论”思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民族音乐学之后的发展。他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并从1896年开始直到1937年退休,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夸扣特尔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音乐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考察研究。他对于传统人类学的演绎研究模式表示强烈不满,并极力主张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获取可观真实的数据,然后小心谨慎地进行理论归纳,并且强调对归纳结论的检验。[1]博厄斯还提出了“历史特殊论”,他极力反对简单进化论,主张进化的法则只能从分析特定地域的实际历史获得。[2]历史特殊论的提出,对于之后人类学“美国学派”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美国从19世纪末起,在批判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文化人类学学派,既博厄斯的文化历史学派。二战前后,欧洲一批优秀的比较音乐学家纷纷移居美国,随着欧洲学者的进入,美国的“文化人类学”派与欧洲的“比较音乐学”派逐渐相融合。他们积极合作,一起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曾经作为柏林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尔索格也拜在博厄斯门下,受到了博厄斯的极大影响。终于在1950年,荷兰学者孔斯特提出了“民族音乐学”这一概念,这一提议在美国受到了热烈欢迎,“美国以阿兰·梅里亚姆等几个有人类学背景的学者不但赞同他的建议,还采取了具体行动,于1955年成立了‘民族音乐学学会’(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简称SEM),这一学会的成立使‘ethnomusicology’作为本学科的新名称在美国得到了确认。”[3]随着Ethnomusicology在美国的的发展,民族音乐学的“美国学派”也逐渐壮大起来。
二、“人类学派”与“音乐学派”溯源
民族音乐学的美国学派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分别侧重于从“人类学”和“音乐学”两个不同的方向着手研究,梅里亚姆认为“最理想”的“是这两种方法的融合,并在实际中对它进行修正。”[4]但在实际研究中,人类学背景的学者通常更多地偏向人类学的视角,而音乐学背景的学者则会更多地偏向音乐学的视角,这也导致民族音乐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流,并出现了以梅里亚姆为代表的“人类学派”,与以胡德为代表的“音乐学派”。
(一)梅里亚姆(Alan P. Merriam 1923-1980)与“人类学派”
梅里亚姆是美国的人类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也是民族音乐学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观念受到了博厄斯很大的影响,“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便是梅里亚姆在博厄斯的影响下提出。梅里亚姆在《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中写到:“民族音乐学可从两个方向来研究,最终目标是融合二者。……但看看民族音乐学的文献,这个理想尚未达到,因为大多数著述仅研究音乐本身,不提音乐所产生的文化背景。民族音乐学主要专注于乐音和结构,因而强调音乐学因素,而不顾人类学因素。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方面不太发达、不太为人们所理解。”[5]梅里亚姆强调音乐与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音乐不仅是声音,也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并且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是文化功能主义的开创者,他认为文化的功能“是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这个结论的重要性是在于人类活动的体系,包括对于物质文化的应用,并不是偶然堆集而成,而是有组织的,完善配置的,及永久的。”[6]
梅里亚姆也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影响,提出音乐具有情绪、审美、娱乐、传播、象征、身体反应、社会控制、服务和社会制度和宗教仪式、文化延续、社会整合十大功能。并在《音乐人类学》中提出了“三重分析模式”(见图1,梅里亚姆三重分析模式),即“概念—行为—音声”。

图1
他在书中明确写到:“由于在研究任何特定人群的音乐时都要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一个急切的问题就是究竟能否建立一种将他们全部包容进去的理论研究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必须兼顾民间评价和分析评价、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关视角以及音乐的多个侧面……这里建议一种模式,它虽然简单但是看来可以满足这些要求。它涉及三个分析层面上的研究——音乐的概念化与音乐相关的行为和音乐本身。”[7]三重分析模式受功能主义影响最为明显,但功能主义忽视了人类在人文方面的需要,梅里亚姆却认为音乐是作为一种人类习得行为而存在,有着很明显的社会特征,并强调了音乐在人文方面的文化行为。梅里亚姆认为,之所以能够产生声音,必然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这样的行为似乎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身体的行为。它又可再细分为实际发生过程中涉及的身体的行为、在发出声音过程中身体的张力和姿势,以及单个有机体对于声音的身体反应。第二类是社会的行为。它也可以再细分位作为音乐家的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行为和非音乐家个体在特定音乐音乐事件中必须履行的行为。第三类是言语行为,这是指通过言语表达的关于音乐体系本身的观念。”[7]“概念、行为、音声”必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了音乐的观念才会有行为的出现,有了行为才会产生乐音,这三者必须同时存在于一个音乐表演中。
在三分模式的大概念下,梅里亚姆提出了“文化中的音乐研究”,并接着提出了“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和“音乐即是文化”,从英文表达来看,这三者分别是“music in culture”、“music as culture”和“music is culture”。对于梅里亚姆提出的这三种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而言,人们显然是更加认可前两种表述,在讨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时,也总是习惯性地把“音乐即是文化”排除在外来讨论前两者。在笔者看来,首先,这三个概念不仅是包含与被包含、对等与不对等的关系,它们更多体现的是音乐与文化本质的问题;其次,这三种不同表达的方式虽然是梅里亚姆在不同时期所提出,但笔者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取代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三者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文化中的音乐这一概念,可以将音乐看作文化的一个下属部分,梅里亚姆已经意识到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但并没有将二者结合,虽然这里的音乐虽然处于文化中,但却还不能摆脱它的艺术本质。音乐作为文化这一概念中,音乐依然可以看作文化的一部分,但这里的音乐已经具有了文化属性,它与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条件下,音乐即可以充分地体现文化、代表文化。音乐即是文化这一概念,薛艺兵先生将其理解为“音乐和文化是同一概念,是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按这句话的逻辑关系,反过来讲‘文化是音乐’(culture is music)应该也能成立”,这一观点笔者是不赞同的。笔者认为,不能将音乐与文化看为简单的对等关系,“音乐即是文化”所指为音乐的本质已经成为了文化,音乐所表达的内涵是文化,所体现的价值也是文化。内特尔认为梅里安姆的定义“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是历史和民族志研究的常规方法,“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专门研究(Nettle,1983:131-132)。[8]
(二)曼特尔·胡德(Mantle Hood 1918-2005)与“音乐学派”
胡德是孔斯特的学生, 他在导师的影响下,进行爪哇调式体系的论文写作,这也让他成为了民族音乐学“音乐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德的“双重音乐能力”是出自语言学的“双重语言能力”,目的是要求民族音乐学的学者熟知自己所研究的音乐文化。“双重音乐能力”的构想,是他在教授印尼甘美兰音乐时所创造的一种教学方法:参与式教学方法。而“双重音乐能力”理论的创作灵感,得益于音乐人类学家查尔斯·西格的“音乐学结合点”学说,即音乐学研究有两种知识或表达方式:言语的和音乐的。言语知识是用语言来描绘音乐,但还应加上音乐知识,通过创造音乐获得音乐知识。通过“做音乐”再加上语言做研究的音乐学,就能相辅相成。[9]“双重音乐能力”实践方法的理论来源,基于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参与观察”的理论和方法之上。内特尔将“双重音乐能力”概括为“不仅要在音乐本身的术语里,也要在与它相关的文化内涵之中研究音乐。”[9]而梅里亚姆对于胡德的“双重音乐能力”并不相信,且批评学者们学习音乐时主动的参与和演出,他和其他一些人在那个时候认为双重音乐能力太主观、太任性、太不科学、没有学术性并且包含了过多的娱乐,即梅里亚姆所谓的“沙箱民族音乐学。”[9]
胡德也受到了博厄斯的影响,所以在他曾经提出过的两个定义中,也涉及到了音乐与文化。一个定义是:“民族音乐学是对一切音乐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8](1969);另一个定义则是:“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主题是音乐。但是与这个主题基本上不同而又互相依存的不妨包括一些有关这些学科的研究,如历史、人种史、民俗学、文学、舞蹈、宗教、戏剧、考古学、词源学、肖像学和其他与文化表现有关的领域……这种研究的似是而非的方法、目的和运用事实上是无止境的,但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题首要的还是音乐”(胡德,1985)。[8]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胡德被认为是“音乐学派”的代表人物,但在他的音乐研究中也是与文化紧密相关的,只是他的音乐与文化是割裂开的,文化只是作为一种途径,其主要研究目的还是对于音乐的研究。
三、“人类学派”与“音乐学派”的分流
胡德和梅里亚姆都是民族音乐学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人们至今仍在沿用他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陈铭道先生曾在文中写到:“1971年,胡德出版《民族音乐学家》一书。从此,进入民族音乐学大师的行列——在民族音乐学的大本营美国,至今没有人写过《民族音乐学家》之类的书。”[10]而梅里亚姆似乎是一个全新的开创者,之后很多学者们都是以他的观念为基础,不断加入新的东西来形成自己的理论。对于梅、胡二者学术的成就与贡献,一些学者指出了他们研究理论的不足,并在他们的观念上,重新拓展自己的观点;一些学者将他们的理论加以改进,提出自己新的见解;一些学者则是直接沿用他们的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便是莱斯、内特尔与中国学者杜亚雄、杨善武等。
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
赖斯是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加州大学教授、巴尔干音乐专家,提出了重建民族音乐学。他认为梅里亚姆的三维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便在梅里亚姆的三维分析模式上加以改进,提出了新的重塑模式(见图2,赖斯的重塑模式),并认为这个层次是辩证地、双向地同另两个层次相联系。

图2①
新模式的来源,一是他在多伦多大学教学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二是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对他的启发。他在《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一文中写到“民族音乐学家应研究音乐中的‘生成过程’,应回答这一表面似乎简单的问题:人们怎样创造音乐?或确切地说:人类怎样按历史构成音乐、由社会维持音乐并通过个人创造、体验音乐?”[11]并提出音乐文化应是“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与个人创造性”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模式。他认为“音乐是基于个人的创造性又是直接跟历史构成行、历史传统有关系,它受到历史传统的制约。音乐创造出来以后,又是社区或者村庄、部落等社会群体来维持的。”[11]在赖斯的这一模式中,“历史构成、社会维持和个人创造与体验”,分别也包括梅里亚姆三重分析模式的“声音、概念、行为”,这个模式中“仍用梅里亚姆的分析层,但各层次之间互相联系的方式较之一元化地探求因果、同源关系则是更灵活多变。因而更易达到。”[11]从而形成了一种纵横交错的立体研究格局。
内特尔(Bruno Nettl 1930-)
内特尔是犹太裔美国人,本科、硕士、博士均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编撰的音乐人类学的著作有14本,他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北美印第安蒙塔纳州的“黑足人”、伊朗德黑兰、印度马德拉斯,他将这些“边缘文化的音乐”价值带到了对“中心文化音乐”的研究,并以文化并置的方法,对中心文化音乐的价值观作了批评。[12]内特尔对文化的理解比较赞同爱德华·B·泰勒关于“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的定义,并将梅里亚姆“研究文化中的音乐”与“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巧妙衔接起来。他认为:“对‘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家和‘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家进行简单的分类,非常容易。有侧重点与何者为先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如下:人们如何考虑音乐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更确切的说,音乐与文化其他部分的关系),以及人们看待文化概念和音乐概念的不同视角。”[13]
他于1979年编著了《民族音乐学研究:29个问题与概念》,之后进行了拓展与补充,在2004年推出了新版的《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问题与概念》,将29个论题增至31个论题。汤亚汀教授认为:“两相比较二者的关键词,可以看出‘音乐与文化’变成了‘文化中的音乐’,‘技术与方法’变成了‘理论的视角’,‘阐释学科史’变成为‘阐释学科进一步拓展的视角’,可见新版载继承旧版目标的同时,更强调‘文化语境’、‘理论视角’和‘学科的新进展’。”[14]《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问题与概念》全书由四部分组成:(一)世界的各种音乐;(二)田野里的音乐;(三)文化中的音乐;(四)多元视角下的音乐。他在书中分析了梅里亚姆关于“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和“作为文化的音乐”,他认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这个概念,暗含了文化是一种有机单元组成的整体观,描述性地赋予音乐一种整体性的角色。然后在田野研究中确证它。称为‘作为文化的音乐’的方法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化,即人们采用一种文化本质的理论,将其应用到音乐中。”[14]并概括了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看待音乐与文化的五种方式,(一)采用列举各种因素的方法来展现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或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二)研究音乐的功能,内特尔认为美中文化中的音乐都有着其独特的功能;(三)将所有音乐生活整合到一种文化模式中;(四)音乐生产与文化的关系线;(五)将音乐与音乐生活看作社会性别、阶级、族群性等权力关系的表征。
内特尔对于梅里亚姆明确区分音乐的用途和功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梅里亚姆“企图表现音乐特征的列举,并非独指音乐,但却能够适用于所有的艺术,无可否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4]并用“金字塔模式”解读音乐的用途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将音乐的用途逐渐抽象为各种音乐功能,并进一步将音乐功能整合到它的文化模式里,通过表层模式与深层模式的结构主义的解析方式进一步深化了音乐与文化的关系的理解。[15]
四、“人类学派”与“音乐学派”的差异
胡德在其著作《音乐民族学家》中写到:“有一点是清楚的,音乐民族学领域中研究的主题是音乐”。梅利亚姆对于这一说法认为:“尽管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确实地同意这一点,但只要我们停下来去考虑如何界定‘音乐’,就发现我们再次陷入了困境。如果音乐民族学的方法是跨文化的,它确实如此,那么界定‘音乐’现象的问题就成为决定性的。音乐民族学家不需要告知在一些简单社会中人们没有‘音乐’概念。”[16]内特尔曾在文中写到:“1950-1970年这段时间最明显——他们倾向于分成两派,互相争执,一派专注于音乐‘本体’,另一派则关注文化背景。前一派通常认为他们是在文化背景中正儿八经地研究核心问题——音乐本体,并把另外那些‘背景论者’贬为不能直接研究音乐的业余爱好者;而另一派则赞成人类学的方法,认为他们的对立派很幼稚,甚至不能理解音乐的人为现象,因为他们没有把音乐看作是文化的产物,不愿研究音乐的概念、人们的态度或行为方式,而只关注音乐作品本身。大约在1980年后,这两派逐步融合。”[17]内特尔文中的两派,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类学派”与“音乐学派”,熊晓辉在《音乐人类学的美国学派研究》中说到:“在音乐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美国还形成了以胡德和梅里亚姆为代表的两大派别的争论,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音乐人类学,它的定义是什么,用什么样的记谱方法才能更科学地反映音乐的原有形态,能否用西方观念来记谱等等。”[18]
胡德曾在文章中写到:“在早期出版的一些刊物里,我曾下了一个总的定义:‘民族音乐学是从它自身的角度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去研究音乐。’我的原话含义很明确,‘从音乐自身的角度’无疑指的是‘作为文化的音乐’,‘从社会文化背景去研究音乐’特指‘音乐乃是文化的一部分。’”[19]对于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梅里亚姆也认为:“音乐人类学是由音乐方面和人类学方面构成的……我们可以从概念上区分为这两个侧面,但其中一方失去了另一方,就不可能是真正完美无缺的了。”[20]杨民康教授认为:从民族音乐学的两类定义和基本概念来看,民族音乐学中“音乐学派”与“人类学派”虽然都不否认自己的研究对象包括音乐和文化内涵两方面内容,但二者在研究观念上仍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前一类学者的观念是建立在功能分化基础上,音乐性(即研究对象的艺术性或审美特性)是其永恒的研究主旨,以致其所认识的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乃是以条块分割为主……而在后一类学者的眼中,音乐与文化之间呈相互包容、不易分割之状,故此应该把音乐置入“文化(环境)中”进行研究,而不是去进行分离性或割裂性的考察。[8]
结 语
通过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的梳理,笔者发现,民族音乐学美国学派的根源是相同的,无论是“人类学派”或是“音乐学派”都受到了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影响,他们都反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并且都不会忽视文化在音乐研究中的重要性。正如内特尔所说,音乐学方面与人类学方面可能只是“反映了个人之间的竞争、学术策略、最多也就是职业侧重点方面略有差异,而非思想流派的差异。”[13]在笔者看来,“人类学派”与“音乐学派”学科属性并无根本区别,由于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背景与知识结构,还有学者们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的侧重不同,才会造成学术方向的差异。
但在一段时间内,很多人们过分的夸大了这二者的差异,认为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这一点是匪夷所思的。并且,随着这一学科不断地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同时在吸收和借鉴他们双方的观点,将二者理论融合,更多地从文化中去理解音乐,从音乐中去阐释文化。由于民族音乐学的派别问题,致使这一学科进入中国后存在着诸多争鸣,例如Ethnomusicology的译名、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等问题,同时,从“人类学派”与“音乐学派”分流出“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两个不同的称谓,也曾在我国引起不小的争议,且至今仍无明确的学科名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历史与文化底蕴,作为当代民族音乐学研究人员,我们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也应当为建立一个符合我国特色、适用于我们本民族的民族音乐学体系而奋斗。
注 释:
①引自孟凡玉.《构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立体结构模式》.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