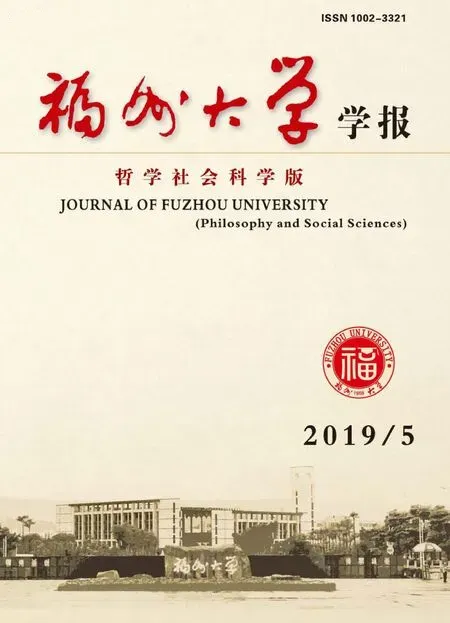中国现代游记的意境探论
2019-03-24陈邑华陈日升
陈邑华 陈日升
(闽江学院人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中国现代游记的创作自“五四”始一直贯穿于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现代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纵观中国现代游记的研究,一是出现了游记文学史,二是游记名家的文本研究,三是游记理论研究亦有进展,主要是探讨游记文体要素、类型特征等,少有专题研究其意境。现代游记许多作品一版再版,成为当下人们喜爱的经典文本。这些现代经典游记往往有其共通处,即富于意境美。这意境呈现出什么审美特点,又是如何创构的?
意境是中国的传统美学命题。王昌龄在《诗格》中率先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1]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集意境理论之大成,将境界提升到文艺本体的地位,涵盖写景、抒情和叙事各类艺术境界。“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2]并将意境分为两种:“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3]宗白华认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4]这三层次揭示了意境的复杂结构与丰富的审美内涵。借鉴唐代王昌龄的“三境”说、近代王国维的“二境”说和现代宗白华的“三层次”说等理论及其分类方法,从现代游记的创作实际出发,以主体把握客体的不同审美方式,将现代游记的艺术境界分为三种类型:物境、情境、意境。物境,即注重自然客体的审美发现;情境,即注重主体移情的审美再造;意境,即注重哲理意蕴的审美探究。三境的划分,立足于主体把握客体的侧重点不同,也呈现“境界层深”的不同层面。物境的逼真如画,情境的诗情画意,意境的物我同化,皆有境界创造,都有各自的艺术内涵与审美价值。三境既“分立”又“互渗”,在互动中转化和升华,都有可能抵达引人入胜的胜境。物境中亦有情感投入和哲理思考,只是重心在于客体景象的再现。情境中亦有景物描写和哲理感悟,只是着重表现主体对客体的情趣。意境创造以物境与情境为基础,以哲理升华为意蕴,寓情理于境象之中,抵达“思与境偕”、“意与境浑”的妙境,意蕴深远。
一、意蕴深远
现代游记意境的生成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审美境层,由物境、情境、意境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如果说,物境的审美观照方式为“以物观物”,情境的审美观照方式为“以我观物”,那么,意境的审美观照方式则为“神与物游”“物我两忘”,即在审美观照中既非“物”胜“我”,亦非“我”胜“物”,而是在“物我两忘”中相融无间,浑然一体,抵达“意与境浑”的境界。正如朱光潜所说:“总而言之,在美感经验中,我和物的界限完全消灭,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自然打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5]
现代游记的物境逼真如画,如孙福熙《安纳西湖》描摹安纳西湖的景致,使人宛如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彩写生画,其审美特点可概括为“真”;情境富于诗情画意,如钟敬文《西湖的雪景——献给许多不能与我共欣赏的朋友》游赏雪中西湖“诗思在灞桥风雪中”的情味,创造了一个个清朗幽逸、诗意盎然的情境,其审美特点可概括为“韵”;而意境物我同化,其审美特点则可概括为“远”。现代的经典游记,审美主体畅游于自然天地间,摒除了平日的喧嚣与烦杂,静观自然山水,“物”生命化了,“我”对象化了,“我”的内心感应着自然的气息,自然亦染上我的性灵,抵达物我浑融的意境。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可谓是现代游记美文的典范之作,描摹荷塘栩栩如生,情景交融,创造了物我同化的意境美。审美主体“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发现“独处的妙处”。月色中的荷风姿迷人,虚静脱俗、淡泊致远,“我”似“荷”,“荷”似“我”,审美主体已融入这荷塘月色,荷塘月色浸透着审美主体淡淡的喜、淡淡的愁,物我合一。荷塘月色,静谧淡泊、超尘脱俗,却又情致动人,有着梦幻般的美。这意境有着无穷的意味,“好似太虚片云,寒塘雁迹,空灵而自然!”[6]
在《钓台的春昼》中,郁达夫溯江而上,描绘了一幅山水长卷。其中对船行到钓台山脚下的一段静景的描写,出神入化:“清清的一条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四围的山包得格外地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并且山容峻峭,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郁达夫敏锐地捕捉住山势带给人的感觉。静寂中,双桨的摇动,虽已无比轻缓,却也有了“幽幽的回响”,以动写静,形神兼具。这片山水静极幽绝,游者身心已融入这幽远之境。
沈从文十多年后返回家乡,行船于昔日的沅水,置身于久别重逢的山水中,熟悉的画面、熟悉的场景,内心深处缱绻的缕缕乡愁,与宋元诗画的意蕴极为契合,《湘行散记》《湘西》行文中多处提及宋人画本。宋元文人画一方面重墨、轻色、尚简,推崇庄子的虚静恬淡;另一方面因文人感怀故国山河,国家兴亡感不时萦绕心间,从而形成了文人画特殊的意境,既淡泊宁静,又潜伏悲凉之情。宋元文人笔下的山水诗亦蕴涵着内敛含藏、似淡实腴的美。如杨万里写西湖的名诗《晓出静慈寺送林子方》,高旷寥廓中,蕴含着“万物生意”的神采。沈从文湘西游记呈现的意境多为宋元文人诗画的意蕴美。如《湘西·泸溪、浦市、箱子岩》描写沅江上游的风光,落日、小渔船、炊烟、水凫,写意般勾勒,银红、紫灰、绿、白,色彩鲜明而沉稳,寥寥几笔,形象逼真且满含着诗情,生动描摹了沅江静美而略带忧郁的景致。《沅陵的人》中,山水烟云、村落长桥、香草山花,景致布局,俨然一幅山水画,绮丽、飘逸,其意境空灵、静美、忧愁。正如沈从文所说:“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桃源与沅州》中,描写沅州上游溪谷里的芷草,“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坐船游白燕溪,可摘花赏花,“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那种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小小洄旋的溪流,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随处可见的兰芷,与周围的崖石、奇葩、溪流,甚至与屈原诗歌交融交织,审美主体已陶醉于这“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这般境界,正如宗白华所说的:“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7]
现代经典游记的意境,具有深远的审美特点。其远,或清丽淡远,或静寂幽远,或陶然悠远。其审美趣味倾向于静远、空灵,近乎禅境,相通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境界;其深,则为“深,像在一和平的梦中,给予观者的感受是一澈透灵魂的安慰和惺惺的微妙的领悟”[8]。
现代游记如何创构这一深远的意境?“这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9]现代游记意境的创构中,最深的“心源”,即为自我的诗性体验,“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即以境悟理。
二、诗性体验
诗性体验“指人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所经历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历程和感情的活动,它直达人的生存的深层,具有心灵性、内在性和知觉性的特征”[10]。现代游记中,这诗性体验独具特色,富于现代性,往往是游者的人生经验、性情志趣于“神与物游”时衍生的一种生命体验,具有自我、自然、社会交融交织的特点,富于个性化,亦具有时代性、社会性。
中西文化熏染下的郁达夫,既有古代名士隐逸的情愫,又有现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深情厚意。特别是移居杭州和南下福建的前后五年,是郁达夫游记创作的鼎盛时期。其游记善于捕捉自然风物的特点,融入自我的人生体验,与之同融共振。如立在五峰书院的楼上,郁达夫听飞瀑清音,仰视、对视、展望四周的景致,“一种幽静,清新,伟大的感觉,自然而然地袭向人来。”(《浙东景物纪略·方岩纪静》)进而体会到宋儒喜欢利用山洞或风景幽丽的地方作讲堂,是想借自然的威力来压制人欲的良苦用心。郁达夫精心描摹远景、近景,自我与自然相互感应、交流,体察自然与人生的关系,创造了神与物游的境界。郁达夫描写雁荡山的秋月,海水似的月光,天色苍苍,四周岑寂,“奇异,神秘,幽寂,诡怪,当时的那一种感觉,我真不知道要用什么字来形容得出!”(《雁荡山的秋月》)深情的摹景与感物的风怀,来自生命的直感与体验,沉郁、深邃。游记中亦常常“旁涉一笔”,讽古喻今,针砭时弊,饱含着感时忧国的深厚情意,其意境情理交融、意味深长。
钟敬文性格内向,自幼喜好读书,知识广博,尤爱“读诗写诗”,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钟敬文喜好山水,尤为喜欢岑寂、清净的景致,欣赏幽逸的情趣。其游记注重游历的感受与体验,善于捕捉欣赏自然山水的情感体验。“衰颓的情调”,“高寒旷朗的感觉”,“幽逸的情致”,“幽渺、古旷的情趣”等,审美主体的情趣、情思悄然融入自然山水的描摹中。如中秋晚上,钟敬文酒后只身到临海公园的短围墙上坐着。海潮高涨,自然的音波华杂,但四周的情调却是无比的寂静。“我这时,默默地遥望那对面如梦的山峰,被一种不可言说的感情支配着,深深地、深深地。海面有三两小舟在浪涛上摇簸,似乎显示着人生的飘荡和我此际心境的无着。这时,酒意都消失了,此身今宵的归宿处,也已觉在迷濛中。”(《海滨》)钟敬文期望在自然中陶然忘我,可现实世界的黑暗污浊、自身处境的苦闷失望,总是如影随形,难以做到真正的超然物外。缘情写景,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总渗入自身的体验,其意境清朗敦醇,自有一番幽情别趣。沈从文写湘西游记,源于离乡十多年后重返魂牵梦绕的故乡之行。往昔湘西熟悉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重现在眼前,目睹今日湘西的人、事、物、景,熟悉湘西历史,挚爱着湘西的沈从文,沉潜心底的情思不再只是游子的离情别绪,而是温情与伤感、哀戚与悲悯、希望与失望并存,交织交融着自身在湘西生活及出门在外的经历体验,融汇着自己对人生,对历史的思悟。湘西游记屡屡提及时间,还以时间的不断转换,将昔日的风景、现实的情景自然组接在一起,由个体的人生哀乐触及湘西的历史以及时代的风云流变,由此引发对湘西生命的境况、湘西存在发展的追问与思考。
冯至的《山水》中,自我溶浸其中,感受、体味生命,感情与理性交融交织。抗战时期的中国,物质匮乏,生活艰难,而昆明朴素的山水给予冯至丰富的精神滋养。里尔克倡导的原人式的观察以及“经验”理论成了冯至的创作理念。正如冯至在《山水》后记中,把体验比喻为一粒种子,在身体里沉埋、发芽、开花、结果。冯至从自然山水、平凡人物中领悟自然,感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真正为战后做积极准备的,正是这些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他们绝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在混沌中他们是一些澄清的药粉,若是混沌能够过去,他们心血的结晶就会化为人间的福利。”(冯至《工作而等待》)冯至坚信踏实努力工作的人,是中国的希望,是喧嚣混乱时代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在幽暗的生活中,冯至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工作而等待”的信念。《山水》富于现代性的哲思,已“化为人间的福利”,给人们无尽的精神滋养。
“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11]现代游记的意境,融入了“深心的自我”,融入了自我对生命、自然、社会、历史、宇宙等的诗性体验。这一诗性体验富于个性色彩,又带着现实社会的印记,既有感性的生动性,又有理性的抽象性,具体而抽象。由此,“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12]
三、以境悟理
游者畅游于自然天地,从最深的“心源”,与“造化”接触,于物我浑融的境界中产生“突然的领悟和震动”[13],以境悟理。正如沈从文所说的,“一切优秀作品的制作,离不了手与心。更重要的,也许还是培养手与心那个‘境’,一个比较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单独把自己从课堂或寝室、朋友或同学拉开,静静的与自然对面,即可慢慢得到。”[14]沈从文是一位勤勉、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创作经验的作家,对于创作心境有着切身的体验。显然,这是作家创作的经验之谈。现代游记意境的创造,游者往往沉浸于“境”中,于物我浑融的自然之“境”中有所思有所悟,以境悟理。
徐志摩在游记中多次提到单独的境,如“‘单独’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的机会。”徐志摩在康桥喜欢单独的状态,在这“单独”的境地,沉醉喧嚣尘世中无法聆听的天籁,寻觅倾心向往的自由、美与爱。“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徐志摩心无旁骛,全身心投身大自然,眼睛、鼻子、耳朵细细地享用着、感受着、发现着大自然的种种美好,收获“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人与自然交融交织,身心愉悦,体悟到自然对生命与人生的重要作用,体悟到深刻的生命哲学:“人是自然的产儿”,“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分取得我们继续的资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在《寄小读者》中,冰心平时一日几次走过慰冰湖,总是形色匆匆,“一边看晚霞,一边心里想着功课”。紧张匆忙中,自然无暇顾及外面的世界。生病了,在沙穰疗养院,不再惦念功课。在单独的环境中,生活简单,却又丰富。“如今呢?过的是花的生活,生长于光天化日之下,微风细雨之中;过的是鸟的生活,游息于山巅水涯,寄身于上下左右空气环围的巢床里;过的是水的生活,自在的潺潺流走;过的是云的生活,随意的袅袅卷舒。”(《寄小读者·通讯十四》)与大自然朝夕相处,自由自在,诗意盎然。“‘闲’又予我以写作的自由,想提笔就提笔,想搁笔就搁笔。这种流水行云的写作态度,是我一生所未经,沙穰最可纪念处也在此!”冰心在这无拘无束的时空中,身心完全放松,尽情尽性地浏览、游荡于大自然,如此诗意如此率性地将所感受的爱与自然的美如此美妙和谐的融合在一起。冰心捕捉着大自然的种种风姿,凝神体察万物之间的关联,体悟物我之间的交流,把自然生命化、性灵化,自然有如启悟性灵、可倾诉情怀、可寄寓情感的智者、母亲、友人。冰心陶醉于自然,于自然中寻味种种哲理启迪,如从蒲公英和雏菊中,“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愿“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人人平等”。(《寄小读者·通讯十二》)由病中女伴的互相怜惜、互相爱护,体悟到“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寄小读者·通讯十九》)
朱自清独自一人赏荷塘月色,在这片幽静的“境”中,对自我对生命的状态亦有了独到的领悟,“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这是独处的妙处”,月色的荷塘朦胧富于诗意,空灵淡远。郁达夫的《方岩纪静》精心描摹了五峰书院天造地设、清幽岑寂的境界,体味着这虚静之“境”,“一种幽静,清新,伟大的感觉,自然而然地袭向人来”,进而体悟到宋儒选择这造化奇境作为书院的良苦用心,即借自然以抑人欲。冯至《山水》中的大部分游记,写于寄居昆明时期,昆明朴素、安静的自然山水成了冯至创作的源泉。《一棵老树》《两句诗》《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描绘了种种虚静之“境”,夕阳、村女、羊、山、树、鼠曲草、水牛、老人,一切都如此安宁和谐,人与自然,浑为一体。“我”也融入了大自然的虚静之境,浑然忘我,意境古朴、悠远。冯至从这些朴素的山水、平凡的人物中获得精神的滋养,生命的启悟。《山水》贯穿着冯至的生命哲学,遵循生命的自然循环,从容淡定面对生与死。生时,勇于担当;死时,坦然面对。意境澄明清朗。
俞平伯在《陶然亭的雪》中,审美主体“悄对着那排向北的窗”,静境中悠然欣赏着“窗外有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册页”。意境清远、静寂,而后不见鸟儿、虫儿,不见行人的叙写,以及对“蝉噪林逾静”,对“乍生乍灭”,“闲闲的意想”的体悟,营造的禅境寂静、幽眇空旷,令人若有所思若有所悟。游者徜徉于自然山水,摒除了平日的嘈杂与烦忧,身心自由、放松,超越了平常的自己,回归本真的自我。“物”生命化了,“我”对象化了,沉潜于物我浑融的境界中,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15]。意境这一审美境层可说是“一种东方艺术中以‘境’悟理的超象审美境层,是意境创造中客观存在着的东方型哲思审美境层”[16]。
中国现代游记的意境,是审美主客体融合、物我同化而富有意蕴的艺术境界。它综合物境与情境之长,超越二者各有所偏的局限,而把游历所见所感所思融会贯通,升华为对自然山水与人生社会内在联系的生命体验和哲理感悟,意蕴深远。这一意蕴从具体景象领悟而来,是具象与抽象、有限与无限的有机统一,是以意化境,以境悟理。物我浑融的自然之“境”充溢着审美主体的诗性智慧,流荡着自然、自我、社会交融交织的感悟哲思,具体而抽象,深远而悠长。
注释:
[1] 王昌龄:《诗格》,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2]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
[3]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页。
[4][6] [7] [8] [9] [11] [12] [13] 宗白华:《艺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7,186,190,197,191,194,198,191页。
[5] 朱光潜:《谈美·文艺心理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4页。
[10]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14]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15] 叶 朗:《胸中之竹》,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16] 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