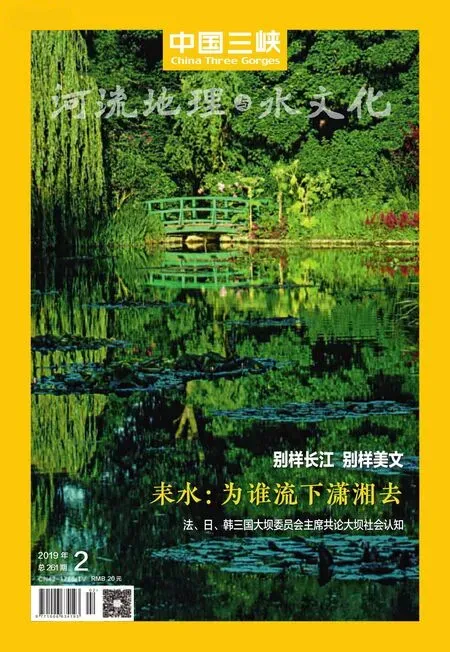蔬食记
2019-03-23文河绘图刘鑫编辑王芳丽
◎ 文 | 文河 绘图 | 刘鑫 编辑 | 王芳丽
白菜
我们这儿,淮北平原,一般农家,都种大白菜。
牲口粪上得足,地壮,菜叶刚长出来,贴地皮儿卷着,水汪汪的。静静看一会儿,心里有淡淡的喜悦感。
白菜挺喜欢张扬的,菜叶四下里散着,你挨着我,我挨着你,蓬蓬松松,仿佛一丛一丛的。到了秋天,就开始收心了,菜帮支棱起来,一层一层向里收,一棵是一棵,每一棵之间都保持着相应的独立距离。就像有些人,年轻时张扬,简直跋扈,入了中年,则变得格外内敛,甚至沉默寡言起来。
下霜了。白菜帮儿收得紧紧的,瓷实。用手按,按不动。仿佛白菜的心里,有太多的事情藏着。
下雪之前,白菜得收回去。
北方的雪大,天寒地冻。白菜冻僵了,会走味儿,所以,最好把白菜放入地窖。没有地窖,放在厨房里也行,一般都是对着锅灶,靠墙角一棵一棵码好,码得整整齐齐的,上面再盖一层干麦秸。冬天,锅灶里烧火,厨房暖和。炒菜味儿,蒸馍味儿,刷锅水味儿,柴草味儿,炊烟味儿,还有白菜清幽幽、暗沉沉的味儿,交织在一起,很好闻。
白菜炖豆腐,北方人的普遍吃法。炖汤,嫩白菜叶、嫩白菜心最好。咕嘟咕嘟滚开的汤,菜叶菜心,稍稍一烫即可,清,鲜。
下锅擀面条,也可以揪几把白菜叶放里面。

白菜帮儿,可以醋溜。生姜片,辣椒,醋,素油。油熬热,姜片和辣椒炒出味儿。菜帮切成长条,大火一过。醋溜白菜,脆,水灵。
儿时,雨雪天黑得早,小北风呼呼刮着。夜晚真漫长呀。窗棂上是新贴的旧报纸,风一点也刮不进来,煤油灯点上,屋里亮堂了。那时,父亲还是小学教师,常从学校拿些旧报纸来练书法、包东西。
母亲问,吃什么呢。
父亲看看天,想了想,就对我说,去,喊你国安大伯去,晚上我俩喝两杯。
我蹬蹬蹬跑到邻居家,刚进院子,还没看到人,就喊道:“大伯,晚上喝两杯!”
国安大伯哈哈大笑,说,好啊。
国安大伯和父亲对坐在椿木小方桌前,母亲很快就整出两个家常菜。父亲用火钳从锅灶里把去了火气的劈柴疙瘩夹几块放在瓦盆里,一盆暗火,暖乎乎的。冷酒伤胃,父亲就把小塑料桶里的高粱烧酒倒进白瓷缸里,在火上温热。两人对酌,说些闲话。
两人喝到高兴的时候,母亲又端上一盘凉拌白菜心,菜心切得细细的,白嫩,清爽。国安大伯用筷子蘸些酒,送到我嘴里。我用舌尖尝了尝,好苦,好辣。
我把房门开个缝,趴那儿向外面看,一股寒意灌了进来,真冷。风嗖嗖掠过房檐,没有星。夜,黑透了。
萝卜
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么,我就爱萝卜吧。但,我不爱空心大萝卜。
我们这儿主要种青萝卜,白肚青把。淤土地里长的水份少,质地密实,炒着吃最好。五花肉切片,萝卜切片,加酱油炒,鲜而不腻。
沙土地里长的萝卜水灵,个儿也更大,微甜,适合凉调,拌萝卜丝。小时候,有两年,初冬,父亲和村里人一起去县城附近买这种萝卜。那时村庄旁的公路上,一天只通一次汽车,去县城很不方便,他们也舍不得花几毛钱坐车。他们就拉着木板车,带着干粮,天麻麻亮出发,走着去,天落黑才回来。一来一回,几十公路,就为了那么一小板车萝卜。那时贫穷,活得执著而热情。
我们这儿也种红萝卜,但种得少。可能红萝卜有点辣吧。红萝卜的形状很好看,圆圆的一团,有温柔的弧线。颜色很艳,切开,萝卜皮儿的里侧,甚至红得发紫。
白萝卜,浑身皆白,只能炖汤,此地不生。
还有一种萝卜简直就是水果,水萝卜。这种萝卜皮儿薄,深青,状若红萝卜而小,水分丰富。算是萝卜中的尤物。洗一洗,直接生吃,咬一口,脆,清甜,原汁原味。
农家节俭,萝卜缨也舍不得丢。洗净,开水煮熟,搭在麻绳上晒干,然后收起来,放袋子里存着,算是干菜。冬天,吃豆面条时,放锅里一些。豆面条煮得黏糊糊的,很好吃。萝卜缨有点青涩味儿,也算是别有风味吧。还可以腌制。萝卜缨洗净,晾去水分,放在坛子里,撒下很多盐。吃的时候,咸味儿洗去,切碎,拌上小磨麻油,香中带一点清苦。

几年前的夏天,去乌镇,细雨绵绵。细雨中的江南小镇,看上去更有韵味。飞檐,曲廊,花砖,青苔,兰草,天井,荷花缸。仿佛整个岁月,就这样在滴滴答答的雨声中,悠悠来了,悠悠去了,又绵绵不尽。沿河两岸,卖有一种腌制的小萝卜,小巧玲珑。套用《红楼梦》中刘姥姥的话来说,这萝卜头长得可真俊!买几包带回去尝尝,咸中带甜,甜中透脆,很是可口。
过了年,开过春,天气变暖,萝卜会发芽。这样,萝卜就变“糠”了,就成了空心萝卜。空心大萝卜,看上去很好,但味儿其实已经寡了。
茄子
我们这儿的农家,都愿意种青茄,极少种紫茄。青茄呈椭圆形,弧线极美。紫茄紫郁郁的,细长,皮儿比青茄略厚。
茄子开花结果,得打杈。杈分公杈、母杈。鲁迅有名言,删夷枝叶者,决得不到花果。但公杈得摘去,否则枝杈纵横,争抢营养,影响通风,不利于结茄子。
茄子的叶子大,糙,涩。钻在茄棵里打杈,手臂给刮得痒辣辣的。
茄子喜水,夏天,太阳毒,得两三天浇灌一次。太阳落下去了,天还很亮,用铁皮桶一桶一桶把水从水井里提出来,倒在沟畦里。流水顺着沟畦流向茄棵,咕咕直响。菜地吃足了水,菜才旺。
茄子垂下来,挨着土的地方,容易起瘢。头茬儿茄子,瘢痕多,但好吃。

新茄子下来,天已经热了。母亲煎茄子,在案板上把茄子切成均匀的小片,放入搅拌好的面糊。猪油炝锅,烧热,煎。煎得微焦,微黄,油亮,锅铲铲出,放入青竹蔑编成的笊簸里。这样,一直煎够一家六口人吃的。茄子煎好,还要熬。锅里放上油,辣椒,大料,炸出味儿,再注入半锅水,烧滚,把煎好的茄片倒入里面烧开,放入一些鲜嫩的小青菜。最后,再放一些刚揪回的大茴香提提味儿,一锅饭就算成了。
母亲做饭,我烧锅,一把把向灶膛填麦草,厨房里闷热。我抱怨,吃顿饭,太麻烦了。母亲便训斥,你是连吃都嫌费事!
现在想想,吃,也真是对生活热爱的一种体现。古乐府里,远方来信,山川阻隔,梦寐相忆的两个人,信里浮言尽去,不作任何寒暄语,唯郑重嘱咐“加餐饭,长相忆”。最深切的关怀,反而只能是这样现实,具体到吃饭穿衣。饭要吃饱,衣要穿暖。
青椒炒茄丝。青椒切细,茄子切丝,大火炒,不能炒老,也是一道家常菜。
蒸茄子。茄子切成条,蒸,蒸烂,蒜泥一拌,即可食用。
《红楼梦》里,贾府做工复杂的“茄鲞”,好吃倒是好吃,但讲究到暴殄天物的程度,已是过分了。吃饭,最重要的是吃得安然。身心安然,如此才好。
小时候,父亲骑大架自行车,带我走亲戚。是家远亲,离得很远,不常来往。天亮出发,到了那儿,已近午时。午餐很丰富,吃的什么,都忘了。唯记得饭后,亲戚家切了一盘生茄条,端上来让我们吃。我家从没生吃过茄子,我大为惊讶。父亲出于礼貌,吃了一根。我坚决不吃。但很多年过去了,那种生茄子浓郁青幽的味道,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入了秋,茄子继续结。秋茄子皮厚,不好吃。青茄子长老,就会变白,进而变黄。秋阳下,黄灿灿的,又很静。风吹过来,菜园一片沙沙响,但某个看不到的地方,还是显得静。老茄子留种,第二年继续种。一年一年,仿佛日子多着呢。但慢慢的,人还是老了。
村子里,很多人,活着活着,就不见了。
蚕豆
蚕豆,亦名罗汉豆。其实,我更喜欢这后一个名字。但我们这,从没这个叫法。
蚕豆的命皮实,可以种在河畔,地边儿,荒疏的林间。丢一粒蚕豆籽,扒个窑儿,埋里面,就不用再过问了。冬天,蚕豆棵青青的,很单薄的样子,但下大雪,也冻不坏。
老家里的人,命都皮实,也像蚕豆棵。所以,也活得豁达,生死无畏。
蚕豆花开了,天变暖和了。
蚕豆花白色的花瓣,带一点跳脱的淡紫。花心处又带一片深黑,像一滴慢慢洇开的焦墨。早晨,太阳出来,黑白分明的花瓣上,大露水珠子闪闪发光。蚕豆花总给我一种奇异神秘的感觉,仿佛它们从遥远的地方,刚刚赶来。
蚕豆花在地头儿静静开着,天空微蓝,有几抹云缕静静停在那儿。花斑鸠在树梢一递一声地叫,两只,东一声,西一声,相互呼应。就那么叫着,叫了很长时间,似乎相互期待着什么。它们怎么不飞到一块儿呢。树上新叶刚刚长齐,还没成荫。仿佛有很多故事,正要开始。
花谢了,蚕豆角长出来了。蚕豆角水嫩,拌面糊,油煎,然后再放汤里煮一下,连皮儿吃,鲜极。但老家人很少这样吃的,说是糟蹋东西。
鲜蚕豆剥壳,一粒一粒,深青,饱满,有点古拙。清水煮,不加任何材料,连盐也不放。煮熟,直接吃,味道鲜而质朴。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吃法了。真山真水,自然无饰。

蚕豆放进小砂锅,八角,桂皮,茴香,辣椒,盐,小火炖。蚕豆炖熟,炖面,滴些小磨麻油,就成了。端起来,放在一张小白木桌上,坐下,用小汤勺一勺一勺盛着吃。院外,香椿树头茬叶子被掰去,第二茬又长大了,成荫了。又听到斑鸠叫。很快,就能听到蝉鸣了。
剥了壳的鲜蚕豆,再剥去皮儿,只要豆瓣,和韭菜放在一起清炒。韭菜的味道张扬,蚕豆的味道内敛,二者恰好互补。青青翠翠的一盘,光阴深秀,滋味鲜美。五月深碧,麦子出穗、断脸儿、灌浆。该准备丰收了。
蚕豆晒干,用油炸,炸焦,炸开花,撒上盐,下酒。冬天,农事已毕。劳累了这么长时间,该歇息歇息,散散身子骨了。
豆芽
豆芽,有绿豆芽,有黄豆芽。这里说的是黄豆芽。
挑拣圆滚饱满的黄豆,清水浸泡,豆皮儿泡软,水倒掉,放在盆里,用湿棉布盖住。盖得严严实实,放在厨房角落的暗影里。母亲说,豆芽见了光,就变绿了。变绿的豆芽有什么不好呢?我想不通,越发对棉布遮盖的豆芽感到好奇,想看看它们萌芽没有,到底怎么样了。就偷偷掀开棉布,看。也没见有什么,倒是闻到一股浓浓的豆腥味儿。
黄豆生芽了,黄莹莹的。两个豆瓣紧紧闭合,向下勾着,有些呆头呆脑。
炒豆芽要用生姜片炝锅,最好再放几个红尖椒,豆味儿重,得用辛辣之味儿压一压。
豆芽炖汤,豆芽炖得越面越好。豆芽根儿炖烂,放几根葱。豆味儿入汤,风清云淡,淡之欲无,汤就变鲜了。

院子里的桂花树下,堆着一堆盖房子剩下的细沙。母亲抓把黄豆埋进去,浇桶清水。过几天,青绿色的豆芽探头探脑地钻出来。母亲扒开细沙,把豆芽拾掇干净,午饭时,清寒的饭桌上,便又多了一盘小菜。我们兄弟几个,吃得高高兴兴,好像额外多得了什么。
懂生活的人,能把清寒,变成清欢。
我们这儿有道菜,豆芽炒粉丝,加肉末,叫蚂蚁上树。
麦子收割后,等一场雨,种豆子。地头儿豆芽出得稠,得剔掉。豆芽刚钻出地皮儿,正好吃。天气热,光照强,南风大,等两天,豆芽就老了,支棱出叶子,只好喂羊。做一只羊,也很好的,一辈子,只吃叶子,简简单单。
有两年,几个朋友,常小聚。一个写古体诗,一个喜欢哲学宗教,还有一个喜欢心理咨询。我们离得也近,聚着方便。小饭馆一坐,点几个家常菜,酒酣耳热,天马行空,高谈阔论。
每次点菜,我都喜欢点一盘炒豆芽。
后来,各自一忙,便聚得少了。偶尔一聚,也少了以前那种闲适和随性。《聊斋》里说,缘来则聚,缘尽则散。很多世事,也只能作这样的达观之想罢。要想更好地热爱这个世界,我们就必需接纳它的种种局限和缺憾。
扁豆
冬夜,拥被卧读。读《聊斋》。
王渔洋题《聊斋》诗,有句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王渔洋诗主神韵说,但这一句,却最是朴素有味。瓜架上面结的是什么瓜呢,吊瓜?丝瓜?瓠瓜?不知道。但豆棚,则是扁豆棚了。

我们这儿,称扁豆为眉豆。眉是浓眉。我们这儿夸一个男人长得帅,则曰,浓眉大眼。浓眉大眼,看上去敞亮。
我们这儿多种青眉豆和紫眉豆。青眉豆开白花,长大了,微微变白。长老了,直白。紫眉豆开紫花,叶梗藤蔓都是紫的,真好看。
清人有个叫艾衲居士的,编著一本短篇小说集,《豆棚闲话》。我读了两篇,觉得并不怎样,就不读了。却很喜欢这个书名。像个随笔集子。累了,坐在豆棚下,说说闲话,谈谈农事。农耕时代的生活图景。
扁豆肯结,越到秋天,越肯结。一簇簇的花,开一茬又一茬。扁豆也结一茬又一茬,一串串缀满藤蔓。秋风吹在扁豆藤蔓上,深青的叶片纷纷翻动,扁豆也带有寒意。摘的时候,放在手里,凉凉的,内心会突然被什么东西触动一下。
扁豆切丝,炒青椒。扁豆切条,炒肉丝。扁豆拌面糊,煎。扁豆的味道比较强悍,冲,得趁大油。
扁豆结得太多了。吃不完,煮。煮熟的豆角,再用灶膛里的草木灰吸去水分,然后放在草席上晒。树叶落了,明亮的日脚斜斜照在堂屋门口,光阴徘徊。母亲和邻居大婶大娘在房檐下坐着,一针一线,纳鞋底,唠家常。豆角晒干晒透,把灰抖去,装入布袋,好好存放。过大年,熬肉汤,汤里放粉丝,海带丝,干扁豆角。扁豆角清水洗干净了,还隐隐有点草木灰的气息,凭添一种独特的风味。
干扁豆角焖五花肉,算是老家旧时生活中的一道家常大菜。
儿时,其实是很贫穷的。偶尔吃顿好的,记忆深刻。回忆起来,天地广阔,仿佛很丰富似的。悟道的禅师说,“曙色未分人尽望,及乎天晓也如常”。如常,才好。旧信里,亲人之间报平安,常写,一切如常,请勿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