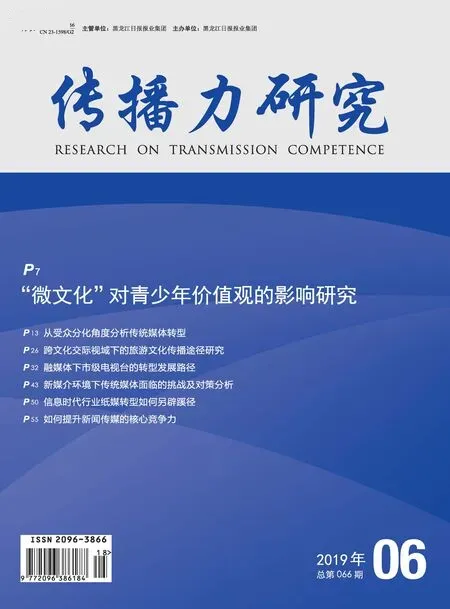身披历史外衣的现实隐喻
——以热播清宫剧《延禧攻略》为例引发的反思
2019-03-22张亚雯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
张亚雯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
暑期档上映的众多影视剧中,《延禧攻略》宛如一匹黑马,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清宫剧一时之间再被提起,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其实,清宫剧的发展已然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以《戏说乾隆》为代表的“戏说风”,到以《宫锁心玉》为一类的“穿越风”,再到如今以《甄嬛传》和《延禧攻略》为一类的“宫斗风”。[1]清宫剧的格调在随着时代以及大众的审美逐渐改变。本文主要以“宫斗风”影视剧为讨论对象,以热播大剧《延禧攻略》为讨论原点,散发开来,讨论女性角色在清宫剧历史上的群像类型及现实社会的隐喻。
一、女性类型的更进之女性意识的崛起
女性,被称之为“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是变成了女人。”[2]社会把第一性的主体地位给予了男性,因此,男性成为了主体。女性与此同时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女性的意志成就着男性的意志,女性的行为囚禁于男权社会。这就是女性被沦为第二性的根本原因。
清代宫廷无疑是一个彻底的男权社会,男权凌驾于女权之上,女性向来是被压抑着存在于宫闱之中。在这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女性群像被“肢解”,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清宫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成为了清宫戏的叙事手段与方法。
(一)悲剧命运之历史必然
我国古代历史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政治婚姻已被实施使用。皇家贵族的婚姻往往无法由自身做主。古代政治家认为,皇权贵族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巩固政权,政治婚姻已远超婚姻本身而存在。尽管清宫剧在叙事中存在着许多虚构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改写,但其政治历史背景却仍旧做以保留,以体现清宫剧的风格调性。依据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宫剧中部分女性指代政治婚姻的牺牲品,成为清宫剧女性群像划分的第一类别。
《延禧攻略》这部影视剧中少有对女性人物政治方向的叙述。皇帝口中的一句:“后宫不得干政”。让剧中叙述重心放置于女性角色的塑造中,从这点来看《延禧攻略》是一部彻底关乎女性的影视作品。其中角色富察·容英为这类人物的主要代表之一。富察·容英是孝贤纯皇后,她样貌风姿卓越、性格温柔典雅,具有影视剧中少有的皇后性情。《延禧攻略》热映之后,紧接着上映的《如懿传》可以看做是《延禧攻略》的前传,剧中人物原型相似,可做为参考进行文本分析。影片文本在第一集弘历选妃时,弘历的额娘便说:“喜欢是一回事,能帮到自己是另一回事。”可见,皇室选妃都以自身利益及政治为重,自然富察·容英被选中不是因为弘历的喜爱,而是富察·容英背后强大的家族支撑。不仅仅是富察·容英,慧贤皇贵妃也是如此。这样的选择之下,女性悲剧的命运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在历朝历代都是男权社会的封建王朝中,女性化作男性“看”的对象。清王朝时期乾隆当政,他的一生有五十多位妃子。可谓是:后宫佳丽三千。皇权的集中和专政代表着皇家的地位与荣耀,而那五十多位妃子所仰慕的便只有皇帝一人。在这个男性宰制的社会里,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附庸。男权意识的附庸便成为清宫剧女性群像中的第二大类别。表面来看,宫中女子大多集自由和权利于一身,任性与刁蛮的女性不在少数。而实质上,自由与权利都是封建皇权赋予她们的。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也就是男权中心主义的社会里,极少数位于身份顶端的太后、皇后,看似有着“母仪天下”的大权,却也无法逃脱其本身的属性,那就是后宫女性中成为男权意识的附庸。《延禧攻略》中身份最高的女性莫过于太后。剧中辉发那拉氏皇后的父亲那尔布被百姓误认为是赈灾的贪官,由于涉及到皇亲国戚的贪污腐败,为了保全皇家颜面,太后毅然秘密处死那尔布,这件事使皇后心中充满了仇恨。可见,即便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太后依旧是整个父权意志的代言。其他的女性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被深深的包裹在其中,无法跳脱,使之牢牢的成为了男权社会男性意识的化身。
(二)“新”女性的诞生之悲剧命运的改写
所谓“新女性”则是争取人格独立、恋爱自由、就业平等,敢于反抗封建制度、传统道德规范、男尊女卑的劣根性思维。将“新女性”的思维观念赋予清宫剧艺术作品中,这一类型的女性则是代表敢于反对宫廷规章制度,勇于成为反皇权文化的象征代表。
继热播的上一部清宫剧《甄嬛传》,《延禧攻略》成为清宫剧历史上的第二部“职场手册”。尤为女性观众提供职场炼狱法则,女性观众学习剧中角色“升职”的方式方法,并幻想有一天将其付诸于现实之中。《延禧攻略》正是因为新型的叙事手段和风格使“宫斗型”清宫剧有所发展,成为大众喜于观看的影视作品。《延禧攻略》被称为披着清宫戏外衣的现代职场打怪爽文。这与剧中人物魏璎珞这一角色是分不开的。剧中人物魏璎珞在进宫之初,一人单枪匹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找到杀害姐姐的凶手,她从一开始的小宫女一路晋升到令妃乃至到最后的贵妃,最终一人真正执掌后宫大权。这一路她披襟斩棘、过关斩将碾压了一个又一个的反派。剧情叙述方式一反之前冗长且人物性情懦弱的常规叙事模式,在剧中塑造出魏璎珞这一名“异类”,一路逼近高歌女性意识使受众直呼“爽”。
不可否认的是,剧中女性魏璎珞具有着进步的女性意识,敢于向封建皇权中的规制所挑战,为“新”女性立言。在清宫剧的所有女性群像中,角色魏璎珞有突出的个性特点,与清宫剧中的其她女性所体现的屈从尊贵的共性有着质的不同。而此种激进的叙事方式实则体现着与现实社会相差甚远的局面,新时代中仍旧存在着诸多性别不平等的客观事实。《延禧攻略》实质上是现实的投射与隐喻,宛如一剂慰藉心灵的汤药,仿佛一声声刚毅的呐喊,在人群中回荡,其进步意义可见一斑。
但当魏璎珞达到人生顶峰状态之时,她不再追求自身的女性价值,而是与君王相伴甘愿止于皇贵妃的尊荣。看似有着“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实则是导演叙“世”的止步与叹息。男权社会只要不曾改变,女性就无法脱身处于独立之状态,并且安乐于在这种安逸的状态下游戏。隐喻且诉说着女性终究无法跳脱的根源不在于女性本身,而是在于这个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社会。
二、使用与满足无法成正比的受众消费观
1959年伊莱休·卡茨正式提出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他强调:在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有其自身的动机和心理机制,往往需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选择来“满足”自身精神的需要。影视剧《延禧攻略》上映后收视破九亿的超高成绩,正是与受众“使用与满足”的消费心理不可分割而语。
(一)“爽”文化的审美需求
现代社会是一个互联网社会,越来越多的“爽文”、“爽剧”充斥在大众的视线之中,快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同时意味着快感制造成为当下文化的发展趋向。在这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促就了人心的焦虑与不安,现实的社会压力使人们极度的渴求释放。“爽文”与“爽剧”实则是一种文化快餐消费。手机成为了承载快餐文化的主要载体,无论是公交车上还是上班期间的空档,大众往往掏出手机,在相应的app上观看。在这个过程中,沉浸于“爽文化”所带来的快感,获得身心的愉悦。并逐渐形成“爽文化”的定向审美需求。
《延禧攻略》中女主魏璎珞成就了受众心中的渴望,不断的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反派,获得了世俗上的成就。受众在观看时将自身沉浸其中,开启了想象性的生活,满足自身在现实中无法超越的阶级桎皓和强权规则,同时忘却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和限制。显然,受众沉迷于这种快感文化中,“满足”着剧中接踵而至的“爽”点,重复的刺激下,受众被“麻醉”其中。当然,清宫剧的改良不该被视为现实社会腐蚀人心的毒药,上文提到的“新”女性中进步意识仍旧是对现实社会中男女权力的不对等关系的警示。
大众审美格局在21世纪发生急剧转变,这与整个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大众已不再需要情感的宣泄与抚慰,他们更多的渴求是情感的释放。文学领域也渐渐由原先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走向如今的言情文学。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爽文”。可以说,大众在这样的文化转变中,是浮躁的。情感缺口需要替代与填补;心中无助、孤独、焦虑的精神压力,需要快速的释放。而这正是“爽文化”的受众审美需要。
(二)受众的沉迷与反抗
《延禧攻略》的火爆收视已经证实受众对其的心理状态是满足与接受的。清宫剧的非现实叙事和娱乐模式,将受众带入了虚妄的境界中,成为现实中的麻醉剂。那么受众终将会禁锢在沉醉的藩篱之中吗?
历史学家对于清宫剧中所发生的事件不予评价,认为清宫剧实则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可参考的价值。它所呈现出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创造和展示了“异样的世界”。清宫剧所遵照的快乐原则,所传播的权谋论、厚黑学的价值理论,使受众慢慢的偏离正确的价值观。沃尔特·李普曼曾提出的“拟态环境”概念,则深深的表达了对公众的担忧。拟态环境是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将过滤了的信息,传达到大众心里。从而使大众无法分辨事实的原委,无法了解客观的真相。清宫剧的盛行对大众辨识真伪造成一定的困惑。受众因此沉浸于虚假的世界中,却不知不觉的追逐这种超现实的生活状态。
然而,从1991年的《戏说乾隆》开始,清宫剧就一直活跃在荧幕上。以《甄嬛传》开始的一类职场“宫斗剧”是近年来清宫剧的转型之作。于正导演的《延禧攻略》虽说饱受好评,但终究逃不过固定不变的程式化。女主魏璎珞的历史命运像极了甄嬛。很难想象,若接下来的清宫剧无法打破职场“宫斗剧”的模式,所呈现的必定是同质化了的且让受众无法接受与满足的作品,收视率可想而之。《理解大众文化》中则对受众有更多的审视,受众不再是被牵制的对象,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具有自我的反思与进步。加之受众本身对清宫剧的审美疲劳会加速清宫剧的衰败,而这正是受众无形的抵制与反抗。
可以说,受众是在不断的沉迷与反抗中筛选着大众主流文化,在这点上,受众具有主体地位。
三、追求平权的个体化时代
现代性社会使人由传统的社会道德、社会机制、生活网络中“逃离”出来,抵达一种依赖“自我”的个体化趋势。“个体化”的提出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贝克认为:“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没有消,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3]
清朝是一个由男性所统治的王朝,男权社会中,男女关系的不平等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清宫剧在情节及人物的设置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做的。《延禧攻略》的一反常态,让女性成为叙事的主角,女主魏璎珞一再挑衅男权社会的体制进而不惜代价去挑衅“当朝天子”乾隆。女性意识的突进在女主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延禧攻略》是现代社会文艺作品的产物,它定然夹杂着创作者的美好祝愿和期望。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不可避免的进入剧中人物的语言、行为、思想等艺术表达之中,影响着女性意识。层层剥离开来,《延禧攻略》影射的则是现代社会仍旧存在着的男女不平等关系。
个体化时代的女性,往往认为自身逃离了传统的约束、道德的绑架。她们的理由则是自由的选择婚恋、生育以及工作,意味着对男性的依赖减弱。传统的核心家庭在现代社会变得极其不稳定,离婚率的上升是这一点的最好例证。事实是,女性身处于个性化时代中则会加剧社会性别的不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性的母性角色,“孩子”成为个性化张扬的“绊脚石”。女性希望与过去传统桎皓决裂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于男性。而男性长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中,无论是在过去的传统社会还是如今的现代社会,皆是如此。
《延禧攻略》这部影视化作品具有深刻的现代文化痕迹。现实中的不平等关系仍在继续,并且是一个无力的社会现实存在。作为女性只能努力的去争取自身的权益,而不是争取女权的胜利。男权与女权的问题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已开始争执不休,男权与女权的探究其实究其根本是无意义的,作为个体化时代的人们应去更多的追求平权以及人权,因为在男性社会里仍旧有男性会感受到不平等。作为个体,不用过多的把男性女性分在两个阵营,任何时候,任何个人都有自身所追求和选择生活的权利。
四、结语
清宫剧《延禧攻略》的成功,不能将其看作是历史的佐证来研读,其叙事内容中所包含的人物、情节以及清代元素无不包裹着现代的痕迹。故事编剧采用清代历史中的一二事件为原点,不断的进行艺术化的创作。事实上与历史正剧无法同类而语。但是,《延禧攻略》背后所产生的社会意义仍旧值得思考。我们每一位人都处于个性化高速扩张的风险社会。女性意识的突进必然带来婚恋观的改变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仍旧需要我们不断的探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