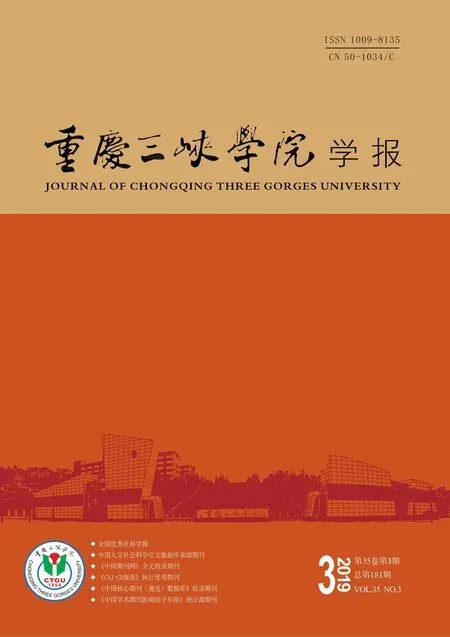朱士端《韩诗释》得失论
2019-03-21吕冠南
吕冠南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朱士端,字铨甫,江苏宝应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其生平学行,详见徐世昌《清儒学案·石臞学案下》[1]。宝应朱氏乃经学世家,朱士端少年时期就学于从父朱彬(以撰《礼记训纂》而著称),后亲炙高邮经学大师王引之,由是学有大成。著有《宜禄堂收藏金石记》《说文校定本》《彊识编》等,皆刻入其《春雨楼丛书》中。朱士端在小学训诂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同时他也擅长辑佚之学,撰有辑录已佚的汉代三家《诗》(《鲁诗》《齐诗》《韩诗》)而成的《齐鲁韩三家诗释》。但此书并未付梓,仅有稿本、钞本散藏于各地。近年,该书已逐渐得到学界重视,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再易稿)已在2008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影印面世,虞万里曾撰专文介绍,同时探讨了此本与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初稿本及国家图书馆所藏清稿本之间的关联,考辨精审,足资参稽[2]。此外,扬州市图书馆亦藏有《齐鲁韩三家诗释》稿本、钞本各一部,为虞文所未及,刘建臻曾对其具体情况作过细致的研究[3],与虞文相得益彰。但是对于国家图书馆所藏《齐鲁韩三家诗释》,至今尚未有专门的论著加以介绍,这不免有所遗憾。笔者此文即以国图藏本为准,不仅是因为此本未得到学界的介绍,还因为此本乃《齐鲁韩三家诗释》之后起钞本①详见虞万里《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齐鲁韩三家诗释〉初探》,《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4期,第62页。,在产生时间上,应在上海图书馆所藏再易稿之后,因为上图藏本中书于夹缝间的补充文字,在此本中多已抄入正文,如上图藏本卷一《关雎》有小字补语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自注:《礼部韵略》引王肃注)。士端按:王肃习《韩诗》。”[4]这段文字已经以正文的形式抄写于国图钞本中[5]卷一,4b,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都可以证明国图钞本是吸收上图钞本相关成果以后产生的新版本。综合来看,国图钞本最接近该书之最终面貌②之所以使用“最接近最终面貌”的字句,是因为国图藏本亦非该书之写定本,最主要的证据便是仍有部分条目存在贴签,例如卷二《邶风·终风》篇有题为“抄《说文形声疏证》”的贴签,以小字抄写了朱氏《说文形声疏证》对该诗“ 㙪㙪其阴”之文的考证,见(清)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卷二,第 3页 a。,其价值胜于其他稿钞本,故本文以之为据。该本卷首有郑氏1956年手题识语[6],叙此本流传经历甚详,可参看。限于篇幅,本文仅以《齐鲁韩三家诗释》的《韩诗释》为研究样本,探讨朱士端在经学辑佚中的得失。
一、《韩诗释》在《韩诗》研究方面的价值
《齐鲁韩三家诗释》起首即为《韩诗释》十卷,书题为“释”,即明该书之悬鹄不仅在辑,更在考释。通观全书,也的确是释胜于辑,几乎每条遗说之下,皆有“士端按”引首的按语,足见朱氏在“释”方面所下的功力。这些考证型的“释”语含蕴的内容极其丰富,既有对清代学者著作的详细引用,如姜炳璋《诗序广义》、臧琳《经义杂记》、陈寿祺《左海经辨》、王引之《经义述闻》、卢文弨《毛诗音义考证》、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等等,亦有朱氏自己的考证,这部分内容更能展现朱氏在《韩诗》研究方面的心得,这些考证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用字特点。《韩诗·周南·兔罝》云:“施于中馗。”《毛诗》“中馗”作“中逵”。朱士端按语云:“《说文》:‘馗,九达道也,似龟背,故谓之馗。馗,高也。或从辵从坴。’据此,则韩用本字,毛用或体。是亦许君本字用《韩诗》,或体用《毛诗》之例。”[5]卷一,8指出了《韩诗》多用本字而《毛诗》多用借字的特点。再如《韩诗·邶风·击鼓》:“于嗟敻兮。”《毛诗》“敻”作“洵”,《毛传》训为“远”,然《尔雅·释言》训“洵”为“均”,可见“洵”并无“远”义,但《韩诗》之“敻”则有“远”义(《释文》引《韩诗》云:“敻亦远也”),所以朱士端认为《毛诗》此处使用的“洵”实乃“用‘敻’之假借字”,再次申明韩、毛在本、借字使用方面的差异。这一看法,在全书中得到一以贯之的展现,而最透辟的表述则是朱士端在《周南·汉广》所作的按语:“三家中训诂声音,有足与毛相发明者。三家今文,多正字;《毛诗》古文,多叚借。无三家,则叚借不通,三家亦岂可尽废哉?甚矣读书论世宜持平也!”[5]卷一,10b这节按语的讨论已不再仅限于韩、毛二家,而是推拓到汉代四家《诗》,认为三家《诗》使用正字居多,而《毛诗》则多使用借字,不过“三家今文,多正字”仍旧包含《韩诗》在内,所以朱士端对于《韩诗》多用正字的现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解诗特点。朱士端对于《韩诗》学派解读《诗经》字义的特点亦有涉及,例如《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朱士端辑《韩诗》遗说云:“一升曰爵,爵,尽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饮当寡少。三升曰觯,觯,适也,饮当自适也。四升曰角,角,触也,饮不能自适,触罪过也。五升曰散,散,讪,饮不能节,为人所谤讪也。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觞者,饷也。觥亦五升,所以罚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过,廓然明著,非所以饷,不得名觞。”对于《韩诗》的这一段解读,朱士端在按语中归纳其解诗的特点:“爵、足,觚、寡,觯、适,角、触,散、讪,觞、饷:皆以声同声近为训。”[5]卷一,5b-6a指出《韩诗》学派的训诂擅长从声同声近方面入手,对经文进行解读。再如《卫风·淇奥》:“绿猗猗。”《释文》引《韩诗》云:“,萹筑也。”朱士端对此条训诂的原因作出分析:“‘萹筑’二字与‘’为叠韵,以叠韵训也。”[5]卷二,16a同篇“绿如箦”,《文选注》引《韩诗》云:“箦,积也。”朱士端谓:“‘箦,积’,以叠韵训也。”[5]卷二,17a这两处按语均指出《韩诗》解诗存在利用叠韵进行训释的特点。
异文问题。朱士端在按语中常常提及《韩诗》学派的文本存在异文,例如《毛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草。”《文选·赠从兄车骑》李善注引《韩诗》作“焉得諠草”[7]455,但《文选·西陵遇风献康乐》李善注引《韩诗》又作“焉得萱草”[7]477。对于同出《韩诗》而有“諠”“萱”之别的情形,朱士端给出的解释是:“《韩诗》作‘諠’,又作‘萱’,音同字异,亦传《韩诗》者,师授不同耳。”[5]卷二,20b-21a这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所谓“传《韩诗》者不一家”[8]的观点相接近,这说明朱士端对于《韩诗》的异文问题有所注意。不过朱士端对此处异文的看法存在一定问题,这是需要予以指出的。范志新先生《〈文选〉李善注韩毛诗称谓义例识小》曾结合李善注《文选》引《诗》之体例,定“萱”应作“諠”[9]。不过朱氏提及的“师授不同”对于解释其他《韩诗》异文问题,仍然存在参考价值,这是他在《韩诗》异文研究中的贡献。但是,“师授不同”这一看法的使用存在限度,那便是异文应当出自古籍明确引录为《韩诗》的内容,一旦突破这个限度,“师授不同”便丧失合理解释《韩诗》异文问题的有效性。在《韩诗释》中,朱士端动辄将《说文解字》《说苑》等古籍所引用的未明所出的《诗经》也视为《韩诗》,并在与真正的《韩诗》产生用字歧义时,也以“师授不同”作为理由,过于武断了。原因很简单:“师授不同”的前提是二者均在《韩诗》的“师授”范围之内,而目前的文献无法证实《说文》《说苑》等书所引必为《韩诗》,所以其“师授”完全可能在《韩诗》系统之外,这样一来,便取消了“师授不同”的前提,自然无从导向“师授不同”的结论。而这一点,则是《韩诗释》全书的根本症结,严重影响了本书所辑《韩诗》遗说的有效性。
二、《韩诗释》的学术局限
朱士端对于不明《诗》学派别的学者和著作往往进行以偏概全的推定,斩截的语气在全书中处处可见,兹列其代表性论断六种,辨明其误。
1.“《水经注》引《诗》皆《韩诗》说”[5]卷一,1a。按:杨化坤曾对《水经注》的引《诗》情况作过专项研究,将该书所引共五十一条《诗经》全部辑出,并逐一与今本《毛诗》对勘,有三十一条内容与《毛诗》完全相同,剩余二十条异于《毛诗》的内容则由汉字特点(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俗体字)或征引三家《诗》而致,所以杨氏的结论是:《水经注》“引《诗》主要来自《毛诗》,但并未为其所囿,而是兼采三家之《诗》”①杨化坤:《〈水经注〉引〈诗〉考论》,《新国学》第九辑,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324页。此文末尾所附“《水经注》引《诗》与今本《毛诗》相同条目表”最足以说明《水经注》引《诗》绝非朱士端所谓“皆《韩诗》说”。。这一结论建立在竭泽而渔式的文献基础之上,故信而有征。朱士端仅因《水经注》征引过“韩婴叙《诗》”之文,即断定“《水经注》引《诗》皆《韩诗》说”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在《水经注》产生的北魏时代,《毛诗》在北方《诗》学界占据着经典地位,《诗》学著作皆围绕《毛诗》进行,无一部《韩诗》著作,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水经注》,其所用《诗》学自然不可能“皆《韩诗》说”,朱士端未考虑上述背景,仅因《水经注》偶尔征引《韩诗》学说便以偏概全,其结论并不可从。
2.“刘向述《韩诗》,《列女传》所引皆《韩诗》也”[5]卷一,1b。按:朱士端持此说的依据是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王氏发现刘向对《诗经》的部分解释与《韩诗》相似,所以得出“刘向所述者乃《韩诗》”的结论。朱氏接受这一结论,并继续用王引之的方法,增补了数条刘向与《韩诗》同解的材料,于是更加确定“刘向述《韩诗》,无疑矣”。这一逻辑看似顺理成章,但实际却存在致命的罅漏。因为刘向说《诗》引《诗》固然存在与《韩诗》相通之处,但同时亦有与《鲁诗》《齐诗》《毛诗》相通之处,遽定其为《韩诗》家显然过于武断。吴正岚曾就今存所有刘向引《诗》用《诗》材料进行分析,发现“刘向著述中的《诗》说与四家《诗》均有合有不合处,因而刘向在其著述中引《诗》说《诗》时,对四家《诗》确实是兼收并蓄的”,刘向的《诗经》学“不拘家法,兼采众说”[10]。这一结论最终印证了清儒全祖望的观察:“向之学极博。其说《诗》,考之《儒林传》,不言所师,在三家中未敢定其为何《诗》也。”①(清)全祖望《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7页。叶德辉《〈三家诗补遗〉叙》曾谓:“两汉经师,惟列传儒林者,其学皆有家法,自余诸人,早晚皆有出入。”见(清)阮元:《三家诗补遗》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页。这与全祖望“考之《儒林传》,不言所师”之语冥符遥契,皆认定只有《儒林传》所记学者才有严格的师法、家法谱系可循,而刘向未被列入《汉书·儒林传》,自然“不言所师”,亦不在“其学皆有家法”之列。正因如此,故不宜、亦不能将其《诗》学归属化约为某一家。吕思勉先生亦与全氏同声相应:“刘向是个博极群书的人,自然不能谨守家法。”[11]总览以上诸家之见,刘向显然非《韩诗》所能牢笼,故“刘向述《韩诗》”之说实为无法证实的假说。
3.“王肃述《韩诗》”[5]卷一,4b。按:朱士端之所以定王肃乃“述《韩诗》”者,系因王肃注《毛诗》时,存在用《韩诗》改易《毛传》的情形,不过这只能说明王肃注解《毛诗》时曾参考过《韩诗》,绝对无法推出“王肃述《韩诗》”的结论。因为“述《韩诗》”直接抽换了王肃的《诗》学立场,与经学史的史实完全相悖。郑玄亦有使用《韩诗》改易《毛传》的案例,但绝对不能将郑玄的《毛诗笺》视为《韩诗》著作,他既为《毛诗》作笺,自然是站在《毛诗》的立场上。而单就注释《毛诗》来看,郑玄动辄改字释经,王肃则大多依循经文,其对《毛诗》的坚守程度远过于郑玄②可参阅史应勇:《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249-323页。,实较后者更接近《毛诗》本位。如果仅因引用《韩诗》的部分说法去注释《毛诗》,便可推出“述《韩诗》”的结论,那么几乎所有汉代以降的《毛诗》学者都是“述《韩诗》”者,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参考过《韩诗》,但这显然与学术史的常识迥不相侔。以汉魏经学史而论,马融、郑玄、王肃等古文经学家在注解《毛诗》时的确存在差别,日本学者伊藤文定对此曾有专门的考察[12],但这一差别均是在《毛诗》系统内部发生的,他们即便偶有参稽《韩诗》之处,也是为了更好地诠释和完善《毛诗》。如果借用旧瓶新酒的比喻,则《韩诗》是古文经学家倒入《毛诗》这一旧瓶中的新酒,但新酒仅为了充实旧瓶,且容量有限,远未达到溢出旧瓶而另换新瓶的程度。所以朱士端所主“王肃述《韩诗》”之说,不啻将王肃塑造为本末倒置的学者,而且表述完全是颠倒事实。刘运好先生在《魏晋经学与诗学》中曾梳理过王肃的《诗》学著作,共有以下五种:《毛诗注》二十卷、《毛诗义驳》八卷、《毛诗奏事》一卷、《毛诗问难》二卷、《毛诗音》(卷数不详)[13]。从这五部书的题名便可看出王肃的《诗》学研究全部围绕《毛诗》展开,从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王肃述《韩诗》”的信息。
4.“《盐铁论》引《诗》皆《韩诗》也”[5]卷二,6a。按:朱士端仅因桓宽《盐铁论》“所引‘宜犴宜狱’‘我是用戒’皆《韩诗》”[5]卷一,5b,便断定《盐铁论》所引《诗经》皆为《韩诗》,这仍然有待商榷。因为《盐铁论》全书共引《诗经》43处,仅凭其中两处与《韩诗》相合,便推定全书所引《诗经》皆为《韩诗》,未免太以偏概全。进一步分析朱氏举出的这两处例证,可以发现均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小雅·小宛》的“宜犴宜狱”虽与《韩诗》相合①《毛诗·小雅·小宛》:“宜岸宜狱。”《释文》云:“《韩诗》作‘犴’。”由此可知《韩诗》此句作“宜犴宜狱”,与《盐铁论》所引相合。,但《文选·后汉书皇帝纪论》李善注引《毛诗》亦作“宜犴宜狱”[7]937,所以无法排除《盐铁论》此处是征引《毛诗》的可能;第二,“我是用戒”乃《小雅·六月》之文,但《韩诗·六月》今已不存,无从与《盐铁论》的引文比较异同,故朱氏以“我是用戒”乃用《韩诗》是毫无依据的判断。由此可见,朱氏举出的两条例证均非绝对有效。如前所述,即便朱氏的两处例证均来自《韩诗》,尚且无从推出《盐铁论》所引《诗经》皆为《韩诗》的结论,何况现在已可断定朱氏所有论据均属无效,所以他对《盐铁论》的《诗》学派别的定位是无效的。龙文玲曾就《盐铁论》征引所有《诗经》条目进行过考察,发现在43处引文中,与《毛诗》相同者有33处之多,剩余10处则交错引用包含《韩诗》在内的三家《诗》;在用《诗》方面,《盐铁论》对于四家《诗》皆有采撷[14]。由此可见,《盐铁论》的引《诗》用《诗》均不限于一家,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曹道衡先生在《〈盐铁论〉与西汉〈诗经〉学》中已经指出:“它不是桓宽个人的著作,而主要是记录别人的发言,而且发言人又并非一人。”[15]这些发言人又并非来自整齐划一的学术派别,所以在讨论中,不免各借其师说来发表意见。桓宽在将这些意见编辑为《盐铁论》时,保留了来自于不同《诗》派的学者的看法,于是形成该书含蕴多家《诗》学的特点。只要明了这一事实,则朱士端将《盐铁论》中异见纷呈的《诗》学一律视为《韩诗》的看法,自然不足为据。
5.“王充述《韩诗》,所引‘传曰’即《韩诗传》也”[5]卷二,15a。按:朱士端并未说明他判定王充习《韩诗》的根据,故此说在全书中相当突兀。王充的《诗》学渊源并无史文明确记录,所以在未经过逻辑论证便遽定为《韩诗》是有欠妥善的。至于王充在《论衡》中所引用的“传曰”,本是两汉古籍常见的引证方式。根据廖群先生的观察,在这种引证方式下的“传”并不是指称某一部具体的释经著作,而是“取其‘传语’即转告传闻之义,即读为‘chuán’”[16]。考诸秦汉典籍所征引的“传曰”,其内容的确多为“转告传闻”的故事,由此可定廖先生的这一释读是准确的。此外,美国汉学家海陶玮(J.R.Hightower)在英译《韩诗外传》的引言中,曾专就《韩诗外传》的“传曰”进行过探讨,他认为韩婴只有征引以下三类文本时,才会冠以“传曰”的字眼:第一,对于道德行为的宏观探讨;第二,格言或警句;第三,泛见于汉前典籍中的故事或逸闻[17]5。而且在海陶玮看来,《外传》中的“传曰”基本和最常用的翻译方式是:“传言说:……。”[17]5这显然是将“传曰”的“传”视为“口头传说”,这与清人将之视为书面的《传》大相径庭。今考《论衡》多处征引的“传曰”,性质与《韩诗外传》所引“传曰”相同,其源头显然不是书面文本。朱士端将其视为镌于竹帛的经籍传(zhuàn)记已有不妥,朱士端更坐实为《韩诗传》,则愈是错上加错了。
6.“郑君注礼,先通《韩诗》”[5]卷二,7a。按:清代学者对于郑玄注释三礼时所用《诗》学曾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郑玄在注解三礼时采用了《韩诗》,例如王引之《经义述闻》就曾明言:“郑君注《礼》时用《韩诗》。”[18]也有学者认为郑玄注礼时使用的是《齐诗》,说详陈乔枞《齐诗遗说考叙》[19]。由此可见,郑玄注礼所用《诗》学存在争议,并不能直接定为《韩诗》。在这一问题上,清代《韩诗》学大师宋绵初在《〈韩诗内传征〉序》中曾作过严肃的检讨:“郑氏虽从张恭祖受《韩诗》,但其学该博,不名一家,如笺《诗》宗毛,有不同则下己意。注《礼》时未得《毛传》,大率皆韩、鲁家言,若确然定为《韩诗》之说,恐未必然也。”[20]《后汉书·郑玄传》曾明确记录郑玄早年从张恭祖受《韩诗》[21],而其注《礼》又在修习《毛诗》之前,故其注所用《诗》学似应定为《韩诗》。但宋绵初从郑玄“不名一家”的学术宗尚出发,认为郑氏不会对《韩诗》师法亦步亦趋,故遽定其注《礼》时纯用《韩诗》是不合理的。这显然是非常客观冷静的看法。叶德辉《阮氏〈三家诗补遗〉叙》也认为不应将郑玄注礼所用《诗》学限于一家一派:“郑氏注《礼》,凡说《诗》义,多与《诗笺》不同,……但其孰为鲁为齐,则不可辨。陈书(笔者按:即陈寿祺父子《齐诗遗说考》)均并入《齐诗》,未免肊断。”[22]综合宋绵初和叶德辉的看法,则郑玄注礼所用《诗》学显然是一个可能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故二家使用的都是“未必然”“不可辨”等带有保留意味的字眼,而朱士端直接认定郑玄以《韩诗》注礼,不免忽视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通过上文所论,可以发现朱士端的不少论断,多是藉助某些学人或著作某一处引《诗》与《韩诗》相同(似),便推定其所有引《诗》用《诗》材料俱为《韩诗》,这种以偏概全的论断,既悖于逻辑,又缺乏文献依据,总体来看是无效的。必须指出的是,《韩诗释》中还有不少藉助此类方法推定学者或著作的《诗》学归属之例,但限于篇幅,兹不缕举了。
除此之外,朱氏的以偏概全还表现在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方面,例如《韩诗释》曾广引文献,证实汉代今文《诗》学曾将《小雅》中的《鹿鸣》《伐木》《采薇》《杕杜》四篇作品理解为刺诗,这是归纳文献材料而做出的判断,较为可信。但朱氏随后下的结论却令人舌挢难下:“《鹿鸣》《伐木》《采薇》《杕杜》皆为刺诗,以四篇观之,知以《小雅》皆为刺诗矣。”[5]卷一,3a《诗经·小雅》凡七十四篇,仅因其中四篇为刺诗,便断定“《小雅》皆为刺诗”,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朱氏不仅要将《小雅》的所有作品贴上“皆刺诗”的标签,还要将“二南”(《周南》《召南》)也一并纳入“刺诗”的行列而后快:“考之汉人之说,二南、正《小雅》皆刺诗也。”[5]卷一,2a按:《韩诗》以“伤夫有恶疾”解《周南·芣苢》,以“说人”解《周南·汉广》,以“辞家”解《周南·汝坟》,这些作品都身处朱氏所谓“刺诗”的行列之中,但读者实在看不出来这些题旨与“刺”有何关联,朱士端的固执与偏激,在此处表露无遗。清儒辑《韩诗》者虽或多或少存在偏颇之处,但像朱士端这样信口雌黄,则百不一见。
三、余 论
必须指出,朱士端在《韩诗》研究方面的得失并非个例,这些特点在清代《韩诗》辑佚史中有着广泛的体现。以清代最负盛名的陈寿祺、陈乔枞父子而言,其合撰的《三家诗遗说考》既有对《韩诗》遗说的精审考证及阐发,亦有因深陷师法、家法的泥淖而误判学者、著作的《诗》学派别之例。晚清号称集三家《诗》研究之大成的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不仅没有对二陈父子的缺失进行纠正,反而将其缺失发展得更加深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师法、家法的误用,为清儒治学带来的深远影响。所以朱士端在《韩诗》研究方面的得失,必须放在有清一代的治学风气中观察,才能获得最根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