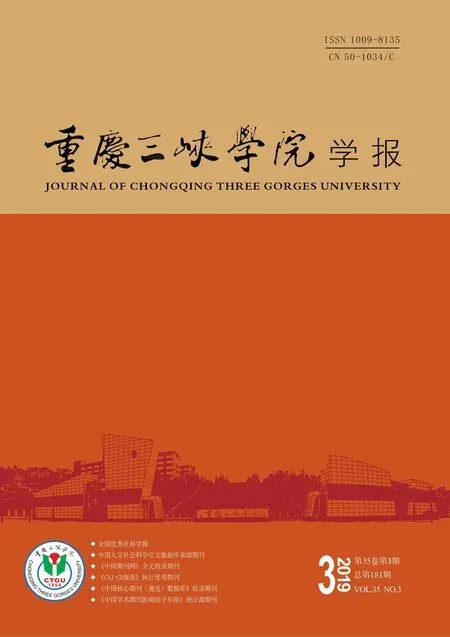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传媒人才培养的元思考
2019-06-04刘利刚
刘利刚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 404020;四川大学,四川成都 610064)
2015年3月5日上午,国家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1]。“互联网+”随即成为大家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梳理之前的研究不难发现,人们对于互联网的认识,还只是停留于将其作为一个外在的辅助工具在相关行业中被应用的层面。实际上,互联网正在或业已摆脱辅助地位,作为核心引擎推动社会各行各业转型升级。互联网角色地位从辅助到核心引擎的转换,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那么我们该如何着手研究这一新的课题?就传媒领域而言,互联网本身就是传媒所依赖的一种工具,与传媒之间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但这仅是传统上对互联网的认识。若把这种认识简化,可以表达为“+互联网”。而“互联网+”看似是符号“+”的后置,实则是对互联网认识水平的大飞跃,是互联网由从属工具到引擎的升格。在“互联网+”驱动下,传媒人才培养也必将走向“传媒教育+”的创新模式。对创新模式的深入挖掘必将有益于传媒教育水平及其所培养的人才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因此,从元思考(meta-thinking)的角度对“传媒教育+‘?’”展开大哉之问,研究如何提升传媒人才核心竞争力,实乃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从“+互联网”到“互联网+”:传媒教育观念的变革
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转变,意味着互联网社会功能角色的翻转。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2]98,符号“+”,这个“再现体”(Representatum)从“互联网”的“左边”移位到“右边”,不仅表现为空间位置的转变,而且还是其深层意指关系的重构。这种重构发生在阐释主体即“解释项”(Interpretant)对于认知“对象”(Object)即互联网“意图定点”[2]184重设当中。在符号学中,“解释项”是一个“变量”,对应于社会关系和意义关系的复杂性。故此,人们对于符号“+”在“互联网”位置的变化,会在各行各业展开“解释项”的无限衍义。这里主要探讨“互联网+”在传媒教育领域引发的观念革新。
(一)对“+互联网”时代传媒人才培养现状的反思
本文把对互联网的认识还未发生翻转之前的认知状态称为“+互联网”。“+互联网”是对互联网所处从属性地位的表征。在“+互联网”时代,传媒人才的培养方式和其他人文社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并无多大差别。在传媒专业的学生就业中,常有被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或理工科专业学生取代的情况。诚如,吴廷俊等在《从内容调整到制度创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出路》一文中就谈到过传媒专业的“可取代性”[3]150-154问题,只不过该文仅把此问题提出而已,并没有展开论述。笔者在研读该文后发现了某种内在的逻辑路线:虽然吴廷俊等声称文章主要针对“两脱离”现象展开讨论,但是其未展开的“可取代性”恰好是“两脱离”产生的严重后果。
吴廷俊等指出,当下中国新闻教育存在严重的“两脱离”——脱离新闻实践,脱离信息时代[3]150-154。尽管文中“两脱离”主要指中国新闻教育,但是这一概括也恰切地总结了目前中国传媒人才的培养现状。新闻教育仅仅是中国传媒人才培养的一个部分,事实上中国传媒教育的园地远大于此,如广告、广播、影视、报纸、杂志及公共关系等等。两脱离现象并非仅仅是新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传媒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笔者认为,传媒人才培养的实践环节,一般都是安排在大学四年级,而且流于形式,学生到了媒体单位,一般干的是文秘工作,对于专业领域内的事情只能进行观摩。实习结束后的评语,一般都是礼貌待人,团结同志,吃苦耐劳,如此云云。而对于专业能力,很少提到。人才培养与实践严重脱节。
另外,学生所学技能与信息时代脱节,大部分学校的实验室仅是摆设,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提升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重硬件、软件建设,却轻利用。当学生从传媒学院毕业后,还必须接受聘用单位的二次培训,与其他文科或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相比,并没有独特的专业技能优势。在就业竞争中缺乏核心专业竞争力,很容易被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取代。
因“两脱离”而被“取而代之”仅乃表层因果,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理念因果。正如刘海龙所指出的要“打破中国传播研究的新闻学框架,去反思另外的可能性”[4]。而恰恰中国传媒教育就被绑定在传统新闻教育这驾马车上,新闻教育的模式成为整个传媒教育的骨架。故此,中国传媒教育难免走上了中国新闻教育“两脱离”的老路子。
(二)对“互联网+”时代传媒人才核心竞争力的探赜
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热词,但是人们对于“互联网+”所蕴含的理念是否心领神会并应用于具体实践,还有待观察和检验。就传媒人才培养而言,“互联网+”对传媒人才培养模式革新带来了哪些契机?这些“契机”能否消除“两脱离”现象?能否解决或缓解传媒人才就业中的“可取代性”问题?这些问题浓缩为一个问题就是:传媒教育应该给予传媒人才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电化教育的奠基人南国农先生对“电教”的“姓氏问题”展开讨论,南先生认为“电教”姓“教”不姓“电”,电教的根基在以“教育学”为主导的“软理论”中,“电化教育”或“教育技术”在中国的教育格局中处于“教辅”位置。
被中国奉为传播学集大成者和创始人的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首次到中国,与中国学者的接头人是电化教育的研究者。“1982年4月,时年75岁的施拉姆教授(时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顾问)在余也鲁教授的陪同下首次来中国,并在华南师范大学作了为期7天的教育传播学学术报告,全国电教界同行参加。施拉姆随后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社以及复旦大学等单位。”[5]在中国传播学史的叙述建构中,施拉姆来华讲学这一事件,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标志性事件。无独有偶,中国电化教育奠基者南国农先生把媒介(“电”)置于“教辅地位”的思想,与当前中国传媒教育置“媒介”为“从属地位”思想何其相似。然而,“互联网+”思想给予了“媒介”翻身的契机:媒介从“附属”变为了“驱动”。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功能角色的转型,研究各类媒介的属性,建构符合各类媒介自身属性的媒介理论,并以这些媒介理论为驱动,协同教育理论,开发传媒人才培养新模式,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把这种新型模式称为“‘互联网+’驱动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互联网+”驱动的传媒人才模式创新,需要充分认识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开放性、去中心化、对等性、公平性。在此基础上,理解“互联网是隐喻,其表意方式有别于传统文化,且能够塑造使用者的思维”[6]96-100。同时也要理解技术进化在当下文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诸如云文化、物联网、大数据、虚拟世界及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文化具有潜在的技术意蕴”[6]96-100。虽说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偏激论调,但是技术的确对文化形态有决定作用。例如,没有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影片《阿凡达》就永远只能漂浮于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想象界”中,正是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等“表达媒介”才使得“想象界”固定为“象征界”。但是,关于技术是什么?人们还缺失一个关于技术的理论——“一门关于技术的‘学’”[7]。对于技术的思考,除了工程师对技术的“内部思考”外,技术使用者还应该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外部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接近技术的本质,娴熟地驾驭技术。是故,传媒人才培养就是要造就谙熟“媒介之道”的“媒介文化”生产者。
二、“互联网+”驱动研、教、学的融合:研、教、学三位一体
“互联网+”理念就是视互联网为媒介融合与衍进的“发动机房”(Powerhouse),而不再是一个各类媒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被动“舞台”。习得互联网思维、领会互联网精神是当前传媒人才培养之关键。那么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以及互联网精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真伪之辨,只有理解深浅之别。随着互联网科技发展以及应用对象之不同,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精神都处于动态变化中,只能有个相对的稳态。从互联网技术特征和媒介技术史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区别于以往媒介的最大特征是最大程度地解放了“用户”。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超过30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40%。由此看来,互联网思维就是“用户思维”,而互联网精神就是“努斯精神”。从此意义上讲,“互联网+”能有效驱动传统传媒教育转向浸透互联网思维及其精神的研、教、学“三位一体”之新型模式。
(一)“行动研究”与“任务驱动”的有效融合
在中国传媒教育领域,师资来源走的是“专业化路线”,而非“师范化路线”。也就是说,中国传媒教育的教师队伍大多毕业于传媒专业,并非接受过专业化的师范教育。许多传媒教育领域的教师在执教前仅接受过数十天的“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对传媒教师的学习活动进行解读:大多数教师对“教什么”思考偏多,而对“如何教”则思考偏少。前者主要指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教授,而后者主要指对教学反思性的元认知活动。故此,传媒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但是,在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又不能放弃教学任务,而且要做到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那么什么样的方法能达到“教”和“学”相长的目的呢?本文认为“行动研究”与“任务驱动”的融合模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于行动研究的理解,无论在我国还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一直存在着争议。然而现代行动研究的倡导者斯登豪斯(Stenhouse,L)、凯米斯(Kemmis,S)和埃利奥特(Elliott,L)等人认为,行动研究的关键特征有四点:“参与”“改进”“系统”和“公开”[8]。因此,依据行动研究的四大特征还是可以对其进行整体把握。行动研究的四大特征与互联网技术的四大特征内在关联,互联网可以有效地支持行动研究的实施。
所谓任务驱动(Task-Driven)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方法,是以“呈现任务-明确任务-完成任务-评价任务”为主要结构的教学模式,是教学诸要素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操作程序,具有稳定性、实践性、可操作性和灵活性[9]。传媒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是任务驱动法极佳的实施场域。任务驱动中的“任务”来源于学习和生活的真实世界及身临其境的体验感,能极大地触发学生强烈的学习、探究欲望。除了真实任务引发的主动学习积极性外,还要施以外在驱动力,使教与学的过程动起来。传媒教育应该把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浓缩于任务中,生活世界的媒介外套即“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不正是媒体人符号编码的结果吗?互联网作为拟态环境建构的支撑系统为传媒人才培养的任务驱动法提供了可行性保证。
尽管认知方法是多元的,但是行动旨归却是一致的。行动研究和任务驱动都指向了“如何教”的问题。只不过行动研究的主体是教师,而任务驱动的主体则是学生。从研、教、学三位一体的角度来说,行动研究是在“教中研”,而任务驱动则是在“研中学”。在“互联网+”引擎的驱动下这两种方法可以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打比方说,互联网乃“行动研究”和“任务驱动”相融合后授之于学生“鱼”和“渔”的“鱼场”。
(二)“碎片化学习”与“系统性学习”的合理兼顾
目前,人们对于互联网的理解远超出对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互联互通的认识,而移动互联网及各种应用APP(全称Application)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互联网的内涵和外延。移动互联网注入互联网的新特性在空间上极大地解放了使用者,不需要用户在“P to P”(Person to Personal Computer)的方式下才能“神游乾坤”。无论身处哪儿,只要轻触终端屏幕,便可“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10]。据《2015年中国大学生媒介使用习惯与媒体品牌认知报告》数据显示,大学生几乎每日都会接触互联网,超过90%的人使用时长超过2小时。每日接触互联网超过8小时以上的大学生占12.2%,远超于每日接触报纸(0.4%)、广播(0.5%)、电视(0.9%)、杂志(0.7%)。QQ是大学生日常社交应用最多的媒介,微信次之,微博居于第三[11]。显而易见,互联网已融入大学生生活。但是,触网的过程并非都是在有效利用时间,而其中许多人是在浪费时间。从人自身生存角度出发,“唯有当此在的存在是时间性存在,是有死的存在,而时间的到来也只是此在存在的展开,生命的运行,此在才会浪费时间,才会虚掷光阴”[12]。因此,传媒教育必须引导学生意识到自身乃是时间性的存在,别以上网学习为由,浪费掉自己宝贵的时间。
传媒教育担负着为以“互联网+”为驱动的新媒体输送人才的任务。传媒人才的培养理当融入新媒体的使用中。非传媒专业的大学生可以把新媒体作为咨询工具和娱乐工具,而传媒专业的学生应当把新媒体作为学习的工具。诚如,各种运行于智能手机的APP提供了极佳的学习工具。其中,微信(WeChat)就是一个方便的学习方式。许多知名的科研院所都开了微信公众号,并定期向订阅受众发送最新动向、最新知识和最新观念,其中也不乏知识亮点、思想亮点。仅传媒领域公众号就有:符号与传媒、人大公共传播研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媒体传播研究会、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刺猬公社等等。相比书本和期刊而言,这些“公众号”具有更新快、知识新、观点前卫等突破传统知识更新模式的特征。传媒专业的学生必须习得使用诸如微信等APP进行“碎片化”学习的习惯,才能跟上信息时代的发展步伐。
但传媒专业的学生,懂得“如何区分有用信息,如何拒绝信息的诱惑”[13],能够充分地利用新媒体进行“碎片化学习”是不够的,要想在就业中不被人取代,还必须得努力进行“系统化学习”。也就是说,碎片化学习取代不了系统化学习。正如郭庆光教授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5年迎新大会讲话中的一个观点:“现在社会上大量的人在消费碎片化信息,碎片化传播,但制作这些碎片化信息的人是有系统积淀的人。”如果传媒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没有系统化学习,而仅是读一些碎片化的知识,那么只能成为一个被影响者。
在“互联网+”时代,传媒专业人才如何处理好碎片化学习和系统化学习的关系,确是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互联网+”驱动下的新模式:从“被动型”加速换挡为“主动型”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在传媒教育中处于被动的教辅地位。而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要作为传媒教育的引擎,主动地驱动传媒人才培养过程。在现代教育技术理念的引领下,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网络远程教育获得了空前发展。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省市校级精品课程、省市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国外大学公开课以及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等。虽然这些大规模的在线课程极大地丰富了学习资源,但是其中绝大多数课程仅仅是传统课程的搬演。它们并未被进行与互联网及相关媒介属性相一致的教学优化设计,也许最可能的优点仅是扩大了潜在的受众数量。若非传媒专业的网络课程开发如此简单操作必须批评的话,那么作为培养运用“媒介”生产“文化”人才的“传媒专业”也如此简单了事,绝对危及到专业生存。
(一)以“主体间性”为模式创新的理念
毕竟传媒教育培养的是能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才,而象牙塔式的传媒教育模式却很难培养出这种人才。目前,传媒教育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培养学生适应信息时代的实践能力。传媒教育的发生过程,并不是理论搬家的过程,而是理论向实际能力转化的过程,其中起到转化的中介作用的是教学模式。有效的教学模式在转化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而无效的教学模式仅是一座海市蜃楼。那么,什么是教学模式?人们基本上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教学模式的:(1)指某种特定的教学方式,比如“协作教学模式”是指包含协作学习的教学方式,“探究教学模式”是指包含问题探究的教学方式;(2)指某种特定的教学程序,比如“读-议-练”教学模式等[14]。第一种作为“教学方式”的教学模式倾向于一种教学理念的表达,没有固定的操作模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特征。而第二种作为“教学程序”的教学模式,过于程序化,极易走向教条主义。
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神经网络,传媒教育理应培养符合这套信息网络之精神的传媒人才,方能驾驭这套网络。而固化程序的教学模式培养出的传媒人才,其精神的拓扑结构与时下的网络精神的拓扑结构实难合拍。故此,本文提倡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思考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即以“主体间性”为核心理念,打破以某个“我”作为绝对主体,从某一视点(Point of View)俯视一切的情况。“主体间性”是现象学的概念,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说:“先验的主体性是一种向自己和向他人显示的主体性,因此,它是一种主体间性。”[15]455先验主体性与日常主体性的不同在于先验主体把主体也“客体化”了。梅洛-庞蒂认为:“以我的主体性和我对他人的超验性为基础的中心现象,在于我是呈现给我自己的。”[15]453也就是说,主体间性是一种在主体之外的主体视点。梅洛-庞蒂认为:“我的自由,我作为我的所有体验的主体具有的基本能力,就是我在世界中的介入。”[15]453通过介入不仅观察世界,也对观察世界之主体进行观察。由此,“主体”才能认识到“这个世界”并非仅是从主体位置上看到的“客体”,而是一种主客体间视域融合的结果。
互联网时代的传媒网络“蜘蛛侠”理应具有现象学精神的拓扑结构。甚或说,栖身于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早就孕育了这样的精神气质。但是,就传媒人才培养而言,如何将这种“自发意识”转化为“自觉意识”?这是传媒人才培养的关键——挖掘传媒人才的潜在机能,使其践行于具体的传媒环境。然而,由于当今的互联网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媒介都具有“机械复制”的特性,所以绝对不能让这种特性成为传媒人才的“便捷窍门”,用来提升自己知识生产的效率。即便是“重复”,也是在“温故而知新”的意义上生产“差异”,而绝不是脑残式的“机械重复”。是故,也许仅当传媒人使“主体间性”融合运行于互联网时,互联网才能起到引擎作用,而不仅仅是手段和工具,同时也才能起到驱动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作用。

图1 互联网驱动的传媒教育之锥
(二)以“互联网+”为驱动的“传媒教育之锥”
据世界编辑论坛发布《新闻编辑部趋势2015》报告指出,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编辑部出现九大趋势:游戏、虚拟现实、可穿戴技术与新闻融合;调查性新闻的威胁增加;自动化新闻的未来;职业安全与目击者新闻伦理;音频复兴引入关注;掀起社交媒体的新浪潮;人人都会进行数据处理;媒体业性别歧视引发关注;来自世界各地的灵感[16]。在这九大趋势中,有七大趋势由新技术驱动,另外两个关涉新闻伦理和性别歧视。而这“七大趋势”发生的“技术语境”就是互联网。这种趋势倒逼传媒教育必须扎根互联网这块沃土中,才能培养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传媒人才。然而,互联网已经成为了“社会公器”,成为人人都能够上手操持的工具,那么传媒人才如何才能玩出不同于普通使用者的新花样,则需要传媒专业的悉心探赜。
本文结合“互联网精神”“互联网思维”“主体间性”及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的“晶体”“循环”概念以及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锥体模式”等思想认识,提出了传媒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互联网驱动的传媒教育之锥”。由图1可知,传媒人才由一个锥体构成,这个锥体被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技术和理论,也就是说,传媒人才理应具备技术并掌握理论知识。第二层是第一层的再分,理论被分为媒介理论和对象理论,例如,从事体育新闻报道的记者,不仅要掌握新闻理论也要掌握体育竞赛规则理论。技术被分为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信息技术主要指硬件和软件的使用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主要指使用硬件和软件处理信息的技术。例如,新闻摄影,照相机和Photoshop使用的是信息技术,而如何取景构图和后期处理照片则是信息处理技术。以上这些是构成传媒人才的静态要素。
在“互联网+”的驱动下,这些静态要素循环了起来。“互联网+”如同一个旋转的“搅拌机”,把构成传媒人才的诸多要素“搅和”在一起,当各要素混合无间在旋转锥体的尖点呈现时,传媒人才也就算培养成功了。这里的关键是,通过“旋转”和“搅和”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就消失了,传统的那种线性的、主客体对立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也就解体了,而充分体现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精神的新型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便生成了。
四、结语:从人本的技术哲学省思“新模式”
“互联网驱动的传媒教育之锥”是以互联网为引擎的传媒教育模式,难免给人以“技术决定论”的刻板印象。技术常被机械地理解为不承载价值观的工具,技术的好与坏取决于使用——也许可以为传媒教育之锥免除技术决定论色彩进行辩护。但是,技术主义的“工具-目的”二元论思想也难免有对“技术”开脱责任之嫌疑。故此,从人本的技术哲学出发,能更好地对传媒教育之锥进行有力的反思,因为人本的技术哲学反对技术主义执持的“工具-目的”二元论。关于人本的技术哲学,“从卡普拉(Frijtof Capra)的《物理学之“道”》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技术之问》,人本的哲学传统可以在不同国家找到。在这种哲学之下,人并不独立于技术而存在,技术和人的存在相互混杂。技术时代并不外在于人,而是人类的家园。技术不仅仅是工程学和科学,而是一种文化的建构”[17]。
是故,互联网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并非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中立物”,始终与人处于“主体间”交融互动中,有助于形成以“师生为本、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18],有助于绿色教育理念向绿色社会实践的转化。然而,在当今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建构中,当技术理性和工具主义成为主流时,人的存在也就变得技术化了,效率和机器化的程序就会反过来重塑文化和社会,技术的律令变成人类的律令,从而人的精神被技术化了,变得麻木了,会误把作为此在的自我的存在当成是非时间性的。殊不知,“作为为其存在而存在的存在者,此在明确或不明确地原本为它自身运用它自己。由于为它自己之故而运用它自己,此在‘用损’它自己。由于‘用损’(verbrauchen)自己,此在需用(brauchen)它自己本身,亦即需用时间。由于需用时间,此在估算时间”[19]。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让我们领会、筹划和珍惜时间。
虽说“主体间性”有意消除主客体之间的距离,但也并未提倡“主-客翻转”,让技术律令成为人类的律令。之所以把技术主义视野中的“技术”放到人本的技术哲学视野中,是为了提升技术附庸性的“工具”属性,把其作为文化看待,也是构成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质言之,“互联网+”是人类对于互联网认识水平的新飞跃,并不是互联网要取代人类而在文化建构中处于主体地位。因此,在“互联网驱动的传媒人才教育之锥”中,互联网被从传统的“教辅地位”提升到了“主导地位”,成为“传媒人才教育之锥”旋转的发动机。但是,旋转何时停转,则是“主体间”协商融合的结果,而非单一主体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