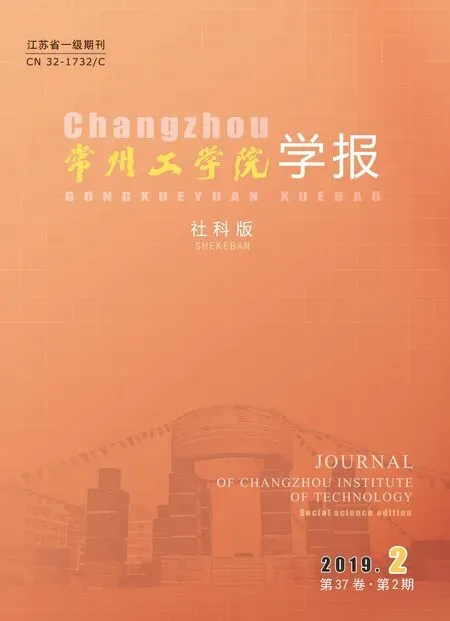中国画论典籍中“氤氲”的内涵源流及英译
——以清代《石涛画语录》为例
2019-03-21张明薇
张明薇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8)
《石涛画语录》这部经典画论典籍曾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画学流变产生深远的影响。《石涛画语录》共18章,记录了中国山水画的基本技法和绘画原理,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重要渠道,反映了以石涛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家的宇宙观、美学观、艺术实践和价值追求。近代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都曾展出石涛的画作,并将其列于馆藏典籍名录中。
近代《石涛画语录》已有多部译著,但现有译本的数量和质量远远比不上文学戏剧典籍的译介成果。画论典籍中的专业术语在西方尚未有统一的译法,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译者如果不仔细辨析,极易误译和错译。文章拟在梳理“氤氲”源流的基础上,列举《石涛画语录》的4种英译本的翻译实例,详细考辨画论典籍中“氤氲”的内涵及文化意义。
一、“氤氲”在画论典籍中的内涵
“氤氲”又可写作“烟煴”或“絪緼”。“氤氲”最早的出处现在已无法考证,《易·系辞》中有“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之句,“氤氲”指天地阴阳二气交汇的绵密之状,使万物因天地二气交密而化育醇厚[1]56。在山水景物和绘画上,“氤氲”指弥漫于天地山川之间的烟雾,和因墨色浓淡变化而形成的有层次的感觉。
“氤氲”根植于中国画学理论体系,是绘画创作和构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氤氲”一词既是画学术语也是哲学术语,亦可理解为气和光混合动荡的样子,通过墨的深浅叠加,展现出山水画的虚远、宁静、缥缈、空灵。樊波教授在《气论与书法审美的三个维度》一文中将“气”归纳为:天地万物的本原之“气”、自然天赋的个性气质、塞于天地间的浩然之气[2]。先秦时期,“气”就被认为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本元基质。“气”与“土”“水”“火”是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气”虽被认为是一种不易察觉的存在,却是一种流动于万物之间活跃的能量,是生命的初始动力,人类的生存和繁衍都离不开“气”。“气”也是中国绘画审美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氤氲”起源于“气”的清浊化生,是“气”的外显活力。“氤氲”的核心是“气”的聚散,而消弭的过程是“化”。这里的“化”既有“幻化”“变化”“化生”之义,也蕴含着古人“参天化育”的人文情怀,氤氲之美也被认为是气化之美。
石涛在《氤氲章》中提到:“笔与墨会,是为氤氲。氤氲不分,是为混沌。”石涛认为“氤氲”是运用墨的浓淡变化,形成云蒸雾绕的意境。“氤氲”也饱含了中国古人对诗意栖居的追寻和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态美学智慧。石涛提出的“氤氲”说将哲学概念中的“氤氲”提升到了画学创作的高度,不仅为“氤氲”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发掘出其美学意义及内涵。“氤氲”与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的“一画”“蒙养”“远尘”“虚实”“生活”“了法”共同反映了中国画学思想的完整性、系统性和结构性。“氤氲”说与中国古代道家、禅宗、儒家思想贯通融合,体现了石涛身处的时代三教圆融的特点,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的重要体现[3]28。
二、画论典籍中术语的英译
截至2018年,利用Worldcat(全球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查阅到《石涛画语录》的译本共有7个,其中英译本5个,德译本1个,法译本1个。《石涛画语录》在翻译过程中有汉学家、华裔学者的“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的“译出”模式,这两种模式产生的文本截然不同。同时,画论典籍的译介还受到国家、市场、消费者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涉及法律、政策等多个方面[4]28。除了这些客观因素,译者所处年代,自身对中国画学的认知、对画学术语的理解都会对译著产生影响。画论本身的专业性很强,以文言文书写,译者不仅要运用翻译学理论,还要具备绘画专业知识和汉语知识。“译者既要审美,又要表现美,而审美是表现美的前提,只有识别了画论中的美学特征,把握了原作中的艺术魅力之所在,才能够再现原作的美。”[5]50关于术语的翻译,姜望琪教授曾在2005年提出3个原则,即透明性、准确性和可读性。侯国金教授于2009年提出了系统—可辨性原则。这两种理论曾引发激烈的论战。实际上,双方的观点从表面看虽然相对立,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互为补充的。“约定俗成性是语言系统性的体现,而准确性、透明性和可读性是通达可辨性的途径,将两者综合起来可作为术语翻译较为理想的指导思想。”[6]107
三、《石涛画语录》中“氤氲”的英译
《氤氲章》仅195字,“氤氲”共出现了4次。“氤氲”在《新英汉大词典》中有3种释义:(of smoke or mist)dense; thick; enshrouding。enshrouding义为“覆盖”“笼罩”,所以“氤氲”也被译为enshrouding mist或dense mist。例如:
(1)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译文1:The Generative force of heaven and earth,by means of which all things are constantly reproduced.(喜仁龙)
译文2: When Heaven and Earth unify intoharmonious atmosphere,ten thousand things will be transformed and purified.(考尔曼)
早在20世纪30年代,瑞典美术史学家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就曾致力于中国美术史及建筑园林的研究,他一生中数次来到中国,1936年喜仁龙在其TheChineseontheArtofPainting一书中,向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介绍了石涛的绘画理论。喜仁龙译本是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最早系统翻译并向西方读者传播石涛绘画理论的著作。喜仁龙将“氤氲”意译为“the Generative force of heaven and earth”,即天地间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宇宙中运动的力量源泉,凸显了“氤氲”在中国画学和哲学概念体系中的地位,符合《易经》对“氤氲”的解释。
在西方,接受度较高的《石涛画语录》译本是林语堂先生的译本和考尔曼教授的译本。例如:
(2) 笔与墨会,是为氤氲,氤氲不分,是为混沌。
译文1: Where the brush and ink blend,cloudy formsare produced.Undifferentiated,suchcloudy formsrepresent chaos.(林语堂)
译文2:When the brush strokes and ink wash are unified,this is calledYin Yün,that is harmo-nious atmosphere.Yin and Yün are not divided; they are harmonized.(考尔曼)
译文3:Ink mingled with water at the tip of brushwork brings about the artistic effect ofshadesof ink.Ink withoutshadesis nothing but a chaos in the painting.(王宏印)
(3)得笔墨之会,解氤氲之分,作辟混沌手,传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
译文1:To be able to control the mixture of brush and ink(stroke and wash),disperse thecloudy formsand create the universe and thus become a good artist on one’s own and be known to posterity—this comes from intelligence.(林语堂)
译文2:By grasping the union of brush strokes and ink wash,understanding the role played by thisharmonious atmosphere,becoming a creative artist who opens heaven and earth(the harmony),and transmitting all of ancients and moderns,one establishes his own school.All this is obtained through wisdom.(考尔曼)
译文3:An artist in his proper position is to handle his ink-and-brushwork in such a way that misting effect is balanced byshades of inkin the great natural scenes.His works then is sure to be high-valued as special and long passed through the ages together with his wonderful skills and talented genius.(王宏印)
(4)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事毕矣。
译文1:Transforming the One into the primevalcloudy forms— this is the height of artistic abi-
lity.(林语堂)
译文2:Transform oneness into thisharmo-nious atmosphere,and this is indeed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art in the world.(考尔曼)
译文3:Out of chaos into great order through myshades of ink! The universe is mine.(王宏印)
《石涛画语录》的全译本由林语堂翻译,是其译著TheChineseTheoryofArt:TranslationsfromtheMasterofChineseArt中的一章,由美国纽约的G.P.Putman’s Sons 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发行。此书收录了从先秦至清代的23篇画论文章,曾掀起20世纪西方研究中国画论的热潮[7]22。林译本的读者定位是不具备中国画论专业知识的西方读者,因此,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顾及读者的接受心理及其理解中国画学的能力,采用了去术语化,也就是归化的翻译方法,将“氤氲”译为cloudy forms,保留了其“烟云缭绕”的基本含义,但无法很好地传达“氤氲”在《石涛画语录》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林语堂的归化翻译策略除了体现在词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句子逻辑结构的处理上。例如:例(3)的汉语原文先描述后总结,属于归纳的逻辑组织方式,体现了汉语结构松散、句尾聚焦的特点;而林语堂在不改变内容的前提下,对句子的逻辑结构进行了调整,加入了to be able to的目的关系,使译文符合英语思维的特点,逻辑更加严谨。
考尔曼教授曾指出,林译本没有漏译之处,比起喜仁龙晦涩的译本更加生动,更加浅显易懂,适合没有中国画论专业知识的西方读者阅读。但也正因为如此,林译本缺少对中国画学术语的诠释,译文略显单薄,缺少原语的专业内涵。例如: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reads: “Where the brush and ink blend,cloudy forms are produced.”The rendering as ‘cloudy form’ fails to convey 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Yin Yün and is at least suggestive.Yin Yün does carry the idea of vagueness or mistiness,but this is not the ordinary mistiness of say,for example,a fog.This mistiness is the profoundly spiritual atmosphere generated by meng yang(蒙养).As has been mentioned,the principle of Yin Yün involves the unific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a fusion which purifies all things.[8]10-11
考尔曼在夏威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领域涉及东方美学与中国画论。1978年海牙的德古意特木桐出版社出版了他在197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PhilosophyofPaintingbyShih-T’ao—AtranslationandExpositionofhisHua-p’u。考尔曼翻译了《画谱》(《石涛画语录》的另一个版本,其作者是否为石涛学界尚无定论),对以往《石涛画语录》和《画谱》的译本进行了校正,并细致深刻地阐释了书中画学术语所蕴含的道家、儒家和禅宗思想。例如,对“氤氲”一词,他作了如下解释:
In painting,Yin Yün represents a revelation of P’o,the supreme simplicity or primordial unity.This expression is traceable to the I-Cing.This fusion of Yin Yün has been applied by Shih-tao to the union of brush strokes and ink washes.The subtle merging of brush and ink can create a spiritual atmosphere which produces transcendental feeling.[8]73
在考尔曼看来,“氤氲”一词可以追溯到《易经》,是笔墨力透纸背的一瞬间,通过墨的浓淡变化、渗透叠加创造出空灵之感,达到一种精神通透的境界。中国道教“齐物”思想在《石涛画语录》中贯穿始终。“齐物”,意为世间万物看似千差万别,实则都浑然一体,需同等看待。对于“氤氲”一词,考尔曼综合了哲学中的“齐物”思想和画学中“笔酣墨饱,气韵相融”的意境,采用了“音译+阐释”的策略,将其译为Yin Yün,that is harmonious atmosphere,在概念上既有独立性又有包容性。同样,在对例(3)的翻译处理上,考尔曼用了4个排比句来仿效汉语原文中句式对仗、环环紧扣的行文特点,使译文与汉语原文行文风格与气势相似。考尔曼的译文不仅传达出了原文思想上的精髓,还兼顾了译语与汉语原文形式上的统一。考尔曼的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审美期待,同时也折射出他对原著及源语文化的尊重,以及他希望将中国画论中的修辞手法和句式特点“复制”到译入语中的意图和努力。
王宏印教授在他编著的《〈画语录〉注译与石涛画论研究》附录部分对《石涛画语录》中的画学基本术语进行了翻译整理,并翻译了《石涛画语录》。王宏印教授对术语“氤氲”的解释为:“氤氲和混沌,既是绘事笔墨功夫,又根源于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理论。氤氲本为天地交合之气,化育万物之功。表现于画面,当然就是大化流行于山川河流之间,体现为道风仙骨之韵。所依据的,只能是笔墨交融之机,水云林霏弥漫之态了。”[1]58《石涛画语录》文风古雅,语言简洁流畅,思想深邃,尤其是画学术语,在哲学语境中有特定的含义,仅仅用一个词很难准确表达其含义。王宏印教授认为“氤氲”有多种译文:shades of ink;cosmic spirit;mist and cloud;blending of ink and water。这几种译文涵盖了“氤氲”的基本定义,云雾升腾、重叠晕染的画学效果,以及“齐物”的哲学思想。
王宏印教授在《〈画语录〉注译与石涛画论研究》中也谈到画学术语的翻译之难,因此译本保留了汉语原文,这样文本的接受对象既可以是热衷于中国文化的英语大众读者,也可以是具有中国画学专业知识的国内外学者。对于《石涛画语录》中出现的石涛画论的独创术语、哲学及禅宗术语、中国国画术语和绘画拟人术语的翻译,王宏印教授以源语为中心,采用了创造性释义、翻译变体、一词多译、保留传统译法和音译等多种翻译策略[9]。他在翻译实践中根据句子语境的变化,使用不同的搭配形式,将术语所承载的画论思想移入目的语中。如例(2)的译文,王宏印教授加入了“ink”一词,强调了墨对宣纸的晕染作用,而“shades”则展现了笔墨交融之后,墨色与水汽幻化衍生的景象,并与句尾的“混沌”呼应。
四、结语
“氤氲”是中国画论典籍中的核心概念,也是画论典籍翻译的难点之一。文章详细梳理了“氤氲”的文化源流,分析了“氤氲”作为画学和哲学术语的内涵,并列举画论典籍的4种英译本的翻译实例,探讨了“氤氲”的不同翻译策略。中国拥有许多画论典籍和书画佳作,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大部分经典著作从未对外译介。画论典籍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