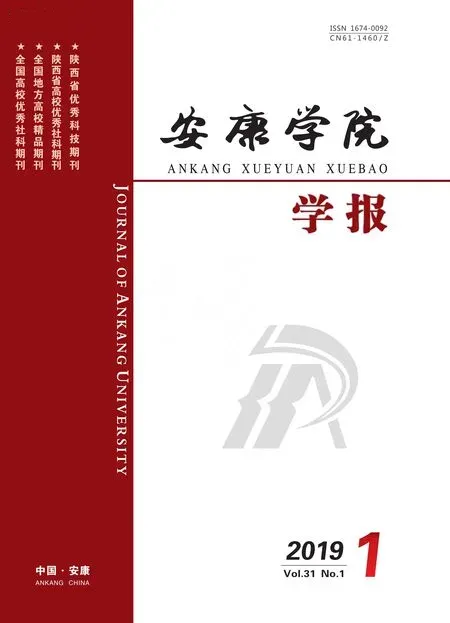《山祭》《水葬》的叙事模式研究
2019-03-15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任何时期的文学文本都带有其独特的人文历史韵味,都被烙上了历史环境文化所给予的印记。看着那些印记就能清晰地识别文学文本从属的时代,而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历史人文风情,自然就可以具象地表现时代的印记。《山祭》 《水葬》所描绘的陕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自然人文景观,正是那些印记在王蓬先生笔下的生动体现。同时,在他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体现出的种种叙事模式,又带给读者很多新鲜感悟。因此,研究《山祭》 《水葬》的叙事模式,对于反映表现在作家身上的时代印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叙事时间:蒙太奇式的穿插嵌入
蒙太奇手法援引爱森斯坦的观点,即合乎逻辑、条理贯通的叙述。“叙事蒙太奇由美国电影大师格里菲斯等人首创,是影视片中最常用的一种叙事方法。它的特征是以交代情节、展示事件为主旨,按照情节发展的时间流程、因果关系来分切组合镜头、场面和段落,从而引导观众理解剧情。”[1]《山祭》 《水葬》中对人物事件的描写,多用到蒙太奇式的穿插嵌入叙事,并且在叙事的过程中以时间为主轴勾连跳跃,小说故事人物情节合乎逻辑且具有戏剧冲突效果。
小说对于人物的叙述描写集中表现了蒙太奇式的叙事,如《山祭》中描写的关键性人物以及对这些人物的详细刻画。小说以宋老师来观音山为缘起,进而写到观音山的环境和他将要生活工作的地方——姚子怀家,随即跳出主线对姚子怀的人物设定进行拓展:“姚子怀是除匪英雄,一个赫赫有名的打山子。我没进山前,没上中学,甚至还没上小学前,就听到过姚子怀勇除土匪杨凤冈的传闻”[2]9,然后回到主线,写姚子怀回家办学校的情节。对郭发丁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是在小说主线到六四社教运动的时候,郭发丁被发展成为骨干,进而对其跳出主线进行书写:“郭发丁是平坝人,叫丁五子。小时家贫,被送到天台山庙里,学敲木鱼,做了和尚”[2]79,在穿插叙事中对这个人物进行描述,使人物形象变得鲜活灵动起来。通过对人物的介绍,将人物性格细化到具体事件中进行刻画,如姚子怀勇斗恶霸土匪杨凤冈:“他弹药不多、想过来拣只土枪,刚从丛林中亮出脑壳,姚子怀就眼圈发红、恨得咬牙、瞅得准确、扣得有力”[2]10。从这段描写中,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姚子怀这个人物形象,将之前的传闻细化到事件,更有效地吸引读者。
此外,蒙太奇式的叙事手法在《水葬》中更为突出,小说写到的蓝明堂、任一成、麻二、何一鸣都运用蒙太奇式的穿插嵌入叙事。小说主线行至任义成与翠翠之间萌生说不明、道不清的关系时,插入蓝明堂这个人物形象:“蓝明堂并非本地人。繁荣的山城吸引着远近山乡的人家。蓝明堂家便是。蓝明堂并不姓蓝,他姓黄,他来到这个世界便是个错误,能够姓黄,更是一个传奇”[3]32-33,这里对蓝明堂的描写也是进行小说叙事不可或缺的支点。写到任义成与翠翠的关系始终没有更进一步时,小说嵌入了任义成的人物背景叙事:“这一切所以发生在任义成身上,实在和他的身世经历、人生信条有关”[3]56,然后回到主线,书写翠翠与任义成一同拾板栗的情节。在主线写任义成与翠翠关系再近一步时,插入麻二的人物描写:“要说,麻二并未撒谎。要说,麻二确实是条经见过世面阵仗的汉子”[3]126-128,进而又回到主线。小说发生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情节冲突,而此时插入麻二的人物描写正加强了小说的矛盾冲突,增强小说的戏剧性。再写到任义成结婚,随即展开联想,进而插入何一鸣这个人物形象,同时也是插入了一段历史故事:“临解放时,何一鸣,正在省立汉中联中读高中。这学校前身为陕南书院,创办于清末,年代悠久,是陕南最享盛名的学府,历来注重师资,包容百家”[3]154-155。在插入的这段历史故事情节中,成功塑造何一鸣这一人形象。在时代的变化中,何一鸣又回到将军驿,进而与小说的主线相接,切合小说的叙事时间。
所有对人物的穿插描写,皆从叙事主线跳出,进行一番丰腴饱满的人物性格刻画,且任何一段对人物的塑造和小说主线都有强烈的黏附感,结构完整且严密。在《山祭》中,宋老师来到观音山被安排在姚子怀家,开始对观音山的整体环境和姚子怀家进行描述,插入姚子怀这个人物,再回到主线:“岂料,和姚子怀第一次见面,他险乎把我撵走”[2]11。小说后面的人物情节安排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在小说整体的结构中介绍人物并对其进行刻画,小说人物反过来又完善小说主体。
蒙太奇式的叙事较为成熟地在小说中呈现。在对人物进行性格方面的完善时,其装帧的时机十分巧妙,丰富了小说情节的感染力,增强其艺术表现力,着重表现为人物故事的冲突。如《水葬》中对麻二这个人物形象进行描写时,是在蓝明堂与其返回将军驿的途中,任义成与翠翠的关系向前推进之时进行的,而没有在小说开头描述麻二与翠翠时插入,或者在其他时段进行展开。对任义成的叙述,是与翠翠有着一种不愿触及的情感时进行展开,能丰富和完善任义成这个人物形象,并且在描写的过程中能对此前这个人物的表现进行有效的印证。又如《山祭》中对庞聋得的描写,并没有在小说开始到家接“我”这个情节对庞聋得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刻画,而是在其要与冬花结婚时进行描写,这就突出了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并且所有的环节都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使得故事情节扣人心弦。
小说叙事时间,也是运用蒙太奇式的时间穿插嵌入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穿插人物嵌入故事,使得所有的故事人物都能在以时间为主轴、以主人公为重心的周围形成紧密结合的故事链。所有的穿插嵌入描写,皆是展现蒙太奇式的时间叙事模式。将前后的故事有条理地进行组合,安排妥当,叙事前后逻辑严密且富有戏剧性。
二、叙事角度:以女性为中心
《山祭》采用以冬花为主的叙事模式。小说记叙宋老师与冬花从初识到最后的漠然,从宋老师的人性迷失到人性救赎,其中穿插了各种故事,如姚子怀与冬花、庞聋得与冬花、蔡万发与冬花,各个情节的铺展都是与冬花紧密相连的。《水葬》的叙事方式以翠翠为主,相较于《山祭》,强化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基调。王蓬先生在最开始着手写这部大作时,小说的书名是《驿道古镇——三条硬汉子与一个弱女子的命运》,写完最后一章时将书名定为《水葬》。小说整体以时间为主线,讲述翠翠与麻二、任义成、蓝明堂、何一鸣交错的情感。
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文本中,着力刻画女性坚韧刚强、勤劳能干、善解人意、人性和善的性格肖像。在《山祭》中,刻画冬花这个女性形象:“恰在这时,冬花从屋里出来,她一只脚踏出门坎,看到这情景,赶紧又躲进屋去,怕我见到她不好意思”[2]24,这里就可以看出冬花的善解人意,不想使“我”难堪。后面对冬花的描写更能表现她善解人意的一面:“眼含娇嗔地瞪我一眼,就又关切地问:‘累得很么?’”[2]39描写冬花准备独自去守夜,体现出她的勤劳能干:“这时,我才发现,她浑身拾掇得整洁利索,扛着杆十分小巧得土枪,腰间挂支玲珑得牛角;显得英姿勃勃,别有风采”[2]44,“只要我有一双手,能出口气,就不能让你受罪,让你挨饿”[2]196。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冬花遇到不幸时能够坚强不屈,凸显了其坚韧刚强的人物性格。
《水葬》中刻画翠翠这个女性形象:“翠翠素来心地善良、赶紧下灶房做饭”[3]16,表现翠翠的勤劳善良、待人和善。“这样,两个本来心心相印地人却相敬如宾,行为上反而疏远了”[3]228,这里体现翠翠人物性格中那份真善美。“挨斗之后,无论多晚,翠嫂都做些可口吃喝,一半分给麻二,一半摸黑给他送去”[3]229,这里体现翠翠的和善与能干,尊重内心的那份真情。“翠嫂受到猛然得扑压,本能地激起种反感。她奋力挣扎,手足并用,一下蹬开了蓝明堂。脸庞涨红,十分恼怒地说:‘一个大男人球没名堂,有这闲工夫多干些正事,让一镇人能把肚子混饱’”[3]280,此处可看出翠翠也有坚韧刚强、不屈服的劲头,面对蓝明堂无理的要求,她断然回绝。
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着重强调了女性在小说中非比常人的人物特质。不论是冬花还是翠翠,在面对时代所带给她们的惨烈遭遇时,都显示出比一般人坚韧;而遇到男人兽性发作时,则展现出非比常人般的刚强;在面对劳累的农活以及繁重的家务时,都是异常的勤劳能干;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心头小鹿乱撞,脸颊泛起红晕,能及时读懂对方的心理;在时代制造的“创口”上,她们都会最大限度地以人性的善去对待自己爱的人和自己亲近的人,更不会去扩大“创口”的感染面积。冬花和翠翠在这两部小说中是伟大的,也是小说叙事的关键。没有这两位女性人物的书写,就没有《山祭》和《水葬》的灵性。同时,王蓬对这两位女性的书写也增添了小说女性主义的色彩。
三、叙事结构:平民化与英雄化、狂欢化与奇观化
《山祭》与《水葬》的文本主角同为特殊时代下的社会底层人物,小说对人物的塑造描写以平民化与英雄化交织呈现。无论是在《山祭》中对姚子怀的描写,还是在《水葬》中对任义成、麻二、陈放、何一鸣的描写,他们都有着平民的一面,同时也有着英雄的一面。姚子怀年轻时在山岭中威震四方,与土匪头子单打独斗,“消息传开,姚子怀就跟打死了老虎的武松一样,披红挂彩”[2]10,展现了姚子怀英雄化的一面。而后他的生活平民化且多坎坷,事实上在人性的角度,他又何尝不是英雄呢。
相较于《山祭》,《水葬》更为突出地强化了这种平民化与英雄化的叙述,加上平淡与辉煌的前后对比,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阅读感。任义成、麻二、陈放、何一鸣的叙事,都能更为细致地表现人物前后的变化,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周围环境上,几乎都达到平民化与英雄化、平淡与辉煌的并存。《水葬》中对任义成英雄事迹的书写:“那陌生人奋身一跃,竟骑马一般坐在那根长长的圆木上,宛如骑着驯服的骏马,向岸边驰来。”[3]20“消息传开,古栈河上下,全晓得将军驿来了个好汉,洪浪中捞得木头,徒手博得巨蟒。”[3]23-24而后由英雄化到平民化的叙述,体现整个小说从辉煌到平淡的转变:“任义成,那鬼这些年委实窝囊,全无了当年气概,并且在运动中疯狗一般乱咬,没了人味”[3]257。无论是对任义成的书写,还是对小说其他人物的书写,都有从辉煌到平淡抑或是从平淡到辉煌的转变。当然,这种辉煌与平淡、英雄化与平民化都是在小说作品中论述,并在小说呈现的那个时空环境中进行探讨的。
小说文本中还体现出狂欢化叙事,呈现了奇观化的画面感。在《山祭》中,谁家办红白喜事抑或是在山里猎获黑熊、野猪、羚牛等,都会叫全村人一起吃“泡汤”,人们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吃得嘴角流油。《山祭》中描述姚子怀准备宣布宋老师与冬花的婚事时这样写道:“正午时候,开始吃‘刨膛’了。一摆出来,所有的人都啧啧称赞,欢呼喝彩。因为不是简单痛快的‘一锅熬’,而是正经八百的‘八大碗’。”[2]63在农村这样的场面并不是时刻都有的,即便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提升的现在,农村所能呈现的狂欢式奇观也越来越少了。在受到自然灾害的那几年,人们期待这样的日子。在《水葬》中,每当有红白喜事或其他值得庆祝的事时,便有这具备仪式感的“八大碗”,以及在一起的聚众谈笑和狂欢。
狂欢化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能缓和人们疲惫的神经,无论是在紧张的生产劳作中,还是在荒诞的历史时期中,都有相同的效果。在紧张的日常劳作的日子里,有一场狂欢,能促进全村人的情感,使得人们情感上有一定的归属,具有缓解压力的功效;在政治斗争时期“大会剥皮,小会攻心”的强大压力下,经历这样的狂欢,能给读者具象地展示荒诞时代诞生的荒诞故事。《山祭》中这样描述:“一到会场,那阵势、气氛,又把人搅得热血沸腾。”[2]109“这一刻钟,所有人的心都像一只奔跑在山林中的草麂,狂奔乱跳,一会跃上峰巅,一会又跌进幽谷,无法安静,难得平静。”[2]110《水葬》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工作组长问得恰到好处,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情绪被鼓动起来。沉闷雄浑的声音引得四周山崖经久不息地回响”[3]214,从中我们可以体验到时代背景下的狂欢叙事以及展现的奇观景象。
小说中的平民化与英雄化、平淡与辉煌、狂欢化与奇观化叙事结构的呈现,不仅形象地刻画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而且增强了小说的阅读性。如同《水葬》中任义成的书写从英雄式的出场,镇里传为神迹,而后归于平淡;或如《山祭》里姚子怀的描写,不仅是著名的“打山子”,而且是为民除害的英雄,随着小说时间主线的推进,姚子怀也随之在时代环境的风云变化中起起伏伏。
()()
综上所述,《山祭》和《水葬》中体现的蒙太奇式的穿插嵌入叙事、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以及平民化与英雄化、狂欢化与奇观化的叙事,为读者理解与认识陕南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同时两篇姊妹小说也为陕南地域文学在全国文学中的发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