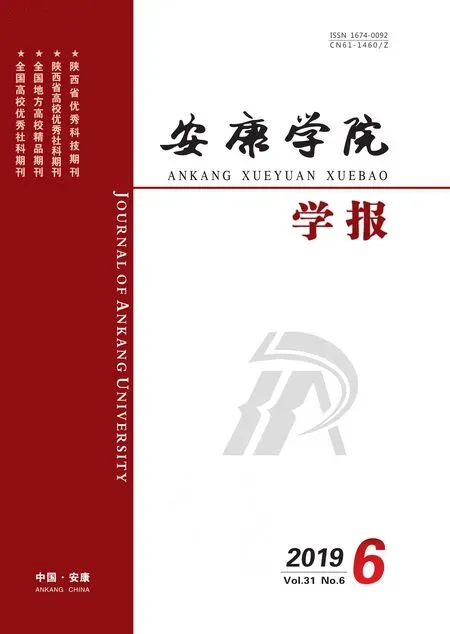严羽“尊唐说”对七子派影响问题探微
2019-03-15韩滢
韩 滢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严羽《沧浪诗话》完成后,最早被同乡人魏庆之著录于《诗人玉屑》,流传至后世。后人在论及严羽诗学之影响时,七子派是经常被提及的“学徒”之一。对于《沧浪诗话》是否真实地影响到作为明代最大诗歌流派的七子派,清初冯班《严氏纠谬》说:“嘉靖之末,王、李名盛。详其诗法,尽本于严沧浪”[1]283。王、李指嘉靖、隆庆年间兴起的后七子中王世贞、李攀龙等诗人,与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为代表的前七子一起被称为“七子派”。但众所周知,七子派的文学运动最终以“因袭模拟”的恶名告终,冯班《严氏纠谬》以攻讦严羽为宗旨,有意把他与七子派拉到一起,实则以七子派的恶名验证严羽诗法的谬误。翻检七子诸人的别集,李梦阳、何景明、康海、李攀龙等人对前代阮嗣宗、杜甫等诗人均有赞语,却独不提严沧浪,也没有引述《沧浪诗话》的只言片语。这样,所谓“尽本于严沧浪”之说就有些过于绝对了。
但是严沧浪影响明代诗学又是不争的事实。在明代,《沧浪诗话》成为诗学权威,“前后七子倡“格调”,他们“诗必盛唐”的拟古主张都分别承袭它的余风[2]。那么严羽与七子派的关系究竟是如何呢?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以学古为名,“诗必盛唐”是李梦阳等七子派的原则立场,而以“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3]又是严沧浪的基本观点,即“尊唐”是其共通点,因而以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探究严羽对七子派的具体影响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一、“唐诗分期说”的演变
七子派“诗必盛唐”的前提便是“四唐说”。钱谦益在《唐诗英华序》中说:“世之论唐诗,必曰初、盛、中、晚,老师竖儒,递相传述。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卿,而成于国初之高棅。”[4]他认为唐诗初、盛、中、晚的分类初创于严羽,成熟于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然而,对于唐诗分期的说法并非自严羽始,早在司空图的《与王驾评诗书》中就有关于唐诗从唐初的逐步发展继而走向顶峰,再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的谈论①《全唐文》卷807:“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琼,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阆仙东野、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听闻,逾褊浅矣。”中华书局,1983,第8486页.,其中已可看出以时来给唐诗分品的雏形,再到北宋理学家杨时更是明确提出了盛、中、晚三唐说②《龟山先生语录》卷二:“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陈伯海主编《唐诗品汇》下册,第3171页.,其划分已基本与严羽一致,可知“创于严沧浪”之说并不准确,那么严沧浪的“五唐分期说”对后世唐诗分期断限的影响有如此大么?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以时论体,把唐诗分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和晚唐体,虽然他将大历和元和分开论述,但是在《诗辨》中又将大历之诗和元白之诗统为一体,名谓“大历以还之诗”并称其“小乘禅”加以区分,在《诗评》中也有“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番言语”“大历以后”等提法,可见严羽已经看到了自大历以后的唐诗已不具有盛唐气象了,因而将其归为一类加以批评,其中实际已可看出“四唐说”的雏形了,这对元明时期的唐诗分类产生了影响。元初方回在评论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时说:“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诸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晚唐诸人,贾岛开一别派,姚和继之,沿而下亦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5]与严羽的思想基本吻合,另外在他的《瀛奎律随》中也有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的说法。到了元末杨士弘于至正四年(1344)编选的《唐音》中,有“始音”“正音”“遗响”一说,已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样的明确称谓(《唐音序》),但是他于“始音”中只收了初唐四杰的诗,“正音”以五、七言古诗、律诗、绝句的体裁分类,又分“唐初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编次。初唐的陈子昂与“沈、宋”并入盛唐诗中,“遗响”收录了唐代非大家之作,并大致按严羽“五唐说”的次序排列,由此可见,“四唐”说以严羽的“五唐说”为基础于元代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年代断限尚不明确。明初高棅继承并完善了“四唐说”,他在《唐诗品汇序》中指出:
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618—655),虞(世南)魏(征)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峤)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颋)、张(说)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义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为韦苏州(应物)之雅淡,刘随州(长卿)之闲旷,钱(起)、郎(士元)之清赡,皇甫(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之冲秀,秦公绪(系)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806—820)之际,则有柳愚溪(尊元)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籍)王(建)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836—840)以后,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浑)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悲,尚能黾勉气格,特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6]7
这是明代对于“四唐说”最为详尽的论证,高棅按品格的高下将唐诗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体,但从他的详细论说中我们可以发现,高棅是将严羽的“五唐说”进行了再加工,虽然他对于唐代分期的时间断限与严羽有明显差异,但是他的“详而分之”很明显是在严羽的影响之下,将严羽单列出来的大历体看作是中唐之再盛,把元和体视作趋于晚唐之变,从而得出“四唐说”的品类划分。如果说严羽的唐诗分期说不仅呈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分期,还包含着一种明确的价值判断,那么高棅则将这种价值判断进一步建立在一种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基础上了。他在《唐诗品汇序》开篇就提出各体诗歌的发展流变都是“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于终”[6]7的,即意图从事物发展流变的一般规律来为盛唐诗歌的品格之高提供依据。《明史·高棅传》中说:“其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尊之。”[7]7336可见这一观点遂成为明代之权威,严羽的“五唐说”流传至明俨然已进一步发展成划分唐诗品格的前提,前后七子也是在此基础上才能得以对唐诗各个时期的艺术风貌和价值做更为具体细致的分析,所谓“诗必盛唐”的口号也正是在对唐诗不同时期作出高下评判之后发出的呼声。
二、七子派对“以盛唐为法”观的继承与修正
在对唐诗作出分期之后,严羽和七子派都提出了要以盛唐为法的观点,只不过严羽的表述更为直接,其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开篇便先定下以“识”为主的学诗风气,并提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将盛唐诗歌和汉魏晋并提,作为学诗的一个楷模。然后在具体论证中,以禅喻诗,确立了正法眼、第一义的原则,同样将汉魏与盛唐诗歌标举为第一义。我们知道学习前人包括三个基本问题:以谁为典范?向典范学什么?如何学习?“以谁为典范”的问题严羽已做出了回答,但在具体向典范学习什么的问题上,严羽独独以盛唐为法,不提汉魏,并不是因为盛唐高于汉魏,而是严羽并未对汉魏与盛唐诗歌作一个高下之分,只是因为“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矣”,也就是说严羽认为盛唐诗可以替代汉魏诗的原因就在于盛唐的诗体更为完备,其不仅有汉魏所有的古体,也有汉魏所没有的律体,且都是“第一义”的,因而严羽独细谈“以盛唐为法”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严羽这种以“盛唐为法”的观点,给后人带来了一定影响。对七子派有开启之功的李东阳就说:“唐人不言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功,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滞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惟严沧浪之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顾其所自为作,徒得唐人体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处。”[8]可以看出,李东阳的尊唐观是受了严羽的影响的。因而现代在论及严羽对七子派诗学观的影响时往往会涉及严羽推崇汉魏晋唐思想对七子派的影响,是不无道理的。反观七子派,首先“诗必盛唐”的口号并非他们的原话,而是出自《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
梦阳才恩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尊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7]7348
显然,这一口号来自他人的概括。虽然七子派中没有人提过“诗必盛唐”的口号,但是他们的学古思想中无不流露出对于盛唐诗歌的赞赏。如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在《缶音序》中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9];后七子谢榛在提及唐诗也说道:“历观(盛唐)十四家所作,咸为可法,当选其诸集中最佳者,录成一轶,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10];李攀龙推崇盛唐的观点则更为偏执,其曾言:“诗自天宝以下,文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11]。由此可见,似乎是前后七子应和了严羽将汉魏盛唐视为学习方向的观点。
然而,二者虽都以盛唐为法,但各自的具体观点仍有差别。就汉魏与盛唐诗歌,即学习楷模的价值定位上有明显差异。如上文所提,严羽并没有对汉魏及盛唐诗歌做一个明显的高下区分,而七子派在严羽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辨析。从李梦阳《缶音序》中提到的“诗至唐,古调亡矣……”可以看出,他认为诗歌发展到了唐代已不具备汉魏诗歌的“古调”了,虽然它自有“唐调”但是“古调”已亡,汉魏的诗风唐代是没能继承下来的,这已经透出了李梦阳的价值判断。发展至后七子这种高下判断则更为直接,李攀龙在《选唐诗序》中直说:“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12]。也就是说,唐代古诗是达不到汉魏五言古诗的高度的,汉魏古诗的价值是要高于唐代古诗的。在这一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七子派提出了具有明显的辨体意识的观点。他们的诗学主张虽然可以笼统地概括为“诗必盛唐”,但他们从来没有像严羽那样笼统地主张“以汉魏晋盛唐为法”,而是古体、近体各有所师。何景明《海叟集序》云:“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李杜)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13]594意思是其学习歌行近体以李白、杜甫为师,再延及唐初与盛唐的大家,但是古诗就必须从汉魏诗歌中才能求来。秉承七子派诗歌理论的胡应麟也在《诗薮》称:“今人律则称唐,古则称汉,然唐之律远不如汉之古。”[14]可以看出七子派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古典诗歌规范化,而要实现规范化,就要为各体诗歌找到典范形态,是辨体意识发展到后期形成的一种观点。因而可以说,七子派主张古体、近体各有所依是对严羽古今体皆以盛唐为法主张的一个修正。
三、七子派对“尊唐抑宋”观的承接与发展
严羽的“五唐分期说”以及对盛唐诗歌的标举实际上含有一种将诗歌好坏系于时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更为直接地投射在他的“尊唐抑宋”观上。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迁书》中自诩“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可见他对于盛唐诗歌的推崇的同时直戳宋诗弊病。既然这样,他就自然要将唐、宋诗歌进行比较。
首先从诗之本色来看,严羽认为盛唐诗歌为“透彻之悟”,而宋诗则落入“野狐外道”“终不悟也”;其次于“兴趣”而言,严羽又提出“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1]26,与之相对“近代诸公”则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其中彰显了严羽对盛唐诗歌含蓄蕴藉、玲珑透彻的境界的推崇以及对宋诗刻意精工的批判,其褒贬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严羽曾多次提及“气象”,其在诗评中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可见严羽以“气象”一词来区分唐、宋诗歌,在诗辨中他又提及:“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当代学者多以风格来解释气象,如王运熙在《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沧浪诗话〉》中认为,诗的气象乃是诗呈露于外的诗歌的精神面貌;陶明濬则将人之气象与诗之气象贯通起来,以为“气象人之仪容”,是诗歌呈现出的整体精神风貌。那么在严羽眼里,唐、宋诗歌整体精神风貌有何不同呢?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迁书》中严羽说:“坡谷诸公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11]252-253子路本性粗豪,需要刻意学习才可符合孔门风范,而“笔力雄壮”是就外化为诗的力量、气魄而言,可见严羽并非仅仅看到符合盛唐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派的盛唐诗歌的审美特征,还看到了与刘勰以来推崇的“风骨”概念所暗含理想一致的盛唐诗歌风格面貌。严羽身处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南宋末年,时代的苦难必然唤起他的现实之感、忧患之情,他本人也写作了多首反映现实、战乱的诗歌,由此他对于“雄壮”诗风的推崇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他对于唐宋诗歌的褒贬不仅是在诗歌的审美特征上,还在于唐宋诗歌的整体精神面貌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虽不满江西诗人的粗豪,也不满企图以细腻圆润的笔调挽救江西之弊的“永嘉四灵”和“江湖派”。
受时代限制,严羽对宋诗的批判并未太过尖锐,如其对宋初尚沿袭唐人之诗的王禹偁、杨亿、欧阳修等人的诗还有所肯定,但其确实成了此种观点的一个先声,使得“尊唐抑宋”观发展至元明则越演越烈。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崧在《乾坤清气序》中说:“诗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诗,称李太白、杜少陵而止……长庆以降,已不复论。宋诗推苏黄,去李杜为近。逮宋季而无诗矣。”[15]其后“宋无诗”的观点便成为“众口一词”的舆论。如果说刘崧对文坛的“宋无诗”的言论影响还不大的话,那么作为明代“文章领袖”的李东阳则在《怀麓堂诗话》直言宋人于诗法有所得于诗则无所得,其对于前后七子的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李梦阳于《缶音序》说:“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言外之意,宋代没有唐调,所以无诗。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16],在《杂言》也说:“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13]666,都是强调唐宋异调,同样是以唐诗为标准来评判宋诗。那么,与其说宋无诗是七子派尊唐的理由,不如说他们是从尊唐的立场出发来判定“宋无诗”的。严羽的“尊唐抑宋”观发展至明已然演变成“一代自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七子派在对宋诗更为严厉以至于极端的批评中扛起了诗歌复古、回归传统审美风格的大旗,看似是对严羽“尊唐抑宋”观的进一步加深,实则是出于自身文学复古、回归诗学传统的目的,从而进行的对诗歌之格更为明确的评判。
综上所述,七子派理论之基础“四唐分期说”是在严羽“五唐说”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与明确的,其“诗必盛唐”的口号实则是对严羽诗法盛唐观的进一步修正,其“尊唐抑宋”观的发扬也是基于严羽的价值判断,结合自身的宗旨、目的所做出的更为笃定的价值选择。因而,从“尊唐观”这三个方面来看,七子派的理论是对严羽的观点的一个修正与发展,而非冯班所言是“近本于沧浪”的,近现代一些过于夸大严羽对七子派的影响,认为七子派直接继承严羽衣钵的观点实则为20世纪以来近现代人们对于理论的过于迷信所造成的结果,七子派与严羽的影响关系问题仍需要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分析,而非盲目地认为前者的理论必然对后者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