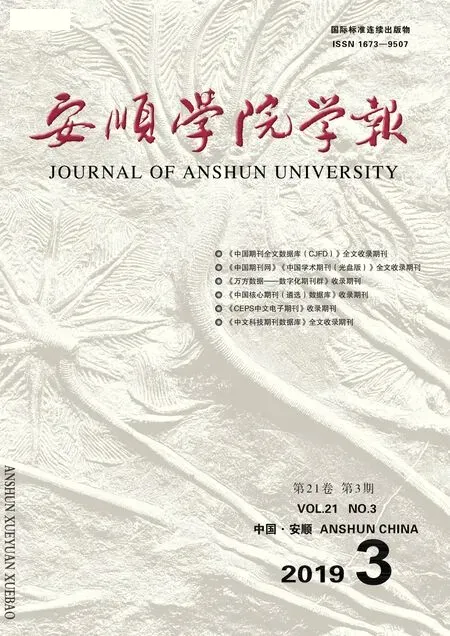沈从文《边城》生命主题的文化书写
2019-03-15
(安顺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以文学手段来描绘民俗,或者通过民俗的书写扩展文学艺术的表现功能,这是乡土作家在其创作中的普遍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沈从文作为乡土作家的优秀代表,其《边城》除了刻画诗意隽永的文学形象之外,同时也描摹了一幅幅美丽神奇的湘西特有的风情画卷,这些民俗文化的书写,不仅让文学作品增添一种文化魅力,而且能让读者从文学的张力中窥视湘西民族的淳朴与湘西民俗文化的深情。从沈从文的《边城》来看,作者对湘西民俗与文化的书写,可谓孜孜不倦,其中有别具一格的河边吊脚楼,有苗家姑娘恋爱的“赶边边场”,有盛大隆重的传统端午节,有感恩神明的赶秋节等等。这些民俗的书写也是读者了解湘西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当然,除了此类的热烈的场面书写之外,沈从文对人的生命主题同样具有一种特殊的关注。尽管沈从文对于生命主题的文化书写并不为多,然而生命主题书写与前面所提到的民俗书写,共同构建了沈从文笔下湘西民俗的风情与画卷,成为沈从文化书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内容。
一
生死作为人类的一种自然规律,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不仅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同时还具有文化的特殊性。沈从文作为一位乡土作家,在其小说《边城》中以优美的笔触,描绘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展现人性的善良美好。然而在现实中,战争、匪患、天灾、瘟疫等等,都窒息着作者的心灵。为此,沈从文将自己耳闻目睹的事件,以“题记”的形式放在了小说之前,这算是作者对生命主题关注的诠释。如其《新题记》中说:
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刊》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入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1]1-2
这段“题记”叙述了沈从文对自己创作《边城》时的一段生活记忆。很显然,这段记忆在很多版本的《边城》都没有收录,而且很多读者在品读沈从文散文时也对此曾有太多的忽略。从这段记忆来看,作者写了战乱中的死难者,写了老百姓的死亡者,写了自己母亲的死。尽管作者对于死亡的表述只有寥寥几字,然而这些死亡所产生的心灵的感受直接刺激作者在《边城》创作中对生命主题的关注,同时以一种乡土的笔调,对湘西茶峒有关死亡这一民俗进行了悲剧性叙述和民俗性书写。鲁迅曾经给悲剧下过这样的定义:“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218从沈从文《边城》的情感基调来看,其实具有非常浓郁的悲剧氛围。可以说,从翠翠的出生,便注定了她的悲剧,小说对此有过这样的叙述和交代: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后,这屯戍兵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职责,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翻考虑后,屯戍兵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业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愧。一面却怀了怜悯,依旧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1]3
从这段叙述来看,小说描写了两个人的死亡,一个是翠翠的父亲,因想逃离军旅追求平常人的生活而无望,最后服毒而死;一个是翠翠母亲,因与屯戍兵士的暧昧关系却又无法得到父亲的理解和支持,心怀羞愧,生了小孩之后,故意喝冷水而死。沈从文在小说中虽说是在着力刻画一个童年失去父爱和母爱的遗孤翠翠不幸的生活遭际,然而从字里行间却又流露出湘西民俗文化的诸多信息。一是湘西人的情,土家文化和苗族文化是湘西这块热土上所表现最为突出的文化形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的婚恋文化里,虽然有恋爱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同样具有很多文化上的禁忌,如果一旦打破了那种文化禁忌,那么就会造成了一系列的家庭悲剧和人生悲剧。从沈从文《边城》对于这种情的书写来看,翠翠母亲的死,就是因为她恋爱打破了文化禁忌,不是以一种光明正大的方式进行恋爱,而是以绝对自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感,最终无法得到世俗的认同,最终选择以死来对社会进行抗争,这种情着实非常高尚,但文化上与世俗之见偏离,因此,这种情在沈从文笔下就显得格外的复杂。二是湘西人的义,翠翠的父亲作为军人,他首先以服从军令天职,然而社会战乱却让无数无辜的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死亡,这对于具有血性和良知的军人来说,他对人生心存怀疑,对社会开始失望,这些让他心灵在矛盾中不断挣扎,并希望通过选择逃离来达到心灵的自我救赎。然而逃离军旅就意味着对职业的一种背叛,而且自己深爱的女人又因那种无法割舍的亲情而不愿跟他一起逃离,最终选择死亡以谢天下。正如在《边城》的《新题记》中说,“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1]1可见,在沈从文笔下的这种生命叙事,是对“义”的一次深刻诠释,其小说对湘西民族文化形态的呈现与表达,不仅赋予了一定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同时也是湘西文化中关于人性问题认知的情感反映。
二
重视家庭亲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亲人间和睦相处是华夏民族想要拥有的生活方式,早在《礼记》就有对亲情定义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任、臣忠,十者谓之人义。”[3]95沈从文在《边城》中对于亲情伦理的书写融入了一种极致的生命意义。《边城》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也许正是因为小说的悲剧性激发着人们心中压抑的那种怜悯与恐惧能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对于翠翠悲剧命运的怜悯与恐惧的产生,除了从小失去父母成为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孤儿所产生的情绪之外,便是与翠翠情感命运不可分割的茶峒小伙天宝和傩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基本伦理准则。从文化风俗来看,对歌是湘西青年自由恋爱的最活泼的方式,同时也是湘西青年男女生命激情最诗意的表现。青年男女通过对歌确定恋爱关系,这是自由恋爱中的基本法则。然而,沈从文对于天宝、傩送与翠翠之间这种诗意的情景安排,却是以一种悲剧来加以呈现。天宝与傩送作为同胞兄弟,他俩同时爱上了翠翠。从湘西的风俗来看,男女青年通过媒人说合来撮合,叫做“走车路”;如果通过男女对歌的方式进行恋爱,叫做“走马路”。天宝走的是车路,不仅喜欢翠翠,当着别人的面赞美翠翠,并且还亲自去试探爷爷的口气。傩送走的是“马路”,他跟翠翠是一种私下里的爱慕,而且翠翠心里更喜欢的是傩送。当天宝知道弟弟傩送也爱上翠翠之后,心里又十分不甘心,他试图说服老二傩送。由于爱情本身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傩送更是不愿放弃翠翠的爱情,还提出了跟哥哥天宝进行平等竞争。由于兄弟俩同时爱上翠翠,这对于船总顺顺来说说,也是一件非常难处理的事情。小说写道:“船总顺顺家中一方面,则天保大老的事已被二老知道了,傩送二老同时也让他哥哥知道了弟弟的心事。这一对难兄难弟原来同时爱上了那个撑渡船的外孙女。这事情在本地人说来并不希奇,边地俗话说:‘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有钱船总儿子,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不能成为稀罕的新闻,有一点困难处,只是这两兄弟到了谁应取得这个女人作媳妇时,是不是也还得照茶峒人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1]118谁能获得翠翠的爱情,兄弟之间是一场竞争,傩送提出用湘西男女最有情趣的对歌的方式进行平等竞争。沈从文对于兄弟俩的爱情争夺有过惟妙惟肖的描述:
我想告那老的,要他说句实在话。只一句话。不成,我跟船下桃源去了;成呢,便是要我撑渡船,我也答应了他。唱歌呢?这是你的拿手好戏,你要去做竹雀你就去吧,我不会捡马粪塞你嘴巴的。[1]122
从老大的只言片语,我们能够看到老大是如何的猝不及防,是一种如何烦恼,是如何的一种爽直和慷慨。当然,老大虽然不甘心,但也理智,他明白自己虽然喜欢翠翠,但翠翠更喜欢的是弟弟傩送。兄弟之间的竞争必然导致兄弟之间的失和,为了成全弟弟的爱情,他最终选择了远游他乡,在下常德的路上翻船遇难。在小说中,沈从文对于这种爱情叙述和书写正是以天宝的死来呈现。作为一名乡土作家,沈从文对于乡土的描绘和书写,总是以乡土的笔法来书写乡土的本真,而且这种乡土本真往往通过生命主题的书写来表达。对于天宝的死,沈从文并没有从正面进行描写,而且通过对一系列人物心理反应进行刻画,如船总顺顺听到儿子噩耗之后显得“异常”的镇定,而当摆渡老人听到噩耗之后却表现得十分地惊讶和惶恐;傩送听到兄弟的死讯,表现出一种深层的痛惜,而翠翠听到消息后感到十分害怕。显然,沈从文的这种侧面书写,一方面也许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敬重,因为年轻的天宝,作为一个具有活力的生命存在,他本来就不应该这么早就死去,而且他的死又是为了成全兄弟爱情的一种不幸;另一方面,也许是对自身生命存在意义的反思。在沈从文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出现朝不保夕的可能。然而,在这种亲情的描述上,这种死与因横祸而死又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沈从文也许想通过这种温情脉脉的亲情的毁灭来反思人生存的本质和意义。除此之外,作者在写作的目的上还具有双重性,他旨在通过一种挚情的描绘,表现湘西人的爱、乐、正直、诚实、伟大与性情之美丽,读后让人怀古幽情,让人不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当然,文学毕竟是文学,在翠翠善良、温情背后,又无不是现实的冷酷与无情,这双重的主题创作中,沈从文着重想刻画和表现的是前者,但后者又不能不表达。于是沈从文将后一主题融注在前一主题之中,从而达到“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的效果。因此当我们读《边城》时,无不被湘西的淳朴人群抓住心灵,但又总被一种莫名的淡淡的悲伤拽住,浅浅的伤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就是沈从文追求的创作风格。
沈从文对于湘西的描绘和书写,又无不体现他作为湘西汉子性情的体现,再苦再累也绝不轻易喊出来!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还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4]129他在《水云》中也说:“我的新书《边城》是出版了……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太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4]526那么作者是在怎样的困苦、屈辱与情绪下写作《边城》的?作者勾画了正直善良湘西人群画像、描摹了唯美的湘西风景画卷的背后是“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4]10,饱含“困苦与屈辱烙印”[4]11,“当时实在只有一面认识人的关系的‘丑恶’,一面认识军人对社会的‘罪恶’……三年中只看到一片杀戮……我看过这种杀戮无数,在待成熟生命中,且居然慢慢当成习惯。一面尽管视成习惯,一面自然即种下永远不承认强权的结子。总觉得现实并不合理……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4]9-10
显然,沈从文对于《边城》中的生命体验,不管是一种浪漫描绘还是现实的书写,这都无不打上了他生活际遇和时代的深深烙印。他曾经因家道中落混迹在军队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又有一段离开军队到北平求学饱尝各种失业、受辱的生活,加上看惯了杀人痛苦的人生经历和黑暗的社会环境让作者敢于直面人生的死亡,死亡相比作者的人生历程那都不是一件什么大事情,因而其小说中对于生命主题的关注与书写正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
三
悲剧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它是人类自由意志与自然规律和命运的搏击拼争,表现主体对现实苦难的困惑与问询,任何逃避的意想都与悲剧无缘。在文学主题的反映上,沈从文的乡土书写,无不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矛盾之下的困惑与回眸。尤其对于人物命运与生命的叙写,成为小说文本诠释话语的艺术与建构,而且这种悲剧的叙述,最终聚焦于老船夫死亡场景的描绘与书写。《边城》中的摆渡老人,他终其一生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曾经经历过女儿死亡的打击,艰难地将翠翠抚养长大成人。由于天宝远游的不幸遇难与翠翠婚事相关,直接导致翠翠婚姻的变故,这种突如其来的事变最终摧垮了老船夫的意志,最终在雷雨交加的夜里突然死去。可以说,这本身就是顺顺与老船夫两家人的共同悲剧。当然,对于老船夫死亡的悲剧叙述,沈从文并没有用过多悲剧性语言进行描绘,而是通过场景的描绘进行渲染和刻画。小说这样描写:“河街上船总顺顺,派人找了一只空船,带上副白木匣子,即刻向碧溪咀撑去。……留老兵守竹筏来往渡人,自己跑到翠翠家去看那个死者,眼泪湿莹莹的,摸了一会躺在床上硬僵僵的老友,又赶忙着做些应做的事情。到帮忙的人来了,从大河船上运来棺木也来了,住在城里的老道士,还带了许多法器,一件旧麻布道袍,并提了一只大公鸡,来尽义务办理念经起水诸事,也从筏上渡过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翠翠只坐在灶边矮凳上呜呜的哭着。”[1]190尽管小说对这些描写比较简洁,而且沈从文也并没有把老船夫的死写得那么悲戚,然而在读者心理也许更让人产生一种沉重感。尤其是老船夫下葬的场景描写,这种气氛显得更加浓烈:“大清早,帮忙的人从城里拿了绳索杠子赶来了。老船夫的白小棺材,为六个人抬着到那个倾屺了的塔后山岨上去埋葬时,船总顺顺,马兵,翠翠,老道士,黄狗皆跟在后面。到了预先掘就的方阱边,老道士照规矩先跳下去,把一点朱砂颗粒同白米安置到阱中四隅及中央,又烧了一点纸钱,爬出阱时就要抬棺木的人动手下肂。一会儿,那棺木便下了阱,拉去绳子,调整了方向,被新土掩盖了,翠翠还坐在地上呜咽。”[1]195
生死作为人类的一种自然规律,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现实。对于老船夫来说,他的死亡并不令人惊讶,也更不让人感觉到意外,然而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它本身带有一种悲剧的存在。当然,从文本书写上看,沈从文描写的是民间的习俗。尤其是对老船夫下葬场景的描写上,表面上是对湘西民俗的一种书写,行文也显得十分平淡,但从深层意义上看,却又是对生命的一种关注。
结 语
沈从文作为一名乡土作家,他对于乡土的描摹,对于乡土的刻画,对于乡土的眷恋,体现其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乡土情结。他用鲜活的人物形象、丰满的人物性格来表达对家乡人们的崇敬。同时,通过对生命主题的关注,他想告知人们,湘西人们是有情有义的。《边城》成功地阐释了“父慈”“子孝”“兄良”“弟弟”等亲情观,体现沈从文文学创作“悲中透喜,喜中折悲,悲喜纵横交错”的悲剧意识,让人感受到湘西人刚毅不屈的品格与热爱生活的态度。因此,探讨《边城》中的生命主题,通过对生命的关注来呈现文化的方式,为研究湘西的民俗文化开拓了新视角,避开了前人悲剧爱情、理想国度等主题研究视角,而边城世界与沈从文的人生世界具体有何种关联有待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