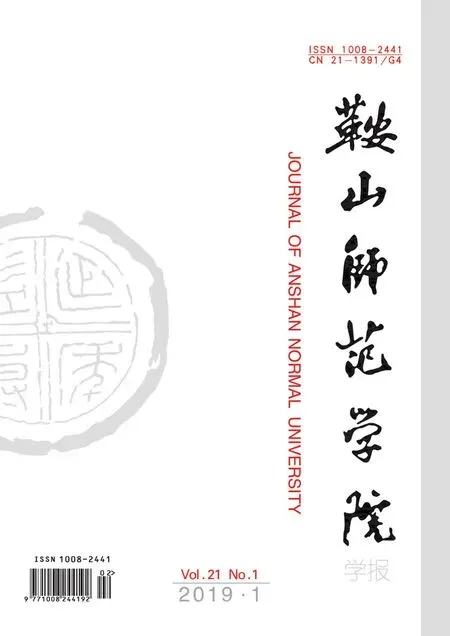新时期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现状
2019-03-15刘倩
刘 倩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1]“文本于经”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其含义主要有二:“一是文应本于经,这是出于对文以载道的期待。一是经为文之本,即文体原于五经”[2]。“五经”即指《诗》《书》《易》《礼》《春秋》五部典籍。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体学发端于先秦时期。若以专门论述文体问题专著的出现作为学科源头,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则应看作其肇始。由此可见,文体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著作中的《论体》篇和分类列纂,系统论述了各种文体的风格要求及流弊,反映了当时的文体观念;宋代开始,总集、笔记、诗话和词话类著作大量涌现,文体的分类越来越走上细化;明代《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两部专门性著作在全面搜集各类文体的基础上,细致论述各文体名称、性质和源流,辨体意识更为高涨;明清之际,对文章辨体的汇编和归纳,在继承前代分类和辨体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创了文体分门别类之先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演变完善史。
文体学虽在中国古代备受关注,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存在着“文体学意识比较淡薄的问题”[3],文体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科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谈及文体和文学,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长期以来,文体学研究处于被忽视被遗忘的境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学者把文体单纯看作是一种形式,然而从事文体学研究并不意味着忽略文章本质内容而走向形式主义。文体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能否很好地把握各种文体的特点和规律,直接关系到能否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理解,更是涉及新时代文学研究能否高效发展和创新的问题。新时期以来,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受到西方学界思想的猛烈冲击,西方对“style”的文学论述被引入国内,西方文体学研究各流派的文体思想也随之而来。但是,中国古代文学体系是建立在以礼乐政治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因此,不可避免造成中西文学观念的巨大差异,为避免西方文体学研究变成阻碍中国文体学发展的桎梏,新时代的文体学研究应遵循“重返中国传统学术史、文学史及价值论的整体思想语境,理当成为我们继续探索的出发点”[4]的理念。随着郭绍虞先生《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一文的发表,文体学迅速成为学界一个学术热点和学术研究前沿问题。近年来,在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逐渐进入学界主流研究领域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
2000年,有人提出要为古代文体立学[5]的主张,许多学者开始从事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吴承学、沙红兵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题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一文中提出“文体学学科”[6]这一概念,系统论述了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这一独立学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时之间,文体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致力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并取得丰富研究成果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郭绍虞、钱志熙、吴承学、何诗海、詹福瑞、任竞泽、胡大雷、郭建勋、罗宗强、郭英德、曾枣庄、蒋长栋、郗文倩等。一些高校十分重视对这一学术热点的探究,如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特别是一些师范类高校,它们较早地开始从事文体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这些大学纷纷成立专门性的文体学研究机构、研究中心或课题组,组织并参与各类中国古代文体学学术研讨会。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山大学中文系先后成立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中国文体学研究会也于2004年的第四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上成立。各研究机构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开展专题研讨会,如“文体史:文学形态发展史”“中国古代文体与文学”“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历史与理论”等主题研讨会,专门就文体学的发展史、具体文体研究等问题进行探讨。国家对这一学术前沿问题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大力的支持,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理念”“中国韵文文体形成与演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宋代文体学研究”“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等,更有大批省级社科项目基金投入研究。此外,许多外国学者也开始进行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赋”体及其相关作品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学者康达维,在对西方汉赋研究的评价中曾有“西方的汉赋研究几乎完全可以用一个名字来概括,即康达维”的说法[7]。2000年以后,随着文体学意识的高涨,文体研究的成果与日俱增,根据李南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著集目:1900—2014》统计,从2000年到2014年的15年间,关于文体学研究新出版专著多达265部,平均每年17部多;博士论文及博士后出站报告共计201篇,平均每年13篇多;硕士论文597篇,平均每年39篇多;期刊论文更是大量涌现,仅通论性论文就多达505篇。其中,关于中国古代文体通论性的专著主要有: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朱玲的《文学文体建构论》,章必功的《文体史话》,马建智的《中国古代问题分类学研究》,中山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学遗产>论坛论文集》《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连娥的《古今文体演变与派生》,吴承学、何诗海合编的《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伦思潮》,曾枣庄的《中国古代文体学》,邓国光的《文章体统:中国文体学的正变与流别》。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总论文体的期刊论文主要有:詹福瑞的《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文初步探索了文体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展望》两篇论文,为新时期文体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郭英德的《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系统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分类方式;钱志熙的《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通过对古代文体学内涵和传统的梳理,寻求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有效门径;吴承学、陈赟《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从宗经和尊体的角度探索了古代文体学的渊源。此外,2016年,由中山大学组织出版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标志着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步入了系统研究的新阶段。
二
“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1]随着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体的种类越来越多,文体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新时期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文体学家文体思想、专著及对文体学整体性把握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上。
(一)对古代文体学家文体思想的研究
“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8]文章的写作与作者的个人性情是紧密联系的,能够创作出《典论·论文》这部真正意义上专门论述文体问题的专著,其作者曹丕的文体思想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本同而末异”的观点,认为文章写作具有共同之处,但在文体上存在区别,进而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分类方法。学者们对曹丕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本同而异末”观点和“四科八体”分类法及二者的意义和影响研究上。如:郭德茂的《曹丕“本同末异”新议》通过对“本”与“末”所指内容的详尽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在曹丕以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限于本而不及末,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是曹丕首先提出来的”[9]这一说法;胡红梅的《曹丕文体学思想新解》一文,从文体的分类说、功能论以及批评法三个方面对曹丕的“本同而末异”与“四科八体”文体观进行细致的解读;墨白的《略论曹丕文体分类对魏晋南北朝文体研究的影响》则通过分析曹丕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家著作中文体观念的内在联系,指出曹丕文体分类思想对文体研究的重要奠基作用。另一个备受学者们关注的专门学者便是刘勰,其“体乎经”、辨体和破体等文体观念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重点。如:李建中的《刘勰“体乎经”的批评文体意义》通过刘勰“以经书为主来定体制”[10],全面分析了刘勰尊体、立体和辨体的文体意识;张利群的《刘勰“辨体”的文体论意蕴及批评学意义》对刘勰辨体的原因、方法、途径及其意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吴承学的《辨体与破体》指出了辨体与破题的辩证关系。
文体学家思想的多样性决定了文体学观点的差异性,中国古代文体学家思想研究呈现出致力于对文体学家就基本问题所持观点进行辨析的主要特点。近年来,研究较多的话题包括“文本于经”观点、文体分类问题、文笔之辨等。研究一门学科,探究其渊源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明确指出:“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自此便有了“文本于经”的说法。以吴承学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普遍认可这一观点。“自有文学写作之日起,就有了文体,也就有了对文体分类的实践操作和理论思考。”[11]可见,文体分类学研究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诗经》《典论·论文》《文心雕龙》等著作的研究都包含对文体分类观念的探究。文笔之辨自六朝兴起,胡大雷通过对言笔之辨的研究,对文笔之辨的“性质和趋向有更明确的认识”[12];王利器等学者则从文笔之辨的探源、嬗变以及意义等角度来探究文与笔之间的关系。
在新时期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以比较的方法介入研究也是进行文体学家思想研究的重要特点。如:赵俊玲对《文心雕龙》和《文选》两部著作中相同文体的系统比较,包括《<文心雕龙>与<文选>“哀”体观辨析》《<文心雕龙>与<文选>“封禅”文体的比较》《<文心雕龙>与<文选>祭文观辨析》《<文心雕龙>与<文选>诔文观辨析》《<文心雕龙>与<文选>檄文观辨析》五篇作品,文中结合两部具体著作,将文体置于一个动态变化的框架内,从两者不同的文体观、不同选文标准、不同侧重点等方面对相同的文体进行了跨时代视域的比较,进而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此类文体研究视野;同时,比较研究也为文体嬗变研究提供了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在探析诗、词、赋的历时性嬗变问题时也具有借鉴意义。又如尹伟的《<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分类辨析》,通过对《文心雕龙》和《文选》两部作品文体分类的不同,探究二者文体学观念的异同及其意义。此处,还有大量关于著作间文体分类观点比较的作品,包括代亮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张少康《<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等,通过对分类方法等的比较来辨析著作中的分类思想。
(二)对古代文体学专著的研究
“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体学思想研究是开展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需要系统而深入的文献整理与阐释研究。”[13]古代文献历来被看是传承思想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对某一文化现象的研究离不开这一领域中相关文献的支撑。同样在文体学中,对文体学古代专著的研究是了解文体学学科发展脉络最重要的手段。从事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学者们对相关的古代文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早期文献研究可上溯至对《论语》《尚书》中文体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古代文体学萌芽于先秦的说法。对这两部著作文体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属夏德靠,其全国高等学校优秀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先秦语言活动与中国早期文化模式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语类文献的生成、编撰及文体研究”对《论语》文体的生成及结构模式进行了系统地探究;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对《尚书》文体及其影响、意义进行了专门分析。专门论述文体的《典论·论文》《文心雕龙》《文选》《昭明文选》等著作更是学者们青睐的研究对象,其中,对《文心雕龙》中文体论的研究占据了中国古代文体学专著研究的半壁江山。这部著作五分之二的篇幅是专门的文体论论述,总论、创作论、批评论三部分的论述中也蕴含着诸如“体乎经”等重要的文体学观点,专著中的文体观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此,中山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对《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了较为典型的研究,中山大学文学院以吴承学为首的学者们从文体的渊源、发展脉络、作用、影响等角度对《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了系统的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者们则从各类文体的社会研究价值和意义角度对文体论中提及文体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辨疑。
新时期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对文体学专著探析主要呈现出以个案研究为主的特点。如:穆克宏的《<文选>文体分类再议》、仲晓婷《<文章辨体>的文体分类数目考》、何诗海与刘湘兰的《<文心雕龙>的文体学思想》等主要对古代较为经典或是在文体学上有重大意义的专著进行专门性研究,在对专著有关文体论说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专著的文体分类观念和分类意义为基础探究古代文体学思想;高黛英《<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学贡献》、吴未意的《论<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学贡献》、马建智的《<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成就和特点》、钱志熙的《<文选>“次文之体”杂议—<文选>在文体学与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局限》则在对专著中文体内容进行详细解读的基础上,探索各专著在历史发展中对文体学的贡献,进而清晰各专著对中国古代文体的继承与创新情况。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个案研究还包括以某一历史时期文体思想为对象开展的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贾奋然的《六朝文体批评研究》和任竞泽的《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前文从古代文体萌生、发展和繁荣三个历史分期所反映的新、旧文体的衍生、变迁研究六朝文体发展的新态势,通过分析六朝文体的体类体貌,辨析文体之争、名实、才性等重要文体问题,全面深入地考察六朝文体在中国古代文体批评的大语境中的独特性,归纳六朝文体与文体批评生成的深层文化原因。后文则通过对《沧浪诗话》《文章正宗》《辞学指南》、总集类书类著作以及帖子词、语录体、杂文乐语等具体文体形态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代表性总集类书及文献、文体中文体学思想的研究,透视出宋代文体学的全貌和总体特征。两篇论文为文体理论批评与文体学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中国古代文体学后世以历史时期为个案的研究开辟了道路。除此以外,对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学者文体思想的研究以及对某一类古代文体学总集的研究均属于古代文体学个案研究的范围。
(三)对古代文体学的整体性研究
鉴于对各种文体全面而系统把握的需要,总论性专著也开始出现。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作为“中国当代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形态学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成果[14]”。附录中的《古代文体分类》详细列出《文选》《文苑英华》《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经史百家杂钞》《骈体文钞》《涵芬楼古今文钞》等总集的文体分类条目,为后世文体分类研究提供了可参考文献。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曾枣庄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等专著都是力求在全面具体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体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新时期中国古代文体学分类研究囊括了对古代各种文体的研究,大致将古代文体分成辞赋、骈散、诗、词、小说、戏曲六个大类,对每一大类中各种文体都有所涉及。在关于各大类的研究中除了常见文体外,一些特殊文体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如辞赋类中的七体、九体、连珠体;骈散类中的八股文、儿郎伟、公牍;诗类中的沈宋体、楹联体、帖子词、唱和体;词类中的刍议词、多片词、櫽括词;小说类中的敦煌变文、笔记体、合生;戏曲中的缠令、鼓子词、集句散曲。在学术研究领域,不仅涌现出了一批关于特殊文体的期刊论文,还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和专著:有关七体、九体、连珠体、八股文等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如东北师范大学王宝红的《汉代“七”体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米建喜的《两汉辞赋“九体”作品研究》、郑州大学符欲静的《南北朝连珠体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林红的《明代八股时文对文学的背离与融通》等;有关沈宋体、帖子词研究的博士研究学位论文,如浙江大学李娟的《“沈宋体”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张晓红的《宋代帖子词研究》等;关于特殊文体的专著主要有王凯符的《八股文概说》、启功的《说八股》、刘乾先的《中国古代常用文体规范读本(八股文)》以及有关公牍文研究的《公牍诠义》《公牍通论》等。
“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学,有利于切实把握中国古代文艺学思想的精髓,有利于沉潜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奥秘。”[15]为切实把握古代文艺学精髓和古代文化思想奥秘,学界对古代文体学展开了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总论性文体学的研究内容总括了文体学辨名、分类、源流、体制、风格、创作、价值与功能等方面;文体学史的研究涉及研究范畴、对象、理论方法、学科史及相关批评等方面。文体的分类别研究也包括对各种文体的源流、体制、创作和批评的研究,并且对其中的每一方面又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以对文体源流的探究为例,在探究文体渊源的过程中,不仅对文体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研究,还对文体的分类、风格等进行探析,如朱玲的《中国古代文体的萌芽和演进》一文,不仅对文体的萌芽、发生分化以及演进进行了分析,还从宏观的角度对文体分类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心雕龙·通变》),文体的嬗变问题是文体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先贤时彦注重以时间为轴线、对同一文体进行纵向的研究,如对诗歌。从先秦《诗经》到唐宋律诗,诗体的变化是丰富的。严羽曾总结:“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16]对不同时期诗体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涵盖对答体、骚体、二言、三言、五言、七言、八言、沈宋体、别梁台体、别体、唱和体、宫体、汉乐府、回文体等诗体。其他文体与诗体也有着相同的发展脉络,大致经过兴起、成熟到衰落的嬗变过程,中国古代文体学对其他文体的研究大致也遵循这一研究轨迹。
三
“文体研究历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17]。伴随着学界文体学意识的觉醒,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涌现出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的文体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国的文体学更是繁难的课题”[18],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有待于学界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均衡的现象,研究者对某一时期或某一文体的研究比较集中,而对其他时期和文体的关注不足、研究不够深入。从纵向上来看,关于古代文体及相关文献的研究覆盖了从先秦到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的典型文体及代表性文体著作都得到了关注,但是具体研究的重点一般集中在先秦、汉魏六朝等历史时期,对明清时期文体学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从对各类文体的横向研究来比较,辞赋文体是目前为止最受关注的文体学研究热点之一,而对小说和戏曲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关于小说体制研究的论文数量只及辞赋类体制论文的一半。关于备受关注的历史时期及文体的文献资料挖掘和利用程度都比较充分,对研究者来说,着手从事此类研究更为便利,这也间接造成了研究者对其他历史时期和文体的忽视。由此可见,还有许多文体现象或内容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想要开拓新的研究点,避免对学术热点的过度重复研究,最重要的是占有丰富的古代文体学文献资料。“文献的搜集辨析乃是历史研究的必备功夫,而文献的解读阐释同样需要具备自觉的历史意识,否则便很难揭示古代文学思想的真实面貌。”[19]基于此,首先,需要全面、系统地整理古代文体学基本文献资料,不断完善中国古代文体学基础文献资料库,为各时期、各文体的研究提供基本的保障;其次,研究者要积极地深入解读这些文献资料,探究其中蕴含的文体观,阐发其文体学研究价值,为相关的文体学研究提供依据和便利。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多集中在对文体或文献的个案研究上,对古代文体缺乏整体性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像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学概论》这种对中国古代文体进行整体性把握的著作并不多见,多数作品致力于从文体学的某一文体现象或者文献著作进行个案分析。如关于古代专著的研究中,因“《文心雕龙》建立了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20],因此,关于文体分类学著作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这一作品上。但是,仅从一个角度开展研究,缺乏对全局的把握,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对文体学基本内容观点不一、看法片面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明确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目的,即在纷繁复杂的文体现象中发掘其背后隐藏的文体观念,以实现对中国古代文体学基本规律的总体把握。在这一目的的指引下,拓宽研究视野,将探索古代文体学总体规律与进行文体或文献个案研究相结合,既要关注个案的特点,又要实现对研究的整体把握。古代文体学是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体学著作、不同文体现象等都蕴涵其中。从这一角度上来看,探索古代文体整体规律的过程也是一个将无数个案分析成果进行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在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只有把对个案的研究置于对整体的把握之中,才能对文体学有一个科学而严谨的认识。
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文体学理论批评研究和文体学思想研究两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文体学理论批评研究成果丰硕,而文体学思想研究相对滞后。在文体学理论批评的研究中,关于尊体、辨体、破体等及某一具体文体的文体批评与文体观念研究不仅成了文体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而且相关科研成果在这一学科领域也占据重要地位。自王常新《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一文发表后,“文体学思想”一词进入了学术的视野。这一术语的提出并未推动研究者对其进行广泛的探索,仅有少数学者的单篇论文偶有涉及,整体性文体思想研究尚且缺乏。虽前文提及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诸如何诗海、刘湘兰的《<文心雕龙>的文体学思想》及任竞泽的《<典论·论文>文体学思想甄微》,但是相对于文体学理论批评,还是属于比较边缘化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依然存在着相对广阔的研究空间与可继续开拓的领域”[21]。这需要研究者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进而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既要充分重视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又要将研究推向新的理论高度,将文体观上升到思想领域的层面进行理解和把握。此外,还应加强文体学思想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融通,“文学思想的发展与哲学思想、艺术思想、宗教思想等等有关系……这些相邻学科影响文学思想,是非常复杂的”[22],同样,文体学思想研究也需要在跨学科意识的指导下,去探究其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并不完整,专门从事文体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并不多见。2000年以后,随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文体学研究中心相继建立,古代文体学研究意识在学界一度高涨,这也带来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但是在整个学术领域内,大量的研究成果多是以个人研究的形式出现,由于个人研究能力的局限性,研究也多以个案性研究为主。中山大学以吴承学为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心在学者们的密切合作下出版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为广大文体研究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这在文体学研究领域是首创性的。近年来,以学术团体合作的方式开展的文体学研究并不多见,“古代文体研究的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23]。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体学学科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二是文体学究的缺乏系统性。因此,在今后文体学研究中,要进一步加强广大学者的古代文体学学科意识,把完善文体学学科建设提上学术研究日程,在充分把握古代文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前提下,明确定位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研究范畴;同时,在与其他学科相交叉、与国外文体学相比较的过程中,要充分保持自身的学科独立性。此外,对古代文体的研究还需具有系统性,一切从史料出发,立足于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挖掘,梳理出清晰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脉络和体系;以个案研究与整体把握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开拓文体学研究的新领域,增强古代文体学研究在学界的影响,进一步提高其学术地位。通过提升意识和推进系统性研究,推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的完善,进而吸引更多学者致力于文体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