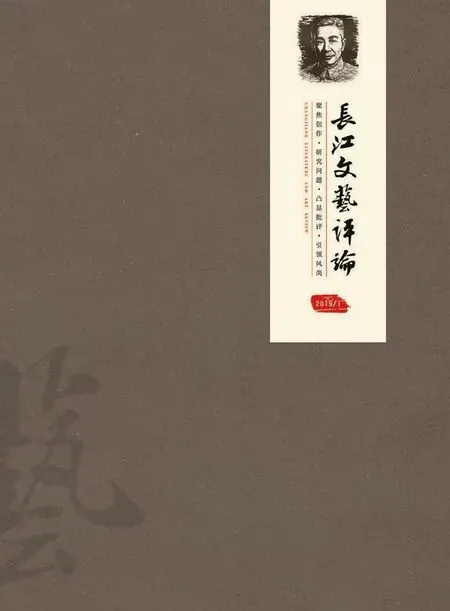主旋律电影的变与不
——近十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叙事研究变
2019-03-15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达到了历史性的606亿元。其中,票房冠军《红海行动》收获了36.48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占2018年全年票房总额的6%,相当于2010年全国电影票房总额的33%。而倘若将《红海行动》置于2017年的电影市场,它所取得的票房成绩还不足以载入史册,当年一部现象级的电影《战狼2》创造了56.8亿元的票房,相当于2010年全国电影票房的56%。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勉强突破100亿元,随后便以每两年增加一个百亿的速度一路高歌猛进。
2010年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确定了坐标体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2010年前后,主旋律电影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09年《建国大业》上映,在与好莱坞大片《2012》同台对垒的情况下,它依然取得了4.6亿元的票房,名列2009年票房榜第三名。而五年前的2004年,备受关注的主旋律影片《张思德》仅取得了2900万的全国票房。
主旋律电影在电影市场上取得较好成绩的时期,也是主旋律电影在叙事层面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正是这种叙事层面的变化,推动了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发展。
一、主旋律电影的叙事变化
2010年前后,以《建国大业》为代表,主旋律电影集中发力,陆续诞生了《建党伟业》《战狼》《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等主旋律电影。这些电影的市场表现和口碑较好,为多年以来持续低迷的主旋律电影市场注入了强心针。
通过图1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主旋律电影市场表现较好,除部分年份外,其他时间均冲进了当年度的票房排行前十。第二,香港导演是缔造主旋律电影票房神话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三,民营资本是投资制作主旋律电影的重要主体之一。第四,在“重大历史题材”“重要历史人物”这两个主旋律电影的传统领域,创作者们已经在遵从规训和迎合市场趣味之间驾轻就熟。譬如对“建国三部曲”的投资主体、导演和演员选任上,有关部门均表现出了较高的宽容度。
通过研究这几部电影的文本可以发现,在叙事层面相较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它们有几个显著的变化。
(一)视觉奇观:连接现实和历史的浮桥
以《建国大业》为标志,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在场面的设计、情景的布置上越发强调“奇观”。这种视觉的奇观化倾向在2014年版的《智取威虎山》中达到顶峰。
香港导演徐克选择营造视觉奇观的方式来改造《智取威虎山》。首先,在时空设置上,他将全片置于“追忆”的氛围中,借用韩庚扮演的姜磊的视角开始寻根、追述之旅。在这样的一种设定中,贯穿于原著、旧版电影、京剧电影里的一个问题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杨子荣到底为什么能够成为“孤”胆英雄?因为他是孙辈追忆里的祖辈,是“记忆”而不是“组织”赋予了他神话般的能力和色彩。在这种血亲关系的设定下,革命英雄巧妙地与现实串联起来成为了“我爷爷那一辈”,从而使得观众在情感体认上实现了从宏观到具体、从历史到个人的可能。
其次,在场面设计上,徐克营造了另一个“龙门客栈”。通过把人物置于密闭的、险象环生的场所里,以人物如何化解接踵而至的危机为叙事动力,从而把历史的惨烈残酷转化为通关式的智斗游戏,把时代洪流的不可抗拒性置换为个人的机敏行动。围绕着危机的爆发和解决,在观看人物如何落入和逃脱险境的过程里,人物就构成了奇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该片结尾用“彩蛋”进一步强化了“奇观”——在孙子的想象中,土匪座山雕与杨子荣爷爷发生了一场飞机大战。这场“飞机大战”采用了香港电影传统的正邪对立模式——将正邪双方置于绝境,以两者智力和武力的较量来区分胜负,最终邪恶力量消亡。《智取威虎山》片尾的“彩蛋”既是导演徐克对香港电影传统的一种延续,也是他在改造主旋律电影方面的一次尝试。同时电影中的孙辈还象征着当代青年对历史的再造与主动融合。

图1
(二)性别叙事:主旋律的“浪漫”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在性别叙事上也有较大的突破。
第一,女性角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她们不再是历史中的旁观者,而是积极主动的建造者之一。“建国三部曲”中出现了众多的女性角色,由于历史事实和叙事体量的庞大,这些女性角色大多是蜻蜓点水式的形象展现,难以真正深入到人物塑造的层次。但相较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女性角色的集中亮相和人物形象呈现出来的青春靓丽,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在《红海行动》的叙事中,女记者、女突击队员同样是捍卫人类和平事业的功臣,而不再是承载爱情想象和性别观看的载体,也不再是等待拯救的“花瓶”。
第二,女性角色蕴含的个人意志的凸显,打破了主旋律电影在表现女性角色时的刻板。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从个人史角度还原了一段香江传奇,片中周迅扮演的“方姑”始终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她因迷恋茅盾的文字而与彭于晏扮演的“刘黑仔”相遇,又在懵懂中加入了游击队,导致母亲被日本人枪杀。“方姑”虽然处于懵懂状态,但她对自身生命的体悟和把握,对自身行为的绝对自主,对战争、正义的本质追问,为我们思考时代裹挟之下个体命运的无常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该片始终以一种疏离的眼光看待香港沦陷的历史,鲜见地不去追问人物的动机和历史的宏大,反倒使得全片具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
这种女性个人意志的凸显,在《云水谣》《智取威虎山》中都是缺位的。《云水谣》中围绕陈秋水设置的两个女性角色,始终未能摆脱“从一而终”的阴影。在情感表达、承继方式日趋多元的当下,强调爱情的坚贞固然是无可指摘的,但持有“女之耽兮不可脱也”的心态则是历史的退步。《智取威虎山》中除了小白鸽外,还有一个承担着重要叙事功能的女性角色马青莲。马青莲被土匪强掳上山,逃跑无望后转而成了座山雕色诱试探众土匪的工具。马青莲的形象,是敌特片、谍战片中女特务形象的畸变,故而就体现不出一丝进步的意味。因此,尽管《明月几时有》的票房表现不尽人意,口碑也呈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但就女性角色的塑造而言,它在一众主旋律电影中是最值得肯定的。
(三)家国想象:共建当代神话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论及国家民族的起源时,以“想象的共同体”来概括它们的本质。他认为在共同体生成的过程中,共同的记忆、语言、仪式和习俗,是维持共同体稳定性的重要来源。对于国家意志而言,主旋律电影在构建共同记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影像再现历史、表现历史,主旋律电影可以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承继性和合理性予以阐释。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文化形式,电影的普及程度较高、接受门槛较低,观众不需要有大量的相关知识储备就能接受、理解电影。因此在实现情感认同和价值观认同方面,电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本文重点讨论的几部主旋律电影中,“建国三部曲”指向的是过去的筚路蓝缕,本质上还是对政权的合法性和历史承继性的再确认。“建国三部曲”选择了大场面、明星集体演绎的方式规避了创世神话中的问题。大量启用了当红演员和“流量明星”,利用演员的影响力在观众当中构造一个“情感共同体”。尽管这个情感共同体指向的不是角色(历史)而是演员,但一样可以导致“移情”。
《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几部影片在构建共同记忆方面,把目标投向了当代,指向的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这几部影片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故事展开的空间发生在中国边境或者是境外。第二,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中国人遭遇了民族生存危机。在《战狼1》中,境外邪恶势力打算利用中国人的基因数据库研发生物武器,以达到灭绝中华民族的目的。《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讲述的是中国人的海外生存遭受暴力侵袭。第三,境外势力是对民族生存的主要威胁,他们是国际军火集团、非法跨国药企、军阀、雇佣兵等。
在美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中,以《007》系列电影、《碟中谍》系列电影、超级英雄系列电影为代表,如何解决邪恶势力带来的生存危机是这些电影不变的母题。“邪恶势力”的表征经历了从苏联、到疯狂的科学家、再到国际军火商、金融寡头、恐怖主义组织乃至外星人的嬗变。通过解决“外来”的危机,内在的矛盾和冲突被掩盖了。从这个角度而言,《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是这些电影的镜像,它们讲述的是在国际邪恶、敌对力量的对抗下,中国人如何争取安全稳定的国际生存空间以及维护民族尊严的故事。它们是主旋律电影发展历程中的必然产物。当革命和创世神话的言说空间越来越小的时候,指向现实、贴近现实是主旋律电影的一个出路。但它又不能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的路数进行创作,只能在当代神话的塑造上去下功夫。通过展示个人遭遇去隐喻民族的国际生存,通过展示国家军备、军队的实力以呼应大国崛起的时代之音。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建立了见证并参与当代神话的仪式感,关于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情感油然而生。
二、变化的观众与变化的“主旋律电影”
以2010年为起点,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来自于观众,观众一手缔造了票房神话和新的观影习惯、电影文化。观众的喜好是市场的风向标,抵达观众实现意识形态认同是主旋律电影的目标。在抵达观众的手段和方法上,以这些电影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真正做到了“多样化”。
作为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旋律电影秉承了教育、指导观众的观念。这种观念并非主旋律电影独有。在中国的语境里,电影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娱乐产品和消费品,而是要与某些思想、价值取向联系起来,电影观众就是这些思想和价值的接受者。在这种受众观念的影响下,以往主旋律电影对于它的观众是淡漠和隔膜的,这就导致了“高大全”式样的主旋律电影越来越脱离市场和观众,而随着媒介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和多元,主旋律电影面对的观众群体更加复杂,也赋予了观众更多选择、解读的权力。一方面,当前的文化市场格外繁荣,人们可以观看的电影从类型和数量上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另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去表达对电影的观点和看法,进而影响到一部电影的口碑和票房。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忽视观众、自觉或不自觉地疏远观众,不仅使得主旋律电影难以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的功能,还有可能面临丧失存在价值的危险。
那么什么是新型观众呢?新型观众之“新”,“新”在他们所处的文化生态。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当代观众是一个处于互联网生态中的特殊群体。相较于历史上的观众而言,他们观看电影、接受电影、评价电影的手段和渠道更加多元,他们理解电影的方式和水平也非常复杂、多样。以豆瓣电影为例,豆瓣电影的用户自发发展出了一套评价电影的标准和方法。在豆瓣电影上,电影不是以形式或内容上的共性归类,而是以烧脑、虐心、禁欲等具有极端个人化、情感指向化的标签而存在的。除此之外,豆瓣电影用户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对某部电影发表评价,这种评价是私人化的、去规范化的,并可以借助网络广泛传播。相较于学术研究文章,网友这种自发的、浅层次的评价具有更强的传播力,也就为网络影评发挥影响力创造了有益的条件。
这种新文化生态下的观众(网民)情绪,与主旋律电影相遇,虽然在爱国主义情感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公约数,但我们也要看到,它还凸显了强烈的、具有叛逆意味的个人情绪,与“主旋律电影”崇尚的集体意识确有抵牾。因此,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如果不加以改进,就很难满足当代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趣味。
在《战狼2》创造中国票房纪录的2017年,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情8》紧随其后,作为系列电影的第八部,该片场均观影人次为37人,高于《战狼2》的36人,票房为26.7亿占全年票房总额的4.8%。《变形金刚5》名列第5名,票房占比2.3%。2017年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二十名中,共有12部好莱坞电影、1部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榜上有名。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里,依然有9部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前二十位。美国电影,尤其是以视觉特效为卖点的电影,在中国依然拥有极强的市场号召力和庞大的观影群体。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叙事和空间营造上的奇观化趋势,既是主旋律电影市场化、商业化的必经之路,也迎合了深受好莱坞影响的一代观众的观影口味。
在“猫眼电影”的网页上有一个“城市画像”功能。一部电影上线后,网络用户可以通过该功能标注“看过”或者“想看”,以表达对某部电影的关注。根据这个功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来看,《建军大业》的观众中有54.8%为女性观众,是“建国三部曲”中女性观众最多的一部。《建军大业》启用了大量的当红年轻男明星。对于年轻观众而言,历史是隔膜的,但扮演历史角色的演员是鲜活的,在这种对演员的迷恋中,观众是有可能由演员“移情”到角色,并引发观众对历史的认同。但这种情感的移情注定不能长久,对主旋律电影而言,将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的目标寄托于演员的魅力,就有可能面临演员自身形象破产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在“建国三部曲”中扮演过历史人物的演员文章、黄海波都陷入了丑闻,而扮演叶挺的“小鲜肉”演员则遭到了叶氏后人的公开抨击。
对于当代观众而言,解构、戏谑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2015年前后,一部网络漫画《那年那兔那些事》横空出世,通过戏说的形式讲述了中国1949年后的历史,在网络上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和追捧。这部漫画采用了网络文化的形式,传达的却是“主旋律”的内容,可见令观众淡漠的并不是价值观念,而是呈现价值观念的形式。任何一种叙事艺术都要与当下发生联系,无论是从价值观上直指当代,还是从形式上更新,都要尽量地贴近时代和受众。如果把“主旋律电影”的意义看作是一个系统,那么它的核心部分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不能自我解构、戏谑的;但在其他层面,则可以通过增加女性角色的重要性、塑造丰富复杂的“边缘英雄”的方式,来吸引观众、引发观众的认同和共鸣。
此外,《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还赋予了观众一种参与当代重大历史、建构家国神话的仪式感。《战狼》等电影的叙事里,把民族的生存置于国际争端和冲突中,并以普通公民个人的遭遇隐喻全体国人的际遇,将角色的忧患置换为民族的忧患,喊出了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口号。当中国国力继续提升,必须寻求更为宽广的国际生存空间,难以避免地与世界发生更多的争端和冲突时,此类以激昂民族情感、提振民族信心为主要诉求的电影,也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和现实需求。
三、“主旋律电影”与“主流电影”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近十年来主旋律电影类型化、明星化的趋势越发明显,似乎与商业电影的界限不那么泾渭分明了。确实,我们很难将《战狼2》《建军大业》和1990年代的《周恩来》《焦裕禄》,或1950年代的《南征北战》并列起来予以比较。因此,倘若不引入新的概念或者对“主旋律电影”的内涵予以扩充和更新,那么“主旋律电影”的确有可能为“主流电影”和“新主流电影”等概念取代。
1987年,在原广电部电影局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主旋律电影”的概念首次提出。当时中国电影在市场化道路上的探索刚刚起步,“娱乐片”方兴未艾,抱着引导、整顿、规范电影市场的目的,倡导“主旋律电影”的思路,首次进入意识形态管理层的视野。
有学者在研究“主旋律电影”的发生时,认为这个概念有两个重要的特点——表述的权威化和内涵(所指)的滑动。亦即主旋律电影不是从创作实践走向理论思考,并由下而上自发形成为一种文艺指导思想的。在世界电影史中,某个电影概念由国家意志提出,并不断赋予其学术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同时拔高此类影片政治门槛的做法是比较少见的。主旋律电影就是其中一个,这种做法也就为它奠定了承载意识形态意图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87年后,主旋律电影的内涵经历了从“宽泛—狭窄—宽泛的曲线变化过程”,但主旋律这个概念的深层次内核却较少遭遇冲击。
1991年,《当代电影》发表评论员文章《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电影创作的广阔道路》,该文对主旋律电影做出了概念界定:“电影创作的主旋律,概括地说,应当是通过具体作品体现出一种紧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潮流,热爱祖国,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积极反应沸腾的现实生活,强烈表现无私奉献精神,基调昂扬向上,能够激发人们追求理想的意志和催人奋进的艺术力量。”
自此,主旋律电影的内涵被概括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而真正流传开来。而“主旋律”和“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早在1994年就以时任最高领导人讲话的方式予以了廓清和明确。“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在这个概念限定的语境内,“主旋律”是根本原则和目的,“多样化”是手段和工具。
九十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海外电影的涌入和国内电影市场的发展,主旋律电影在内容、人物、情节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尝试和改变,但收效甚微,票房表现和口碑都不尽如人意。也是这一时期,学界提出了“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的说法。
西方电影文化语境中的“主流电影”,源于西方通行的对商业电影的指称,是从形式上、题材上、情节上对某些电影的概括总结,它指向的是电影的商品属性和类型特征。而在中国的语境里,“主流电影”是对电影的内涵、思想和精神气质的凝练,是一种价值导向和文化属性。因此在借用“主流电影”这个概念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原始含义必然指向消费主义,其次还要考虑如何缝合主流形式和主流价值观。“新主流电影”则是中国学者的创造,它关注的是如何在一部电影中将意识形态、市场需求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两个概念大行其道的时候,正是主旋律电影在创作上寻求多样化,并出现向类型片借鉴创作经验苗头的时候。尽管近年来主旋律电影表现亮眼,但从中国电影市场来看,这些主旋律电影并未能形成强大的规模效应,依然存在着大量未能在市场上激起一点水花的主旋律电影。如《信仰者》(2018年,票房1151万元)、《李保国》(2018年,票房 1233万元)、《柴生芳》(2015年,票房2万元)等,以及未能进入院线的主旋律电影,如《红盾先锋》《红军乡》等等只有网络介绍而没有任何放映记录的电影。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状,使得主旋律电影的面貌越发暧昧不明。
“新主流电影”也是如此。它先要面临“主流电影”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别于主旋律电影的概念而存在。其次还要面临如何平衡意识形态与市场需求。作为商品的电影以实现销售为目标,作为文艺作品的电影则要“文以载道”。如何解决两种逻辑的内在冲突,则是“新主流电影”这个概念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尽管称谓发生了流变,边界得到了拓展,但“主流”也好、“新主流”也好,本质上还是“主旋律”这个坚硬的内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反映。“主旋律电影”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主旋律”。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门户网站:http://www.sapprft.gov.cn/。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3]现代电影史上有软性电影和左翼电影的论争,当代电影史里也有对娱乐片主体论的批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电影的宣教功能和娱乐功能是相互对立的。
[4]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中心门户网站:http://www.cn nic.net.cn/。
[5]有学者认为,主旋律电影中的主人公形象可以概括为“原生态英雄”“凡俗(边缘)英雄”,后者以贴近日常的方式消解了英雄和普通人的心理距离,可以在观众中产生亲和力和情感认同。参见彭涛《“边缘英雄”当适可而止——评近年来军事题材电视剧英雄形象塑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1期。
[6][7]彭涛:《坚守与兼容——主旋律电影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8]《当代电影》杂志评论员:《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电影创作的广阔道路》,《当代电影》,1991年第1期。
[9]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10]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1996年12月16日电,《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第1版。
[11]参见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当代电影》,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