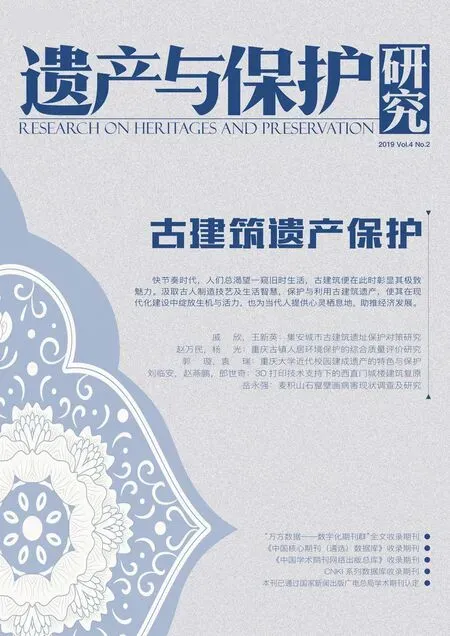绮春园历史沿革及布局特征初探
2019-03-12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北京 100044)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原是康熙帝赐予第四子胤禛的宅邸。后来,胤禛继位,改年号为雍正,圆明园便成为皇帝避喧听政的主要场所,此后历代皇帝陆续进行改建、扩建、添建。现如今,大众所熟知的圆明园仅为整座园林的一部分,其全貌应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又称为“圆明三园”。绮春园和其他二园一起,经历了多次营建,直至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其主体工程基本完成,至此“圆明三园”的规模达到最大。
1 绮春园简述
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的形态大致呈倒“品”字形,总面积约为350 hm2[1]。其中,绮春园位于圆明园的东南侧,是由若干个小型园林组合而成,占地约53.7 hm2,是清朝末年皇家最主要的居住游玩之处(图1)。
根据《清史稿、职官志》的记载,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增设绮春园总领一人,这是“绮春园”之名始见于史籍。再根据《雷氏旨意档》的记载,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改换三园八处殿宇名称,第一项即改绮春园为万春园[2]。其实, 万春园这个名称是同治皇帝重修绮春园时更改的,但最终因国库拮据,重修工程并未完成,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万春园并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仍称之为绮春园更为合适[3]。这便是绮春、万春名称变更的来源。
2 绮春园的历史沿革
2.1 清康熙年间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康熙帝在京西启建畅春园,开始了西郊皇家园林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时期,绮春园的前身——萼辉园——开始修建。萼辉园是康熙帝赐予裕亲王福全的宅邸,所谓“萼辉”,有“花复萼、萼承花、花萼相辉”之意,象征兄弟之间的亲密情谊。关于萼辉园的详细修建时间,并未见有史料记载,但有学者根据康熙所作《萼辉园记》推测,其始建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
关于萼辉园的位置,《萼辉园记》中写道,“东北御果园旧地,以赐裕亲王。”由此可见,萼辉园在畅春园的东北方向,其具体位置大致在御园北侧的索戚畹园(即后来的澄怀园)以东,淑春园以北、熙春园以西,也就是绮春园(全盛规模时期)的西南部[4],这个区域大致为今天一○一中学所在地。
2.2 清雍正年间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和硕裕亲王保泰(裕宪亲王福全第三子)被夺爵、锁禁,其赐园被朝廷收回。次年,皇帝赐予怡贤亲王胤祥(即允祥)交辉园,虽它与萼辉园名称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位于畅春园东北、索戚畹园以东,且园名均保留了“辉”字。同时,《御制绮春园记》中还记载,“斯园先名交辉园,为怡贤亲王赐邸。”由此可以确定,萼辉园是绮春园的前身。
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胤祥逝世,其第七子弘晓袭封和硕怡僖亲王,成为园子的新主人。直到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弘晓一家迁出交辉园。
2.3 清乾隆年间
根据《御制绮春园记》记载,“斯园……又改赐傅恒及福隆安,呈进后,蒙皇考定名绮春”。即在弘晓迁出的第二年,富察.傅恒便搬进此园,并更名为春和园。在《养吉斋丛录卷之十八》中也有记载,“绮春园在圆明园东,有复道相属。旧为大学士傅恒及其子大学士福康安(笔者注:此处与《御制绮春园记》所记不同)赐园,殁后缴进。嘉庆间始加缮葺”[4]。
在绮春园的南侧,曾建有淑春园(即春熙院),包括朗润园、鸣鹤园、镜春园等部分。和硕醇亲王奕譞曾作诗《鸣鹤园》(收录于《九思堂诗稿》中),并有诗注,“是园初为傅文忠公邸宅”。由此说明,傅恒后来又迁出绮春园,搬入南边的鸣鹤园[5]。这与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春和园被收归圆明园统一管理,并更名为绮春园相吻合。
此后,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成哲亲王永瑆搬入春和园,并将此处更名为西爽村,在现今绮春园的西侧。
2.4 清嘉庆年间
继康、雍、乾三世的连续营建,清嘉庆帝也希望能像先皇那样,继续扩建圆明园。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曾消耗盐政中的10万两白银用于绮春园的扩建工程[6]。在这一阶段,绮春园格局的变化主要包括: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西爽村并入绮春园;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于西爽村内开辟含晖园,并赐予庄敬和硕公主,直到公主逝世,将此园缴回,并改称“南园”(即绮春园西南隅部分),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才被取消。
在春和园收归圆明园管理的第二年,即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绮春园添建宫门和朝房,并开始整修公主寝宫。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绮春园西南部的正觉寺落成。在清乾隆年间,除了这两处建筑外,几乎没有其他大型建设活动,只有一些小型亭台楼阁点缀其中。
清嘉庆帝自登基伊始,便着手修建绮春园。直至清嘉庆十年,建成“绮春园三十景”,即敷春堂、鉴德书屋、翠合轩、凌虚阁、协性斋、澄光榭、问月楼、我见室、蔚藻堂、蔼芳圃、镜绿亭、淙玉轩、舒卉轩、竹林院、夕霏榭、清夏斋、镜虹馆、喜雨山房、含光楼、涵秋馆、华滋庭、苔香室、虚明镜、含淳堂、春泽斋、水心榭、四宜书屋、茗柯精舍、来薰室、般若观。后来,又陆续建成了20多景。很明显,嘉庆年间的绮春园规模,与乾隆年间相比,已有很大改变[7](表1、图2)。

表1 绮春园格局的变化历程
2.5 清嘉庆之后
自清嘉庆起,清朝国力逐渐衰退,仅是圆明园的日常运转对清政府来说已是沉重的负担,更难于持续建设。所以,在道光年间,对年久失修又无力维护的建筑进行了拆除。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大火焚烧了圆明园[8]。到了清同治年间,皇帝借“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为由,计划重修圆明园,但最终因国库资金不足而终止。直到1900年及以后,圆明园历经多次掠夺和摧毁,最终变成了一片废墟,连同绮春园在内的圆明三园无一幸免。
3 绮春园的布局特征
3.1 园景的整体格局
绮春园由若干个不同时期的园子合并而成,且形状不规则,所以园林总体较为松散,各个小园子形成组群,相互之间或以围墙相隔,或散布于水边山间。然而,经过多年的添建修葺,独特的山水格局又巧妙地将全园组合成一个整体,并在局部环境处理和景观塑造上呈现出独到之处[9](图3)。
正觉寺北部有一组岛屿,没有进行专门的建筑空间营造,而是用环绕式的土山形成一个自然空间。从整体格局来看,该岛屿位于中心位置,它不仅起到了分隔景区、水面的作用,而且从竖向空间上来看,当人站在土山上时,可以俯视整个绮春园的景致,这种利用自然地形或通过人工手段而形成高低变换的景象,是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常用的手法。那么,从南北向的空间序列来看,土山的设置运用了一种欲显而隐的造园手法,即从正觉寺进入绮春园内部,并非直接的、开门见山式的,而是用山把景遮挡起来,营造出曲径通幽的感觉。
3.2 绮春园的四序景观
与圆明园和长春园相较,绮春园内最能凸显其造园意境之处的便是春、夏、秋、冬的四季时序景观,即:敷春堂、清夏斋、涵秋馆和生冬室。这4处景观内的建筑占据了御制《绮春园三十景》诗目的大部分,并且清嘉庆帝在《御制绮春园记》中运用了大量篇幅表达“春、夏、秋、冬”所蕴含的意义,足以显示景观的重要性和价值。
(1)春景为敷春堂。作为皇家在绮春园中最主要的寝宫区,不仅建筑规模庞大,而且其周围的山水空间十分丰富。敷春堂北侧和西侧均为开敞的湖面,但是建筑群的东侧却是山峦叠嶂、水岸曲折,这与北侧和西侧的广阔空间形成了对比,整体空间富有韵律感和层次感。
(2)夏景为清夏斋。原是西爽村内的一处建筑,后经过改建,更名为清夏斋。清夏斋的建筑空间并不讲求中轴对称的呆板格局,而且将建筑、亭、廊、室外滨水场地、湖、山等要素结合在一起,既有室外游乐空间,又有室内起居空间[10],同时院内还有“修竹数杆,苍松百尺”。这里的整体环境尺度宜人、随性有趣,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3)秋景为涵秋馆。位于绮春园面积最大的两个湖面的交接处,巧妙地将两侧空间联系在一起。同时在涵秋馆东部外侧的山凹处,有仙人承露台,人们无论是从两侧的湖上,还是周围的岸边,都能看到这一突出的景点,并且露水神台寓意承接天降甘露,这一景物的布置完全符合秋天“宰制庶物、涵育众生”的内在含义。
(4)冬景为生冬室。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清乾隆时期,被称为“明善堂”。后陆续进行改建,易名为“含淳堂”,又于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将这组建筑命名为生冬室,并作有题咏。生冬室与北侧、南侧建筑均隔水而立,这种虚实结合的空间序列,将中国古典园林善用山水意境的造园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园林从不以个体建筑取胜,而是侧重整体环境的完美,充分把握景物的相互关系[11]。
4 结束语
绮春园作为圆明三园中规模最小的园子,园中建筑和院落并不像圆明园那样雄伟壮丽,并且后期绮春园的占地情况严重,使得大众对于绮春园的印象并不深刻。然而,该园作为清朝末年皇家最主要的起居空间,对于圆明三园的整体认知和价值判定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春、夏、秋、冬四季作为造景的内在逻辑,亦是皇家园林中不多见的实例。故而,笔者希望通过对绮春园的历史和景区的解析,不仅可以加强人们对绮春园的认识,还能够完善中国皇家园林造园艺术的相关研究,并对今后“三山五园”的整体保护与科学利用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