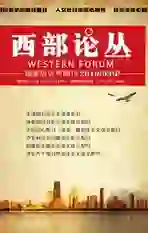浅析奥古斯丁的“两座城”学说
2019-03-08孙一令
孙一令
摘 要:“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有着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两者具有天壤之别,但在现世生活中“两座城”却相互交织、彼此相混,两者的重叠部分组成了 “地上的和平”,对于追求终极信仰的基督徒,尘世的生活仍然有些许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上帝之城 地上之城 地上的和平
一、引言
奥古斯丁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乐园、尘世、天国,分别对应上帝造人、人类堕落、上帝对人类的拯救。在乐园中,人的身体不死,拥有丰厚无忧的物质条件,同时具有伦理选择上的自由,能够认识真理避免作恶,人的生活和谐且美好。但是人类的始祖滥用自由而犯罪,于是人类遭到了上帝的惩罚,被逐出乐园,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将面临死亡,从此人类世界进入尘世,尘世中人们的生活是悲惨的,不断地遭受罪与罚。始祖将他的罪遗传给了后代,所以人生来有罪,这是原罪,如果人到达一定年龄后继续犯罪,则是本罪。所有的人都有罪,因此所有人都将面临上帝的惩罚。然而上帝是仁慈的,他会在末世审判的时候从人类中拣选一部分人进入天国从而得救,天国是一个“新天新地”,这里的人们享受着永恒的幸福和真正的自由,天国中没有罪,人也没有犯罪的可能与倾向,人们得到灵性的身体,不朽不死。这些被拣选的人就构成了“上帝之城”,而被抛弃的人则组成了“地上之城”,这个理论因此被称为“双城论”。
二、“两座城”理论
(一)两座城的背景
奥古斯丁将上帝最初造物时世界的状态定义为“自然本性”,上帝创造世界时只有善,因此这种自然本性在根本上是善的,而恶只能起源于始祖堕落之后。因为如果恶的自然本性是存在的,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帝创造了恶,这就违背了上帝至善的信仰;另一种是上帝之外其他的神创造了恶,这又会违背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万物的信仰。因此,世界上的恶不源于善的自然本性,而是源于理性的造物(天使和人),理性造物凭借自由意志犯罪,将恶带进了本不存在恶的世界。
两座城的开端,在于天使作出的自由选择:善的天使选择依靠上帝,恶的天使选择背弃上帝,两座城的区别由此产生。类似于天使,人类的自由选择使两座城在人类中产生区分。“上帝之城”以基督为王,“地上之城”以魔鬼为首领,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上帝之城”的公民因信称义,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达到上帝之城,一旦信仰丧失,便无法企及。奥古斯丁认为,“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不能等同于现实世界中任何国家或组织,即使是教会也不能等同于“上帝之城”,原因有几点:首先,“上帝之城”除了包含善的人类之外还包含善的天使;其次,在人类世界产生教会之前,地上就已经有“上帝之城”中的公民了;再次,并非所有在教会中的人都会得救;最后,有些不在教会中的人最终也会被上帝挑选进入天国。
两座城可以用特定的国家或组织代表,圣城耶路撒冷代表着地上的“上帝之城”,而罗马则是“地下之城”在尘世的代表。“基督教会并不等同于‘上帝之城,因为教会内也混杂有灵魂尚未得救的人。世俗国家也并不等同于‘地上之城,因为所有现存的权力都是上帝设置的……不过,根据奥古斯丁的看法,上帝之城至少可以由教会来代表,世人之城可以由异教国家来代表” [1]。
奥古斯丁使用了各种称谓来指代两座城,他把“上帝之城”称作:天上之城、圣洁之城、上方之城、永久之城、自由之城、最荣耀之城、圣人之城、所爱之城。“地上之城”称作:不虔之城、不信者之城、人之城、尘世之城、属世之城、魔鬼之城。[2]同时他还用“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分别象征“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實际上,他借助“两座城”的说法表达了世界上的两类人、两个社会群体。古往今来的所有人类和天使都可以归入这两座城,善的人类和天使属于“上帝之城”,恶的人类和天使属于“地上之城”。上帝之城的人类部分在现实中作客旅,奥古斯丁所谓的客旅不意味着对现世事物的完全放弃,而是强调基督徒不能完全认同现实生活,应该坚定对天国的渴望,明确自己在现世中只是一个外乡人。
(二)两座城的区别与对立
两座城的划分与地理、人种、民族、文化等等因素全无关系,然而这两座城却是截然对立的,并且这种对立是根本的、鲜明的、尖锐的。首先在信仰上,“上帝之城”是虔诚信仰的群体,而“地上之城”则是不信者和异教徒的城,“上帝之城”坚持对上帝的信仰,靠信仰生活,“地上之城”的人们崇拜伪神,不靠信仰生活。其次在成员的产生方式上,“上帝之城”的公民通过重生产生,“地上之城”的成员则通过生育产生,“地上之城”产生于人类堕落后的自然本性,“上帝之城”产生于超越自然本性的上帝的恩典。再次,这两座城公民的最终命运截然不同,“上帝之城”的公民进入天国得到永生,而“地上之城”的公民终会灭亡,并且在末日审判后将进入地狱接受永罚,两者的差别是永久的生命和短暂的欢乐的区别。最后,在现世生活中,“天上之城”的公民拥有和平、秩序与和谐,“人们互相慈爱,统治者用政令爱,在下者用服从爱” [3],“地上之城”为了自我利益而争执斗争,“在地上之城,君主们追求统治万国,就像自己被统治欲统治一样” [4]。在“地上之城”中,充满了自我的、私己的爱,人们骄傲的追求个人的智慧,反而使自己变得愚笨;在“上帝之城”中,人们的爱是共同且长久的,人的智慧除了虔诚笃信便无其他。
“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根本区别就是爱,“上帝之城”公民的爱是对上帝的爱,“地上之城”公民的爱是对自己的爱。“上帝之城”代表着善,这种善是根本的、终极的,“地上之城”也包含着某种善,但这种善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地上之城所追求者并非不善,问题只是它忽略了更高的善。‘地上之城的德性并非真德性,却好过没有德行。” [5]
(三)两座城的交织与重叠
奥古斯丁将人们目前所处的现实世界称为“尘世”阶段,此阶段处于“堕落”和“审判”之间,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阶段。“上帝之城”的成员在尘世客旅,与“地上之城”的成员混杂在一起,直到最后审判时才会分开。而上帝挑选谁进入“上帝之城”之城完全是随机的,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努力而改变。
在尘世中,人们摆脱不了与生俱来的罪,但依然可以保持身上一部分的善。对基督徒来说,尘世生活既意味着惩罚与痛苦,又意味着希望与期待,尘世中虽然充满罪恶,但人类只有借助现世才能达到永恒,也即尘世是通向“上帝之城”的必须经历的阶段。“‘尘世根本上意味着一种两面性:生活中的悲苦与自然本性上的善始终并存,善人与恶人(两座城)也始终并存。” [6]两座城虽然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在尘世生活中,又并非毫不相干、泾渭分明。两者在现实世界中彼此相混,相互交织,只有在最终审判后两者才会彻底分开。
在奥古斯丁看来,和平就是秩序的平稳、是事物的有序状态,和平是最可贵的善,是尘世中最值得追求的善。和平分为两类,“地上之城”的和平与“上帝之城”中永久的终极的和平,这两种和平并非对立排斥的。一切自然本性都以实现和平为目的,基督徒所追求的至善就是天国中永久的和平。“上帝之城”的公民尚在尘世中客旅,要利用许多现世中所必需的事物,“地上之城”的和平对于他们来说是同样需要的,“天上之城,或更确切地说,天上之城的一部分,在这必朽的旅行中,按照信仰生活,也有必要利用这种和平,因为在这必朽的生命结束之前,这种和平也是有必要的” [7]。这种尘世的和平是“上帝之城”的公民与“地上之城”的公民所共同享有的。
虽然两座城的公民都需要利用现世的事物,但两者的目的却十分不同。“在‘地上之城中所有人对现世之物的使用皆归诸对地上和平的享受;在‘天上之城中,归诸对永久和平的享受。” [8]上帝对于“上帝之城”公民的要求是,在利用地上的和平时,要时刻意识自己只是客旅尘世,不能被其引诱迷惑,而是要将天上的和平视为自己的终极追求,虽然地上的和平也是一种善,但相比于天上的和平这种终极的善,地上的和平便全然成了悲。“总之,奥古斯丁肯定现世生活中的善。他所否定的,不是现世之善本身,而是那种将现世之善作为终极目标的态度。他的思路是以‘天上超越‘地上,而不是以前者全盘否定后者。” [9]国家用强制权威和惩罚的手段维持“地上的和平”,基督徒应该服从它,不能躲避或推脱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基督徒也不能忘记国家局限性和其世俗的本质,不能为了尘世中的利益而忽视对信仰和终极价值的追求。
奥古斯丁通过“尘世”与“地上的和平”的概念,为“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重合部分找到了相容的可能性。虽然两座城在终极信仰上截然对立,但在此“尘世”中却无法分辨,两座城的公民同享“地上的和平”,只要不涉及爱和信仰,两座城就能和谐相处。
三、对“双城论”的完善
西塞罗将共和定义为“人民之事”,而人民则是“按照对正义的认同和共同利益集合起来的团体” [10]。奥古斯丁认为如果西塞罗对共和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罗马就从来没有共和,因为共和是人民之事,而人民又是通过对正义的共同认可联合起来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没有正义便没有人民,没有人民也就谈不上共和。那么什么是正义呢?柏拉图和西塞罗对正义的定义是每个人各得其所,这一点奥古斯丁是同意的。但在他看来,自从始祖堕落以后,所有人都被魔鬼统治,因此世上再无正义。使人服从于他人也是不正义的,但是,如果不依靠这种不正义,共和就无法创建和发展,“对于一个庞大的共和国来说,如果帝国之城不采用这种非正义,就不能借助诸省。” [11]政治中必然需要统治与被统治、服从于被服从,奥古斯丁认为这已经不是正义了,但是所有的共和都必须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因此,国家必然是非正义的,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共和。
为了完善“双城论”,奥古斯丁又将人民做了一个新的定义,“人民就是众多理性动物的集合,这些理性动物因为热爱的事情相和谐而组成社会” [12],也就是说,只要是有理性的一群人,共同热爱某一项事物,不论这个事物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他们就组成了人民。不管热爱的事物是好还是坏,只要人们达成共识就可以。按照這个定义,虽然世俗国家中没有正义,但人民依旧可以称为人民,由人民组成的国家依旧可以称为共和。
奥古斯丁对共和与人民的定义是精心设计的,目的是为“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重叠,也即“地上的和平”留出空间。“地上和平是所有人都关心的,不论是天上之城的,还是地上之城的公民;双方都看重它、热爱它。”共和中的人民不需要在最高价值上达成一致,也不需要具备相同的终极信仰,他们只需要拥有“地上的和平”这一种共同价值。“组成世俗之城的人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终极追求,有各种各样的价值体系,这些都可以非常不同;但是,地上和平对他们都很重要,虽然他们未必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来理解地上和平” [13]。世俗国家负责提供“地上的和平”,保护所有公民不遭受侵犯,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并且不干涉公民的信仰,这样的世俗国家颇有现代政教分离国家的彩。
注 释
[1]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66页。
[2] 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8-89页。
[3]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6页。
[4]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6页。
[5] 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5-96页。
[6] 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1页
[7]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3页。
[8] 夏洞奇:《“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奥古斯丁思想中的两分倾向》,载《现代哲学》2005年第03期。
[9] 夏洞奇:《“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奥古斯丁思想中的两分倾向》,载《现代哲学》2005年第03期。
[10]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2页。
[11]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6-157页。
[12]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第164页。
[13] 吴飞:《奥古斯丁与尘世政治的价值》,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