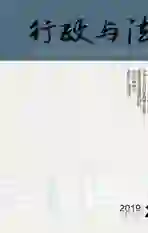彩礼返还行为刍议
2019-03-06郭英华杜琼
郭英华 杜琼
摘 要:在我国,给付彩礼作为一种风俗习惯根植于传统和地域文化之中,不宜用法律的方式予以禁止,只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司法裁判规范其行为。本文分析了彩礼的法律性质,将彩礼赠与目的进行了扩大解释,并试图在彩礼返还请求权的基础上论证彩礼返还的正当性,以期对合理解决彩礼纠纷有所助益。
关 键 词:请求权;彩礼返还;目的性赠与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9)02-0115-09
收稿日期:2018-11-28
作者简介:郭英华(1965—),女,江苏南京人,河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法、合同法;杜琼(1992—),女,江苏镇江人,河海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法、合同法。
一、问题的提出
彩礼是古人订婚仪式的一种制度设计,其作为传统婚姻习俗既丰富了传统的礼仪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婚姻的长久性。[1]目前,彩礼在我国民间仍广泛存在,实务中因彩礼引发的财产纠纷甚至刑事纠纷亦是司法机关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难题,因其不仅关乎财产问题,更关乎双方的名声与“尊严”。
2004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①以及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提及的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②是现有彩礼返还的裁判依据。当前,对于彩礼造成的婚约财产纠纷虽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处理模式,但在审判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困境。笔者以2017年江苏地区法院系统的132个婚约财产纠纷为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的裁判困境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虽然对彩礼的返还数额提出了考量因素,但并没有对各种考量因素做出具体衡量标准,由此导致司法实务中裁判标准大相径庭。其二,司法实务中出现了主体为未办理结婚登记且未共同生活的男女双方在婚约取消后主张返还彩礼的情形,而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对其做出相应规范。在该种情形下,法官基本类推适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尚待考究。因此,有必要以明确彩礼的性质为出发点,探寻彩礼返还的请求权基础,为彩礼返还寻求一个合理有效的裁判思路。
二、彩礼返还的请求权基础
传统意义上的彩礼既是一种婚姻礼仪制度,也是一种礼节和结婚的必经程序。如今的彩礼却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彩礼制度的回归和复制,而是作为一种民事法律之债的形貌出现,[2]给付与收受彩礼的双方实际上赋予了该行为一定的民事法律意义,期许其发生某种法律效果并受法律保护。结合王泽鉴提出的“请求权基础体系”的次序检查方法,[3]彩礼返还的债权请求权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合同之债的返还请求权和缔约过失返还请求权。
(一)合同之债的返还请求权
探寻彩礼返还的请求权基础首先应明确彩礼的法律性质。学界对于彩礼性质的认定主要有定金担保说、一般赠与说、附义务的赠与说、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说和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对于“定金担保说”,根据定金罚,如果接受彩礼的女方悔婚,女方需要双倍返还彩礼,这与实务中女方将彩礼最多只是悉数返还不符。此外,若将彩礼作为定金担保合同,“婚约”便是其主合同,这与婚约具有人身属性不能作为合同标的相悖。 对于“一般赠与说”,则忽视了彩礼赠与的目的和意义,将彩礼与婚前的一般赠与相混同。对于“附义务的赠与说”,根据附义务赠与的理论,当女方接受彩礼却不履行婚姻登记的义务时,男方有权要求女方继续履行办理结婚登记的义务。这种观点有欠妥当,因为在女方不履行所附义务且明确表示不愿同男方结婚的情形下继续要求其履行义务,具有强迫性质,违背了婚姻自由和公序良俗,而且结婚在法律上的性质并不属于给付行为。对于“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说”,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如果女方为了自己的不正当利益,未在约定的日期办理结婚登记,并且一再拖延,这种情况下并不能依据此款视为条件已成就,首先是因为违背婚姻自由,而且婚姻关系必须经过登记,其次是因为结婚具有身份属性,不能适用此款。以上对于彩礼性质认定的各种观点均有不足之处,相比之下,被普遍认可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与我国现行法律以是否登记为分界点的规定是一致的。该观点将彩礼定义为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就(即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赠与物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即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但该观点不仅容易造成“一刀切”的裁判现象,还忽视了现代社会背景下彩礼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无法涵盖实务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如无法诠释“已登记的男女双方确为共同生活的可以主张返还彩礼”,只能将其作为例外规定而已。因此,笔者认为,将彩礼的性质定义为目的性赠与更加合适。给付彩礼与收受彩礼的双方之间存在目的性赠与合同,男方当事人可以在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落空时,主张撤销目的性赠与,要求彩礼返还请求权。目的性赠与是赠与人在赠与行为中含有明确的目的性约定,是赠与人要达到一定目的或帮助受赠人达到某一具体目的或要求受赠人将所赠与财产用于特定用途,当目的不能实现时,可以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解除合同,并要求受赠人返还财产。[4] 然而,对有彩礼习俗的地区而言,给付彩礼是缔结婚姻的一种礼仪和程序,对双方均有道德约束力,具有担保缔结婚姻的作用,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5]在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彩礼的功能也被重新调整。彩礼不仅仅是两个家庭之间的财产移转,更多的是家庭内部之间的财富传承。当前,越来越多的新婚夫妻将彩礼用来经营共同生活,彩礼对具有婚约的男女双方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小家庭的建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6]这一定性也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相呼应。立法者以是否办理结婚登记作为是否返还彩礼的标准,认为给付彩礼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受到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彩礼范围认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彩礼数额或物品的举证证明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證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法院只认可当事人能够证明的给付的彩礼数额。二是交往过程中财物的属性问题。主流观点认为,彩礼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民间彩礼习俗,婚前由一方给付另一方价值较大的金钱和物品,而双方在交往过程中互赠礼物表情达意、节假日的礼尚往来及双方因缔结婚约产生的正常礼尚往来只是一般赠与。少数观点则认为,只要是以缔结婚约为目的,按照民间彩礼风俗所给付的财物就是彩礼。笔者认为,将彩礼的性质定义为目的性赠与可以明确彩礼的范围。根据彩礼是目的性赠与的性质,依据当地习俗和双方家庭的协商,为缔结婚姻这个目的特意赠送的财物就是彩礼,无论财物的价值如何。如恋爱期间为维系和发展情感的支出、亲戚朋友送的财物以及为缔结婚约产生的正常礼尚往来等都不属于彩礼。因此,彩礼的性质宜定性为实现双方日后能够缔结婚姻关系所订立的目的性赠与合同。
(二)缔约过失的返还请求权
缔约过失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有的义务,使另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7]作为缔约过失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在缔约阶段一方当事人有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缔约过失责任,采过错责任原则。当婚约取消时,以缔约过失主张返还彩礼是将该“缔约过失”中的“约”误解成了“缔结婚姻”,认为因对方存在过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导致未能缔结婚姻,故而提出缔约过失责任。实际上,彩礼作为目的性赠与是一个独立并完整的阶段,在给付与收受彩礼之时就是在履行该赠与合同,而不是处于双方为缔结婚姻进行的接触磋商阶段。同时,给付彩礼也不是缔结婚姻的附随义务或者先合同义务,缔结婚姻只是该目的性赠与的目的而已,并且该目的的达成并不具备强制性、义务性。因此,当双方取消婚约时,给付彩礼的一方有权依据目的性赠与合同主张债权请求权,要求对方返还彩礼。
三、彩礼返还情形的检视
(一)彩礼返还的判断依据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将婚姻登记作为是否需要返还彩礼的首要判断标准,将已经办理婚姻登记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的情形作为例外。这一规定提供了尚且比较清晰的彩礼返还裁判思路,主要考量因素为男女双方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但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所提及的关于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的彩礼返还规定却改变了之前以是否办理婚姻登记为判断标准的情况。通过考察2017年江苏地区法院系统的132个婚约财产纠纷可以发现,现有的裁判结果较混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有效的裁判标准。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审判实践中涉及彩礼返还纠纷的男女双方以未办理结婚登记为由的占绝大多数,占据样本案例的87%。对于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在离婚时提出返还彩礼的纠纷,通过《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可以解决是否需要返还的问题,但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形还要再细分是否曾共同生活。同时,《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通知》为未办理婚姻登记但共同生活的情形下彩礼的返还数额提供了考量因素,而实务中大部分法官也类比运用这一思维去评估未办理结婚登记且未共同生活的男女双方的彩礼返还数额。如样本中涉及双方未办理登记手续且未共同生活的案例有30个,其中77%参考共同生活的情形下彩礼的返还数额的考量因素判决酌情部分返还,23%因不存在共同生活,直接判决全部返还。
尽管现有的裁判依据在实务中较为混乱,但并不妨碍从中抽象出立法者的意图,从而重新梳理出判断彩礼返还的标准。从2004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到2011年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实际上是将给付彩礼的目的——缔结婚姻,做出了更加迎合时代发展与家庭发展的扩大解释。所谓“缔结婚姻”并不仅仅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这一简单的形式流程,而是注重其背后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性生活等,夫妻之间权利义务的行使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仅以是否办理婚姻登记作为衡量标准过于简单且有失公正。因此,判断彩礼赠与目的是否达到,除了形式要件之外,更应关注的是实质要件。该实质要件就是指“共同生活”。正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所规定的,如果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却未共同生活则应当返还彩礼,如果在给付彩礼后没有登记结婚,未必就一定要返还彩礼,还要对其是否具备实质要件进行考察。
(二)“共同生活”的界定
司法实务中存在三种判断“共同生活”的做法:一是以长时间同居为判断标准;二是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共同居住为判断标准;三是以形成长时间履行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判断标准。前两种判断标准是形式标准,如果双方当事人存在长时间居住在一起生活或者以夫妻名义持续共同生活的形式则认定为共同生活。第三种判断标准是实质标准,从配偶间的权利义务角度出发,如果双方形成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则认定共同生活。笔者认为,应当从实质角度做出判断,包括但不限于履行夫妻关系的权利义务。基于《婚姻法》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传统伦理观念,夫妻“共同生活”应是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持续稳定的家庭共同体,不仅客观上存在家庭义务和互相扶养的义务,在精神上也要有长期共同生活的愿望,并基于配偶生活能够互相理解和慰藉。[8]因此,居住在一起的时间长短和是否发生性关系并不是判断是否共同生活的主要因素。如在陈某与陆某婚约财产纠纷①一案中,陆某多次借口拖延结婚且两人异地生活,尽管二人居住在一起一段时间且距离结婚仪式也经过了两年,但也不构成共同生活,法院根據双方同居一段时间这一情节判决酌情返还实有不妥。
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的双方,赠与目的的达成与否与共同生活的时间有关,如共同生活超过两年则视为附目的性赠与目的达成。根据社会学者的调查,目前的彩礼逐渐成为新婚夫妻追求独立生活的表现,父母不再对彩礼独享支配权。彩礼一般用于经营新婚夫妻的共同生活,彩礼从两个家庭之间的转移逐渐变成父辈到子辈之间的代际转移。之所以设定为“两年”,是因为笔者通过查阅大量彩礼纠纷案件发现含“未婚同居”因素的案件中同居时间少于一年的占了绝大多数,且同居时间越久,彩礼返还的数额越少。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这里的“分居”是由感情不和引起的夫妻间不再共同生活,不再互相履行夫妻义务,包括经济上不再合作,生活上不再互相关心、互相扶助,停止两性生活等。具有分居两年的情形,说明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9]反之,如果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了两年以上,至少说明双方具有符合婚姻生活内容的外观,包括共同的物质生活和两性生活。尽管目前我国已经不承认事实婚姻了,但依照《婚姻法》第八条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依此,建议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举行了结婚仪式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两年以上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尽早补办结婚登记,以使自己的婚姻行为合法化。[10]通过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彩礼纠纷亦能看出,在给付彩礼后一方或双方并不积极实现赠与目的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其中自相矛盾的是双方又通过同居行为进行信号传递,传达出愿意同对方一起生活的信息。以“两年”为时间段,目的在于督促一方将双方的“同居关系”转变为“夫妻关系”,同时又能减少一方为骗取彩礼拖延不婚的情况。 所以,当双方共同生活不足两年且未办理结婚登记时,彩礼给付者可以主张返还彩礼。因为该目的性赠与的目的并未达成,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
四、彩礼返还行为的法治思考
(一)彩礼返还情形的重构
通过检视现有彩礼返还的裁判依据和裁判实务,笔者建议对彩礼返还情形的规定应摒弃以“是否办理婚姻登记”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衡量给付彩礼目的达成的标准是其实质要件——共同经营婚姻家庭生活,因此,需要将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结合判断。以“共同生活”为实质要件,辅以“结婚登记”的形式要件,将彩礼返还情形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情形是双方共同生活不足两年且未办理结婚登记,彩礼给付者可以主张返还彩礼。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该目的性赠与的目的并未达成,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另一种情形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之后确未共同生活,彩礼给付者可以主张返还彩礼。我国著名法学家史尚宽概括“婚姻”有两大本质要素:一是男女两性结合,这是婚姻形成的自然要素;二是共同生活,包括精神的生活共同(互相亲爱,精神的结合)、性的生活共同(肉体的结合)和经济的生活共同(家计共有)。[11]值得注意的是,不符合共同生活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就是“确未共同生活”,“确未共同生活”需因客观上所造成的不能而导致。如果办理结婚登记之后双方确未共同生活是因为客观上所造成的不能,而非主观上故意不愿共同生活,给付彩礼的一方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彩礼。一方面,从“缔结婚姻”的广义上考量,双方建立婚姻关系是为了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的共同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基于公平原则,由于客观上的不能导致双方并未共同生活,如果不予返还彩礼则会造成对一方的不公平,也与社会习俗相背离。
此外,建议废除《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中婚前给付导致生活困难应返还彩礼的情形。一方面,彩礼是目的性赠与,是否需要返还彩礼仅仅取决于其目的是否达成;另一方面,尽管这一规定是出于对因婚前给付彩礼而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考量,但是其适用存在困境。如在蒋某与孟某离婚纠纷①一案与徐某与张某离婚纠纷②一案中,同样主张婚前给付导致生活困难,但是前者法院判决返还50%,后者法院判决不予返还彩礼。这样的结果表面上是两个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和举证责任问题,实质上是因为在彩礼纠纷中“婚前给付导致生活困难”尚未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主张生活困难所提出的证据基本均为证人证言、向外举债的欠条或为基层自治组织提供的证明。在各判决书中都未体现出群众自治组织所出具的“生活困难”的证明究竟是以何作为衡量标准,而且“生活困难”的证明应由群众自治组织还是民政局出具尚存在争议,“生活困难”只是被笼统的运用到了实践中。故“生活困难”不能成为离婚后不予返还彩礼的例外。“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是以离婚为前提,既然给付彩礼之后双方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那么彩礼担保婚姻实现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债权而言,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因此再要一方退还彩礼是不合理的。对于生活困难的情况,可以通过《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解决③。
(二)彩礼返还数额的确定
司法实务中彩礼返还的数额值得反思,通过对以下案例进行比较以窥司法实务中关于确定彩礼返还数额的具体操作情况:⑴在郑某与张某婚约财产纠纷④一案中,双方共同生活6天,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和张某为筹备婚礼的合理支出,酌定张某返还郑某220000元,返还率约占84%。⑵在殷某与黎某婚约财产纠纷⑤一案中,双方共同生活1年有余,“根据本案实际,酌情认定黎某应向殷某返还彩礼140000元”,返还率约占80%。⑶在陶某与李某婚约财产纠纷⑥一案中,双方共同生活一个月,法院判决酌定返还彩礼款的70%。⑷在刘某与许某婚约财产纠纷⑦一案中,双方共同生活一个月,法院认为,综合考虑当地习俗、许某接受彩礼的数额、双方未办结婚登记的原因、许某为结婚支出的有关费用及黄金价格差等因素,对许某应当返还的彩礼酌情确定为59000元,返还率约占55%。⑸在智某与仲某婚约财产纠纷⑧一案中,双方共同生活一年有余,法院认为,结合当地习俗及二人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过错程度,考虑到举行婚礼时双方均有花费的具体情况,酌情确认仲某返还彩礼款的40%。⑹陶某与曹某婚约财产纠纷①一案中,双方共同生活两年有余,法院认定彩礼数额为20000元,判决曹某返还陶某18000元,返还率达90%,在判决书中未说明理由。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⑴⑵两个案例中,彩礼的返还比例相近,但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却相差较大;在⑶和⑷、⑵和⑸两组案例中,每组共同生活时间相似,但彩礼的返还比例也有差距;而⑹中双方共同生活时间长达两年有余,是以上六个案例中共同生活时间最久却也是彩礼返还比例最高的。通过法官的判决理由可以发现,造成這些差异的实质原因是缺乏请求权基础,导致具体的返还规则的缺位,仅靠自由裁量权决定返还数额且法官对于彩礼返还考量因素的判断标准各异。彩礼的返还数额应当在其建立的请求权基础之上,依据相应的返还规则确定数额。
(三)基于目的性赠与之撤销的彩礼返还数额
彩礼作为附目的性赠与,是给付彩礼与收受彩礼的双方之间成立的目的性赠与合同关系。通常情况下的赠与合同是一种单务、无偿合同,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但也有例外情形,如《合同法》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此外,学理上存在“目的性赠与”这一概念,指赠与人是基于特定目的而为的赠与,并非课受赠予人义务。大陆法系通常认为,附义务赠与和目的性赠与均为赠与的不同类型属一般赠与的例外情形,且不具有无偿性。当男方给付彩礼时,其所期望的是日后能够和女方缔结婚姻组成家庭、共同生活的精神利益,而不是完全无偿的单方赠与。因此,当目的不能达成时,给付彩礼的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受领给付的一方应当返还财产。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也会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共同生活开支费用折抵、女方堕胎流产、过错等因素判决酌情返还彩礼。笔者认为,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保护弱势一方的利益,但除了能够减少诉累之外,从法理的角度来说并不合理。彩礼纠纷是以彩礼为标的物,双方形成目的性赠与的债权法律关系。被告无论是主张原告返还部分共同生活开支,还是赔偿或补偿因堕胎流产造成的健康权损害亦或因男方家暴造成的侵权损害赔偿等,既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也与本诉不具有牵连性不能构成反诉,因此不能一并处理,对于被告的这些主张可以通过另行起诉予以救济。彩礼是以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的目的性赠与,“缔结婚姻”的目的只有达成和未达成之分,并不存在部分达成,故对于财产的返还数额也无需考量目标达成进度。如果目的落空则可解除合同,应当将彩礼全部返还;反之,不用返还彩礼。
總之,作为民间习俗的“彩礼”要“取其精华”,给付有度。作为民事法律之债的“彩礼”则要合乎法度,也要合乎情理。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彩礼的认识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当明确彩礼的法律性质为目的性赠与,给付彩礼与收受彩礼的双方之间所形成目的性赠与合同就是彩礼返还的请求权基础。检视彩礼返还的判断标准,对彩礼赠与目的做出扩大释义,重构彩礼返还的情形,以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只有在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的同时,与时俱进,迎合时代对彩礼发展的需要,才能够为解决彩礼纠纷提供一个合理的裁判思路。
【参考文献】
[1]李霞.民间习俗中的彩礼及其流变[J].民俗研究,2018,(03).
[2]李拥军.当代中国法律对亲属的调整:文本与实践的背反及统合[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04).
[3]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江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5]黄振威.嫁资视野下的中国彩礼制度[J].法制与社会,2017,(04).
[6]陈年风.民间习俗中的彩礼及其流变[J].民俗研究,2018,(03).
[7]崔建远.合同法[M].中国法律出版社,2007.
[8]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乔巴生.如何界定夫妻“共同生活”[EB/OL].新疆法院网,http://www.xj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0364.
[9]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第三十二条[EB/OL].法律快车,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34886.html.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第八条[EB/OL].找法网,http://china.findlaw.cn/info/hy/hunyinfagui/hyfsy/111746.html.
[11]史尚宽.亲属法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苗政军)
Absrtact:In our country,as a custom and custom,lottery gift is rooted in traditional and regional culture.It should not be prohibited by law,but can only regulate its behavior through judicial judgmen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This paper analyses the legal nature of lottery gifts,expan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urpose of lottery gifts,and tries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lottery gifts return on the basis of the claim of lottery gifts return,with a view to helping to solve the disputes of lottery gifts reasonably.
Key words:right of claim;lottery gifts return;purposive g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