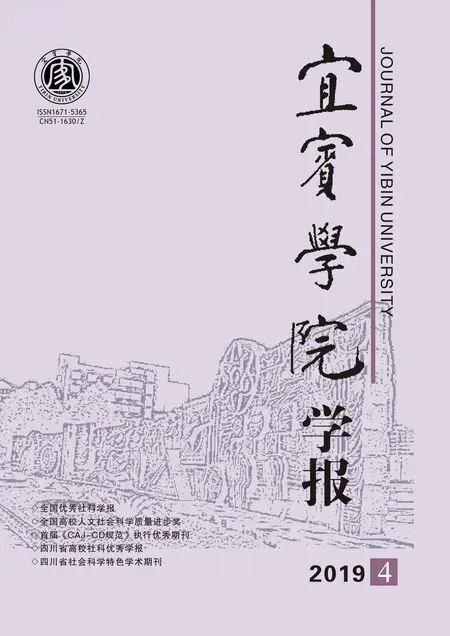媒介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旅游演艺
——基于演艺产品质量视角
2019-03-05李茂华
李 姝,李茂华
(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自2000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文化需求增强,文化与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的消费日常。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批准设立。从新一轮的国家机构改革举措中,不难读解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积极信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18年10月发布的《2017-2018中国旅游演艺发展研究报告》中界定了“旅游演艺是以游客为主要观众,综合运用歌舞、戏剧、杂技和曲艺等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娱乐性、商业性、体验性、区域性、季节性等特点的文化产品,包括驻场演出、实景演出、主题公园演出等类型”[1]。报告同时指出,旅游演艺行业的消费人群在过去一年增长了27%,票房增幅达20%,达到了51亿元,比中国电影的票房增长的还要快速。诚然,“旅游是一种现代社会高度工业化、都市化的产物”[2]296。旅游演艺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行走的景观”和“凝视的狂欢”。如同美术史家休斯(Robert Hughes)所说:“我们与祖辈不同, 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世界里……‘自然’已经被拥塞的文化取代了,这里指城市及大众宣传工具的拥塞。”[3]289随着大众媒介的兴起,信息爆炸与视觉消费过剩催生了新的人造景观与注意力经济。
纵观旅游演艺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深圳的“锦绣中华”民俗村到90年代的“世界之窗”主题公园,从上海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表演、西安唐乐宫的“仿唐乐舞”到丽江的“纳西古乐”,旅游演艺的概念其实早已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迈入新世纪,央视的品牌节目之中秋晚会开创了“中华情”——全息山水景观晚会的先河,并带动了二三线城市的旅游文化产业蓬勃发展。随后“印象”“山水”“千古情”系列大型实景旅游演出、地方特色以及富有科技感的剧场旅游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旅游演出、红色旅游演出等遍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300多个旅游演出项目,但其中80%处于亏损状态,盈利的是少数[4]。源自管理学的“二八定律”在文化旅游演出市场同样适用。如何打破单一的“门票经济”?打破受众对文化旅游演出认可度不高的尴尬局面?如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顺应社会需求和时代潮流,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不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获准设立。2019年1月,在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中提出,推动传统技艺、表演艺术等门类非遗项目进重点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推进红色旅游、旅游演艺、文化遗产旅游、主题公园、文化主题酒店等已有融合发展业态提质升级。[5]一系列积极的政策信号表明,当下中国旅游演出发展势头喜人,但其演出模式、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等久未更新,正面临着严肃的挑战。旅游演艺的蓬勃发展,为旅游本身这种行走中的个人体验带来了更加广泛的空间,其中最为突出的表征便是以主题公园和影视城为代表的虚拟景观的创造发明,以及流动的游客所带来的集体凝视的狂欢。作为复杂社会活动的旅游演艺在消费市场、文化审美等多重需求下也逐渐体现出了泛艺术化的跨界倾向。
一、行走的景观:心灵体验与身体解放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的人们依然信奉“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今天,国人的旅游需求和消费逐年递增。毋庸置疑,旅游已不再被认为是奢侈品或者不必要的产品,人们对“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呼声已经被视为一种新的权利和生活方式。事实上,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毕业旅行或出国留学的学生,选择旅行结婚或度蜜月的新娘和新郎,调休年假只为海岛相聚的三五好友,背包徒步活出人生第二春的退休人士……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在路上”已经成为他们人生的常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于1990年首次出版的开创性专著《游客凝视》(或译《观光客》)(TheTouristGaze)中提道:“游客的目光集中在景观和城市景观的特征上,这些特征将他们与日常体验区分开来。”[6]他的“目的地形象感知”“游客体验”等旅游凝视理论在全球化融媒时代的今天,对于读解旅游业以及文化旅游演出依然有着指导意义。现代大众媒介包裹下的“文化工业”催生了“景观社会”(Society of spectacle),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批判的文化工业对人的异化,塑造伪个性主义,到居伊·德波(Guy Debord)批判的现代生产带来无所不在的庞大奇观堆聚,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渴望与欲望在奇观乱相中得以“使用与满足”[7]。不得不承认,旅游演出正以它越发活跃的姿态填补着人们对庸常生活的不满足。
2001年,山东曲阜的大型广场乐舞《杏坛圣梦》首演,取得了社会美誉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该剧磅礴大气、场面恢宏,以史诗般的歌舞演绎《论语》经典,不仅活用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传播了华夏文明,更对“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大众旅游方式进行了革新与提升。该剧被喻为“开创了长江以北大型广场式主题旅游文化演艺的先河”。
2002年,云南丽江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丽水金沙》用“序—水—山—情”的叙述线,将滇西高原的秀美山水和神秘的东巴文化以舞蹈、诗画、服饰表演的方式,为游客们揭开了古朴纳西王国多民族聚居和多彩民俗生活画卷。纳西族的“棒棒会”、傈僳族的“赶猪调”、藏族的“织氆氇”、摩梭族的走婚……应有尽有,该剧曾被外籍人士称赞为“中国的百老汇”,可见其艺术形式和文化创新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
2003年,《云南映像》紧随其后,这是由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担任艺术总监的国内首部大型原生态歌舞演出,也是云南作为旅游大省和歌舞之乡向世人输出的民族民间文化经典。据称,该演出70%的表演者均系土生土长的云南少数民族演员。对自然伟力的赞颂和对生命图腾的崇拜汇聚成对舞蹈的热爱。非专业的舞蹈者充满了来自乡间田野原始歌咏和生命的勃发能量。灵动的肢体语言、生动的方言演唱、多彩的道具服装、富有科技感的舞美……传统与现代实现了整合与重构,杨丽萍领衔的“月光”“女儿国”“火祭”“雀之灵”等段落更是美轮美奂,歌舞演绎出彝、苗、藏、傣等数十个少数民族对故土和乡情的礼赞。
2004年,中国旅游集团旗下的天创国际演绎推出的舞台剧《功夫传奇》曾号称是“国内唯一实现百老汇模式的剧目”,除了在山东泰安长期驻场演出,同时在国内外巡回演出超过6 000余场。毗邻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泰山,该剧落户山东泰安也为当地增加一张厚重历史之外的旅游名片,中国功夫享誉国际,而欣赏中国功夫秀、读解功夫拳法背后的禅意却要到山东泰安。该演出集合了武术、杂技、音乐、舞蹈,将功夫精神融入小和尚的成长故事中,以武僧们的英勇形象传递民族气节。同年,中国首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广西漓江正式公演。该演出由第五代著名导演张艺谋和开创“山水实景演出”的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梅帅元共同策划导演,一经推出,影响空前。其后续的“印象”系列(《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大红袍》《印象武隆》等)也缔造了国内旅游的首个IP,引领旅游演出行业十余年。
2005年,央视的品牌节目“中华情”中秋晚会开创了“全息山水景观晚会”的先河,并带动了二三线城市的旅游文化产业蓬勃发展。随后“山水”“千古情”系列大型实景旅游演出、地方特色以及富有科技感的剧场旅游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旅游演出等遍地开花。西藏拉萨的《文成公主》,河北承德的《康熙大典》,安徽徽州《宏村阿菊》,江西鹰潭的《寻梦龙虎山》……南有《井冈山》,北有《延安保卫战》。杭州还有被媒体誉为与拉斯维加斯的“O”秀、巴黎红磨坊并称“世界三大名秀”之一的《宋城千古情》。而推出该剧的宋城集团除了在杭州宋城景区的演出外,还在云南丽江、海南三亚、四川九寨、广东佛山、陕西西安、湖南张家界、上海等多地续写着“千古情”系列。
首部漂移互动体验剧《知音号》和创造“边走边看”沉浸式演出的《法门往事》等更拓展了旅游演出的形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自由空间,属于身体的快感也就成为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具有了积极的意义”[8]40。沉浸式的旅游演出剧目和旅途中行走的景观交互作用,让身体的感受多个维度地丰富了起来。越来越多的旅游演艺呈现出集各大艺术于一身的综合特点,科技感的绚丽舞台,升降旋转的360环幕,震撼的视听效果,出其不意浸入式的表演……旅游演出竭尽所能地带给受众“视、听、触、味、嗅”的全方位感官体验。
回顾当下国内旅游演艺发展,习惯了视觉奇观的受众对山水景观的饱览和单一凝视逐渐朝向人文景观的互动需求转变。“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①不再是帝王将相的获胜宣言,业已成为新时代旅行者到此一游“打卡”之后的图文潜台词。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凝视”理论,指出凝视背后的权利关系和主客体,到英国学者约翰·厄里的“旅游凝视”学说,提出受众对旅游的潜在心理和对异己生活的内心追求。在旅途行走的过程中,看与被看的角色得到转化,主客体权力关系展开博弈。选择主动出走和“在路上”的游客们对外部世界的“凝视”正逐渐转向内心世界的“审视”。行走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还有眼前移动的景观。旅游演艺提供了大众媒介之外的“行径式”视觉狂欢。某种意义上而言,旅游演艺是“行走的景观”,它和后现代电影、偶像真人秀以及商业广告里塑造的视听“景观”相似又有着不同,它同样有着对雅俗文化的同化和收编,但在行走中的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中,旅游演出极大程度地解放了人们的身体,在山水画卷和“人山人海”的风景之外提供了新的凝视对象——人际关系和自我内省力。
二、沸腾的市场:感性消费与生态乱象
一方面,观赏或体验旅游演出俨然已成为旅游的“正餐”和在路上的“标配”;但另一方面,过路消费的感性和盲目,回头客少或美誉度不高,盈利少亏损多,单一的门票经济,同质化的“印象”“山水”“千古情”演出内容,扎堆的演出季编排,宏大歌舞叙事的虚假满足等也是旅游这个沸腾的市场之下暴露出的生态乱象。演出、盈利、开发和治理等模式亟待升级和更新。国家机构改革已将文化和旅游两大部门强强联合,如何在“互联网+”的全球化格局中找寻文旅、经济、艺术创作的平衡,输出文化自信,获得持久生命力,是当前旅游演艺需要思考的问题。
约翰·厄里在其《游客凝视》一书中把大众旅游的发展描述为旅游业的死亡,当旅游变成了“旅游文化”,类似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大众旅游使一切变得娱乐化、感官化和消费化。文化工业“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求提供标准产品”[9]112,大众旅游作为旅游文化的显性标志,曾是旅游民主化和标准化的特征,当今另辟蹊径的旅行者正在寻求个性化的有品味的私人定制,从而产生了新的文化精英,他们追求真实的、审美的、甚至是苦行僧式的独一无二的旅游文化。此外,我们在旅游和休闲方面的众多新兴选择正全方位地包裹席卷着我们,这些选择正在催生交通、住宿、餐饮、娱乐、零售、健康和保健、摄影、娱乐、文化艺术、电子产品等新行业。旅游业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价值数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世界军事开支。
据《2017-2018年度中国旅游演艺行业研究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我国旅游演出观众人次达6 821.2万人次,旅游演艺消费人群增长了26.5%,票房增幅近20%,达到了51.46亿元,创历史新高。该报告从旅游演出剧目、场次、观众、需求等几大方面进行盘点了沸腾的文化旅游市场,并指出,受益于中国经济转型以及消费升级,旅游人群对旅游内容要求日益增高,从原来单一的观光模式转变成“观光+体验+文化”模式,推动了旅游演艺大幅增长。报告还提及主题公园旅游演出发展势头强劲,以9.6%的台数贡献了45.3%的票房。而剧场旅游演出剧目数量有171台,占总台数的62.9%,票房收入只占到26.4%。[4]旅游演艺市场的二八定律,未跟景区结合旅游演出剧目是目前市场乱相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近年来,以《ERA-时空之旅》《又见平遥》为代表的杂糅了戏曲、歌舞、杂技、民俗风情与戏剧叙事的驻场演出,以《长恨歌》《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为代表的旅游景点为背景依托,结合当地文化的实景演出和《长隆大马戏》、“千古情”系列等复合型旅游综合体的主题公园或主题剧场的演出是当下的三大主要旅游演艺类型。然而,无论是上千人的超大型演出还是几百人小剧场演出,纵观国内的旅游演艺,即便受邀奔赴国外巡演,也难觅对文化IP的真正版权保护。如果将国内各地的万达主题公园和落户上海的美国迪士尼主题公园相提并论,就不难看出其差异。前者虽也遍地开花,却缺乏国际视野与文化生命力,盈利模式也较为单一。后者依靠动漫形象和影视作品的IP绑定已深入人心,且持续更新,用不完工。打通了跨行业的链条,变被动的门票兜售为主动的纪念品消费,主题公园的各类IP衍生品销售占据了迪士尼旅游收入的半壁江山,也成就了迪士尼“梦想帝国”的伟业。
当然,也有很多旅游大国效仿美国迪士尼。以中国人最常去的出境游目的地新加坡和泰国为例,新加坡圣淘沙的水幕喷泉电影秀和泰国普吉岛幻多奇公园内的梦幻王国剧场秀,虽然IP版权保护意识很强,曾经严禁观众拍照录像,演出前的安检十分严格。但由于过多杂糅了民俗歌舞、杂技、魔术、滑稽戏等类型,观赏过程信息量太大且观剧过程束缚较多,导致其依然无法形成本土的“迪士尼王国”,其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旅游文化形象的缺乏。无论是国内的旅游演出还是东南亚邻国的旅游表演,在学习美国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同时,应抓住其部署“体验经济”的本质是提供给民众历史和情感的链接。旅游地的空间场所“不仅仅是功能性的,而是情感性的和有影响力的”[10]。动画片不是儿童的专属,而是打破代际,找寻文化认同的妙计。迪士尼的动画师为了绘制IP形象,可以很长时间蹲守在美国国家森林公园进行调研,足以窥见其对“文化工业”标准化与同质化商品的反叛。“人人都可以做梦”是美国梦的精髓,迪士尼所传递的国家文化自信也许是其保持旅游演艺持久创新,塑造独特生态世界以及构建全球化企业环境的根基所在。
三、凝视的狂欢:被忽视的泛艺术创作
国内的旅游演艺常常只出现在旅游、环境或经管行业的研究报告中,而在艺术创作的各项研究中是被忽视和被遮蔽的。这说明,旅游演艺虽然产业增速度较快,甚至票房增幅超过中国电影,但其艺术性,至少在当下,也许是被七大、八大艺术(文学、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戏剧、建筑、电影、电视)研究排除在外的。而旅游演出对各大艺术门类的综合运用以及跨媒体科学技术的融合,其系统性、复杂性,甚至艺术性实际上早已超越了传统剧场的叙事艺术或单一展览、互动装置的小众影响。尤其伴随旅游途中行走的景观与被解放的身体,多维度的感官体验对大众的影像是立体的、深远的。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论断“人人都是艺术家”,让当代艺术被拉下神坛,泛艺术化的倾向使得生活和艺术无法分割。
对比一下传统曲艺、歌舞、戏剧、电影电视、网络视频与旅游演艺的观演关系,前面的各种文艺形式大都只是听觉惑视觉的感受模式,观赏仪式也是单一的“镜框”式或“静坐”式,而旅游演艺无论前文提到的驻场演出、实景演出还是主题公园演出,任意一种类型因为旅游景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可以相对自由地提供“视、听、触、味、嗅”的统觉感受,迪士尼主题公园内若干个小剧场中“突如其来的雨滴、扑面而来的香气、从天而降的玩偶”等便是绝佳案例。再如,陕西西安因其厚重的历史和非凡的古都气质成为旅游“网红”,其在旅游演出方面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西安的两大知名旅游演出《法门往事》和《驼铃传奇》,前者创造了“行径中”的观赏和沉浸式表演令很多摇滚青年感慨:这比站着看的音乐节还酷。后者实现的360度环绕舞台和真实的动物表演将民俗、传统、历史、典故、民间故事等借由移动的山水景观徐徐展开,观众仿佛置身画卷,在即时的表演中找到历史和自我的双重坐标。
人们的身体不再是消极被动的场所,而是“一种感觉性——实践性的行动因子,形塑着文化,生产着文化”[11]586。旅游者既是消费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旅游的空间位移过程中,如果有意识地进行跨界合作与泛艺术化创作,目的地的实体景观与媒介再现、创造的虚拟景观就构成了现代旅游独特的“凝视狂欢”。以泛艺术创作来考量上述旅游演艺,其文化价值功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供心理补偿
旅游演艺在创造主题乐园、影视城等虚拟景观的同时,对观赏行为的创新也由静态延展为动态,单向度接受变为行走中的互动沉浸体验。旅游演艺为旅途中因舟车劳顿和筋骨辛劳提供了身体到心灵的“按摩”。随着旅游演出的观演模式不断革新,地缘文化、民俗传统、多民族习俗等伴随旅游的身体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等感官记忆同时生成,相伴相生。对于本土观众找到身份认同,树立文化自信;对于外来游客促进其理解中国文化,一举多得。越来越多的跨省或跨地域旅游演出就是一个进步的现象。人们不是因为到了景点才看演出,而是为了看演出才更期待去景点旅游。
(二)完成社交仪式
旅游演出的本质是秀、是剧,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超真实”“记忆”和“想象之地”。信息的内爆和互联网地球村带来的扁平世界,人们时常分不清想象和现实之境。面对全球化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候鸟”生活、“空巢”老人、新城市移民的身份焦虑和代际交往的文化隔阂,也许在家庭旅游、亲子旅游及其共同观赏旅游演出的过程中可以找到身份归属,打破壁垒,完成文化认同。有人说音乐和影视等也是促进圈层交往的社交媒介,但旅游演出的受众群更大、更广、更多元。愿意走出熟悉的家园去看世界的人们,主动社交的目的性更强,找到“遥远相似性”的可能比影视弹幕或网络社群里的偶然灵犀要大得多。
(三)促进媒介融合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称“媒介即讯息”,旅游演艺因其跨学科、跨媒介属性,对作品的视听呈现及感官体验要求十分复杂。它不是简单的综合舞台艺术与声光电技术的叠加,也不是对实体景观的歌舞再现或戏曲演绎,更不会仅仅满足于山水画卷里涂抹焰火来博人眼球,旅游演艺是由当下人们的生存方式构建的“流动的文化”。旅游演艺的泛艺术特性对于视、听、触、味、嗅等多感官的媒体融合与认知传播研究起到了极好的促进作用。其现场性、即时性的类戏剧特征十分明显,同时旅游演艺对互动表演的追求、虚实感官的混合、理性思考与感性记忆并存的体验也许会使传统的视听媒介,甚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视频节目褪去光芒。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慌和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也许会随着旅游演艺的良性发展被重新审视。
综上,技术的进步让人们看到了情感的宝贵。机器人也许能帮助人类完成七成以上的工作,但人类的情感世界却是技术无法替代的,而且也是一个可研究的话题。真实人生的戏剧性诉求是现代社会人们抵御苦难日常的诗意,行走的景观不只是在路上的身体更是旅途中收获的观念和烙进记忆的经历。百老汇的戏剧百变、多姿、神秘又令人充满期待,八成以上的观众来自纽约以外或海外游客。为何一部剧目能数十年经久不衰,并且仍然一票难求?旅游演艺如果将社交仪式、文化符号、意识形态与泛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对地区消费、生产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其代表作《单面人》(One-DimensionalMan)中指出虚假的文化繁荣和消费需求会让人变得只有单一的向度,失去批判性和否定思维。技术和技术理性“在操纵人这个工具,不只是身体,而且是头脑,甚至还包括灵魂”[12]537。如果人们通过优秀的旅游演出改变对景观硬件、区域边界、空间领属、人际距离和文化代际的整体看法,那么旅游业就可以成为“文化的保护者”。以贩卖视觉奇观为主要形式的表演是物质的和短暂的,而以精神培育和文化审美为信条的表演是有力的和持久的。如果故乡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养分,旅游演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维系区域连贯性和完整性的黏合剂,这也许是所谓的“文化内卷或文化复归”(cultural involution)。[13]
约翰·厄里在“旅游凝视”理论之后还提出了“文化经济”[14]的概念,即文化资本增加了资本的估值和数量。然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理所当然,以夏威夷游客在娱乐和文化景点上的花费为例,“夏威夷博物馆和文化景点的经济影响的估计表明,其贡献远远超过预期,为3.4亿美元。然而,这只占夏威夷120亿美元旅游业的3%,或仅占国家总产值的0.7%”[15]。正如本文提到当下国内旅游演艺的泛艺术性被轻视,价值被低估。台湾作家李敖曾主张“反旅游论”,认为饱读诗书,在文学的世界遨游所获得的想象力比到处走马观花、无头苍蝇式的游山玩水更重要。他几十年未离开过台湾,更没有机会踏足过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的理念曾遭受过巨大质疑,而如今以泛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读解“反旅游论”,其对文化的认知更显得隔靴搔痒。并非旅游一定会带来正向收益,旅游演艺的现状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毕竟“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的抽象性和旅游学的跨学科趋势在多元文化的今天更需要交流,而不是割裂,需要开放包容而不是画地为牢、故步自封。旅游演艺因受众的跨地域性,多元化知识背景,更能促进艺术创作打破知识边界,最终“他乡变故乡”,以主人翁的姿态迎接八方宾客。而这正是旅游演艺所追求的目标——以国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以不断创新的技术表达艺术审美,最终弘扬民族文化自信。
注释:
①源自拉丁文“Veni Vidi Vici”,译为“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语出公元前47年凯撒大帝在泽拉战役中打败本都国王法尔纳克二世之后,写给罗马元老院的著名捷报口号,宣告凯撒胜利和不可抵抗的力量。参见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Veni,_vidi,_vici)此处引用此句意指当代游客追求异己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