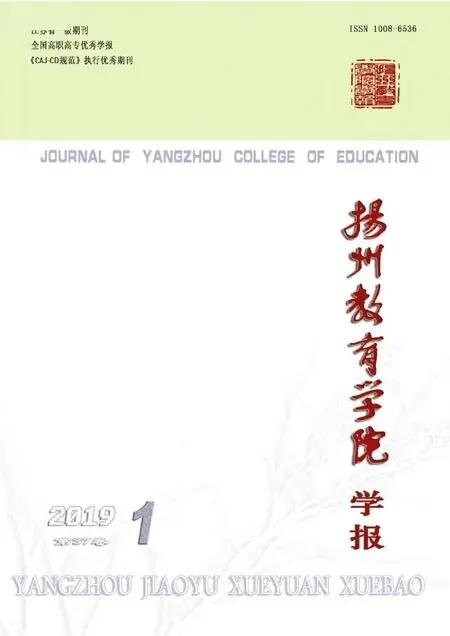金农题画文学中的多元趣味
2019-03-05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芜湖 241000)
金农,字寿门,是历经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一位独具特色的艺术家。他的艺术生涯极其丰富,在诗、书、画、印等领域均有造诣,尤其在书画领域。他的绘画取材广泛,主要题材有竹、梅、马、人物等,偶有山水小品的创作,题材之广、笔路之宽,少有人匹敌,可就绘画水平而言,竹画不及郑燮、梅画难敌李方膺、马画有明显的造型缺陷、人物画似乎也不在黄慎之上。何以金农被誉为“扬州八怪之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农独树一帜的题画艺术。题画文学是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画上题诗作跋是文人画的一大特色,始自宋代苏轼、米芾,至清代已为滥觞。金农更是擅长题跋的个中能手,他作画几乎每画必题,但不是简单地为画作注解,而是包含着无限深意和多元趣味,画与题相互关照,妙趣横生。金农的题画文学中包含的多元趣味,可以从文人情趣、世俗谐趣和禅宗理趣三大方面阐析。
一、文人情趣
金农少负诗名,青年时便得到了诗界泰斗毛奇龄和诗坛领袖朱彝尊的高度赞扬,“怀人绝句三十首”,《景申集》更是使30岁的金农名震扬州文坛。金农前半生都在进行文学创作,直至知天命之年才开始作画。他先是文人,再是画家,所以他的文人情怀,会不自觉地抒发运用到题画创作中,或托物言志,或感怀世事,题画一体,境界独特、情趣盎然。
金农虽以布衣雄世,但作为一个自幼饱读四书五经的儒生,“学而优则仕”的至理名言也时常在影响着他。他在画马图如是题道:“……今予画马,苍苍凉凉,有顾影酸嘶自怜之态,其悲跋涉之劳乎?世无伯乐,即遇其人,亦云暮矣。吾不欲求知于风尘漠野之间也。”[1]280金农虽然是画马,其实是在刻画自己,画跋所言更是在感慨自己这匹千里马,无慧眼之人赏识。纵观金农的一生,除了青年时期拜皇子侍读何焯门下,过了几年悠然生活,但随着何焯因谋反罪被捕而告终。其余几十年都在游历天下、广交名士,希望得到他人赏识,然而结果却是“无所遇而归”。如此,金农这一匹自傲的“千里马”,疲于跋涉,终无用武之地,顾影自怜,发出“世无伯乐”的呐喊,是积郁所致、顺理成章。这种对世无伯乐的慨叹在其它画马题记中也多有体现,总之,金农在为马画像的同时,更在为自我写照。
金农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在梅花图《寄人篱下》中更是表露无遗,寥寥几笔勾勒出的篱墙,一梅枝将出篱墙而未出,右侧配上四个写经体楷书大字“寄人篱下”,升华全画。当墨笔在画纸上游走,厚重浓墨的大字饱含了金农多少心酸。“梅花香自苦寒来”,梅本该傲立风雪,愈是冷风料峭愈是香气四溢,而不是给这小小的樊篱围困。金农自比被围困的梅,他也想突围,一生游历却无落脚之地,“寄人篱下”短短四字道出金农无尽的愤懑,也似是他郁郁不得志后“掷地有声”的反抗。“雪比精神略瘦些,二三冷朵尚矜夸。近来老丑无人赏,耻向春风开好花。”[2]156金农在七十三岁时写下这首题画诗,他这一生都在等待闻香人,无奈已是人至古稀,却没盼到赏识之人。但他依旧保持文人的风骨,以画中的梅画自比,在寒冬腊月,尽管无人欣赏,仍然花开两朵,保持其傲然本色,迎接着春天的到来。
康乾盛世表面太平,其实早已波涛暗涌,官场腐败、文化专制等黑暗面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金农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当然有拯救苍生的情怀,但面对此情此景也束手无策。既无“达则兼济天下”的机遇,他只好“穷则独善其身”,这种思想在画跋中也多有体现。“古战场中数箭瘢,悲凉老马忆桑乾。而今衰草斜阳里,人作牛羊一例看。”[1]278浴血奋战、战功赫赫的老马,因无力服役便被人轻视,与牛羊家养牲口相提并论,人们对“战斗英雄”尚且如此,何况一介草民。战马是如此,百姓也是这样。康乾盛世下,统治者只是愚弄百姓、利用百姓,利益得到便弃之不理、不再过问。如《墨竹图》题:“跛道士,梅沙弥,写竹一竿极似之。不补桃花三两枝,何须贵人题恶诗。”[1]257毫不留情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大腹便便、衣冠楚楚和装腔作势、附庸风雅。“东邻满座管弦闹,西舍终朝车马喧。只有老夫贪午睡,梅花开后不开门。”[1]272这是金农再题梅花图的一首诗,任他门庭若市,丝毫与我不相干,此时的金农不再酸酸地自言“世无伯乐”了,他只想在这浑浊的世间洁身自好,保持独立精神。金农自言画竹就是表现自己的平生高岸之气,如画竹题跋:“先民有言:‘同能不如独诣。’又曰:‘众毁不如独赏。’独诣可求于己,独赏罕难逢其人。予画竹亦然,不趋时流,不干名誉,丛篁一枝,出自灵府……”[1]251这是金农画竹的艺术纲领,更是金农做人的准则,不怕寂寞,敢于孤独,不人云亦云,不为名利所累,似枝竹笔直挺拔,遗世独立。
金农在出仕和入仕中踌躇,把绘画当做抒情的工具,他描绘的事物、书写的题跋无不寄寓着他的文人情怀。金农画的虽是马、梅、竹,但借此寄托的却是自己的情思。他重视对生活的体悟,疲于奔命后以冷眼看世界,抒发自己喜怒哀乐。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幅画卷,配以金农特有的画跋,顿时意趣无穷、耐人寻味,其中人格化、情感化倾向更让人难忘。如此,金农无愧受到褒赞,更有人称金农为传统中国最后一位真正的文人画家。
二、世俗谐趣
金农一生的仕途理想,伴随着他博学鸿词科的失意而最终破灭了。时年50岁的金农,或许是没有衣锦还乡的资本,落寞的他,最后选择寓居扬州。在这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商人“咸近士风”,金农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扬州民谚曰:“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市场对于书画有着广泛需求,贫困的金农迫于生计也依靠鬻书卖画而自给自足。金农在《墨梅图》中自嘲道:“……画梅乞米寻常事,那得高流送米至。我竟长饥鹤缺粮,携鹤且抱梅花睡……”[1]271因为鉴赏对象从文人转向了大众,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金农创作了有世俗风情倾向的画作,这类画作贴近日常生活,亦庄亦谐,再从题跋观照,通俗易懂,引人发笑,同时又给予人深思。
金农努力在画面之外,利用题跋营构另一个充满趣味的场景,并不意蕴高远,而是别具生活气息。如:“客窗偶见绯梅半树,因用玉楼人口脂画之,彼姝晓妆,毋恼老奴窃其香奁而损其一点红也,不觉失笑。”[1]274题跋中的“口脂”指的是现在的口红,“香奁”指女子的梳妆盒。金农为了让梅花更加绯红,竟偷用女子的口红上色,惹恼了妇人。金农究竟有没有用口红给梅花上色,不得而知,但却因此题跋给梅花平添一种香艳之气。在此之外,金农用饶有谐趣的题跋,营造了闺房内,恼火的妇人,低头认错的丈夫这样一副妙趣横生的场景。金农的《消夏图》画面仅作几片红瓤黑子西瓜,单调无味,配以题跋后,则趣味无穷了。“行人午热,得此能消渴。想着青门门外路,凉亭侧,瓜新切,一钱便买得。”[2]131典故出自东平侯邵平种瓜青门的故事,寥寥数语,营造了一幅画面,正午太阳当头,大汗淋漓的路人在凉亭边啃着西瓜,霎时暑气全消,伴着微风是何等惬意。再看看图中三片单调的西瓜,好似拯救病人的灵丹妙药了,花这一钱,便可得到如此享受。画、跋一体,细细品来,稍加联想,仿佛在凉亭边吃西瓜的就是自己,置身画中,这三片西瓜果真消夏!
为了迎合世俗多元趣味的需要,金农作为文人做出不少牺牲,但与此同时,他用通俗易懂的手段向民众传递自己的情感,也敢为困苦的百姓发声,用谐趣的方式抨击了世间的污浊。“美髯如公,三百六十酒场中,日日相逢。游戏游戏,何屑骂山魈林魅。头上乌纱,赐自官家,多少争看多少夸。好文章换来人前摇摆,却不费一钱买。”[2]141头戴乌纱的官员人人竞看,世人攀附权贵可见一斑。但官员并不为民做主,而是在酒场游戏中厮混。虽是题钟馗像,天上神仙尚且如此,何况人间。再如题《杨梅图》“萧山山下湘湖滨,五月杨梅饱啖新。一颗酸浆酸不了,世闲多少皱眉人。”[2]128世人是因为杨梅的酸而皱眉吗,显然不是,新采摘的杨梅尚未到酸时,能让世人皱眉乃是世间种种不平之事。“豆荚青,豆花白;豆荚肥,秋雨湿。想见田家午饭时,此中滋味,问着肉食贵人全不知。”[2]131田家午饭,全凭农人劳作所得,自然滋味无穷。饕餮盛宴,尽是搜刮民膏而来,必定味如嚼蜡。
金农靠鬻书卖画维持生活,而新兴市民作为其主要买画对象,或多或少影响到画家的创作。在表达上,画家将目光投向了世俗,乐于与民众交流,了解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创作了许多大众喜闻乐见的画作,也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在扬州“岁入千金”的画家中,金农便是其中之一。
三、禅宗理趣
古稀之年的金农困苦不堪,妻子早已作古,女儿也因难产丧生,他感到尘缘已了,于是遣散了自己的童仆和哑妾,住进了扬州西方寺,皈依了佛门,写经之暇,画佛为事。这时,他给自己起了几个别号,如“心出家庵粥饭僧”“莲身居士”,其淡出俗世之心是很明显的。其禅宗思想在画跋也时有体现,具有哲理,表达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3]
成佛乃是玄而又玄的事情,而金农在《香林扫塔图》中用调侃语气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曰:“佛门以洒扫为第一执事,自沙弥至老秃无不早起勤作也。香林有塔,扫而洗,洗而又扫,舍利放大光明不在塔中而在手中矣。”[4]金农所言,貌似将舍利“放大光明”的功劳归于僧人手中的扫帚,实际并不是指成佛入道只是扫地而已,成佛是未来不可知的,不是在宝殿里诵读佛经就可以达到的,而是指向当下,佛在手中、在每个人心目中,无论是扫地僧、伙头僧或是满披袈裟的得道高僧,本质并没有不同,立足当下,做好眼前事,活好每一天,人人皆可成佛。“世无文殊,谁能见赏香温茶熟时,只好自看也。”[1]258文殊指的是文殊菩萨,世上没有活佛,自看不是独赏,而是独立,独立真实的生命是他追求的目标,也是他融入禅宗后的特殊体验,佛自在人心中。金农《画吾自画图册》,画中怪石从中芭蕉三株,上题有一诗:“绿得僧窗梦不成,芭蕉偏向竹间生。秋来叶上无情雨,白了人头是此声。”[2]164在禅宗里,芭蕉是生命的象征,同时也是虚幻、短暂、脆弱的代名词,表现出浓厚的生命意识。随着禅宗思想不断的深入,晚年金农以画佛为终结,少有梅画、马作。金农在《画佛题记》中表达自己的转变,“从此不复写衰草斜阳,嘶酸之状也,近奉空王,自称心出家庵粥饭僧,工写诸佛,墨池龙树,常现智慧云……”[1]284。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金农已经彻底放下仕进之心,对自己早期的绘画予以否定,“工写诸佛”,极尽肃穆庄严,没有了文人的洒脱不羁,此时的金农心已入禅定,“常现智慧”亦是禅宗思想的体现。他又在另一佛画中题道:“余年逾七十,世间一切妄念,种种不生。”[1]283这与佛家经典《坛经》的思想吻合,金农也觉得自己达到成佛的标准,在古稀之年,自号“我佛如来最小之弟”。[4]
金农一生不断辗转于文人理想与从仕抱负之间,在街头鬻书卖画的确为当时所谓正统文人不耻。加上亲人相继离世,心无所寄的金农依靠禅宗摆脱现世的烦恼,金农在佛光普照下走完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因这特殊的经历,赋予金农的题跋特有的生命力,不再流于阐释精深的佛理,而是通过笔触融入画中,给人启迪、发人深省。
四、结语
画以有题而名贵,题亦以有画而趣味多元,金农的绘画作品,饱含了情感寄托,“性情逋峭,以迂怪目”的他更是用题跋直接与鉴赏者交流。金农是“自负诗名的诗人”,通过绘画作品进行精神上的宣泄,画梅、绘马、作竹无不是其人格化的体现,充满了文人情趣;金农也是“鬻书卖画的文人”,在扬州鬻书卖画的生活让他“岁入千金”,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他创作出一系列具有世俗情趣的绘画作品;金农更是“深谙禅理的僧人”,看破凡事,遁入空门,把深邃的佛理用题跋的方式体现,充斥着禅宗理趣。如此,画跋一体,极具个性,金农冠绝“扬州八怪”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