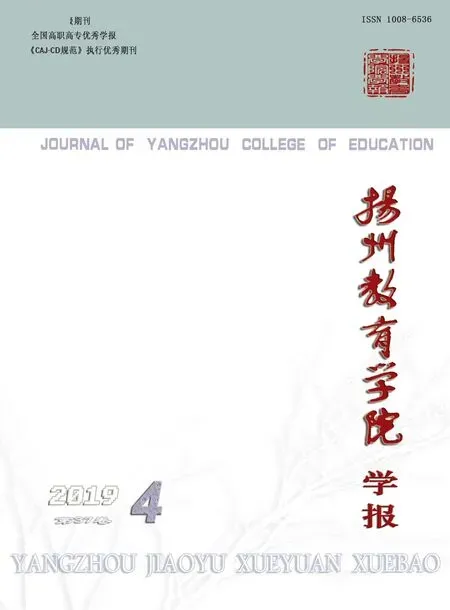扬州摘星楼小考
2019-03-05陈雪飞王催霞
陈雪飞, 王催霞
(盐城市滨海县明达中学, 江苏 盐城 224000)
摘星楼,两宋时期扬州名楼也,其遗址在今观音山禅寺内。观音山禅寺位于扬州城北之蜀冈东峰,蜀冈东峰虽非蜀冈丘陵最高点,但因其毗邻扬州城,又较冈下的长江冲击平原要高出不少,反倒成了扬州城的自然制高点,于此处俯瞰,“江淮南北一目可尽”[1],摘星楼也因此而得名。扬州摘星楼,史籍中多有记载,今人对此也论述颇丰,但对于摘星楼之兴废过程,摘星楼与摘星亭、摘星台及摘星寺之关系,摘星楼是否就是隋炀帝所建迷楼旧址等三个问题仍语焉不详,且多有抵牾。笔者在搜罗目前可见的所有与扬州摘星楼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爬梳对比,力图厘清以上三个问题。
一、扬州摘星楼之兴废
摘星楼始建于何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不少学者以为此楼乃晁补之哲宗元祐年间通判扬州时所建,并引晁补之《南京谢到任表》中所言“臣补之言臣昨知齐州,为扬州修过摘星楼事”及《(嘉靖)惟扬志》卷七中所引《续资治通鉴长编》[2],此条乃载哲宗绍圣二年事,今本《长编》缺哲宗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部分。“晁补之坐修故摘星楼,不覆实支省钱,降通判应天府”两条佐证之[3]。此处两条确载晁补之修摘星楼事,但仅言“修”,非言始筑也。
早在晁补之通判扬州前,就有关于扬州摘星楼的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张舜民因作诗讽刺前线将官而被贬监邕州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后又改监郴州酒税。张舜民将自开封赴郴州途中的一路见闻按日记下,汇成《郴行录》一文。其自开封沿汴河入淮,再顺着扬州运河南下,期间在扬州逗留数日,而在广陵时便曾登临摘星楼,其自言:
己巳,徐瓘承议、丘朝奉、辛大观,游建隆寺、九曲池。登大明寺塔、摘星楼故基,望江南山水,烟雨隐显如图画。酌水试茶井,在《茶经》为第五品。建隆寺即太祖濯征之地,有御容香火殿。九曲、摘星皆前朝故迹。大率今之所谓扬州者,视故地东南一角,无虑四分之一尔,其唐室故地,皆榛莽也。[4]237
据张舜民所言,神宗元丰年间扬州已有摘星楼,此楼绝非晁补之元祐间在扬时始建。另据张舜民文中“九曲、摘星皆前朝故迹”可知,摘星楼与九曲池一样,非宋代始有,而是“前朝”已有。然此处的“前朝”实际有歧义,就文意来理解,当是后文中所谓“唐室故地”的唐王朝;但由九曲池来看,似又非唐朝事。元丰年间出知扬州的鲜于侁在《广陵杂诗序》中尝记道:“炀帝奏乐于此(九曲池)。初,帝欲幸江都,命乐府撰水调九曲,工人王令言为子曰:“此曲无宫声,又无回韵,汝必不还。”[4]326苏辙在《扬州五咏·九曲池》一诗中也写道:“嵇老清弹怨广陵,隋家水调寄哀音。可怜九曲遗声尽,惟有一池春水深。”[5]9942则九曲池之得名实际与隋炀帝有关,乃“隋家”事,而张舜民又谓“九曲、摘星皆前朝故迹”,则摘星楼也当始于隋代。此处囿于《郴行录》外无其他史料涉及摘星楼始建时间,姑且将摘星楼修建时间笼统断为隋唐时期。
摘星楼虽始建于隋唐时期,但笔者爬梳史料,并未在今存隋唐史料中找到关于摘星楼的相关记载,其在隋唐时期的情况也不得而知了。而就张舜民“摘星楼故基”的描述来看,北宋元丰年间,摘星楼虽有迹可循,但当已荒废,仅存“故基”。故而才有元祐年间,时任扬州通判的晁补之重修摘星楼一事。实际元祐间重修摘星楼的并非晁说之,而是时任扬州太守的苏轼。晁补之元祐五年(1090)至七年(1092)通判扬州,而苏轼恰自元祐七年(1092)三月至九月出知扬州,摘星楼修葺一事恰好是在苏轼任内。众知,晁补之乃“苏门四学士”之一,其与苏轼交往甚密,诗文更是深受东坡影响。苏轼来扬,晁补之特作《东坡先生移守广陵以诗往迎先生以淮南旱书中教虎头祈雨法始走诸祠即得甘泽因为贺》一诗迎之[5]12826,此后二人多有诗文唱和。二人不仅在文学领域有师徒之情,职务上也是上下级关系。苏轼时任扬州太守,晁补之为扬州通判,乃太守副职。二人此时的密切关系,晁补之曾以“先生门弟子,佐守同一国”两句来概括[5]12768。也正是基于二人的亲密关系,无论从师徒情谊层面,还是政事运作角度来看,修葺摘星楼一事苏轼必然知情,且对此持赞同态度,否则执弟子及下属之礼的晁补之断不可能一意孤行强行修葺。实际在绍圣二年(1095),晁补之因坐修摘星楼一事被贬后,苏轼在与张耒的信件中已承认修楼乃出于己意,其在《答张文潜四首》中言道:“无咎(晁补之字)竟坐修造,不肖累之也。”[6]1539文中的“不肖”即苏轼自称,乃自谦之词,“不肖累之也”一方面是说晁补之本身并无过错,之所以被贬乃是新党攻击打压自己的一种方式;而另一方面即因为修摘星楼一事乃是出于自己的授意,晁补之因此事被贬实为自己所累。晁补之因修摘星楼被贬,不想元祐以后,摘星楼反倒因晁补之坐修事而声名日炽,后世扬州地方志凡涉及摘星楼必言晁补之坐修一事。
此后直至北宋末南宋初年,摘星楼都保存完好。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载,建炎三年金人至扬州城,便尝“引兵屯摘星楼下,纵火城内”[7]。金人之所以屯兵此处,当是考虑到此处乃扬州之自然制高点,于此居高临下,可俯瞰蜀冈下整个扬州城,便于控扼、监察百姓。
南宋时期,王象之《舆地纪胜》及祝穆《方舆胜览》均收“摘星楼”条,二书所载完全一致,言“(摘星楼)在城西角,江淮南北,一目可尽”[8]1159,此处《方舆胜览》沿袭借鉴《舆地纪胜》痕迹明显。当然,由二书所载亦可知,至南宋中后期,扬州摘星楼仍在。而有学者以为,《舆地纪胜》中多次言及摘星楼,在“迷楼九曲,珠帘十里”条中王象之引《南部烟花录》言:“炀帝于扬州作迷楼,今摘星楼基,即迷楼之旧址。”[8]1154而在稍后“迷楼”条,又对此说法存疑,以为:“迷楼……或云摘星楼。”[8]1157之所以一面肯定,一面又存疑,就是因为在《舆地纪胜》成书之时,摘星楼已成遗迹,故而无法确证《南部烟花录》中所言[9]53。此说谬矣,实际直至南宋末年,扬州仍有摘星楼。
南宋末,李庭芝以两淮安抚制置使出知扬州,时王义山作《代通扬州制置李庭芝》一文与李庭芝联络,文中强调了南宋扬州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其中亦言及摘星楼,曰:“南躡乎钜海之浒,北压乎重淮之流,盖自唐以来为节镇,南渡后尤为大藩屏,登摘星楼,江淮南北可一目而尽。”[10]可见至李庭芝守扬州时的南宋末年,扬州摘星楼仍在,且因其地处扬州城之自然制高点,发挥着重要的军事职能。
实际直至南宋灭亡的德祐二年(1276),扬州摘星楼仍存。文天祥德祐二年(1276)正月奉旨诣元军求和,被拘,押至镇江。后文天祥逃出,连夜入真州。初真州守将苗再成颇信任文天祥,然淮东制置李庭芝却怀疑文天祥已降元,遣人谕苗再成,以为文天祥此番来真州,不过充当元人奸细。苗再成将信将疑,用计逐文天祥一行出城,并派兵监视其往淮西见夏贵,文天祥以为与夏贵不熟,执意往扬州见李庭芝,以打消李庭芝对其的误解。文天祥自真州来扬途中,历经艰险,其《出真州》《至扬州》两组诗详细记述了一路之所见所闻,而当中便曾言及扬州摘星楼。《出真州》其十三曰:“真州送骏已回城,暗里依随马桗行。一阵西州三十里,摘星楼下初打更。”[5]43006而在另一首《扬州地分官》中,文天祥言:“便当缟素驾戎车,畏贼何当畏如虎。看取摘星楼咫尺,可怜城下哭包胥。”[5]43010由此二诗,特别是“看取摘星楼咫尺”一句可知,此处的摘星楼绝非用典,而是文天祥亲眼所见,可知至德祐二年(1276),扬州摘星楼仍在。而南宋扬州地方政府之所以要保留摘星楼,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此楼盛名在外,乃当时扬州城的地标之一;另一方面更是因其地处蜀冈东峰居高临下的制高点位置,有重要的军事价值,绝不可弃。
不止是南宋时期,入元以后,扬州仍有摘星楼。元人魏初《寄扬州金使君》一诗开篇便言:“两年不到摘星楼,雁隔江声送客愁。”[11]2013魏初,金人,金亡后入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魏初以侍御史行御史台事于扬州,直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于扬州擢江西湖广道提刑按察使,在扬州首尾三年。此诗中直接以“摘星楼”指代扬州,“两年不到摘星楼”即言离开扬州已经两年,则此诗当作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前后。而就魏初诗句所述,虽不知至元二十五年(1288)摘星楼之情况,但至少在他在扬州前,即至元二十三年(1286)时,摘星楼仍在,且是当时扬州一标志性建筑,否则魏初不当以此来指代扬州。魏初以外,元人王奕词中亦言及扬州摘星楼。王奕,由南宋入元,其尝有《八声甘州·题维扬摘星楼》一词,云:“问苍天,苍天閴言,浩歌摘星楼。这茫茫禹迹,南来第一是古扬州。”[11]1293此词既言“题维扬摘星楼”,显然作此词时摘星楼仍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谢枋得被元人所执押送大都后不久,王奕“愤至元乱华,作义约,倡率一时名士东奠孔林,当时从者不知几百十人”,他们一行人自玉山出发,由鄱阳湖入长江,顺流东下,到扬州循运河北上进入山东。而此词恰好作于在扬州期间,则至元年二十六年(1289)前后,扬州摘星楼仍在。
扬州摘星楼实际毁于明代。嘉靖年间,程文德来扬,尝有《焦范溪侍御邀游西阁》一诗,云:“九曲池荒蔓草生,摘星楼废野云阴。不须感慨重怀古,明日重来即古今。”[12]就诗中“摘星楼废野云阴”一句来看,当时摘星楼已废。同是明代人,姚孙业《同夏仲宽谢次侃陈灵生泛舟至清平桥登平山堂过观音寺小憩归舟赏荷花》一诗言及其与友人游玩扬州情形,诗中亦曾提及摘星楼,云:“摘星楼址尽草莱,隋皇胜安在哉。”此中亦可见明时扬州摘星楼已废弃。摘星楼虽已荒废“尽草莱”,但遗迹尚在,又因其靠近平山堂、大明寺等名胜,时常有游人来此。明人杨本仁《送凤冈徐子和之扬州》中言“摘星楼下暮江横”,程文德“摘星楼废野云阴”外,尚有“摘星楼外碧烟浮,山含宿雾迷茺环”两句,可见此处楼虽废弃,但景色尚佳,仍可临观。
综上可知,扬州摘星楼始建于隋唐,入宋后渐废,仅存遗址;苏轼及晁补之在扬州时修葺之,后其声名日炽,逐渐成为扬州城之标志性建筑;南宋末元初,摘星楼仍在,直至入明以后,摘星楼渐废,成为“草莱”之地,但此时摘星楼遗迹尚存,不乏临观者。
二、摘星楼与摘星亭、摘星台及摘星寺之关系
摘星楼外,宋代扬州尚有摘星亭、摘星台及摘星寺,皆冠以“摘星”之名。摘星亭始见于苏辙《扬州五咏·摘星亭》一诗,云:“阙角孤高特地迷,迷藏浑忘日东西。江流入海情无限,莫雨连山醉似泥。梦里兴亡应未觉,後来愁思独难齐。只堪留作游观地,看遍峰峦处处低。”[5]9943摘星寺则最早见于秦观《与李乐天简》一文中,秦观言:“遂登摘星寺,寺迷楼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门诸山历历皆在履下。”[13]1008摘星台见于史料则较摘星亭及摘星寺要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四中载:“郭仲威迎谒于摘星台,(王)德手擒之。”[6]800
而有学者借明清扬州地方志及《大明一统志》中所载(将摘星楼、摘星亭、摘星台分条叙述),以为摘星楼与摘星亭、摘星台、摘星寺或不在一处[9]53-55,笔者以为非也。
首先,今之所见明清方志关于扬州摘星楼、摘星亭、摘星寺之说实际均沿袭自《大明一统志》(其成书早于明代扬州诸方志),然《大明一统志》中对于摘星楼诸说的记述实际有抵牾之处。其中言摘星楼“在府城西角”,此处显然是抄录自南宋《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二书中“摘星楼在城西角”一句,且此处将“城”改为“府城”,实际完全张冠李戴。南宋时期扬州是典型的三重城形制,蜀冈上堡寨城,即后之宝祐城,蜀冈下宋大城,两城之间则有夹城联通,整体呈现蜂腰式结构。而《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二书中所谓的“城西角”,以宋三城的形制去看实际特指蜀冈上的宝祐城。摘星楼所在的蜀冈东峰正在宝祐城内,恰在城西角。而入元以后,宝祐城即被毁弃,此后扬州城都在蜀冈下,蜀冈上已无城。明万历之前的扬州城实际是截取南宋扬州三城之一的宋大城的西南部分而成,其规模及形制与南宋扬州城完全不同,其与摘星楼相距甚远,根本不相接,何谈在“西角”呢?实际以明旧城位置来看,摘星楼所在的蜀冈东峰当在其西北数里,此实际与《大明一统志》所载的“摘星亭在府城北七里”暗合。明人编《大明一统志》时未见宋、明两代扬州城池之变动,误承前人之说,而今人又不查,以致一误再误。
其次,由名称来看,无论是摘星楼、摘星寺、摘星亭还是摘星台,皆有“摘星”二字,既有此命名,四者之间必有关联,即使不在一处,也当相去不远。一如扬州之九曲池与九曲亭,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载,九曲亭就在九曲池上,二者就在同一处。
第三,宋人在言及摘星楼及摘星亭、摘星寺时,均言为隋代迷楼古迹。苏辙在《扬州五咏·摘星亭》一诗自注中言:“(摘星亭)迷楼旧址。”[5]9943秦观文中亦言“(摘星)寺迷楼故址也”[13]1008。且不论摘星寺及摘星楼是否为迷楼旧址,只以迷楼为参照,二者也当在同一处。
第四,以扬州之独特地势来看,四者也当在同一处。上文已讲,摘星楼在蜀冈东峰,乃扬州城之自然制高点,于此可眺望江南诸山。而由此处苏辙“阙角孤高特地迷……看遍峰峦处处低”[5]9943及秦观“其地最高,金陵、海门诸山历历皆在履下”[13]1008的描述来看,摘星亭与摘星寺都当在扬州高处,能眺望远处山峦。而扬州地区自古无山,周边仅蜀冈一条山脉,其中又尤以蜀冈东峰地势最高,摘星楼即在蜀冈东峰上。由此来看,摘星亭及摘星寺也当在蜀冈东峰,换言之,摘星楼与摘星亭、摘星寺实际在一处。
摘星楼、摘星亭、摘星寺之关系,当如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所言的:“观音寺,一名观音阁,在宋《宝祐志》为摘星寺。明《维扬志》云:即摘星亭旧址。《方舆胜览》谓之摘星楼。”[14]365即在一处也。再具体点来讲,北宋蜀冈东峰有摘星寺,摘星楼、摘星亭一类均在寺内。入元后,摘星寺不存,“元至元间僧申律”建观音寺,后明洪武二十年,“僧惠整重建”观音寺,“题之曰功德山”[14]365。
三、摘星楼非迷楼旧址
除此以外,关于摘星楼还有一个疑问,即摘星楼是否就是隋代迷楼旧址。就上文所引苏辙及秦观二人诗文来看,似乎坐实了扬州摘星楼就是迷楼的论断,此后《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明清诸地方志及不少前辈学者都坚持苏、秦二公之观点,以为摘星楼就是迷楼旧址。笔者以为此观点实际错漏百出,仍有待商榷。
首先,这一观点成立有一决定性的条件,即隋代迷楼确实存在过,且就在扬州,然就今日所存史料来看,这一先决条件实际不能满足。迷楼之说,实际并不见于正史,无论是《隋书》,还是《旧唐书》,亦或是北宋编纂之《新唐书》,正史当中对于隋炀帝功过论述颇详,其中不乏对炀帝劳民伤财、大兴土木的口诛笔伐,但却只字未提迷楼。《大业杂记》《大业略记》《隋季革命记》等专记隋朝旧事的唐代笔记中也未见迷楼踪迹。就陈尚君先生考证,迷楼之说实际始于中唐以后。贞元间诗人包何《同诸公寻李方真不遇》云:“闻说到扬州,吹箫有旧游。人来多不见,莫是上迷楼。”[15]166至元和间,白居易《新乐府隋堤柳》中云:“南幸江南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蛾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15]145同样是元和年间,李绅在《宿扬州》一诗中云:“今日市朝此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15]286大中年间,许浑有《汴河亭》一诗,云:“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15]888之后更有罗隐之《迷楼赋》及传奇《大业拾遗记》(又称《南部烟花录》)和《迷楼记》,将隋炀帝修建迷楼一事断为定论,尽嘲炀帝之奢靡。
综上,迷楼之说实际起于隋亡后一百多年的唐朝中后期,而在此之前并未见有相关记载。唐人以史为鉴,以隋二世而亡为警,又因其王朝乃继隋而起,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有丑化杨隋之必要。《大业拾遗记》《迷楼记》诸书中更是尽揭隋炀帝阴事,将炀帝刻画得荒淫无道、残酷暴虐。如《迷楼记》中言隋炀帝在迷楼中“诏选后宫良家女数千人,以居楼中,每一幸有经月而不出”[16]1028,而臣下更是进御童女车之类奇技,何其夸张荒诞也。此迷楼之说不可信之一也。
其次,北宋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时,对文献真伪斟酌极其严苛,书中尽言隋炀帝一生事迹,包括隋炀帝在扬州开运河、通龙舟、营建江都宫等诸多事迹,却唯独未曾提及《大业拾遗记》及《迷楼记》中营建迷楼事也,此亦即侧面之一证也。
第三,《大业拾遗记》等诸书中所记迷楼地点实际自相抵牾。罗隐《迷楼赋》中言:“岁在甲申,余不幸于春官兮凭羸车以东驱魏阙之三千里兮,得隋家之故都。”[16]1688就其记述来看,迷楼当在扬州。《大业拾遗记》中言迷楼乃炀帝东幸江都时所建,也当在江都。而《迷楼记》中却言迷楼最终乃“唐帝提兵号令入京”时所焚,隋炀帝虽曾下诏“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16]2388,将江都提升到与都城近乎同等地位,但隋代江都毕竟不是都城,且唐朝皇帝从未来过扬州,《迷楼记》中的“京”显然不可能是扬州。
综上所析,笔者以为,隋炀帝于扬州建迷楼一事很可能出于唐人之杜撰,迷楼或根本就不存在,既如此,又何来摘星楼即迷楼旧址之说呢?如此,言摘星楼即迷楼旧址完全是张冠李戴,牵强附会。
四、结语
扬州摘星楼位于扬州蜀冈东峰之上,因其地处扬州城的自然制高点,“江淮南北一目可尽”,故以“摘星”名之。其确切建造时间据今之现存史料已不可考,但基本可断建于隋唐时期,但当与传闻中隋代迷楼无关,并非志书中所谓隋炀帝迷楼旧址;至北宋时已渐废,元祐间,时任扬州通判的晁补之复葺之,后补之因此而获罪被贬,而摘星楼反因晁补之坐修一事而名扬天下。两宋时,摘星楼外,蜀冈东峰尚有摘星寺、摘星台、摘星亭等同冠以“摘星”之名的建筑。这类建筑,无论是从正名定义的角度,亦或是从扬州周边地势角度考量,都当在一处,即在蜀冈东峰上;此后直至南宋末,因其地处扬州城之自然制高点,仍在发挥重要的军事职能;入元以后,摘星楼仍在,且仍是当时扬州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时人常以“摘星楼”代指扬州;至明时,摘星楼方毁,楼址亦随之沦为“草莱”之地,但因其盛名在外,且尚存遗迹,故而当时仍不乏观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