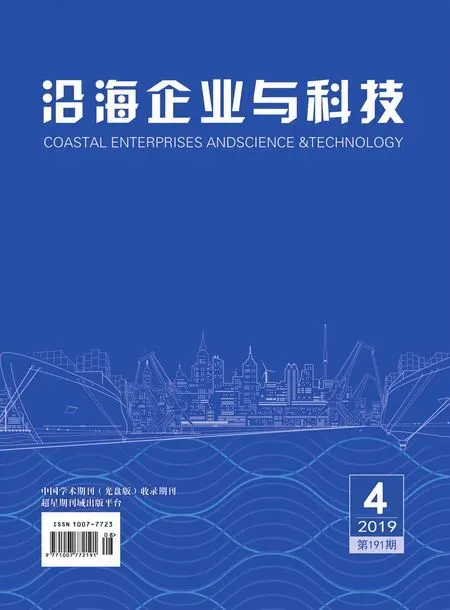回归教育的本质
——关于当代教育问题的批判性反思之六
2019-03-04简圣宇
简圣宇
教育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正视自身局限是持续进步的前提。作为教师,最重要的事情是研究自己直接面对的学生。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关键是专注于对学生的具体培养。教育是一个良心活,我们作为教师,必须认真对待,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审慎思考。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基层教学不断面对各种新出现的问题,如何在直面现实的前提下改变现实,是教育工作者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
须知,教育的本质就是让学生通过对知识的学习逐步获得超越知识本身的能力。教育不是讲授具体的技能,而是让学生在焕发自身潜能的过程中真切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和认识世界。学生应当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发现自己力量的愉悦,如果仅仅是为了分数和荣誉等外在刺激而学习,这种学习要么是无法持续的,要么存在走向“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危险。
一、从精英化到大众化:教学和管理机制应随时代变化而调整
当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阶段,我们自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与以往有着巨大差异的教育教学问题。但从管理层到基层,很多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精英教育阶段。如果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不能得到及时调整,那么他们采取的步骤必然难以摆脱旧式教育的局限。笔者在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愈加意识到,当面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诸多新问题时,基层教师最需要的是来自上级授予的在改革上更大的相对自主权,并且提供更多可以凭依的资源,以及尝试(包括试错)的宽松环境,而非遭遇更严厉的问责或听从更束缚手脚的行政指令。正如有学者提到的那样,“尽管学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几乎所有的教员都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共同的专业规范和价值观,包括自主性,学术自由共同智力和知识追求。”[1]行政管理层需要尊重教员的相对自主权,因为作为基层人员的教员更熟悉具体的教学事务。古人尚且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宽容,如果现代教育环境下基层被僵化地管理,就实在是太遗憾了。
基层教师面对诸多尴尬。第一,学生素质出现“整体下降,少数上升”的二重状况,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给大部分学生补课,同时挑出尖子生进行精英班教育,但目前受制于超负荷工作量而难以开展。第二,改变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仰赖于上层的管理科学化,如果出现上层的科学化管理步伐缓慢的问题,基层教师是无法有效展开工作的。
笔者原本在一个地方艺术院校从事通识课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到2006年后,学生整体素质开始快速下滑。以往原本可行的各种传统教学措施,在面对新一批的大学生时已经难以推行。笔者开始还以为这只是部分地区的问题,但在全国会议与其他同行的交流中得知,这其实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而且据笔者十多年来的观察,一方面是学生整体素质在逐年下滑,但另一方面有的尖子生一年比一年强,这种素质上的两极分化正愈加显著。这说明,在大学里为一部分学生开设精英班为大部分学生开设加强班,已经是现实趋势。
由于相当数量的学生基础素质滑落的幅度较大,所以笔者在大学语文课程中只能加入高中的内容来给学生“补课”,诸如从文言文的辨读到各种代表性作品都耐心手把手地重新教一遍。有时候笔者感到自己能在整体上延缓真实教学质量的下滑就已经相当吃力了,再奢谈所谓的“在更高层次上创新”已有些不切实际,除非将尖子生从自然班中识别和分流出来,开展分级教学。如果将一个人的能力比作金字塔的话,其“创新能力”处于最顶端。如果这个人的基础部分不牢靠,怎么指望他的顶端部分有很大作为?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多的耐心和更智慧的方案来应对学生整体素质下滑的现实,而非用更花俏时尚的教改理论来建构“精致的形式主义”。
学者费坚提出:“大学权力博弈是在大学特定的场域中,针对特定的目标,各权力主体之间按照‘游戏规则’进行的博弈。其结果常常导致各类权力主体在大学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改变,并引起大学权力结构的变迁。”又言:“大学组织要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协调各种权力关系,以使它们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2]他的分析可谓鞭策入里,但在相当多的地方高校,最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正如蘑菇喜欢长在缺少阳光的角落,而没有权力博弈和制衡的地方,正是“精致的形式主义”繁衍得最茂盛的地方。
笔者在原单位担任教研室主任期间,曾试图推动包括精英班在内的诸多教育改革。但听到的差不多全都是抵制的声音。不但某些一向保守的老教师反对,而且就连支持改革的年轻教师也有抵触情绪。年轻教师苦笑说:不是我不想跟着你改,只是现在工作量只增不减,本来就已经是超负荷工作状态,如果再按你这些改革提议推进分类识别工作,那就变成“超超负荷”工作状态了,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说,以科学化、智慧化的管理改革减轻基层工作负担,是推动精细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没有“减量设计”就不可能真正推动精细化、智慧化的举措。一些提要求的管理层人士往往对基层教学不了解,对自己学生整体素质的下滑亦讳言,而对于精细化改革必须配套的政策措施也没能跟进,只是带着美好的愿望希望基层教师通过各种创新让教学质量稳步上升,那么其最终的实际效果如何,无需赘言。无非是要么遭到基层的坚决抵制,要么就是基层在被迫改革时采用各种对策来“巧妙应对”。并非基层故意跟管理层对着干,而实在是在精力上已经严重透支了。
当时有一些二级学院提意见,希望我们教研室以更有针对性的细化措施去按照不同专业开展精细化教学,比如给不同专业的学生专门性地开设如何撰写古典诗词、赋、对联等,让学生在创作中国画和书法时更有底蕴。这些意见的初衷甚好,然而学生整体素质在近五年里已经严重下滑,有较大比例的学生已经连800字的现代汉语作文都写不通顺了,许多学生不认识繁体字,对文言文也有着强烈的抵触心理,更何况创作诗词、赋、对联等需要个人灵气的文体。而大学语文课程在学生四年本科中仅仅占36个课时,如何能够承担此等厚望。如果要针对每个专业开展精细化教学,那么目前的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案等就将从统一的一种变为几十种,我们教研室本来就已经在超负荷工作,这其中骤然多出的巨大工作量如何消化?精细化教学的理念再好,也必须面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现实问题。在不增加人手,也不通过网络公开课来减少总课时的情况下,其实任何精细化改革都难以推进。
即便不普遍实行精细化教学按照设想从全体学生中选拔尖子生集中起来开设精英班,也仍然需要上级部门给予基层以各种资源的实质性支持。因为按照培养精英的精细度去教学,所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远高于大班授课。仅以作业批改为例,在精英班进行的频度和精度需要是普通班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如果没有管理科学化的顶层设计作为前提,即便笔者作为教研室主任身先士卒鞠躬尽瘁,也难以保证手下其他教师同样奋不顾身。精细化小班教学相当于宫廷造顶尖瓷器,而普通的近百人的大班教学相当于民间手艺人造陶罐,哪里有可能建立起“精细化的大班教学”?如果学校不以数倍的程度加大资源投入,也不建立提升民间手艺人水准的机制并且有足够的耐心,而是要求民间手艺人尽快用陶土来造顶尖瓷器,那么手艺人们最多也就是在陶土上敷衍一层瓷皮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设计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管理设计模式,让工作既有“加法”也有“减法”。加的是精细化措施,减的是工作量,这样才能让基础在使命感的感召下自觉推行管理层的战略性举措[3]。
在很多地方高校有这样的怪现状:明明很好的改革创意,但是基层就是按兵不动,拒绝或者拖延执行,管理层在这过程中不反思自己顶层设计出了哪些问题,只是直观感觉是下面在怠工,于是又召开更多的会议号召基层“不讲条件讲奉献”。结果本来分给务实工作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现在再挤出时间去反复开会,用于直接投入工作的时间更被挤占。教师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面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学生日渐分化(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加上上层的管理科学化步调缓慢但要求基层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是很多地方院校基层教学的死结。基层员工在一直保持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下谈提高教学质量,就像晋惠帝曾言的“何不食肉糜”。如果没有基层获得相对自主权这一前提,也没有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那么管理层提出的各种初衷美好的构想很可能都只会是镜花水月。
二、“抢跑”教育后遗症:初等教育对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问题
另外,笔者2017年工作调动到东部高校之后,逐步发现这些“教育发达省份”区域的高校学生又有自己的问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初等教育的“打激素式”学习导致高等教育发生连锁反应,出现“透支性厌学”问题。当下中国高等教育遇到的包括大学生厌学等诸多问题,笔者认为源头在初等教育。
学者阎光才撰有一文提到:“日本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校园生活的核心环节就是考试”,然而“以考试为中心的知识是碎片化的,为应对考试剧烈的竞争、大量的补课和机械的学习”,学生“不仅经受了极端枯燥、痛苦、烦躁和折磨等体验,对学习有强烈的排斥感,而且驯化出来一种极为复杂与矛盾的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冷漠人格”。这些学生到大学时代时,会出现诸多学习和心理问题,“习惯了依靠记忆来完成有明确答案的闭卷考试,而对于如何利用知识对事实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开放考试束手无策;表面上很顺从,但对课堂上有积极活跃表现的学生予以集体性的孤立;大量逃课,即使人到了课堂却心不在焉、昏昏欲睡和百无聊赖”“众多学生并不清楚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什么与过程并不重要,学习尤如一个仪式与表演”[4]。其实何止是日本,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都存在这种相似的问题。这些考试背后隐含着支配它的文化权力的具体作用,正所谓“文化是在团体情境之下共同创作的产物,一且学习的过程完毕,文化即成为个体面对外在世界与内在自我的基本态度”,而且“权力不只是强制和阻止,它也是生产性的。权力不仅是种控制和支配的力量与能力,权力还能吸引、拉拢、诱感、赢得赞同”[5]考试已经演化为一种无形的手,把控着整个社会场域的升学欲望和焦虑。
目前,中国高考基本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标准,这意味着考试成绩仍然是最核心的判断指标。在当代语境下,高考的确是社会公平最重要的保障之一,但以考试成绩为中心的录取方式弊端仍然相当显著。它作为指挥棒,直接深刻影响着作为预备期的初等教育。江浙鲁豫等省普遍存在小学阶段教育就开始“抢跑”现象,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被迫在周末和寒暑假去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这导致他们本该丰富多彩的童年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灰暗乏味,并且还由此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严重问题:不少孩子产生了发自骨子里的厌学症。须知,适度的竞争可以有效提升孩子的竞争意识,但烈度过高的竞争则可能会扭曲他们的心灵,催生出一批功利主义者或自暴自弃者。
就我在江苏的观感,其实本地老百姓跟广西相比,过得并不那么舒坦。虽然本地GDP等指标远高于广西,高收入者众多,不过平民收入仅略高于广西,但他们却要用这样的收入去面对高于数倍广西的房价、租金等等。同样阶层的平民,在住房条件、饮食层次等日常生活方面,广西反而比江苏要好许多。而且由于江苏经济排名一直保持全国前列,使得很多本地居民认为离开这个发达省份到其他省份就业形同从“第一世界”到了“第三世界”,所以出省意愿较弱,这反映在高考上,就是考生选择报考院校时在本省扎堆,这也导致江苏高考格外难考,反过来又致使本省中小学“抢跑”教育难以改变,陷入僵局。当一群从小接受“抢跑”教育的儿童,长大后又扎堆在一起高考,其竞争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6]P284青少年时代心灵得不到自由舒展,长大之后在思维转换时就会缺少创意,这就是一个常识,但在“抢跑”氛围浓重的地方,这一基本常识不得不让位给升学压力。按照原本的生长逻辑,青少年阶段必须留够嬉戏娱乐的时间,从而为日后在大学和工作阶段的“发力”积蓄能量,但这些教育发达省份的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在青少年阶段就被严重削弱。原本按照某些孩子自身的天然发展逻辑,他们在青少年阶段最多只能发展出最终能力的六七成,剩下的部分将由他们日后自己慢慢积淀和萌发。然而本地家长在升学的压力下,通过补习班这类外在方式打乱孩子生长的自然节奏,导致不少孩子的潜力在教育初期阶段就被过早开发出来。孩子们在各种补习的刺激下就像打了激素的饲料鸡,个头大而生长快,但味道却丧失了应有的香韵。
诚如学者刘铁芳所言:“我们的教育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庞大的教育机器有序地运转,但我们却看不到教育的根本性目标,短近的(考试)目标取代终极性的(育人)目标成为日常教育的追求,我们的教育早已在对物质化、技术化社会的被动适应中失去了自身原本不充分的理想。”[7]学者郑泉水也谈到:“一些高考或竞赛意义上的顶尖学生过于关注短期目标(如每次考试的成绩)以及与同学之间的竞争,缺乏源于兴趣和志向的内生动力,且形成的学习方法、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具有巨大的惯性,很难改变。显然,围绕高考和竞赛进行的学习,并不有利于他们成为创新人才。”[8]
笔者注意到,很多江苏学生考试分数相当高,然而一旦老师对之委以相应任务,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能力很弱。因为在从小学开始的日复一日的考试训练中,他们已经对考试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一旦离开这种熟悉的思维路径往往就会不知所措。学生的实际能力与其考试成绩严重不成正比,甚至让人怀疑他们的分数之所以如此之高,可能是因为把本应用于发展自己其他生活和学习能力的时间精力都调用来备考了,故而才造成其整体能力得不到良好的协调发展。
笔者还在广西地方高校任教时就已经发现,就高考分数而言,江浙鲁豫等省的学生按比值一般要高出西南地区学生甚多,但在整体素质上,很多高分入学的教育发达省份的孩子其实并不比西南地区地方高校的学生高(当然,前者在视野上一般的确比后者要开阔)。特别是来自某些东部地区的孩子,有性格缺陷乃至人格缺陷的比例相当大,其中有的孩子缺少团队精神,对待学习的功利主义态度也比较显著。有的孩子则习惯于不求进取,很容易自暴自弃,把自己归类为“佛系”青年。笔者接触他们时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随缘”,但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真正“随缘”,而只能主动进取,设法让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为如果放任自流,就很可能走向“小洞不补,大洞难补”的结局,到时候就算想“随缘”都“随”不了了。
笔者当时不能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到了江苏高校任教,又遇到相似的困惑。笔者所在扬州大学作为一本重点大学,学生入学分数换算起来足足高出一般西南地区地方高校一大截,但就笔者与学生具体接触的经验来说,比如以文学院学生为例,他们在大三之后整体上其实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同年级学生的水平大致相当,只是略高一些而已。这就让笔者非常诧异,因为按照逻辑推论,既然考入扬州大学文学院的竞争激烈程度远大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那么这些考入扬州大学文学院的高中生,理论上在大学阶段的能力发展应该大幅领先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才对。所以这一悖论似乎暗示着几个问题。
第一,其实大学才是孩子们发力的黄金阶段,这个时候他们心智开始初步成熟,对事物的理解趋于辩证,用一份力所能获得的成效,比中小学时用数份力所能取得的还大,这是“事倍功半”和“事倍功半”之间的区别,故而中小学时期的“抢跑”教育完全没有必要,反而是一种“赶在下雨前浇花”的行为。如果把教育投资比喻成一桩生意的话,那么以江苏地区为代表的教育发达省份的家长们做了一种非常不划算的买卖。在这场买卖中,除了补习班的培训者之外没有任何人能从中受益,而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学者余党绪曾以语文教育为例谈过功利主义对教学的渗透问题,他感慨:“如果语文教育彻底沦为技术与功利,而没有了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内容,那语文教育就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现实恰恰就是如此:技术主义与功利主义合谋,让语文教育陷人叶开先生所说的“最危险”的境地。不仅如此,它还使得语文老师也陷人‘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因为按照技术的法则,训练能出成果,时间就是效率,只要你肯花费时间、花费精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总能提高一分半分。在这种残酷的日复一日的操练中,在越来越耀眼的效益中,不知多少青年才俊被‘煮’了”。其实何尝只是语文教育,整个教育都需要回归本质和初心,抵制功利主义的侵袭[9]。
第二,教育发达省份的高考分数被人为抬高了,他们的考试竞争已经过于惨烈,导致出现了一种在高考分数上的“通货膨胀”。本来考试是用来判断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的工具,但长时段针对学生应考而开展的培训却扰乱了这一工具的作用。学生考试分数之所以高,可能并非其实际能力提高了,而是他们愈加适应这些考试形式,谙熟应对之道了。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江浙鲁豫等省从小学阶段就开始的针对考试开展的“抢跑”教育,这种教育抬高了分数线,却将孩子们的素质教育也给连带伤害了。就像看电影时,第一排的人忽然站了起来,为了看到电影,后面几排的人也被迫站起来。虽然电影还是那部电影,但看的人却不舒服了。而且还不能正常坐着看,否则就看不到银幕。这种“站着看电影”的状况,似乎就是教育发达省份中小学教育的写照。而且这种状况也在暗示:“抢跑”教育实际上是将本该在大学时代爆发的力量,提前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透支了,得不偿失。
就像学者石毓智所说的那样:“中国学生的学习是前紧后松,美国学生则是前松后紧,而读大学之时则是这‘松’和‘紧’的分水岭。”[10]学者张瑞香也提到:“中国学生的基本功很强,但创造性不够;美国学生绘画基本功弱,但创造性强。”[11]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中小学教育往往缺失了关键的一环:“创造性思维的培养”[12]。还有学者秦春华提到:“在美国课堂里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学生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诵什么东西。”结果美国小学生看似各方面低于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孩子,但思维被打开了。而美国也由此发展出一个奇特的模式:“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支撑起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所以他提出质疑:“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13]笔者认为,其实这就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孩子在中小学“抢跑教育”和“死记硬背至上主义”带来的恶果。我们总想着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但其实有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跨越性停顿”[14]。
笔者在江苏任教时不断与学生的接触后的直观感触是,来自江浙鲁豫等省的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存在显著的“透支性厌学”问题,此问题在孩子身上的不同也只是其程度有所差异而已。这些孩子从小在反人性的补习班和苛刻的父母的约束下被迫痛苦学习了这么多年,对刻苦学习早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他们把大学当成终于可以自由放纵的地方,有时间就看电影、玩网络游戏、四处溜达,甚至宁愿发呆都不想再投入学习。University,成了谐音中的“由你玩世界”。而这就是江浙鲁豫等省在中小学阶段“抢跑”,过度透支学生潜力的恶果。
第三,现在中国重点高校为了争夺一流的学科地位而对自身定位发生偏移。原本科研和教学是高校教学的两大关键基柱,但过度强调科研而轻视教学事实上已经成为大部分重点高校的日常状况。在措辞上有一定情绪化成分,但基本道出教师的现实困境:评职称看的都是科研成果,教学成果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全身投入教学,结局很可能是被“末位淘汰”,结果教师每天早上起床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申报国家课题和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从而满足学校的考核要求和评职称的标准,这样的状态下还能有多少心思投入本科教学上面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我们教育界现在的考核评价体系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一方面,片面重视学生的分数而非其全面发展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片面强调教师每年要发论文、报课题而非鼓励教师甘坐“冷板凳”在相应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地“深耕”。这两个问题交错在一起,就是今天各种教育浮躁的重要源头。如果不正视也不下力气扭转这种局面,可能在未来会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构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丘成桐先生曾提到,在美国顶尖大学,教授会跟本科学生有非常密切的互动,而在国内,这样的互动就很少,教师都是忙着做课题、写论文这些“立竿见影”的工作。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曾就一个数学猜想在中国办了一个讨论班,这个讨论班是开放式的,吸引了很多青年学者。但是后来有些参加的教授自己不想做了,因为他们考虑如果做这个事情,写文章时间就少了,而每一年写多少论文才是他们关心的,做这种费力的事情他们觉得划不来。
按道理,判断一个老师是否优秀,最关键的标准不是他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学术成就,而是他培养出了什么样的优秀人才。现在各个高校考核的都是教师中是否有一流的人才,但其实我们最应该关心的是这些高校能否为在学生中培养出一流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果一个高校聚集了非常多的教授,却培养不出相应的优秀毕业生,那这些教授本身的学术成就再高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如果现有批判教师的标准不变革,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三、真心关爱:呵护学生心灵的健康成长
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以心会心”式的教育理念,尝试从主体间性的层面尊重和爱护学生[15]。并且以一种满怀关爱的言说方式“修补”目前教育的缺失,真正以制度性的方式去关心孩子内心的需求[16]。有时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塞给自己的孩子,却没关心孩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有的学生通过“抢跑”的方式考上名牌大学,最后却发现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与这些学校的要求相匹配,结果自寻短见。可谓是“赢在起跑线,输在路程中”。他们的父母如果知道有如此后果,会不会宁愿自己的孩子平凡而开心地活着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孩子按照自己的生长节奏来自由舒展,而非要去竭尽全力复制别人的成功,按照别人的方式生活呢?
诚如学者胡春光所言:“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体验到自由时,他才能定义他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人才可能追求和构想那些善的、对的及神圣的目的。人只有在自由中,个体的精神才能获得自主发展和提升,情感才能获得不断丰富和拓展,个体才能把自己内在最好、最优秀的东西发挥出来。”“假如教师以某种教育方式摧残学生的自由,使学生自觉地放弃自己;假如教师以某种方式规限学生的精神成长,使学生不能成为自我的引导者;假如教师以某种名义阻碍了学生的自由选择,使学生不能表达自己的权利;假如教师灌输着一切的既定东西,使学生不能进行独立思考,那么,教师就毁灭了学生内在的实现自由的能力以及在自由实践中学习自由、实现自由的机会,教育就是在规训、塑模甚至是奴役。”所以教师必须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培养学生的积极自由理念和批判思维的建构者角色,真正呵护学生心灵的健康成长[17]。
笔者记得自己小学时放学回家,父母有时候会问我:“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些什么东西没有?”。而通常其他人的家长会问:“你今天测试(考试)考了多少分?”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现如今回头想起,才理解了父母的用意:成绩是外在之考评,能得到也可能失去;但学到的东西则是内化之技艺,它就像酿酒一样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散发出更为香醇的芬芳。知识内在化的速度要远比外在化来得慢,而知识只有经过内在化才能转化为见识,否则,正如人体摄入的营养不能转化为肌肉就会变成腹部脂肪,外在化的知识也只会成为一种精神拖累。
很多父母都抱着这样一种自我催眠的心理:孩子只有读好的学校才能有好的未来,而考上好大学需要读好高中,读好高中则需要读好初中,以此类推,连幼儿园入学都要设法挤进“最好的”一所。这种自我催眠就是“抢跑”的内在心理动因,这些父母是在以他们有限的见识去限制自己孩子的自由发展。就读“好学校”只是成功的原因之一而非全部,正如,今日政界商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都不是高考状元。
网上有篇文章中的一句话颇耐人寻味:“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几百年前殖民战争中土著部队很勇敢,但输掉了每一次战争,根本原因并不是武器落后,而是他们的行为太可预测了。”当你总是按照特定套路出牌并且被人摸清楚之后,败局差不多就已经定下了。无论是美洲土著、“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北洋海军,还是科举考试思维下的中国父母,走的都是同一路径。中国父母总想依据一条可预测的路径去安排子女的未来,而现实是,未来往往是不可预测的,有太多偶然因素在特定时刻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为什么总是成功的人一旦失败起来常会比经常失败的人败得还惨,因为长期的成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反过来会控制他的人生道路。毕竟,在特定路径上持续的成功会限制一个人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尝试新方法的意志和勇气。有时候失败是个好东西,它让人在急速冒进中停下来,避免步伐走得快于自己掌控的范围,更可以迫使自己痛定思痛,更深刻地洞悉自己的真实能力和周边世界的复杂微妙。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良好的判断力来源于经验,而经验则往往来自于错误的判断。”我们成功的高度往往跟遇到的挫折和失败的深度是成正比的,如果父母总是害怕自己子女失败,就相当于在“以爱之名”去剥夺孩子在挫折中自我优化、提升的契机,从而导致子女日后遭遇更大的挫折和失败。所以说,“自由不是教师的馈赠,也不是教育的恩赐,而是教育必须保障的权利,是必须实现的一种教育状态。”[18]P15只有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促进学生自我完善意识的教育,才是健康的好教育[19]。毕竟,只有通过不断的自由探索,孩子们才能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全方位的自然生长。
实际上,教育发达省份由于初等教育长期处于这种高强度的扭曲状态,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自我催眠和社会心理合法化的“集体记忆”,不但早已“见怪不怪”,而且觉得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正常”。以笔者接触到的许多家长为例,对于江苏这种近乎摧残儿童的教育方式,他们不是感到深恶痛绝,而反倒有些沾沾自喜,不但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这种病态教育状态的受害者,反而带着某种优越感地问我:“你看,江苏的小学教育比广西的先进不少吧?”不但是这些家长,几乎笔者所有的扬州朋友,都提到扬州的小学教育水准“相当高”。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个杯子就只能盛一个杯子的水,你就算倒一桶水进去,最后也只是能盛一杯水。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能够完全在轻松快乐下获得的成功,但是我们追求成功是为了让生活更轻松和快乐。如果某些看似荣耀的成功、名誉和地位只能给你带来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那么说明它们根本不适合你,所以不要也罢。同样,我们要让孩子追求“散步式”的成功,不要追求“掂着脚走路”的成功。如果成功非得一直痛苦地掂着脚走,那还不如就地休息,为走稳日后的漫漫长路积蓄力量。
四、结 语
加拿大学者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曾言:“教育变革的成败取决于教师的所思所为,事实就是如此简单,也是如此复杂。”[20]不过在中国语境下,主导教育变革的基本是负责顶层设计的管理层。顶层设计的科学化和合理化稍微推动一步,基层的进步就会大幅迈进一大截,反过来,如果顶层设计稍微出现一点问题,基层的问题就很可能会恶化。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我们必须优先思考的管理学问题。
笔者所举的关于当下教育的几点忧思案例,都涉及近些年积弊甚深的结构性问题,解决起来绝非一朝一夕的易事。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现在我们不认真正视这些正在发展中的问题,任由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就很可能日后对教育界造成更为深远的伤害。正如学者王建疆所言:“只有以人为本,关怀人的生命、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人文学科才能具有产生思想的土壤。”[21]倡导通过具体的科学化管理和人文关怀来积极面对大众化教育阶段出现的各种偏离教育本质的浮躁,呼唤有品格、有情怀的高等教育,笔者在本文所谈关于当下中国教育几点忧思的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