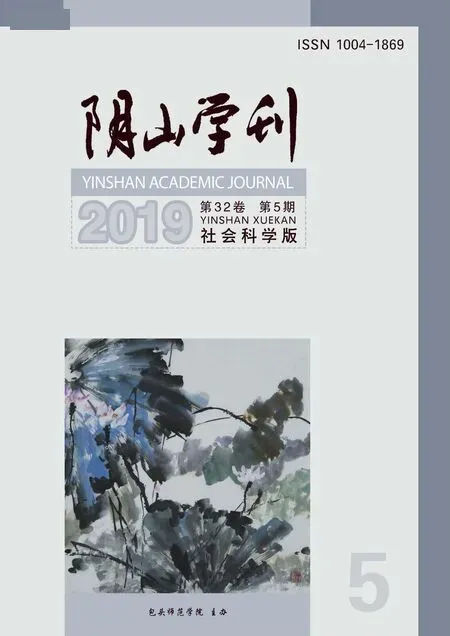试论元代北方草原文学的文化融合 *
2019-03-03温斌
温 斌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元代是中国古代多元文化交融、融合最为活跃的时期,疆域的无比辽阔、“两都制”的建立、儒家学说的逐步深入人心、传统“华夷之辨”等观念的逐步消解、多种宗教文化的并存共生,为元代文化交融奠定坚实土壤。文化融合深深影响并推进着北方草原文学对美的追求与实践,主要体现在文人创作队伍的民族融合、文学活动的民族融合、审美追求的文化融合等方面。
一是疆域的无比辽阔提供了地理意义上的有益条件。《元史·地理志·序》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代是中国古代又一个更为阔大、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其幅员辽阔堪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之最。元世祖忽必烈极其自信地说:“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1]所谓“四方未禀正朔之国,愿来臣服者,踵相蹑于道,十余年间,际天所覆,咸为一家,土宇之广,开辟以来未有也。”[2]文化的融合没有了地理意义上的制约。
二是“两都制”的建立,客观上为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滋养了肥沃土壤。成吉思汗曾对几个儿子说:“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占领国土。”[3]“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4]2553牧业极为重要,“出猎射生,纯肉食,少食饭,人好饮牛马奶酪。”[5]重牧贱农成为社会共识,直到元世祖即位才有了明显的改变,“世祖即位,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4]2354建立两都制就成为一重要举措,“逐幸上都,避暑于朔。虑畜牧之妨农,逐水草于广漠;”[6]一方面借两都巡幸保护蒙古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一方面体察民情、了解农桑之事。元人袁桷《龙虎台》一诗说“先皇雄略深,省方岁巡狩。翠华悬中天,问俗首耕耨。”[7]
三是儒家学说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元朝政治统治的核心思想。成吉思汗逐渐接受耶律楚材“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8]的正确观念,欣赏道教全真教丘处机“敬天爱民”“清心寡欲”的主张,为蒙古民族统治接受儒家思想奠定基础。到忽必烈时对儒学的接受就更为深厚、牢固。郝经曾说:“主上虽在潜邸,又符人望,而又以亲则尊,以德则厚,以功则大,以理则顺,爱养中国,宽仁爱人,乐贤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加以地广众盛,将猛兵强,神断威灵,…其为天下主无疑也。”[9]对忽必烈推行汉法极为赞同。而“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成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4]3771265年在颁发给日本的诏书中讲:“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4]4601所谓“元为中国帝,行中国事,其民为中国人,族为中国族。”[10]由此可见儒家“天下一统”、民族共存、皆为一体等观念的深入。
四是汉民族文士自觉为蒙元王朝服务,成为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交融史上的盛况。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只有耶律楚材、丘处机等契丹贵胄、方外人物受诏出仕,不能代表汉民族文士的主流,而至忽必烈时期,北方汉人的所有大儒、名士,如赵璧、王鄂、刘秉忠、张德辉、许衡、郝经、“一代宗匠”元好问、词赋状元王鄂等皆云集于世祖周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汉族文士集团,直接为大元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竭尽智慧、奔走呼号。他们从传统经学关于“道统”、“王统”、“正统”的漩涡中挣脱出来,践行一种知行合一、灵活调适的新的华夷价值体系。元代文人杨维桢曾说:“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吾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原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11]强调元朝亦是传统“道统”、“君统”一体实现的王朝。而郝经、许衡等则自觉认为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推崇、实践儒学,就是“正统”、“道统”之所在。所谓“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12]汉民族士大夫主动仕元逐渐蔚为大观,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交融也就愈加深入。
五是多种宗教文化的并存共生,使元代文化交融更加全面。萨满信仰是蒙古大元王朝国家宗教祭祀文化的核心,《元史·祭祀志一》说:“元与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玄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4]1781意味着萨满信仰依然是蒙古民族追念祖先、渴求自然之神佑助的主要宗教行为。《元史·祭祀志三》说“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4]1831同时,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也风行天下,“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4]4517一方面说明藏传佛教与萨满信仰的相近特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治意图,说明元代宗教实用主义的盛行。元人汪元量曾作诗说道:“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13]意味宗教的实用性、世俗性的极为突出,以至于《世界征服者史》讲到:“因为成吉思汗不信宗教,不崇拜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以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种宗教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14]各种宗教文化空间广阔,从而初步奠定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共生、发展的局面,对元代文化交融影响深远。
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北方草原文学的文化融合之花夺目绽放,主要体现在文人创作队伍的民族融合、文学活动的民族融合、审美追求的文化融合等方面。
首先是文人创作队伍的民族融合。客观地说,古代文学史自先秦滥觞以来,其创作主体始终是以汉民族文人为主,虽时有少数民族作品问世,但多为民歌或贵族阶层创作;只有延至元王朝,挺立于文学史上的少数民族文人队伍才真正形成。元人戴良在《丁鹤年诗集序》中坦言:“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成公廷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一是说在蒙古民族横扫西北大地过程中,西域地区的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等北方少数民族更早地融合于蒙古民族的浩荡洪流之中,均表现出对于汉民族传统文化、文学的特殊的喜好,“舍弓马而事诗书”,完成了由弓马之业而向诗书之好的华丽转身,成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二是讲他们并非偶然为之,而是倾心创作,使诗文成为他们生活的有机组成,成为构筑自我精神世界、展现人生价值追求的主要载体,“以诗名世”,成为元代文化建设、文学演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三是言西北少数民族文人在自觉不自觉汲取汉民族文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领风骚,自成一派,如清代顾嗣立所编《元诗选》初集二中所言:“要而论之,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並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达兼善、仍易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競秀。亦可谓極一时之盛者欤!”而这一少数民族文人与汉民族文人并驾齐驱、共同挥洒的美好景象的产生,实是文人相互切磋、交流融合的结果。
元朝少数民族文人主要由西而来,而蒙古民族西征的过程亦是与西域各民族接触、交融的过程,尤其是维吾尔民族的先民。翁独健先生曾说:“其中居住于别失八里、哈剌火州一带的畏兀儿人,由于最先归附蒙古,在蒙古西征中亚、南伐中原的征服活动中效力甚多,因此很受蒙元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畏兀儿人在元朝政治生活中颇为活跃。据《元史氏族表》的统计,畏兀儿人入仕元朝的竟达三十三族之多。至于畏兀儿首领亦都护及其家族,更被蒙古君主‘宠异冠诸国’。这个家族自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降附蒙古后,格外受到成吉思汗的优遇,被准许‘仍领其地及部民’,世世承袭亦都护之职。”[15]实际说明,蒙古民族的征伐,虽然本质上是军事征战、王朝建立,但客观上加剧了古代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西域多种民族在自身广泛交融的同时,伴随着蒙古铁骑的不断南下,与汉民族深度交融。元人王德渊对西域色目薛昂夫极其了解,在《薛昂夫诗集序》中深刻解读其姓氏名字的民族文化意蕴:“薛超吾字昂夫,其氏族为回鹘人,其名为蒙古人,其字为汉人。盖人之生世封域不同,瓜瓞绵亘,而能氏不忘祖,孝也。仕元朝水土之恩,名不忘国,忠也。读中夏模范之书,免牛马襟裾之诮,字不忘师,智也。”[12]18充分说明薛昂夫深受多民族文化浸润,因此其姓氏、名字有着诸般文化内涵。蒙古族诗人泰不华与汉族文人交往更是密集,与之唱和酬答的既有虞集、杨载等元代诗文领军文人,也有西域少数民族文人廼贤等。元人苏天爵高度赞美他的诗歌创作,曾在《题兼善尚书自书所作诗》一文中评价道:“白野尚书向居会稽,等宋山,泛曲水,日与高人羽客游。间偶遇佳纸妙笔,辄书所作歌诗以自适,清标雅韵,蔚有魏晋风度。”[16]说泰不华如汉民族文人一样,留连山水、投身自然,日渐形成诗书遣兴抒怀的文人习惯,全然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风神标格。廼贤是一位西域回族文人,在元代文坛上独占一席,他与南方文人过从甚密,曾拜汉族文人郑觉民为师,汉学修养极深;元著名学者黄溍说他“雅志高洁,不屑为科举利禄之文,平生之学悉资以为诗。”[17]凡此,均意味着元代文人创作队伍民族文化融合的深化。
其次是文学活动的融合极为活跃。纵览中国古代文学史,像元代这样有如此密集的多民族文学活动极为罕见,一是同一题材、对象的历时性咏唱,比如对于元上都的集中咏唱。由于两都制的确定,远在塞北草原的上都即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盟正蓝旗上都镇也成为元朝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每到夏天,皇帝巡幸,大批各族大臣、文人随驾扈从,在上都进行各种文学活动,产生了多部“上京纪行诗”诗集,如袁桷的《开平四集》、胡助的《上京纪行诗》、柳贯的《上京纪行诗》、周伯琦的《扈从集》、张昱的《辇下曲》、杨允孚的《滦京杂咏》等专集,其它还有大量的题咏上都题材的诗词歌赋,使上都成为元代北方草原的文化文学活动中心。二是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竞相举办各种文士雅集活动,成为极具文化融合特质的文学现象。比如西域色目高昌人廉希宪组织的廉相泉园文人聚会。廉希宪深受元世祖赏识,治理西北政事,经常舞文弄墨、四方交游,时人有“宾客填门惟慕德,诗书满架不知贫”[18]之语。清雍正《陕西通志》卷七十三《古迹》“廉相泉园”条目记载:“元至元中平章廉希宪行省陕右,爱秦中山水,逐于樊川杜曲林泉佳处葺治厅馆亭榭,导泉灌园,移植汉沔东洛奇花异卉,畦分碁布,松桧梅竹罗列成行,暇日同姚雪斋、许鲁斋、杨紫阳、商左山、前进士邳大用、来明之、郭周卿、张君美樽酒论文,弹琴煮茗,雅歌投壶,燕乐于此。教授李庭之为记,征西参军畸亭陈邃还题诗。”[19]陈邃还有《廉相泉园》一诗写道:“乱朵繁茎次第花,牡丹全盛动京华。红云一片春风好,便是山中宰相家。”描绘了廉希宪泉园牡丹盛开、分外喜人的情景。从中可见廉希宪与汉族文士交往繁密,对其文学创作影响较大。后来廉希宪到京城为官,廉氏家族的私家园林廉园又成为京城大都文人饮酒聚会的重要场所,即使是廉希宪去世之后,廉氏家族依然延续了这一文化传统。参加廉园文学活动的著名文人先后有王恽、姚燧、张养浩、袁桷、赵孟頫、卢挚、贯云石等,其中王恽、姚燧等皆为忽必烈重用之臣,张养浩、卢挚是元代汉族散曲大家,而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后裔,贯云石则是西域少数民族著名诗人。文人雅聚,必然会兴到意会、赋诗唱和,有力地促进了诗歌艺术的交流。王恽曾有《秋日宴廉园清露堂诗序》对此说明:“右相廉公奉诏分陕,七月初一宴集贤、翰林两院诸君留别,中斋有诗以记燕衎。因继严韵作二诗,奉平章相公一粲。时座间闻有后命,故诗中及之。”张养浩也多次提到廉园会聚一事,以《廉园秋日即事》《廉园会饮》《寒食游廉园》等以作纪念,其中《廉园会饮》写道:“倥傯常终岁,从容偶此闲。雾松遮老丑,雪石护苍顽。池小能容月,墙低不碍山。殷勤问沙鸟,肯与侧其间。”写游历京城最大私家园林胜景的感受。元代最著名的是南方汉族名士顾瑛主办的玉山文人雅集活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88曾有一段评论:“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于辋川、云溪。其宾客之佳,文词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虽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元末文人李祁《草堂名胜集序》记载了其中一次文人雅集的场景:“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来,与朝士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之焉,之则欢意浓浃。随兴所至,……列席赋诗,分题步韵,无间宾主。仙翁释子亦往往而在。”[20]7既有享誉文坛、画坛、书坛的汉民族名士杨惟桢、倪瓒、黄公望、朱珪等,又有元后期少数民族的杰出文人泰不华、聂镛等,可谓元代后期多民族文人文学交流活动的集中体现。参与过玉山雅集的元末文人郑元佑于《写萧元泰诗序后怀达兼善》一文中表达了对泰不华的思念:“尊师与予皆与白野达兼善公相友善,白野公为庸田使时,得玉山君诗读之,常欲扁舟访君界溪,未果,而除浙东师。安知公死于王事,忠义之烈,昭如日星。……援笔感念,为之慨然。”[20]273从郑文可知,玉山之所以吸引了如泰不华这样的名满天下的西域贵胄文人,除了山水之美的精心打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对于文学艺术的共同的喜好,慕诗而来、共同提高才是最主要的活动追求。即如被顾瑛称为“西夏郎官”的西域文人昂吉,生长于江南名山秀水,多次参与玉山雅集,顾瑛曾说昂吉“登戍子进士榜,受绍兴录事参军。多留吴中,时扁舟过余草堂。其为人廉谨寡言笑。非独述作可称,其行犹足尚也。”[21]顾瑛之说突出了以下两点,一是他作为元末名动江南的大名士,与昂吉交流频繁,对昂吉诗作和为人极为推崇;二是昂吉多次参与玉山雅会,诗文、行为等深深刻印在顾瑛头脑之中。大诗人杨惟桢在《送启文会试诗》称美昂吉为“西凉家世东瓯学,公子才名久擅场。”昂吉在《至正九年听雪斋诗集序》中记录了玉山雅集的一次盛况:“至正九年冬,余泛舟界溪,访玉山主人。时积雪在树,冻光户牖间,主人置酒宴客于听雪斋中,命二娃唱歌行酒。霰雪复作,夜气袭人,客有岸巾起舞唱《青天歌》,声如怒雷。于是众客乐甚,饮遂大醉。匡庐道士诚童子取雪水煮茶,主人具纸笔,以斋中春题分韵赋诗者十人,俾书成卷,各列姓名于左。是会十有二月望日也。”[20]279言语详尽,描绘出文人雅集的基本特点,饮酒赋诗交相而至,风度雅量、诗才高低,尽展才艺。蒙古族诗人聂镛也是玉山雅集的常客。他与杨惟桢交往极多,清人张其淦说:“茂宣自幼通经术,诗歌意气皆纵横。集中尤工小乐章,天锡音节同铿锵。乃识太拙生巧手,玉山铁崖尽心倾。”[22]茂宣是聂镛的字,清人所言指出聂镛汉学修养深厚,作诗意气纵横,极具萨都剌的风范,致使顾瑛、杨惟桢等拜服不已。聂镛也在《题可诗斋》说道:“久知顾况好清吟,结得茅斋深复深。千年再庚周大雅,无言能继汉遗音。竹声绕屋风如水,梅萼吹香雪满襟。何日扁舟载春酒,为君题句一登临。”[20]131首句以中唐大文豪顾况好诗惜才发语,将顾瑛玉山雅集提举自己与天下名流交游的感受加以表达,接着赞美杨惟桢诗歌直承风雅传统,深得汉唐遗韵之美。可见二人交流之深。
最后,是审美追求的多相交融。一是传统审美风尚与北方草原审美风尚的交融,二是南方地域审美风尚与北方草原审美风尚的交融,三是市民审美风尚与传统审美、草原审美的交融。同时,不同审美风尚交织一起,共同促进了元代文学美学追求的时代性演进。我们知道,从先秦至唐宋,中国古代文学始终以典雅庄重、沉健厚实的“雅风”“雅美”为主,“诗言志”“词缘情”“文明道”的印迹深刻而鲜明,文人自觉不自觉的遵循着儒家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原则。进入元代,由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日益深广,自然爽利、朴野通俗、豪壮有力的北方草原审美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审美格局。张晶先生在《辽金元诗歌史论》说道:“中国诗歌越来越圆熟,艺术表现也越来越细致,以至于圆熟得缺少生机,缺少那种朴野的生气,辽金元诗歌往往以自然朴野的气息,为诗中注入了新的生机,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诗人,也许正是还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完全汉化,也许是不肖于拘守某种诗学蹊径,也许正是那种豪放伉爽的民族性格决定他们以本色天然之语,朴野之风,给人以新鲜的审美感受,给诗坛带来了一股生新朴野的新活力。”[23]实际上,不仅诗歌,整个元代文学均受到北方草原审美文化的有力冲击。比如作为诗歌变体的散曲完成了古代诗歌真正意义上的返璞归真,明代学者王世贞《曲藻序》所言:“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原,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意味散曲出现与北方草原民族音乐文化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同时,随着北方草原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对歌舞特殊的喜好以及与歌舞并生的民族文化习性,直接导致了戏曲表演艺术的繁荣,带来了俗文艺的盛极一时,对豪壮勇力的草原英雄的崇拜、歌颂,对北方草原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追述、赞颂,对富有现实生活色彩的世俗之美的追求、表达,对传统礼教规约下所形成的人格道德的有力冲破、重建,对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文化范式的颠覆、重塑,对文学创作传统审美类型的重新审视和表现等等。从此,俗文学崛起而成为古代文学的主流。
地域文化在文学艺术中的渗透,先秦文学就初现端倪,《诗经·秦风》既有婉柔折曲的《蒹葭》的咏叹低吟,更有掷地有声的铿锵战歌。延至唐朝,北方草原特有的自然之美、戍边生活催生了大量以南人视野审视北方草原的边塞诗篇,南北地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交汇、深入。进入元朝,北人南下,南人北上,密集而频繁,促使元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交融之花竞相开放。从地域文化而言,南北各有其独特之美,梁启超曾说:“其在文学上,则千余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响,尤有彰明较著者,……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24]北人以气概为尚、南人以柔情为尊。刘师培针对中国南北地区的差异也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祟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5]
元代更是如此,北方少数民族文人均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北方草原民族特有的审美精神、审美情感。元世祖麾下大将伯颜的《奉使收江南》一诗,气魄宏壮、境界深阔,一个“收”字直写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北人征服精神,所谓“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全诗气吞天下、势压群雄,显现出北方蒙古草原民族昂扬奔放、豪勇无敌的积极进取精神;语言简洁明快、通俗质朴,表现出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审美倾向。贯云石虽然没有经历过祖先血雨腥风的战争洗礼,但崇尚孔武有力和好勇斗狠的民族精神深深流淌在血液之中;即使是感慨人生无常、时运不济的散曲之作,也一样回荡着草原男郎的壮美之态。《中吕醉高歌过·红绣鞋》唱道:“看别人鞍马上胡颜,叹自己如尘世污眼。英雄谁识男儿汉,岂肯向人行诉难?阳气盛冰消北岸,暮云遮日落西山,四时天气尚轮还。秦甘罗疾发禄,姜吕望晚登坛,迟和疾时运里攒。”叹世和归隐之曲往往充斥着哀怨、无奈,而在草原民族文人贯云石笔下,却激荡着一种郁勃不平、待时而起的乐观向上之志。北方草原民族“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生存环境的艰难和部落征战的频繁使草原民族生就果勇好战、豪放达观的心理特征,逐演化为一种昂扬不羁、自由奔腾之气。元人邓文原在《贯云石公文集序》说:“示所著诗若文,予读之尽编,而知公之才气英迈,信如先生所言,宜其词章驰骋上下,如天骥摆脱絷羁,一踔千里。”用天马行空来形容贯云石诗文的自由不拘、腾跃不已的风格特征。此外,贯云石长期生活于江南地区,耳濡目染皆为清婉香柔之象、低哝浅吟之语,但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性依然深深吸引着他,散曲《清江引·杂咏》中说“靠蒲团坐观古今书,赓和新诗句。浓煎凤髓茶,细割羊头肉。与江湖做些风月主。”意味着他依旧无法忘怀草原民族的浓郁风情,即使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渗透着草原男儿的民族本性。他经常捕捉富有江南文化意蕴的对象入诗,《蒲剑》一诗既香草美人、指事用典,又冷峭激荡、风起云涌,一种积压已久的奔腾力量之状:“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风斫碎一川波。长桥有影蛟龙惧,流水无声日夜磨。两岸带烟生杀气,五更弹雨和渔歌。秋来只恐西风恶,销尽锋棱恨转多。”蒲即菖蒲,是南方水草之地的花类植物,自古与水仙、菊花、荷花并称“花中四雅”,是古代文人墨客寄托情思的主要对象,而且往往与求仙访道、隐居湖泽相关。唐朝诗人张籍《寄菖蒲》曾说:“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节。仙人劝我食,令我头青面如雪。逢人寄君一绛囊,书中不得传此方。君能来作栖霞侣,与君同入丹玄乡。”突出的是炼丹求道、直入仙界,显现的是轻柔温婉的南地的情调。贯云石的诗却是刀光与柔情并生。太阿搅碎江水,“斫”字尽显北人之气概;江水两岸并非烟波浩渺、雾气朦胧,却是杀气弥漫、危机潜伏,密密麻麻的雨点在诗人的眼里演化为征战的枪林弹雨,而婉转渔歌声中深隐着深重不平之气。同样,西域诗人马祖常的诗风也体现了南北地域文化的交融。虞集说他“用意深刻,思致高远,亦自成一家。”[12]265意味其诗是北方草原刚健有力、雄浑质实之深蕴与江南温柔秀婉之美质的深度交融,形成了北方草原阳刚豪健而又不失江南清丽灵秀的交融之美的美学世界。马祖常熟谙江南“竹枝词”民歌的美学情韵,创作了多首“竹枝词”体诗歌,堪为南北文化交融的经典之作。比如《和王左司柳枝词十首》中的“春日烟雨秋日霜,麯尘丝织衫袖长。谁言折柳独送客,章台还堪系马缰”。“都门辇路花万株,塞垣苦寒多白榆。独怜柳枝弱袅袅,有情好写闺中书。”等。第一首折柳送别,却将江南烟雨与北方秋霜融为一体,把深挚柔婉的离情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柔情细语之中注入了些许北方草原的刚劲之气。第二首抒发闺中之情,但出语却以北方特有的孤寂苦寒来衬托南方花开遍野,使女子的相思之感随着袅袅摇摆的柳枝散发开来,从而产生了一种具有北人特有的力量之感。还有一首直写北人至南的生活感触:“北客到吴亦懊侬,苧衫蘭桨膏饰容。日食海错一百品,不敢上京来住冬。”先写北人来到南方,言语不通,不惯吴侬软语,多少有些懊恼之意。但是长时期历练,特别是每日海鲜品尝,让人大快朵颐,不由的已尽失北人风致,恐怕冬天也不敢来北方居住了。马祖常之“竹枝词”完全改变了唐人柳宗元以来的南方民歌的流利婉转之风,代之而来的是豪健自然之美的强力介入。元代后期廼贤的作品也是如此,他的《送吴月舟之湖州教授》一诗写道:“天涯作客少清欢,剪烛裁诗强自宽。江树莫云离思远,杏花春雨客怨寒。”表面上是送人之作,实际也是作者人生沦落之慨。与传统送别之诗相较,境界顿开,天涯之状使沉沦之思陡然开阔,一句“剪烛”不由使人想起浩渺的江南烟雨,而尾句的“杏花春雨”更是将人带入迷离深渺的楼台送别之中,从而使得诗情于缠绵悱恻中带有北国的寒意,一种峭拔峻冷之意随之散发。
戏曲也体现出鲜明的文化交融之美。女真族剧作家石君宝精心创作的杂剧《秋胡戏妻》就是多种审美文化交融凝结的艺术结晶。女主人公罗梅英既具有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妇德之美”“孝道之美”,又高度融合女真民族文化、蒙古民族文化等北方草原文化,其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发出了“整顿我妻纲”的人生誓言,充溢着摆脱依附男性、争取生存独立的女性光辉。传统女性或以死相拼、以死殉情、以死卫道,但本质上依附男性的社会属性并没有改变;而罗梅英“是比罗敷格外有力和刚毅的,她不仅和罗敷一样一再拒绝了男性的卑劣的诱引,并且还体现了一个能够独立生活,不受男性支配束缚的比较更坚强的女性性格。”[26]而蒙古民族剧作家杨景贤杂剧《西游记》中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有意张扬了冲破传统礼教观念的市民世俗化追求,对男女性爱大胆肯定,对宗教禁欲主义积极批判。对于封建女性的成长而言,禁锢灵魂、灭绝人性的最大力量无疑是“夫权”和“贞节”的文化制约,而《西游记》中的女性以其绝大的勇气不断冲击着这一腐朽文化制度对她们的束缚。女儿国国王面对唐僧以佛教中人的神圣感、使命感违心相拒和苦苦挣扎,大胆抱住唐僧,强行欢娱,显露出人性欲望的不可阻挡和宗教禁欲主义的虚伪乏力,呈现出市民壮大之后的对世俗文化之美积极追求的生活愿望。
总之,文化融合之风深刻而鲜明地体现在元代文学的各个方面,对于元代文学的别开生面、另有天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