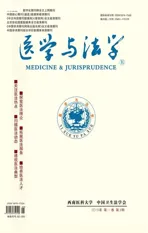论民法典之“生前预嘱”规定的基础与方式*
2019-03-03陶鑫明
陶鑫明
一、引论
随着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入,对生命的质量愈益珍视。而在患者生命末期,其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是其生理上的病痛,还包括其精神层面的痛苦感;在病情不可逆的前提下,其更加渴望得到的应该是程度更低的痛苦,而非由“无谓的努力”带来的生命维持。据统计,我国每年以千万计的死亡人数中,有近百万人伴随着剧烈疼痛而去世。[1]现实中,部分患者不堪忍受如此折磨,请求放弃维生技术生存治疗措施。如是请求可能是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主动要求,也可能是其家人请求,还可能是根据患者先前订立之相关指示,即“生前预嘱”。①2018年2月28日,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因心梗辞世,其生前与另一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罗点点一同创立“选择与尊严”网站。该网站后来发展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系全国唯一专门性“生前预嘱”推广机构。早在2017年,琼瑶即向社会公开其“生前预嘱”,不希望其在不得不离世之际,自己的躯壳被勉强留住并备受折磨。[2]随着这些“热点事件”的传播,“生前预嘱”为更多民众所知晓,其背后的“尊严死”理念亦渐渐获得人们理解。
我国法制对此专门规范尚付阙如,相关的实务亟待指引与规制。国外如美国加州、南澳州等地,皆有相应规范,允许自然人预先订立“生前预嘱”或类似文书,为其未来特定情况下的医疗措施作出预先指示。②2018年8月27-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以下简作《草案》),《草案》共六编,其中包括独立成编的人格权编,是社会关注之焦点。[3]《草案》相较于2017年6月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专家建议稿》(以下简作《专家建议稿》),删去了《专家建议稿》第八条。该条内容为放弃生命末期维生治疗规范,即“生前预嘱”条款,未被《草案》采纳,原因尚不清楚。③《草案》二审稿于第七百八十三条新增自然人有权维护生命尊严之表述,似能理解为“安乐死”与“尊严死”之规范基础,但仍需解释。
鉴于现实中已有“生前预嘱”出现,且具一定基础,故比较法上将之以法律形式固定,趋势明显,可资参酌。《民法总则》第一条写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涉及放弃生命之模式是否与宪法所倡两相抵牾?如有矛盾,原因何在?若存空间,如何入典?此一系列问题,皆待探究。当此民法典编纂关键时期,笔者拟对上列疑问展开讨论,权作抛砖引玉,以求智识支持,而助益法典完善。
二、生前预嘱与相关概念
“生前预嘱”(Living will)之概念尚无确切定义,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将其定义为“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其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其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可见,“生前预嘱”系关于医疗护理的指示性文件,其属预先医疗指示之一种。“预先医疗指示”概念可涵盖涉及医疗的全过程,不止于生命末期,甚至不关涉疾病,如生育行为等。[4]与“生前预嘱”相关的概念甚多,如“安乐死”“尊严死”“预先指示”“医疗预嘱”“安宁疗护”“缓和医疗”等,并在既有讨论中常被混用,如此不利于正确认识个中内涵、性质与功能。
(一)“安乐死”与“尊严死”
“安乐死”,指出于怜悯而造成或加速一个遭受不可治愈疾病或末期疾病(尤其是痛苦难耐的那种疾病)的人的死亡的行为。[5]其可分为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二者区分之标准在于执行人的行为方式。普通民众通常所理解的“安乐死”指的是积极安乐死,需要执行人通过积极作为达到结束患者生命之目的。正因如是行为架构,安乐死饱受争议,使人们在理解和接受上存有困难。让民法典直接“一步到位”规定安乐死条款,对于天然具有保守倾向的立法机关而言,并不现实。消极安乐死几乎等同于“尊严死”概念之所指,因患者此时多依赖于维生措施以维持生命,执行人撤出维生设备,患者便会因疾病死亡。[6]对于“尊严死”的界定,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多有尝试,多集中于刑法学界,如植木哲认为,“尊严死”即指治疗行为的中断,是患者自己作出决定,以停止无意义的治疗;[7]陈子平认为,“尊严死”系指对于没有恢复可能的末期病患,终止其延命医疗;[8]我国大陆地区权威的刑法学者张明楷教授认为,“尊严死”就是指撤除植物人维持生命装置的行为。④
“生前预嘱”即尊严死之重要文件形式。笔者认为,学界对安乐死进行类型化,有助于精细讨论个中问题,殊为必要;但较为务实的做法是将安乐死作最狭义理解,即“安乐死”仅指积极安乐死。首先,其与民众所理解与熟知的含义相契合;再者,若不加区分地一同提及,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混淆;最后,可在讨论尊严死问题时最大限度消解不必要的观念障碍。
(二)“生前预嘱”与“预先指示”
“预先指示”,即指预先医疗指示,是一种在未来欠缺意思表达能力或者无法交流时表明自己医疗意愿的声明,是一种法律文件。[9]预先指示可细分为指令型预先指示和代理型预先指示,后者是新发展出的一种指定替代医疗决策者的预先指示文件。[10]“生前预嘱”所指属于指令型预先指示。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预先指示,“生前预嘱”的特殊性表现在:在时间上,它是患者处于不可逆之疾病或生命末期时的有关指示;在内容上,它系关于维生措施(设备)需要与否的指示;在订立程序上,因其内容直接关乎生命,故较之其他阶段、内容的预先指示更为严格。此外,“预先指示”与“医疗预嘱”等提法并无实质差别。
(三)“安宁疗护”与“缓和医疗”
“安宁疗护”“缓和医疗”与“临终关怀”“舒缓治疗”“姑息治疗”“宁养照顾”等概念,究其本质并无差异,仅观察和描述角度不同而已。医学技术与理疗伦理的发展于20世纪初催生了如上概念,使“缓和医疗”之所指成为医学领域中的新兴的学科,“安宁疗护”之所指则更多系医疗服务层面的内容。世卫组织对于“缓和医疗”的定义为:一种提供给患有危及生命疾病之患者与家属的,旨在提高其生活质量及面对危机能力的系统方法,其通过早期识别痛苦、疼痛及严谨的评估和有效的管理,满足患者及家属所有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需求。⑤这一系列概念的核心在于:为处于生命末期之患者及家属提供系统的、旨在减轻患者生理以及患者与家属心理层面的痛苦的医疗服务。
(四)小结
作为医学领域的新兴领域,缓和医疗的勃兴反映出人文关怀的光芒开始照亮人的生命末期,使得人们能得以最小程度的痛苦度过生命的最后一程。缓和医疗包含尊严死这一方式,通过撤除处于生命末期患者的维生治疗措施,让患者不再忍受身心折磨地从容离去。自然人欲在生命末期实现尊严死,须订立生前预嘱。“生前预嘱”与尊严死的关系,即工具与目的、表现方式与支撑理念的关系,二者均可统摄入缓和医疗领域内。
三、“生前预嘱”的宪法出路
安乐死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争论,是因为其本身涉及到伦理道德这一极为复杂、又极度抽象的因素。考虑到生命之重要性、法律之权威性,学界对这一原本充满价值对立的问题更加争论不休;而从不承认安乐死,到部分国家立法予以严格规制,比较法上的态势似乎昭示着安乐死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及地区的承认与立法上的保护。然就我国而言,国内对此远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安乐死无法获得合宪性基础,其脱离了现代宪法价值。[11]
相较于安乐死立法上的严峻态势,尊严死立法在比较法上更加乐观,立法明确尊严死方式的国家及地区远超安乐死。我国学者对于尊严死立法的讨论,纵有分歧,但主流观业已渐成,认为应予以立法规范之。就实务而言,尊严死的实务也远多于安乐死的实务。综而观之,尊严死的立法极有可能,然学者论述却多基于现实需要或既有实务,似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立法进程必经合宪性检验,学界对此亦几近集体失语。尊严死能否找寻宪法上出路?本文欲求之。
(一)我国《宪法》与生命权
比较宪法上,五分之四左右的主权国家以各种形式规定了生命权,足见世界潮流。[12]我国《宪法》文本并无关于生命权之表述,但切不可由此便当然地以为我国《宪法》未规定生命权,更不可得出我国不保护生命权之荒谬结论。自宪法解释学角度,可通过《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之表述或第三十七条“人身自由”条款,推定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属性;[13]或是通过自然法精神,使生命权归入宪法“非真正未列举权利”中去,比如《刑法》《行政法》等法律对于人民生命的保护规范足以见得宪法实质上的生命权对立法的要求。
宪法规定生命权,是生命权保护的宪法判断准据,为生命权的保护提供了立法依据与解释根据。[14]故此,民法典能否规定“生前预嘱”条款,首要判断的是:“生前预嘱”所执行的尊严死是否构成对生命权之侵害?其次,在事实层面,执行“生前预嘱”必然对生命造成损害当无疑问,然此一行为就得受非难么?解决上述问题,需对生命权进行简要考察。
(二)何为生命权
宪法视生命权为一基本权利,民法将其视为最重要之具体人格权;而人格权系兼具宪法权利与私法权利之性质的双重权利。[15]生命权在法学内部不同学科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生命权必然包含维护生命安全之内容,此为生命权作为绝对权而言的对世性特征,国家、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生命权。生命权中多有争议的内容,在于其是否包含支配权能;对此问题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对待安乐死、尊严死、自杀的态度。
赞同生命权具有支配权能的观点认为,自然人得就生命利益享有优先的支配权,并以献身与安乐死为例来予以说明。[16]相关观点否认这一看法,并就该二为进来予行反驳,认为所谓的献身仅仅系事实层面上的,法律对此至少是难以评价的,更不可能将其作为一种权利看待;自杀与安乐死问题则属于违法与合法之外的第三种状态,即法外空间。[17]
笔者认为,应肯定生命权具有支配权能,但其支配限度应有法律严格限定。赞同生命权支配权能的学者亦主张支配的范围、限度、程序必须严格限于法律规定内;对于权利的认识不宜囿于纯粹的价值判断,还应着眼于时代的发展与现实的需求。生命价值的重要性使得人们谈及生命时变得格外小心、谨慎,甚至畏手畏脚,这体现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敬畏与珍惜。人们对于生命的额外关注,往往集中于出生与死亡这两个时间段;这二者分别对应生命的诞生与消逝,其中间过程的生命系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便有生变故,生命也瞬时倾向于消逝一侧。对于生命的诞生,关注焦点在于胚胎、胎儿之上,包括胚胎性质与地位、胎儿利益之保护、代孕行为的认识以及堕胎行为之规制。就生命的消逝而言,涉及自然人主观意愿与生命客观逝去的行为与事物都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如自杀、安乐死等。如此种种,皆因科技之发展而引发法律对其反思、思考:如何在规范层面进行规制?解释论为宜或立法论更佳?面对新问题,解释与立法均要历经来自伦理、道德的检验,即所提出的方案是否契合社会大多数人的观念,是否具有可接受性。以人体胚胎为例,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体胚胎冷冻保存成为可能,商业利用也就随之渐次展开。就此所生问题甚多,比如冷冻胚胎在性质上是否为纯粹之物?如此解释是否是对时下生命关怀思潮的背离?正如爱尔兰最高法院所言,人体胚胎具有“道德地位”。⑥故相应的讨论自然不可能跳脱时代的潮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审视人体胚胎问题便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人体胚胎的所有者可否是同性恋伴侣或夫妇?或者说,人体胚胎成为胎儿、自然人后,同性恋伴侣或夫妇能否成为其父母?随着人们的认识和观念不断深入和解放,牵涉传统与时代道德伦理,相互碰撞的问题聚合在一起,纯粹的价值判断此时显得更加无能为力。若一国或地区范围内的科学性的实证计划可付诸实践,并得到全面、真实的实证资料,或许可成为解决此类问题最有力之注脚,故此事之难易可见一斑。
对于生命及生命权的理解同样如此。今天人们对于生命的理解仍然承继着近代以降人文主义的遗风,对生命十分珍视。可以获得普遍共识的是,人们对于生物生命之外的生命内涵亦着眼甚多。多有学者论证,人之主体地位系于精神层面之生命,否则法律意义上的主客体区分不具有什么实质意义。[18]生命的层次与意蕴逐渐区分清晰,精神层面的生命逐渐越过生物生命,为现代人们所主要关注。作为人格权的生命权,其根本在于生命权上的精神利益。难以计数的言论、思想,都表明生命的质量为生命价值所在,亦即生命的长度不再是生命价值的唯一度量。在此意义而言,献身行为确可如上评价。生命权的保护应自绝对化模式渐渐转向双轨制模式,以正视精神生命的地位。[19]而生命绝对至上的伦理原则,如今不应固守,那些出于好意而担心精神生命权为人滥用的人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良好的立法技术与技巧足以弥补,这需要立法过程中各方协力。
利益系权利之目的。生命利益的考量如矩形面积之计算:生命长度与生命宽度之积。所谓生命之宽度,即可理解为自我对于生命历程之满足。生命权保障权利人得享有生命利益,若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遭受着剧烈的生理疼痛与心理煎熬,患者选择安乐死结束生命也好,选择尊严死与安宁疗护这一方式自然逝去也罢,都是患者基于自己所享有的生命利益支配所带来的。其实,即使是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在其余下论述中也不自觉地向着承认生命权之支配权能靠拢。如认为安乐死与生命本体价值相冲突的学者也承认,在提到尊严死时“谈及尊重人的自我决定权还是必要的”;再如,有的学者仅认为在名称上不宜称“支配”,而应为“自主”,但内容无实质差别。[20]“生命权并不意味着人有“生存的义务”,而人格尊严意味着人不仅要有尊严地活着,而且还要有尊严地死亡。”[21]这实际上也是生命权行使方式之一种。生命教育,特别是死亡教育对于国民而言仍然匮乏,其实施是社会共同之责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22]
(三)“生前预嘱”与侵害生命权
尊严死适用的前提是患者罹患现代医学认为不可治愈之疾病。死亡只是时间问题,尊严死并非剥夺患者生命权。⑦生命末期的患者承受着病魔带来的巨大生理疼痛,长期以往磨耗精神。巨额的医疗开销也对患者造成精神压力,患者甚至可能心生对家庭的愧疚。维生治疗对于患者的形象也是一种破坏,患者可能对此感到有失尊严。在此情形下,患者选择撤除维生措施以尊严死,当无伦理困境,亦符合医疗伦理四原则。
从本质上说,尊严死体现的是患者医疗自主权的结果。[23]患者的医疗自主权以一般人格权作为支撑,是生命权在医疗领域的体现。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医疗自主权的应有之义,因为患者对于自身病情当然地拥有知情权。在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情、医生的诊断意见、治疗方案及风险的基础上,患者对某种医疗措施拥有同意与否的权利。患者此项权利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预先指示。触发尊严死执行的生前预嘱本身即是针对不可逆转疾病而订立的,意在表明订立人对于病情、治疗效果已有清楚认识。换言之,生前预嘱本身就是订立人对于进入生命末期后,对医疗措施的选择作出的理性决定。从某种角度上说,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被提前行使,欲达之效为书面形式所固定。是故,生前预嘱的订立系患者自身权利行使之产物,尊严死的执行是对生前预嘱的执行,患者的医疗自主权是尊严死的法理基础所在。可以明确的是,“生前预嘱的订立人侵害自己的生命权”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在一起案件中,被告家属遭车祸入院,经治疗后无好转迹象,医院向被告送达病危通知书,后被告决定放弃手术。原告保险公司认为,被告家属的死亡系被告主动放弃治疗所致,不应赔付。法院认为,被告此举实属无奈,并无任何过错。⑧此案中,法院认可家属的代为放弃治疗行为,则患者本人的明确意思表示或者可得推知的意思表示当然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医生或其他执行生前预嘱的主体(以下简称“执行主体”)是否构成侵害生命权呢?执行主体参照生前预嘱,撤除患者的维生措施,患者因此提前死亡,貌似患者的生命因此遭受侵害,成立生命权侵权,但实则不然。撤除维生措施与生命权遭受侵害之间并无因果关系,而是罹患无法治愈之疾病导致生命权侵害。⑨实务中,多有患者处于无医疗决定能力时,家属代为放弃维生治疗。如在一起案件中,患者家属已在《要求终止维持生命支持治疗同意书》中签字,要求放弃某些抢救措施。⑩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多认为,患者的死亡与家属的放弃治疗决定和医疗机构的执行行为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指令型生前预嘱目前并未见诸于我国司法实践。只能说,执行主体的行为导致了患者死亡时间的提前。然如上所述,生前预嘱本身即患者对于此种特殊情形下医疗措施的预先指示,表明了患者对于生命利益的支配,对于相应的后果也有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外化为生前预嘱的文本,体现了患者对于自身生命利益的支配,执行主体依此行为,是对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尊重。退言之,执行主体若不据此执行,对于患者的合法权益亦为侵害,执行主体于此陷入两难境地,无论作为与不作为,均为侵权,显然不合理。至于执行主体在判断患者是否进入生前预嘱所确立的触发标准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进而错误地执行或不执行生前预嘱,则涉及到违反生前预嘱的责任问题。在家属代为决定放弃维生治疗的情形时,所涉问题在于患者缺乏医疗决定能力时的行为规制与责任分配。原则上,有权代为决定者,应遵循替代判断标准与最佳利益标准。
(四)小结
我国虽在宪法文本上未见有关于生命权之表述,但生命权的宪法保护不言自明。尊严死这一涉及人之性命的模式必须经合宪性考察。在时代的背景下,生命权的内涵包括有限的生命利益支配,尊严死以其与患者自主决定权作为支撑,在宪法与民法上都存有空间。作为尊严死的重要文本,生前预嘱的订立与执行均不构成对于生命权的侵害。是故,尊严死可得合宪性考验,具有民法基础,作为尊严死之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的生前预嘱无法理上障碍。
四、“生前预嘱”入典之路径
(一)比较法考察
拒绝医疗权在美国最早是通过Schloendorff v.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案确立的,并随着医疗技术,特别是抢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此项权利是否能在那些不施予治疗将会导致死亡的情况行使的疑惑。世界上第一部明文规定生前预嘱的法规为美国加州的《自然死亡法案》,于1976年通过,作为《加利福利亚健康安全法》的一部分。随后,美国部分州相继在州法律层面认可这一制度。至1990年Cruzan v.Director.Missouri Department of Health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可患者拒绝卫生医疗权为宪法之基本权利。一年后,美国联邦通过《联邦患者自决法案》,统一了各州对于生前预嘱不尽相同的规定。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蒙大拿州甚至规定了安乐死条款。由此可见,在美国,生前预嘱的规范基础发端于判例确立的拒绝医疗权,后由各州根据情况进行立法,多以专门法案形式规定;联邦层面上也以专门法案的形式对患者医疗自决进行规定,其中包括生前预嘱制度。
同以专门法形式规制的还有奥地利,其有专门的《生前预嘱法》,并在民法典中规定了代理型预先指示。这种模式是将指令型预先指示与代理型预先指示分别规定,后者为民法中监护、代理制度所吸收。新加坡于1996年制定了《预先医疗指示法》,南澳州也有相应的《自然死亡法》。韩国在2009年就已于个案中批准“尊严死”,其更是在2018年开始试行《尊严死法》。[24]
瑞士则在其民法典中规定了预先指示,但与奥地利的规定不同,瑞士民法典中同时规定了指令型预先指示和代理型预先指示。
由此可见,比较法上多以专门法形式规制生前预嘱。这主要是因为生前预嘱同时涉及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的问题,并以后者为主。生前预嘱的完整规范应包括:生前预嘱的定义;订立主体、条件、形式与程序;文本的更新、公证;生前预嘱的执行标准、判断程序;执行程序;生前预嘱的撤回与撤销;违反生前预嘱之责任等。如是,专门法方有充足容量,以免有所遗漏。
(二)我国的立法倡导
我国法制中,检索关涉尊严死的规范,仅寻得《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后半句关于患者近亲属的同意权以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关于无法取得患者或其家属意见时治疗方案选择的规定。二者均未直接指向患者自己的医疗决定权,尤其是直接决定生死存亡的医疗措施的决定权。我国曾有政协委员多次提出议案,建议制定相关的“自然死亡法”,以对渐渐发展的生前预嘱实践进行规范层面的规制,但可惜的是均无下文。[25]学界也有同样主张。[26]
由龙卫球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则编》草案建议稿在其第三节“自然人”的监护中,用三个条文(第六十至六十二条)规定了患者的预先指示。⑪有学者结合《民法总则》关于意定监护的规定,认为意定监护制度可为尊严死提供制度保障。[27]《专家建议稿》第八条更是直接规定了生前预嘱条款。此类建议与瑞士法模式相似,主张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综合分析
如前所述,生前预嘱的完整规制需要足够容量,以专门法形式规定可满足如此要求。完全由一国之民法典规定,必然会有损立法之简洁,且特殊问题若都纳入民法典中,法典体系与内在逻辑必然被破坏,因此不宜全盘由民法典承揽此项任务。我国《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3月15日正式颁布,其中在监护的部分,并未规定患者的预先指示。未来民法典最终出台若能采纳增补患者预先指示的规定,则可谓一步到位,不但对生前预嘱进行规定,也完善了患者医疗决定权制度。但这一期待似乎不易实现,《民法总则》未来入典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改变。
在制定特别法的路径上,我国曾有政协委员提出议案,但最后无疾而终,既有资料难以探寻个中缘由。笔者认为,立法者可能会考虑到生前预嘱及尊严死理念在我国虽有部分实践,但尚未为广大群众所认知与接受的事实,贸然推出关于尊严死的特别法或条例,恐会让人不知所以。在缺乏广泛认知基础的情况下推出,存在一定的危险。加之学界对此并无太多关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介绍缺乏本土化转化,立法的智识资源不足以支撑全面规定生前预嘱。
笔者认为,当此民法典编纂之际,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考虑到我国已有的生前预嘱实践,宜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之生命权部分规定生前预嘱条款,为现有实践或了解后欲实践的人们提供规范保护。待学界讨论充足,时机成熟时,再制定“生前预嘱条例”或“自然死亡法”以全面规制。如此建议,理由如下:
第一,民法典的时代使命与特色要求民法典关注生前预嘱的问题。“我们的民法典应当充分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真正体现法典与时俱进的品格。”从世界范围来看,安乐死的技术与讨论的展开不过百年之间,生前预嘱之提出亦六十余年,世界各国纷纷就此进行法律上的回应,以跟上实践发展之步伐,维护其中各方权益。我国的生前预嘱实践自新世纪以来逐渐扩展,目前可得统计的已达数万,尚有大多难以统计之例。人民对于生命的看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好死不如赖活”。社会风气渐开,人们能够接受生命末期放弃维生治疗,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减少痛苦,安然离去。这是时代发展造成的思想解放,系当今时代特色在人们观念上的反应。民法典对此必须予以关注。
第二,民法典作为公民权利宣言书,对于生前预嘱的实践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诚然,对于生前预嘱的订立与执行,不少人仍心存顾虑。尤其是对于执行主体而言,担心若可能因此而需承担法律责任,从而逃避或拒绝执行,使得患者意愿难以落实。我国民法典突出对人身关系的调整,一改“成熟民法典”的通病,提高了对于人身关系的保护。生前预嘱规定入民法典中,是这一改变的体现。对于人民而言,其可有规范依据展开实践。原本颇为担心的执行主体在此“宣言书”上,也可获得勇于执行的支持。这对于生前预嘱实践的进一步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这一立法体例为生前预嘱条款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参酌比较法经验与学界讨论可知,若单纯由民法典总则编的监护或代理部分中规定生前预嘱条款,则其必然属于代理型预先指示,相对我国现行相关规范而言,只不过是由条例、单行立法中转移到法典中,并无太大实益。若在此基础上,于“自然人”部分中专门规定指令型预先指示,则与代理型预先指示一起可完成逻辑周延的规制,但这样预先指示的条款被分拆为二,分置于不同章节之中,找法存有一定障碍,且零星式的规定不利于法典条文的精简。若完善侵权责任编关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规定,则不能从正面规定患者可得实施何种行为,而是需要通过解释,在法典编纂之际,这样的安排是不经济的。
就目前来看,我国民法典最大的优势与特色在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生前预嘱条款放入人格权编“生命权”部分最为恰当。一方面,生命权的内容包含生命利益的有限支配,生前预嘱之功用正是在于为生命末期患者的生命利益支配作形式固定。另一方面,人格权编能够最直接和全面保护人的尊严。生前预嘱的基础在于人之尊严的维护,其与人格权编存在的基础一致,都是为了保护人的尊严。人格权编的规范围绕着人格尊严展开,有生前预嘱条文的编纂基础,且独立成编的人格权编有此容量规定之。《草案》目前关于生命权的规定宣誓性过强,应予以细化。[28]
第四,人格权编要求对人格权的积极权能进行规定。人格权法作为权利法,必然要求对于人格权确认以及积极利用作出规定。恰如精神性人格权中的姓名权、肖像权可为积极利用般,作为物质性人格权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亦可为积极利用。此虽在学理上有所争议,但实践已经有力地佐证了物质性人格要素的积极利用,无须过多纠结。在生命权上,积极利用之例即是安乐死。但诚如所言,安乐死所牵涉之争议目前尚无定论,比较法支撑也难谓有力,着实不宜纳入我国民法典中。但尊严死之方式已如前文所论述,可寻得宪法上的出路,具有民法与实践的基础,可得入典。虽然在表现上有所差异,但尊严死亦体现了自然人对于生命末期生命利益的有限支配,是积极利用之表现。
具体的规范设计上,《专家建议稿》第八条以及四川大学法学院的陈界融教授在其设计的人格权编建议稿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特殊病人拒绝维生医疗权和临终关怀”条文可资借鉴:自然人身患绝症不能治愈或年事已高,生活不能自理,继续生存将遭受极度痛苦,经本人书面请求,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不少于十五人的、由医学、伦理学、法学专家和社会贤达人士参加的听证,认为申请人确属不可治愈或生理极度痛苦的、终止生命符合医学伦理和法律规定的程序的,可以采用人道的方式结束生命。
未来我国应以特别法形式,特别是从订立程序以及代理决定两方面,详尽规定生前预嘱。对于违反生前预嘱的责任,涉及的痛苦延长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延命期间的医疗费用、违反医疗合同约定之违约责任等问题皆可在现行侵权法与合同法规范下得到解决。
笔者建议可在第七百六十八条后增加一条生前预嘱条款,条文及理由如下:
基于维护自然人人格尊严的需要,自然人可订立书面生前预嘱,指明在罹患不可治愈疾病且死亡在近期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接受或拒绝维持生命治疗。
自然人进入前款临床条件且缺乏医疗决定能力时,其家属可代为决定接受或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但不得违背该自然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
判断自然人是否进入其生前预嘱确定的临床条件,需两名或以上医师共同诊断并达成一致意见。
如此规定的考虑在于:首先,本条不可能事无巨细将所有关涉生前预嘱订立、执行、违反责任的事项全盘规定,仅就生前预嘱订立目的、形式、内容、特殊情况下的家属代理以及执行生前预嘱的必经判断程序等较为关键的事项作出规定。其次,本条第一款的表述在于宣示自然人有权就自己于特定情形的维生治疗作出预先安排,第二款则补充了特殊情况下的家属代理情形。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条最后一款仅就判断是否可执行生前预嘱的程序作出三项限制:一是数量上,至少为两名医师;二是参与诊断的必须是获得执业资格之医师;三是参与诊断的医师需达成一致意见。但实际上,对于第二项限制是否恰当,本文难以给出明确回答,因为只要获得执业资格者,均为“医师”。易言之,在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完成相关要求的实习或规培后即成为医师,但如此便可参与如是诊断,就非专业人士而言恐存有接受上的困难。笔者认为,是否应考虑给予一定限制较为妥适?如工作经验满五年,或具有正高职称的医师等。毕竟对于旁人,尤其是非专业人士的患者近亲属而言,让一个取得医师资格不久的人来参与关乎维生治疗撤除与否的诊断,难以接受。具体的限制,应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医学界,特别是缓和医疗领域的专家之意见。
五、余论
在强调人格尊严维护的今天,我们应将目光触及生命的最后一瞬,为维护患者必要的生活质量作出努力。这不但有赖于医疗科学的发展,还对制度保护提出了要求。缓和医疗的勃兴在医学教育上有所反应和显现,越来越多的医学院相继开展舒缓医疗、生命教育课程。以往,医生可能会因患者的逝去而感受到挫折感,自我价值遭到怀疑,而生前预嘱的出现可缓和这一现象,帮助医生在职业伦理上减轻压力。我国对于生命法学的关注尚不足以为这些新发展的生命领域之实践提供足够的智识支持。未来生命法学的发展应是光明的,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欣喜的是,无论是宪法学界对于生命权的关注和系统研究,还是生命法学的勃兴,都在昭示着我国法制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
强调人文关怀的我国民法典应对此应予关注,体现对患者自主选择的尊重,彰显法律在更大程度上许可个人决定其命运的态度;让患者选择以具有尊严和体面的方式离世,确保在其生命的全部过程中充分享有尊严,同时对于患者一方经济压力的缓解以及社会公共医疗资源的优先利用都具有积极意义。再者,饱受争议的人格权编更应在具体条文和制度上拾漏补缺,完善现有规范,充分体现人格权编尊重和维护人格尊严的基本价值,无愧于时代赋予之使命。
注释
①本文作者曾于2018年7月前往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进行调研,协会工作人员称,目前已有约三万余人完成生前预嘱的订立。
②美国加州议会于1976年通过《自然死亡法案》,1983年南澳洲通过《自然死亡法》;除此之外,荷兰,英国,比利时,新加坡,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均有相关立法,日本则通过判例承认之。
③该条规定“基于维护自然人人格尊严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自然人可以自主决定放弃救治,但实施该行为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④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学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187页。除此之外,日本学者甲斐克则、大冢仁、曾根威彦,中国学者李惠、黄丁全、倪正茂等对此亦有论述,难以一一展开。
⑤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Definition of Palliative Care[EB/OL].网 址 :http://www.who.int/cancer/palliative/definition/en/#,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22日。
⑥Roche v Roche[2009]IESC 82(Sup Ct(Irl)),para.38,per.Hardiman J.
⑦可以预料的一种反驳是:死亡是人之必然,无论人系健康或患病,自然死亡与外在因素介入加速死亡的时间差也不应被人为破坏。本文认为,必须要考虑到尊严死的适用前提,即如此疾病使得患者是如此地接近死亡,且不论通过指令型或代理型预先指示(生前预嘱),其意思效果皆出于患者。
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292号民事判决书。
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10251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2489号民事判决书。
⑩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6)青0103民初2046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例可见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4)运民初字第352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6415号民事判决书。
⑪北航法学院课题组(龙卫球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则编》草案建议稿,网址:http://www.fxcxw.org/index.php/home/xuejie/artindex/id/959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22日。其中第六十条规定:完全行为能力可以预先作出医疗决定,明确在其丧失或部分丧失判断能力时同意或拒绝的特定医疗措施。此项医疗决定在该成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判断能力且应当实施特定的医疗措施时生效。自然人也可以委托他人在其丧失或部分丧失判断能力时为自己作出医疗决定,在此也可以要求受托人遵从其预先作出的医疗决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该委托合同自委托人丧失或部分丧失判断能力时生效。前款的受托人不能是对委托人进行治疗的医疗机构的经营者、医生或其他雇员,但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婚姻、收养或血缘关系的除外。第六十一条规定:患者预先指示和任意监护委托协议都须以书面的形式作出,并且要签名、注明年月日。没有采用书面形式的患者预先指示,也应当作为负责治疗的医生作出决定的考量因素。患者预先指示可以任意撤回,不必采取前款规定的书面形式。第六十二条规定:负责治疗的医生应当遵从患者的预先指示,除非该指示违反了法律的强行性规定,或者可以合理怀疑非出于患者的自愿或仍然符合患者被推定的当前意思。负责治疗的医生也应当遵从患者受托人作出的医疗决定,除非该医疗决定违反了法律的强行性规定。患者被推定的当前意思,应当结合患者当前的病情、患者作出预先指示以后的医疗技术的实质性发展、患者自身宗教信仰等价值观的变化等因素综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