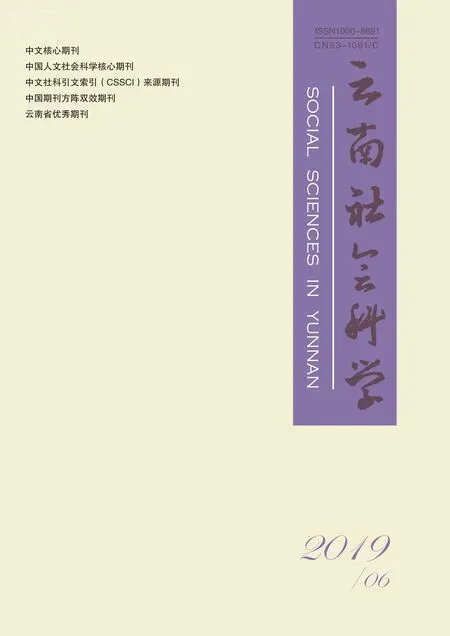唐赋的叙事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
2019-03-03周兴泰
周兴泰 王 萍
明代李梦阳、何景明、胡应麟等复古派文人主张“唐无赋”说①李梦阳曰:“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骚赋于唐汉之上。”(《潜虬山人记》)何景明曰:“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何子·杂言》)胡应麟曰:“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诗薮·内编》),实乃其祖骚宗汉心态之反映。他们因批判律赋而否定所有体裁的唐赋作品,观点未免过于偏激。其实,细察《文苑英华》与《全唐文》,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唐不仅有赋,而且数量繁多、众体皆备、优秀之作频见。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就从文体演变的角度,对唐赋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推崇备至:“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昌其盈矣。”②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这一评价客观来看是较为允当的。
众所周知,中国人擅于抒情,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深远悠长。但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看,叙事与文学也存在紧密联系,由此形成了与抒情传统并行的叙事传统。赋体虽旧,但唐人也尝试用它来叙事,这与唐人喜用传奇体写小说有关。将唐赋放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总体视阈下进行观照,它取得了突出的叙事成就,并对后世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自觉的虚构意识:人的叙事能力的日趋成熟
辞赋文学的一大重要特征就在于,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虚构人物、故事与场景,由此体现出鲜明的叙事性。如宋玉《风赋》、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曹植《洛神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等,无不如此。郭绍虞先生曾这样说过:“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而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①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7页。他是把赋看作由诗歌而到小说的中间环节的,而赋“为小说之滥觞”的观点,指明了赋在虚构性这点上与小说之间的深厚渊源。
在继承前代赋虚构叙事的良好传统的基础上,唐代赋家往往从史事、神话、寓言、传说中取材,并进行一番新的重述与铺衍。这些素材多是简洁的记录,较少在细节处进行敷采描摹,但唐代赋家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让素材中的故事和人物先在自己的脑海中活跃起来,然后形诸文字,生发出丰富的情节,渲染出精彩的场景,刻画出鲜活的人物,从而彰显出虚构叙事的特性。唐赋作品由单纯实录到加以虚构的转变,充分反映了人的叙事思维与叙事能力的进步,也是小说文体得以产生并最终走向独立的一大关键。
唐人独孤授作有《斩蛟夺宝剑赋》,其事出自《吕氏春秋》:“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还反涉江,至于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非谓舟人曰:‘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见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宝剑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弃剑以全己,余奚爱焉? ’于是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②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恃君览第八》,北京: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346页。故事情节简单,人物语言质朴。独孤绶以律赋形式重述此事,想象新颖,文采斐然:
乃言曰:“彼亦奚逃?徒为汝劳。冲黭黮以天暝,蹙嵯峨而浪高。徒观夫鼎尔腾沸,雷然怒号。虽欲穀其口,牙其刀,抗尔以千艘;踣若质,流若膏,尔能伤予之一毛?既激气于烟景,忽碎尔于灵涛!”
其特色主要有二:一是面对气势汹汹的蛟龙,作者专门为佽飞设计了这段独白,与原故事佽飞与舟人的对话大异其趣。二是语言掷地有声又生动幽默。佽飞不但未被蛟龙的气焰吓倒,反而对蛟龙说你往哪里逃,你逃跑亦是徒劳,我甚至要扒你的皮,吃你的肉,你能伤我乎?表现出佽飞的镇定勇敢与满怀豪情。接着赋文从正面铺叙佽飞斩蛟之场景:
及其沸渭砰訇,风号雷惊。骧首如玄云阻色,腾眸而白日韬精。须臾勇气励,神机生。拂首摧爪,奋喉裂缨。方澒洞于重险,已支离于浚瀛。于是海荡山覆,川停浪肃。莫不骇其类,奔其族。玄黄之血,随重沫于渊沦;磔裂之形,蚀余威而蹙缩。卒使剑返人安,鳞穷血残。极浦烟霁,澄江景阑。逶迤然鷁首光转,错落尔龙泉影寒。冰彩犹鲜,激金铛之照曜;星文尚湿,归宝匣以阑千。③简宗梧、李时铭:《全唐赋》(第3册),台北:里仁书局,2011年,第1887-1888页。
先从视听两方面渲染蛟龙的声威气势,接着对佽飞斩蛟的过程展开铺张描摹,再交待搏斗后的情形。这段叙述,时间清晰有序,过程丰富刺激。赋文最后以“至今人语其风,见英姿之卓尔”结尾,对佽飞英勇无畏的风姿予以极力赞赏。作者以其出色的想象力与华彩之笔,对原有故事进行重编,敷演场景,设想独白,描摹动作,刻画出一个沉着冷静、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唐人成熟的叙事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白行简《欧冶子铸剑赋》《澹台灭明斩龙毁璧赋》、谢观《汉以木女解平城围赋》等,也多增衍想象之词,体现出作者改造旧故事、熔铸新故事的虚构能力。因有叙事主体出色的想象力与自觉的虚构意识为基础,唐赋才富有浓厚的叙事色彩。当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唐赋叙事与小说叙事还是有区别的:小说叙事主要以戏剧性取胜,即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行动;唐赋作者还不太善于让人物自我演示,其故事多靠作者讲述出来。究其原因,与赋的文体特性和艺术追求关系密切,赋毕竟重在以华辞丽藻展示才学。尽管唐赋作者的叙事思维还未能达到创设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的高度,但他们尝试以辞赋形式重新编排故事,已呈现出向小说迈进的趋势,这对以唐传奇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传奇作者的长技是“幻设为文”,即假设人物、虚构故事,即使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他们也要改变原型,加入某些离奇的情节。其目的是异常逼真地把虚构的人物、故事、情境展现出来,创造出几可乱真的“第二自然”,读者明知是虚构,却因其细节的真实而信以为真,从中获得高度的审美愉悦。如沈亚之《秦梦记》,以自叙手法写他在梦中与秦穆公之女弄玉结婚的故事。弄玉前夫萧史先死,沈亚之入秦后因其突出的军政才干深得秦穆公赏识,并把弄玉嫁给他。二人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弄玉忽然无疾而终,亚之沉痛为之作挽歌、墓志铭,并题诗于翠微宫而去。文章叙述宛转,文情奇诡。在这个故事里,史实、传说与虚构相杂糅,秦穆公在历史上真有其人,弄玉萧史吹箫引凤、得道成仙属固有传说,而作者把传说中的眷侣拆散,让萧史先死,弄玉再改嫁,而后弄玉又死,改写成一个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这属于作者的想象。董乃斌说:“文学叙事不仅要求把一桩实事以生动凝练、富于激情的笔调记录下来,而且要进一步做到创造出逼真的‘第二自然’——它源于生活,一切过程与细节是那样酷似活生生的现实,但它又确确实实是作家凭着主观的想象加工编织制造出来的‘虚的实体’,读者即使明知其‘虚’,却也不能不信服其‘真’。”①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9页。董乃斌对文学叙事中作者消化加工原素材并创造出逼真的“第二自然”的虚构能力予以了高度赞赏。唐代文人(包括传奇作家、乐府作家、赋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心中始终秉持着这样一种理念:重要的不在于什么题材可以进入他们的笔端,而在于怎样构思,才能够创造出几可乱真的“第二自然”。这是整个社会的大潮流与大趋势。
程毅中在细致考察屈原《渔父》、宋玉《高唐赋》、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扬雄《长杨赋》、曹植《洛神赋》等叙事赋的演进后,曾这样阐述叙事赋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从叙事赋的发展史,大致可以看出,叙事赋的虚构手法,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自觉的文学虚构手法,正是在赋家的手里完成的,比之先秦诸子寓言有了重大的进步。”②程毅中:《叙事赋与中国小说的发展》,《中国文化》2007年第1期。那些叙事性较浓厚的唐赋,虽不能如程先生那样定义为纯粹的叙事赋,但唐代赋家继承前代叙事赋的优良传统,在自觉的虚构意识方面已然娴熟,这是唐赋在叙事思维上的巨大进步,给人以强烈的精神愉悦与审美意义;另外,唐赋作家在对历史故事、寓言传说等原型进行复述与敷演时加入了自己的认识与思想,提出了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与道理,这是唐赋叙事在思想内容上的进步,显示出高明深刻的思想意义。由此可知,唐赋虚构叙事的审美意义与思想意义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二、多样的叙事语调:千姿百态的文学语调的孳育
凡是用语言文字表述的口头或书面文本,无不存在一定的语调。所谓语调,就是作者在叙述事情、阐发思想、表达情感时所采用的基本口吻、态度、格调。由于文章的题材选择、思想倾向、故事情节与人物设计的不同,由于作者的人生境遇、思想气质、文化教养、审美情趣、创作习惯的差异,文学作品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叙事语调。
细细体悟唐赋作品,其叙事语调呈现出丰富多样性,有热情豪放的,有细腻入微的,有深沉哀婉的,有诙谐幽默的,等等。如白行简《澹台灭明斩龙毁璧赋》、独孤绶《斩蛟夺宝剑赋》叙述澹台灭明、佽飞剑斩蛟龙的事迹,赞颂不畏强暴、勇敢无敌、心怀仁义的英雄;白居易《汉高祖斩白蛇赋》叙述汉高祖力斩白蛇的史实,赞美其平定天下的丰功伟绩;张随《纵火牛攻围赋》,详细铺叙田单纵火牛攻破燕人重围的故事,对田单的高超智谋予以由衷的赞叹。这些赋作充满着无尽的气势,显示出豪气奔放的叙事语调,与作者在题材上选择了那些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伟大事迹并对他们予以高度赞赏的思想倾向相统一。浩虚舟《陶母截发赋》叙述陶母截发置米及酒肉招待儿子好友的故事,作者设身处地揭示了陶母的矛盾挣扎、痛苦纠葛与坚定决心,因其重在刻画人物的心灵世界,而显现出细腻入微的叙事语调,与上述赋作的热情豪放大相径庭。康僚《汉武帝重见李夫人赋》重述李夫人死后,武帝思念心切,有方士以法术使李夫人重现于汉武帝眼前的传闻,不仅刻画了一个美丽动人、含情脉脉、羞涩无言的李夫人形象,而且写出了汉武帝怀抱希冀又怅然失望的内心活动;白行简《望夫化为石赋》叙写贞妇送别丈夫,日夜站立,守望丈夫归来,终化为石头的传说,塑造出一个坚贞哀怨的贞妇形象;蒋防《姮娥奔月赋》叙述姮娥奔月故事,揭示出姮娥由奔月前的坚定与希望到奔月后的苦寂与失望的内心变化,塑造出一个超然皎洁又寂寞孤苦的姮娥形象,这些赋作的题材都是有关生离死别的,所以语调上显得深沉哀婉、缠绵悱恻。
中国赋体文学在出现之初,就体现出与子史类文章严肃庄重语调相异的滑稽戏谑的叙事语调。那些倡俳优伶,往往在君王面前演绎一些民间传说或谐辞隐语,目的是为了取悦、献谀其主。如淳于髡、优孟之徒,东方朔、枚皋等赋家,除以赋文逢迎君主外,还经常在赋文中以诙谐风趣之笔嘲讽现实、宣泄牢骚。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曰:“于是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70-271页。刘勰以赋为“俳”,乃因其与“俳”一样具有俳谐戏谑的意味,这在汉魏六朝的赋中非常普遍。如王褒《责须髯奴辞》、扬雄《逐贫赋》、左思《白发赋》、张敏《头责子羽文》等,都以幽默滑稽的叙事语调,或自我嘲弄,或批判现实。
唐赋继承了先秦以来俳谐杂赋揭露黑暗、批判丑陋的传统,在行文中往往出现游戏谐谑、诙谐滑稽的叙事语调。这主要体现在两类赋中:一类是那些以拟人化言说方式叙事的类赋之文。如韩愈《送穷文》,巧设主人与穷鬼相互问答的形式,开头写主人“三揖穷鬼而告之”,想要驱赶穷鬼,遇此情境,穷鬼表白当年主人遭厄时,它也惨遭欺凌,却未弃主人而去的忠心;接着主人历数祸害他的“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个穷鬼,穷鬼则嘲笑主人陪伴其自身的只剩穷鬼了;主人最后不但未送走穷鬼,反而“延之上座”,尊为贵宾。赋作以“送鬼”起头,最后竟以“留鬼”作结,嘲讽人情世态,疏泄牢骚之气,同时暗含自炫之意。不论是对问答本身的叙写,还是对穷鬼面目表情、行为动作、心理反应的摹写,作者都寓之于幽默诙谐的语调,使嘲讽之意显得更为痛快淋漓。柳宗元《骂尸虫文》《乞巧文》等,亦在人物对话的叙述框架中,借助滑稽戏谑的语调,来揭露社会丑态。
另一类是敦煌俗赋。如赵洽《丑妇赋》,作者不仅写丑妇外貌之丑:“飞蓬兮成鬓,涂嫩甚兮为唇。……天生面上没媚,鼻头足津。闲则如能穷舌,馋则佯推有娠。耽眠嗜睡,爱釜憎薪。有笑兮如哭,有戏兮如嗔。眉间有千般碎皱,项底有百道粗筋。贮多年之垢污,停累月之重皲。”而且写其言行之丑:“结束则前褰后,披掩则藏头出齿。……豪豪横横,或恐马而惊驴;咋咋邹邹,即喧邻兮聒里。……尔乃只爱说非,何曾道是。闻人行兮撼战,见客过兮自捶。打女而高声怒气,何忍更涂香相貌,摆敷妆眉。只是丑上添丑,衰中道衰。告冤屈者胡粉,称苦痛者烟脂。”作者由此感慨:“人家有此怪疹,亦实枉食枉衣。须则糠火发遣,不得稽迟。勿客死外,宁可生离。所有男女总收取,所有资藉任将随。”②简宗梧、李时铭:《全唐赋》(第8册),台北:里仁书局,2011年,第5005-5007页。作者对丑妇外貌形体、言行举止乃至内在心灵之丑的描摹,显得如此可笑甚至怪诞,由此形成一种滑稽诙谐的叙事语调。在这种语调氛围中,读者得到了一种强烈的感官刺激与精神愉悦。
刘瑕《驾幸温泉赋》,无论是描摹天子仪仗的雄伟、温泉景观的瑰丽,还是叙写访仙求药的奇妙经历,作者都寓以诙谐轻松、幽默滑稽的语调。结尾作者还自嘲其如不肖子穷奇、迷途之阮籍。自己虽然相貌丑陋,却擅长技艺,能写卓绝文章,就算卢骆杨王,也都不是他的对手。然命途多舛,梦里的富贵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唯有痴心等待千年一遇的良机,恳求天子千万不要让其美梦化为泡影:“今日千年逢一遇,口头莫问五角六张”,是一种含泪的诙谐。唐人郑棨《开天传信记》即言此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道出其在叙事语调上诙谐调侃的鲜明特征。《燕子赋》在雀儿形象的塑造上,也尽显讽刺滑稽的叙事语调。开头即以漫画式笔触勾勒其猥琐之貌:“头脑峻削,倚街傍巷”。后面叙述雀儿强占燕巢并毒打燕子,燕子到凤凰面前申诉,凤凰命鸨鹩前去捉拿雀儿,雀儿套近乎、拖时间,未能得逞;到凤凰跟前,雀儿又溜须逢迎、百般推脱;公堂上雀儿狡诈哄骗、抵赖诬陷,甚至搬出“上柱国勋”之王牌,得以免罪。赋文通过对这一系列情节的细腻叙写,尖锐讽刺了雀儿这个丑角的滑稽可笑。这是对当时丑恶不公现实社会的直接映照,读者在嬉笑怒骂之余,获得了幽默愉悦的审美感受。
唐赋在叙事语调上的丰富多样性,为唐传奇乃至后世文学语调的千姿百态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具有不可抹杀的影响。由于小说与史述同属叙事文的范畴,小说在叙事语调上必然深受史述的影响。不少唐传奇作品开头结尾的行文俨然史述,一般来说,是平实庄重的。如《补江总白猿传》开头曰:“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蔺饮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深入险阻。”叙述是客观平静的。然而接下去写欧阳纥妻之美、欧阳纥部下的警告、欧阳纥的防范及欧阳纥夜里失踪的情节,则纯属夸张、渲染之笔,充满着诙谐戏谑、讥嘲调笑的语调,这种语调的形成直接受到了辞赋(包括唐赋)的影响。沈既济《任氏传》是一个关于狐精的传奇故事,其叙事语调显示出鲜明的幽默戏谑的意味,如写男主人公郑六与狐女任氏的相遇,郑六见到任氏的美貌后又惊又喜,于是先骑着驴忽前忽后地小心试探,待任氏有所心动后,又大胆地以言语相挑逗,而任氏的笑答更使其信心大增,主动表示要把自己的驴借给她,最后的“相视大笑”蕴含着两人的相见恨晚之叹。而后写韦崟不相信郑六能得到美色,于是派了个小僮偷偷地进行了一番侦察,小僮回来后向韦崟汇报的情景更是诙谐滑稽。主仆二人,一个迫不及待地问是否美,一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并故意以“天下未尝见之”相答;一个频频以“孰若某美”相问,一个却始终答之以“非其伦也”。而后又是沐浴,又是修饰仪容,精心打扮后才前往见任氏。这段文字在一问一答之间,逗引出韦崟对于美色急不可耐的心理,读来活泼有趣。这种谐谑滑稽的叙事语调在《柳毅传》《南柯太守传》《游仙窟》《异梦录》《崔环》《吴全素》等唐传奇作品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以戏谑的语调讲述一个幽默有趣的故事,正是唐传奇之所以富于传奇色彩的表现手法之一。当然,唐传奇的叙事语调不唯幽默戏谑一种,而是千姿百态的。同是叙写爱情故事,叙事语调却各具特点。如陈玄祐《离魂记》采用的是浪漫热烈的语调,与篇中所要表达的男女相慕至深而魂牵梦系的狂热相谐。许尧佐《柳氏传》写韩翃与柳氏的爱情悲喜剧,语调略显凝重深沉,这与男主人公的性格懦弱密切相联。蒋防《霍小玉传》叙述大历中长安名妓霍小玉和李益相爱而终被李益抛弃的悲剧,作者怜惜与愤慨交织的语调鲜明体现出其爱憎情感。唐传奇涉及“人化虎”故事的作品有多篇,叙事语调表现出多姿多彩的特色,如《天宝选人》叙述虎女初被人窃去,后被娶为人妻,终而重新变为老虎之事,语调比较平实直白;《崔韬》写崔韬与虎女的相遇及其结为夫妇的故事,却显得委婉细腻;《李征》假老虎之口,诉说一个落魄士人的遭遇及其痛苦心情,语调凄怆悲愤。同样,后世小说、戏剧中所显现出来的叙事语调也是丰富多彩、异彩纷呈的,说其受到了唐赋多样叙事语调的间接影响,应该是不为过的。
三、精细的描摹能力:中国文学反映客体世界的重要助推
朱光潜曾从情趣与意象配合的角度把中国古诗的演进分三步:汉魏以前为第一步,因情生景;汉魏时代为第二步,情景吻合;六朝为第三步,即景生情。并说:“从大小谢滋情山水起,自然景物的描绘从陪衬地位抬到主要地位,如山水画在图画中自成一大宗派一样,后来偏渐趋于艳丽一途了。……转变的关键是赋。赋偏重铺陈景物,把诗人的注意渐从内心变化引到自然界变化方面去。从赋的兴起,中国才有大规模的描写诗,也从赋的兴起,中国诗才渐由情趣富于意象的《国风》转到六朝人意象富于情趣的艳丽之作。”①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1页。不仅厘清了中国古诗乃至整个文学演进的三个大致阶段及各自不同的特征,而且指明了赋在此演进过程中的枢纽作用。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使大批作家习惯于以情观物,物无不打上作家主观情志的深深烙印。作家们毕其一生往往只塑造了一个人物,即他们自己。赋的本质在于铺采描摹,它使作家的视线由表现内在转向反映外在。这是中国文学突破抒情的藩篱向叙事迈进的转捩点。赋家竭力将自己的目光向外转,转向琳琅满目的大千世界,他们恨不得把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笼挫于自己的笔端,并加以精致周详的描绘,于是便出现了铺张扬厉的汉大赋。马积高先生在《赋史》中指出:“在体物上下工夫,力求做到形似”②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是汉赋作者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并举《诗经》、楚辞、汉赋中的作品为例加以论证,勾勒出文学对客体世界的描绘由粗略到精细的过程。虽然汉赋作家的审美能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世界的描摹已非常精密巧妙,但他们此时尚未真正把握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创作规律,只是一古脑儿地堆砌材料、罗列名物,客观事物的形象并不鲜明,因此招致“情少而辞多”的批评。后来诸多赋家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如曹植《洛神赋》,在刻画洛神形象方面十分成功,影响颇深,后世很多小说在描摹人物形象时,多模仿此赋从容貌体态、服饰举止、风姿神韵等角度叙写人物的做法。
唐赋在汉魏六朝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客体世界的描叙更趋精致细腻、丰富具体,主要表现为唐赋在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描写景物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绩。唐赋与传奇小说基本上同时,说明时人有着一致的创作趋势,那就是大家都想讲故事,写人物。但唐赋与传奇小说媒介不同,文体不同,唐赋毕竟不是小说,它只是呼应了叙事写人的大趋势而已。在此趋势下,唐赋精细的描摹能力对于中国文学反映客体世界产生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寓言为题材的唐律赋通常详尽细致、逼真生动地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其中穿插生动的场景描写、丰富的氛围渲染、细腻的形象刻画,塑造出众多的形神毕具的人物形象。
且看宋言《效鸡鸣度关赋》。典出《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55页。讲述孟尝君被秦囚禁,靠门客中的鸡鸣之徒才得以脱身的故事。宋赋即将此事作如下敷演:
昔者田文,久为秦质。东归齐国之日,夜及函关之际。顾追骑以将临,念国门之尚闭。君臣相视,方怀累卵之危;豪侠同谋,未有脱身之计。下客无名,潜来献诚:“君祸方垂于虎口,臣愚请效于鸡鸣。”
以律赋之笔重述孟尝君为秦质,经过重重困难逃至函谷关,却又陷入关门未开、后有追兵的危急境地。情节交代清楚简洁,然后重笔浓墨地描绘出效鸡鸣者形象:
于是鹰扬负气,鹗立含情。迥夜遥天,未变沉沉之色。攒眉鼓臂,因为喔喔之声。审听真如,遥闻酷似。高穿紫塞之上,深入黄河之里。一鸣而守吏先惊,三唱而行人尽起。回瞻满座,皆默默以无言;散入荒村,渐胶胶而不已。②简宗梧、李时铭:《全唐赋》(第6册),台北:里仁书局,2011年,第3917页。
宋言带着推崇欣赏之心,不吝用“扬”“立”“攒”等一连串动词,摹画点缀效鸡鸣者的光辉形象。在绝境中,一个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人物被推到了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只见他紧锁眉头,鼓动臂膀,像飞扬的鹰、耸立的鹤一样负气含情,发出喔喔的鸡鸣声。“高穿紫塞之上,深入黄河之里”一联着力渲染出鸡鸣之声高穿长城、深入黄河的深厚穿透力,“散入荒村,渐胶胶而不已”一句则凸显出鸡鸣之声回响不已的巨大震撼力,这些都为效鸡鸣者形象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于是在孟尝君出逃成功的同时,一个新的前所未见的英雄形象诞生了。
另外,白敏中《息夫人不言赋》中的息夫人不言故事与息夫人形象、王起《延陵季子挂剑赋》中的季子挂剑故事与季子形象、康僚《汉武帝重见李夫人赋》中的李夫人形象与朦胧迷离的气氛、周繇《梦舞钟馗赋》中的钟馗形象与神秘恐怖的氛围等,都表明唐赋作家对客观世界进行精细周到描绘的不懈追求。而唐代俗赋《韩朋赋》《燕子赋》等,其中不论是对韩朋、贞夫爱情悲剧的曲折叙述,对燕雀争巢故事的寓言化描叙,还是对贞夫、韩朋形象的生动塑造,对雀儿、燕子形象的拟人化刻画,也都体现出唐代文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向繁复化方向发展的态势。与前代赋家相比,唐赋作家在描摹客观世界方面更进一步,即由单纯地重述故事到在敷演故事时着力烘托人物,显现出其叙事能力的极大增强。
唐传奇作家在描绘客体世界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体现出创作思维的巨大变革,董乃斌对此变革的历史作用深入剖析道:“他们一致要求冲破表现主观的陈套,让心灵、眼光、手腕全都向外转,转向反映自身以外的客观世界。不是像从前那样对客观世界做主观化的描写讴吟,而是按照客观世界本来的样子作真实、负责的反映,不是满足于抒发自己个人的情怀志向,而是把笔触伸向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从而创造出以往抒情诗歌中少有的人物形象……艺术思维方式的这一变革和飞跃,其伟大意义在于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使原先偏重主观而反映客观不足的倾向得到纠正,使创作主体更加主动自觉地超越自身而向客观世界靠拢,从而也就使主客观两者获得了新的、更高的和谐……而小说文体的独立和此后的发展,则改变了中国文学侧重于表现主观一隅的传统偏向,使中国文学走上表现主观和反映客观双轨并进的道路,从而使中国文学史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①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33-234页。。董先生所论主要着眼于唐传奇作家在创作思维的变革方面为小说文体的独立提供原动力及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如果以此来观照唐赋,不难发现,唐赋其实如唐传奇、新乐府一样,都是对大千世界真实细腻的反映,是中国文学由表现主观向反映客观转变的重要桥梁。前面所述已能充分证明唐代作家在赋这种文体中尽情发挥了他们的叙事才能,但不可否认的是,赋的优长还在于言志。经过不断探索,文人们逐渐认识到,赋体作品在叙事艺术的拓展上,有着较大的局限与阻碍,只有小说才最长于叙事。赋与小说在创作思维上的共通性,使赋呈现出向小说迈进的趋势。同时,两者在文体上的各自优势与欠缺,也使赋向小说的发展成为可能,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体演变之路途。
四、结 语
与小说相比,赋并不是最适合于叙事的文体,它擅长言志抒情。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赋曾经在自觉的虚构意识、多样的叙事语调、对客体世界的精细描叙等方面所取得的叙事成就,及其在后世小说、戏剧等文体上打下的烙印。
当从叙事视角重审中国文学史时,以虚构叙事为基本特征的小说戏剧自然是考察的重心,但若将范围仅仅限定于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体,难免流于片面,因为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它遍存于一切材料、一切文类乃至一切地域、一切时代、一切社会。诗词赋等非叙事性文体中的叙事因子普遍的存在着,而诸如人物传记、碑铭墓志、寓言小品等文学性文章,从叙事学视角加以研究,也大有可为;即便那些如章表奏议、诏书檄文等应用性文章因其蕴含着或强或弱的叙事性,也应将它们纳入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研究行列。总之,中国文学史的叙事学视角或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是与一种新的大文学史观紧密联系着的。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文类样式都与“事”有不解之缘,它们以各自程度不等、性质不一的叙事性,构成了中国文学深厚悠长的叙事传统。唐赋作为赋体文学发展的高峰,在继承前代赋作优良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诸多成熟新颖的叙事特性,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唐代作家不光在传奇小说中,也在赋体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他们高超的叙事思维及其艺术表达能力。在人的艺术思维及表达能力由稚嫩而成熟并在小说中臻于极致的发展过程中,赋特别是唐赋因其对外部客体世界的精细描叙而使人的叙事思维第一次大步向前跨越,因而具有不可估量的桥梁意义与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