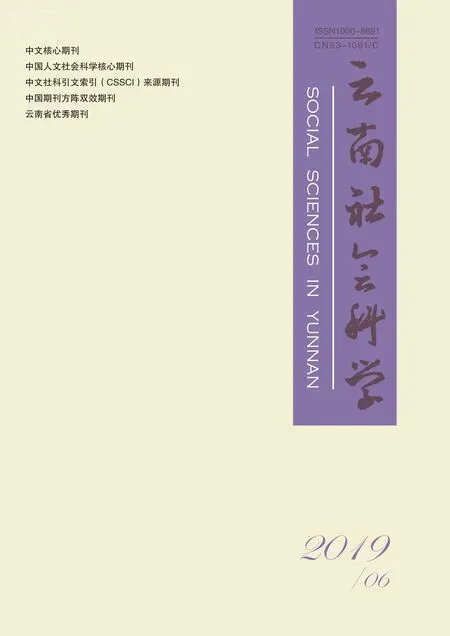论宋词本事的特殊性及其意义
2019-12-19刘杰
刘 杰
一、本事与词本事
“本事”一词,最早的出处是《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小序①(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意指与《春秋》经书匹配的史实。而最早将“本事”与诗歌联系起来的是唐吴兢《乐府古题要录》卷上《乌生八九子》题解:“若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言咏乌而已,不言本事。”②(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页。吴兢遗憾这首乐府没有相关的本事记载,所以无法得知其原义。通过这两则材料可以大致了解“本事”的含义,即与一个既定文本相关的“事”。在文本本身意义不确定的情况下,确定其“本事”可以框定其意义,换言之,“本事”的存在限制了阐释的可能性。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诞生了所谓的“本事批评”,亦即通过诗歌文本产生的背景和相关史实来探求作者的本义,其源头或可追溯至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说③有关这一批评思路,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批评方法研究》第一章“以意逆志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103页。,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将这种阐释方式的思维原理归纳为“本事(background)→本意(intention)→本义(meaning)”④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
本事批评起源甚早,几乎是与文学批评相伴而生。早期对诗本事的记录大体上呈现出三类文体形态:一是诗注,其实最早的毛传就已经在为《诗经》的文本寻找本事,例如《鄘风·载驰》之小序称此诗为许穆夫人欲归卫国不得而作⑤北京大学整理本:《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3(三之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此外《文选》五臣注也常为诗歌添补背景,如曹植《朔风》诗,原诗只是写北风,五臣注则为其补充了写作背景:“时为东阿王,在藩,感北风思归,故有此诗。”⑥(梁)萧统选编: 《新校订六家注文选》卷29,(唐)吕延济等注,俞绍初、刘群栋、王翠红点校,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91页。二是诗序,尤其是中唐以后,诗人经常在诗前附较长的诗序,交代与诗歌写作有关的来龙去脉,例如后来被《本事诗》收录的元稹《黄名府诗》小序①(唐)《元稹撰元稹集》卷10,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1页。此序亦见于见(唐)孟启《本事诗·事感第二》,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页。。三是最为人所熟知的笔记小说,例如《世说新语·文学》所载的著名的“七步成诗”的故事②《世说新语·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见(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8页。。此外唐末《本事诗》的出现堪称一个标志,此书以发明诗歌“厥义”(《本事诗序目》)③(唐)孟启:《本事诗》,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2页。为出发点,集中收录了一批诗歌本事,开创了后世纪事类诗话和总集的先河。
《本事诗》问世后不久,便出现了处常子《续本事诗》、聂奉先《续广本事诗》等仿作,针对诗歌进行本事批评的热潮至宋代仍然方兴未艾。作为诗话开山之作的欧阳修《六一诗话》即以“资闲谈”④《六一诗话》篇首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见(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28,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949页。为目的,其记录的内容也大多是一些与诗人诗歌相关的轶事,后来的《温公续诗话》《中山诗话》也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纪事内容。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人们对于新兴文体——词也采取了同样的批评策略。今可见最早的两部宋人词话,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⑤是书凡140余则。久佚,今有赵万里辑本,凡9则,收入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和杨湜《古今词话》⑥是书亦久佚,散见他书称引。近人赵万里从《苕溪渔隐丛话》《岁时广记》《笺注草堂诗馀》《花草粹编》《绿窗新话》等书中辑得凡67则,合为1卷,收入唐圭璋编《词话丛编》。都偏重于纪事,前者成书于神宗元丰初年,系仿孟棨《本事诗》体,所录上及唐五代词,但以“时贤”为主;后者约成书于绍兴初年,最早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引,是书记唐五代以来词林逸事,“大都出于传闻”⑦唐圭璋题《古今词话》前,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7页。,已经近于小说。除了此类词话的集中收录,有关词本事的记载还散见于其时的各种笔记之中。清人张思岩辑录有《词林纪事》22卷⑧(清)张思岩:《词林纪事》,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即将前代笔记词话中的词本事整合为一书,以人为纲,引述材料注明出处,针对具体史实也有一定的考证;但此书卷帙浩繁,收录了很多与纪事无关的评语类条目,颇有冗杂之弊。清末叶申芗亦辑有《本事词》2卷⑨(清)叶申芗:《本事词》,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与《本事诗》合订。,收录较精,但其钞录前代材料不注出处,而且还随意篡改字句,使用颇为不便。近人唐圭璋先生整理有《宋词纪事》⑩唐圭璋:《宋词纪事》,“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一书,采集众书,详注出处,并注意穷究原始材料,最为精良。本文所讨论的词本事大多出自上文提及的这些词话和笔记著作,也包括现代学者对词人生平的考证成果。
学界有关词本事的研究成果业已十分丰富,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针对某一本事或某一词人的专题个案研究,例如对苏轼词作的一系列艳情本事的考辨⑪参见吴德岗:《东坡词的艳情本事》,《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对陆游《钗头凤》本事的考证⑫相关成果参见高利华:《陆游〈钗头凤〉词研究综述》,《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等,这些研究侧重于文献考证和史实辨析,无疑为整体性的本事研究打下了基础;另一类是将词本事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综合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类研究,例如项鸿强《北宋词本事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郝青《北宋词本事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宋学达《从“词本事”看宋词之“尊体”》(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等,这类研究所处理的材料更多,涉及的范围更广,但也因此容易流于表面化的归类总结和简单的词学观念的提炼,缺乏对本事批评这种批评方式的理论化思考。就笔者所见,对后者问题有所思考的是李剑亮先生的《词本事与词诠释之关系及其评价》⑬李剑亮:《词本事与词诠释之关系及其评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其认为就诠释的可能性而言,本事批评限制了读者对作品进行创造性阅读,因此是一种不够理想的阐释途径。这一判断不无道理,但也失之武断,且对词本事的独特性认知不足,如上文所述,“本事”产生的目的就是限制阐释的可能性,故这一结论其实可以适用于所有本事,并不能反映词本事的特性。本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联系词体的特点探究本事批评之于宋词的可行性及其意义。
二、词本事之特殊性与本事批评的常见误区
苏轼以词为“诗之苗裔”①这一说法出自《风月堂诗话》,原文为:“东坡以词曲为诗之苗裔,其言良是。”其所本何书则不详。见(宋)朱弁撰:《风月堂诗话》卷之上,陈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1页。,在普罗大众的接受层面,诗、词亦被视为同一类型的抒情韵文。就这一层面而言,词本事是广义的“诗歌”本事的一种,因此也符合“诗歌”本事的一般情节模式。但是,作为两种文体,词与诗的区别还是相当显著的,这不仅表现在外形上的句式格律层面,在内在的情致格调上也存在着分野。李清照在北宋末年即已提出词“别是一家”②(宋)李清照:《词论》,见(宋)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廖德明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54页。的观点,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指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③王国维:《校注人间词话》卷下,徐调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7页。缪钺先生将其中的区别具体总结为“文小”“质轻”“径狭”“境隐”④缪钺:《论词》,见缪钺:《缪钺说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在其盛行之初的宋代,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文体,词与诗在地位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决定了其本事在题材和真实性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
首先,是在题材方面。尽管“情感”类是《本事诗》中数量最多的,也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类本事,但《本事诗》毕竟还收录了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等六类本事故事,合而论之,数量也并不在少数。虽然男女恋爱故事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题材,但诗歌毕竟是一种题材和主题相对广泛的抒情文体,故其本事也相应地覆盖了各种爱情之外的题材。相比之下词本事在题材方面就显得单调一些了,因为词本身就是一种题材相对单一的文体,缪钺先生所谓的“径狭”,《花间集序》即指出词的功能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⑤欧阳炯:《花间集序》,见(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校注》,杨景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终宋之世,尽管有苏轼、辛弃疾等词人努力拓展词的表现范围,但人们对词的普遍认识还是没有突破“词为艳科”⑥按“词为艳科”这一说法虽是由现代词学家胡云翼先生提出,但这种观念则产生甚早,详见谢枋得:《词为艳科辨》,《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的传统观念,文人与歌妓的爱情故事也在词本事的题材构成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上文提到的《古今词话》,今天所能见到的条目即“侧重冶艳故实”,乃至于与专录恋爱故事的小说集《丽情集》《云斋广录》相类⑦唐圭璋评:《古今词话》,见《古今词话》,第17页。。甚至一些根本不是写艳情的词也被附会上爱情本事,例如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就被附会为是为一个暗恋词人的女子而作,主人公有“王氏女子”⑧《能改斋漫录》卷16乐府上“东坡卜算子词”,见(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79-480页。和“温超超”⑨最早见于《女红余志》,原书已佚,转引自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历代词话》卷5,第1168页。两种说法。这些附会自然不可能是真实的,但其的出现颇能体现词本事构建的题材倾向。
其次,是有关词的代言属性的。因为词在经苏轼等士大夫的改造后逐渐成为了一种与诗分庭抗礼的抒情文体,读者很容易会忽略其本身的“代言”属性,如浦江清先生所言:“凡词曲多代言体。……词中抒情非必作者自己之情,乃代为各色人等语,其中尤以张生、莺莺式之才子佳人语为多,亦即男女钟情的语言。”⑩浦江清:《中国古典诗歌讲稿·词的讲解》,浦汉明,彭书麟整理,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281页。即便是在词的成熟期,这种“代言”式的写作也不在少数。在整个宋代,词都主要是一种歌筵欢场上的应用文学,词里所写的相思相忆也未必就可以对应作者本人的现实经历。美国学者艾朗诺的新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即以此为切入点,指出李清照的词不一定就是她个人生活的写照。①《才女之累》:“上述解读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将词中女子等同于李清照本人。事实上,李清照出身官宦之家,深谙词体文学的表演程式。她的父亲厕身于当时的高级文人圈,年轻的李清照在宴饮或聚会唱和一定见过人们填词,听过词乐表演,即便当时不在场也会有所耳闻。这些场合下演唱的歌词多为情爱之作(其他文化亦然),或是写失恋女子的孤独,或是刻画女子在男人面前搔首弄姿。李清照对当时的词体文学极其熟稔,这从他的《词论》便可看出,我们无法想象她对男性填词的程式懵懂无知。”见[美]艾朗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84页。这一观点相当具有启发性,面对一个男子写的闺阁情思,读者很容易便能够做出代言的判断;但是当一个女性以女性的口吻写爱情的时候,读者便想当然地忘记了这种文体的代言属性,直接将其与词人的现实生活对应,这在本事批评中是一种很危险的思维方式。事实上,由于词的代言属性,人们对于任何词本事的真实性都应该保持警惕,不管其与词的正文有多少呼应,其实都未必是真实的故事,因为作者所写的很可能并不是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再次,是有关词中所抒发的感情。这与第二点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带有高度应用性的文体,词是带有很强的“逢场作戏”成分的。也就是说,即便一个词人为一个歌妓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词作,表达了他内心真实的情感,但是,这种感情很可能就是一时的逢场作戏。它或许是真诚的,但并不等同于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忠贞不二、百转千回的感情。一个经典的例子便是陆游的名作《钗头凤》,这首词因附会上了陆游与前妻的爱情故事而知名,其本身也写得哀婉动人,那种遗憾、惋惜的惆怅溢于言表。但这份情感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据考证,这首词是为凤州歌妓而作,开头的“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也是化用了凤州的 “三出”②吴熊和:《陆游钗头凤词本事质疑》,载《文学欣赏与评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所以这很可能就是一首欢场上逢场作戏的作品,但并不妨碍其文辞缠绵悱恻,也不能说其感情就一定不真实,只是这种感情与后世所理解的基于忠贞的爱情不尽相同。
最后,是有关词作之独立性的问题。与后世成套数联排的曲不同,词的演唱方式为短章歌唱、彼此独立,这种音乐形式也影响到了其写作和阅读的方式。如上文所再三强调的那样,词是一种题材单一的应用性文体,故不同的作品之间经常会出现意象、主题、典故等方面的雷同。尤其是当同一作者的作品中出现了这种雷同的时候,读者很容易便会将这部分作品联系起来,拼接出一个与作者生平有关的“本事”。这种解读方式运用于诗歌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诗歌是“言志”的,作品多与作者的生平相关,便可以借诗人生平不同的作品串起;但词不同,如上文第二点所言,词以代言居多,此外还具有短章歌唱的独立性,理论上每一首词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创作情境,除非作者在题序中特意说明,应默认其各自的本事之间并无关联。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张草纫在《小山词笺注》的导言中对晏几道词作中爱情本事的建构。③(宋)晏殊、晏几道:《二晏词笺注》,张草纫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3-271页。其从小山词中解读出了晏几道与青梅竹马、西楼歌女和采莲女子等人的爱情故事,方式都是将提及同一意象的作品汇集到一处,再根据词意拼贴出一个爱情故事的来龙去脉。以最完整跌宕的“西楼歌女”本事为例,张草纫先是发现《小山词》中有不少作品都包含“西楼”二字,进而将《采桑子》(西楼月下当时见)、《少年游》(西楼别后)、《采桑子》(前欢几处笙歌地)、《鹧鸪天》(题破香笺小砑红)、《西江月》(南苑垂鞭路冷)、《木兰花》(念奴初唱离亭宴)等作品集中在一起,根据词意归纳出一个“初见-离别-相思-书信-重访-病逝”的情节梗概,由此便构建出了晏几道与一个歌女从相知到生离死别的故事。这样的解读看似有理有据,但实际上西楼只是一个很常见的意象,明清甚至还有《西楼记》。而且晏几道的词都是这种写艳情的小令,没有任何可靠的编年信息,在这些作品的具体写作年代不详的情况下,仅凭词意这么推测并没有说服力。
综合这四点来看,本事批评之于宋词的最大误区就是过度解读作品原文,读者希望能从作品中读出一个美丽的故事,一旦故事与原文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便很容易轻信其真实性。实际上,宋词是一种高度应用化的使用文体,其狭窄的题材范围、突出的代言属性和“逢场作戏”性质,以及短章歌唱的独立性都提醒着读者,作品文本并非“本事”的可靠依据。但在强大的本事批评传统的影响下,近现代的研究者也时常陷入这一误区,下面即以著名的姜夔“合肥情事”为例,通过对这一本事建构过程的分析总结出词本事建构的一般模式及其缺陷。
三、论词本事建构的可能性
姜夔与合肥姐妹的本事故事是夏承焘在《姜夔行实考》①(宋)姜夔:《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3-320页。中提出的,这篇文章专门有一节讲“合肥情事”,大意是姜夔与合肥的一对勾栏姐妹相知相恋,饱受相思之苦,最后亦不了了之,终成憾事,其词作中有不少作品都是这段感情的记录或回忆。夏承焘在《姜夔行实考》中详细交待了有关“合肥情事”的考证思路。其钩稽这段本事的最初动机是发现姜夔有两首词的序和正文不相合:一是《浣溪沙》(著酒行行满袂风),“序记游观之适,而与词语‘销魂’以下四句意不相属,且不知词所云‘四弦’‘千驿’者所感何事”②(宋)姜夔:《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第270页。;二是《长亭怨慢》(渐吹尽、枝头香絮),夏承焘认为“初玩此词与序,似仅敷衍庾信《枯树赋》语,近乎因文造情,白石不应有此;又词用韦皋玉箫事,序中所无,亦不知何指”③(宋)姜夔:《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第270页。。这两处疑问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牵强之嫌:“销魂”“四弦”所写不过是词中常见的离愁别绪,韦皋玉箫也是常用的艳情典故,未必就是实指,也不需要在序中特意点明缘起;至于“因文造情”,在白石词中也并非仅见,著名的《暗香》《疏影》即是。但夏承焘显然认为,这两首词的序言未能含括全词的内容,其背后应该有一些隐秘的本事。带着这份疑问,他重新检视了白石全集,果然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夏承焘发现白石有两首相思主题的词作都出现了“合肥”地名:一是《鹧鸪天·元夕有所梦》,首句点明“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④本文所引姜夔词及题序原文,文本皆出自夏承焘笺校《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不再一一出注。;二是《浣溪沙·辛亥正月二十四日,发合肥》,题序点明创作情境,词中则写到了“钗燕笼云晚不忺。拟将裙带系郎船”“别离滋味又今年”,背后似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其次,他发现姜夔在词中不止一次地使用桃根桃叶、大乔小乔的典故,又经常写到古筝、琵琶等弦乐器,如“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踏莎行》),“为大乔、能拨春风,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解连环》),“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琵琶仙》),据此推测姜夔的情人是一对擅长音乐的姐妹。再次,夏承焘又注意到姜夔词里写到合肥和相思的地方经常写到梅和柳。姜夔本人在词序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合肥的柳树:“近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苍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淡黄柳》序)、“合肥苍陌皆种柳,秋风夕起骚骚然”(《凄凉犯》序)。此外,《琵琶仙》《长亭怨慢》《醉吟商小品》等不少写及恋情的词皆以柳起兴或寄寓。又姜夔最后往来合肥是在光宗绍熙二年辛亥(1191),此年亦数度往返,其中两次离别皆逢梅花开放(初春和冬季),故其写及合肥情事时也往往会提到梅花,最典型的是庆元二年(1196)《江梅引》之“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又如《暗香》《疏影》写梅兼怀人,所怀当亦为合肥情人。既然这两种意象对这段合肥情事有特殊的意义,夏承焘进而推测其他写梅写柳的词也或多或少的与合肥姐妹有关。最后,将以上所涉及的元素(相思、合肥、乐器、姐妹典故、梅、柳)汇总到一起,便可以拼凑出一个爱情故事的大致雏形:姜夔在合肥期间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其所眷恋的对象为一对擅弹筝琶的姐妹,很可能为勾栏女子,但因为种种原因,姜夔与姐妹二人未能结成连理,在此后的生活里,姐妹二人美丽的身影和合肥的寒梅嫩柳叠加在一起,成为了词人内心深处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可以在白石词的原文中找到依据,其凄美的情致也符合作品本身的风格意境,看似有理有据,圆满无缺,也因此成为了宋词本事的经典案例。但仔细推敲会发现,这则本事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存在于姜夔或同时代文人笔下,夏承焘完全是通过对白石词作的文本解读来勾勒出这个故事的。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知这种本事建构方式的危险性,带着这种警惕来回顾这则本事的建构过程,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疑点:
其一,如上节第二点所述,词为代言,不一定反映词人的现实生活。在词里写到相思别调是词这种文体决定的,未必就能对应词人的真实生活。比如词人写“见梅枝,忽相思”,所写的可能就是词人见到梅花后心底升起的一种旖旎的情感,不能就此断定词人在现实中一定有这样一段与梅花有关的恋情。
其二,如上文第四点所述,词是短章歌唱、彼此独立的一种抒情文体,即便某一两首词背后真的存在着一段恋情往事,也不能引申扩大到其他写相思的词中。换言之,词本事是不能凭主观“叠加”的。像夏承焘先生这一仅凭一两种相同的元素便将创作时间不同、主题不同的作品串联起来,拼贴出一个故事,并不符合词本事的一般属性。笔者将夏承焘所标举的有关合肥情事的21首作品①夏承焘云其谱中列词22首,但笔者反复核验后发现夏先生列出的只有21首。一一分析,发现没有一首作品是涵括了怀人、合肥、乐器、姐妹典故、梅、柳等所有合肥情事构成元素的:

姜夔合肥情事相关词作本事元素分析
所有这些作品都只包含了这一本事中的两三个元素,涉及元素有重合的词便被认为是有关同一件本事。例如第一首词写到了合肥和相思,第二首涉及合肥和柳,那么柳树的元素就被认为是与合肥情事有关;第三首词写柳树,又提到了姐妹和琵琶,那么这些新元素也被纳入进这个故事里。根据本文第二章的分析,这种“叠加”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词人希望读者了解其“本事”吗?姜夔的词大都附有题序,简单交代了其创作的背景,但没有一则小序提到过合肥情事。上文提及夏先生考证合肥情事的起因便是发现词的小序与作品原文不相符合,但他并没有深入思考这种矛盾现象的成因,而只是简单地理解为“其孤往之怀有不见谅于人而宛转不能自已者”②(宋)姜夔:《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第272页。,亦即认为合肥情事涉及一些难言之隐,故不能明言,只能在作品中进行隐晦的暗示。这其实是一种循环论证:研究者预设姜夔有这样一段情事,再在其作品里找蛛丝马迹去印证这段本事,又为作者为什么自己在序里不交代而找借口。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但仅凭主观推测便下断语未免显得武断;而且即便这种情况是真,读者也不应忽视姜夔题序中的表达,因为这其实反映了词人希望读者关注什么。姜夔的词序可以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新作自度曲的音律之美,如《暗香》《疏影》序③序曰:“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一类是简介触动其填词的情境,如《一萼红》序④序曰:“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堂下曲沼,沼西负古垣,有卢橘幽篁,一径深曲。穿径而南,官梅数十株,如椒、如菽,或红破白露,枝影扶疏。著屐苍苔细石间,野兴横生,亟命驾登定王台。乱湘流、入麓山,湘云低昂,湘波容与。兴尽悲来,醉吟成调。”。由此可见,词人最希望读者关注的并不是作品背后的隐秘过往,而是词本身的音律和意境之新之美。可以作为参照的是晏几道,他在《小山词自序》中详细记述了自己与沈、陈两家歌女莲、鸿、蘋、云的交往①《小山词自序》:“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见(宋)晏殊、晏几道:《二晏词笺注》,第602页。,词中也多次提到了这几位歌女的名字,这说明作者希望读者了解作品背后的本事,否则便无法很好地理解作品的文本,笔者将这种想法称为“本事意识”。但对于姜夔来说,他显然没有这么强烈的“本事意识”,恰恰相反,那些风流往事即便真实存在,他也尽量将其写得隐晦,以至于让人难辨其踪。在他看来,读者不了解本事也并不影响其理解作品,换句话说,他们的作品并不依附于本事而存在。因此,过分强调其本事及本人的经历,然后与词文本相对应,其实反倒违背了作者的意图。
四、普适与私人——本事批评之意义反思
上节以经典的姜夔“合肥情事”为例,分析了此类依托于作品文本的本事建构之缺陷。的确,与诗歌相比,建构和考证词本事的难度要更大,误区也更多。但笔者想要在这里声明的是,真实性绝非评判诗词本事的绝对标准。事实上,不论是诗本事还是词本事,流传到后世的版本绝大多数都是小说家言,但并不妨碍人们对其进行阅读和欣赏。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本事批评这种批评方式究竟为人们解读词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或影响。
对此李剑亮有一篇专题论文《词本事与词诠释之关系及其评价》②李剑亮:《词本事与词诠释之关系及其评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文中作者列举了一些词本事的类型,质疑了部分本事的真实性,结论是“这种方法(按指本事批评)显然不利于诠释者主动介入文本、对文本开展创造性的阅读,并导致宋词作品意义的诠释走向单一与封闭的倾向。”所谓“创造性阅读”,作者的定义是:“诠释者完全可以在自己的阅读过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不断地丰富词的内涵,与词人产生共鸣,形成一种双向的交流。而这才是将词学诠释带向创新的有效途径。”文中举了王国维的三重境界说,认为这是抛开了词句本身的本事和含义,从读者自身出发对文本进行的创造性演绎。但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有些偏激,而且并不现实。“三重境界说”这种“创造性阅读”其实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也只有王国维先生的学识和气魄可以提出这一解读并产生很大影响,普通读者如法炮制只能流为空中楼阁。回归“本事”的问题,其实作者想要批判的是一种僵化的信念——将一件没有过硬文献依据的“本事”当作真实的信史,并将其视为解读作品的唯一参考——而非本事批评本身。前者的确有使得阅读诠释走向“单一与封闭”的倾向,而后者只是一种批评方式,未必就会导致阅读途径的窄化、僵化。葛晓音先生曾指出汉魏乐府与文人五言诗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其“抒情视角的普适性”:“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③葛晓音:《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在这一点上,后起的词与乐府不谋而合,同样也是没有特定的事件和背景,抒发的也只是套路化的春感秋悲,抒情主人公和倾诉对象也都是高度符号化的虚构人物。但这种模糊性也正为本事批评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就其本质而言,本事批评的原理实际上就是为词作赋予一个具体的情境,从而将作品所表达的那种普适化、套路化的情感具体为某一特定场景下私人性质的情感。本事不一定就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一篇作品的本事也不一定只有一个版本,因此本事批评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针对特定作品的“创造性误读”。
这种“创造性误读”的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古今词话》记载的苏轼《贺新郎》本事:
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具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车,属意于兰,见其晚来,恚恨未已,责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兰力辩,不能止倅之怒。是时,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兰收泪无言。子瞻作《贺新凉》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词曰:……子瞻之作,皆纪目前事,盖取其沐浴新凉,曲名《贺新凉》也,后人不知之,误为《贺新郎》,盖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谓风流太守也,岂可与俗吏同日语哉。①(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27-328页。
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钞录了这则故事,就其真实性大加挞伐,认为其属无稽之谈,玷辱先贤。就常识而言,显然这不可能是苏轼创作此词的真实背景,但若能抛开对本事真实性的考证执念,则《古今词话》的记载未尝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而且其每个情节都可以在《贺新郎》原文中找到照应,本事与作品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性”。在这则案例中,《贺新郎》原本是一首没有具体情境的抒情作品,但在《古今词话》所载的本事语境中,其文本竟也拥有了一定的叙事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获得了与仅仅阅读原文完全不同的体验。
此外,本事批评也不是单一、封闭的,因为围绕同一首词其实可以有不止一则本事。例如下面的《雨中花慢》:
事往人离,还似暮峡归云,陇上流泉。奈强分圆镜,枉断哀弦。常记酒阑歌畔,难忘月底花前。旧携手处,层楼朱户,触目依然。从来惯向,绣帏罗帐,镇效比翼纹鸳。谁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户不如飞絮,傍怀争及炉烟。这回休也,一生心事,为尔萦牵。
宋人笔记中记载了有关其创作背景的两则本事:
太学生任昉,字少明,□一官妓,五夜未尝暂离。昉既善限所抱,案句有脱误。而妓以老妪间隔。妓曰:“吾二人情意若此,莫若寻一利刃共死处。”昉姑诺之。后以一木刀裹以银纸,密卷纸数重,置于枕下,择日就行,妓深诺之。昉遂迁延时日,妓乃生疑,开纸观之,乃一木刀也,遂大恸绝昉。昉怀惓惓,遂作《雨中花》以贻妓曰:……妓得歌之,遂复如初。(《古今词话》)
元符中,饶州举子张生游太学,与东曲妓杨六者好甚密。会张生南宫不利归,妓欲与之俱,而张不可。约半岁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则任其从人。张偶以亲之命,后约几月,始至京师。首访旧游,其邻僦舍者迎谓曰,君非饶州张君乎,六娘每恨君失约,日托我访来期于学舍,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前三日,母以归洛阳富人张氏,遂偕去矣。临发涕泣,多与我金钱,令候君来,引观故居毕,乃僦后人。生入观,则小楼奥室,欢馆宛然。几榻犹设不动,知其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感怆,不能自持,迹其所向,百计不能知矣。作雨中花词,盛传于都下。或云,即知常之子予功焘也。其词云:……此得之廉宣仲布所记云。(《玉照新志》)②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古今词话》,第40页。
依《古今词话》所载,则《雨中花慢》词是作者因自身贪生怕死而辜负恋人后向对方的赔罪之作,既有明确的赠予对象,则结尾的“这回休也,一生心事,为尔萦牵”便带有一定的讨好意味;但依《玉照新志》,作者是因客观因素未能赴约而永远的失去了恋人,故这首词也便成为了一首纯粹的抒怀之作,结句的“这回休也”也不再是情人间赔罪式的山盟海誓,而是心碎后的沉痛独白。由此可见,不同的本事可以为同一首作品提供不同的解读方式,因此,只要摆脱本事即信史的观念,便可对不同版本的本事都持一种开放接受的态度。
综上,本事批评属于文本解读方式的一种,其本身并不会让文本的诠释变得单一、封闭;相反,如果对“小说家言”的本事一概斥之,反而会使词文本的解读减少了很多可能性。对于词本事而言,人们需要注意的是本事批评只是一种批评方式,本事不等于史实,由于词这种文体的特殊性,人们今天见到的大部分的词本事的真实性都是存疑的,此外像夏承焘、张草纫先生那样单纯依托作品文本构建词本事的研究方式也是不符合词体特点的。只要摒除了本事即事实、一个文本只能有一种解读这样的执念,本事批评不妨是人们解读作品的一种很有用而且很有趣味的方式。简而言之,在具体的研究中,对某一词人或作品本事的考证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尤其是不要轻易依托作品文本构建前人记载所无的“本事”;而对于前人记载已有的本事故事则不妨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不要把他们当成唯一的事实,只是一种解读的可能,而且可以透过这些本事故事加深人们对词体本身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