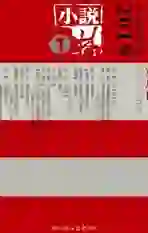灯火味道(短篇小说)
2019-02-28木糖

那个冬天的早晨,冷得实在让人难过。我去参加一个葬礼,在遗体告别大厅的门口遇见了他。他叫赵子。
“请问,有火吗?”赵子叼着烟问我。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摇摇头。
“看来,你好像跟死者并不怎么熟。”赵子的眼中挤出一丝讨厌的狡黠。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个作家,善于观察。”
我神色淡然地扫了他一眼,嘲弄道:“那么,你一定有很多大作。”
赵子一脸严肃地回答:“不,无非一群手拉手的破烂。但我最近写的一个小说还不错,想听吗?”
不等我回答,趙子便喋喋不休地讲了起来,真是讨厌。
他说,这个小说的名字暂定为《灯火味道》,主人公叫钱丑,一个善良温厚的小伙,样子长得还不错,只是个头不高,有双热切欢快的大眼睛,像一只刚刚长大的公鹿。
小说当然要有故事,那么就从钱丑的职业说起吧。他是个做灯箱的,有次,一家蛋糕店开业,店主将钱丑找去,准备做个灯箱,立在门口招揽生意。
蛋糕店临着街,钱丑做灯箱的时候,灌了满耳的车水马龙与人声鼎沸,可钱丑对此却充耳不闻,目光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店内溜,去留意店主跟他的妻子说话。店主叫孙寅,白白胖胖,五官原本很清秀,却被岁月弄得一塌糊涂,并且还是个大胡子。他的妻子李卯则身材苗条,双腿修长,眉宇间总带着一丝来历不明的忧色。
李卯正是钱丑喜欢的那类型女子,因此多看了两眼,尽管钱丑应该是个正派的小伙,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他只是带着欣赏的目光去看,毫无邪念,所以我觉得这对他的品行是没什么影响的。你看,我总是小心翼翼维护钱丑的形象,因为我做好了准备,去喜欢上这个小伙子。
当时,李卯跟孙寅应该说什么呢?让我想想,哦,对了,李卯在跟孙寅讲她昨晚做的一个梦,孙寅拿着一块抹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但不管他走到哪里,李卯都始终跟在身后,极其细致描述着梦中情景,严肃得仿佛那是一件千真万确发生过的事。孙寅则哈欠连天,心不在焉。李卯被惹怒了,质问道,你到底在没在听?孙寅看了一眼妻子嗔怒的样子,反而笑了,连忙赔不是,脖子往前探探,做出专心听讲的姿势。李卯被逗笑了,接着讲了下去,可没说几句,又被孙寅打断,只见他嘟着嘴不满地说,怎么你的梦里总是没有我。李卯娇笑道,你怎么对梦里的人也吃醋?李卯是满意的。男人的醋意是女人自信的营养液,李卯是女人,李卯不例外。
李卯最终也没能将那个梦讲完,后来,他们切了一盘西瓜,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吃。一不留神,孙寅汗衫的胸口上粘了一粒西瓜籽,李卯伸手将其捏下来,责备说,挺大个人,吃东西这么不小心。孙寅咧嘴一笑,想必这句话含糖很高,比西瓜更甜。然而,孙寅忽然想起另外一件事来,笑意立即被冻死,他张了张口,刚想将那件事告诉李卯,却见李卯朝着正丁丁当当做灯箱的钱丑努了努嘴说,去给那个小师傅也送块西瓜。
其实这时候,钱丑一直在留意他们说话,一见孙寅拿着西瓜走过来,慌忙站直身子,用手背擦了擦脑门上的汗,顺势又隔着孙寅一耸一耸的胖肩膀,飞快地瞅了李卯一眼。
你看,我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都是慢腾腾的细节,既然是故事,就该有事故,所以我打算让孙寅走着走着,忽然一个趔趄,随着,一枚硬币从兜里掉出来,朝公路方向滚去,孙寅猫着腰,连跑带颠地追在后面,指尖刚搭到硬币上面,一辆疯疯癫癫的大客车猛地从侧面开来,不由分说就将孙寅撞飞。这一幕场景,立即将李卯骇呆了,呼吸片刻中断后,她惊恐万分地大声喊了起来。
“不,不,不会这样的。”赵子尖着嗓子模仿李卯的声音,大声喊着。一个站在前排的老人,转过脸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这才从那故事里挣脱出来,很不好意思地说:“你看,我总是一不留神就进去了。”
我没理他,转过脸望向死者停放的地方,这时候,殡仪馆的司仪正在介绍死者的生平,刚才光顾听赵子讲他的小说,竟然没有听见死者叫什么?赵子没猜错,我跟死者确实不熟,甚至素昧平生,我只是无意中走到这里来的。
司仪的声音低沉而丝毫不带感情,对他来说,每个死者的一生,都是一篇大同小异的说明文。这样一想,我心里忽然很不得劲儿,他们就算千篇一律,至少还有自己的职业,籍贯,民族,可我除了性别之外,全都不记得。
幸好,我还记得她,那个让我刻骨难忘的女人。
我是在一家歌厅认识的她,她浓妆艳抹,满身劣质香水气味,说话的声音又甜又腻,典型的浪荡女子,卖身吃饭。然而,我还是被她迷住,搂着她高唱一曲《死了都要爱》,随后,对着麦克风大声说,嫁给我吧,我给你赎身。全场的人都把目光围拢过来,万分惊讶地盯着我这个一身酒气满脸胡须的疯子。
她愣住,猛地抽了我一个耳光说:“你有病吧,我又不是青楼女子。”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依然对着麦克说:“我是要用一生的爱,赎你一生的幸福。”我诗情画意的表白,赢来全场掌声。这群感情麻木的人啊,即便看了一万本琼瑶席绢张小娴的爱情写意,也还在怀疑浪漫在生活里是否能存活。但那一刻,我让他们信了。
她垂下头,低声说:“可我不想当杜十娘。”
我哈哈大笑地问:“你有百宝箱吗?”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了,登记结婚购置新房。我履行诺言,对她千依百顺,可她却总也忘不掉自己曾经的职业,跟任何男人说话都小心翼翼,很少同我一起逛街,生怕遇见昔日的某个嫖客,引来那句盗墓一般的搭讪。对此,我常常劝她,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难道你非得让我列出一张猎杀名单,将那些跟你上过床的男人,统统干掉吗?
她偎依在我怀里,悄声问:“可我哪样好,值得你这么认真地爱?”
我说:“也许我是悔不当初的那个李甲,回到此生来赎罪。”这句话,一点不感人,甚至伤人,她脸色微微一变,是啊,有些事即便斩草除根也是忘不掉的。
为了让她对我的爱深信不疑,我决定再做一件浪漫的事。那天她过生日,我订了个两米多高的蛋糕,让人送到家里。蛋糕太大,从门口进不去,蛋糕店的人索性将其放在楼下,围过来很多人,指指点点,好似在参观一块从天而降的肥陨石。
她瞠目结舌地站在蛋糕前,不知所措。蛋糕店的人递过来一把大砍刀似的塑料刀,又搬了个圆凳,让她站在上面将蛋糕切开。她环目四顾,没有在人群里找到我,于是将刀放下说:“我得等我丈夫。”蛋糕店的人笑眯眯地说:“这正是你丈夫安排的,等你切开蛋糕后,他就会出现。”
她左右看了看,拿起塑料刀,一记力劈华山,蛋糕一分为二,我猛地从里面蹦了出来,像粘了满身奶油的哪吒三太子,脚踩莲花,光临人世。围观的人们都愣住了,随后嘻嘻哈哈地鼓起掌来,哎,我的浪漫总是借用这种热闹的陪衬。幸好,她被感动了。
我想,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巨大的夹心蛋糕。浪漫本身没什么,但它却是一份精心设计的心意。
就在我沉浸在美不可言,满是糖浆味道的往事之中时,赵子很不知趣地捅了捅我,想将他的小说接着说下去。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极其不耐烦地瞅了赵子一眼。
赵子接着说——
当时孙寅并没有死,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往医院,李卯也跟着去了,走得匆忙,连门也没锁。钱丑站在门口,望着呼啸而去的救护车,发了一会儿呆,转身走进店内,但凡有窗户的地方,都有阳光涌入,可钱丑还是觉得这明亮过于肃静,在屋内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
后来,钱丑转到厨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将近两米高的大冰柜,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想打开看看,走到跟前,钱丑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最讨厌打开冰柜时一股凉气迎面而来的感觉,还是暖乎乎的烤箱更适合他。
这时,烤箱里还有一盘刚刚做好的曲奇,钱丑犹豫了一下,伸手取了一个,做贼似的吃了,哦,确实也是贼,当我写到此处时,曾想过这个细节似乎并不符合善良温厚的钱丑,本想删掉,可曲奇的味道实在太迷人,几乎要从键盘的缝隙里飘出来,二十六个字母挤挤插插地咽口水,算了,还是将其留下吧。
钱丑吃得太急,不小心被噎住,四处找水。忽然,他想起放在门口台阶上的那盘西瓜,连忙走出去,等坐下来吃西瓜的时候,钱丑这才猛地想起刚才孙寅被车撞到的情景,是啊,孙寅想必救不活了,应该为他难过一下。我不是说过了吗?钱丑是个仁厚的小伙子,所以得让他对别人的生死有一种怜悯之情。那么,在钱丑吃完西瓜之后,他就该将灯箱认认真真地做完,然后才离开。
你看,你看,我老是沉迷这些细节,下面我说得快一些,免得你听不下去。
后来,钱丑听说孙寅死了,很难过,钱丑是陪着李卯失去爱人而难过的,也不知道她现在怎样?钱丑放心不下,有天晚上,他特意跑到蛋糕店去看看,可门却在里面锁着,屋内也没开灯。一开始,钱丑也没太在意,以为李卯睡得早。可是第二天他来的时候,依然如此,满街的灯都亮着,唯有蛋糕店里死气沉沉的黑。
钱丑想,一个女人,丈夫刚刚死去,她会怎样?坐在没有灯光的房间里哭,还是……钱丑慌了,想去敲门,又觉得不妥,在门口转来转去没有办法,索性坐在台阶上,每隔一会儿,钱丑就朝屋内望望,他多么希望,能看见一盏灯鲜艳而欢快地亮起在她的窗前。
此后的几天里,钱丑总是守在门口,不仅屋内灯光全无,即便自己做的那个灯箱,也像个还没出生的小兽,默默地蹲在门口,陪着他分分秒秒的慌虑。李卯会不会真的想不开,已经服药、悬梁或者割腕了?哎呀,这可不妙,钱丑猛地站起来,准备将门一脚踢开。也就在这时,街上响起警车的鸣叫声,几个警察饿虎扑食地将钱丑擒住,带回警局。
你可能想不到,报警的人就是李卯。她只是没开灯而已,人还活着,也从来没想过服药、悬梁或者割腕。这几天,钱丑守在门外,她隔着窗户看得一清二楚,哪晓得他安的什么心,还是打电话报警吧。
在警察局,钱丑百口难辩,最后他说,自己给蛋糕店做了一个灯箱,账还没结,是想去要钱。警察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将钱丑放了。
钱丑不死心,又跑去蛋糕店,由于天还没黑,蛋糕店开着门。一见钱丑,李卯便掏出做灯箱的钱,想必警察已经跟她说了。可这并不是钱丑的真正来意,他拿着钱,站在门口犹犹豫豫不肯走,最后低声说:“其实,我是怕你想不开,才守在门口。”
李卯愣住,缓过味儿后,笑笑说:“谢谢你。”顿了顿又说:“假如你不急着走,可以尝尝我新作的曲奇。”
这一次的曲奇与上次吃的味道自然不同,钱丑既慌乱又开心,吃完后问:“这个店,你还打算开下去吗?”
李卯叹口气:“我总得活下去,不过,我只会做曲奇。汉堡了,三明治了,我是不会的,那些太麻烦,还得往里面夹蔬菜和肉。”提到肉,她忽然想起厨房里那个庞然大物的冰柜,孙寅活着时候,买的这个冰柜,往里面储藏了很多肉。
巧得很,錢丑也想起那个冰柜,随口说一句:“那个家伙好大,都能装下一具木乃伊了。”
李卯说:“当时我老公买的时候,我也这样说。”话说到这里,李卯忽然想起孙寅,那些过往,一想起来便如同上刑,李卯低下头去,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
钱丑手足无措地连声说对不起,他见不得自己喜欢的人难过,这也是一种惩罚。
李卯将头抬起来说:“看得出你是好人,这样吧,我烧两道菜,你陪我喝点酒。”
李卯手脚麻利,或许早已准备好,酒菜很快就端上桌,摆了三双筷子,三把椅子。
“今天,是他的头七,或者还能回来看看。”李卯湿着眼睛说。
钱丑悄悄地左右环顾一圈,心想,即便孙寅来了,我也看不见,可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有些发慌。
接下去就是一男一女相对而坐喝酒。太阳走了,暮色深去,酒意浇灌愁肠,这样情景之下会发生什么?钱丑会向自己心仪多日的女人一诉衷肠吗?不,尽管他被李卯优雅而高洁的气质,迷得神魂颠倒,死而后已,可他始终忘不了这个女子刚刚死去最爱的人。李卯当然也不会有别的想法,她深信不疑,孙寅已经将自己全部的爱都带走了,即便生死相隔,那坚不可摧的爱也会如铁索桥一样横跨阴阳两界,此后,唯有两岸相望,一生终了。
后来,李卯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钱丑起身想将她抱在床上。就在这时,讨厌的欲望忽然附体,钱丑的心颤了一下,又把心中的火苗狠狠掐死。那张床如同雷池。
钱丑离开的时候,随手将灯关掉,随即又摁亮,轻轻掩上门走开。已经走出很远,钱丑又回头望一眼从窗口涌出的灯光,心里稳稳当当的舒坦,只要亮着灯,就说明李卯还活着,哪怕为谁活。
说到这里,赵子满脸得意地瞅着我,言外之意,如此构思堪称绝妙,该得到称赞。然而我却硬邦邦地沉默着,以至于他很失望。其实对我而言,小说再好也是小说,人生再坏也是人生。
我的沉默,千斤闸似的挡住了赵子。也好,趁此想一想,那些与我有关的往事。
那天早晨,她说想吃泥鳅,让我去市场买。没错,无论怎么浪漫,都避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泥鳅。结果我们美好而平静的生活,就被几斤泥鳅给扰乱了。
我买完泥鳅后,顺道去银行取了点钱,不想被一个丧心病狂的劫匪瞄上。他一直跟着我,在一条幽雅而僻静的巷子里,猛地窜出来,一棒子将我打晕,抢走我身上的钱后还不满足,又将我背到他的家中。那是一个满是发霉味道的小黑屋,墙上挂满翁美玲、梅艳芳、张国荣的照片,厕所的水龙头老化了,总是不停地滴滴答答漏水。
他将我五花大绑地捆在一把高背椅子上,双手托腮坐在对面一张黑漆漆的铁桌旁,一动不动盯着我。即便我放声大喊救命,他也不制止,直到我喊得浑身无力,他才得意洋洋地说:“这附近连个人渣都没有,你喊个屁呀。”我开始好言相求:“不是要钱吗?我银行卡里还有不少钱,密码完全可以告诉你。”
他嘿嘿一笑,摸走我的钥匙链,套在食指上转来转去。我猛然醒悟,他是要去我的家里。一想到这里,我不由吓得魂飞魄散,她还独自在家里,若是遇见这个疯子,后果难以想象。
劫匪很欣赏我惊恐的样子,隔了老半天才哑着嗓子说:“怕有个屁用,赶快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
我瞪着他骂道:“你这个疯子,休想。”
劫匪朝我扮了个鬼脸,转身取来一个电钻,慢悠悠地插上电源,再次问我:“到底说不说?”
我望着嗡嗡转动的电钻,心里怕极了,可是假如我说了,随后面对劫匪的就是她,就是那个即便熟睡之际,我也满怀柔情,手托双腮凝望良久的女人。想到此处,我的惧意立即就换成固若金汤的一声不。
劫匪狞笑着说:“现在不说,待会儿可就没机会了。其实我也很好奇,一个人的满口牙都被电钻搅断,会是什么样子。”
眼见劫匪一步步走近,我用力挣扎着,不想身子一歪,连人带椅子都倒在地上。随后,一只大脚便踩在我的脸上,电钻尖叫着,慢慢移向我的嘴,我不敢大骂或者求救,紧紧闭着嘴,但满口的牙却酸疼得一塌糊涂,拼命地打颤。嗡嗡嗡,那是来自地狱里的声音,在牙齿被绞碎之前,我忽然大声喊道:“我说。”
在我说出自家门牌号的时候,那个曾让我觉得是这世上最温暖的地方,立即隔世一般的恍惚起来。劫匪用食指转动着我的钥匙链,得意洋洋地走了。我缩在绳索里,呜呜痛哭。那一刻,羞辱、自责与另外一种绝望的厌恶让我忘记了她的安危。直到月色被晨光溶解,灌了满满一屋子耀眼的阳光,我才猛然警觉,这个时候,劫匪早已去过我的家了,她会不会被……也便在此时,我忽然发现,系住自己双手的那根绳子,只不过是打了一个活结。我又惊又喜又满心恶苦,没有人能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那个充满嘲弄的活结,才是最坏的魔鬼。
我咬开绳索,飞奔回家。走到门口时我却犹疑了,很显然,那个劫匪昨晚已经来过,那么,等待我的定然是一幕可怕的场景。我的妻子或者已经惨遭杀害或者五花大绑衣服破碎被那劫匪糟蹋了,我想象不出第三种可能。然而,第三种可能却忽然出现眼前。妻子推开门从屋里走出,除了双眼有些浮肿之外,浑身上下一丝不乱。
你没事吧,我们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随后,我上下左右打量她,又冲进屋内四处查看,最后一屁股坐在地板上,长长松了一口气。
她一脸不满地问:“怎么,你怀疑我在屋里藏了人?”
我摇了摇头问:“昨天晚上,没有劫匪闯进来吧?”
她哼了一声说:“什么劫匪?我看你是想问奸夫吧?奸夫没有,淫妇倒有一个,就站在你眼前。”跟着,她的眼圈一红,絮絮叨叨盘问起我怎么一晚上没回来,让她担心受怕。
我放心了,也许那个劫匪昨天遇见别的事,没有来。结局竟然是个惊喜,仿佛中奖,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惊喜之余,我心里也有一丝死亡般的难过,仿佛在祭奠什么。
这件事,我当然瞒着她。接下去,生活一如既往,只是我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不遗余力地去爱了,总觉得我们之间隔着另外一个人,这个第三者,也许就是那个曾鬼魅般出现过一次的自己。
想到鬼,我不由猛地打了一个寒戰。这个冬天的早晨好冷,那个刚刚死去不久的陌生人,是否已经变成了鬼。
这时,人群开始缓缓移动,挤牙膏似的在前排挤出一条队伍,绕过死者的遗体,向他告别。喋喋不休的小说家,也从他虚构的世界里抽身出来,跟我一前一后地经过死者遗体。我忽然发现,赵子的脸上现出一种古怪的神情,与其说是悲痛,还不如说是悔恨。
从大厅走出来后,天还没有亮,四下里影影绰绰,赵子终于借了火将烟点燃。我很好奇他跟死者的关系,刚要开口询问,可他却吐了一口烟圈,又讲起那个小说——
那天以后,钱丑经常去蛋糕店,却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爱意。李卯也将这个理解为一种同情,欣然接受了。
刚才我不是说过吗?钱丑是做灯箱的,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就好似自己是个巨大的发光体,每一个灯箱都是从他身上割下来的切片。假如,那家找他做灯箱的店铺,恰好在万贯街,他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屁颠屁颠地赶去。对了,我忘记交代,李卯的蛋糕店所在街道就是万贯街。
钱丑有个心愿,就是希望万贯街的每一个灯箱都出自他的手,那样,一到晚上,满街的灯箱都陪着李卯,就好似他守在李卯的身边一样。
这天,钱丑又坐着公交车去万贯街找李卯,手里还拿着一个用罐头瓶做的灯笼。说起这个灯笼,还是他很小时候,母亲给他做的呢。那是一瓶海棠果的罐头,吃完之后,母亲在里面安了一个座,插上蜡烛,再将瓶壁贴上一层红纸,绑上铜丝,用木棍挑着,一个灯笼就做好了。钱丑管这盏灯笼叫海棠灯。
钱丑拎着海棠灯满街跑,红影摇曳,蜡烛燃烧的地方,仿佛还有丝丝缕缕海棠果的甜味飘来。灯笼并不是很亮,可钱丑却觉得世上所有的光都在这里,满街黑漆漆的,他真想拎着海棠灯,在每户人家门口都站一会儿,给他们照照亮。当然,现在钱丑只想将这盏海棠灯送给李卯。
路上,两个乘客坐在身旁,嘁嘁喳喳小声说话,一个说,你知道吗?最近有个疯子,总是拿着一串钥匙,挨家挨户地开门。另一个说,是啊,我也听说过,不过,这两天却没听到他的消息,说不定去了什么地方。前一个说,这样的疯子却也没什么,最怕的是另外一种疯子,拿着汽油自焚。后一个说,自焚就自焚呗,还非得到公交车上,拉着别人一起陪他死。说到这儿,两人都住了嘴,紧张兮兮地左右望望,好似真有人要拿着汽油自焚似的。
那两人的话,钱丑一一都听进耳内,不由想到,若是我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呢?惊慌失措地跟着大家一起逃命吗?不,自己平凡得这么久,实在厌烦了,不如做一回英雄,到时候,一声断喝,先将自焚的人镇住,然后,紧紧将那人抱住,让其他乘客一个个逃走。火烧到身当然撕心裂肺地疼,那人拼命挣扎,可我死死将其抱住,就是不松手。
想到这里,钱丑仿佛感到身上真的有股火辣辣的灼痛,却也悲壮。不过既然是想象,他就对自己开恩了一下,最终并没有被烧死,只是毁容了。当天的报纸、电视都对他的英雄行为大加宣传,医院的走廊挤满了慕名而来的人,争先恐后地为他献血。以前的熟人,都以认识他为荣,尤其是李卯,她万万没有想到,曾经暗暗喜欢她的这个灯箱匠,竟然如此英雄了得。
钱丑越想越激动,只可惜车到站了。他依依不舍地下了车,伸手一看,掌心激动得满是汗,不由摇头苦笑。就在这时,钱丑忽然想起那盏海棠灯忘记在车上,连忙去追公交车。一个乘客摇开车窗,作势要将海棠灯扔出来。钱丑失声喊道,别扔。可已经晚了,那人一扬手,海棠灯便飞出车窗。钱丑跌跌撞撞地伸出手去接,同时,一辆卡车迎面而来,钱丑被撞飞了出去,几乎是和海棠灯同时摔落到地面上。玻璃破碎的声音,在这个夕阳欲落的黄昏里是那般哀伤与惆怅。
钱丑仰面躺在路中间,用手指碰了碰海棠灯的碎片,仿佛再次闻到一丝甜甜的海棠果味道,那是来自童年的味道。同时,那辆公交车里的乘客都伸长了脖子,回头朝这边看,满脸的好奇与隐隐约约的兴奋,那可是钱丑在想象里搭救过的人们啊。
钱丑刚一死,夜色就裹尸布一般蒙住了万贯街,灯,一盏接着一盏亮了。李卯走出蛋糕店,将灯箱点亮,她也看见很多人朝着远处跑去,想必又出车祸了。想起孙寅死时的情景,李卯一阵眩晕的难过,慌忙转身进屋。李卯哪里知道,那个刚刚死去的人是钱丑,更想不到那盏破碎的海棠灯,本是要送给她的。
故事到此结束,赵子就好似功力全都化去的武林高手,浑身无力地坐在路边。尽管我一直表现得很淡漠,但还是为钱丑的死微微难过了一下 。
“抽一根吗?”半晌后,赵子微微仰起脸,疲惫地问。
我接过烟,极其自然地取出火机,将烟点燃。赵子没有问,为何我有打火机刚才却不借给他,而我也没为此感到难为情。为拒绝而拒绝,这已成了习惯。
“今天,可真冷。”赵子一遍遍重复这句话,将衣领竖起,挡住半边脸孔。
此时,死者已经火化完毕,他的亲属将骨灰划拉划拉,都收拾到一个方方正正的骨灰盒内,然后,捧着骨灰盒往存放处走去。也就在这时,我忽然看见骨灰盒上的照片以及死者的名字,赫然竟是钱丑。
我不可置信地看了赵子一眼,他像躲避暗器似的,侧了一下身子,然后满脸歉意地说:“没错,死者就是钱丑,我不该将他写死,我太自私了,为了让自己的小说更有震撼力,就牺牲了钱丑,难道小说一定要以悲剧收场才能打动人心,称得上好小说吗?”
我没有理会赵子,默默地吸了一口烟,当淡蓝色的烟雾缓缓飘起之时,我也随着飘回到往事之中。
那件事之后,我不止对爱情绕道而行,也失去了做爱的功力,甚至还养成了疑神疑鬼的毛病。每次,她出门的时候,若是化妆,我必然要冷言冷语地追问一番。
她最怕的事终于还是出现了,解释是多余的,唯有沉默。那个暖融融的家,像被岁月打进万劫不复的冷宫,默然凝霜。其实,我也恨自己的多疑,本该要相信她的,可每次都忍不住胡思乱想。或许,我暗中更希望她真能做一件对不起自己的事。我出卖她,她背叛我,这样才算扯平了。
有一天,我假装去跟朋友打麻将。临走时我告诉她,自己晚上不回去了。然后,我坐在对面的酒店,一直喝到深夜,醉出雄心豹子胆,这才晃晃悠悠地离去。快到家的时候,我的胃里翻江倒海,于是蹲在路边吐了起来。就在这时,我忽然看见有一条人影鬼鬼祟祟站在我的家门口,转动手中钥匙将门打开,随后闪进屋内。
嘿,她在外面果然有人,连家里的钥匙都给他配了一把。我又惊又怒,同时也有一丝兴奋,拎起一块砖头,蹑手蹑脚跟了进去。快到那人身后时,我低喝了一声,去死吧,砖头狠狠砸了下去。那人一声没吭便倒了下去。我怒冲冲地将灯打开,她竟然没有在家,回头再看躺在地上的人,我不由愣住,死者却是当初的那个劫匪,他可真不经打,一砖头就毙了命。
我坐在地板上,怕得要命,到底怎么回事?劫匪为何隔了好几个月才找到我的家?难道他忘记我告诉他的地址了吗?以至于这些天一直在找?我摸了摸劫匪的兜,只有一枚两面都是人头的硬币,顺手放进自己兜里,然后将他的尸体藏在厨房的冰柜里。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我将这事瞒着没说,免得深更半夜吓到她。第二天早晨,我和她坐在门口吃西瓜,就在我打算告诉她的时候,她忽然让我去给做灯箱的小伙子送块西瓜。我的醋意又来了,很不情愿地走了过去。忽然,劫匪的那枚硬币从我兜里掉出来,这还了得,若是被人发现,很有可能顺藤摸瓜找到劫匪的尸体。我慌忙去追,結果一辆卡车直奔我而来,好似预谋已久。
是的,我想起来了,我叫孙寅,我已经死了,死在赵子的小说里。
据说,人死之后最怕光。现在黎明将至,远处的地平线上霞光隐现,很快就会有一轮太阳出世,我好似正在等它。
作者简介:木糖,男,汉族,原名李洪有,现居黑龙江大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林》《岁月》《北方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儿童长篇小说《春知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