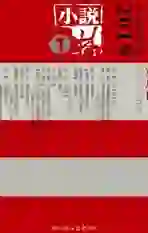在西乡见到曾楚桥
2019-02-28曾楚桥
美国人道格拉斯是当代巫术大师。他是个遗腹子,出生于法国南部风景优美的普罗旺斯。根据《道格拉斯传》里所载,老道格拉斯是费城一个落魄商人的儿子,兴趣广泛,曾一度竞选过州长,失败后心灰意冷地远走法国,在普罗旺斯邂逅当地一个陪酒姑娘玛丽。老道格拉斯对玛丽谈不上爱情,只是身体在夜晚短暂地相互吸引。除此,还有另一个原因:老道格拉斯到了普罗旺斯后,已经穷得口袋丁当响了,他内心向往西班牙,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斗牛士,为此,他只能打陪酒女郞玛丽的主意。
老道格拉斯不愧是个调情高手,他在极短的时间内骗取了玛丽的信任,并成功得到她的一笔资助,此举明显过于卑鄙,因此《道格拉斯传》里仅一笔带过,后世的研究者却针对此大做文章,认为老道格拉斯绝对是个薄情寡义之人。然而玛丽对他却是一见钟情,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甚至为他怀上孩子也不后悔。但老道格拉斯对此毫不知情,他在普罗旺斯仅仅度过了一个星期,就谎称要远渡重洋到中国做陶瓷的生意,实际上他是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并在马德里顺利地成为一名斗牛士。可惜的是,仅仅半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年仅二十八岁的老道格拉斯就把身体挂在公牛的尖角上,成为第三十二位死于斗牛的美国人。关于他的死,大着肚子招摇过市的玛丽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收到,她还以为老道格拉斯到了万里长城,到了东方的瓷都,留恋着东方的花花世界不愿意回来了。
道格拉斯和他父亲一样,也是个兴趣极其广泛的人。他天资聪颖,十八岁即到英国的剑桥大学攻读天体物理学。但只读了两年,就把兴趣转到了巫术上来。他遍访英国民间巫术师,虚心向他们求教,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学习和研究,道格拉斯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巫术大师。他的成就令世界为之瞩目。在巫术界一直流行他最惊人的论断:
巫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主宰时间。
据闻,为了证明他这个观点,他在乡间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验证会,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施用巫术,让年老色衰的玛丽回到了当陪酒姑娘时的美丽样貌,因此轰动一时。如此巨大的成就,当母亲的自然欢喜,事实上,玛丽更为之心花怒放的是,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还能找回到丢失已久的青春,仍然是过往当陪酒女时那么美丽动人。玛丽看着镜中的自己,抚摸着手上那不敢相信的水嫩肌肤,往事便影影绰绰而来。当玛丽委婉地向儿子传达希望他到中国寻找父亲时,道格拉斯便一口答应下来。道格拉斯早就对东方的神秘学产生了怀疑。尤其是中国的特异功能,他认为不过是中国流行的一种江湖小骗术罢了。
临行前,母亲告诉道格拉斯,他父亲在中国是正当的商人,做的是陶瓷生意。她再三叮嘱道格拉斯,他父亲最喜爱的运动不是足球,而是斗牛,只是不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没有这项运动。这是道格拉斯所能知道的关于他父亲的所有信息。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想在茫茫人海里找到自己的父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他之所以前往中国,除了安慰母亲之外,他想更多地了解这个充满神秘的国度。
道格拉斯的第一站到了中国的景德镇,在那里,面对着那些瓶瓶罐罐,他了无趣味,更无心寻找父亲。父亲在他的脑海里面目相当模糊。当他打听到湖南才是中国的巫术之乡时,他选择了南下。在湘潭大学,他逗留了足足五年。他除了学到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之外,还学到了湖南人的好勇斗狠。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江湖大学教授李瑄,这个自号书生的大学教授,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无意中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内部刊物上看到一篇关于湘西赶尸的论文,论文的作者叫曾楚桥。这篇论文,以一个赶尸人的身份,从灵魂学上解释湘西赶尸行为的种种可能性和可行性。令书生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此文作者曾楚桥自称是中国目前唯一还懂得此道术的传人。
关于曾楚桥,书生还是有所了解,在深圳的打工文学作家里,还算得上是个人物。据说,其小说艰涩难懂,在圈子里被读者普遍认为是故弄玄虚之作。在某次作协会议上,书生还见过其人。印象中,有点非洲人的皮肤,牙齿特别白,但又有点印度人的感觉。
书生感兴趣的不是曾楚桥本人或者是他的小说,而是作为湘西赶尸术的唯一传人,曾楚桥在他的论文中言之凿凿地坚称他曾执此为业。他在论文的后面附上一篇通俗易懂的故事。故事的大概是曾楚桥在某年某月为一个贫穷而客死深圳的工友赶尸回乡。文中附有照片,照片上客死他乡的打工人面目狰狞,眉宇间流露出难以诉说的怨恨与愁苦。单凭这篇论文和故事加上几张看上去年代久远的照片,很难判断事件的真實性。毕竟湘西的赶尸术在民间只是个传说。但书生却宁可信其有。他电邀远在湘潭大学的外国朋友道格拉斯前来深圳,他希望能够在骄傲的道格拉斯面前好好地展示一下中国的巫术,让这个外国佬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当然,如果这一切只是子虚乌有,那么他也算是为中国的学术打打假,面子上也还算过得去。
年届五十五岁的美国人道格拉斯受书生之邀来到深圳宝安,书生和他经过商量,选定了在西乡医院相邻一间名叫洞庭渔家的饭店宴请曾楚桥。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如果这一切如曾楚桥的论文中所说,那么医院里的停尸间,将是曾楚桥大展拳脚且又是最便捷的地方。他们固执地认为,医生既然是这世界真正的刽子手,那么医院就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死人用作表演。
时值西方圣诞节,饭店的门口早早就安排圣诞老人在迎接每一位客人的到来。饭局原定下午五点开始,但在约定的时间里,赶尸人曾楚桥没能准时来到。书生打了几次电话,得到的答复仍然是路上大堵车,一时还无法到达西乡。道格拉斯和书生两人在包间里坐得索然无味。喝淡了一壶陈年普洱之后,书生打电话给他的入室女弟子肖菲菲,让她前来作陪。肖菲菲在书生的研究生里是最出色的一位,而且还是书生的秘密情人。他们保持这种地下情人的关系已经整整八年。在此之前,书生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起过他的这位特别的女弟子。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又或者书生面对的这位外国朋友据说还是个老处男,忽然就有了倾诉的欲望。
“我的朋友,我老实告诉你吧,我这位弟子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她身上有着人性中最本真的一面。每个和她认识的人,几乎都在说她的好。她天性善良,乐于助人,成绩还特别优秀,是我二十五年的教书生涯中,最为优秀的学生。”书生的话题一经打开,便滔滔不绝地夸起他的女弟子来。书生对他的这位女弟子可谓一点儿也不吝赞美,从天上夸到地下,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过分。不过稍为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书生在赞美他的这位稀世女弟子时,没有一句话涉及到肖菲菲的外貌。书生只在赞美临结束时加上了一句:“其实,我爱她,非常爱她。为了她,我可以倾家荡产。我一天不见她就茶饭不思。”由此可以猜测,肖菲菲在书生的女弟子里肯定也是最美丽的,否则很难让书生达到一天不见就茶饭不思的地步。
“我知道。”美国人耸耸肩答。
“你知道?”书生问。
“没错。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道格拉斯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
“我还没开始说,你能知道啥?”书生有些诧异地抬起头来,看着眼前这位外国朋友,颇有点不以为然。
“我当然知道。要不要我讲一讲你们之间的故事?”道格拉斯摆出一副挑衅的样子,神态十足的那些湖南痞子。
“你们相识于2006年9月,肖就是那一年考上了江湖大学,肖到江湖大学报到,你在林荫树下碰到她。报到的那一天太阳很白,肖穿着很薄的白衬衣,汗水淋漓地拖着她的大皮箱,你看到湿衬衣下肖的坚挺乳房,一下子你的精虫就上脑了。”道格拉斯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接着又特别地加了一句:“对,就是精虫上脑了,这是最准确的描述。”
书生此刻像喝了酒一样,面色绯红,眼神迷离起来。他还记得,第一眼看到肖菲菲时,他听到内心轰然一声巨响,他知道他一直维护了多年的道德之墙终于倒塌了,他对自己说,是你了。一定是你了。在那一刻间,他像年轻了十岁,他顾不上众人的目光,毫不犹豫地帮肖菲菲拉上她的大皮箱,脚步轻快地走在江湖大学的林荫道上。
“你强奸肖是在一个下雨的晚上。你以辅导为名,把肖骗到你的书房,狂风大雨给你做了很好的掩护。肖一进入你的书房,你一下子就跪到了她的脚下,像狗一样亲吻她湿滑的脚面。当然现在说你强奸她,可能不太恰当,应该说是顺奸。肖后来应该是顺从了的。”道格拉斯说到这里嘴巴带着一丝怜悯的笑意望着他的中国朋友。
“是的,我当时确是强奸了她,可是我并不后悔。”书生说。
那个雨夜,书生在他的书房里坐立不安。一本《百年孤独》翻开停在一百零五页的地方不动了。书生的眼睛盯着页面,但心思却飞到了肖菲菲的身上,下这么大的雨,他不知道她会不会来。大雨会不会打湿她的白衬衣?他设想了无数种可能,但没有一种能让他安下心来的。书生把头伸出窗外,让大雨把头发淋个湿透,他想当然地以为雨水或者能让他清醒了一点,但淋湿之后,却发现他竟然不可遏止地想白衣飘飘的肖菲菲,想她衬衣湿透后隐约可见的坚挺乳房。书生像傻子一样给了自己两巴掌,他听到清脆的巴掌聲,同时,也听到了敲门声。当肖菲菲出现在他面前时,所有的可能都失效,他只感到腿一软,就跪到了肖菲菲的脚下。当嘴唇与她的脚面接触的那一刹,这个一向站在道德的高坡上对学生们指手画脚的教授,终于泪水长流起来。他像一个在黑暗里迷路的孩子,一双鸡爪一样的瘦手,在肖菲菲的身上艰难地乱扯起来。
“不好。”肖菲菲说。
“OK。”书生带着哭腔说。
“不好。”
“OK。”
那个雨夜的许多细节,并不为人所知。它们像一坛陈年佳酿存放在书生的记忆里,历久弥香。
“我的中国朋友,关于你们的第一次,有一个细节我想探究一下。我之所以说是顺奸,是基于后来肖叫你别扯坏了她的裤子。她心疼那新买的裤子。我想不明白,也无法理解,对于中国女人来说,贞操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比一条裤子要宝贵得多。可是,当时肖是主动解开了她的裤带,如此,你才能得逞,对不对?我的朋友,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道格拉斯双眼充满了疑问。
“肖菲菲吃过太多的苦。她是个贫穷家庭的孩子。你不知道,为了凑够学费,她爸爸把唯一的一头耕牛给卖了。你知道一头耕牛对一户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我的朋友,那意味着一家人的口粮!一件新衣服对她来说,则意味着一个月的伙食。我承认,我当时是精虫上脑了,即便是换作现在,我还是会跪到她的脚下,亲她的脚趾头。没有她,我的生活将暗无天日。没有她,我活着如行尸走肉。一句话,生不如死。你明白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的大师。”书生接着解释说。
“我知道,我能理解。我的教授,你一直资助她读完大学,还资助她继续深造,读完你的研究生。这对她本人来说,肯定是没有错。对她的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她付出了常人无法比拟的代价,她最宝贵的贞操和青春都贡献给了你。为了你,肖三次流产,她甚至等了你足足八年,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一个抗战都结束了。现在肖想嫁人,可是你却百般阻挠,你要是真的爱她,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离婚?你这样做不觉得很不道德吗?告诉我,教授,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道格拉斯神情严肃了起来。
“这些可都是我的隐私,你是怎么知道的?”大冷的天,书生额上却冒汗了,他现在才惊恐地发现,他在道格拉斯面前简直就是一个透明的人。刚才只顾着想念他的肖菲菲,并没往深里想,现在他越想越是害怕。眼前这个深眼窝鹰钩鼻的洋鬼子,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不是说,你们中国的巫术天下无双吗?能起死回生,能让死人再活过来吗?请问你的赶尸人来了没有?”道格拉斯看着眼前这个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大学教授,此刻却表现得如此狼狈不堪,不禁冷笑一声,心里显然是畅快之极。
书生顾不得满头大汗,掏出手机又给曾楚桥打电话,但得到的答复还是那一句,堵车呀!书生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学着外国人耸耸双肩,双手故作洒脱地向外一摊,表示无可奈何。
书生确实也无可奈何,又何止是无可奈何那么简单!这边是等了他八年且贴心贴肺的小情人肖菲菲,另一边是和他相濡以沫二十年之久的妻子。对他来说,他根本无法选择,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伤害。如果自己的妻子是个不讲情理的人,他说不定还能真的离了。但书生的妻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作为一个女人,她心细如发,岂能感觉不到自己的丈夫有外遇?但她并没有横加指责,她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在外人看起来,教授的家庭仍然是那么和谐幸福,仍然是那么值得人们羡慕。
“你真的爱肖吗?”道格拉斯忽然问道。
“这还用问吗?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吧,你听了这个故事大概就知道我有多么爱她了。是去年的十月份吧,她回了一趟老家,在她回家之前,我们刚刚吵了一架,她是赌气回家的。她发誓说回家之后就找个农民嫁了。她前脚进了家门,后脚她的家人便给她介绍男人。这男人是她家乡小县城一个小老板,她把小老板的照片发给我看,她的意思很明显,比我帅还比我年轻有钱的人有一大把。她还告诉我,她现在每天早上七点都准时和小老板去喝早茶,她还特意提到,他们喝早茶的地点,就是我和她经常去的那个酒店。老实说,我一看她发给我的这些信息,我就受不了。一下子精虫又上脑了,半夜十二点就打了个出租车风风火火地赶过去,四百多公里的路程啊。光出租车的车费就花了一千五百多。我在她说的那个酒店等她。我想亲眼看到她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是六点到的酒店,七点钟还差十分,我迫不及待地给肖菲菲发信息,我问她在哪,她回我说正和老板在酒店里喝早茶。我一看到她回的信息就笑了。谎言不攻自破。那一刻,我欢喜得流下眼泪来。我都这个年纪了,还像个小青年一样爱哭,但我不觉得丢人。因为我知道她也是舍不得我,一直爱着我的。她肯定看不上那些小老板。我告诉她我现在就在酒店里喝早茶。她不相信,我让她过来看。十分钟后她赶了过来,看到我真的在,泪水一下就出来了,就扑到我怀里不管不顾地大哭了起来。那一刻才会真正体会古代诗人的诗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啊。我的大师,你说,这是不是真爱?”书生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眼圈都红了。
“你确定你真的爱肖,无论她变成什么模样,老了你也爱她?”道格拉斯直视书生,很认真地问道。
“是的,我爱她,无论她变成什么模样。”书生说。
“好。我的朋友,我以你为荣。”道格拉斯笑了笑,脸上闪过一丝诡异的神色。
巫术师道格拉斯向服务员要了一碗冰水。他就着这碗冰水,洗了一把脸。然后用洗过水的手,出其不意地在书生的脸上也抹了一把。一阵清凉袭来,让书生无端地打了一个冷颤。
“朋友,你被爱情冲昏了头,我得让你清醒一下,你不会介意吧?”道格拉斯一脸坏笑的表情。
书生只有苦笑。他眼巴巴地望着门外,希望能见到他的心肝宝贝肖菲菲,但肖菲菲迟迟未到,这在他们之间,从来没试过。要在以前,书生一个电话,肖菲菲总能在十分钟内就赶到了。书生不禁烦躁起来。此前他打电话给肖菲菲时就在道格拉斯面前大言不惭地吹嘘说,他的小情人在十分钟之内就会到了。但现在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宝贝肖菲菲居然还没有来。书生拿出电话,想了想,又放回到口袋里。
“她会来的。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到。”书生满脸通红,样子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OK,我相信。肖就快到了。”道格拉斯微笑着说。
爱情对道格拉斯来说,就是两个傻子在黑夜里不知疲倦地相互摩擦,能不能擦出火花,或者说能不能互为温暖,姑且不论,单说这个过程,实在也无趣得很。只有巫术才能令世界变得美好。老处男道格拉斯的巫术无可置疑,他对世界的理解很简单,没有人逃得过时间的检验。自始至终他认为巫术能让世间的一切原形毕露,包括爱情亦复如是。
老处男微笑着,胸有成竹地喝着越来越淡的茶,意味深长地打量着他的中国朋友。偶或把手放进碗中洗一把,保持手的湿度。
当服务员端上第一道湖南菜红烧肉时,书生的宝贝情人肖菲菲终于姗姗来迟。不过她不是一个人来,她另外带来一个更年轻也更漂亮的女孩。女孩叫蓉蓉。
两个女孩一进入包间,说时迟,那时快,道格拉斯就捧起那碗洗手的冰水,猛地泼向肖菲菲。在一片的惊呼声中,只见年轻美丽的研究生肖菲菲,顷刻间容颜尽失。取而代之的是,满头白发加上满脸皱纹,她一下子竟然已经苍老了六十岁!老态龙钟的肖菲菲,样子显得相当怪异,身上穿着一身时尚的冬衣,行动迟缓地走到饭桌旁,浑浊的双眼望了一眼书生,仿佛似曾相识,但记忆却是如此模糊,她缺牙少齿的嘴动了动,大概是想問点什么,可出口的却是:“红烧肉啊,我最爱吃!”
包间里能听到书生长长的叹息声。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眼前的事实不能不让他相信巫术真的可以主宰时间!显然,这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他镇定自若地招呼蓉蓉坐下来,极有风度地向他的外国朋友抱抱拳头,表示佩服。此刻,道格拉斯一把将肖菲菲拉到身旁坐下来,亲自给她夹了一块红烧肉,这才招呼书生和蓉蓉:“吃吧。你们。”
短暂的惊愕之后,便是顺理成章的吃饭。蓉蓉边吃边抬头看肖菲菲,但此时的肖菲菲,已经不认识她了。在她的人生长河里,连情人书生都只是一个过客,就别说一个感情并不深的朋友了。她低着头只顾吃她的红烧肉,间或抬起头来,看看道格拉斯,又看看书生,仍然一脸茫然,她搞不清自己怎么就到了这里,这是谁在请她吃饭。她现在只知道红烧肉是她最爱吃的一道家乡菜,也只有这道菜她能啃得动,其他菜,她只能望菜兴叹。书生呢,既忙于向蓉蓉解释,也忙着给她夹菜,俨然把蓉蓉当成了他最爱的肖菲菲。大家在推杯换盏之间,他们都忘记了另一个前来赴宴的赶尸人曾楚桥。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曾楚桥迟迟不来,也许他根本就是大话说过头了,借口堵车不敢来了。书生他们不可能这样等下去。虽说是堵车,但失去了起码的礼貌。
酒过三巡,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借着点酒意,道格拉斯居然伸手在肖菲菲的脸上摸了一把。一阵短暂的冰凉如风一般掠过,肖菲菲的老脸一时间竟也红了一块。这个过程,蓉蓉看到了,书生也看到了。他们不约而同地都笑了起来。书生为此还和道格拉斯干了一杯。他甚至觉得现在的肖菲菲和这老处男真是绝配。他不怀好意地想,这个老处男,说不定就此喜欢上了老太婆肖菲菲。
“教授,你还爱肖吗?”道格拉斯盯着书生问。
“她现在都不认识我了。呵呵。”书生打了个太极,既不说爱,也不说不爱。
“是的,爱情不过如此。转眼间就不相识了。不过这样也好。肖现在可以嫁人了。”道格拉斯说。
“她现在这样还能嫁人吗?”书生越发觉得老处男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故意这样说,:“人都老成这样了,还谈婚论嫁干吗?”
“能。会有人爱她的。”道格拉斯话音刚落,包间的门口忽然出现一个白衣白裤的中年男子。该男子忽然一步跳到桌边,目光呆滞地看着道格拉斯。书生正想问这男子是干吗的,却见那男子忽然把双手弓起放到头上,仿佛两只尖角一般,左一下右一下地像头公牛一样在包间里奔突起来。那男子奔了一会又停在道格拉斯面前,眼光仍然呆滞,但嘴里却咕噜咕噜地吐着英语。他说得极快,书生的英文不是很好,仅听懂几个简单的单词,好像是父亲呀,斗牛呀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这男子是什么来头。男子脸色如纸一样白,像久病不起行将就木的病人一般瘦弱,皮包骨的手指伸开来,竹枝一般,动作虽然快,但并不协调,甚至有点僵硬的味道。不过看起来肯定是中国人,只是英语说得如此流利却是少有。
那男子用英语对道格拉斯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道格拉斯的脸色突然大变,额上汗水涔涔而下。书生看到道格拉斯眼里已满是泪水,只见他冲那男子叫了一声:“Dad!”伸手要去拉那男子。男子刚答了句“Son”,就啪的一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令人措手不及。书生虽然搞不太懂英文但他听到道格拉斯叫那男子做爸爸,而那男子在倒地前分明也在叫他儿子。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正惊愕不定,包间里忽地又涌进几个身穿白大褂的男子。一看就知道是医院里的医生。医生一来就俯身给那男子做检查。简单的检查完了,医生摇摇头表示人已经死了。
“真是奇怪。明明是死了的人。他是如何跑到这里来的?”医生向书生他们道过歉后带着疑问便把死人抬走了。包间里只听到道格拉斯的抽泣声,他双手抱头,撑在饭桌上一边叫爸爸,一边泪流满面。他哭得如此伤心,仿佛那死了的男子就是他的父亲一般。没人知道刚才被医生抬走的男子到底和道格拉斯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仍然活在道格拉斯的心中。
大家正不知如何劝说道格拉斯,忽然一人长笑着进入包间来。书生定眼一看,竟然就是迟迟不来的曾楚桥。这个被评论家号称是深圳的打工作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苦大仇深,虽然还是那么黑,但他壮硕如牛的身体无一不表明,他活得挺滋润的。作家目光炯炯盯着书生看了一会,然后却朗声笑着把手伸给了道格拉斯,他也许不屑于和书生这种伪君子握手了。老处男道格拉斯颤抖着伸出他巫术大师的手,紧紧地和作家握在一起,使劲摇了摇抽泣着连连说了几声谢谢。
“时间能建立一切,但也能毁掉一切。”曾楚桥对道格拉斯说。
“OK,你带她走吧。”道格拉斯说着眼睛望向了肖菲菲。肖菲菲此刻眼睛忽然亮了,她迅速地站起来,像见到久别的情人一样,亲热地扑进了曾楚桥的怀里叫了一声:“爹!”
“丫头,委屈你了。我们走吧。”曾楚桥拉起肖菲菲,走出饭店的大门,然后渐渐消失在灯火通明的西乡大街。
作者简介:曾楚桥,男。广东化州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六届网络作家班学员、广东省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作品曾获全国首届鲲鹏文学报告文学一等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深圳第五届青年文学奖、第十届《作品》奖等奖项。小说多次被《文学教育》《小说选刊》《作品·选刊》等选刊选载,并入选《2007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3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05-2006年广东小说精选》《2007-2008年广东小说精选》《深圳读本》《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等多种文学选本。部分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观生》《幸福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