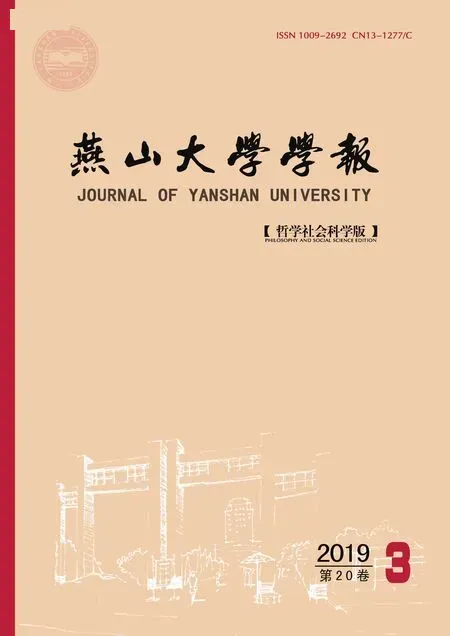1945年以前《道德经》在德国的译介研究
2019-02-25唐雪
唐 雪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北碚400715)
一、译介背景:第一次“道”的热潮
《道德经》(又称《老子》)是道家思想最重要的典籍,这部经典充满了深沉的智慧之言,展示了老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之一,也早已被翻译成包括德语在内的三十多种外语,是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著作之一。1870年,波莱恩克那教士(Reinhold von Plaenckner)和神学家史陶斯(Victor von Strauss)先后以“TAO 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和“LAO TSE'S TAO TA KING”为名出版了最初的两个《道德经》的德语全译本,打开了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序幕,自此之后老子学说开始迅速在德语国家传播。德国学术界对老子的接受和研究在1920年左右达到了高潮,为第一次“道的热潮”①。究其根源,特定的学术根源和时代背景造就了该阶段的翻译和研究热潮。
首先,这股热潮与欧洲老子研究的兴起和繁荣密切相关。18世纪初,以白晋(Joachim Bouvet)和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为代表的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开始尝试系统地探究《道德经》与《旧约》之间的关系。在白晋等人之前,由于儒家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更广泛和深入,因此入华传教士们对儒家典籍的研究更为重视,老子和《道德经》则鲜有西方人关注。而白晋等人运用对《旧约》的索隐式注释方法来研究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典籍②,他们对《道德经》的研究打破了西方世界中忽视老子学说的传统,对《道德经》在欧洲世界的传播起到关键的促进作用。此后,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于1823年发表了《关于老子的生平以及作品报告》,并在文中选译了《道德经》的部分章节。他的弟子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法语全译本于1842年出版,这两位学者将《道德经》的影响辐射到欧洲其他诸国。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道德经》自然开始传播至德国并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
其次,这一时段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饱受战乱折磨的动荡时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去的各种灾难和战后的社会秩序重组使知识分子们的精神追求和社会物质发展产生巨大失衡,思想界笼罩着悲观和消极的情绪,“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思想界,普遍弥漫着一种文化危机和价值重估的倾向”③。因此他们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和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东方文化研究成为欧洲学术界的新热潮,《道德经》中的“自然”“无为”等概念在德国知识分子界引起了共鸣,最早翻译《道德经》的波莱恩克那教士在其译作前言中的呼吁反映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心声:“而是向所有对中国、中国人和来自中国的事物吹毛求疵和嘲笑的人展示:在最古老和最遥远的时代,拥有健康而高尚的思维方式的智者已经在中国生活着……我认为……摆脱物质主义,能够引向一种纯洁或者更纯洁的神学观和世界观。”④
然而随着希特勒上台,整个汉学研究界都随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933年后的政治事件使德国汉学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损失的一部分已无可弥补。”⑤原本发展迅速的汉学研究在第三帝国时期却成为政治的工具,一方面出于政治因素,德国当局对中国的关注度未曾减弱,二战期间设在北京的“德国研究所”一直受到当时德国外交部的资助,德方工作人员都是由政府派遣。⑥而另一方面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许多德国汉学研究者们或被迫停止研究或流亡他乡。在此背景下,德国的《道德经》的译介和研究逐渐式微,出版的译本数量急剧减少,“1927年后几乎没有《道德经》译本出版”⑦。迫于政治压力,许多译者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发行,或选择将译本在国外出版。但正是这些译者们的坚持,才使《道德经》在德国的译介历程没有被迫中断,他们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最早的《道德经》德语全译本考述
德国的《道德经》翻译虽晚于欧洲许多国家,但是《道德经》进入德国之初便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之处。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最早的两个德语全译本均在1870年出版。其中一部的译者为波莱恩克那教士,书名为《道德经——美德之路》(TAO 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另一部由神学家史陶斯翻译并以《老子的道德经》(LAO TSE'S TAO TA KING)为名出版。由于两部译作面世的间隔时间较短,且后者的影响更广泛和持久,因此在一些研究中混淆上述两个译本的出版顺序和作者,甚至误将史陶斯的译本看作是第一部德语全译本。根据史陶斯在译本前言中谈及,在他刚完成这篇前言之后,他便得到一本波莱恩克那翻译的名为《道德经——美德之路》的书⑧,据此可知,波莱恩克那教士的译本较先出版,应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道德经》德语全译本。
当时,法国学者们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在开始时间和发展程度上都先于德国,两位最早的《道德经》徳译者显然受到雷慕沙和儒莲的影响,在译本前言都评论了两位法国前辈的译文。尤其是波莱恩克那教士还坦言,他的翻译受到雷慕沙认为《道德经》晦涩难懂因而放弃全译的启发,他认为《道德经》是一部完整和完美的图画,其内部的各个部分精妙地编织成一个整体并构建了逻辑化的思想体系,因此将单个的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开是不可能理解这本书的,只有在多次的阅读和研究整本书之后,才能准确把握《道德经》中的思想。
虽然波莱恩克那教士的译本出版时间更早,但史陶斯的译本影响更深远,传播和接受更广泛。1923年版的《勃罗克豪百科辞典》将史陶斯的译本称为“最佳德译本”⑨,他的译本至1959年为止再版4次,被众多后继译者借鉴和学习,并且被许多学者视为了解老子学说的重要途径。史陶斯受“索隐派”的影响,认为像老子这样的东方智者拥有对上帝的正确认识,《道德经》就是包含基督教教义的重要典籍和《圣经》隐喻式的表达。然而,与“索隐派”直接比较《道德经》与《圣经》的方法不同,史陶斯则主张从《道德经》本身去探究“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三、代表译者的宏观阐释及翻译观解析
(一)最早的《道德经》德译者史陶斯(Victor von Strauss)
作为《道德经》德语译介的开启者,史陶斯(1808—1899)对《道德经》的翻译和阐释建立在与基督教密切联系的基础上,首先从译者对“道”的理解便可探知他翻译时的这种神学倾向。史陶斯在译本中将“道”在《道德经》不同章节的主要含义罗列出来:“道”是不可捉摸的永恒存在(第25章);“道”具有空虚无形和不可估量的特征(第4章),以及不可确定、不可听见、隐匿无形(第14章),是万物的根源(第1章)和所有本质的祖先(第4章);道”既是万物之始祖(第21章),又是万物之终点(第16章);“道”永远没有需求和要求(第34章),也不会变老(第30章、55章);“道”蕴含精准的思想(第21章);按照“道”的准则做事,就能成为“道”的一部分(第23章);“道”能够带来和平(第46章)、庇护善人、拯救恶人(第62章)。⑩经过上述归纳,史陶斯最终提出,能够同时兼具上述特征的“道”就是“上帝,只能是上帝”⑪。但在译文中,他却将“道”直接音译为“Täo”,而不似有些译者翻译为“神”(Gott)或“上帝”(HERR),因为他认识到古代汉语中没有与“上帝”相对等的词语,因此没有必要为了将“道”德语化而生硬翻译,这反映了史陶斯在翻译时并不局限在神学阐释的范围中,为了让译文更加贴近原文会灵活处理。
史陶斯意识到当英、法等国的学者们通过努力翻译将中国古代思想介绍给本国国民时,德国学术界却对此未显示相应的热情,只有少量学者开始翻译中国典籍,更遗憾的是,许多德国人对中国思想的看法相当片面。因此,他希望自己的译文不仅为一般学者,还特别为哲学、宗教学研究者翻译和阐释中国最重要的古代哲学思想。所以,史陶斯提出翻译需要保证最大的精确性和尽量接近原文的简洁。但是,单个汉字的多种意义无法与德语或者欧洲其他语言一一对应转换,译者时常找不到相应表达。鉴于此,史陶斯在译文后加入每个章节的详细评论,一方面保持了译文的简洁风格,另一方面详尽展示译者对《道德经》的阐释和让尚未了解老子思想的读者们更易理解,这种排版形式也成为之后《道德经》译本常用的模式。
(二)神学影响下的《道德经》德译者于连·戈利尔(Julius Grill)
将老子与耶稣作平行比较是天主教神学家和东方学家于连·戈利尔(1840—1930)于1910年出版的译作《最高本质和最善的老子之书(道德经)》(Lao-tszes Buch vom höchsten Wesen und vom höchsten Gut.(Tao-te-king))的亮点。译者早年获神学和东方学博士学位,自1888年起任图林根新教神学院教授,他的学术背景深刻影响了他对《道德经》的理解,因此他认为老子和耶稣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相似关系,译者希望在《道德经》与《新约》中找到老子的哲学思想与耶稣的宗教思想之间的相似性,并且以此作为翻译的目的。为了印证自己的上述观点和研究成果,译者在附录中专门将《道德经》和《新约》的章节整理成表格以直观地展示两者的对比。
戈利尔认为,老子与耶稣的基本道德观惊人的一致。在老子和耶稣相似的性情下将《道德经》与《新约》放在一起汇编会展示一种特别的关联性,前者在哲学思想与后者在宗教思想中建立起一种奇妙的协调。⑫但是与“索隐派”极力在《道德经》中找到基督教启示的痕迹不同,戈利尔一开始就将老子和耶稣放在相等的研究地位上进行比较,在他的译本中“更为重要、更独特和更多的是与《新约》的平行对照……”⑬。戈列尔不只将《道德经》视作一部哲学作品,同时他还认为《道德经》是一部蕴含基督教教义的宗教作品。他认为,老子在《道德经》中将这种“最高本质”描述为一种深刻且生动的敬畏、爱与升华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在基督教中通过将最高准则人格化(“上帝”)而产生。由此,老子的哲学思想与耶稣的宗教思想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仅将“最高本质”理解为“善”的原型,还赋予了该概念一切人类美德的完美典范。⑭
戈利尔虽然将“道”理解为“最高本质”,但是在译文中却未用德语单词翻译“道”。在他的译本出版之前,学者们对“道”的翻译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以雷蒙沙为代表的部分译者将“道”译为“理性”(ratios)或“逻各斯”(Logos),戈利尔认为这种阐释不能体现“道”的比喻含义;第二,以儒莲为代表的译者将“道”简单译为“道路”(Weg),戈利尔认为这种翻译不能展示“道”的形而上含义,无法直观体现“道”是被赋予一切理性和美德的概念;第三,还有一些译本将“道”直接译为“上帝”(Gott),这也遭到译者的批判,因为《道德经》中的“道”是一个存粹的哲学概念而非宗教概念。⑮译者首先将再现原文作为翻译的基础,反对在翻译时刻意将《道德经》德语化,因此如“最高准则”这样的概念不应该打上译者个人烙印。同时为了适应原文迂腐地将德语变形,也会导致译文生涩难懂,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需灵活处理两种语言的差异。戈利尔期望在当时“困难且沮丧”的社会背景下唤起读者对《道德经》的关注,因此他将译文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希望通过自己的译本引导读者去探索《道德经》的思想奥秘和接近老子哲学思想中的精髓。⑯
(三)最经典的《道德经》德译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卫礼贤(1873—1930)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被誉为“中国与欧洲的思想中介者”⑰。1899年被普通福音新教传教协会(Allgemeinen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 Missionsverein)委派至青岛传教,但他对传教任务并不重视,反而对研究中国语言、历史、文化和社会兴致盎然,“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办医院、办学校和学习钻研中国文化上”。⑱他不仅通过翻译中国典籍将中国文化介绍和传播至德国,还专注于全面且深入的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开展研究。在当时德国政府驻青岛特派员单威廉(Wilhelm Schrameier)的鼓励下和劳乃宣等学者的帮助下,他开始翻译中国书籍,共计出版了包括《道德经》在内的9部中国典籍译著。他的中国典籍德译本和汉学专著成为影响欧洲乃至世界的经典作品。卫礼贤对中国典籍的释义和翻译并没有局限在传教士的身份中,而是试图从中国文化视角出发理解中国思想,因此他的译作成为东西方思想沟通的重要桥梁。1921年,卫礼贤作为德国外交顾问赴任北京,并在北京大学担任德国文学教授直至1924年返回德国。回德后,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并创建了德国第一所汉学研究所——中国研究所(China Institut),他将精力投入到中国文化的传播和研究所的建设中,并坚持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在晚年仍出版了大量翻译作品和论著。
1911年,卫礼贤出版了名为《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Laotse,Tao Te 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的《道德经》德译本,这部译本以严谨的考据、精准的翻译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德语译本之一,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此外,卫礼贤的译本也成为众多后继译者的重要参考版本,并在广度和深度上对《道德经》的读者影响深远,促进了《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传播。译者认为,“道”对老子而言仅是一个数学符号般的标志,正如“吾不知其名,强谓之道”,用以表示不能用言语明说的概念。与史陶斯认为中文中没有与“Gott”完全一致的词语相似,卫礼贤提出德语中也没有与“道”完全对应的单词。即使“道”的内涵范围非常广泛,但是译者出于审美仍坚持在译文中将“道”翻译成德语单词,并最终选择了“SINN”(意义)来表示“道”。为此,译者详细说明了德语单词“Sinn”在各个意义层面上都最接近“道”:“Sinn”原始含义是“道路”和“方向”,具体有以下几层内涵:(1)“人类内在的东西”;(2)“作为意识、感知、思想和思考的人类内在”“内在意义”;(3)“身体的情感生活(内在世界)”;(4)“文字、图画和情节的意见、概念、含义”⑲,上述释义中只有第三点与“道”相差较大,剩下的都非常一致。“德”则被译为“生命”(LEBEN)。译者指出,汉字“德”本意是“产生万物生命称为‘德'”(Was die Wesen erhalten,um zu entstehen,heißt de)⑳:首先,《道德经》 中的“道生之,德畜之”表示“德”即是养育万物之概念;其次,译者借鉴了《管子·心术》中的“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表示“德”产生了万物生命;最后,卫礼贤根据《约翰福音》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㉑指出德语单词“Leben”含有产生万物生命之意,因此他认为“德”译为“LEBEN”可较好传达汉字“德”的本意。
即使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卫礼贤在翻译《道德经》时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书中的奥秘和晦涩之处需要深思熟虑才能知晓,但《道德经》是中国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翻译《道德经》却又是汉学家不得不完成的挑战。卫礼贤认为,与其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作品进行现代化还原,不如通过翻译让老子自己发出声音。所以将欧洲现存的《道德经》相关书籍进行简单的汇编,还不如重新翻译原著。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每天都能在《道德经》中找到新发现,而某些之前的观点就会过时,加之人无完人,没有译者能保证不犯错误,所以重译《道德经》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卫礼贤出版过两个《道德经》版本,第一个版本于1911年以《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Laotse,Tao Te 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为名在耶拿出版,该译本一经出版就受到广泛的流传,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成为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广的译本㉒,在1911至1944年期间再版5次㉓。但是卫礼贤在此版本已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下,仍坚持研究原文,对此译本反复修改,甚至对一些章句重译,在1957年他将多年的研究和修改成果整理后出版了第二个《道德经》译本,第二版沿用了《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Laotse,Tao Te 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的书名。
(四)早期学院派德译者鲁雅文(Erwin Rousselle)
曾在华任教的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鲁雅文教授(1890—1949)也是该阶段值得重点关注的汉学家和译者。鲁雅文自1916年起在海德堡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开始修法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在1924年到1929年作为卫礼贤的后继者在北京大学任德国哲学教授,并在清华大学任比较语言学客座教授,同时还兼任燕京大学“中国—印度研究所”所长。卫礼贤去世后,他接任了由卫礼贤创办的法兰克福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的职务。在这两位汉学家的努力下,该研究所成为当时德国一流的汉学研究中心且成为欧洲汉学的重要研究基地之一。
鲁雅文在1942年出版的译本《老子,永恒的引导和力量。(道德经)》(Lau-dse,Führung und Kraft aus der Ewigkeit.(Dau-Dö-Ging))中从对东西方古代智者思想的对比出发,希望通过翻译《道德经》阐释老子对人类哲学思想传承上作出的伟大贡献。译者认为,东西方的人类思想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开始同时觉醒,智者们开始探索和认识到与整个世界根基紧密联系的思想根源。东方的两大文明古国的智者,在中国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在印度以耆那教创始人玛哈维拉(Mahavira)和佛教始创者释迦摩尼为代表;在西方世界,则是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赫西俄德(Hesiod)为智者代表。㉔由此可见,译者给予老子极大肯定。他还提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古代中国都产生深远影响,但孔子侧重于对社会的建构,而老子则注重对世界的思考。因此,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政权已然倒塌,但老子的智慧却因其没有时代限制而经久不衰。㉕
与之前的译者相比,鲁雅文对《道德经》的理解独树一帜。他提出老子的哲学思想来自母系社会文化。因此,“道”是“伟大的母神”(Große-Göttin-Mutter),而不是“父神”(Gottvater)或哲学上的抽象概念。译者认为,理解《道德经》的关键在于对“道”字的结构分析,“走之旁”和“首”的结合表示头脑决定该如何前进和走向何方,所以汉字“道”兼含名词“道路”和动词“指导方向”之意。而《道德经》中“道可以为万物始”,因此“道”不应该译为名词“道路”(Weg),而是表示动词的名词化形式。因此,他将“道”译为“宇宙的(女)主宰”(die Führerin des Alls),一方面用阴性名词“Führerin”(女领导、女主宰)体现老子思想来源于母系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将表“指导方向”的动词“führen”名词化体现译者对“道”的理解。
他强调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具有德语单词没有的形象性和画面感,这是在翻译时尤其需要注意的重点和难点,他的译本突显了汉字的象形性。因此他反对用表示抽象概念的德语单词来解释形象的汉字概念,如在对“敦兮其若朴”的“朴”字翻译时,他放弃了抽象名词“Einfachkeit”(简单、朴素)而选择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Rohhloz”(原木),因为“朴”字的木字旁向读者形象地传递了“朴素”的画面感;再如汉字“骄”由马字旁构成,所以他不使用“hochmütig”(骄傲的),而用具有“抬高脚步”含义的“hochtrabend”(浮夸的)与“马”旁相对应,因此在翻译时将这种汉字的象形特征再现给德国读者是必要的。㉖
四、结语
通过对1945年以前《道德经》在德国的译介综述和分析,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重要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首先,德语国家学术界对《道德经》的接受和译介受到时代背景的巨大影响。因此,在世纪之交时期的社会危机下,出现了第一次“道”的热潮,具体体现为:其一,译本数量增多。仅在20世纪初《老子》的德译本就有8种之多㉗,其中包括对《道德经》海外译介颇具影响力的卫礼贤译本;其二,影响了德语文学界。在这一时期德布林通过先锋派的写作手法创作了他的道家思想小说《王伦三跳》,黑塞和布莱希特阅读了《道德经》并影响了他们之后的创作;其三,对德语哲学界同样产生影响,如马克斯·韦伯完成了关于儒家和道家的作品《儒教与道教》,该著作将道家思想变成了流行的哲学。而此后,随着希特勒上台,同样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下第一次“道”的热潮逐渐降温。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德国的《道德经》译介几乎停滞,鲜有译本可以在此期间出版。
其次,在西方宗教文化影响下,该阶段的译本往往具有宗教因素。无论是神学家史陶斯、于连·戈利尔,还是入华传教士卫礼贤都在译本中掺杂神学因素,他们或通过研究《道德经》以说明道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同宗同源,或引用《圣经》以阐释《道德经》的哲理,或将《圣经》与《道德经》作平行比较,就连并未具有神学背景的汉学家鲁雅文也将《道德经》视为一部具有母系社会文化思想的神秘主义之书。由此可见,德语学者们在此阶段对《道德经》的译介和接受往往从宗教角度出发,而并未将《道德经》单纯地视为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综上所述,1945年前的《道德经》译介对这部典籍在德语世界的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该阶段不仅包含了对《道德经》的第一次接受热潮,也为二战后至今的道家典籍和道家思想的译介与研究奠定了基础,该阶段的经典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最重要的《道德经》德语译本,从而使得老子学说对德国的文学、哲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 Oliver Grasmück: Geschichte und Aktualität der Daoismusrezeptio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Münster:LIT Verlag,2004:60.
② 柯兰霓著,李岩译,张西平、雷立柏审校:《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③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田农、吴琼等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④ Reinhold von Plaenckner:LAO-TSE TÁO-TE-KING,DER WEG ZUR TUGEND,Leipzig:F.A.Brockhaus,1870:xv.
⑤ 马汉茂、汉雅娜、张西平、李雪涛:《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河南: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
⑥ 王维江:《20世纪德国的汉学研究》,Historical Review,2004年第5期,第7-13页。
⑦ Oliver Grasmück:Geschichte und Aktualität der Daoismusrezeptio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Münster:LIT Verlag,2004:61.
⑧ Victor von Strauss:LAO-TSE'S TAO TE KING,Leipzig :Verlag von Fridrich,1870:XIII.
⑨ 胡其鼎:《由一角藏书看德国汉学研究》,《读书》,1983年第5期,第123页。
⑩ 同⑧,第ⅩⅩⅩⅣ-ⅩⅩⅩⅤ页。
⑪ 同⑧,第ⅩⅩⅩⅤ页。
⑫ Julius Grill:Lao-tszes Buch vom höchsten Wesen und vom höchsten Gut.(Tao-te-king),Tübingen:Verlag von J.C.B.Mohr(Paul Siebeck),1910:Ⅵ.
⑬ 同⑫,第 203 页。
⑭ 同⑫,第Ⅵ-VII 页。
⑮ 同⑫,第 11-12 页。
⑯ 同⑫,第Ⅵ页。
⑰ Hartmut Walravens:Richard Wilhelm(1873—1930):Missionar in China und Vermittler chinesischen Geistesguts,Nettetal:Steyler Verlagsbuchhandlung,2008:7.
⑱ 杨武能:《三叶集——德语文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404页。
⑲ Richard Wilhelm:Laotse.Tao Te 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Hamburg:Nikol Verlag,2013:20.
⑳同⑲。
㉑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新约》,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3年第104页。
㉒ Oliver Grasmück:Geschichte und Aktualitätt der Daoismusrezeptio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Münster:LIT Verlag,2004:43.
㉓ 同㉒,第 59 页。
㉔ Erwin Rousselle: Lao-tse.Führung und Kraft aus der Ewigkeit,Baden-Baden:Insel Taschenbuch,1985:95.
㉕ 同㉔,第 97 页。
㉖ 同㉔,第 101 页。
㉗ 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