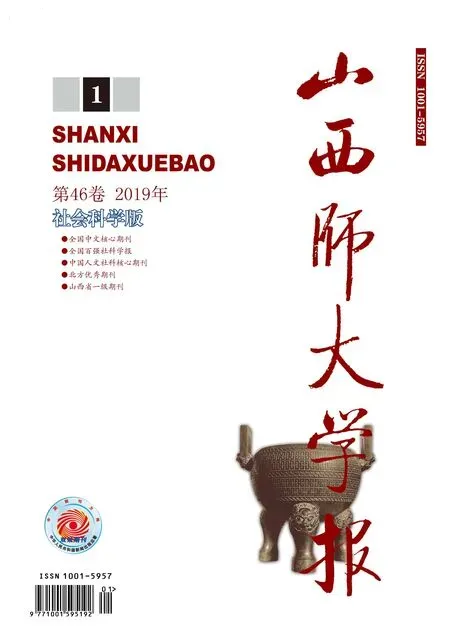图像转型时代女性身体的哲学困境与艺术化生存
2019-02-22赵卫东
赵 卫 东
(南阳理工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4)
当今时代,随着图像技术的日臻完美以及网络、视频、手机、微信等新媒介的渐趋普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图像化的转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女性身体展示自我的平台渐趋增多,女性身体视像成了消费文化的主题之一和视觉事件,身体景观和身体事件频频出现,不断刺激和诱惑着消费大众的感官视线,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和消费的风尚:灵巧的面庞,丰满的胸部,性感的大腿,妖冶的身姿,细腻莹白的皮肤,幸福迷人的微笑……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在印证着消费时代的身体神话,不断地生产和满足着消费者的身体梦幻和欲望的乌托邦。
然而,当代中国妇女真的获得自由和幸福了吗?在技术主义、符号主义盛行的沉沦时代,真正的妇女身体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她还能否在历史的舞台上重新出场?她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由此,作为实体而存在的女性身体,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在纷乱喧嚣的“世界图像”中使身体自我走向澄明和有意义?这是女性身体面对身体景观需要解决的哲学难题。其次,必须回答:怎样才能使女性身体回归自我,以“身体性”的方式生活和存在。这是女性身体在交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女性身体的哲学维度与现实沉沦
什么是女性的身体存在?妇女身体如何“身体性”地存在?这将涉及到一个关键性问题,即身体存在与作为存在者的此在的关系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这一关系作了准确细致的阐释:“彻底解答存在问题就等于说: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这个问题的发问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DASEIN)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突出而透彻的提法要求我们事先就某种存在者[此在]的存在来对这种存在者加以适当解说。”[1]62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就是实有,存在的意义不仅表现为作为独立存在者的此在与他物的差异性以及与其自身的同一性,而且也存在于与其他世界的关联之中,并在时间和空间中通达无限。在此意义上,此在在存在者和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存在必然是此在的存在而且体现为此在的存在样式。在艺术本源的发生中,在女性身体的持存和绽出中,以本真方式存在的此在模式只有嵌入其中,即作为存在者的此在只有在场,“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悟宣告出来。”[1]219“‘真理’乃是存在者的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状态才成其本质。一切人类行为和姿态都在它的敞开域中展开。因此,人乃以绽出之生存的方式存在。”[1]219女性身体只有以绽出之生存方式存在的时候,女性身体的真理才以祛蔽的方式自我彰显并走向澄明,女性身体的自由本性才切实地向着“在其中”的女性身体敞开并通达身体存在。
存在论意义上的女性身体界定与探讨实际上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研究范式,要想使女性身体通达存在并获取自由,就必须使身体自由即本真存在奠定在此在的基础之上,让女性身体成为一种统辖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心灵与肉体、情感与欲望等多重要素的身体存在,让身体自身在自身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寻找意义,自己为自己寻求自由,让身体以自由的方式陈述、言说、表达并探求快乐。而在传统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美学观念中,妇女身体却是一个脱离肉身的精神概念,是一个失去了主体性、可被观赏的客体对象,一个失去了个性特质的、以满足主体欲望需求为特征的语言符号。无论是传统时代的精神概念,还是读图时代的肉身符号,都背离了身体存在而误入了歧途,女性的身体存在被最终遗忘。海德格尔指出:“为存在者提供根据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特性乃在于, 形而上学从在场者出发去表象在其在场状态中的在场者, 并因此从其根据而来把它展示为有根据的在场者。”[2]69“存在是不可能从概念上去把握的, 作为概念的存在只是一个存在者,存在自身被概念所遮蔽。”[3]
从存在论哲学层面究其原因,乃是形而上学遮蔽了存在, 从而导致了存在的被遗忘。形而上学对于存在的遮蔽导致了身体的沉沦,原因在于语言的存在维度已经丧失。身体的隐匿与语言存在有着很大的关系,身体并不否定语言,身体的感受和表达需要语言来表达,身体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通达存在。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住在语言之寓所中。”[4]566语言绝非人类交际的工具,而是向着存在敞开的,“语言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相反,唯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惟有语言处, 才有世界。”[5]40语言中之语词本身不是一物,也不是任何存在者,语词之所以能赋予万物以存在,在于它能把一切物保存于存在之中,在于它把某物带入世界并让它作为世界性的存在者显现出来。既然语言经验存在,身体存在向着语言无限敞开,那么有关身体的道说就不单纯地意指身体概念本身,而是把身体带入世界并让它作为世界性的存在者显现出来。于是,身体之维通过存在的敞开无限呈现出来,身体的关联性、世界性在语言的引领和昭示中成就其本来的面貌。既然身体是携带着道说之本质向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么,唯有将作为道说的语言带向有声表达的词语, 才能将身体的存在之维彰显出来, 也才能使我们真正通达存在之路。
而在一个身体存在被遮蔽的彻底符号化了的技术时代,女性身体的存在问题首先在媒介领域浮出历史地表,身体已被悬置在括号之内而不能出场。身体语言受技术之规定, 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符号化,语言符号通过编码而被纳入学术体系和机器系统之中而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无论是女性身体的“肉身化” “图像化”,还是女性身体的“事件化” “情景化”,事实上都已经沦为不能说、不能思、游离于身体之外的“他者”。身体符号的“他者”身份进一步疏离了身体的存在,把思维活动领域限定在无意识范畴,以能指的形式完成了女性身体的性别区分,炮制出主体/客体、看/被看等男性消费模式;并使之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植根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消费社会身体符码的生产和消费未有脱离形而上学的误区,女性身体存在的规定性再一次被遮蔽了,一方面, 妇女身体存在自身被遮蔽,妇女身体并未有出场;另一方面, 妇女身体表征为以“性”征出场的存在者,在场的存在者同样遮蔽了缺席的身体存在。女性身体符号已经脱离身体存在,沦为了男性的欲望客体和消费对象,女性身体存在的被遮蔽、身体被降解为肉身已成为一种宿命。
如果我们把肉身符号的技术编排仍然视为身体言说的话,那么,这种话语言说已经丧失了身体经验的可能性,它本身是存在问题的。首先,这种身体言说背离了语言的本质,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对于道的接近。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之本质现身乃是作为道示的道说。”[6]251在存在主义哲学来看,道乃是世界的本体,道说是存在在说话,并在诗中得以呈现。以身体符码形式呈现的话语言说意在传达某种文化并服务于某种社会需要,它本身是不自由的也不以追求自由为目标,因而不具有关联性和世界性的特征,不可能向着存在敞开,也不可能接近于道本身。其次,这种身体言说并非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言说,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语言的言说,是一种舍弃了存在的非本真言说,非本性的语言不仅不能敞开存在, 反而遮蔽了存在, 甚至成了存在的牢笼。身体的编码在把女性身体拖向了技术主义一途的过程中,也就消除了语言经验存在的可能性。最后,身体语言作为经验存在,唯在身体语词与外物的关联中,唯在身体语言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的可能性的条件下,才会向着存在的意义无限敞开,身体符码作为抽空了感性经验的概念符号,切断了身体符号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性,从而遮蔽了妇女身体向着无限的存在意义敞开的可能性,成为一种抽去了存在意义的空洞能指。
二、图像转型背景下女性身体的哲学困境
在传统的认识论研究模式中,由于女性身体被置于主体/客体、男性/女性、灵魂/肉身、理性/感性等二元对立的主从结构中,特别是女性身体被纳入语言秩序之中,以超验能指的形式接受逻各斯权力的重新编排和性别区分。由于这一秩序建构并规范了权力—知识模式,所谓身体意识、女性气质、身体话语、身体叙事等知识概念,由权力—知识模式生产出来,内化为特定文化阶层所需要的文化观念,它们作为权力模式炮制出来的知识要素和虚假需求,既不携带女性身体的存在经验,也不通达女性身体的存在之路。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当今时代女性身体图像化、情景化,同样难以接近作为存在经验的女性身体,因为身体图像、身体景观并非作为存在者而存在,而是作为服务于使用目的的技术符号发挥作用,图像景观不仅脱离了女性身体的生存处境,而且难以由此返回女性身体的存在经验。
图像转型时代由于身体话语存在维度的丧失,女性身体回归自我已不可能。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即使力图克服存在的遗忘, 并把存在重新规定为思想的根据, 这仍然是充满着问题的:一方面, 存在不可避免还要被遮蔽;另一方面, 寻求根据的做法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3]“世界此时已经不再是人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而是一个被算计的技术形式。当代视觉文化突出可看世界的技术性和工具性,而把承担传统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基础放弃了,结果使审美活动从一种教化人心的活动变成了一种满足人类意欲的操作手段。”[7]199在世界图像中,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已经演化为对存在者的命题性表象的思索,非对象的本真之思已演化为以对象化的方式对于存在对象的阐释,在看/被看的模式的引领下,“思维的自我在被表象状态的自我确证着的‘共处’之中,亦即在意识中,获得了其本质。如此这般,表象之思不再意味着向公开场合敞开,而意味着抓牢、确立、特质。”[8]93表象之思为意识所遮蔽,它传达的只能是一种观念意识,不可能通达自由之路。女性身体在被图像化、在被编码的过程中,它的肉身化、符号化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在存在中所是的东西,不可能是让身体作为存在者存在的东西,而仅仅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9]90。在这里,身体表象之构图先行设定了被看的东西,即已经以观念的形式传达了“性”消费的文化意蕴,存在身体既没有作为存在者而存在着,也没有通达存在,它既没有获得存在对于存在者的主动允诺,也没有以身体的方式存在着,因而它毫无自由可言。在逻各斯一统天下的语言之网中,女性身体失去了灵性,依靠语词的物性和知识结构来界定和表征自身,由此宣告了身体存在的终结和身体意义的丧失。妇女身体不仅失去了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性,也失去了感受世界、体验存在的能力,沦为消费社会的肉身符号和欲望工具。
图像转型时代,在现代技术的规定下,身体的编码与生产一开始便服从于某种功利化的要求,按照技术标准炮制出来的女性身体,时尚、性感、妩媚、妖艳,身体曲线分明,它们以超自然的特征生产、复制着景观化的身体奇观,制造着看/被看的男权消费模式,以达到满足商业消费的实用目的。超自然世界中的女性身体也非本真的女性身体,而是复制的、仿真的女性身体,它以其技术性、无根性、批量性和复制性制造着身体符号的“内爆”(鲍德里亚语),由此引导和推动着消费时代源源不断的欲望消费。为此,女性身体要想找回通往存在的道路,就必须克服由技术主义命题和逻辑判断所构成的形而上学限定,在诗化的语言或诗歌中返回到遗落的存在,因为唯有将语言从欲望消费的虚假需求中挣脱出来,重新面向身体的经验者和言说者本身,才能在“思”和“诗”的对话中聆听到道的脚步声并通达身体的存在自由。
从存在论的意义来讲,妇女身体的实存不是孤零零的东西,海德格尔对于梵高的作品《鞋》的分析表明,物的实存不仅仅占有空间,而且拥有历史,诗人、画家的艺术世界就是它的家园,作为实存的农妇鞋子只有置身于广袤无垠的大地和绵延无期的历史长河之中,才能真正显示出它的艺术价值和存在意义。同样道理,女性身体只有栖身于世界的大地上,跨越理性和逻辑的狭窄巷道,穿越于广袤的“存在荒野”和幽深的“现象丛林”,在无限的时空中感受、体验和把握幽冥中萌动的存在,存在的意义才能向着女性身体无限敞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性身体的自由本性与诗性特质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让语言重返身体的存在经验并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女性身体的自由本质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彰显,而这一本真呈现也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领悟。
三、女性身体的诗性特质与艺术化生存
从根本上说,诗性的尺度乃是语言对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逆反,自由的存在和诗性的尺度是同一的。海德格尔认为,“做诗乃是原初性的筑造。做诗首先让人之栖居进入其本质之中。做诗乃是原始的让栖居。”“当我们说‘在大地上’时,我们所命名的东西只是就人栖居于大地并且在栖居中让大地成为大地而言才存在。”[1]219海德格尔之所以推崇荷尔德林的诗歌,乃在于他看到了诗人语言的“语言性”也即诗性。诗的本质在于让语言自行彰显,这一彰显过程正是诗人创作自由的体现。唯有使语言自行呈现、自我创造,女性身体的诗性特征和自由特质才能本真地体现出来。因此,身体语言的诗性特征,最能体现语言的存在维度,并将语言的持存展示为人的一种特性和存在状态,以在身体的有限存在中呈现出无限来。
为此,必须将女性身体置入存在论领域,在诗和思的关联中寻求身体的自由和幸福。首先,必须对女性身体进行存在性的思考。我们在道说身体的时候,并不单纯意指身体本身,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切断与外界联系的孤零零的女性身体,而是把某物带入世界并让它作为世界性的存在者显现出来。形而上学的主客体思维方式粗暴地切分了人与物的相互关联,把女性身体以及与其关联的世界万物都孤立起来,最终摧毁了身体的存在维度。放弃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将女性身体的感受和理解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才能真正通向存在之路并为妇女身体祛蔽。其次,妇女身体的祛蔽需要通过诗化的手法来完成,而神秘的诗性尺度能够使身体话语以诗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诗歌的本性来看,诗歌的本质不在于描绘,而在于创造,诗人并不用现成的日常用语作诗,而是让语言自行道说。诗歌能为我们带来宇宙世界中前所未有的东西,正如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的诗歌时所言,“诗人之为诗人,并不是去描写天空和大地的单纯显现。诗人在天空景象中召唤那种东西,后者在自行揭露中恰恰让自行遮蔽着的东西显现出来。在种种熟悉的现象中,诗人召唤那种疏异的东西——不可见者保持其不可知而归于这种疏异的东西。”[10]110
女性身体的诗性特质,可以借助于诗化语言从女性身体的生理心理、气质个性等多个方面来加以叙述和表达,女性的生命经验和心理情感等性别资源,也可以借助于叙述模式、空间布局、美学形式等重新分配,进而完成身体话语在文本结构和话语陈述中的艺术实践,而女性身体的真理也正是在这样的艺术追求、结构生成、诗意表达中,不断地使自己向着世界进一步绽出。从视觉经验范式的转换来看,女性身体图像适应了消费社会的观看方式,因而内含有美学解放的现代性质,并通过美学化的途径获得了合法的位置。但是,问题在于,身体欲望的扩张是来自妇女身体还是某种外在需求?是否任何作为观念和意义层面的视觉图式都能促进感性意义的身体解放?在技术主义和大众传媒的控制下,由看/被看模式所主导的视觉消费模式能否步出身体消费的文化困境?怎样保证性态话语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能与女性的身体存在保持同一性,不再发生异化现象?也许,身处外部环境的层级压制中放逐了的女性身体,应该追问的是:我的身体应该表征为什么样的身份?我身处何时何地又走向哪里?怎样使我的身体和生存状态变得有意义?
在此,我们不妨从身体文化学的视域中抽出身来,将身体的哲学高度从存在论转向生存论的新的起点,并从新的学科领域寻求和探索女性身体获取自由的新的路径。法国社会学家福柯从身体的行为伦理学方面探讨了如何通过改变自我来构建一个诗化的、风格化的行为主体,即以诗性的标准改造自我并使个性化的身体回归到诗意的存在状态。在其论著《性经验史》中,福柯推崇古希腊人的伦理行为方式,因为他在古希腊人的生存美学和自我技术中看到了其行为伦理方式的合理性,特别是“性”行为的享受和快乐。在古希腊人那里,“性”行为不受外在法律和规则的约束,完全可以通过自我技术进行内省和调节,内省和调节的方式就是通过养生的方法规定身体快感的享用,通过节欲的方式完善自我修行,古希腊人由此构建了以自我为伦理主体的道德行为模式,它既是生活的,也是艺术的,既是伦理的,也是审美的,既是个体的、生存化的,也是自由的、理想化的。福柯认为,主体的这种伦理行为就是自我艺术化、审美化的过程,即“通过改变自身, 将自己的生活塑造成具有美学价值和风格化的艺术品”[11]。 在这里,伦理主体通过道德的反思完成了生活的艺术化和自由的风格化,道德通向了诗性的道路, 成为一种个性化的自由化的生存艺术和规定评判身体伦理行为的美学标准。此外,美国学者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也为妇女身体步出迷津、走向自由昭示出某种路径。与身体现象学家梅洛—庞蒂主张回归“非反思的”“无意识的”“直接的”身体不同,舒斯特曼主张一种“反思的”“实践的”“改良的”身体。“身体美学”主张身体应该走出理论的象牙塔,投身于实际的应用实践活动中,以身体作为为审美活动的基点,追求身与心、外在与内在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共进。尽管身体美学主张通过节食、瑜伽、体操、亚历山大技法等肢体活动来恢复身体意识的做法尚有争议,但是,它批判当代社会身体的缺失现象以及对于身体的形而上学理解,肯定身体的感性存在和内在灵性,力求通过身心合一和实践性的活动来实现“身体性的存在”,这对于清除遮蔽身体存在的障碍、回归身体的存在维度、抵制有关女性身体的欲望化、客体化的消费倾向,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为进一步走出身体美学的现代困境,当代中国学者彭富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一, 化欲为情;其二, 由技到艺;其三, 肉身成道。[12]所谓“化欲为情”,就是以心理情感来缓解生理欲望的扩张,重新谋求感性与理性的和谐关系;“由技到艺”就是批判技术的实用与美学的无用,以艺术化的活动来代替技术性的、实用性的训练,从艺术化、审美化的层面来推进身体的自由和解放,而不仅仅是达到某种实用性的目的;“肉身成道”就是将肉体返回到生命的轨道上来,在灵与肉统一的基础上上升到生命的高度,在生命的本真和自由中实现肉身的涅槃。
也许,将女性身体置于生存论的视域,从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探寻女性身体艺术化生存方式的做法不是女性身体走向自由和解放的最佳路径,但是,海德格尔的生存美学思想、舒斯特曼的“身心合一”的美学思想、福柯的艺术化生存美学思想对于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它们在向我们表明,在这样一个身体沉沦的图像转型时代,必须面对女性身体的现实生存状况,在坚持身心合一的前提下将女性身体提升到哲学生存论的高度,通过审美之维的重构和诗性身体的重塑,克服技术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控制,推动当代中国女性走向自由和艺术化生存。